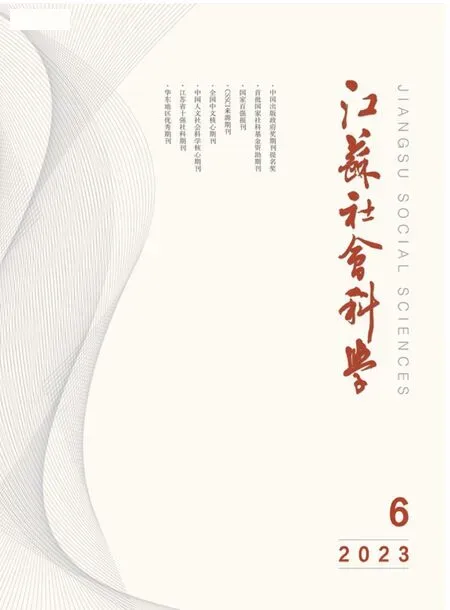辩证逻辑与“语言学之后”的建构
邓晓芒
内容提要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和形式逻辑并列的另类逻辑,而是以形式逻辑为其初阶的大写的“逻辑”,它将语言的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统一为一种“自否定”的创造主体,不仅是用来建构“语言学之后”的逻辑方法,而且是这一形而上学体系本身的灵魂。但黑格尔并未充分意识到辩证逻辑与“语言学之后”的关系,而是仅仅从逻辑形式上容纳了内容中的某些非逻辑效果,却把其中的诗性精神和隐喻结构全部置于“意谓”(Meinung)之中不加言说,最终使辩证逻辑窄化为传统本体论(存在论)的一种表达形式或工具。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劳动学说引出语言起源上的辩证本性,又以现象学的眼光将这种语言本性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层次,最后在这一层次上揭示出语言本质上的诗性或隐喻结构,这有助于呈现辩证逻辑的全部内涵,探究语言的自否定结构作为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通过对中西不同形而上学原理的嫁接来建构这一形而上学的设想。
我在《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1]邓晓芒:《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上)》,《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邓晓芒:《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下)》,《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在中西形而上学都走向了自己的没落的当代,唯一有可能超越以往形而上学而重建新型形而上学的,就是与“物理学之后”和“伦理学之后”都不同的“语言学之后”。而这一设想的关键就在于对黑格尔所创立的辩证法或辩证逻辑进行一番重释和改造,使之不仅成为一种用来建构“语言学之后”的方法,而且本身成为这一形而上学体系的灵魂。在这方面,黑格尔在完成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时所创造的诸多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他也由于自己的致命缺陷,而未能突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陈旧桎梏,最终封住了通往“语言学之后”的道路。这个致命缺陷就在于,他未能立足于语言本位深入挖掘语言本身在逻辑功能底下所原本具有的诗性功能,而使语言的本质局限于陈述真理的工具,不再具有独立而超越的研究价值。但他毕竟也凭借辩证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的超越,暗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一、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反思和突破
其实,以辩证逻辑把语言的诗性功能和逻辑功能统一起来,是黑格尔建立他自己的不同于传统形式逻辑的“逻辑学”的初衷。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把这种逻辑学直接称作“辩证逻辑”,在他看来,他的逻辑就是全称的或大写的“逻辑”;但在通常人们对逻辑的形式化的理解中,总是不能不将他的逻辑冠以“辩证”的限定语,以区别于普通的形式逻辑[1]“辩证逻辑”是否能够被正当地称作“逻辑”,历来也是有争议的。如黑格尔研究专家卢本(P.Ruben)主张:“首先要把‘逻辑学’和‘辩证法’这两个术语区别开来使用——特别是为了弄清楚《逻辑学》的内容起见。……辩证法不是特种的逻辑学,也不是‘更高的’逻辑学,反过来说,逻辑也不是辩证法,也不是辩证法的表达手段。”(Seminar,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Rolf-Peter Horstmann,Frankfurt am Mein:Suhrkamp, 1978,S.81.)可以看出,这些说法都是“非黑格尔”的。。这种将逻辑划分为两种逻辑的做法并非始于康德的“真理的逻辑”和“幻相的逻辑”,而是始于17 世纪第一个正式提出“诠释学”概念的丹恩豪尔(J.K.Dannhauer)。据伽达默尔说,丹恩豪尔“试图通过他的诠释学达到一种可与逻辑学相匹敌的、在一般理解文本时的人性和逻辑的正确性。正是这种趋于一种新逻辑学的倾向导致他拿分析逻辑来对比,最后明确地摒弃分析逻辑”[2]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6页,第353页,第427页。。与所谓“分析逻辑”相对,这种“新逻辑学”是一种“综合逻辑”。“丹恩豪尔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中实际上发现了一种综合过程(话语由其部分组合而成)。他把作为分析的诠释学挪到这种综合的陈述逻辑之旁,亚里士多德分析论的这种扩展具有重要的后果。正如形式推论理论只保证内在合乎逻辑性而不确保它的实际正确性,诠释学在丹恩豪尔那里也只表明某个陈述的正确意义,但并不指明一个正确陈述的意义”,在此,丹恩豪尔“是在把诠释学归并到逻辑学”[3]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6页,第353页,第427页。。但与丹恩豪尔这种外在的逻辑划分不同,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作了一种内在的处理,即形式逻辑只不过是整个辩证逻辑体系内部属于“主观逻辑”阶段的一个环节,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更准确地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在为形式逻辑奠基,只不过形式逻辑并未自觉到这一点而已,因而辩证逻辑无非是形式逻辑的自我意识阶段[4]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为形式逻辑的奠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收入邓晓芒:《西方哲学探赜》(修订版),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234页。。所以,黑格尔把自己的辩证逻辑直接称为“逻辑学”,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因此,由黑格尔所创立的辩证逻辑就具有形式逻辑的逻辑功能,但这种逻辑功能与完全分析性的逻辑功能又有所不同。由于隶属于辩证逻辑,黑格尔的逻辑又带有综合性的功能,而这种综合性的功能本身并不基于逻辑功能,而是基于逻辑底下的“意谓”(Meinung)。这种意谓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含义模糊的“双关语”。伽达默尔说:“双关语的多义性代表着思辨最具诗意的显现形式,它蕴含在互相矛盾的判断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说,辩证法就是思辨的表现。”[5]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6页,第353页,第427页。与“双关语”类似,黑格尔的用词是“内在伸缩性”(immanent plastisch),一个富于内在伸缩性的陈述往往不被人们注意到,而是“本能地和无意识地贯穿于我们的精神之中”,例如在德语中,有些词本身就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但“一个有伸缩性的陈述,也需要在接受上和理解上,有富于伸缩性的感受力”[6]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19页。。据此我曾提出,黑格尔辩证法与主体的内心体验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因为“辩证逻辑术语所遵从的规则或法则不可能是由外部提供的,而是从它自己内部产生出来并被体验到的,撇开这种体验内容而寻求外在的系统结构或规则是不可能的。在黑格尔那里,表面看起来像是‘体系’、‘规则’或‘框架’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体验和‘悟入’的轨迹或步骤”[1]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0页,第485页,第485—486页,第487页,第489页。。虽然黑格尔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把一切概念都建立在诗性直观之上的做法有尖锐的批判,但他自己实际上也把直观看作自己的逻辑学的最高形态。这也是他的每个三段式的第三阶段的特点:“这是一种概念本身的直接性,即具体概念,它包含有丰富的规定性于自身,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复合体’,而是一个单纯之物,是个别的东西和能动的东西;它就是对自身的一种总体的把握、综合的自由的力量;就其为一种直接性而言,它当然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就其为两个环节的‘真理’而言,它就是全过程的内在的动力、真正的灵魂。”[2]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0页,第485页,第485—486页,第487页,第489页。“这种直观本身是一种体验,但不是感性的(情绪的、情感的、表象的)体验,而是概念的自我综合的体验,不是静观的体验,而是能动的生命体验,不是艺术家灵感式的体验,而是以普遍的逻辑形式为根据的体验”,即一种“思维着的直观”[3]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0页,第485页,第485—486页,第487页,第489页。。
但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一旦把感性的体验归结为思辨的、概念运动的内心体验,辩证逻辑作为语言两大功能即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诗性功能)的统一就成了似是而非的了。由此就暴露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前述致命缺陷,这就是我所断言的:“对感性直观体验(情感、感觉、情绪、欲望等)的舍弃,对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和现实的感性活动的舍弃。黑格尔用理性的逻各斯或逻辑形式来规范其生命体验的内容,但最终把这种内容颠倒为逻辑形式的一种自我表达。……理性可以撇开感性而有自己的内容,那么这内容必定也只能是抽象的纯理性的内容;尽管在这抽象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又可以建立起特种的‘具体的东西’,但归根结底这种‘具体’仍然是抽象的,是离开了特殊的普遍。”[4]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0页,第485页,第485—486页,第487页,第489页。然而,尽管如此,体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确具有隐秘而又极其重要的作用,哪怕他实际上并未将“体验”(Erlebnis)一词当作自己特殊的术语,但它使得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再是像形式逻辑那样的外在的间接性的认识工具,而是对于对象的直接体验,因而是真理本身,是一个自身中介了的生命运动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虽然不是感性的具体,不能用手去触摸,但它内在地包含着存在与本质的全部丰富内容,从而暗示出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5]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0页,第485页,第485—486页,第487页,第489页。。在这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无比宏大的隐喻亦不为过。
然而,这种感悟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从黑格尔那些才气横溢的字里行间所体会到的,而不是黑格尔自己有意促成的。就黑格尔的本意来说,他从《精神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出发,一直走到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和“绝对认知”,就再也没有回到起点,而是在《逻辑学》中一劳永逸地把原生态的感性抛弃了(虽然也时常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再次提起)。受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和束缚,他的眼界超不出“物理学之后”的“科学”的范畴;而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对语言本身的结构方式和形成机制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只是把语言当成表达和论证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必要手段、一种虽然有价值但绝对不值得停留的证据。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即使在谈论感性确定性在语词上必定走上共相之路时,一旦触及语言的“意谓”层次,也便立刻止步不前,将其排斥于语言范围之外,只剩下语词的概念和逻辑在唱主角,并按照这些概念的内在必然性而越走越远,直到超出日常语言而抵达绝对认知的“圣言”。这样,即使是丰富多彩的感性内容,在概念的无所不至的操控下也变得苍白了。这也是当年费尔巴哈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发难的原因。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就是对他背叛感性的批判,在他看来,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只是口头上的,因而在他那里,“语言是比较真实的东西”,即从一开始黑格尔就把重点从真正的感性确定性转移到口头语言上去了,凡是不可言说的都被直接忽略掉了。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把语言从这种工具地位提升上来,将意谓也归于语言本身,反而干脆认为,“语言在这里根本无关紧要”,感性意识并不由于不可言说而被驳倒,反而驳倒了语言。费尔巴哈说:“我们在《逻辑学》的开端中所遇见的那个直接的矛盾和分歧,现在在《现象学》的开端里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作为现象学的对象的存在与作为感性意识的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分歧。”[1]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王太庆、刘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9页。费尔巴哈这里对语言的理解是极其表面的和抽象的,也就是在日常所谓“口头承诺”“口惠而实不至”意义上的语言。所以,他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首先必须解决它与感性实在的矛盾:“真理并不在于与它的对立面的统一,而在于驳倒这个对立面。辩证法并不是思辨的独白,而是思辨与经验的对话。”[2]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王太庆、刘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6页,第70页。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到感性意识背后的感性直观,在他那里,“感性意识之为对象,只是作为自我意识、思想的对象”,因此“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而是从关于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3]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王太庆、刘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6页,第70页。。
但问题在于,费尔巴哈的感性仅限于自然主义观点下的五官感觉、情感情绪、意愿和欲望,而不包括主体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第54页。,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第54页。,从而不屑一顾。但在马克思看来,能够将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正是实践活动,这就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第78页,第80页。原来,真正全面丰富的感性既不是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的直观,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而是主体有意识的感性活动,即作为劳动的实践活动;只有在这种场合下,动物的感觉才成了人的感觉,“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第78页,第80页。。但对于感觉在实践中如何变成“理论家”,马克思语焉不详,因为他此时的任务不是重建形而上学,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也就是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因此,对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这一传统哲学的对立,他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第78页,第80页。正是在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这种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一条最终将通达形而上学重建的道路。
二、通向“语言学之后”的三个路标
这条路上有三个最突出的路标:第一个是感性的、实践的人类学,即马克思的劳动学说;第二个是对这种人类学的现象学还原,使它提升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第三个则是揭示这种哲学人类学中最深层次的自否定的辩证结构。其中,第一步解释了语言的起源,第二步展示了语言的意谓,第三步确定了语言的本质结构即隐喻。在我看来,这三步将使这种辩证法走向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1.感性的、实践的人类学
首先,就劳动学说而言,马克思所依据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黑格尔,是对黑格尔的劳动异化论的批判的考察。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赞赏远过于批评。他说:
因此,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的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这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即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这仍然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第116—117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学说的批评只有两点:一是黑格尔的劳动只是异化劳动,黑格尔没有看到这种异化劳动的“消极方面”;二是“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也就是构成哲学本质的劳动[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第116—117页。。但显然,马克思这段话中并没有否定异化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是认为“人同作为类的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只有通过异化劳动“才是可能的”;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否定精神劳动,没有否定这种精神劳动构成哲学的本质。他高度赞扬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即提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这里的“否定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Negativotät)之所以不能理解成“消极的辩证法”,是因为它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必然是“自否定”,也就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象化同时就是非对象化,是对于外化的扬弃。同时,他还揭示出这一过程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人类的共同活动”即社会性(共时性维度),另一个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历时性维度),它们都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自否定才有可能。
但是,劳动的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是如何实现的呢?马克思只是从哲学的角度确定了这一既成事实,还没有从人类学方面给这一断言提供具体的发生学解释。我对人类劳动起源的分析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当。人类通过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劳动而实现了从动物到人性的飞跃,其中,携带工具最终使人和自然界达到了感性上的一体,使人直接感觉到自然界(工具)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于是人能够把他物或他人设想为自身(民胞物与),这就使人具有了跨越个体的身体界限而与自然和他人相互沟通的能力。最早的手势语就是原始人类用来组织群体劳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工具或是直接用手和肢体当“工具”做出各种姿态,而与他人传达交流信息、统一步调,以完成单独一人难以完成的劳动过程;后来的有声语言则是借助于语音媒介“工具”的表意功能的升级版。看来,劳动能够成为人类共同的活动,以至于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历史性的活动,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功不可没。而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神奇的作用,正是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自否定,就是说,它们都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形态,而且同时代表着并未直接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意义,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意谓”。手势和语音意味着它们既是显现在自然界中的形象,又不是这些形象,而是这些形象所代表、所象征、所隐喻的意谓,至于这些形象代表的是哪些意谓,则是由劳动中的具体场景及共同参与者对这些场景的记忆的连贯性所决定的。因此,这种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根据不同的劳动群体或族群环境而有其偶然性,从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各民族语言系统。公孙龙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以及禅宗的“指月”之喻,讲的就是这回事。万物都可以是所指,但能指本身并非所指;然而,尽管能指本身不是所指,我们却必须在一定的场合下把两者视为同一,是=不是,A=¬A。如果坚持两者的区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就没有语言甚至没有手势,语言和手势就会退回到单纯的空气振动和肢体动作,只剩下自然现象的意义,而失去其表达意谓的意义了。可见,表现为自然现象的手势和语音绝不只是自然现象,而是自否定的语言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以单纯自然科学的眼光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马克思说:“甚至思维本身的要素,作为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也是感性的自然界。”[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思维本身就是意谓(所指),而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的语言则是这个意谓的“生命表现的要素”。这两者不可等同,但也不可分离,两者的统一体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但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哲学人类学的理解,我们不能只盯着作为声音振动的语言这样一种自然现象,而必须借助于现象学还原来展现其中所体现的本质结构。没有现象学的眼光,人类学就只能是一门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而不可能有什么哲学人类学。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哲学)实际上已经进入现象学的方法论层次[2]邓晓芒:《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增订本),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第92—104页,第94页。,只是尚未像胡塞尔那样将这种方法论建立为一种系统理论而已。
2.对劳动活动的现象学还原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我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不能像那些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看作劳动的动物,只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这就是用自然科学的量化观点来看待劳动,这种片面的抽象化了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在我看来,在马克思要揭示的异化劳动中,“人的完整的、直接的内在体验,他的感觉、他与对象的直接的意向性关系,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把握也用不着把握的黑箱,他们关注的只是劳动和资本这一系统的外部效应。在这里,劳动者和他的生产对象、产品被看作同样的自然物,而劳动者同这些自然物的本应是属人的关系却被忽略了,或被转移为有产者对自然物的间接的、抽象的拥有关系(私有制)了”[5]邓晓芒:《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增订本),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第92—104页,第94页。。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是从人在劳动这种感性活动中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感觉出发看待整个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因此,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是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
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动物、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了享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对“感性在自己的实践中变成了理论家”的现象学诠释,即是说,从理论方面和从实践方面,劳动都使外部自然界内化成了人的一部分,即“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和“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对劳动的这样一种现象学还原,我们对同一个自然物就有了双重的眼光。物不仅是摆在眼前的对象,而且是具有人性的“意谓”的对象,如马克思所说:“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第16页,第12—13页,第48—49页,第49页,第79页。但这种只对“我的感觉”才有意义的对象,恰好并不是我个人所独有的,而是社会共同的以至于历史共享的:
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第75页。
当然,感受到声音、线条与感受到音乐美、形式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又是作为同一件事情而向我的感觉呈现出来的;如果分开来看,则前者是个人的,后者是社会性的;或者说,个人的事情同时具有了社会性。因此,在劳动中,感觉成了“人的”感觉,也就是社会的感觉。这正是语言本身的自否定本质或隐喻结构的发生学起源。当我说A的时候,我意指的其实并非A,而是作为非A的B,但它又只有通过说A才能说出来。所以,语言从根本上说,就既“是”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语言自己就否定了自己的私人性而肯定了自己的社会性,哪怕只是在个人内心中的社会性。语言即使不说出来,也不是内心独白,而是内心对话。所以马克思又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借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第75页。伽达默尔后来也说:“讲话和谈话都出现在交往过程之中,科学陈述或科学证明方式的独白性只是这种过程中的一个特例。语言的进行方式是对话,甚至可说是灵魂和自己的对话,就如柏拉图对思想所描述的。”[3]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3页。保罗·利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尚未厘清其中的具体关联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把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同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形式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这个尝试本身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参见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68页。这些说法都只有立足于现象学还原的层次才能说得出来,也就是必须将日常理解的主观和客观、个人和社会、精神和物质等的对立置于“括号”之内,才能显示出其中的本质结构。只不过伽达默尔是自觉地这么做的,而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还只是在进行一种天才的猜测和试探。
3.语言的自否定本性
正是凭借上述哲学人类学的现象学分析,才能揭示其中最深层次的自否定的辩证结构,这种结构在劳动中就是对象化和异化,而在语言中就是辩证法,以至于辩证逻辑。这就是马克思那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结性评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深义。通常人们会认为,辩证法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肯定性的,另一种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在黑格尔以前,所有谈到辩证法的哲学都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的,直到康德还是如此。而这种消极意义的辩证法起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也就是诡辩学派。智者所关心的是语言的对话方式,即论辩术,他们的“智慧”尤其体现在教授论辩技巧和修辞方法上,并为此制定了希腊语的语法,但不管谈话的内容。他们常常故意用一套辩证技巧来违反日常习惯和常识,所以辩证法在当时就等于诡辩。智者最极端的代表是高尔吉亚,他曾提出三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著名命题: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即使认识了,也无法说出来告诉别人。他对这三个命题进行了详细的逻辑论证[4]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可以看出,这三个命题都是否定性的,其推演程序则是从存在论(本体论)出发,经过认识论,再进到语言对内容的言说,但全部都是严格依照语言的逻辑功能来操作的。
但这一顺序到了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颠倒过来了,柏拉图是从“辩证法”来推演“理念”以确立存在与非存在,亚里士多德则是直接从语言即我们的说话方式出发,从语言与所表达的对象的认识关系(主词-宾词,主体-客体)而确定了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实体)。从此,辩证法对语言、认识和存在的否定就转变成了不言而喻的肯定。只不过在他们这里,与高尔吉亚一样,辩证法和言说方式仍然只是我们用来抵达存在或非存在的工具,本身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直到黑格尔才第一次确立起来的。当然,黑格尔是通过把辩证法、认识论和本体论捆绑在一起而建立起了这个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其中存在论仍然按照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始终占据着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却并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赋予辩证法以独立的、高出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意义。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语言学一直处于阴影之中,只是偶尔冒出来作为一种初级入门的铺垫被顺便提及,辩证法只被视为本体论所自带的一种装备,虽然极为有用和锐利,但是并没有自己的领地,没有人单独考察语言本身的形而上学意义。自那以来,对语言的这一定位几乎成为共识,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所以就连伽达默尔也说:“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语言,只存在对活生生的语言中取出的概念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所打上的印记。”[1]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3页,第445页。尽管如此,在某些地方,黑格尔还是透露出了辩证法在语言的逻辑功能方面的某种更高、更原始的定位,类似于圣经中“太初有道(Logos)”式的创造性,暗示了某种“语言学之后”的本源的形而上学。他之所以未能公开地将这种形而上学宣示出来,是因为骨子里还受到传统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的存在论的束缚。而真正要进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必须首先将存在论或本体论置于括号中加以超越和扬弃,并对传统认识论加以改造才行。这是一种非存在论的或者超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意义上,的确存在形而上学的语言和语言本身的形而上学,但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前还基本上谈不上。
但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以辩证法为主题所展示出来的“辩证逻辑”,则无形中给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可望也可及的台阶。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积极意义伽达默尔也有所领会,伽达默尔说:
辩证法自古以来就是把内容的对立命题发展成矛盾,而且当对两个对立命题的维护不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是要达到矛盾的统一,那么这就达到最大的可能性,即使形而上学的思想,亦即在原初希腊概念意义上的思想能够把握绝对。生命就是自由和精神。黑格尔在辩证法中看到了哲学证明的理想,这种辩证法的内在后果使他实际上能够超越主体的主观性,并把精神同样思考成客观的,……在辩证法的本体论结果中这种运动重又终结并复兴于自我展现的精神的绝对在场之中,就如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结尾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辩证法不去解毁希腊的概念而是努力把它们继续发展成精神和自由的辩证概念并且仿佛把自己的思想也同时驯化了。[2]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3页,第445页。
显然,伽达默尔已经看到黑格尔辩证法并不只是如同古代辩证法或诡辩术那样解构一切概念,而是要把它们“发展成精神和自由的辩证概念”。当然,他和黑格尔一样,也将这种辩证法的积极性当成一种策略,为的是让传统的形而上学能够“把握绝对”,达到客观精神的“本体论结果”;然而,他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也终于意识到,辩证法所担负的这一本体论包袱可能过于沉重了。他发现,海德格尔“后期作品女巫式的文风”就是为了解构和扬弃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和我们的语言困境”,并“借助荷尔德林诗的语言排除形而上学语言”;但伽达默尔在此之外还指出了另外两种方式来“克服辩证法特有的本体论自我克制”,“其中的一条路就是从辩证法回到对话再回到谈话”,这就是他的“哲学诠释学”,而另一条就是德里达的“解构”的路:“这条道路并不是在谈话的生动性中重新唤起业已失落的意义。相反,它要在作为一切谈话之基础的意义关联的背景中,亦即在本体论的écriture(书写)概念中——而不是在闲话或谈话中——去消除意义的统一性,从而实现对形而上学的真正摧毁。”[1]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45—446 页,第447 页,第448页,第448页。但伽达默尔并不赞同德里达的这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之路,他的哲学诠释学之路正是要使辩证法返回到古代意义上的“逻各斯”。
在我看来,辩证法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大扩张的整体,不管是黑格尔语言用法中的“逻辑的东西”还是早已为西方哲学定下了第一步的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重新提出存在问题的试图,以及他叫作“返回步伐”的东西都是从辩证法的返回之路。[2]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45—446 页,第447 页,第448页,第448页。
克服形而上学不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局限于诗的语言,又简单排除形而上学语言,而必须将传统形而上学“大大扩张”,使传统形而上学成为逻各斯的辩证法整体中的一个成分,不是让辩证法为这一成分服务,而是由这一成分返回到逻各斯整体:这就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之路。用他的话来说,“我试图从谈话以及在谈话中寻找并构成的共同语言出发——在这种共同语言中问答逻辑被证明是有决定作用的——去摆脱实体—本体论的遗传重负”[3]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45—446 页,第447 页,第448页,第448页。,这是一条比较折中的路,它既不同于海德格尔那种“女巫式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又不同于黑格尔视为“科学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因为,“当黑格尔把辩证法归入一种科学和方法的概念时,他实际上乃是掩盖了它真正的起源,亦即在语言中的起源。因此,哲学诠释学注意到在说出的和未说出的之间产生作用的思辨的两者统一的关联,这种统一其实是辩证法发展到矛盾及其在新的陈述中得到扬弃的前提条件”[4]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45—446 页,第447 页,第448页,第448页。。海德格尔对于人们通常用“言谈”“陈述”“判断”来译希腊文深表不满,认为“这种貌似正当的翻译仍然可能使的基本含义交臂失之”,他主张,严格说来这个词应当追溯其最原始的词源含义,即理解为“展示出来让人看”[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41页。,或者译作“采集”[6]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9页以下。。这就完全解构了逻各斯一词的“语言”“话语”的含义,尤其是解构掉了它的逻辑、理性的含义[7]相反,伽达默尔则坚持和发挥了传统逻各斯的基本含义,他说“实际上,逻各斯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语言”,并且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这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人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了实际现存的东西,就在于他具有对未来的感觉”,“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具有逻各斯的。……人能够说话。也就是说他能够通过他的话语表达出当下并未出现的东西,从而使其他人能够预先了解”。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4—175页。。诚然,海德格尔说过:“在思想中存在进到了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这个栖身处。思想者和作诗者都是这个栖身处的看守者。”[8]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366 页。引用时有改动,参考德文版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am Main,1976。但这里的“语言”是德文的Sprache,在海德格尔看来,它是绝对不可能与希腊文的混为一谈的,它在其本质中只包含“思想”(Denken)和“作诗”(Dichten),而不包含陈述(Aussagen)、判断(Urteilen),更不包含逻辑。与此相对照,黑格尔则认为,逻辑学要讨论的就是逻各斯的辩证法问题:“认识到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构成逻辑学上一个主要的课题。”[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页。伽达默尔则是在某种程度上从海德格尔向黑格尔逻辑学的返回。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辩证逻辑哪怕具有诗化的内容,仍然可以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被视为“逻辑”,并且是比形式逻辑更加全面深刻的逻辑。当我们在诗性思维中运用隐喻或象征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是隐喻或象征,正是因为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期待视野”,这就是“S是P”,但同时又领会到“S是¬P”,或“S不是P”;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里有一种“既是又不是”的自相矛盾关系,我们的语言才具有了意思。伽达默尔也说:“双关语的多义性代表着思辨最具诗意的显现形式,它蕴含在互相矛盾的判断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说,辩证法就是思辨的表现。”[5]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7页。例如当我们说“人生是一场戏”时,我们当然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戏,因为人生只能是人生。我们甚至会说:“这哪里是人生!这分明是一场戏啊!”光说“人生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同语反复。当然,不仅是这种诗的语言,就连像“树叶是绿的”以及“白马是马”之类的一般命题,通常人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诗意,也不觉得里面有什么隐喻,但这类命题其实最初还是由隐喻建立起来的,换成明喻的话,是在说“树叶是(颜色)像绿(即荩草色)那样的东西”以及“白马是像所有的马那样的东西”。所有这些命题里面都包含一个基本的结构,这就是逻辑上的悖论:既“是”又“不是”;而在感觉上则是“像”,即以此喻彼,在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表象之间建立起类比的意义联系[6]“在讲话中的情况即是:一个词给出了另一个词,并由此发展了我们的思想。……人们说着这种词,而这种词又把人们远远引向他们自身也许看不出的后果和目标。……只有当我们冒险提出某些东西并跟从它的含义的时候,我们的说话才是说话。”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7页。。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本身完全是靠诗性的想象力而获得自己的生命的。
三、建构“语言学之后”从中西比较开始
由以上三个步骤,我们已经开始走进了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我们揭示了语言本身的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的不可分离及互为前提,不仅展示了语言的诗性本质(如维柯所发现的),而且阐明了这种诗性本质以辩证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必要性。对语言的本质和结构的这样一种揭示已经是一种形而上学了,它既高于和先于西方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也高于和先于中国的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1]康德曾认为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参见《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76 页),但显然,一种“批判”并不能单独构成一门形而上学,而只能成为“未来形而上学”的一个“导论”。,没有它,其他一切形而上学都无从表达,或者说,即使表达出来,也仍然不够形而上学,而是隐藏着某种形而下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却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学,更不是那种要借助于上帝的“圣言”才能超凡脱俗的形而上学,而是日用而不知的形而上学[2]如朱熹说的,“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参见朱熹:《隆兴府学先生祠记》,《文集》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8页)。,它不仅在形式上给语言的逻辑功能提供了非逻辑功能的源头,而且在质料上凭借自身而建构起一整套句法体系。
卡西尔认为,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的区别包含“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只有命题语言才是人所独有而动物不具备的[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第37页。。他说:
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人的全部话语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这一层。但是,有一种言语形式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里,语词不仅仅只是感叹词,并不只是感情的无意识表露,而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句子的一部分。[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第37页。
卡西尔这一划分虽然切中要害,但不完全准确,因为动物的叫声不能称作“语言”,而人的情感语言也是动物所不具备的。他只重视人的命题语言,而忽视了人类的诗的语言和其他非逻辑语言。后来的研究者,如迈克尔·托马塞洛,在考察人类语言的起源时根据新发现的实证材料,不再简单化地把人类语言模式划分为命题语言和情感语言,而是基于三个“关于人类沟通起源的假说”而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语法模式。首先,基于“人类的合作式沟通”(以手指物和比画示意)而建立起了“请求的语法”;其次,基于“由共享意图的技巧和动机”而形成“告知的语法”;最后是“在本身就带有意义的合作活动中”产生的“完全任意的语言惯例”,由此建立起“分享和叙事的语法”[5]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1页,第227页。。就是说,请求协助、告知信息和分享情感,是“三个基本的人类合作沟通动机”[6]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1页,第227页。。最初的人类语言(包括手势语和言语)就是以告知、请求和分享这三种模式而表达着人的知、意、情三个方面的要求,这三种语法模式在口头语中就是陈述句、命令句和感叹句,也就是三种句法模式。这三种句法模式是“语言学之后”体现在日用而不知中的形而上学原理,但它们不是通过逻辑规范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句法形式甚至是通过言语中的语调和语气词呈现出来,在现代书面语言中则辅之以一整套标点符号来表达和暗示这种语气。如果要说“语音中心主义”的话,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语音中心主义,但它不是按照音节间的所谓“分环勾连”(Artikulation),而是按照全句音调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高低转折、悬而未决等,来表达语言的本质上的“对话性”。如伽达默尔说的,“语言仅仅存在于谈话之中”[7]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9页。,甚至“正是在我们的语言经验中,在我们进入和成长于这种和自身的内心对话中——这同时又是先期的和其他人的对话并把他人牵入和我们对话的过程——世界才在一切经验领域向我们唯一展现和整理出来”[1]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0页。。我们在谈话中和他人切磋思想,其实同时也是在与自己进行内心的对话,这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否定本质。
伽达默尔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的哲学诠释学把语言的本质引向了“对话”(Dialog 或Gespräch);然而,他对这种对话中最重要的要素即“语气”却不置一词。这也许不是他个人的疏漏,而是与西方人的语言和对话的习惯有关。我们中国人在谈话中讲究的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在听人说话时不仅要关注那些词的含义以及词与词之间的逻辑连接(分环勾连),而且要从语气中听出“言外之意”,在书面语中则发展出了比任何其他语言都要多的语气词。其实所谓“言外之意”并不准确,因为既然可以从“语气”中听出意思来,已经说明意思并不在“言外”,而就在“言中”即语气之中了。但西方人在谈话时就不太注重这方面,他们重视的更多的是语言的逻辑方面,往往是能够以命题形式写在契约和文书上、语义清晰、能够严格表达(哪怕不在眼前的)客观对象的句子,而不在以什么样的语调说出来上花心思。这种文化差异直到今天都时常在对外谈判之类的场合显露出来,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但真正要谈语言学之后的原理,语气这方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是语言本身的自否定本质的最内在、最直接的表现,也就是突破命题语言的单一的“词化”倾向(在此可以说是“命题化”倾向),而在隐喻中展示出更多自由的语言空间。
因此,我说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如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形而上学”),即所谓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具有开放性的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中国形而上学从来不认为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逻辑学)是最高的学问,如《易经》中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讨论圣人如何治天下的事。但我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加上了自己新的解释,即将“道”理解为最原始的语言(道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是想把道和语言隔离开来,但他没有想到,和“言”(口头言语)隔离开的道仍然是“元语言”(metalingua,也可译作“后语言”)。中国人讲的“道”通常讲的是治国之道或为人之道,上升为自然之道或天道则是为了抬高到形而上学。“道”字的本意是“行走”(实践),引申义是“道说”。我在哲学人类学上讲的形而上之道,则把这两层意思合为一体,即最初的语言就是行走、携带、挥舞、示意等,也就是肢体语言和手势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携带工具的动物”也就等于说,人是语言的动物。这里的“语言”指最原始的语言、“元语言”。这当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形而上学了,而是中西形而上学的合璧,我的形而上学就相当于“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或译作“语言学之后”);但也不是西方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家(如塔斯基)讲的“元语言学”,因为他们没有把元语言学理解为形而上学,他们的形而上学已经有固定的含义,即“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所以他们仍然把“元语言学”理解为附属于“元物理学”(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论或工具论(逻辑学),顶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而不是“语言的形而上学”。所以我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实是对中、西两种形而上学的改造和嫁接,既有西方语言哲学的思辨性,又有中国道学的实践性,但同时超出双方,使“道”(“道说”)成了一种行动的隐喻或隐喻的行动,也就是一种具有“自否定”结构的行动。
在对语言和语言学的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着手来建构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