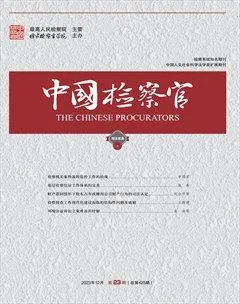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资源犯罪中的适用
王猛
摘 要:生态恢复性司法拓展了运用刑事司法手段保护和修复受损环境资源的方法和路径,但生态恢复性司法在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适用中呈现出适用率偏低、罪名和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修复方式多样、轻缓刑率高的特点。在实践中存在法律和政策不完备、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缺乏技术支撑、行刑衔接不畅、民众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的问题,可通过统一量刑标准、落实具体规定、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应用技术保障、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发挥典型案例和生态修复基地的引导作用,促进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专业化、常态化、社会化,为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发展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环境资源犯罪 生态恢复性司法 行刑反向衔接
民法典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专章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为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提供了法律遵循。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应用,在促进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涵、功能价值及实践方式
(一)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涵
生态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法律手段推动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和保护的司法理念和实践。它强调在环境资源受到破坏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机关的介入,依法追究破坏者的责任,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以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平衡。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可评估性、可监控性,促进了生态修复的履行效果。生态恢复性司法可以划分为:行为性措施、货币性措施和协议性措施。交纳修复资金或保证金、赔偿生态修复费用等涉及货币方式属于货币性措施;土地复垦、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土壤修复、第三方代履行、环保公益劳动等属于行为措施;签订修复生态环境协议或修复承诺书、制定生态修复方案等属于协议性措施,也叫混合性措施。[1]
(二)生態恢复性司法的功能价值
生态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以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刑事司法手段,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具有多重功能价值。在打击犯罪方面,生态恢复性司法回应对法益的救济,犯罪者参与生态修复,认识对环境的损害,产生悔过之心,从而降低再犯率。在预防犯罪方面,通过提高公民对环境资源的认识,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使社会大众更加关注环境资源问题,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氛围,减少对生态的破坏,降低犯罪发生率。在保护环境资源方面,司法人员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评价被破坏的环境资源情况、督促行为人对生态进行即时修复、全流程监控生态修复效果,有利于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司法服务新格局。
(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践方式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在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资源,主要适用于环境资源类犯罪,其他犯罪中涉及生态修复的亦可适用[2]。生态恢复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实践方式。一是作为量刑情节,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时,全面评估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程度和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状况,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刑罚。如谭某某滥伐林木案,其积极缴纳生态修复补偿金,可依法从轻处罚。[3]二是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公益诉讼的赔偿措施,在生态恢复性司法适用过程中,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公益诉讼途径,要求破坏环境资源的个人或单位对破坏的环境资源进行修复赔偿。如廖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法院判处廖某某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修复费用1763.52元。[4]如周某某、罗某某非法狩猎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131.7元,补种树苗100株,并制作张贴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标语60份。[5]三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类的司法建议,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过程中,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保护不力与治理漏洞问题,积极向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发送治理建议。敦促其强化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用检察建议等司法建议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价值引领,发挥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的协同作用,推进源头保护和社会治理。
二、生态恢复性司法在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一)适用率偏低
2018年至2022年,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案件的刑事判决书分别为21958份、25388份、25097份、9227份、1742份,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刑事一审判决书分别为990份、1647份、2791份、1048 份、191份,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案件中占比分别为4.5%、6.49%、11.12%、11.36%、10.97%。[6]上述数据说明,2018年到2020年,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一审判决书数量占比虽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显示出社会、政府和司法领域对生态修复的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加的态势。由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1年至2022年案件数量出现了下降,存在不稳定性,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比率仍然高于2019年之前。但总体上,2018年至2022年,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一审判决书比率较低,最低为4.5%、最高不足12%。这反映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生态修复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司法适用中仍存较大的局限,影响了该项司法原则适用效能的充分发挥。
(二)罪名和区域分布相对集中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整体特征影响,罪名分布和区域分布比较集中。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显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涉案罪名主要集中在污染环境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狩猎罪、滥伐林木罪这6个罪名,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位居第一。2018年至2022年,全国受理审查起诉这6个罪名案件共171013件291981人,分别占受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总件数和人数的81.66%和82.88%,涉及水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林木、农业资源等领域,分布省份主要在黑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浙江省和福建省。[7]
(三)修复方式多样,但以经济性补偿为主
生态修复方式有:增殖放流、复垦复绿、放飞活体、赔礼道歉、设立野生动物宣传保护牌、印刷野生动物的宣传册等,修复方式多样,以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平衡。如崔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过覆土、栽植、育苗,恢复该处地貌。[8]但生态修复方式多为经济性补偿,如“生态修复费用”“补偿金”“损害赔偿费”“赔偿协议”等,这些款项的收存单位不一致,有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如杨某某的生态修复费用暂存于如皋市人民法院[9];许某某等4人的生态修复工程所需费用交由寿县人民检察院暂为保管[10];曾某某缴纳生态修复费交由商南县林业局代为修复[11]。
(四)轻缓刑率高、易实现修复效果
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可评估性、可监控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在程序上从简、实体上从宽处理,行为人自愿认罪认罚、修复生态的自愿性与可行性增加,其中认罪认罚适用率接近百分之百,大多数行为人被判处轻缓刑,进一步促进了生态修复的履行效果。2022年,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191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刑事判决书中,适用缓刑的约143份,占比74.87%;单独判处罚金刑的约15份,占比7.85%;免予刑事处罚的约1份,占比0.52%。[12]笔者发现,判处轻缓刑的案件,其生态修复相对容易,技术性要求不高,修复周期短,修复成本相对较低。如河南省破坏生物资源保护案件中,被侵害物种多为常见的生物资源,大部分为鲫鱼、河虾、麻雀、雉鸡、杨树等普通动植物,涉案地点多为生活居住区的附近河流、山丘等,具有偶发性、非经营性的特点,如张某某非法狩猎雉鸡案。[13]
三、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和政策不完备
恢复性司法在环境资源领域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这是其适用率低最直接的原因。[14]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单项法规对生态修复规定了相应的追责条款,《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污染环境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修复生态可从轻处理,但缺乏对生态恢复性司法具体的方式方法、恢复标准、监管职责、从轻幅度的规定。《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及各省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关于生态修复的规定过于概括、执行难度高、标准不易衡量,在修复措施中未提及司法适用措施,法律和政策之间存在不连贯,生态恢复性司法难以落实。
(二)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缺乏技术支撑
生态恢复性司法要求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环境资源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往往忽视对办案人员进行生态恢复性司法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其难以认识到环境资源类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减弱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施效果。生态恢复性司法需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进行环境资源的影响评估、生态修复方案设计和效果监测等工作,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难以普及各级司法执法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生态恢复性司法适用情况的全程管理、追溯和监控效果不佳,限制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际应用。
(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刑衔接不畅
生态恢复性司法需要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效配合,但由于信息共享不畅、分工不明确等原因,导致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衔接不畅。一旦行为人被移送司法机关,相关生态修复工作往往会被行政机关忽视,而司法机关往往关注对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追究和惩处,生态修复得不到足够重视,再加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缺乏统一的指导意见和标准,生态损害的修复工作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缺乏有力的推动和监督,从而使生态恢复性司法应用缺失。
(四)社会认知和环保意识淡薄
部分群众不了解环境资源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修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不足,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感漠然置之。部分地区因其历史传统或习俗的影响,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推进缺乏舆论支持和社会助力。经济压力和生存需求迫使部分人员用非法手段获取经济收益,比如非法采矿、砍伐森林等,不利于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
四、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优化路径
(一)统一量刑标准,落实具体规定
为实现量刑公正,建议在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部分(第三部分),增加修复生态的从宽量刑情节,综合生态修复的方式方法、修复效果等情况,确定梯度式从宽幅度和调节基准刑的比例,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如比照第三部分第(十一)项,根据生态修复效果,设置“减少基准刑40%以下”至“减少基准刑20%以下”的多档从宽标准。结合《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规定,根据实践需求,加强法律和政策之間的协调与衔接,针对森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态环境,细化植树造林、复垦复绿、增殖放流等生态修复的方式和相应的修复数量,确保生态修复工作可持续进行和生态修复的效果得到有效监督和评估,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更加具体和可操作的指导。
(二)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应用技术保障
加大对生态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组织生态恢复性司法适用的专门培训,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司法机关内部协作配合,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司法团队,集中办理环境资源类案件。各级司法机关应配备必要的信息技术设备,招录遥感、大数据等专业人员,提高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监测生态环境变化,评估生态恢复效果,为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司法机关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森林碳汇补偿等创新机制,运用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和方法,提高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水平和适用成效。
(三)促进司法与行政部门协同发力,强化行刑反向衔接
强化检察、行政机关的联席会商机制、跟踪督促机制、跟进监督机制,通过内部线索移送、调查核实权运用等方式,将恢复性司法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形成生态恢复工作协同配合共治格局。借助大数据积极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由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建专家智库,健全环境资源工作辅助咨询论证机制,探索碳汇价值损失评定方面系统、流程、规范,共同助力生态恢复司法行刑衔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打破“重刑事轻行政”传统思想,充分借助“林长+检察长”等机制,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将不予刑事处罚人员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四)注重发挥典型案例和生态修复基地的引导作用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树牢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办案时追求极致,提高案件质效,增加执法司法透明度,及时公布宣传生态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发挥典型案例对群众生态保护的舆论引导作用。建立和完善生态司法保障基地,在环境较好的区域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在林场、山体等遭到生态破坏的区域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集“生态理念宣传、生态成果展示、生态文化推广、生态保护体验”于一体,为社会群体、学生提供生态现场教学基地,营造生态保护氛围,强化生态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