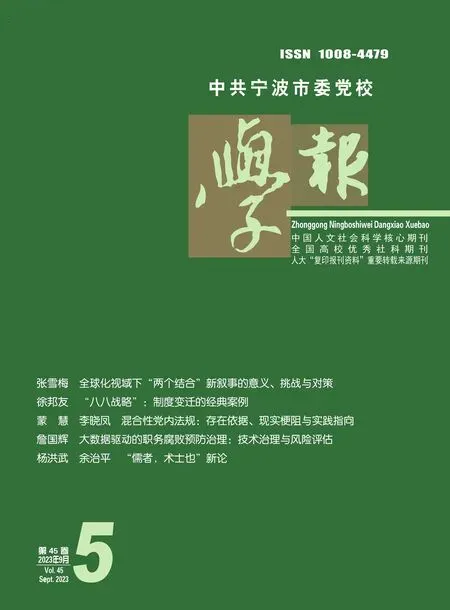何为颜子克己?
——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陈 昊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朱学陆学,究竟有何不同?历来讨论朱陆异同,有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1]3037,由此,朱陆学术分歧是为学方法的差别[1]1885。又有所谓“心即理”与“性即理”的不同,据此,朱学陆学是哲学系统的差异[2]467—470。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论述可知,冯友兰最早提出“心学”“理学”的哲学体系存在根本差异的看法[3]806,他从哲学体系本身出发,探讨朱陆学术差异的思路与观点,又被牟宗三继承与发扬,尽管是以一种批判形态[4]。此外,任继愈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框架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又往往以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分判朱陆哲学[5]269。
无论是为学方法的差别、哲学系统的不同,或分属唯心主义的不同派别,综观前人论朱陆之异,似乎多了几分“以今格古”的建构,少了一些“历史现场”的声画还原。实际上,朱陆论学分歧如何演变成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其中一些精彩的历史细节,隐含在二贤对“颜回克己”的不同解说中。尽管,朱陆诠说“颜回克己”的义理差异、不同工夫指向,已有丰富研究成果,然而,将这个看似经学诠释的题目纳入思想史轨道,重新考察朱陆异同,却为我们探析这八百多年前的学术公案提供了新的视角。
针对《论语》“颜渊问仁章”,孔子告颜回“克己复礼以为仁”,朱陆都以“克己”为“克除己私”。进一步追问,颜回所克“己私”具体指什么?朱陆就有了分歧,一指声色利欲的私欲,一指个人知见的私意。朱熹据天理人欲之辨论克己,陆九渊却对理欲之辨深表怀疑,并对克私欲不以为然,相反,陆九渊立足“天德己见之进退”,强调克除私意①。不仅对“己私”各作诠解,相应的工夫主张,朱陆也大相径庭。朱熹以知行交发的工夫框架说克己复礼,认为颜子先有一截分辨天理人欲的穷理工夫,由见得明而刚决力行,从而克胜一己私欲还复天理。然而,如对垒打擂一般,陆九渊却教人跳脱繁复支离的书册讲论,主张易简工夫,指点学者在自家身心上体认千古一理与圣贤之心。陆九渊阐发颜子克己工夫,强调学者置身天德己见进退之间,着力克除一己私见的病痛。
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争论,并未止步于己私的义理差异、心性工夫主张的不同。当朱陆从分歧走向冲突,“颜回克己”的问题就溢出经学界限,扩大升级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也猛烈批评江西之学,痛斥陆九渊“克除意见”“无意见”之说。由此可知,颜回克私欲或克私意,并非单纯义理训释的经学问题,而是关联朱陆异同的学术公案,这一点也是本研究进于既有克己研究之处。此外,前人论朱陆异同,或谓之“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别,或谓之“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分,本文则由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出发,重返朱陆论争历史现场,提供考辨朱陆异同的新视角。
一、朱熹释颜回克己:偏重“克胜身之私欲”
朱陆诠说颜回克己,多有相同之处。朱陆同训“克”作“胜”,克己为克胜(除)己私。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杨简的解说则不同,杨简训“克”作“能”[6]2134,故克己不是克胜私己,而是正面挺立自我、发挥积极自我②。朱陆还同在“反本复初”的复性(心)论结构上论克己工夫。朱陆也都赞赏颜回资质高明,表彰克己为高阶工夫。但在这些地方进一步详察,朱陆分歧暴露无疑。朱陆对颜子克己的不同看法,首先落在己私的内涵。己私,究竟指声色利欲的私欲,还是个人知见的私意?
朱熹立足天理人欲之辨,认为颜子所克是负面消极的“身之私欲”,因此,朱熹说克己私,偏重说“克胜身之私欲”。朱熹《论语集注》释“克己复礼以为仁”曰: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全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于我矣。……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其仁不可胜用矣。[7]167
朱熹从天理人欲的三层复性结构解说颜回克己:本心仁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仁体破坏丢失(心之全德天理坏于人欲)、复归仁体(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朱熹着重以“私欲”论克己私,又兼顾己私之为“私意”的方面。在《论语集注》释“颜渊问仁”部分,朱熹就补充性地引用程子以己私为私意之说:
程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7]167
程子礼意对言,以非礼处的私意来定义己私,朱子引此说,意在兼顾“私意”的内涵。单就《论语集注》看,朱熹主“私欲”说己私,兼带以“私意”说己私。与之对应的克己工夫就意味着,学者克己,应当克胜与己身关涉的声色利欲的私欲,又要警惕非礼处的私意。这不免令人疑惑:朱熹何以如此“缠绕”,既然重言克私欲,何必兼说克私意?既然克己工夫是克胜身之私欲,何故又要兼顾警惕私意?此处,有朱子的良苦用心。朱子始终提防学者以克私意工夫的名义,看轻读书讲论(因读书讲论被视作意见、私意而予以摒除)。朱子怀抱忧虑,学者若束手不做格物穷理工夫,将流于佛老。
换句话说,如何理解颜子克己,必有相应的工夫主张与工夫后果。朱熹其实知晓,单纯考察义理内涵,“己私”包括私意、私欲两方面。在注释《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时,朱熹已做出明白辨析。朱熹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解尊德性,又所谓“存心”,即“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7]53于此一节,朱子向弟子剖陈他的“费心”考量:
问:“《(中庸)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发出来要去做底。今人说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见得是小,所以不广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则昏浊沉坠即不高明矣。某解此处,下这般字义极费心思。”[8]2133—2134
在朱熹看来,私意是人心中所发将要人有所作为的私智与故意,私意使人自蔽,以至于见识狭小封闭而不能广大;私欲则系于人身耳目鼻口,私欲令人自累,将使人意识昏浊意志沉坠。朱熹费心辨析的,是私意与私欲引发的心性与道德方面的后果,即由广大而入于狭小、由高明而堕入卑污。
(广大、高明)此二句全在自蔽与自累上。盖为私意所蔽时,这广大便被他隔了,所以不广大。为私欲所累时,沉坠在物欲之下,故卑污而无所谓高明矣。[8]2134
既然朱熹明白,私欲自累与私意自蔽,二者同为学者致病之源。那么,朱熹何以必主“克私欲”而略说“克私意”?原因之一,前文已言及,对己私内涵不同认定,必然引发不同的克己工夫主张,并带来不同的心性工夫后果。就此而言,朱熹对流于禅家空虚无念的为学倾向,对学者束手心性与悬空捉理等为学弊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如何避免偏在心上用工的病痛?在朱子看来,必得落实在即物穷理、应事接物等格致工夫上,并与克胜身之私欲的克己工夫配合,如此才算工夫完备而无缺漏。此外,朱子无法赞同“灭除己见”“克除私意”之说,或许还在于,朱熹不得不为他终生热衷的读书著述、讲明义理的“意见活动”做某种自我辩护。
综上,笔者试点破朱子的隐秘心迹:朱子明白知晓,单论字义训释,颜回所克己私的确涵盖私欲与私意两方面的内容。然而,进一步考量克己工夫,则“克私意”实在不是稳妥的工夫,学者沿此做工夫,多歧病而无实地。因而,颜回克己之为克私意,这一层意思无需声张。相反,学者应更多围绕耳目口鼻等与身相关的私欲物欲,做克胜私欲的切身工夫,如此才稳健、着实、切己,才有工夫下手处。朱子如此曲折心意,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二、陆九渊说颜回克己:克除知见蒙蔽
较之朱子的曲折心迹与“苦心安排”,陆九渊的克己主张简明直截(这也正是陆学本身特质)。理论上说,己私涵盖私意与私欲两种内涵,陆九渊却明白指出,颜回非克私欲,而是克除“私意、私见、私智”。
……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恨纵肆之失,夫子答其“问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地者,皆其私也。颜子之所以异乎众人者,为其不安乎此,极钻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践“克己复礼”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贡之明达,固居游夏之右,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之识,绝凡民远矣。从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传乃不在子贡,顾在曾子,私见锢人,难于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天德己见消长之验,莫著于此矣。[9]8
陆九渊申明,颜子如此贤明,“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恨纵肆之失”,在克己问题上,应引起学者注意的是“私见锢人”的病痛。陆九渊还援引孔门弟子传道情形,做辨析与证明。陆九渊认为,孔子告颜子克己,孔子警示的和颜回领会的,是克除“自命仁义道德、自期圣贤之意”的私意,且曾子就是凭借无私见而得道(以鲁得之);相反,子贡擅用私智、自以为博闻,却终究不能得道。陆九渊还说:
颜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释然处。[9]454
陆九渊这一极为高调的宣示,后来被人归纳为“颜子无己可克”的说法。依此说,颜回无需如常人般克除声色货利、眼耳鼻口等身之私欲,颜回所克的只是一点“未释然处”的私意。陆九渊的说法,与朱子克胜身之私欲的说法针锋相对。何以认定颜子无私欲可克?陆九渊的根据在于:颜子有精神,其贤明远胜众人常人,因而谓“颜子无己可克”,亦无问题。陆九渊强调克私意,也有他的考量,并指向特定的“不良学风”③:
人心有消杀不得处,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牵义,牵枝引蔓,牵今引古,为证为靠。[9]458
在陆九渊看来,颜子所克己私不落在道德生活领域的克胜声色货利的私欲,而应定位在知识领域、学术思想活动方面,克除私见、私智与私意。陆九渊“天德己见”的说法,意味着人的知识活动与德性修养相互对立,存在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这与朱熹强调的“天理人欲”论互相抵牾。陆九渊对天理人欲说不以为然,认为此说出于老氏,并非儒家正传: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出于老氏。《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之,而后好恶形焉。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此。《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9]395
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若是,则动亦是,静亦是,岂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则静亦不是,岂有动静之间哉?[9]475
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与朱熹一样,也承认克己具有克胜私欲与克除私意的双重内涵。陆九渊明确指出,克利欲与克知见这两方面,各自对应不同根器与品级的人群。众人常人要克利欲,颜子只须克去一点私意;愚者不肖之人要克利欲,智者却应克除知见。陆九渊说:
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9]9
陆九渊认为,物欲与意见作为致病原因,各自影响的人群虽有不同,导致的后果却是一致的,二者都将导致“本心蒙蔽”的后果,即学者失其本心、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
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见,高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则一也。然蔽溺在污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弃者是也。蔽溺在高洁者,大抵自是而难解,诸子百家是也。[9]11
在陆九渊看来,卑陋、无志行与无操守的常人,陷溺于物欲蔽累;学者、智者与贤者,及历史上如诸子百家等学派,则往往蔽于私智、知见与意见。进言之,前一类人群易于引导,使之超拔振奋而得解救,后一类人却沉溺私见、自以为是而难以点醒。陆九渊感叹道:
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难。[9]398
显然,私欲与私意之间,陆九渊着力反对私意,也就是反对学者意见、个人知见与私见。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作陆九渊“学术史探寻”的必然结论,也是鹅湖之会陆九渊隐而未发的“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说[9]491的翻版。依照陆九渊所持学术思想的发展观念看来,从古至今,学说与知见随历史的发展而叠加增益,越是后来衍生的学说知见,距离历史源头与真理本源越远。不仅如此,近世学说知见愈发雕琢、支离、缠绕与造作,也就与陆学尊崇的本心道理愈加隔绝。
后世言易者以为易道至幽至深,学者皆不敢轻言。然圣人赞易则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9]4
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理不明,内无所主,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藉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妇人童子听之而喻;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穷年卒岁,靡所底丽,岂不重可怜哉?使生在治古盛时,蒙被先圣王之泽,必无此病。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9]4
陆九渊对“易简之道”多加阐发,也对他心目中“学术退化”的思想图景大加挞伐。陆九渊心目中“学绝道丧”的思想发展图景,构成他主张易简之学的依据之一。一方面,陆九渊本人勤读、苦读、善读书册,也不是不教人读书;另一方面,陆九渊易简之学的核心与重点,却落在发明本心与教人自立超拔。两方面对比,后者始终压倒前者,因此,上文“以学术杀天下”的说法,自陆学系统内部看并不奇怪。而在重视读书讲论与学术思辨的朱学视角看来,此说真是石破天惊!无怪乎朱子与后世学者,遂有“陆学不读书”的看法。总的来看,陆九渊上述“学术复杂化即学术退化”的论断,意在依托易简直截的学术标准,纠正两宋诠说经学的学术风尚,批判繁复支离的学术风气,最终立足人人皆具的本心来重建学统。不仅如此,陆九渊还举起复古旗号,自信地接续阐扬孔孟道统。陆九渊论孔门之传,别有深意:
孔门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贡,虽不遇圣人,亦足号名学者,为万世师。然卒得圣人之传者,柴之愚,参之鲁。盖病后世学者溺于文义,知见缴缴,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9]470
由于知见纷繁蔽溺本心,孔门之传在“愚鲁”的子羔与曾参,不在知见纷纷的子贡等弟子。然则,今之柴与参为谁?今之子贡又是谁?在陆九渊心中,将谓己为柴参,而以朱熹比子贡了。(陆九渊在无极太极辩中,批评朱子“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9]27。详后。)
陆九渊以克除私意说克己,还关联着他的本心论、发明本心的工夫。陆学直承孟学,主张人的本心光明、至善、有力量、与理为一,只是由于物欲与意见(又以后者为严重),才使人蒙蔽本心、陷溺本心、本心不得其正。陆九渊说,“人心至灵,惟受蔽者失其灵耳。”[9]189相应的颜子克己工夫,就在于扫除心中各种意见谬传,还复本心。陆九渊要人跳脱繁复支离的书册讲论,回复古圣先贤相传的简约之道,“直截”在自家身心上体认千古一理、与圣人同然之本心:
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一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周道之衰,文貌日胜,良心正理,日就芜没,其为吾道害者,岂特声色货利而已哉?杨墨皆当世之英,人所称贤,孟子之所排斥拒绝者,其为力劳于斥仪衍辈多矣。所自许以承三圣者,盖在杨墨,而不在衍仪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简而易从,初非甚高难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学以克其私,而后可言也……[9]149—150
陆九渊以讲学为拯溺、复本心,如此,讲学不仅不是书册传注,相反,书册传注使人沉溺意见私说、令人丢失光明正大的本心。陆九渊也强调讲学,也说讲学在穷理、在格物致知,可仔细看来,陆九渊所谓穷理格物,绝非朱学式的探究天下物理,归根到底,只是明其在我之理,也就是发明本心:
“……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9]440
综上可知,在陆九渊那里,声色货利的私欲与私智、意见、知见,二者都将导致本心的蒙蔽沉溺。与朱熹区分“私欲自累”与“私意自蔽”不同,陆九渊主张区分人群的品类根器,认为寻常之人众人沉溺物欲,贤人学者却多蒙蔽于私意。基于此,陆九渊注重面向沉溺知见书册的“贤者智者”,展开某种“唤醒”工作。一方面,陆九渊经由某种“学术史批判”,提倡扫荡古今学者智者的私意意见,整顿当时学风,重建学统道统;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陆九渊号召学者回归易简之学、易简之道,做发明本心工夫,要求学者自信而超拔流俗,以期还复本心天理。然而,陆九渊的这些观点,逐渐被简化为“无意见”“克除意见”的工夫与说法。而陆九渊的学术批评与“扫荡意见”之说,也无可避免地直指“留情传注”“埋首书册”的朱熹。朱陆围绕“是否克除意见”,最终爆发出持续的、极富思想史意味的激烈论争。
三、朱陆的“意见论争”及其学术异同
朱陆论说克己,各有侧重与不同。围绕“颜子克己”的义理训释、克己工夫与为学倾向,朱陆之间由观点的对立,逐渐演变为学术论辩,最终形成二人学术决裂的一个爆发点。具体来说,朱子强调天理人欲之辨,重说克胜身之私欲;陆九渊则看轻物欲之累,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说克己。朱子重说克胜私欲,又“捎带着说”克私意,朱子之意在于,学者既要克除身之私欲,不为物欲所累,脱离卑污而趋向高明,同时,也应谨防私意的自蔽,以摆脱固陋。朱子规划的是,学者既做克己工夫,又加以穷理格物的进学工夫,最终趋向本末精粗无不到的广大学问境界。总之,不可以“克除意见”名义,束手不做格物穷理的进学工夫④。相比之下,陆九渊的工夫主张易简直截。陆九渊主张克除知见私意,并一再强调,学者士人已知晓为学趋向即已经摆脱物欲之累,对学者士人来说,更为根深蒂固而难以对治的恰恰是私意与意见的贤者病痛。
由此而往,陆九渊不无偏激地提出“颜子无己可克”之说。陆九渊认为,颜回贤明高明,无需再做声色货利等私欲上的克己工夫。反观朱熹,终其一生对克己工夫反复再三⑤。依朱子定见,颜回克己工夫高明难作,“而凡学者亦不可不勉”[7]168。在朱子看来,当问题从“颜子如何克己”,一变成为“颜子是否需要克己”,势必再转为“(当世)学者是否要做克己工夫”。这一问题的三个层面,尤其第三个层面,直接关系现实中道学士人的为学倾向、学术风气与工夫选择,引发朱子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从具体的观念与工夫看,一方面,沿着“颜子无己可克”的观点走下去,学者将对身之私欲、声色货利放松警惕;另一方面,陆九渊“克除意见”之说,或将使学者滑向束手不做工夫的地步,更由于缺乏明理工夫,学者将陷于“认欲为理”的境地而不自知。基于以上担忧与考量,朱熹对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说、“克除意见”工夫,发出尖锐批评。
黄达才问:“颜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厉声曰:“公而今去何处勘验颜子不用克己!既是夫子与他说时,便是他要这个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说,道颜子不似他人样有偏处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尝见他与某人一书说道,才是要克己时便不是了。这正是禅家之说,如杲老说‘不可说,不可思’之类。他说到那险处时,又却不说破,却又将那虚处说起来。如某所说克己,便是说外障,如他说,是说里障。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着他紧处。别人不晓禅,便被他谩。某却晓得禅,所以被某看破了。”[8]1465—1466
钱穆考证此条语录为朱子六十四岁以后所说,“象山卒于朱子六十三岁时。其时二人讲学已决裂,故此条记朱子语气极峻厉。”[10]455尽管出自弟子记录,仍可见朱熹面对“颜回不需克己”说的激烈反应。显然,朱熹将“颜子无己可克”的具体论题,扩大到对陆九渊学术的整体评判。朱熹不仅批评“无己可克”“无意见”的说法,更猛烈攻击陆学整体上陷入“禅病”。朱熹批评陆九渊的“无意见”“无己可克”说,非此处偶见。
某向与子静说话,子静以为意见。某曰:“邪意见不可有,正意见不可无。”子静说:“此是闲议论。”某曰:“闲议论不可议论,合议论则不可不议论。”先生又曰:“《大学》不曾说‘无意’,而说‘诚意’。若无意见,将何物去择乎中庸?将何物去察迩言?《论语》‘无意’只是要无私意,若是正意,则不可无。”先生又曰:“他之无意见,则是不理会理,只是胡撞将去。若无意见,成甚么人在这里?”[8]3880
克己是否就是克除知见、无意见,这是朱学面对陆学必争之毫厘。寻其原委,鹅湖之会已埋下伏笔。鹅湖之会,陆子寿诗“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与陆九渊诗“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9]427—428,都是批评朱熹留情传注,认为朱熹讲学病在支离。此后,陆九渊与朱子激辩无极太极,书信往来中,陆九渊对朱熹的经义校释与学术论辩多有讥评,如说朱熹“轻于立论,徒为多说”与“句句而论,字字而议”等[9]23,甚至直以子贡“多学而识之之见”病朱子。其书有图穷匕见之处:
古人质实,不尚智巧,言论未详,事实先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夫子而师承之,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无疑。先行之训,予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子,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9]27
陆九渊对这段“判词”颇为满意,认为它不局限于与朱熹作无极太极辩论,更是自身为学宗旨的纲领性展示。《与曾宅之》书全文录此段[9]5,《与林叔虎》曰:“复晦翁第二书,多是提此学之纲,非独辨无极之说而已”[9]127。详味此书,其中对朱熹其人其学,不留情面地指摘刺痛。无怪事后朱子言及此处,依旧义愤难平,甚至遗憾来不及在陆九渊生前与之面论痛辩。而这一切,也都经由陆九渊的“颜回无己可克”说、“克除意见”说牵连引爆。
基于他汀类药物与贝特类药物在合用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通过大量的总结研究对于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提出了建议:建议70岁以上的老人和老年女性慎用他汀类药物,肾功能不全者应慎用他汀类药物,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时不能同时服用环孢霉素、红霉素、蛋白酶抑制剂、维拉帕米、伊曲康挫等等相关药物。
因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子克己处,曰:“看此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分晓。此乃捉着真赃真贼,惜方见之,不及与之痛辩。其说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讲习却是大病,乃所当克治者。如禅家干屎橛等语,其上更无意义,又不得别思义理。将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然有明快处,方谓之得。……”[8]3881
从朱熹的视角看,陆九渊重言颜回克己为克除私意,故主张“无意见”的说法与工夫,并视思索讲习为大病、要人不思义理,这分明是禅家说法。另一方面,回归陆九渊学术立场来看,之所以认定义理讲习非学者急务,是因为陆学自有其核心主张,为学先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确立学者超拔之志。二贤为学倾向与论学思路,的确有针锋相对、形如冰炭之处。于是,在是否读书讲论、有意无意的问题上,朱熹推重经义讲习、义理穷格的明理工夫,必然痛斥陆九渊“无意见”说,判定其“宗旨是禅”。
有一学者云:“学者须是除意见。陆子静说颜子克己之学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盖欲于意念所起处,将来克去。”先生痛加诮责,以为:“此三字误天下学者。自尧舜相传至历代圣贤,书册上并无此三字。某谓除去不好底意见则可,若好底意见须是存留。如饥之思食,渴之思饮,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见也。圣贤之学如一条大路,甚次第分明。缘有除意见横在心里,便更不在做。如日间所行之事,想见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见。所以目视霄汉,悠悠过日,下梢只成得个狂妄。今只理会除意见,安知除意见之心,又非所谓意见乎?”[8]3880—3881
以上,朱熹仍是回应与批判陆九渊“除意见”“无意见”之说。朱熹认为,陆说毫无儒家文本的经典依据,不仅如此,不论是非好坏、凡意见皆务去除的极端说法,将贻误学者,使学者蹈空务虚、把捉悬空,故绝不可援引无意见说、无己可克说指导为学工夫。朱熹还敏锐地指出,意见有好有坏,有合理的自然的、有人为的造作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灭除,不仅流于禅学空疏无实,且倡导“灭除意见”的主张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意见呢?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朱熹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小人喻义利”章,朱子对陆氏的讲说极为赞许。朱熹《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曰:“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几其可以不迷于入德之方也。”[11]3852—3853朱陆也曾同声相应,有如此调试协和的交往。然而,同年朱子罢郡东归,在给吕伯恭信中,朱子即直言陆学“去除意见”之病,并深表忧怀:“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著‘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渠虽唯唯,然终亦未竟穷也。”[11]1515朱熹此书所言,与前文所引观点一致。可惜的是,吕祖谦作为朱陆二人学术异同的居间调停者,于同年(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至此,围绕是否克己、是否克除意见的朱陆学术裂缝逐渐扩大,最终引爆成为某种学术决裂[12]771,789,820。
值得说明的是,朱陆因“颜子是否克己”的问题,引发为学“是否去除意见”的论争,二贤虽针锋相对、愈演愈烈,却并非意气之争,也不落于后世津津乐道的门户争斗。相反,何为颜子克己、与此紧密关联的工夫观点与为学主张,恰是朱陆立足各自学术立场,不得不辨的枢要。
四、小结
朱陆的克己主张,粗看见其同。然而,何为颜子克己?细致考察克胜私欲、克除私意这两方面义理内涵,则朱陆的工夫主张、学术宗旨、为学风格,其间的差异暴露无遗。陆九渊论学,要在学者克除私意、亲近师友与发明本心。朱熹既承认义理上“己私”包含私欲与私意两方面内涵,又坚持工夫实操方面,“诚意不可无”,学者需提防“认私欲作天理”,因而格物穷理、读书应事的明理工夫绝不可无。更重要的是,朱熹出于严辨儒佛的考量,激烈反对“无己可克”“无意见”说,并警惕学者由此滑转成空疏的为学趋向。经由“颜子克己”这一棱镜,可一窥朱陆学术分歧如何扩大、观点如何冲突升级,朱陆学术破裂的历史过程与思想逻辑。
不过,朱陆为学的实际情况、朱陆学术论争,又绝非朱熹主克私欲、陆九渊主克私意可一言尽之,反而有许多曲折处、难言处。略举其三。其一,有关陆九渊与读书。陆九渊论颜子非克胜利欲之私、而是克除私见,意在指点学者跳脱书册意见、避免传注支离,从而先立其大以还复本心。陆九渊这一主张,的确在其门人中间,产生块守一心、不读书不应事等不良后果。然而须知,陆九渊本人非不读书,也屡教人读书之法。陆九渊反对书册传注与讲论知见,针对的是当时沉溺著述讲论的学术风气,客观来说,具有某种“解缚”效果。陆九渊也并非与朱子作对为难,只是恰巧朱子为学推崇格物穷理、偏重解经读书。其二,有关陆九渊与禅学。朱熹屡说金溪似禅,这既出于严辨儒佛的宗派立场,也是朱子着实渐进做工夫的为学趋向必然产生的后果。以此,朱熹严防无意见、克除意见的说法,也不是朱熹对陆九渊其人其学存有偏见,而是出于朱子捍卫道学纯粹性、建立系统完备为学工夫不得不然之举。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其实也“排佛”,他揭露佛家根底于自私。这其中,何为异端、佛老何以是异端、异端在儒门内部呈现何种倾向等等问题,朱陆各有不同的标准与分判。其三,为免流于禅学,朱熹坚决反对“无意见”“克私意”说,同时也承认“私欲自累”“私意自蔽”二者同为学者致病之原。理论上说,颜子克己工夫既要克胜私欲,也要克除私意。在此,朱子的确显露出某种隐秘的纠结和忌讳(牟宗三语)[4]12。简言之,令朱子纠结忌讳的,正是陆九渊自信推崇的人的本心与心体。在力求构建一套稳妥而完备为学工夫系统的朱子看来,人类心灵涵盖的幽深莫测的心意,终究不是寻常人普遍开展心性工夫的门径所在。或许正因如此,朱子不仅对诚意问题纠结一生,也对陆九渊“无意见”之说持警惕的、拒斥的态度。私欲与私意的深层关联,朱熹未能清晰阐明,直到明末王夫之,才对此做出“私意亦导源于私欲”的论说[13]376—380,但这已是后话了。
[注 释]
① 除“私意”,陆九渊还使用“己意、私意、私见、私智”等称谓,指代学者的个人知解、言说与意见。
② 朱熹也注意到了杨简(敬仲)以能训克之说,并作了评论。在朱熹看来,克的字义固然可以训作能、克己训能己,但这一训义或将引发不做工夫的消极后果。“问:杨敬仲说:‘克字训能。此己,元不是不好底。为仁由己,何尝不好?克己复礼,是能以此己去复礼也。’”“曰:艾轩亦训克作能,谓能自主宰。此说虽未善,然犹是着工夫。若敬仲之言,是谓无已可克也。”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15)[Z].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543).
③ 颜子有精神,其贤明远胜众人常人。对这一前提,朱陆有相同判定,所做推论与进一步的工夫主张却相反。不仅如此,朱陆的经学诠释,也有截然不同的现实指向。二人心目中“不良学术风气”,因学术立场、视角、体验等各方面的差异,也所指不同。朱熹警惕当时学者不做工夫的风气,陆九渊却批评学者困守书册讲论。
④ 朱子用意,在求工夫主张的周全完备,消除其中潜在的漏洞与隐患。
⑤ 对颜回克己工夫,朱熹自中年至晚年,呈现出逐渐着重表彰的一个变化过程。尤其将克己与持敬两方面比较,可见朱子不断发掘与看重克己工夫的变动趋向。根据今本《论语集注》“颜渊问仁章”朱子最后改定的“愚按”(朱子往往于“愚按”中,申明贯彻自己的独立见解)可知,朱子晚年用克己替代持敬,视前者为“圣门第一工夫”。此说钱穆先生详述于《朱子新学案》,并可参见乐爱国,陈昊.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J].学术界,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