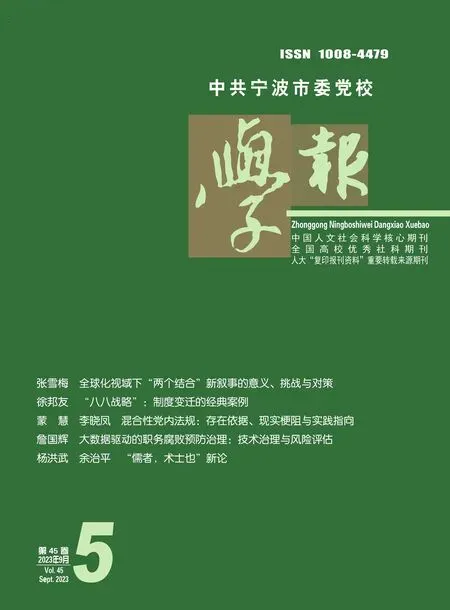“儒者,术士也”新论
——早期中国知识人阶层的兴起
杨洪武,余治平
(1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9;2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上古中国,文化普及率极低,祭祀、礼乐、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往往只被少数人所掌握并垄断,这些精英则首先出现在官场。文明初建之时,政治、宗教、社会生产、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官方直接操持和经营。官主一切,以至于后世中国的许多行业、职业都从官场流变而出,儒、士阶层也不例外。作为王官之学主管者的卜、宗、祝、史,其职事内容多与后世儒者有涉,是官员中的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中的官员,因而是官学,也是学官。而卜、宗、祝、史之职官,却又被后世不加区分地统称为文职化的“史”①。刘师培《史职篇》曰:“三代之初,最崇祀典。天事、人事,相为表里,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盖称天而治,自古已然。故司天之史,或‘史’、‘祝’并称,或‘史’、‘卜’并列,掌祭祀而辨昭穆,诚哉!非史莫由矣。”[1]一七八九卜、宗、祝、史之官,皆归于史类。而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刘师培又说,“史”被当作包含甚广的职官,“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故“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2]四四八七。君王的政教律令,皆本于为史官所掌握的学术。王国维也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3]269既是掌书之官,则应该是时代知识的化身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虽然中古汉语里,儒与士经常联称,章太炎《原儒》亦曰:“儒者,术士也”[4]544,但在最初的起源上,儒并不直接就是士,儒、士有别,并非一源。胡适《说儒》称,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5]626。周治之下,殷人中的祝、宗、卜、史阶层似乎具有多重身份,角色非常复杂。在殷族人的眼里,他们是祖先文化的保存者和继承者,他们传播着本民族的宗教,他们的身份无疑已经具有古礼教师和神职人员的性质;而在周族人的眼里,他们又成为现实文化的总结者、创造者,他们是丰富当下人们精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专门人才,甚至并不排除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新兴贵族的清客顾问。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血统相异于周,所以即便具备了很好的德艺才气,也难以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论其地位,最多也只能与周族统治阶级中最下层的士相当。时间一久,人们也便以“士”称呼他们了,儒、士一同,重叠使用,界限模糊而不相区分。所以,“亡国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士。”“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5]627相对于亡国奴的日子,殷士的生活似乎还过得去,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或治丧、相礼,或教书、育人,虽不可能获得再高一点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但也始终没有被人踩在脚底下。“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诨名。”[5]628于是,殷周的祝、宗、卜、史,是官,属于知识人阶层,而不是民,一旦被虐称为“儒”,则说明他们已经衰落而走下坡路了。所以,早先的儒并不是一个响亮而值得自豪的称谓,总与衣着古板、从事一些祭祀崇拜活动、观念陈旧保守、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与能力联系在一起。
一、士,并不全都是儒
儒与士的概念区分,值得引起注意并予以辨析清楚。尽管士、儒一源,儒由士出,但总体而言,士众而儒寡,士泛而儒专,士早而儒晚。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职业分工系统,却始终没有产生地位固化乃至对立的阶级。牟宗三《历史哲学》指出:“中国自古即无固定阶级世世相传于人间。士农工商,非阶级之意”[6]55,社会分工不同,职业也就有所不同,但绝不至于构成相互对立的政治阶级。古今中国,都是有阶层而无阶级的。“皇帝以下,一律平等”[6]55,社会成员的地位有差等,却因为拒绝了世卿世禄之制,致使社会阶层始终都没有凝固化、板结化。“自周以前言,伊尹耕于有莘,则农也。傅说起于版筑,则工也”[6]55,每一个行业都能出经纶天下的人才,社会阶层上下浮动、升降的灵活性与空间都比较大,各阶层人员的地位转变随时都有可能。而“士皆出其中”②,士阶层的兴起实际上也就产生于每个具体行业之中,每个士几乎都有一线工作的经历,也都是行业的翘楚或成功者。
士,西周铭文中,字形类“王”,具体则像一把斧钺,可能表意王者身边手持兵器的武卒。至于《虞书·舜典》所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即指刑官,处理刑狱案件的司法官,蔡沉《书集传》曰:“理官也”[7]15;甚至说,“士”是五帝时代的治狱刑官,则皆是后人的引申,而并非“士”字的本义。士,在古汉语中长期都指一种官名,贵族中的最低等级,地位次于大夫。按照周制,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③,这是中央朝廷的治理组织架构,士则处于官阶秩序的最底层,是最卑微的从政者,但也可能与民众的距离最近,因而也最接地气。周代的士,也有同姓异姓、有爵无爵之别。同姓而无爵之士,在祭祀赐酒时,则以昭穆为序④。牟宗三《历史哲学》说“士为贵族与庶民之衔接处”,在社会的上层与底层之间发挥连结和沟通作用,并且“贵族,年代久远者,既可沦为士、为庶民,则庶民自亦可以升为士也”⑤。可见,士的来源是可以上、下流动的。贾谊《过秦论》曰:“致天下之士,……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8]二《周礼》一书所记录的机构设置与官职安排,几乎涉及所有生产生活领域,仅直接名以“士”的官吏,《夏官》篇就有司士,至《秋官》篇则更多,士师、遂士、县士、方士、讶士、朝士、都士、家士。士,经过从西周到春秋的数百年演进,然后才是对体制内、具有一定专业技能人员的共同称呼,其中也包括善于读书并以文化为职事的知识阶层。余英时曾说:“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认作知识阶层。‘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他根据古代文献“士”的各种用法,参照以“事”训“士”的文字解释,认为“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9]3,6。显然,士虽然是一种体制内的存在,但品级、地位都不高。《说文》亦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桂馥《义证》曰:“闻一知十,为士。”[10]44许慎《说文》因声训义,指士为事,懵懂地猜测到了士的起源与官场职事的关联。《论语》之《公冶长》篇有“闻一以知十”之说⑥,《述而》篇也要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⑦,这都意味着士有悟性,知识面广,所以应该是全才、通才。《说文》段《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但能事其事的人,也未必都是士。士有职业,但并非天底下所有的职业都能够被士所囊括。《白虎通·爵》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11]3517,士的职责似乎主要让人有理性,阅尽古今人事物,知识丰富,确立自我价值系统,能够自主判断是否对错,而不受外界所左右。余英时认为“古代知识阶层始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时代”[9]4,把“士”的起点设置得太迟太晚了。周初时代即已有“士”,充当王室与地方的官吏,及至春秋、战国之交,则已经蜕变出队伍庞大、形成气候的儒者阶层了。顾颉刚《杂识》称:“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12]八五,士是体制内、管理平民的低级官吏,直接把士纳入贵族则显得突兀。士也未必都是从事文案的基层官吏,他们或可出征沙场,为国而战。士有文士,也有武士,都服务于君王政治和国家需要。
求证于文献,则有《孟子·万章下》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赵岐《注》曰:“子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天子,所列官阶之至尊,但也只是其中之一爵,如果德行不高,或做得不好,照样可以被王室其他成员所弹劾。公、侯、伯分别占一位,子、男则合占一位。孔子著《春秋》,已改《王制》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为“公、侯、伯子男”三等爵,而在《孟子》,天子之下,则分四等爵,天子属于其中之一等⑧。至于“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把天子包括在内,下至士,总共分为六等。士的内部,又分上、中、下三等。无论在大国、次国、小国,“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即最低一等的士尽管也是体制内的贵族,其待遇却与刚进入体制内的庶民一样。
诸侯的封国之内,臣子等级有分疏,官阶有差,序位列治。《礼记·王制》曰:“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可见,在上古中国的官僚体系里,其品级分疏,无论是六等爵还是五等爵,士皆为最低的一个档次,与庶人最接近,掌管着王权的基层事务。士无下级,无可使唤,所以,办事还得役使自家弟子。据《左传·桓公二年》,晋国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天子分土裂国,可以使唤封侯;诸侯分采邑于卿大夫,卿大夫之室则为家;大夫有宗室,杜预《注》曰:“适子为小宗,次者为贰宗,以相辅贰”,故也有宗室之内的子弟可供差遣;至于士,杜预《注》曰:“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13]七六士的工作对象是庶人,但仍需要帮手,无人可供使唤的情况下,自己的子弟则首当其冲。古代中国的官吏,或因为岗位世袭,或因为一人俸禄得养全家,所以做起事情来经常都是公私不分的,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很难划清它们的界限。这就跟早期儒者的情况相类似了,儒者必须自己干活,才能完成相礼事务,才能有收入以养家糊口。士,既然不在五等爵之内,那么,其死也不当有谥封。《仪礼·士冠礼》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谥号是有爵位者的死后待遇。郑玄《注》曰:“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14]34士在周的体制内为下三等,虽也为贵族,但死无谥封。
尽管从起源上看,先士后儒,儒是士的流变,但儒的早期来源和人员构成决不只限于士这一支。士人队伍中,不论是从事文案工作的文士,还是拼杀在疆场的武士,也只有一部分人最终蜕变到了儒者群体里面去。随着王权坍塌、体制消失而逐渐化身为儒者的,显然不可能是他们的全部。殷商灭亡之后,许多遗老遗少无法在新兴周王室的体制内找一碗饭吃,便俯身向下,浪迹民间,凭借自己掌握的礼乐知识,为千家万户操办红白喜事,最终也不得不把这种相礼活动当作自己的职业,操持经营,养家糊口。这些遗民,不乏卿大夫,他们曾经的地位都是大于士、高于士、重于士的,也都是曾经的贵族,只不过原先所依存的体制靠山不复存在了,不得不靠本事吃饭而自谋生路。于是,他们慢慢就成了最早的儒。
二、术士,作为知识人阶层
术士,是比“士”的意义指向更趋精准、贴切的称谓。士,最初的含义还可文可武,但术士则显然已经是掌握一定技能人员的代称了。术士,更具有专业含量,更具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技能。《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⑨。实际上,早在汉末,“儒”就已经被直接等同于“术士”了。刘师培《释儒》曰:“儒为术士,惟通经致用,始被此称。孔子治经,故以‘儒家’标说。”[15]三七九六儒家之名,出现得很晚。孔子之前没人自称为儒家,即便存在着儒者,也是通称,指代天下所有的道术系统及其载体和传承者,并不专指狭义上做仁道研究和著述的某一个门派。孔子在世的时候,提醒弟子要力争做“君子儒”,而不做“小人儒”。钱穆《新解》指出:儒为“士之具六艺之能以求仕于时者”⑩,显然,此时的儒,已经具有研习“六艺”的专业技能。孔子之后,分工加强,专业化程度趋高,儒的含义开始收敛、内卷,只限定于孔子及其门徒所继承和发展的单一学派,可以明显与从其自身中裂变出来的道、法、墨、名、阴阳家等相分疏和区别。
术士之人,也是知识人,属于早期儒者之一种。《说文》训“术”曰:“邑中道也。”⑪道、术互训,指义相合,无论是道还是术,都具有人所共同认可的知识系统含义,其原本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已经向智慧敞开,澄明而透彻,恰恰是因为人自己经常被污浊不堪的事相所干扰,才遮蔽了道术的光芒,而使其变得晦暗幽闭。而“邑中”即国中,刘师培曰:“三代授学之区,必于都邑。故治学之士,必萃邑中”[15]三七九四—三七九五,说的就是《小戴礼记·王制篇》中那些“升于司徒”“升于学”⑫之士,他们不但汇聚在官层体制之中,并且也汇聚到王城、都城,学在民间不太可能,学在王城、都城之外的城邑也不太可能。上古中国的道术,从一开始就是以高度集中的面目出现的。刘师培《释儒》说:“‘儒’为术士之称,示与野人相区异。”术士在体制内是最早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群,不可能是乡野土民。早期的儒者群体都诞生于官层之内,但不可能只是士人阶层,比士人地位更高的官员,甚至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宗伯、小宗伯、大史、小史之类在落魄之后变成为儒,也不是不可能。
在《周礼》的职官设计中,士是一个比大夫地位还低的阶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之类已经在体制内,只需要逐级提拔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再次进身到体制内。但刘师培《释儒》却指出:“古代术士之学,盖明习六艺,以俟进用”,术士之学的基本内容、职业目标,是先修习六经之书,然后等待机会被录用。等级考试与入职考试当然是不一样的,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一个已经上车坐稳,一个还没挤进来。刘师培用隋唐之后科举试子的处境揣度上古术士的身份,显然是有问题的,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按照《释儒》的思路,对于术士而言,读书、习礼是进身的必须条件,不可绕开。《礼记·文王世子篇》强调“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在适合的季节读适合的书,故“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⑬。上古读书是一种雅趣,是贵族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非常高尚的事情。士人的读书活动必须有序进行,而不是任意为之的。《礼记·王制》篇曰:“乐正顺先王《诗》《书》《乐》《礼》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作为乐官之长,也掌管着公卿大夫的继续教育、国子的学习培养和民间人才的选拔,其职责非常重要。郑玄《注》曰:“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16]256读书也得遵阴阳之序,天道逻辑也应该体现在王者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士是造出来的,始于有意识的培养。周王的太子和众多庶子,三公、诸侯的嫡长子,卿、大夫、上士的嫡子,一样需要有意识的培养。故“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⑭这里,术士显然是后来才被选拔进体制内的民间俊彦,术士最初并不在职官序列之中。可以作为佐证的一点是,《王制》篇又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贤者以告王。论定,然后官;论官,然后爵;位定,然后禄”。司马之职,也掌管人才开发工作,其职责之一就是发现人才,郑玄《注》曰:“辨其论,官其材,观其所长”;职责之二是使用人才,“各署其所长”⑮,论其才学水平而委任相应职务。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生活在民间的、尚未进身于官层的那些士,必须有条件识字,如果连字都不识,还谈什么读书和步入仕途?所以,刘师培的观点明显是把士的形成往后推延了,放在了学校教育已经成熟,从王城太学、州郡庠序到县学体系较为完备的皇权时代。这种背景错置,让他觉得,饱读诗书的术士之人通过官方组织的“辨论官材”活动就可以被选拔进入官僚体制之中,谋得一个位置,领取一份俸禄。
三、进身入官而服务社会
术士,显然是有专业知识、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目前还在民间,还处于等候朝廷启用的状态,进入官方体制内对他们来说,既是出于生存方面的需要,又是出于追求精神理想的需要。这双重需要交织在一起,驱动着无数士子学以精进,把诗书读好、吃透其内在脉络与要旨当作自己的阶段性目标。一旦进身成功,则可以立即转向这些知识储备的社会应用。《礼记·儒行》记,鲁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这里的“待聘”“待问”“待举”“待取”足以说明孔子在世时儒者所处的一种等候被录用的行状,那种期待被体制接纳、期待被官方认可的急切心情,已经跃然纸上。儒者本身始终是具有附着性、依赖性的,其存在价值必须在被别的社会群体所需要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确认和实现,它自身是不能独立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在人格、思想和精神境界方面又恰恰是十分独立的。寄存于同一个主体内的这种独立与依附之间的紧张关系,经常把术士人群的身心世界撕裂得特别疼痛。
按照《周礼》的职官谱系,士已经在体制内了,只需要提拔,而不需要进身。但按照刘师培的观点,士必须以学进身。《释儒》曰:“古代惟术士以学进身。”[15]三七九六这个“古代”并不是上古,毋宁是近古。战国末期,术士阶层才在民间大肆兴起,他们或以专攻“六艺”之书,或以拥有一技之长,而著名于世。童书业《春秋史》称,春秋初年有“尚贤主义的兴起”,“各国竞争渐烈,任用贤才的观念也发达起来,士以下的阶层因此渐次抬起头来;又因为教育较前普及,平民的势力格外容易发展,这使世族的地位急剧地倒塌。”[17]247儒者群体当然属于平民阶层,他们最初能够接受教育是相当不容易的。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在饱读了一筐诗书之后,才周游列国,寻求用才之伯乐和自己施展才华之空间的。《庄子·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成玄英《疏》曰:“方,道也。自轩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18]554人才队伍逐渐专业化,这是大势所趋,但中央王权到了战国末期则已经彻底瓦解,这些专业人才已经无法寻找到一个统一而稳固的体制能够安身立命,只能寄生于大大小小的诸侯王门下,于是,养士之风又开始流行。当然,大部分的诸侯王豢养术士之人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在兼并别国、为天下王者的时候能够用得上这种智囊团队。对于术士之人而言,尽管没了体制,也没有相应的爵位封号,但似乎也可以算“以学进身”,毕竟诸侯王的供给、俸禄也可以看作是对自己才学的一种承认。
术士之人进身入官的标准,《荀子·王霸》篇曰:“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杨倞《注》曰:“官施,谓建百官,施布职事。”王先谦《集解》曰:“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19]210荀子这里的“论德使能”标准与《礼记·王制》中的“辨论官材”之说其实并不完全一致。《王霸》篇把德提升到了第一位,而《王制》篇则相对看重才干、才能。大凡圣王置官用贤,皆具有针对性,皆能够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曰:“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⑯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注重发挥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其为人,自在自如,自由自得。术士之人得以进身为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得益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儒者特性和气质。《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四曰:“儒,柔也,谓柔愞也。”[20]1121既称为儒,就意味着柔弱、软弱,这就是早期儒者群体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释儒》引郑玄《三礼目录》曰:“儒之言,优也,柔也。其与人交接,常能优柔。”进身官场之前、之后,术士之人似乎都能够做到谦逊为本,自守弱势,而绝不凌驾于别人之上。刘师培曰:“盖儒者以柔让为德,以待用为怀,故字从‘需’声。”[15]3796看起来,儒者只是因为“待用”期间才装出一番谦逊、低调的样子,夹着尾巴做人;而一旦掌权得势,就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了。实际上,儒者这个团体从根底发源处、从内在到外表都很和蔼可亲,从来都不可能有盛气凌人、藐视他者、桀骜不驯的架势。据《礼记·儒行》,“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⑰,也早已把仕与不仕置之度外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一个伟大的儒者,即便是官层和社会地位都很低的士,也相当了不起。术士进身仕途,所获得爵位之高低,原则上取决于每个人的德行才学之水平。《荀子·效儒》篇曰:“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大儒、小儒之尊卑分疏,由谁来决定呢?杨倞《注》曰:“人主之柄也”⑱,乃一国之最高行政首长。于是,同源共体的官、学,皆接受王者人主的绝对领导。
儒家是善于以进用为术的。无论是在职业起源上,还是在发展流变中,儒家都注定与官层、与政治权力密切相联系,儒家的血液和骨髓里都埋藏着做官、治理天下国家的欲求。孔子本人就一心只想做官,颠沛流离十多年,周游列国,汲汲营营于王者权贵,并不是孔子有多么大的权力欲,而是他实在太想借助君王威权架构的神力,以便把儒家的仁道主义精神贯彻到现实政治中来,使万千民众免受痛苦。孔门儒学甚至以“不仕,无义”而批评“丈人”,谴责退隐之长老漠视国家危难,对苦厄民众袖手旁观。据《论语·微子》篇,子路曰:“不仕,无义”,在国族有需要的时刻,有才能的社会精英却不出仕为官,而放任世道败坏,根本就是不道德的,对芸芸苍生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和怜悯情怀。“欲洁其身而乱大伦”⑲,面对恶人逞强,只愿意守住一个人的干净,却置群体利益于危险之中、执意要让整个社会的秩序陷入混乱局面,就是最大的不人道,就是最大的犯罪。
四、结语
古今中国,官层对社会资源的调遣能力、控制程度和管理水平,都是任何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儒家不是官迷,只是善于计算推行仁义的成本而已,要想改造社会就必须利用官层的威权架构与力量,抓住君王,紧扣政治,虽未必一劳永逸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精力之付出。远离权力中心的任何社会改造,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做官可以做大事,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拯救芸芸众生,可以建设美好社会。所以,在儒家看来,有本事的人不做官,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和左右权力运作,是不符合仁道主义基本要求的。《论语·为政》篇中,有人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借《周书·君陈》“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而作答,并且反诘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⑳这是一种不出仕而从政,在家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实际上也是一种为政。这一表态,显然只是孔子的无奈。孔门儒者之中,子张对政治最为敏感,算得上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为政》篇记录,“子张学干禄。”钱穆解曰:“干,求义。求禄即求仕。”直白点说,就是钻营当官,追名逐利。然而,有意思的却是,孔子并没有反对子张“汲汲于谋禄仕”,孔子只是悄悄地建议子张必须改变求仕的策略和方法,“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必须先在学问上多闻多识,释疑解惑,谨言慎行,寡过少悔,这样就可以行云流水一般,功到自然成。“谋职求禄之道即在其中”[21]42,43,不露痕迹,不露声色。这里,“仕”“学”甚至可以互训,意义相通,内容也有高度一致之处。故术士之学,后来即被孔子所直接继承,并构成儒家学派最基本、最原始的学术对象和礼法资源。刘师培《释儒》曰:“儒家以通经为本,故以孔子为宗,然均古代术士之遗教也。”[15]三七九七儒者从上古的职官脱胎而出,儒学的旨意保留着上古术士的教化风格,因而很值得我们作深度的挖掘和探赜。
[注 释]
① 仅从字面上看,卜、宗、祝、史似乎皆为文职之官,但在甲骨卜辞中,史则首先为武官。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一文指出:“史在卜辞有用为事者,如言‘协王事’‘协朕事’‘协我事’,皆言协服殷王战事之义。”或言“我有事”“我亡事”“今岁有事”“今秉有事”,也“多指战事而言。”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阳:《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第183—195 页。郭静云也指出:“殷商的史者都是使者,为武官,非文官。”见《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450 页。史的文官化、书生化可能是周代以后的事情。
② 秦汉之后,“士人握治权,其于阶级之消失,贡献尤大”。见【民国】牟宗三:《历史哲学》,见吴兴文主编:《牟宗三文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 年,第55 页。
③ 元,原作“员”,元士,即“天子之士”。见【清】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官制象天第二十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 页。
④ 参阅张雁勇:《祭祖经邦——〈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研究》,北京:研究出版社,2022 年,第396 页。
⑤ 并且,士人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逐渐成为王权统御和皇权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自春秋后,经过战国,士级露头角,占社会之大势力,周之贵族政治遂必趋于崩溃,而转为秦汉后之君主专制。自此以后,治权上之民主遂得大开放,其形态直维持至今日而不变。”武帝“更化”之后,“士人出路由选举征辟”;魏晋南北朝期间,“门第形成”,士人阶层“治权独占,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隋唐开始,“科举制成立,门第贵族逐渐打破”;再经宋、明、清,“此制不变”,天下“治权遂大开放”。所以,在古代中国,尽管政权总不可撼动,因为它是高祖皇帝打下来的,但治权则长期攥在士人阶层的手中。引文见【民国】牟宗三:《历史哲学》,吴兴文主编:《牟宗三文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 年,第45 页。
⑥ 参阅钱穆:《论语新解·公冶长篇第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116 页。
⑦ 参阅钱穆:《论语新解·述而篇第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172页。
⑧ 【宋】孙奭《疏》曰:“盖以孟子所言则周制,而《王制》所言则夏、商之制也。”实际上,孟子把天子纳入爵等秩序蕴涵着限制王权的要求,不当解为周制,则《礼记·王制》的“五等爵”也并非夏、商之制,毋宁是战国末期直至汉代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周制,不足为信。引文参阅【汉】赵岐,【宋】孙奭:《重刻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记·万章下》,【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见《十三经注疏》(8),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 年,第179 页上。然而,《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却曰:“五等者,谓虞夏及周制。殷制三等,公、侯、伯也”,则大致可信。见【汉】郑玄,【唐】孔颖达:《重刻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王制》,【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见《十三经注疏》(5),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 年,第212 页下。
⑨ 参阅【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人部》,济南:齐鲁书社,1987 年,第681 页下。
⑩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句,是孔子劝告子夏的话。钱穆把“儒”解释为具备“六艺之能”并且希望入仕当朝,以及“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后来逐渐成为学派之称”,这些都是对的,但说“孔门称儒家,孔子乃创此学派者”,则有待商榷。孔子及其弟子,称“儒”,而从没有自称过“儒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肇始人并非孔子,孔子之前已经有儒者,已经有儒家学派,孔子只是儒家队伍发展到春秋末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总结者、集大成者,是一个能够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引文见《论语新解·雍也篇第六》,第151 页。
⑪ 参阅【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彳部》,第167 页下。
⑫ 参阅陈戍国点校:《礼记·王制第五》,第334页。
⑬ 春季适宜吟诵歌乐篇章,夏季则适宜演奏诗歌乐章,皆由太师昭告、教授和带领。至秋季,则在西边的瞽宗里学《礼》习礼,由掌礼之官负责指导。冬季,则适宜在上庠里学习《书》,由主《书》之官讲解、领读。引文见陈戍国点校:《礼记·文王世子第八》,第362 页。
⑭ 参阅陈戍国点校:《礼记·王制第五》,第334页。
⑮ 选士任官,乃司马的工作内容。《周礼·夏官》中也有司马一职,列天子六卿,掌管国家军政大事,参与天子册命典礼,地位很高。其下属包括:司勋,掌封赏;司士,掌群臣版籍,以德定爵,以功定禄。引文见【汉】郑玄,【唐】孔颖达:《重刻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王制》,【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见《十三经注疏》(5),第259页上。
⑯ 参阅【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子张问入官》,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一四一页。
⑰ 参阅陈戍国点校:《礼记·儒行第四十一》,第529、530 页。
⑱ 参阅【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第144 页。
⑲ 参阅钱穆:《论语新解·微子篇十八》,第473、474 页。
⑳ 孔子论政,“常以政治为人道中一端”,“人道”大而“政治”小,更何况“处家”也有“家政”,居家修身也是一种政事,是个体化的政治。“孔子虽重政治,然更重人道”,人活世上,可以不为政,却不可以不做人。为政只是无数职业中的一种而已,切不可以为从了政、当了官就目空一切,盛气凌人。“苟失为人之道,又何为政可言?”做人为本,这是底线,而不可丧失。见钱穆:《论语新解·为政篇第二》,第45、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