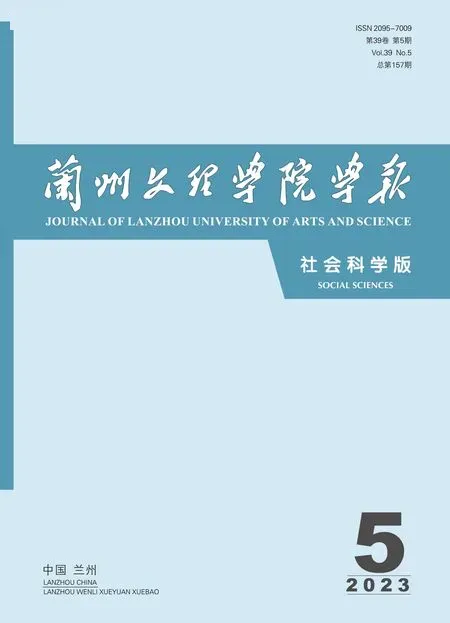幽冥·炽热·澄澈:古马诗歌色彩审美的三重维度
罗 立 桂,张 欣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作为西部诗群的一员,古马善用画家的眼睛绘色,通过对色彩的想象与创造,诗意地再现客观物象,实现诗歌语言对灵魂、人性及生命的表达。在《胭脂牛角》《红灯照墨》《落日谣》《大河源》《飞行的湖》等诗集中,古马立足西部的人文与自然,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客观限制,将色彩的象征意味纳入个体的生存经验与情感的表达方式,在色彩的流动与交错中,捕捉并表现情绪的变换。从色彩的差异来看,古马或为客观事物有意着色,或利用事物本来的颜色穿透客观现实,丢弃日常的惯性感知,重新创造出幽冥、炽热、澄澈等符合诗人心境的虚构世界。从色彩的设置来看,古马常在变动不居的色相、明度、色调与光线中烘托氛围,形成色彩、情感与现实的多维融合。从色彩的表现来看,古马不但利用多种颜色的对比与映衬将意象融为一体,造成强烈的视觉刺激,也借色彩的具象化与陌生化表达,刻意区隔开诗人、读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形成语意的多义与朦胧。实际上,古马对色彩的塑造归根结底源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从而唤起人们对色彩自然的反应与无意识联想。但古马又将超越日常生活的形而上思考诉诸于色彩,利用对色彩的幻想形成“一种离开现实的‘他性’”[1],绘制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意世界,言说其丰富的情感体验。
黑格尔认为,“颜色感应该是艺术家所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所特有的掌握色调和就色调构思的一种能力,所以也是再现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2],诗人古马在其诗歌创作中明显体现了这一创作品质。色彩本是自然光波作用下的物理现象,但当其作为情感的折射进入诗人的文学视野时,已逐渐从人类原始的色彩本能中解放出来,成为诗人衡量与表现客观世界的“内在尺度”,同时也呈现着诗人独特的色彩审美。在诗人与色彩的动态交流中,“被感情引导的感觉发现自然中的形体与色调变化,同时,被感觉到的形体与色彩立即对主体产生自身应有的作用力”[3]。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使色彩在诗人的视觉感官和心理状态中不断被延伸,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心灵表现的手段,以便在色彩创设的画面中表达情绪,色彩书写因此也成为读者打开诗人内心的“秘钥”。
一、黑色:于幽冥处寄托灵魂
诗歌“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4],诗人古马常以疏离现实的姿态,在黑色的陌生化与具象化书写中,转喻他对自我灵魂的感触。在中国的色彩观念里,“黑色的色感事实上也最具‘哲学’意味”[5]。在古马的诗歌中,黑色兼具中西方的文化感知,使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色彩,不言自明地表征着诗人灵魂的不安与焦虑。古马的生存体验创造了黑色被言说的可能,他将黑色同“黑夜”“黑水”“墨”甚至“乌鸦”“蚂蚁”等客观意象对等,以点染、铺设等笔法创设了一种幽冥境界。这种幽冥之境具有幽惧、神秘、压抑的审美质地,因而“产生着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6],唤起诗人感知与想象的双重共鸣以凝视灵魂,成为古马安放灵魂的玄妙之处。
古马对黑色的宏观化处理中,以浓厚的诗意笔触、大胆的色彩铺设及陌生化的色彩处理形成了视觉与知觉的双重暗示,加强了黑色给读者带来的感受。诗歌《寄自丝绸之路某个古代驿站的八封私信》(八)[7]就以纯粹的黑色塑造了一个幽冥、孤独及迷茫的诗境,以此呈现了诗人的内心状态。诗歌延续了古马简约质朴的语言风格,却淡而有味,令人发省。诗人借民间谚语入诗,开篇以“路上坑多天上星多”大面积铺设黑色,创设一种混沌、迷茫之境,借以渲染“我”作为异乡人处境之艰难。“在夜晚飞翔的鹰的灵魂在寻找新的寓所,并且/通过风的手/把黑暗的花/安插进我疼痛的/骨头缝里”,“鹰”在夜晚飞翔,今晚“我”就如鹰般在黑暗中找寻灵魂的归属,但哪里又寻得到方向呢?“黑暗的花”也只能暂时慰藉“我”人生旅途中疲乏的身心。而面对无尽的黑夜,“我”在哪里?“我”该何去何从?诗人用黑色将内心的茫然与人生方向的迷失外化,甚至其中也夹杂着问道的困惑。此时诗人由茫然、压抑、无奈带来的无限心酸与悲伤已抵极点,终于从心中发出了呼喊——“今夜呵,我是生和死的旅馆”。古马把“‘夜’作为时间概念,‘旅馆’作为空间概念,‘生和死’作为生命概念,同时出现在‘我’身上,未知的生命状态在无限的时间中融入特定的空间,封闭的空间让人感觉生命的压抑、切己与有限,‘我’像一间小小的旅馆,承担了无尽的夜,未知的生和死”[8]。在生命快要崩溃之际,唯有长叹后的低语——“像世界一样,辽阔无垠”才能荡开“我”心中无尽的压抑。“我”解脱了,同时“我”也迷失在了生与死的无限黑暗中。诗人用黑色为客观世界上色,从侧面反映了自我内心的压抑与迷茫,形成内外的和谐统一。
除此之外,诗歌《福利院》[9]也将黑色化作一团萦绕在诗人周围的“雾气”,“他叫喊/但他的喉咙/似乎被黑暗卡紧了”,以此流露出诗人对“黑”的恐惧。《旅夜》[10]写道:“剩有乱麻似的黑暗了/在我心里/就只剩我一个人抱膝团坐。”诗人让黑色依附在带有时间意义的“黑夜”,或是具有抽象意义上的“黑暗”等意象中,借以渲染他内心的压抑、恐惧与孤独。或许,最想淡忘的也往往展现其难忘性。诗人拼命寻求灵魂解脱,于是求助星星,让点点星光驱除黑暗,他轻松写道:“真的可以淡忘与一个人或者一个世界相关的一切了/是的,一颗星正在教我忘记/教我如何独自摆脱全部的黑暗”,然而诗人不知道的是,从黑暗中逃离才是痛苦的开始。当诗人自认从黑暗中解脱时,他又陷入了身心的痛苦与迷茫,诗歌《失眠》[7]30是作者内心矛盾的生动体现。“发红的灯泡”为“我”驱走了黑暗、带来光明,无奈光明灼伤“我”的眼睛,熬煎“我”的心灵,在光明下“我”无处遁寻,灵魂也无处安放,看来“我”终究是属于黑夜的。
黑色扼杀光明,却也孕育光明,其自身带有的复杂性成了古马情感滋生的源头。如果说,古马在黑色的陌生化与宏观化思考下,表现出了对灵魂、对未来的恐惧,那么在黑色的具象化处理中,则展现了古马在恐惧之余,渴求找到解脱之路的愿望。在诗人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幽冥之境中,一方面,他恐惧黑色的未知与神秘的同时又渴求光明,另一方面,诗人却又在黑色中保持清醒,寻求灵魂的栖居地。《秋日私语》[10]63将黑色具象为一只“野兽”,“我还相信/黑夜会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注视我/像一个过于肥胖的野兽/微微喘着粗气”。黑色带来的压抑即将摧毁诗人的内心,诗人急需寻求光明。《来临》[10]64写道:“明月照临/ 我内心的黑暗依旧/仿佛积雪难以渗透的煤炭/保持着岩石清醒与痛苦的棱角。”即使明月朗照,“我”仍选择在黑暗中保持对生命、对世界的敏感与思考。即使黑暗弥漫于无限的时空带来痛苦,但诗人痛定思痛还是选择身处其中,因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一段又一段的苦痛体验给诗人带来的疲倦,唯有黑暗才能将其解脱,也唯有在黑暗中才能安慰诗人的灵魂,给予诗人思考的空间。
诗人对自己的内心不断叩问,对日常存在保持敏感,使他不至于冷漠和麻木。因此,“黑色对诗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恐惧,还意味着庇佑,是他能够与自己心灵对话的避难所”[6]83。当诗人与一只“通体的黑”的蚂蚁共度了彼此生命的短暂时间后,他在诗歌《来世》[10]149~150中巧妙地将黑色具象为一只“蚂蚁”,并利用对比修辞,尝试从黑暗中解脱。“一只蚂蚁/它通体的黑/或许由一个人前世全部的荒唐和罪孽造成/它不会知晓/也不会用文字记录情感”,蚂蚁没有感情,在现存世界中往往如尘埃般被忽视,可当无限的时空聚焦在一只“通体的黑”的蚂蚁身上,它们是那么的“纯粹/自在”。它们的欲望是有限的,没有人的儿女情长:“不似被一代又一代的情种挖成寒窑的月亮/会引发冲垮海岸的潮汐”;也不会执着于功名利禄:“在日落中/它所看到的/不会是痛苦的黄金”,蚂蚁在面对生命的本质——活着时,仍然自由地享受生命的本然状态,执着地用触角“探向未知的境地和它本身的命运”。整首诗以小见大,将生命放置在更广阔的视角下,把一个黑点无限放大,延伸至主体、整个世界乃至指代抽象的生命,蚂蚁身上有限的“黑”与未知的世界与命运无尽的“黑”作对比;蚂蚁的渺小与生命的脆弱、世界的强大作对比,把自然之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为人的生存探寻到了答案——面对人自身的脆弱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蚂蚁仍能用纯粹自在的触角去探索未知,人又何尝不能以蚂蚁的方式生存。
古马以黑色构筑诗歌语言色彩美的同时,也是一种略语,直击他灵魂深处的秘密。黑色作为古马生命体验的象征符号,在陌生化、宏观化与具象化等手法创造的幽冥诗境中,构成了一幅复杂又和谐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每一个元素都产生于一种自动的、无阻止的,然而又是受到控制的神情集中的内在过程”[11],成为沟通诗人与读者、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自发地承载着古马对自我灵魂的忧思。
二、红色:于炽热处赞美生命
古马的个人阅历,以及他骨子里透出的西北汉子的坚韧、宽厚与勇毅,使得其诗歌带有西北民间传统文化气息,尤其表现在他对生命的崇敬与顽强的生命意识上。同“生命”一词最为接近的颜色便是“红”。在希伯来语中,“血”与“红”本就是同源的。在爱斯基摩语中,红色从字面上直译过来是“像血一样”。这两种经验在所有的文化和时代都有存在的意义,此象征性意义也相应深刻地扎根于意识之中。古马诗歌利用不同明度的红色投之于他眼中的生命,执意地找回原始生命的魅力。“鲜红”与“暗红”等色调为古马视界里的客观之物着色,共同“吹奏低音的关怀”[12],指向勃发的生命力与顽强的生命韧性。然而,古马绝不是沉溺于自我世界狭隘地抒情,“西部地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方面交互早已化作古马的骨血”[13],使他的诗歌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中流露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价值。
明度作为色彩运用的重要一环,极大地影响着画面的氛围和感情的基调。相同颜色或明或暗会形成对意境的互相阐释,不同明度的搭配则会给读者带来视觉的冲击,色彩明度的变换会形成巨大的表现能力与空间流动感,从而引起情绪的起伏。古马借用红色的明暗交织与纯度调和,在红色的动态转换中完成对生命的描摹。古马常用鲜亮的红色塑造强烈的视觉体验,彰显年轻生命的活力,譬如《冬旅》[7]76中,“年关近了/黄昏里次第亮起大红的灯笼//红光映雪,木栅低矮/炊烟熏醉山头的星星/醉了的,还有那明天将要合卺的新人/他们将要交换瓢中清水,庄重饮下/看见自己喜悦的泪花,出自对方眼中”。诗歌用鲜亮的红色衬托两个喜庆的日子,一方面,大红色本就是中国的传统色彩,用红色装饰新年是传统习俗的缩影;另一方面,古马用红色预示着吉祥、幸福、新生与希望,暗示着两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孕育出的生机。诗歌色彩浓厚,“大红灯笼”仿佛要将村庄点燃,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境界,诗人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将主体情绪的敏锐感知通过颜色展现出来,使诗本身也生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民歌》[9]203以色写人,形神兼备,颇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诗人用红色奠定了全诗明快、喜悦的基调,也意在通过新婚的喜庆表现生命的勃勃生机。“急的是/偷扯了一把火烧云揣进怀里的人/那红到耳垂的云/红过半分就是大红的盖头/红过一分就是抖开的红绸/红绸抖开/大红被子暖和的风”一句,诗人对新婚夫妇的幸福生活未提一字,而是选取“火烧云”等多种明度相似的意象为新婚夫妇的出场营造氛围,再将红色的明度层次逐级提升至“红绸”“红被子”,以不断加深的红色带给读者感官刺激,画面明快、情感愉悦。诗歌《破冰》也用“积雪”“热血”“太阳”“剁冰取火”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象形成鲜明的红白对比,凸显出个体面对新生活迸发出的生命活力。
同时,诗人也常用明度较低的红色彰显生命的短暂与生命的韧性。“诗,不仅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找回。”[14]面对生命的短暂,古马习惯于站在西部的土地上回望历史烟云,并以暗红色为其附着沧桑之感,以此言说他的无奈与忧思。在诗歌《乌鞘岭》[9]159中,诗人借“彤云”将大面积的红色作为诗歌背景,悲悼英雄生命之短暂。当诗人看着如剑出鞘的“西去的机车”,远处的白马与正午的太阳将他带进另一空间:“金轮轧轧/自河西走廊东端险峰陡岭/一路滚动,滚向彤云红透的西天/——那依旧是霍去病的征车杀伐无阻的影子吗”,漫天的彤云从眼前之景烧至天边,烧开历史的封存,在西北茫茫的黄沙上,英雄的印记终将被黄沙淹没,像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仍逃不过被生命的控制,更何况普通人。诗人悲从中来,就这样思索良久,最终放下执念,回归现实,“金盏菊承露/我的脚边已是星星闪烁灯火闪烁”。诗人由眼前之景回忆历史,最终又回到现实,如此往返交错,将主体在时间面前最终只能化为历史尘灰的无力感层层渲染,悲伤之感也层层加重。《鄂尔多斯:飞行的湖》(六)[9]309因一只蜘蛛勾起诗人的无限思绪。当诗人来到伊金霍洛旗,想起曾经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你瞧,那只孤独的野鸭子/就是忽兰皇后不时翘起的靴尖/倒映的火烧云/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里,灯火依旧璀璨”,现今已人去楼空,只剩下永久的火烧云,剩下“黄昏栏杆上永久的流浪者”——蜘蛛,世人只能在残垣断壁中想象当时的场景。昔日倒映在护栏木伦湖上的“火烧云”与如今的“黄昏”构成时空对比,突出了诗人对历史更替、英雄已去的无限悲凉。
在忧思生命的短暂之余,古马也赞叹着生命的顽强。诗歌《黄昏谣》与组诗《光和影的剪辑:大地湾遗址》都展现着诗人对坚韧生命力的赞颂。《黄昏谣》[7]21写道:“水银泄进麦地/小布谷,小布谷/收起你的声音/最后的红布/请死去的人用磷点灯/让活着的人/用血熬油。”全诗用“黄昏”“红布”“血”三种不同纯度的红色层层递进,活着的人“和村庄隔河相望的坟墓”共同构成了历史,死亡“离过去很近离我也不远”,但即便如此,“我”同现在活着的人也继续“用血熬油”努力且坚毅地活着。《光和影的剪辑:大地湾遗址》[10]18~23则集中歌颂底层人民顽强的生命力。诗歌中由红色衍生出来的“大火”“黄昏”“落日”“血”“高粱”等意象再现了底层人民对生活葆有的坚持与恳切。“落日是飞累的你吐出的一口鲜血”“像是被时间之犁犁掉的先民的手指/把泥土一次次攥出血来”,诗歌底色由红到黑的动态变化是诗人对底层生命的深情注视,在悲悯他们艰难生存的同时,也涌动着诗人对坚韧生命力的敬畏。而《西凉短歌》(十)[7]27则在红色的流动性、变化性、强烈性中逐渐晕染了一个悲凉、哀伤的文本意境,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淡淡忧思,拓展出丰富的想象空间。“一个瘦男子/他指着落日的手指/像失血的胡萝卜/渐渐变黑,风干”,将“落日”这一比红更接近黑的颜色作为底色进行大面积的铺设,在奠定诗歌感情基调的同时又给人一种时间流逝的苍凉之感。“失血的胡萝卜”比喻本就生命衰微的男子的手指,“渐渐变黑,风干”则将画面的层次感展现出来,表面上写出颜色的变化,其实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流逝之感,体现着诗人面对个体对于生命的无法控制,当生命的有限性与时空的无限性之间产生矛盾时所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力感。
生命在时间上的短暂性决定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无休止的变化”[3]79,诗人古马却刻意疏离了生命在客观意义上的短暂,意图以诗意的语言维持生命在形式上的永恒性。面对生命,古马借用“红色”的色彩特征,或延续人们的固有经验,或打破日常经验,变形、拼凑并重组新的意象,造成诗歌明显地脱离日常,进入哲学的境界。古马将西部历史文化的厚重与人们生命的坚韧不屈熔铸进富有炽热情感的红色之中,诗人以此赞美生命的本真、奔放与坚毅,谱写了一曲热情奔放的生命赞歌。
三、白色:于澄澈处彰显人性
当古马从现实世界的喧闹、焦虑与迷茫中归于平静后,他也在积极寻找人性中的静谧与安宁。或许黑色过于冷峻、红色过于热烈,在古马眼里,白色通过与黑色的对比而被理想化,如同他笔下的“月光”一般明亮澄澈、温暖纯净。古马将内心的理想与柔软附着在“白鸟”“白杨”“白莲”“白云”“月光”等意象中,试图在白色的澄澈、宁静、纯洁与质朴之下,构筑起心灵的乌托邦。诗人不仅追求诗歌意象的纯净与洁白,还追求诗歌语言的不加修饰,意图在内容与形式上创造出融合了诗人独特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的澄澈之境,隐喻出人性的温暖美好与纯净本真的同时,也回归到诗人内心对纯洁、本真的追求,以及至真、至性、至情的诗性思考。
诗人内心是柔弱的,当他面对亲情、爱情以及友情时,既含着几分羞涩甜蜜,又显现着西北汉子的豪爽,这种既羞涩又浓厚的美好情感在自然的纯粹与静谧间娓娓道来。《西凉月光小曲》[7]22就以含蓄的笔法用月光描绘了一幅温暖却又哀伤的画面。一方面,月光在诗中是情感的储存,已战死在沙场的将士只能化作柔柔月光回到心爱的女子身边,用月光的纯洁象征着男子与女子之间爱情的美好纯粹;另一方面诗人借月光赞美人与人之间温暖感情的同时,也用月光的惨白隐喻了男子与女子之间终究不能团圆的爱情悲剧。整首诗歌在隐隐月光的照耀下流露着淡淡的忧伤。
白色意象在古马的诗歌中也常被用来指代亲人间的情感。诗歌《雪乡》[10]73~74借“雪”的白与母亲的“白发”做联想,利用月光与雪的纯净映衬母亲的温柔与诗人对母亲深深的眷恋。“白雪覆盖的冬小麦/那些地底下的人/愿他们睡得甜美/永远不再醒来”,由此闪回到从前,那在雪下睡着的还有诗人的母亲,她也曾是“早起扫雪的新媳妇”,“她爱着沉睡四野的白雪/她爱着白雪爱着美好的生活”,在诗人的心中,母亲有着如白雪一样纯洁的心灵,唯有白雪可以覆盖母亲的灵魂。全诗时空交错,先眼前后回忆,充满诗人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之情。《青海的草》[7]8写道:“二月呵,马蹄轻些再轻些/别让积雪下的白骨误作千里之外的捣衣声”,将“马蹄声”与“捣衣声”交织在一起,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去感受征战沙场的将士与母亲之间割舍不下的思念,“白骨”一词则又为母子情抹上了悲伤的色彩,短短二十多字就将诗人悲天悯人的气质晕染开来。
白色还隐喻着诗人对纯净内心的追求,字里行间闪烁的温情时刻审视着诗人的内心。在诗歌《山隅》[10]187中,古马将诗歌的感性与情感的理性表达付诸于“天空”“云”“卷心菜”等意象所带来的想象空间中。古马化身为“对景写生的画家”,通过自然意象的“转场”将“溪水潺潺”“天空的蓝和云朵的白”联系在一起,在动态与静态的交织中以白色独有的纯洁隐喻诗人内心追求的纯净、简单与质朴。整首诗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真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间隔,形成了自然意象与诗人情感的呼应与互释。诗歌《净月》[9]67~68语言简单质朴却富有韵味,整首诗以叙事的手法将自己看见月亮一刹那的情感缓缓道来,借由一再被强调的月光传达内心的纯粹与坚持,情感真挚、感人肺腑。“浑身烟酒气味的我”回到“居家的小区”,满身风尘,疲惫不堪。“偶然抬头/楼顶的月亮/就像一片药/就像十全十美的童年/胰子在母亲手里/那么白净/就像/我拾过杏花玩过泥巴的手/那么白那么净”,月光洒下的一片白净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带着诗人回到过去,想起童年,其实想起的是那时的快乐、单纯与温暖,那片白净也代表着诗人内心守护着孩子般的天真纯洁。“‘月亮亮/月亮光/开开后门洗衣裳’/我要流泪了/我逼迫无声的泪水/倒淌回脏腑/洗涤我心”一句,月白与今日的昏暗、母亲与童年的我、在耳边回响的昔日歌谣等事象与物象在诗人抬头望月的一瞬间交织在一起。视觉与听觉、时间与空间被诗人同时调动,使眼前之月亮、自然之时空、内心之遥想暗合,更加让人心中摇摇、思绪无尽,最终化成“无声的泪水”“洗涤我心”。在诗人笔下,月白就是对自我的审视,唯有内心纯粹才有资格拥抱这片白净,这片白净净化了他的内心,同时也是对他灵魂的拷问。
组诗《煨桑》[10]132~134纵使没有频繁运用白色渲染,却富有深度和力度。“洁白的花朵半夜涌现/在孽障人的手指/阿弥陀佛”“柏烟缭绕——漫长的有缺陷的今生/让我们如蝼蚁一般完整的度过//来世的白莲/还让我们如蝼蚁一般/抵达它根部”。人的生命犹如蝼蚁一般渺小又短暂,能被赋予如“月光”“白莲”这般无暇色彩的仅是内心纯净、朴实善良的人。那些被皎洁的月光沐浴的文字是诗人执着追求的纯净与本真的内心写照,是诗人所能体悟到的心底的温暖,即使是在“有缺陷的今生”,仍能给予我们追求内心的“白莲”的力量,让我们“完整地度过”一生。诗歌《幻象》[7]32开篇即写道:“积雪覆盖的岩石间/明月,幻化成蓬松而清新的/天山雪莲”,诗人首先以“积雪”“明月”“雪莲”三种自然意象形成物理空间的设置,紧接着以“幻”“蓬松”“清新”形容词巧妙地扩展诗歌的想象空间,在物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映衬、呼应与阐释下营造了一种空灵、纯净的艺术世界。诗歌以“明月雪莲/赤裸着,走进我心里”结尾,仅仅十二个字便将诗人对内心纯洁与干净的追求表露无遗。此诗语言简单易懂,正如古马所言:“语言当如此呈现,不加修饰,直接、质朴,直达心灵,布施光辉。”[15]
在古马的笔下,白色的简约质朴与人性的纯洁美好等修辞联袂而行。古马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明月”“白莲”等由白色延展出的意象,营造了一种澄澈的诗境。诗人将亲情的真挚、爱情的美好以及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纯粹寄托在白色独有的特征之中,既显示了诗人对人性美的追求,也表征着诗人对内心宁静、纯净的恪守,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想要远离世俗樊篱的愿望。
四、结语
如果说,“诗比其他任何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更能把它的过去鲜活地带进现在”[1]14,那么古马的诗歌创作则实现了客观上具有稳定性的色彩与诗人的生存经验间的“通灵”,形成超越现在、过去与未来的跨时空交流。在自然生态、地域历史、多元文化共同孕育的西部诗歌群里,古马以诗人的身份与画家的眼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正如胡戈·弗里德里希所说:“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16]在西部这张干净又辽阔的画纸上,古马常用隐含着黑、红、白等具有色彩内涵的词构建诗歌的氛围,将自己的诗歌调和成一幅幅心灵悸动的图画,为日常生活赋予具有隐喻特质的审美意义。黑、红、白三色并非仅停留在简单的修辞层面,古马用它们建构出了诗歌幽冥、炽热与澄澈的审美意境,以此呈现生活的内在肌理与生命的脉络。在古马的诗歌中,色彩以直接的视觉冲击与强烈的想象意味,帮助古马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古马也在敏锐的色彩感知中舞动着诗歌的张力,诗意地重构现实世界。纵观古马的诗歌,诗人在“向内转”抒情的同时,也关照着生命的活力与韧性;在疏离日常的同时,也深入生活,关注着人们与生俱来的悲痛、爱、恨,追求人性的美丽与光辉。由此看来,古马诗歌中的色彩书写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是诗人感性世界的载体,是其诗歌创作里藏匿着的一个升腾的灵魂,让读者在感受视觉冲击的同时,可以触摸到诗人内心的柔软、细腻与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