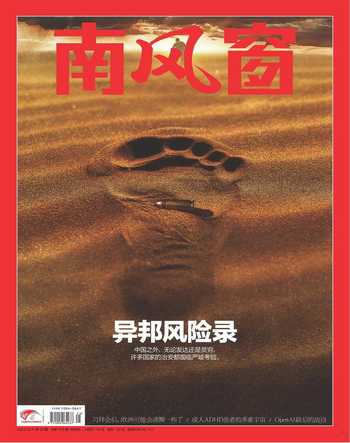长治久安,秘诀在哪里?
谭保罗

如果要列举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那么中国一定是首屈一指的。很多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甚至是西方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社会治安的水平也远远不如中国。到这些国家旅游或者商务考察,旅行者基本不敢“露富”,不敢把自己的新款手机放在显眼处,更不敢把名牌包轻松地挎在肩上。
更夸张的是,在一些特定城区,你都不敢穿好一点的运动鞋。因为,当地年轻人痴迷于搜集某些特定品牌的运动鞋,特别是那些100美元以上的款式。然而,他们没有工作,只有一身发达的肌肉和无处发泄的荷尔蒙。为了一双鞋,他们可能突然对你发起袭击。
也就是说,治安这个问题,它和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并非是一种完全的对应关系。那么,治安好不好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因素有很多。从大的层面来说,国家治理的良好,特别强大的财政能力带来对社会治安支出的慷慨投入,以及科层治理的严密性和社会管理的高效率,必然是社会治安良好最容易被理解的原因。
文化传统也很重要。比如,巴西的人均GDP早已达到9000美元的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中亚国家,然而在中亚的城市旅行,安全系数肯定要比在里约热内卢高得多。很多中亚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还经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时代,这使得它们的社会文化传统截然不同,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治安水平全球顶尖也不难理解。比如,在中国的文化中,“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直被视为社会安定的理想状态,这其实代表了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稳定和宁静的状态,是对社会治理状态的评判标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
国家治理和文化传统,无疑是决定治安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但这一问题也可以换个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毕竟大多数人的行为,最终都是靠着经济激励,而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则是最现实的心理约束。
穷人和通胀
不少人对国外一些地方治安较差的印象,多半来自三个途径:一是传媒,二是出国旅行的感同身受,另外一个则是影视作品的影响。
通过这些途径获取的印象,可能会让人对社会治安水平较差的原因形成理解偏差。比如,某些国家虽然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但贫富差距大,社会治理失败,政客只关心选票,而根本不关心非票仓地带的治安问题;或者,在旅游景点的“犯罪分子”都是外来移民,其他地方还好。
影视作品带来的理解偏差更需要纠正。“黑帮火并”和“打劫银行”是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两种名场面。为了增加可看性,这样的场面被设计得极其火爆,参与者都一表人才,有的还是科技怪杰或者退役特工。总之,情节设计得让人印象深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对国外治安问题的理解。它让人误以为,治安问题的表征充满了极端现象。
货币快速而剧烈的贬值,会让很多人无法安排明天的生活,当生活资料的获取失去了可掌控性和可预期性,那么实施“超短期行为”—抢劫或盗窃就具有了吸引力。
实际上,在一些国家最常见的治安问题,并不是“打劫银行”那种极端事件,而是一些看似日常的行为,比如抢劫或者行窃。换句话说,这些行为并不是要挑战现任政府权威,或者通过非法手段实现一夜暴富,而不过是一位青壮年要维持日常基本物质生活所致。让人铤而走险,通胀可能难辞其咎。
在国外一些地区,穷人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没有抵抗通胀的资产,比如房产、优质的债券和股票,以及家里存放着的美元和黄金。穷人不但没有好的资产,可能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即使有临时性的体力工作,老板也并不会根据通胀指数进行定期涨薪,这意味着他们对物价变化的敏感程度超乎想象。
巴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从 1980年代开始,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枪战、贩毒、抢劫每天都在发生。如果衣着华丽,尤其是带着高端相机希望拍照的外国游客,一定要到此一游的话,那么必须在警察的陪同下才敢深入这些充满暴力和毒品的地带。
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故事被全世界知晓,但很少有人注意,贫民窟治安的恶化和巴西的通脹大爆发,在时间上是高度重合的。1981年开始,巴西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胀。
1981年,由于债务危机爆发,巴西的GDP增速从接近10%,降到了负数,即经济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通货膨胀率开始飙升,整个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都是巴西的高通胀时代。这一时期,每年的通胀率经常高达100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薪酬提升不和通胀率挂钩,那么很多白领的物质生活保障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贫民窟的底层家庭。
另一个因为治安问题而被人熟知的地带是非洲。非洲一些国家被全球的经济学家视为主权货币失败的典型,比如,津巴布韦就以超级通胀闻名。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但凡那些治安较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多半都有严重的通胀问题,穷人往往朝不保夕。
在非洲投资的一些企业家发现一个有趣的观察: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如果放弃当地的主权货币,在交易中使用欧元、美元或者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那么当地的经济往往发展更好,普通人的生活也更稳定。因为,这些强势的国际性货币不会导致严重通胀,会让企业家和普通人对手中现金的价值,以及对未来生产生活都有明确的预期。
通胀对穷人的杀伤力是惊人的。从常识来说,货币快速而剧烈的贬值,会让很多人无法安排明天的生活,当生活资料的获取失去了可掌控性和可预期性,那么实施“超短期行为”—抢劫或盗窃就具有了吸引力。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这种行为也并不算是某些人在高通胀之下的最坏选择。于是,治安问题便拥有了一种社会心理结构上的内生机制。
对任何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治理通胀都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要发展就容易经济过热,当需求增加超过了供给,那么通胀就上来了。但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国。中国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伴随长期的高通胀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那么,中国的秘诀在哪里?
城市化和工业化
近年来,中国的通胀率长期保持在低于3%的这一合理水平。合理的通胀,意味着适度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会推动企业家扩大再生产,而消费者或者说工薪一族,也可以理性地预测自己的财务前景。
但不能忽略,在1980年代末期,中国也出现过比较突出的通胀问题,最严重的时候,通胀率超过了20%。虽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高通胀相比,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也对当时企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影响,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开放,通胀率降了下来。
纵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通胀,给中国的经济治理带来了一些教训,也是经验。之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直都将CPI视为极为重要的指标,时刻保持紧盯这一数据。某种意义上讲,必须将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金融纪律。
一般而言,当通胀率超过5%,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明显的现金贬值“痛感”。这也是很多后发经济体因为无法控制通胀,给国民生活带来严重冲击,进而给社会治安带来困扰的原因。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值得很多后发国家参考。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房子这种特殊“商品”之外,如果拉长时间到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看,中国人的收入增速是高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增速的。这一点,从普通人的肉类、奶制品摄入量一直在增长,就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中国是如何解决通胀问题的呢?这必须和影响社会治安水平的另一因素—城市化,结合起来分析才行。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平衡,带来城市就业岗位的增速大大低于人口集聚的速度,必然导致地理空间上犯罪行为的易生性和集聚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基本上所有以黑帮和犯罪组织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发生地多半都是位于城市的特定区域,比如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贫民窟,还有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特定街区,比如纽约意大利裔集中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很多都没有就业机会,要么游手好闲,要么做起了影响治安的那些行当。
换句话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平衡,带来城市就业岗位的增速大大低于人口集聚的速度,必然导致地理空间上犯罪行为的易生性和集聚性。一些数据让人吃惊。比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85%,而早在1990年,巴西的这个数字就已经是70%,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准。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超过了中国(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5.22%)。比如,利比亚城市化率是80%,而南非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也达到了68%。
城市化率的计算,以城市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基准,并不体现居住质量,更不体现背后的就业质量。因此,在很多特定情形下,这个数据可能并非一个正向的指标。
2022年,我国的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33.2%。而拉美和一些非洲國家,尽管其城市化率高于中国,但这一指标却远远低于我国。比如,巴西近年就稳定在20%的水平,并且还出现了下行趋势。
城市化必须和工业化同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除了日本等少数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和经济体,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作为一个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农业都是收入最低的行业。因此,一旦人口流动管制解除,农业人口就有天然的进城诉求。无论拉美、非洲,还是东亚,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通过工业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让进城人口得到足够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放弃“超短期行为”,而是选择“长期行为”,通过计酬的正当工作来改善人生和家庭。
如果城市化大大超前于工业化,再叠加金融治理失误带来的通胀,那么治安问题就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病。经济治理的逻辑十分简单,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所发生的奇迹,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同时,也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非凡事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通道中,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成功破解通胀难题,最终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无疑为很多后发经济体提供了极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