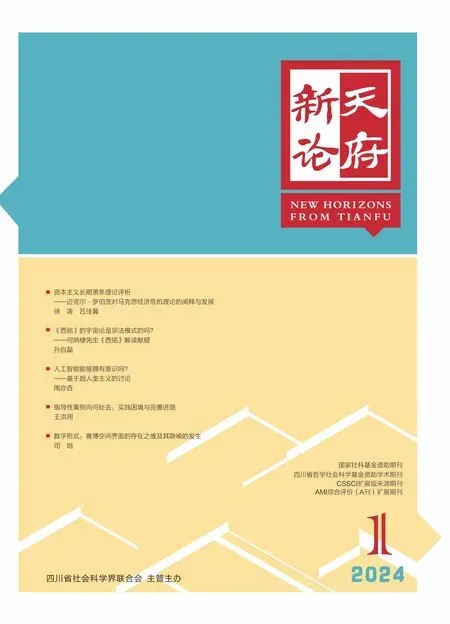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
——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王羿龙
自宋代提倡《大学》以至于明代,儒者对本体论不断予以申说和深化,“内圣外王”的工夫论被重新发扬,道德关怀逐渐成为儒学的核心。在这一关注下,不仅个人道德被视为是否有利于国家、天下的重要枢纽,而且士人的聚焦点逐渐从外界的规范转移向自身的道德。有学者将这种转向视为个体与国家相分离的契机,并称之为“新儒家个人主义”。在这种论说中,通过对自身道德的关注,“英雄的事迹”与“自我牺牲的殉难行为”成为士人临难之际“自我陶醉”“自我怜惜”与“自得其乐”的重要寄托。(1)参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中华书局,2016年,第94页。这一论断固然倒置了求道与自得其乐的本末关系,但就宋末、明季士人殉节异于前代的史实而言,以道德为核心的思想转向促成了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产生。与之相表里的是对名节的关注。名节观念作为士人处变之际的原则性问题,随着王学对良知本体的崇尚与对仪文度数的忽视,在由宋至明间人们的名节观因之发生转折,并对晚明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将“名节”作为立身之本仍为多数士人所坚守,但王学内部的活泛与争讼,不但打开了名节与道之间的缝隙,还因对“名节”一词中潜在语义的表彰,引发了明季士人在实践层面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
就明季殉节作为一种现象而言,一方面,历代士人的出处与生死在不断的重复与诠释中被赋予了层累式的意义。经由元、明士人对宋季诸公的追溯与模仿,宋季殉节不论是激烈程度还是殉节人数,在后世往往呈现为一种“想象”或“虚像”;这种虚像本身即可视为道德严格化的具体表征。(2)如熊燕军便将宋季忠义视为一种“虚像”。其原因之一在于,这一“虚像”是经由包括元修《宋史·忠义传》在内的后人书写放大后的结果。诚然,《宋史》“(厓山一役)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的说法似以为十万人皆自决于战败之后,固是夸辞;《忠义传》中著录77位宋末殉节者,其数量亦远超历代。这一著录选择当然可以代表元代史臣的趋向,但并不意味着宋季的忠义就是全然由其所放大的“虚像”。值得关注的是,《昭忠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殉死者的著作出于宋季遗民之手,这至少意味着,作为一种现象的殉节或死难开始进入士人的视野。一方面,文化显现大多源于现实差异,借此可以推测其时殉节人数大概多于前代;另一方面,此书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代表其时士大夫的共同关注。参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45页;熊燕军:《宋元易代与宋季忠义人的历史书写——以〈宋史·陈炤传〉立传始末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够在嗣后数百年间被不断地重复与诠释,也正源于传统语境下士人对忠、孝的崇尚。在这种意义上,“层累”这一行为本身即可以代表中国士大夫以儒家为主干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这种更严格的道德标准也经由非道德的刺激而促成。道德与非道德作为同一概念的两个面向,往往相互影响。明末的贰臣群体每为时人所关注,既表明时事的剧烈冲击,也意味着时人仍聚焦于“节”这一概念本身。如在对南逃在京官员处理一事上,弘光君臣之严厉甚至苛刻的条目固与当时党争的复杂背景相关,但道德被当作一种“工具”而得以为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所利用,亦可表明这种严苛在其时已然成为一种风尚。(3)以周钟案为标志,马、阮肆兴“顺案”,可视为与东林相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拟定六等从逆人员名单的过程中,如解石帆(学龙)、刘蕺山等人从轻处之,却与后人平常所见之严峻显然不同。参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221—224页;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1 545—1 547页。
然而,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政治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自身所带有的政治遗民与族群遗民的双重属性往往与历代遗民有别。由于“遗”介于过去与现实、生与死之间,他们对贰臣或变节的诋责有时隐含对“罔死”的批评。一方面,过于严苛的评价挤压了士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明遗民也借此达成对阳明以来明代学术的检讨。他们在关注“名节”自觉性的同时,重新梳理它作为一种“节”的对外和对内的两重含义,不仅用以树立一种模范或典范,而且通过对死节与名节的分别而为自身的生存撑开空间。
一、王学与“节”的两极化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对“是非”的认知在由宋至明间发生了转向。宋人对忠贞与变节的看法仍然因袭了前代的观点,似尚未形成特殊的评价方式。虽仍有效死者、遗民与贰臣的区分,但士人总体的价值崇尚仍然趋同,差异仅体现于个体行为的抉择上,常被视为阴阳或善恶在人事的自然显现,并未在评价中极于两端。至明季,原本被认为“非”的行为,在王学的范围内被赋予了“是”的可能。不论何种抉择,皆可以从中为自我寻求正当性根据。(4)明季贰臣每以伍子胥、程婴、魏徵、张良、姜维、许衡等为原型自比,即意在通过图功、安民等途径消解传统视域下不可逾越的“忠节”。这皆与王学诠释空间的扩张密切相关。明季贰臣的原型自比可参见刘萱:《复社贰臣的身份认同——以咏史怀古作品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陈宝良认为:“明代的士大夫已经歧为以下两端:一些人‘胡乱说话’,号称‘不拘小节’;而另一些人,凡事无不‘循礼’而行,号称‘道学’。”(5)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节义观念及其行为抉择》,《明史研究》第十四辑,黄山书社,2015年。此种风气固不必至晚明方才形成,但在这一特殊时期,时人将对贰臣的讽刺与忠节相对立,确实证成了其在易代之际的延续。
与宋、元人作《昭忠录》《昭忠逸咏》和以“昭忠”的方式奖忠节而励来者不同的是,明季士人的重点常在于以死节来凸显变节者之众。不论是明季殉节者每呼“以一死而愧人臣之贰心者”(6)江宁武举黄士彩(金玺)语。见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4 765页。,还是遗民作文每言“一脉张不可谓绝,一目存不可谓乱,一夫立志不可谓土崩”“曷不观夫背明而生者为何如”(7)高宇泰著、何树仑附注、张寿镛补注:《雪交亭正气录·自序》,《四明丛书》约园刊本,第1a—1b页。,皆足以证明,明人眼中的“贰臣”或“变节”已然成为一种影响政局的重要现象。

这与王学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可能性”密切相关。在程、朱传统中既定的、明确的标准下,人物各依其职分而行,但在这种谨严的规则之内,个体反而因此获得一种宽容的秩序。士人对此形成了共同的认知,并将其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而遵循。是、非这两个相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皆得到确定:不仅是与非之间界限分明,对于什么是“是”也有清晰的辨说。这种宽容意味着,生与死作为时序上后于守节的问题,并不足以构成对是否守节的质疑,故尚未为宋人所争论。此时,生与死皆与守节并行而不悖,生死问题既未成为一种时代现象,亦不足以被纳入士人的讨论核心。
与之相对的是由王学开出的新的路径所带来的争讼。致良知被视为一种“权论”,当属王门学者的共识。(9)如阳明即谓:“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后学邓定宇亦以为是“权论”。参见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7页;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在这一语境下,但察其于心、理,而不求之于经典,原为宋人所慎的行“权”为大贤以上事的警惕或被忽视。(10)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 380页。原本固定的、常行的“经”被打破,当士人倚靠这种“权”为准则时,也就意味着原本应当被遵循的规则都可以此为借口而被破坏甚至非议。同一种“崇尚”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为士人拓展选择的同时,使每个个体陷入困境或牢笼中,反因此种选择的空间而至于两皆不可的两难境地。宋季奖死善生、励节耻降的风气于此时转换并被讨论:死者耻生者之贪生,生者责死者之罔死,遗民痛贰臣之失节,贰臣讥遗民之泥古。在生与死、守与变之中虽仍有一种崇尚死节和守节的根底或风向,但这种争论的出现即意味着,以士人的选择为核心,在传统的死节与守节之外打开了另一种正当的可能性。由此导向的对外界规范的忽视乃至鄙夷,为士人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它不必然指向殉节或变节,但至少意味着每种选择都可以因此获得一种正当性说明。
是与非的边界相对模糊,对于什么是“是”的争议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期引出不同的选择。对士人的选择或观念而言,王阳明无照无不照、无善无不善的逻辑,必至于无可无不可、无是无不是的境地:且不论其所指,但“照”与“不照”、“善”与“不善”、“可”与“不可”作为概念即能指而言是两两相对的,以无照则无所不照、无善则无所不善来推论,通过消解“照”和“善”作为一种实体的意义,从而将其导向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内涵。无可无不可的流衍则更甚:它不仅具有无善无不善的形上依据,且足以影响士人的实际取舍,甚至可以说,不论是江右王门的苦修工夫还是浙中王门的放浪形骸,这种极于两端的工夫论都是根于此种论断——惟心斋之流为害滋甚,尤为人所诟病。(11)如黄宗羲即谓“王门惟心斋氏盛传其说,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学乐’,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申言之,当所有选择都被纳入“可”的范围时,同时也就意味着它都是“不可”的:没有由“不可”所照应的“可”,则作为确立自身存在的表征,是、非间的边界因此而模糊。此时,“可”已然与“不可”同质化,不仅丧失了其自身作为“可”的意义,亦必然会有导向“不可”的可能或倾向。这种介乎“可”与“不可”间的张力固然只是一种争议或空间,而不足以将事物皆列于“不可”的范畴,但作为选择而言,解释空间在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士人选择空间的缩窄。当作为概念的“可”与“不可”失去自身的立足点时,也就使其所指称的行为失去了既有的价值判断。此时,陆王学者自信的易简工夫因失去规范,适以导致聚讼纷纭,这种看似宽容的选择空间,在“无可”的论述之下,有时却带来了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与评价。
二、工夫严峻化:趋向死节的名节
自欧阳文忠为《五代史》作《死节传》以来,“重节义”的影响直通明季。这与对五代时冯道等人不重节义、甚至耻语节义的反思密切相关。宋以后,多数学者都强调理学对士人名节观念的影响。(12)如左东岭即认为“程朱理学的确对士人自我节操的培育具有很大的作用”。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8页。后世士人在议论宋季死节时,其核心皆在于名节或死节本身之可贵。不论是毛奇龄对宋季殉节一案的非议,还是全谢山的回护,其潜在语义皆在于“学理应当至于名节”或“学理可以至于名节”。(13)参见全祖望:《答诸生思复堂集帖》,黄宗羲著、全祖望修补:《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 436—2 437页。全祖望:《九灵先生山房记》,转引自钱穆:《读〈九灵山房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与汉、唐所带有的功利主义倾向不同,作为合于外部规范的重要途径,修养逐渐为宋代儒者所重。此时,士人自身的道德品质被认为是其功效得以成立的本质原因——这也是自宋以来儒学以道德主义为核心的重要根据之一。宋学逐渐摆脱了汉唐以来以绳墨为规矩、以科条为法令的传统;上体天道,转而内求,也就意味着原本被歧为内外两端者得以被勾连成一个整体。宋、明士人乐称“平居有犯颜敢谏之士,则临难必有仗节死义之臣”,依托于对经权、道器关系的重构,被汉儒视为两截者,于此皆被纳于同一规范之下。
一方面,“犯颜敢谏”与“仗节死义”被视为士人所具有的同一种性质在平居与临难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体现。宋儒反对汉人“反经为权”的观点,作为能指的“权”与“经”开始交叉,两者的概念边界逐渐模糊。此时,“权”与“经”不仅具有变与常的特质,且“权”常被视为“经”在特殊时期的显现。所谓“权只是经”(伊川语)(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权”在被释为“经之变”的同时,在经学语境下与“经”相对(即“反经”)的意义被消解,“权”与“经”两者的概念趋于一致。在这种语境下,客观的、独立的天理被凸显,而借由这一“天理”的统合,也使得处变与居常的工夫逐渐趋同。
另一方面,使一事有一理,则一事有一事之工夫;但在程朱学者理一分殊的论说下,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5)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将工夫收摄为一,以心论为纽结。未发工夫既可达于已发,则自平居之常亦可以窥测其临难之变。朱子谓“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封事》,《朱子全书》第二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4页。,约为此义。此时,经权、内外、道器皆非两截,合权于经、合外于内、合器于道,两种概念的疆界被打破,从而导向了一种统合式的一致。如视平居类同于经常或未发,视临难类同于权变或已发,则内在理路确有相近之处。
但相较于宋儒双向提举已发、未发,必置未发于已发之中、言已发于未发之时,受王学及江右学者的影响,在晚明时形成了一种苦修式的工夫。他们一方面延续了宋学以来的传统,以名节可以统贯常变,言路之苛刻与殉节之激烈确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另一方面,自阳明以求生死贯彻致良知以来,“涵养须用敬”或被忽视,以处变者处常已成为其时士人之常谈。(17)“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王守仁:《次谦之韵》,《王阳明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64页。“千古学术,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违,不违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独。”王畿:《水西会语》,载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242页。以对《论语》“无终食”章的诠释为例:
言君子为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存养之功密,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
此章只是教人安贫贱而不易所守。于此不处,即是于彼不去。必双提富贵、贫贱两关者,欲即此以勘此心欲恶之几,乘于道与非道之辨,十分清楚,而后谓之仁故也。造次亦就贫贱说。……或问:“何以知终食亦说贫贱之终食?”曰:富贵既不处,贫贱既不去,则此一食之顷,果在何地?“然则注有添存养之说,何如?”曰:存养之功,亦即在取舍之辨上见,非有二也。以为能为仁而后能贞遇者,亦非也。陈白沙先生曰:“名节者,道之藩篱,藩篱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见道之言也。(蕺山)(19)刘宗周:《论语学案·里仁第四》,《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朱子之“无时无处”,至蕺山已为“安贫贱而不易所守”,由终食、造次、颠沛间的渐进加密,至蕺山,三者已皆就贫贱立说。(20)参见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9页。“无时无处”自然显现为居常用敬,于此被导向一种险绝的境地,即就“无时无处”自身而言,也在有意无意间被忽视。蕺山对“添存养”的认知核心即所指与朱子并无二致,都将取舍与存养视为变与常两种境地下的不同显现,但蕺山所重既在于“取舍”与“贞遇”,则两者的能指已然不同。强调人在贫贱或危难等“变”的境遇下选择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将这一境遇日常化,提倡以“处变”的方式“居常”。从工夫论而言,这与宋人将居常、处变视为一理之下的两种状态确有不同。由此引向的更为严峻的工夫在临难之际可能会为士人趋死提供某种“鼓励”。不论居常或处变,明儒既已倾向以一种艰难的方式磨砺品性,则在两可的抉择之中,往往会走向更加激烈的一端。
从分别常变到视变为常,这一路径与宋、明儒对善、恶的观念歧异亦相一致,可视为王学形上化或本体化的重要思路之一。王学学者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21)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的论述中,对“至善”作为“道理”或“天命之性”而非善恶之“善”的强调,忽视了至善作为善恶之“善”的意义。就所指而论,与朱子等宋儒固无差别,但至善在形下的当然显现既是善而非恶,适成就其为“至善”,而非“至恶”。王学道德严格化的表征之一即在于,对“非圣人则非人”的强调会导向一种非善即恶的两极化论述,从而将原属于善一边的“过”与“不及”皆视为恶。此时,与天理统合下的变与常向“变”的转换类似,至善统合下的善与恶逐渐向“恶”倾斜,“恶”在成为善的另一种形式的同时,也因之与“善”相对立,原被宋儒视为善的不完全的恶,于此成为与善相对立的一种概念而为明儒所重。换言之,明人聚焦于“恶”,既成就了其以《日录》等形式为代表的“克己” (而非涵养)工夫;同时,恶与变作为有著于形貌的、易为人所体察的形式而为明人所重,也使得这种已在道德严格化视域之内的“克己”工夫愈加严峻。出恶于善,即如出变于常,两者皆出于同一种逻辑思路,而将宋儒重善端、添存养转化为一种求末的险绝工夫。从这一点来看,阳明以来求生死的路线正与其本体论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明季士人对生与死孰难孰易的意见未必统一,即殉节者如祁忠敏亦言“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22)祁理孙:《先大夫世培府君殉节述》,弘光元年(1645)自刻本,第7a—7b页。,但以此而言,殉节者之所以选择死,恐并非如何冠彪诸人所言在于舍难取易(23)舍难取易说参见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4—45页、第146页、第206页。。相反,有得于一贯之工夫与选择之惯性,明季士人常于非必死之死处为自我之死寻求正当性——即所谓求其难者。城守者之死于城、居朝者之死于位固不必多言,基于道德主义下对自身行为的正当性论说,布衣殉死与士夫相约殉节,皆在传统的“名节”之外开出更为广泛的殉节缘由,亦可见严峻工夫在临难之际的重要影响。(24)以目前有名姓的记载而论,宋季殉死布衣凡83人,占总人数456人的18.20%;明季殉死布衣凡4 425人,占总7 611人的58.14%。由此可见布衣殉死的差异。又,明季士人父子、师弟、朋友、夫妻间相约殉节所见不鲜,如王玄趾投水而致书其师蕺山以速其死,夏瑗公约友陈卧子同赴嵩塘,高鲁瞻(岱)、高朗父子先后自靖,乡约谢鹏登暨妻杨氏同殉。按:宋季数据据《昭忠录》 《钱塘遗事》 《宋史·忠义传》及《宋季忠义录》整理而成。时间上据《昭忠录》,溯至绍定间(1228—1233),下迄于谢叠山之死(至元二十六年,1289)。明季数据据《自靖录考略》 《雪交亭正气录》 《续甬上耆旧诗》和《明清史料》甲编、《明清史料》己编及《南明史》整理而成。时间上溯至崇祯十七年(1644),下据《南明史·周玉传》,迄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吴十八起义殉节。
如果我们可以肯认,士人平日之工夫足以显现于处变之际,那么在宋、明两朝末期殉死风气的差异上亦可以见出其学术影响之不同。宋儒之添存养与明儒之求生死,工夫既已有异,在殉节一案确已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趋向。物来顺应与居易俟命使得宋人固守自身应守之职分,殉节者固不避死而逃,亦鲜有主动求死者。此即张南轩“君子不避难,亦不入于难”(25)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岳麓书社,2010年,第840页。之义。明人则不然。与文山入狱唯不自杀不同,一方面,“自杀”作为明人自我终结的重要方式有别于宋人,另一方面,如被俘后曹兆京三上《请死书》(26)曹大镐:《化碧录》,《贵池先哲遗书》刻本,《丛书集成续编》第一百五十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23页。,瞿文忠谓“求死无门”(27)瞿式耜:《东日堂诗》,常熟图书馆藏永历瞿昌文刻本,第34a页。,张苍水谓“莫谓轻生易,应怜速死难”(28)张煌言:《张苍水集》卷四《采薇吟》,《四明丛书》约园刊本,第6b页。,求死或速死对于几乎处于必死之地的明人而言仍是有意义的。更遑论明臣被俘后清人首要在于防范其自决,而不论殉节者或遗民,亦多有祈死待尽者。这一行为关乎明人一种严峻的工夫论,既可以彰显其人之志向,又足以体现其时包括尚死在内的一种严格的士风。
相较于宋人,明人面对临难时的态度由被动转向主动,甚至由不避转向祈望,显然与其求生死的风向紧密相关。如赵园所言,可不贫之贫、非必死之死已被视为成仁的必由路径;(29)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同时,也就意味着不贫、不死处已不足为士人立节,平居之富、临难之生不论在何种境地下都有被质疑的可能——不论它究竟是否正当。虽不谓富与生必非正当,但在这一视角下,作为一种事件或状态的贫与死确实被视为“道”的寄托。此时,对人物或事件的评判已不再被追问原因,而经由对“贫”与“死”的强调与对“富”与“生”的质疑,王学的形上化与本体化反而使得道德趋向于一种条目,而脱离了其自身的本体论意义。
三、名节非道:“名节”语义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如以明学作为宋学的开新这一视野来看,由宋至明的过程中,在继承传统名节观并因一种道德的严格化而使得名节被缩紧并几乎被定义为死节的同时,王学自有的诠释空间也让部分后学通过对“名节”与“道”之关系的重塑,而为部分士人“临难苟免”找寻借口。
靖难后方正学诸公之殉节被当今学者视为“儒家之绝唱”(30)有关这一说法的讨论,参见徐立新:《儒家之绝唱——方孝孺悲剧根源剖析》,《台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第123页。,其影响之一即在于直接导致了明中叶以来政治高压下的士风软媚。(31)“是时去建文时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为非。岂非利害之说深溺而不可返耶?”于慎行:《谷山笔麈》,转引自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以陈白沙为首,拒仕固然是士人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但从其对学生是否出仕的态度来看,生死作为一种切己的选择既不必延伸至于他人,则这一行为指向显然在于使一种作为概念(能指)的“士人”从原有的语境中脱离出来。士人不必依靠出仕的方式成就自身,其群体的独立意义得到凸显,隐逸也被视为在治统下重立道统、为士人在出仕以外开辟存在空间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隐逸不仅为个体生存提供空间,也使得“士人”仍足以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而存在。从这个视角去看白沙“名节,道之藩篱。藩篱不守,其中未有能独存者也”(32)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87页。一句,虽然未指名节为道,甚至仅以名节作为入道之门径,但其重心显然在于名节作为“藩篱”所具有的防闲意义。(33)将名节视为一种防闲,其用意与宋人一致。这一点甚至被明人视为宋季多守节者的重要原因。陆放翁谓“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其出于宋儒重涵养之工夫外,还强调了防闲的现实意义。程篁墩在《宋郑所南先生传》中说“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彝伦不坠者,以有节义为之闲也”,显然也将宋季之事归结于防闲之义。陆游:《自勉》,《陆游全集校注》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之十三,嘉靖二至四年(1523—1525)程威等刻本,第3a页。
这一论述在明中叶出现了转向。由观念流行导向社会风气的转变,时间既久,则宿弊纷出。大致在正德、嘉靖间,黄久庵(绾)谓已然形成一种好名尚节的风气。(34)参见黄绾:《明道篇》,转引自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久庵之所以抨击名节,既出于对时弊的反思,也与王学重视形上之理路密切相关。(35)聂双江虽未必如泰州学者之激进,将名节视为不必为之事,但从其“探其中而责其实,要其久而持其归,求其充然有以慰满人望,而无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见一二可数也”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对当时风尚的反思。参见聂豹:《困辨录·辨诚》,载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385页。以对白沙“名节”句的诠释为核心,如谓:
石翁“名节,道之藩篱者”,云藩篱耳,非即道也。若谓即道,然则东汉之名节,晨门荷篑之高尚,皆为得道耶?盖无其本也。(湛甘泉《答王顺渠》)(36)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885页,第873页,第864—865页。
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王阳明)(37)王守仁:《传习录》卷下,《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吾人在世,所保者名节,所重者道谊。若为名节所管摄,为道谊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独往独来大豪杰。(王龙溪《与魏敬吾》)(38)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二,丁宾编,黄玄、张汝霖校,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第2b—3a页。
“名节,吾道之藩篱”,斯语大须味。舍名节,岂更有道?只着名节不可耳。(刘冲倩《证记》)(39)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885页,第873页,第864—865页。
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在对同一理念的书写中,论述重心与切入点之转移既足以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指向。与上节论宋、明工夫论的转向相似,通过构建不同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使得原有的潜在语义(latent semantic)浮现成为主语义(major semantic),为白沙所重的作为藩篱或防闲意义的名节此时被阐述为“非即道”:两者所指固然相同,但聚焦于作为“非道”的名节而非作为“道之藩篱”的名节,则此种能指的转换与其时士风转向互为因果;从王学自身特有的诠释空间来看,亦可谓与王学的形上化、本体化倾向相终始。单提本体,也就意味着一切刑名度数有被轻视的危险。名节所带有的形下性质与其防闲意义既被视为“管摄”或“拘持”,则对形上之道的探求极易以跨越或忽视名节的方式而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名节不但不必是求道的必经之路,甚至有可能成为卫道的缚绳。
这一点也体现在明人追述程子对东汉党锢诸公的评价上:
问:“前世所谓隐者,或守一节,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则不肯守一节一行也。如此等人,鲜明理,多取古人一节事专行之。孟子曰:‘服尧之服,行尧之行。’古人有杀一不义,虽得天下不为,则我亦杀一不义,虽得天下不为。古人有高尚隐逸,不肯就仕,则我亦高尚隐逸不仕。如此等,则放效前人所为耳,于道鲜自得也。是以东汉尚名节,有虽杀身不悔者,只为不知道也。”(伊川)(4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第4页。
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伊川)(41)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第4页。
若谓(名节)即道,然则东汉之名节,晨门荷篑之高尚,皆为得道耶?盖无其本也。(湛甘泉)
程子曰:“东汉尚名节,有虽杀身不悔者,只为不知道。”嗟乎!使诸人而知道,则其所造就,所康济,当更何如?……文成兹旨,岂特不为世道之病而已乎?(周海门《九解》五)(42)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885页,第873页,第864—865页。
然而,程伊川所诃责者在于“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是否“知道”的指向在于士人的具体行为,而非对“名节”的认知或定义:其生死选择究竟是出于亦步亦趋的效法、一时崇尚的风气,还是作为主体的自觉。也就是说,其责备的实质是由于东汉士人之杀身不悔取决于人,并非认知天理后的个体的自由意志,但程子并未否认名节本身的正当性。换言之,倘死于名节出于后汉士人的自我意识,则未必招致程子之责备。明儒在延续这一脉络的同时,与宋学以来的传统虽未截然相悖,但湛甘泉、周海门诸公引据此言,能指却与伊川截然不同:其是否“知道”的指向在于名节与道的关系,而非行为之所由,论述重心从士人行为的出发点转移到了观念本身。陈白沙以名节为“道之藩篱”,意味着名节仅被视为道之末,而非特殊情节下“道”自身在人事的具体显现,与伊川以“自得”为“知道”已不同;同时,在其时重本轻末的语境下,湛甘泉、周海门诸人又脱离了名节作为“藩篱”的防闲意义,反强调道的超越性,则不免将道与名节歧而二之。这也是高景逸抨击“姚江之弊……
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43)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 424页,第1 369页。的重要原因。借此,在王学舍末求本的语境下,以保全百姓为名节之本成为贰臣变节的重要借口。从贰臣多以姜维、魏徵、许衡等人自比来看,将个人名节与兴民政、继绝学相剥离,显然是其为自我寻求正当性的依据之一。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禅学与节义。一方面,王学历来被诟病杂于佛老,“无善无不善”之说在突破固有的善恶边界的同时,也使得士人之学行愈趋于异教。这与时人对名节的忽视与跨越是一致的。明季士人反复强调“忠孝之人有不道学者,未有道学而不忠孝者”(44)魏禧:《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805页。,试图在名节被消解后重塑儒学中的忠孝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见出儒学语境下忠孝的本体论意义:忠、孝固非本体,但以人之性善而不可掩而言,忠、孝往往被视为天理在人伦关系中的具体显现。此即黄宗羲将黄元公(端伯)诸公之殉节归为“此血性不可埋没之处,诚之不可掩”(45)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 424页,第1 369页。之意。因此,虽然明清易代之际禅悦而殉节者众多,遗民之所以仍保留对此的批评,甚至延伸至遗民而逃禅者,其意义即或在于由此而引发的恶的空间。(46)黄宗羲虽为王学中人,仍以为佞佛之流衍在于“无善无不善,事理双遣,有无不著,故万事瓦裂。恶名埋没之夫,一入其中,逍遥而便无愧怍”,可谓真知其弊。因此,他在称许黄元公、蔡忠襄(懋德)、马文忠(世奇)、金文毅(声)、钱清溪(启忠)诸公之殉节的同时,尤其提示“后人见学佛之徒,忠义出焉,遂以此为佛学中所有,儒者亦遂谓佛学无碍于忠孝……吾儒真种子,切勿因诸公而误认也。”其用意即在于,在高扬忠孝名义的同时尤其强调其儒家属性,即强调它与儒家的根本性——即使王学亦常被他人视为是沾染了忠孝的佛学。与黄宗羲相似,王夫之固将“刀刺不伤、火焚不爇之习气”归因于聃、朱、庄、列,但所谓“荡忠孝之心、弃善恶之辨,谓名义皆前职也,谓是非一天籁也”,显有所指。在同书中,他曾多次指责由“无善无恶”所导向的“耽酒渔色、逐名罔利”,与此地所言“为善不力,为恶不力,漠然于身,漠然于天下”相表里。换言之,在黄、王二公看来,不仅如王汎森所说,“他们(按:指佛学)的思想中未替忠义名节安排任何位置,所以易于被利用来作违犯名节忠义之事”,由此而推出的对学术的批评、对道之一二的认知与影响更为其所重。这又可以为上述关于善恶歧异的理路作补充。分明儒佛疆界以惕后之来者,在此意义上说,黄宗羲的这种表达中亦未必没有对误读黄、蔡诸公所导向的危险的批评。此外,明儒对禅悦与节义相关的批评,亦可以参见赵园的有关研究。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36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483—484页、第505页;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初的学术、思想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然而,王学在突破原有秩序的同时,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并未能因之重构一个新的秩序。一方面,它基于宋学以来道德内转的倾向而开新,固无法脱离原有的土壤而别立本根;另一方面,由虚无的工夫论所导向的两可两不可的结果也使得其无法成就固定的秩序。作为某种附着却有别于主流思想的“小传统”,王学固然可以为超越名节提供一种解释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却未必为主流士大夫所接受,以防闲为核心的名节仍被认为是一种根植于天理人心的重要观念。由“无可”所导向的“无不可”在明清易代之时仅作为一种可能或借口而为失节者所利用,却未必是士人所公认的共同价值。布衣潘定国起义被俘后,诡称自己是“明朝大将军”(47)高承埏著,高佑釲补,王逢辰考略:《自靖录考略》卷六,咸丰八年(1858)竹里王氏槐花吟馆刻本,第9a—9b页。,布衣潘文焕自决谓其子“我死忠,汝死孝,传之后世,有颂述焉;不然,一老氓也,谁复知”(48)徐鼒:《小腆纪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467页,第555页。,王玄趾谓“吾辈声色中人,久则难持,及今早死为愈”(49)徐鼒:《小腆纪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467页,第555页。,皆可视为宋以来提倡的名节防闲作用在晚明的影响。
四、明遗民的反省与回归
以对名节与道之关系的重构为核心,士人固可以跨越名节为借口,在其外重开一条道路;但随着名节内涵的缩窄,死节仍是众多明季士人在临难之际守节的唯一选择。死节与变节作为明季士人的全部选择,在极于两端的同时,不仅压缩了士人的选择空间,将其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严苛境地;且原本作为概念的善恶指向具体事件,宋儒善恶分明下尚可存有的宽容被进一步抹除,“两可”有时呈现为“两不可”。
明季殉节者与变节者之多,在此种论述下似不无扞格:既然仅此两条道路,那么两者何以同时呈现出“多”的样貌?一方面,同时期对两者的横向比较,并不能掩盖其在历史流衍中的变化。经由王学导向的歧异与严厉,迫使士人做出选择。自职分而言,在将更多士人群体纳入政治语境之中的同时,也使得殉节者与变节者的人数与影响都甚于过往。另一方面,此两种现象虽可以视为被放大的“虚像”,但放大本身即意味着其来源于时人的真实感知。(50)司徒琳(Lynn A. Struve)认为,以张茂滋所撰写的《余生录》为代表的明季士人叙述,“是一个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也同时是个人纪念的‘私’,但却在象征意义上又是纪念某个人的祖父(以及受这位祖父在道德上直接影响人士)隆重又属于‘公’的自我牺牲”,“目的即在描写所有事件中的核心部份——(张)肯堂的典范(作为一个家长),使之在文字中不朽,供所有后世之人阅读”。这既证成了儒家勾连公与私、个体与公共的传统,同时也意味着,与时人对殉死者的宽宥相一致——即不以殉死者之生平而断其是非,殉节者在幸存者眼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参见司徒琳:《儒者的创伤——〈余生录〉的阅读》,王成勉译,《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39期。目击耳闻中由家国飘零与亲友死亡所带来的冲击确难以为当事者忽视,情感所带有的倾向性往往在其人的表述中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因此构成的信息茧房当然不意味着时人之判断出于蔽目之叶,以其自身之真实与不完整而论,已具有正当性,何况这一“茧房”竟笼罩于所有明季士人之上;但应当进一步讨论的是,经由对两者失序的反思,与对明学的拨正与发展,“名节”这一概念在明遗民处如何得到进一步生发。
遗民之有政治见地者,多试图调适由可与不可这一诠释空间所引起的争讼,以试图重建一种理想政治图景下的儒家秩序。由此呈现的君子、小人之争,不仅以小人干政与变节为恶,而且君子与小人争是非也因忽视所可能导向的后果而遭受非议——尤其这种后果被置于明清易代这一“夷夏倒置”的背景之下。换言之,明遗民未必诟病争讼本身,但至少“君子争是非”这一在明季严格的道德主义下绝无可议空间的事件,于遗民时代被解读为由“所争者正”到“以争为正”(51)赵园以为:“尤其精彩的是,他(王船山)指出‘争’的目的化——由‘所争者正’到‘以争为正’,由争是非到争意气,降低了‘君子’的道德水准,致使君子小人‘杂糅’于‘争’这一行为中难以区分。”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从而在明清鼎革、 “夷夏倒置”之际被赋予了更现实的意义。(52)王夫之谓“气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谋,而愤兴于不自已。……言勿问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汉、唐之季,其倾也皆然,而宋为甚”。如将其视为以宋观明,则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明而发的。且谓“一浮而是者已非”,其意似乎不仅在于如赵园所言,指责其时士人以争讼为是,更在于其以争讼为非。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页。
值得注意的是,明遗民政治群体的形成,其一在于通过为遗民这一身份赋予“社群”或“族群”的意义,使得其在脱离政治场域后仍具有拒仕的正当性,其二即在于重新回归到“遗”的意义,在当时严苛的士风下打破了“不死则降”的桎梏,拓宽了士人的选择空间。此两者正是明遗民显别于历代遗民的重要体现。诚然,明遗民作为“遗民”这一概念群中的一种,内部仍因袭了历代遗民“忠义”这一特征,但与前代相比,某种观念的有无远胜于明遗民内部持此观念人数之多寡。不论是对“罔死”的反省,还是对明王朝的批评,虽皆可视为部分明遗民“忠”的体现,但其表现形式既与传统不侔,则自人数而言必非主流。然而,相较于此前对“死”的一概赞扬,甚至士林一度以死为是、而非审所以死者为是非,则如高檗庵、陈乾初、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反省,确以其“遗民”的身份而出乎明季视域之外。这正构成了明遗民之为“明”与“遗民”的特征。因此,与其自人数来判定明遗民的主体,毋宁将这一群体中显别于历代遗民的特质作为论述的中心,从而使得历史背景得到凸显,时代精神亦因此而得以表彰。
一方面,由党争引发的宗社颠覆与“夷夏倒置”,无疑被明遗民视为由一种失序(正邪)引发的更大的失序(“尊卑” “夷夏”)。君子与小人争,其意固在维持既有的天秩,但争既不足以维持,而恰以这种争激化甚至促成了秩序的崩溃与解体,则“争”本身反而不当。王夫之谓“弋获国士之名,自诩清流之党,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祸,国家亦何赖有此士哉”(53)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6页。,魏叔子谓“即或立风节、轻生死,皎然为世名臣;一当变事,则束手垂头不能稍有所济”(54)魏禧:《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805页。,甚至计六奇论吴磊斋(麟征)重在反驳“世徒以殉节目公”(55)“燕京之难,殉者数人。然死则死耳,于国事未有济也。惟公则不然,使‘弃宁远、徙吴帅’之说行,上则为奉天之李晟,次则为汴都之种师道,无难也,何至封豕长蛇凭凌无忌,覆我宗社,贼我君父哉?即不然,人尽坚守如公,贼顿兵城下,援师渐集,有鸟奔兽溃耳!况得早从公‘南司马节制诸帅’之议,威柄既肃,勤王义旅可一呼集乎!然则世徒以殉节目公,岂为知公者哉?”其将守节置于其次,而首言其军事谋略,显然意在凸显臣之所以为臣更有甚于忠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529页。,皆可自此见出由明亡所引发的对“名节”的反省。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56)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51页。之说作为对明季殉节诸公的评论固属荒诞,但晚明士人确需面对有关仗义死节以外者。
如从其时士人之死每言“以愧为人臣而怀贰心者”一点来看,殉死,尤其是每为后人所责的自杀式殉死,亦可视为时人借由“死亡”这一形式对变节者的抗争。明季士人趋死的主动性,同时也意味着由此引发的对秩序的突破。相较于失节,当然以死节为尚,但死节却未必是士人守节的唯一抉择——尤其在未临难时。
以陈乾初(确)为代表的明遗民对“罔死”的批评和纠正,其着眼点之一即在于此。明季死节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这一倾向形成的根源之一,被认为在于由以“有意求之”为表征的对“节”的忽视。一方面,秩序作为天理在形下世界的自然显现被强调,否决“有意”意味着为乾初所非议的“靖难之祸,益为惨毒”“甲申以来,死者犹众”的情景与“一死之为快”“不必死而死”的抉择,正是由一种尚死风气下的“有意”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注重“中节”之难,其根源出于《中庸》,与宋、明儒学理路一致;但同为拔高了品评人物的标准,则以主动性来否决士人抉择的正当性,甚至以死者之众为“非义之义”,已与“以死为尚”之说并无二致,亦未出其时道德严格主义的语境。
另一方面,所谓“国家亦何赖有此士”,不仅意味着所争者未必为君子,甚至以一种个体与群体的视角,将君子从争的风气中剥离出来。这一点在王夫之处尤为明显。王夫之每言作为一种士气的争,如谓“宋之多有此也,不审者以为士气之昌也,不知其气之已枵也”“以士气鸣者,士之荑稗也,嘉谷以荒矣”(58)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第326页。,其意似在于凸显个体在此之下的抉择。由争而导向的一种苛厉与严峻的习气为士人所警惕,赵园视之为“作为士人反省能力的证明”(5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固然如此;但更重要的是,其时士人在意图恢复“价值感”的同时,更着重于秩序本身的重构。王夫之并未质疑倡其风者的合理性,但且谓“闻风而起、见影而驰,如骛如奔,逐行随队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由此导向的习气确使得个体为之裹挟。(60)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第326页。所谓“裹挟”,不仅在于一种实际的强迫性而具有不得不如此的意味,而且作为一种场域(field),使每个个体都处于其中、受其影响而不得自由。这一点与前述程子论东汉士人相似:它所带来的后果在于,事出于情而未必出于理(即程子之“不知道”)即有可能导向前后行径之大变。所谓“激以为义,非必出于伪,而义终不固”(61)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659页,第715页。,王夫之在斥责陈宜中诸人之上书干政,其意义即在于此:向之愤然攘臂者临难而逃,至有“群殴北徙,瘃足堕指”之讥,长为后世所笑,乃谓忠义者不过如此。(62)参见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326页。与之相关的,是明季海宁未仕举人祝开美(渊)的殉节。祝开美曾于崇祯六年(1633)会试入都时疏救刘蕺山,嗣后拜入其门下。乙酉(1645)六月清军入浙,有人劝以不必死,即曰:“诸生非上书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莽有无逃之义;害之所在,缩首而避之。何以见鲁、卫之士乎?”其前后之一致,适以证王夫之之言。见祝渊:《重订祝子遗书》,民国六年(1917)祝廷锡刻本,《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88册,黄山书社,2016年,第185页下栏。
王夫之在批评士人随风而行时,着眼点亦在于由“风”这一概念所导向的一种宽泛的可能:肯认某种风气下士人殉死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即从“风”的正当性来肯认“殉死”这一行为的正当性,而非将其是非归结于个体的自由意志。这也就意味着,在另一种风气下的贰臣变节也可因之得到宽恕甚至认同。回视有得于王学所提供的某种“可能性”,贰臣已足以引证历史上的例子而为自身之变节作出注脚,那么将自身行为的是非归结于一种“风气”,确也可以成为不必斥责变节的重要借口。
但与一般学者体认不同的是,以陈乾初、王夫之为代表的遗民否认“名节之风”或“殉死之风”的完全正当性,既不意味着否认殉死本身具有正当的可能,即王夫之所谓“非必出于伪”之为“非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风向下的个体行为全不正当。在这一视角下,士人并非齐视君子与小人,而失去其惩恶扬善之本色。如王夫之极力反对君子清议可能造成的恶果,并不意味着他否认清议本身。他亦曾一再强调“薰莸并御之朝廷,不如水火交争之士气”(63)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659页,第715页。。经历晚明的劫难与动荡,遗民都将以清议或节义所引发的争讼从“最重要”或“最正当”中剥离出来,却并未因此而否认它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与防范意义——即使需要经过语境的凸显。明季士人惯于以相约自尽自期,部分遗民惯于以“死”与“能死”为尚,将“清议”或“殉死”从明季“最正当”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既保留了其自身所带有的某种“正当性”,也经由对“自得”的强调,而达成对宋儒的回归。这正与伊川对党锢士人“效仿前人”的批评相一致。
王夫之指责陈静观(宜之)诸人临难逃亡,即意味着“就孔子之堂,择干净土以为死所”确是士子应为的重要方式。从士人前后抉择之一致,可以见出其行为之出于道、具有显然的士人自觉,而非出于情、为士气所裹挟;更重要的是,这种肯认也可视为是通过对名节“防闲”之义的强调,而达成对明季殉节者的表彰。顾炎武谓“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64)陈垣:《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2页。,王夫之谓“清议者,似无益于人国者也,而国无是不足以立”(65)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291页,第929页。,“故义者,人心之制,而曰名义;节者,天理之闲,而曰名节;教者,圣人率性以尽人之性,而曰名教”(66)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291页,第929页。,黄宗羲谓“清议息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红本。……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67)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 375页,第1 375页。,张杨园谓“学者能砥砺名节,一变可以至道。若轻视名节,未有不至于同流合污者”(6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1 078页。。以诠释学观点来看,顾、黄、王诸公虽仍将清议、名节从明季“最正当”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可视为对士风或学风的反省,但明季士人变节既成为时人眼中某种被放大的“虚像”而为其所重,则以能指而言,注重于“防闲”义与前述龙溪、海门诸人对“非道”的强调确已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学者的一些讨论。赵园引陈乾初《死节论》一文及黄宗羲为乾初所作《墓志铭》中的相关称述,认为明遗民仍然延续了以“名节非道”为重心的叙说,并称之为“一些士人的共识”。(69)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张晖与之类似,也因此认为黄宗羲“内心是不赞成轻易一死的”(70)张晖:《丧乱之际的生与死——论黄宗羲对于死亡的态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八辑)——中国文化的理念、偏好与争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这一观点恐非正解。黄宗羲所谓“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蕴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71)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第1 375页,第1 375页。,显然未将名节之死视为不当,更未将生视为高于死的抉择。相反,不以一节名,并不意味着“节”本身不足以当之。明遗民重塑名节的“防闲”之义,不仅是对陈白沙“道之藩篱”一语的回归,从陈乾初、徐俟斋将“节”视为“道”来看,亦可视为对程子的回归。(72)参见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节义观念及其行为抉择》,《明史研究》第十四辑,黄山书社,2015年。孙夏峰以金伯玉(铉)之死为“忠到足色”,赵园称之为“未出‘时论’”,实未必然。(73)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130页。不论在陈乾初、黄宗羲、徐俟斋抑或是其他明遗民,他们对尚死这一“风气”的反省仅仅存在于“以死之事为尚”,而非反对名节本身。名节及名节之事仍是值得称许的,但只有“合于道”时,方获得最高的正当性。因此,陈乾初之称祝开美,孙夏峰之称金伯玉,皆称其人而后称其节义,故曰“非徒争此区区之节者也”“善处死”;不以“节”或“死”为是,而强调所以“节”与“死”,正因此而带有强烈的遗民色彩。
五、余 论
以对“名节”的诠释为核心,在阳明学中所形成的严格与宽泛的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一种争讼的空间。对前者来说,出于“非圣人则非人”的观念,部分士人将“是”或“善”之中的“过”与“不及”视为“恶”,善恶、是非间的边界被模糊,借由渐趋严苛的工夫论,导向一种“尚死”的场域或风气,从而使得明清易代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对后者来说,这部分士人注重于“名节,道之藩篱”一句中潜在的“名节非道”的语义,在王学形上化与本体化的倾向下,借由对更本质的“道”或“天理”的追求,而有忽视名节的危险,并为明清之际的士人变节提供了借口。换个角度来看,将“过”与“不及”视为恶,则传统语境下善、恶原本相对固定的概念被消解,在流动之中既可以通过对“恶”的重视,而以此作为道德严格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因对“善”的发扬而为某种道德的虚无化作出注脚。
部分明遗民正出于对这一争讼空间的反省,试图以澄清学术路径的方式重建理想的政治秩序,从而使得“遗民”之“遗”的意义得到凸显。赵园以为明遗民“将政治得失归结于学术纯驳”“经义不明……被作为了易代之际的痛切经验”(7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确系如此。
一方面,对“风”的批评与由此引发的悖离道德的可能有关。在明季道德严格主义的风向下,所有士人都被纳入政治语境之中,也就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需面对死节或变节的抉择。严苛的逼迫在挤压士人生存空间的同时,在两极化选择之下,也可能导向与之截然相反的一面。不论是王夫之对“争”的诋责,还是陈乾初借对“死节一案”的反省而对“从众”的批评,其意皆在于强调士人自身的自觉性,从而将对行为的是非评判归结于行为主体,而非一时风气。这一点与伊川论党锢士人一致,正可视为丧乱后明人对王学的反省与对宋儒的回归。
另一方面,陈乾初、徐俟斋以“名节”为“道”,在回归宋儒语境的同时,仍带有鲜明的阳明学色彩。通过对形上的“道”的追求,名节的防闲义虽仍为其所重,但“节”作为“道”在形下的特殊显现,此时却因忽视了“死节”之为“死”,而使其几同于道。所谓“君子且不可苟死,况可苟生;不苟贫贱死,况苟富贵生!君子之于生,无所苟而已”(《死节论》)(75)陈确:《陈确集·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155页。,正基于对一种完满的善的追求,仍将过与不及视为恶,在批评“苟死”与“苟生”的同时,成就了对道德严格主义的延伸。其所指与乃师刘蕺山并无差别,但对“无所苟”的强调,确已脱离了江右、东林一脉“就贫贱说”的艰苦工夫,而导向了另一种严苛的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遗民在对“风”和“罔死”的反省中,仍然坚持名节作为一种“藩篱”或“防闲”的意义。即使在陈乾初的语境下,“苟死”胜于“苟生”也意味着对朱子“与其贪生忍耻,终无以有益于斯世,则不若捐躯以就死,犹或有以争救于万一之间”(76)朱熹:《四书或问·孟子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67页。和宋人“宁前一尺,毋却一寸”(77)宋季殉节尚书卓善夫(得庆)语,张寿镛据《宋史翼》引《福建通志》。万斯同辑,万世标校:《宋季忠义录》卷八,《四明丛书》约园刊本,第17b页。的延续。这与殉节者正相一致。但与之不同的是,相较于陈乾初此种更为严苛的论断,王夫之通过区分疵与绝、过与逆,其用意或即在于通过打破求仁至圣的期必,从而为明季士人的选择拓宽空间;强调“名节”作为一种“防闲”的意义,不仅是为士人守节提供依据,而且也打开了“死节”与“名节”间的缝隙。(78)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13年,第365页、第500—501页。于道德紧张处立下防闲,既是对外者的拒斥,也是对内者的宽容。圣人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矩”的意义大概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