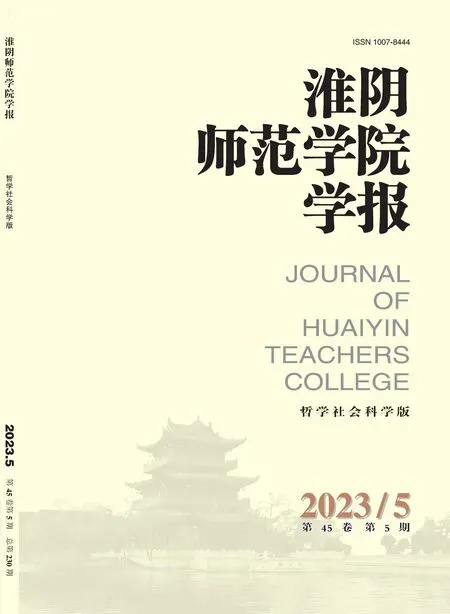混沌世界与混沌叙事
——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的文学人类学意义
高 山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赵本夫的小说创作,早期具有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一般特征,比如《进城》《西瓜熟了》等;然而其小说整体审美气韵与艺术追求却别有风味。处女作《买驴》中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既非社会解冻的征兆,也非精巧的故事,而是孙三老汉对大青驴复杂深沉的情感,是兽医王老尚治愈大青驴时精湛神奇的医术。第二篇小说《“狐仙”择偶记》更是把目光投向农民情欲与乡村权力结构的复杂纠葛。这些简单的列举,即可约略显示赵本夫小说创作从起步阶段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视野,他把目光和触角伸向乡土中国更世俗、更具民间文化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他把日常生活中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放在民间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凸显。生存的沉重、民间的传奇、人性的光辉与黑暗都是他关注的主题,大洪水、土地、女性/母性是他喜欢的意象。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关注着大地和大地人。关注大地,就是关注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关注大地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关注文明对大地的影响和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变异,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的许多作品转向上述内容。”[1]
然而学界对赵本夫小说的研究一直走不出乡土、农民、苏北地域文化等范围,即使探讨他小说的艺术性也仍然无法摆脱因为题材带来的这些天然标签。这样说并非否定从上述视角出发研究赵本夫小说所得到的成果,而是惋惜赵本夫小说中被这种标签似的断语所遮蔽的东西,尤其是他长篇系列小说《地母》三部曲里那些无法用现成的批评范畴限定的东西——文学人类学(1)本文的文学人类学定义取自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在具体分析文本时略有拓展。意义。其实已有学者发现赵本夫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人类学内涵,可惜其中既有把文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注脚之嫌,又言之不详[2]313。赵本夫本人也一再声明:“多年来,我在许多作品中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形态生命意识,在人类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永恒的东西。……我要表现的是人类文明过程中的生命形态。”[2]311其实,“文学本身就应该孕育着自发的人类学意识,或者说本然地就带有人类学思想色彩”[3],因此,本文将以《地母》三部曲为例,解析赵本夫小说的文学人类学特征和意义。
一、《地母》三部曲的混沌世界
1997年八九月间,赵本夫和李星围绕着《逝水》(后改名为《黑蚂蚁蓝眼睛》,是《地母》三部曲第一部)有一番很有意味的书信对话。对话既显示出赵本夫创作转向后的某种迷惘,也显示出当时文学批评界对《逝水》这种样的长篇小说没有办法立即给予恰当的回应。通信中,李星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逝水》问世已经一到两年了,据我所知至今为止,它在文学界的反应不算很强烈,这可能很令你痛苦,但我以为这不能说是你这部作品的失败,而只能说它的面貌太奇特了,既不是面向当前生活的现实主义,又不是面向心理情绪的现代主义,既不是农村题材,也不是城市题材,既不像历史,又不像现实。”[4]313-31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逝水》发表之初,人们对它的艺术流派、题材范畴、形式特征都难以下判断,多少有些无所适从;而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逝水》中有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批评视角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东西(2)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关键,因为当时人们对《逝水》模棱两可的认知,其实恰恰可能从侧面揭示了这部小说非凡的特色,可惜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够给出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说它不像现实主义,是因为它瓦解了一般现实主义赖以确立的“社会—历史”叙事模式;说它不像面向心理情绪的现代主义,是因为小说不以单个人的自我意识为中心,而且人物具有一定程度的前现代性;说它不像历史,是因为小说中几乎没有一般历史小说中对史料的借用;说它不像现实,则是因为其中的神秘主义、神话原型、土地情结在当时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李星的这段多少有些含糊其词的话,今天看来却是歪打正着、甚至一语中的,因为他在无意中揭示了小说两种意义上的混沌性——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状态和小说虚构方式的混沌叙事。这两种混沌性体现出了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的文学人类学特征和意义。
先谈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状态。
第一部《逝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写黄河决口以后的那一段时空。那一段时空是人类文明的中断,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秩序等一切文明社会的规范全消失了。大水中幸存的人们重新成为自然人,土地也重新成为自然之物,人和土地全都自由了。黄河决口对人类文明是一次毁灭,但对人和土地本身也许是一种解放,使人和土地重新找回迷失的本性”[5]。这种混沌性在第一部中表现得也最突出:时空断裂,秩序崩塌,文明解体,人兽共处,神人合一,人和万物复归混沌。幸存者们陷入荒原,失去了时空感:“当大洪水落下,双脚踩住满是泥浆的土地时,他们甚至失去了方位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大地上的一切原有的标记都消失了”[6]32,“几年以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概念,只知道黑夜白天,阴晴雾雨”[6]90。整部小说中既没有清晰的时间线索,也没有具体的空间方位;虽然勉强可以发现围绕柴姑重建的“草儿洼”,由近及远有黄口镇、桃花渡、七棵树、凤城等地名,但是这些地名已经失去了为小说中的人物标记空间方位的功能。幸存者们“谁也不认识谁,只像鬼影一样在大地上飘荡,……他们不再有羞耻感,只剩下生命的本能”[6]32。本能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然而本能是盲目的,所以他们互相依偎、互相杀戮,甚至互相吞噬;他们与动物为伍:柴姑和蚁群,老大和羲犬,小迷娘和蛇,腊和老牛,还有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狼群和给他们充饥的鱼虾、鼠兔。
第二部《天地月亮地》中文明的秩序以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为核心在慢慢恢复中,“大水过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这片荒原的所有土地都有了主人”[7]14,“柴姑在经历过多年的拼杀之后,蓦然发现荒原已经建立了新的秩序,哪种人吃哪碗饭都已排定座次:鬼子吃土匪,土匪吃老百姓,老百姓吃土地。没有人能更改”[7]185。然而,无论是柴姑和她的伙计们在草儿洼经营土地,还是后来的土改和合作社时期,土匪的劫掠、饥荒的折磨、人心的混乱、情欲的纠结,这些种种的无序又是那么明显;所以《天地月亮地》中,小说虚构了一个从混沌到秩序、秩序中又包含着无序的混沌世界。
第三部《无土时代》的混沌性相对较弱,因为小说虚构世界的历史进程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形态,木城发达的城市文明几乎完全脱去了前两部小说中的蒙昧状态。然而小说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狂乱,乡村的衰败,城市人生命力的委顿,政协委员们天马行空的议案,天易对土地魂魄的追寻,柴门对城市文明的反思,谷子寻找柴门的梦幻之旅,天柱用庄稼占领城市的神来之笔,这些众多线索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和时空关联又使得小说虚构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扑朔迷离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主要集中体现在人物天易的迷失和人格、意识一分为三的分裂:天易迷失于历史时间的断裂,石陀迷失于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柴门迷失于追寻土地魂魄的精神之旅。
统观《地母》三部曲,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性各具特色:《黑蚂蚁蓝眼睛》是大洪水摧毁人类文明后原始野性的混沌;《天地月亮地》是人类文明以土地的占有为核心的农业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艰难生存、暴力血腥的混沌;《无土时代》则是人类文明向更高级的现代社会阶段发展过程中土地乡村衰落、城市人性颓败以及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疏离所形成的混沌状态。然而这种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性又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小说家主动放弃了以往小说以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单一元素为主导的虚构框架,以人的生命形态的复杂样态作为小说虚构的主要考量指标[2]311,小说中凸显的是人与土地深厚复杂的生存性关系,是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人性扭结、情欲纠缠所形成的丰厚混沌的生命样态,这使得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必然。
二、《地母》三部曲的混沌叙事
相对而言,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状态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作为小说叙述方式的混沌性,或者小说的混沌叙事,却需要仔细辨析和解说。小说叙事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是也不妨有比较简洁明了的概括,叙事“是一部小说全部话语行为的文本形式。叙事由两部分组成:叙述和故事。按照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是由能指——叙述,和所指——故事一同来体现的。叙述表现故事本身的意义,而叙事却可以追求故事以外的意义。叙述是语言行为,而叙事的本质是对事物意义的显现”[8]。因此,《地母》三部曲的叙事问题,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具有混沌特征的故事,即小说虚构出来的混沌世界;另一个部分就是下文要展开分析的具有混沌特性的叙述方式,即小说的混沌叙事。
混沌世界决定了小说混沌叙事方式。混沌叙事首先表现为小说虚构时空体的非因果、非逻辑、非线性等非历史性特征。最早关注小说时空体的是巴赫金,他认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9]他对小说时空体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现代小说的叙事危机也缘此而出现,“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只要想一想‘性格’‘行动’‘命运’,以及事件的完整性、情节的起承转合、因果律以及时间的连续性等等,就会发现这一套曾经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模式的要素已经多么远离了现实”[10]。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有意无意中应对了这种叙事危机,小说从各个人物生存本能的需求出发,叙述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个体生命形态,打碎了时空统一的幻象,几乎完全抛弃了以往长篇小说“主线因果导控”的时空统一体叙述模式。
这种非历史性叙事具体表现为小说故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历史时间,没有标识事件发生的具体纪年。虽然整个系列小说叙述了从晚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一直到2002年左右将近150年历史时空中发生的故事(3)前者在作者创作自述中可寻,后者从小说中引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不知道》推测可知。如果从老石匠出生开始算起时空跨度应该有四五百年。,但是小说中没有标识一个具体的年份。这种叙事消解了小说的历史感,抹去了读者判断故事在真实历史时空中的坐标,打破了读者凭借历史知识预先把握小说语境和历史时空特征的可能性,消除了先在的历史对小说虚构时空体的干扰和对小说虚构意义与价值的沾染。虽然小说中也有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晚清军政举措,有土改、合作社、抗美援朝、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元素出现,但是这些历史元素也往往因为具体时间标志的缺失,以一种片断化、碎片化的方式成为展现人物生存状态、生命形态的手段或背景。这使得小说的叙述时空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由灵活状态。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历史、神话、现实、想象、幻觉等不同质性的时空同时涌现。整个小说叙事在不同的个体和展示其独特生命形态的故事之间跳跃翻滚,故事与故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逻辑的、必然的、因果的联系,故事与故事的勾连往往是隐晦的、偶然的、片断的。
因此小说第一卷刚刚发表,就有这样的判断:“人们习惯于注视某种新的或时髦概念的小说,不习惯于思想主题散漫不显的小说,习惯于故事单一、因素鲜明的小说,不习惯于许多故事套在一起,看了28万字仍不能以理意命名的小说。”[4]314表面的否定中暗含着对小说非历史性叙述特征的概括。然而从宏观视角考察小说的时空体,也可以发现小说故事间模糊的关联性。比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天易,仿佛是一个时空穿越者在小说巨大的时空织体中穿梭往来——第一卷14页:“几百年后,一位作家来到石洼村,带着人生的伤痕和疲惫,在故乡的土地上流连,寻找失落的童年。他叫天易,是老石匠的后人。”第二卷15页:“很多年后,天易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一直在作品中探讨人类的生命意识,他被认为是个偏执狂。”小说前两卷中还有多处这样的叙述,使得小说碎片般断裂的时空体奇异地胶合在一起。
《地母》三部曲的混沌叙事还表现在小说家主动放弃了以往小说以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单一元素为主导的虚构框架,采取了以生命形态的复杂存在方式为小说虚构世界的主要指标的生命形态叙事。“家族小说最普遍的主题,是通过家族的兴衰表现人物的命运,表现历史的变迁,这也是最传统的主题。这当然无可非议,但诸多小说的雷同已是无法避免。我走的是另一条路,就是离开社会学意义上的主题,去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2]306这种生命形态叙事特征也正是小说非历史性叙事的后果。《地母》三部曲总体上既没有中国现代性启蒙与救亡意义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寓言化叙事,也缺乏现代个体成长的主体性叙事,甚至没有单一文化历史传统主控的社会历史叙事,因此小说既不像《红旗谱》以中国农民革命的起源和合法性为主线,也不像《创业史》以土改、合作社等社会政治事件为主导,更不像《青春之歌》以中国知识分子革命主体的召唤与成长为主干,甚至不像《白鹿原》以儒家文化及其社会形式——宗法制度为核心。
《地母》三部曲揭示的是人与神话、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幽暗隐晦的复杂纠葛,是野性弥漫的生存本能、生命意识和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是人与土地、自然相互疏离的文明忧思。这就形成了小说某种超越具体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形上视野和叙事品格,这种形上视野和叙事品格混沌、深沉,又直截了当。它们展现人类文明崩塌、断裂、重建、衰落的过程和这个过程中自然人性的生长、生命形态的杂多。仅以几个女性形象为例,我们就可以领悟小说对生命形态的高度关注。柴姑集灭世者蚁王和创世者地母于一身,小迷娘则是逍遥蛇女,作为男性引导者和婴儿哺育者的茶,以女红为诱饵的女同性恋者花娘和女儿蛋蛋,石女梦柳,与公公通奸的八哥,讨饭女小鸽子,饥饿的买地者天易娘,内心分裂的举报者钱美姿,等等,只是这样简单的列举就能够让人体会到这些女性人物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态和人性色相。小说中甚至还刻画了蚂蚁、狼、狗、蛇、狐狸、乌龟等非人类生命形态样式。这种可称为生命形态叙事的正是《地母》三部曲混沌叙事的特征之一。
当小说把生命形态作为叙事的中心,并且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消解了虚构框架的单一主导因素之后,小说家和小说必然面临一种困境,那就是如何使得众多个体的生命形态及其日常性、世俗性故事、细节具有意义。这个困境如果不能克服,那么小说将无法避免沦为日常生活奇闻异事叙述体的悲剧命运。而这个困境及其解决之道与《地母》三部曲混沌叙事的第三个特征——“个体神话叙事”(4)此概念受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中“个体的神话诗学”概念的启发。相关。
法国学者乔治·杜梅齐尔在其著作《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中,对从神话到小说的文体转述的研究,既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又切中《地母》三部曲个体神话叙事建构的关键。杜梅齐尔提出了两个内涵相近的问题,“一个属于个人的、以情欲为动力的故事情节如何取代了一个由社会最古老的习俗予以规范的、全部记载武功的脚本”[11]148和“一个心理学的、纯属个人性的情节线索如何取代了一个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叙述”[11]149。这两个问题探索从神话到小说的文体转述过程中个体日常生活叙事如何取代集体神话叙事,杜梅齐尔发现一种“中介”“一个内心悲剧的中介”:“在战士的灵魂里点燃那个可怕的、但却符合人性的怒火的,是一种个人的、姓氏的、民族的骄傲加上对于女性的弱点的蔑视”[11]148,杜梅齐尔发现的这个中介正是属人的,是人性的弱点对神性灵魂的入侵。然而对于《地母》三部曲来说,这个问题恰恰需要颠倒过来理解,也就是说小说中众多个体生命形态及其日常性、世俗性故事、细节如何被重新神话化,或者说神话性如何侵入人性,或者说祛魅的世界如何复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地母》三部曲创造了笔者称之为“个体神话叙事”或“个体神话诗学”的、具有混沌属性的小说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
“个体的神话诗学首先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个体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可以用一种可能远远超出了个人意识范围的、具有更广阔的人类历史、意识背景的经验图式来加以讲述”[10]259,而“现代作家所使用的个体的神话诗学,既是通过对集体意识、集体经验的普遍历程加以个人化的构拟、以进入创造性的个人的神话……也是对现代社会杂乱经验的整饬、赋予暧昧的个人经验及其内部活动的一种神话类比和象征结构”[10]258。《地母》三部曲正是通过神话传说、神话原型和神秘主义文化这些“远远超出了个人意识范围的、具有更广阔的人类历史、意识背景的经验图式”,将小说中日常性、世俗性的故事重构为神话而赋予其人类学的意义。
小说第一部从蚁王柴姑率领神秘蚁群摧毁黄河大堤、发动大洪水的“灭世神话”开始,并且让拥有共同血脉的柴姑和老石屋守候者“老鳏夫”的三个儿子重新演绎“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的“创世神话”,而且赋予柴姑“地母原型”所承载的、与土地相关的容纳、生殖、繁衍、甚至死亡等神话功能;即使在完成了世界祛魅过程的第三部《无土时代》中,作者仍然创造了一种带有荒诞色彩的神话:用庄稼占领木城,以唤起城市的人们对祖先种植的记忆[12]。这些神话原型、神话叙事贯穿小说三部曲始终。更重要的是小说家用众多的神话传说、神话原型、神奇动物、神秘原始文化把众多个体的生命形态与土地、与自然、与人类文明进程相联系,使得小说中个体生存故事和其日常生活具有了一种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混沌性质与形态,这才是个体神话叙事的真正内涵。
其实近来已有学者发现了20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混沌化趋势,认为这种文体的混沌化“是长篇小说文体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一方面,它复杂多元,可以包含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叙述传统和古今中外的一切文体因素;另一方面,它单纯到极致,所有艺术元素被安放得恰如其分,彼此交融,浑然天成,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13]文章说出了许多具有学术见地的话语和判断,比如把长篇小说文体的混沌化看成是小说艺术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和20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普遍趋向。可惜作者眼光局限在20世纪以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水乳大地》《丑行或浪漫》《村庄秘史》《古炉》等少数几部小说,忽略了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等更具代表性的文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仅仅把长篇小说文体的混沌化看成一个形式问题,没有发现小说叙事形式的混沌化与小说虚构世界的混沌性之间的必然联系。
当然,从非历史性叙事、生命形态叙事和个体神话叙事三个角度分析《地母》三部曲的混沌叙事特征,并未穷尽其混沌叙事的内涵,还有许多值得探寻的空间有待开掘;《地母》三部曲的叙事特征也并非仅以混沌叙事就可以完全概括,而且《地母》三部曲本身的叙事也并非完美无瑕。但是混沌世界与混沌叙事这样的理论概括,比较贴近《地母》三部曲创作的实际情况,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地母》三部曲的文学人类学意义
“混沌”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学、人类学概念,与洪水神话、创世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5)参见向柏松《洪水神话的原型与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刘向政《“混沌”创世神话的原始象征意义与宇宙观》(《求索》2007年第2期)和饶春球等《“混沌”与洪水神话》(《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等文章。;因此本文使用“混沌世界”与“混沌叙事”分别描述和概括《地母》三部曲的小说虚构文本特征和小说叙事特征,原本就是要以此揭示小说为其虚构世界复魅的文学人类学企图。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学术与政治》中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性转型中世界“祛魅”的理性化进程。而“世界的祛魅就是驱除巫术、魔法和神秘性,就是驱除‘克力斯玛’的神秘光环,由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转变,就是驱除传统、情感乃至价值理性而向工具理性发展的过程”[14]。其后果之一部分就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世俗化、人与自然的疏离、原始神秘文化的消失。中国现代性社会进程虽然与西方有着巨大差异,然而由于其现代性动力源于西方,这就造成了其现代性后果与西方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现代性转型中世界“祛魅”的后果及其造成的危机,在新时期以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形势下,显得尤为严重。无论是人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还是人对自然神性的蔑视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萎缩都令人触目惊心。
对这种危机率先有所反应的是文学界。许多作家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展开一种“世界的复魅”行动,于是出现了一些被称为“人类学小说”的作品。它们主要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来的《尘埃落定》,范稳的《水乳大地》,贾平凹的《怀念狼》,赵宇共的《走婚》《炎黄》,姜戎的《狼图腾》”[15]102。“这些被称为‘人类学小说’的作品大致包括三个思想旨趣:文化寻根与神话还原,地域描写与地方性知识的解释,原始主义题旨与文明反思。”[15]103按照这种评判标准,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甚至比上述列举的某些作品更加接近“人类学小说”的内涵。
《地母》三部曲的文学人类学意义最突出地表现在其浓厚的神话叙事氛围上。小说第一部一开始就叙述了家族远祖“圣手石匠”的神秘天命,为系列小说奠定了神话叙事结构;而后,身兼蚁王和地母双重神话身份的柴姑创造了“灭世神话”和“创世神话”,则更清楚地显示出小说家以神话原型重构人类生命形态和文明进程的野心。整个系列小说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核心,所以作为“地母原型”的具体承载者柴姑对土地和女性的认同在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女人生娃娃和土地里长粮食,都是一样奇妙的事情”[6]207,“我只崇拜土地!……土地里能长山,长森林,长草木,长庄稼,长万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土地是世上真正了不起的东西和天一样了不起”[6]259,“她觉得自己的心已变得像她的土地一样辽阔,土地什么都能承受,什么烂东西都能包容,连粪便污物都能化腐朽为神奇”[7]133。在这种认同中,小说揭示了土地与女性异质同构的神话关系:柴姑和她的土地容纳男人和女人,生养儿女和庄稼,包容生命和死亡,承受灾难和痛苦。
《地母》三部曲是一部家族小说,虽然小说家避开了一般家族小说社会学层面上的架构,但是却从个体生命形态层面重构了父母两个家族的起源神话。具体体现这一点的是柴姑与老鳏夫三个儿子对“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神话的重演。《独异志》这样描绘兄妹结婚神话: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16]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源于原始血亲结合禁忌给兄妹二人带来的“羞耻感”,和向上天祈求意旨的咒语。小说对这个神话原型的转述更具戏剧性,不仅让柴姑成为老鳏夫三个儿子共同的女人,而且让老大和柴姑肩负了血脉传承的繁衍功能,承担起溃堤蚁群与黄河不死魂魄之间的仇恨,于是兄妹之间的交媾被神话成战争:
这是一场洗劫。一条血性的汉子,双脚蹬地,弓起脊背,饱满的筋肉鼓凸暴起,一声又一声大吼,一声又一声尖叫,你不堪忍受了吗?你的蚁穴顶不住长堤的压迫,一次次想撑开,一次次压下去。千里长堤般的身躯和杵槌足以让你崩然开裂,威武的长堤依然雄踞,它将探入你生命的黑暗,撩开蚁穴的奥秘,直至鲜红的血喷出。[6]151
柴姑与老大之间这种惊心动魄的两性战争贯穿系列小说的前两部。在此男女生殖器分别被转喻成黄河的长堤和溃堤的蚁穴,蓬勃的生命力汪洋恣肆。也许这才是小说重述神话的用意。那种血亲“相奸”的“羞耻”虽然会使老大产生片刻的罪孽感,让他觉得黄河决口是天地祖宗对他们的惩罚,然而真正默默承受这种“羞耻”痛苦折磨的却是老鳏夫,他即使在洪水中成为鬼魂也在劫难逃。小说第二部,在最后一次和老大舍命交媾后,柴姑杀死了自己的这个血亲兄弟、也是柴姑众多儿女的父亲,血亲乱伦、相弑的悲剧终于让老鳏夫不肯安息的魂灵也大哭。这时小说叙述者清醒地叙述了世界因此而祛魅的过程:
但柴姑没有想到,从此以后所有的神秘现象都将从草儿洼消失,她再也没有看到老鳏夫,也没有看到成群结队如黑水般流淌的蚁群。
其实,随着荒原人气渐旺,连狼的影子都很少看到了……
荒原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荒原,荒原已一片片变成了庄稼地和一座座村庄。
荒原已变成真正的人间。[7]184
《地母》三部曲中神人合一、人鬼共处、人兽一体、人与自然融合的神秘主义、原始主义叙事,也是其文学人类学意义的具体阐释。圣手石匠的神奇天命,朵朵和老大都遇见老鳏夫的鬼魂和一只火狐相伴而行,陪伴柴姑一生的黑蚁群在她死去的时候变成了白蚁群,小迷娘的蛇群不仅治愈了她糜烂的下体、还咬死了拆毁蛇塔的日本军人,老大与白羲,腊与大黑牛,等等,这些充满神奇奥秘的故事并非仅仅渲染小说神秘原始的色彩,而是与各式各样男人、女人们丰富复杂的生命形态、生命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比如,在天易的感知里,蓝水河像一个完整的女人的子宫,而他竟然在河水里体验了原初生命状态的神秘回溯,实现了与自然的圆融合一。
第三部《无土时代》,小说则采用了荒诞主义神话叙事方式:一方面让失踪者天易人格一分为三,天易、石陀、柴门;另一方面让寻找者各自经历不同的人生旅途——寻找天易的天柱用庄稼占领城市以恢复城市人对祖先种植的记忆,跟踪石陀的梁子发现石陀的土地情结和无解的秘密,寻找柴门的谷子经历了自我身份确认的神秘梦幻之旅。小说临近结尾时,谷子把她寻找柴门的过程中遭遇的神秘人物和不可思议之事告诉出版社的同事梁朝东和许一桃后,小说这样叙述:
梁朝东终于开口,说许姐,你是个有神论者吗?
许一桃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的其实很少。[12]298
祛魅时代人们却不约而同拥有了为世界复魅的梦想。
总而言之,《地母》三部曲以其多样的神话原型和神秘文化塑造了多样的生命形态,表现了深厚执着的土地情结,表达了对农耕文明的赞美与复归,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混沌世界和混沌叙事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文学人类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