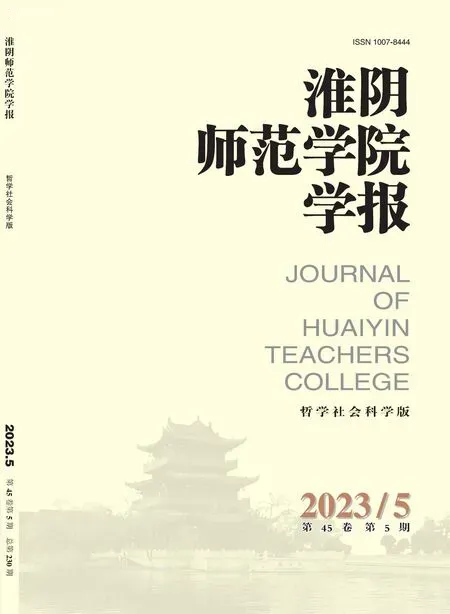雕塑的物性与观念表达:从材料视角出发的讨论
孙 琳
(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物性”(objecthood),即物体的属性。西方哲学史对“物”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诸属性的实体;二是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三是具有形式的质料[1]。本文所讨论“材料”,偏重于“具有形式的质料”这一层内涵,并延伸至材料的文化属性。本文将从雕塑材料的文化属性、客观属性、在场性与具身性,以及虚拟物等角度展开讨论,并将这些讨论放置在雕塑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试图勾画出雕塑“材料物性”对于观念表达作用方式的基本轮廓。
一、作为“文化物”的雕塑材料
自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摄影术以来,“绘画已死”的言论就不绝于耳。随后,“雕塑已死”的提法也屡见不鲜。这些担忧都体现出反现代性的倾向。但事实正如我们所见,所有“已死”之物非但没有死亡,反倒因为与其对立面的遭遇而得以自我更新。对于雕塑来说,新的材料及其技术,让这一古老的艺术门类重思自身的边界及本质。
与绘画相比,雕塑先天具有“跨媒材”的基本属性。无论是“他律”的、事关生产生活的器物,还是“自律”的、以审美性为主旨的雕塑作品,始终依赖特定的材料及其技术。换句话说,材料作为雕塑艺术创作的重要基础,不仅决定了它作为物质存在的方式:形状、体量、质感,同时也决定了它所能传达的观念。在当代语境下,材料及其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让雕塑创作者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我们往往会忽视选择背后所要面临的风险:“用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为何用”。英国学者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化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作用于精神生活。故此,所谓“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类似于同义反复[2]。这道出了材料中蕴含的文化与物质统一的本质。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经典作品《金盐盒》中,抛开艺术家的技巧和表现能力不说,黄金材料的使用增加了该物品在世俗层面的价值,同时,因为黄金的特有属性又在指明:这是属于“君权神授”的君主及其所属阶级的艺术。
如果我们将材料视为蕴藏文化符码的“文化物”,选择材料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件作品所要表现的立场。换句话说,选择某种材料,便是选择了相应的文化立场。以雕塑家展望运用不锈钢材质创作的“假山石”系列作品为例。作为生活领域中大量出现的金属产品,不锈钢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标准化的不锈钢产品背后,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谓“单向度”的人的境况。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表征的假山石形态与此材料结合,便可以立即产生时空错位与文化碰撞。而在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给上帝的爱》中,艺术家将若干名贵钻石镶嵌在一具17世纪欧洲男子头骨复制品上。作品因为其极致奢侈的物品价值和死亡意象本身形成交错的文化震荡,通过对价值和死亡的并置,道出了“本来无一物”的虚空。同理,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气球狗”系列作品,以高饱和度的烤漆色附着在不锈钢材料表面,正是奢侈品牌为代表的消费主义美学形态。昆斯的作品无论是意在批判消费主义,还是暧昧地传递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此材质的选择都已经让上述讨论在作品中自动生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考究、一丝不苟以至于标准化的艺术“产品”,尖锐地揭示出当下西方社会中的膨胀物欲和对表面效果的盲目追随。
二、雕塑材料的客观属性影响观念
所谓雕塑材料的客观属性,是比文化属性更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然之物的属性。比如:大理石材料的重量、冰冷与光滑;玻璃材料的光感、易碎与锐利;木材的松软、有机与腐烂;金属材料的韧性、色泽与氧化。可以说,雕塑的“物性”强烈地参与到了它最终向世人呈现的状态。然而,将材料的客观属性与其文化属性割裂开来,就容易落到纯粹形式主义的窠臼,正如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所谓现代雕塑的“客观物质性”(object-nature):“它们拥有一种完整性,一种自身具备的物质品质,对自身结构和内在关系的自主权,这使得它们可以作为现实中的人和一种模型独立存在。”[3]现代雕塑的“独立存在”,被包豪斯重要创始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定义为“体量的艺术”。他宣称,“当一个人站在材料面前感受它、审视它时,就能强烈地感受到:材料最本质的体现就是它的体量。”[4]实际上,所谓客观属性在艺术体验的一瞬间就已经转化为文化属性:如大理石雕塑质感造成的宏大叙事,金属雕塑表面的氧化效果造成对时间性与历史感的联想,木质雕塑的纹理甚至气味指向的文化象征意义,玻璃材质强化的光感则与现代卫生学以及神秘主义的意象有所关联等。
例如艺术家刘韡在其雕塑《微观世界No.3》中使用曲面铝板材料,观众透过真空般的玻璃罩子环视作品的内部结构:尽可能轻薄的铝板经过切割和拼接,构造出互相环绕、交错的生长状态。铝板本身介于软硬材料之间的金属弹性也使得作品具有在时间中持续完形的扩张趋势。它所形成的弧线、球面,以及在顶部均匀光源映照下的“皮肤”质感,与作为“后感性”成员的艺术家的身体性表达重新产生联系。再者,印度裔英国艺术家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作品《云门》是由多块不锈钢板经过抛光焊接成型,整个雕塑高10米余,巨大的弧形镜面重构了芝加哥的城市景观,当观者走近作品时,会看到自身形象在镜面中发生的变形,造成一种超现实的感受。卡普尔的雕塑因此成功地在观者和作品之间缔结了联系,同时也在艺术家的文化身份与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了中继点。
三、雕塑材料的“在场性”与“具身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极简主义(Minimalism)将雕塑的材料进一步扩展至其所处的空间环境,并将雕塑与观者之间的关系纳入作品中。因此,批评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嘲讽极简主义只专注于提供“在场性”(或“剧场性”,presentness),而不像现代主义绘画那样“击溃或是悬搁了它自身的物性”。他认为艺术理应是一种“非物体”(nonobject),而强调物性的艺术则是“非艺术”(non-art)。他对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所谓的“特殊物品”大加批判,但后者却声称自己的创作最重要的目的是“有趣”[5]。需要注意,古典雕塑已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极简主义雕塑中的“在场性”。例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最早必须被视为与建筑空间是一个整体,较为典型的是圣伯多禄锁链堂的《摩西像》。面对这件雕塑,我们不是仅仅去“看”,而是在一系列的视听体验中包含着“看雕塑”这一动作。从这些意义上说,极简主义及此后的前卫雕塑实践无非是朝向“独立存在”的回归,而非早期现代艺术纯粹的、机械的、脱离社会情境的形式主义进路。唯有如此,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作品《等价物8》才能在当代艺术叙事中保有合法性。1972年,卡尔·安德烈在英国泰特美术馆的展厅中平铺120块耐火砖,在场的观众以及当地的媒体和艺术界,都对这件作品大为诧异。120块耐火砖以矩形排列在当代艺术展厅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便足以形成这件雕塑作品的“剧场性”。而作品在现场对于美术馆的“占领”,形成一个空间情境,正是借助了寻常之物耐火砖与美术馆空间锃亮木质地板的“物性”:廉价的建筑材料何以登堂入室成为昂贵的艺术作品?
对于“在场性”之关注的另外一个方向,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大地艺术”(land art)实践。将雕塑还归其物质存在的本来场所,在非展厅、非人造空间的环境中凸显其物质存在,是大地艺术的重要诉求。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最广为人所知的作品《螺旋形防波堤》,除了调用外部的景观资源,同时也讨论了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即能量处在不断“熵”过程之中的状态。时间性进一步参与到作品的完形中,作品使我们“忘记了未来而不是想起过去”,“过去和未来都被放入一个客观的现在之中”。最终,艺术家以作品本身物质的消逝完成了一场反纪念碑的“新纪念碑”创作[6]。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雕塑材料本身的“在场性”,是通过创作者、观看者双重主体与“物”的交互来实现的,即所谓的“具身性”(embodiment)。就创作主体来说,雕塑艺术家更多地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中介,经由姿态、动作连接技术,借助手感与触觉连接材料。罗伦佐·吉伯尔蒂(Lorenzo Ghiberti)早在15世纪就断言欣赏雕塑不能仅仅用眼睛来看,更应该通过触摸来实现,而雕塑家便是其作品最初的观者[7]。雕塑家面对材料时,并不是单方面地对后者进行利用和改造,而是在此过程中与材料形成交互关系。例如,揉捏黏土时不断产生的触觉感受,形体在空间中逐渐生成、彰显的过程,就是这种“人—物”的交互过程,这实际上也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物我两忘”有相似之处。
同样地,在雕塑的场域之中,观者感受体量、质地、结构造成的总体感觉,并自愿投入雕塑造成的综合的情境之中。我们知道,雕塑是需要身临其境的艺术。就像我们如果要了解一幢建筑的构造,起码要制作出建筑的模型。雕塑也正是如此,我们最多可以通过在尺度上将其缩小,尽管这完全无法替代真实的“在场性”。实际上,雕塑的“具身化”属性确实和建筑空间的功能类似,即在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中激发行动与事件的主体能动性。以此来说,欣赏雕塑作品绝非一种孤立的艺术欣赏行为,而是在观看作品的同时召唤“我”之知觉和意识,并与作品融为一体。这一点在美国艺术家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耗时近半个世纪(1970—2022)才新近完成的大型雕塑作品《城市》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件位于内华达沙漠里的作品由一系列建筑空间、雕塑构成,材料则完全取自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观众在其中徜徉以至“迷失”,主体的肉身与材料之间的边界逐渐消逝,并最终相融于作品构成的整个“纯粹城市”的情境中。
四、变化中的雕塑:虚拟物的介入
在层出不穷的新材料中,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物质性的材料介入雕塑,开始变得普遍,诸如声音、气味、光线、电流等。但正如前文提及的,雕塑在历史中一直具有“跨媒材”属性。例如,古典时期的教堂中的雕塑与音场、光线和构造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一系列的新材料、新技术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数字构成的“虚拟物”(virtual object),因为它在根本上改变了雕塑材料物性的形态,实现了材料物性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转换。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用“数码第三持存”(1)相对于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说的第一持存(当下的记忆)及第二持存(记忆)。来定义这些“对记忆和时间因素的物质上的空间上的复制,人工地将其保存下来”的事物[8]。对于当代雕塑来说,以建模、参数化、AI算法为主要手段,以数码物为主要元素的方式重新构建了当代雕塑的创作模式。为了不落入技术社会“为技术而技术”的怪圈,选择与艺术家主体契合的材料与技术是其创作在内部自洽的关键。遗憾的是,时下流行的科技艺术,大多停留在具有“科技感”或讨论科技话题的范围,而非将科技本身视为新材料。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长期采取的“艺术—科学”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艺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下,艺术家在抉择某种材料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具身化”的过程。就虚拟物来说,也许进入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谓的“赛博格”(Cyborg)状态中,将技术与主体(人或其他有机体)进行综合,从而创造出更符合新时代语境的雕塑作品。
虚拟物的介入,使雕塑概念的外延继续扩大。过去不认为是雕塑的实践,现在也可以被视为“新雕塑”。以2010年在英国成立的艺术小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为例,小组成员来自艺术、建筑、自然科学、法律、新闻、IT、历史等领域,他们通过调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争议性案件,运用跨学科的方式重新还原事件现场,包括3D还原动画、制作空间模型、地图数据等,以期为案件的审判提供更加直观的视听化的数码证据。这种创作通过重“塑”真相,成功地让艺术实践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数码雕塑。又如,202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AR公共艺术节上,策展人和艺术家在泰晤士河沿岸布置了30个数字互动雕塑,游客使用手机程序来搜寻、欣赏这些介乎真假之间的公共艺术作品。该作品除了讨论虚拟体量与真实空间的虚实关系,也不失为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下,当代雕塑的生态、低碳、可持续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材料之于雕塑的优势在于其高效的传播,以及突破了原本需要身临其境观看的限制,为雕塑在当代的持续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结语
对雕塑材料的“物性”与其背后观念表达的讨论,并非要雕塑回归到一种本质主义的框架中,而是为了在“泛雕塑”的状态中重新确立雕塑可以触及观念表达的边界和可能。对于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来说,对历史及现实中材料“物性”及其技术的重新审视,将有助于我们确立在全球雕塑实践中的民族坐标。正如我们在本文讨论的那样:选择何种材料将会影响雕塑作品的立场与观念。雕塑材料的“艺术/技艺”自有属于其自身的时代性烙印,最终构成了形神兼备的雕塑作品——“器”与“道”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