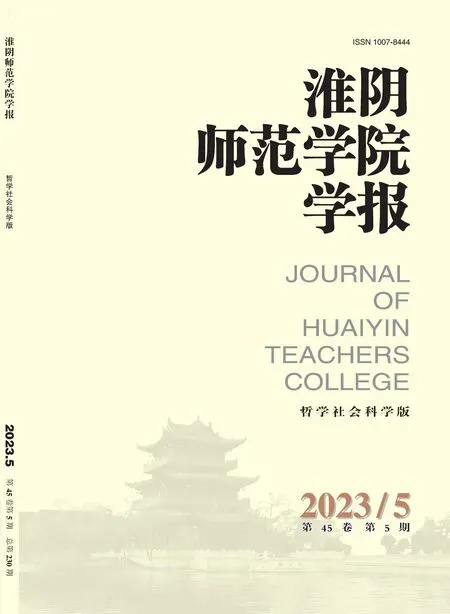《读史方舆纪要》所记长江及顾祖禹的江防军事思想
张文华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长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还体现在作为天堑的军事价值方面。早在三国时期,面对江面宽阔、波涛汹涌的滚滚长江,魏文帝曹丕就发出“天所以限南北也”[1]的慨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作为古代军事地理的集大成之作,自然对长江格外关注。在“川渎异同”篇中,顾祖禹较为细致地记述了沿江地理条件,江流之广狭缓急,支脉之汇散分合,江防之险易变幻。在“南直”“湖广”“四川”诸卷中,重点记述了沿江军事重镇要隘及其攻守形势。这些记述,以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为指导,揭示了长江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渗透着顾祖禹的江防军事思想。长期以来,“川渎异同”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与研究。本文拟以“川渎异同”所记载的“长江篇”为核心,探讨顾祖禹的军事地理主张及江防军事思想,冀以丰富对“川渎异同”的认识,深化对顾祖禹思想的研究。
一、《读史方舆纪要》所记长江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军事价值
顾祖禹对长江的记述,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兹分述如下。
(一)注重对长江总体情况的概括,力图揭示不同江段的水文特征及其军事意义
顾祖禹在“川渎异同”中记述诸大川流移变化,往往是从比较的视角展开的。“四渎”之外,汉水也是一条大河。北方的河、淮、济,南方的江、汉,这五条河流的河情、水性不同。大体而言,河无常,江广大,汉屈曲,淮襟要,济早夭;江、河长,淮、汉短;河、汉浊,江、淮清;黄强淮弱,江清汉浊。在“川渎异同”中,顾祖禹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概述了长江的总体特点,他说:“川之大者,大河而外,莫如大江。然河流朝夕不常,江流亘古不改,周匝西垂,吞吐百川,江诚浩博矣哉。”[2]5446长江是与黄河并驾的大河,长江支流众多、水系发达,江流浩淼博大,这些都是符合长江实际的。但他所说的“江流亘古不改”仅是相对于变化无常的黄河而言,其实长江的荆江段和下游段,河道变迁还是比较大的。
长江浩荡悠长,跨越多省,流经地域地理形势不同,各段的河道、水性特点各异,对此,顾祖禹多所用力,作出了比较具体的描述和揭示。对于长江上游河段,顾祖禹引《舆程记》云:“自江源至成都九百九十里,水不甚急。自泸州以东,长川巨浸悉委于岷江,而波流益以浩衍,百石大船,止于泸州。自泸以西江水渐狭也。由瞿唐而下,谓之峡江。”[2]3114就水势而言,从江源至泸州段江流阔狭不常,或缓或急,尤其是嘉定州以上段,重山曲折,水流迅疾;泸州以下大川汇集,水量大增,江深岸阔。就通航而论,嘉定州以上“崖高流迅,牵挽益艰”[2]5449;泸州以下虽然滩碛间列,但“江淮朦艟,可以溯流而达”[2]5449;瞿塘峡以下的三峡段,两岸连山,重岩叠嶂,蔽日隐天,诚为山川之奇胜,谓之峡江。峡江段波涛澎湃,“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能及也”[2]3114。
长江中游的荆江段情况比较复杂,顾祖禹根据晋人郭仲产《荆州记》的记载作了细致的描绘。江流刚出三峡段时,水流迅猛,势若建瓴,尤其在夏秋泛涨之际,一泻千里。但夷陵以上,由于两岸山阜耸峙阻挡,并不能形成泛滥之灾。自嘉鱼以下,江面浩阔,水流顺直,水势迅疾,但由于两岸地势低平,平衍下湿,容易发生漫流。尤其是江陵至嘉鱼段,河道迂回屈曲,来水量增大,决口泛滥多发生于此。“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之间,江流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迂回,至岳阳复自西南转东北,湖水迸流,易于涨遏,故决害多在荆州。夹江南北,往往沿岸为堤,咫尺不坚,千里为壑矣。”[2]5451-5452荆江段沿岸筑堤,势如水上长城,成为长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这里河道曲折,水流势猛,“咫尺不坚,千里为壑”,成为新的忧患。
长江下游河段,顾祖禹重在描述其洲港河汊的特殊地理条件和军事价值。湖口以下望江县段的雷港口,地处南直、湖广、江西之交,“犬牙相错,滨江环峙”[2]5455,为军事重地。安庆府有皖口,桐城县有枞阳口。池州府有梅根港,铜陵县有丁家洲、荻港,池州江段“汊港丛杂,戍守切矣”[2]5455。无为州有泥汊河口、鲁港、裕溪口。太平府有牛渚,和州有横江浦。应天府有江浦、瓜埠口、黄天荡、龙潭,这一带“洲港错杂,防闲未易”[2]5457。镇江府有瓜洲,为“天下之吭”[2]5457。常州府有孟渎口,江阴县有夏港。这些洲浦港汊,既是重要的军防戍守据点,也是敌军掩藏屏蔽的天然凭藉。
顾祖禹十分重视山川地理的军事意义,但他一再强调地非有恒常,一则不同时期军事形势不同,二则地理条件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长江下游的水陆形势变迁较大,顾祖禹再三强调。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的采石,西接乌江,北连建康,这里江面狭窄,自古以来即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渡口,古代北方军队南下进攻江南,大多由长江西岸的横江浦横渡采石,所谓“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2]883,因而采石素为渡江要害,“形胜莫重焉”[2]5456。但顾祖禹指出,采石的这种地理形势在明末清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沙洲横亘”,“延袤相接,益复回远,滩浅错杂,舟行甚艰,故道出采石者益少”[2]5456,采石已不再是最为有利的渡江之地了。鉴于此,顾祖禹不无感慨地说:“天地之气,日就迁移,山川形胜,岂有常哉?”[2]5456应该说,这不仅仅是针对采石地理变迁的喟叹,更是在强调宇宙自然的变化规律了。顾祖禹指出,采石自然地理形势的变化,必然引起军事防御地理空间格局的改变,“昔人言京口、采石,并为东南重镇,而采石江岸比京口为狭,故备采石者恒切于京口。乃今昔变迁,京口江面殆更不及昔时之采石矣,安得不以备采石者转而备京口乎?”[2]5457
长江江阴段,靖江的水陆变迁最大。江北岸原来自泰兴以东为如皋县南境,大江距离县城约六十里,而靖江县在江阴西北,隔江相望,有四十余里。靖江孤悬江中,被视为京口外卫。但至明末清初,情况已经大变,顾祖禹指出:“今北面湮为平陆,东北与如皋接,西北与泰兴接,而东西南三面屹峙江滨,与江阴、武进为唇齿之势云。”[2]5458海门原在通州以东一百余里,为江、海出入之门,但随着江海的不断变动,海门的海陆形势大变,顾祖禹指出:“今海门益沦于海,形势又一变矣。”[2]5459
此外,顾祖禹对各段江流的广狭缓急十分关注,并作了较为具体的记录。如华容县江段,“江流深阔,商旅往来,所在辐辏”[2]5452。九江段,“江流至此,阔二十余里,波涛浩瀚,谓之浔阳江”[2]5454。池州段,“梅根港而上,江岸颇狭,今南北往来者往往截流而渡,南至池州出江右走闽、广,北自庐州走濠、寿趋徐、汴,为捷径云”[2]5455。梅根港以下又东北二十里为大通驿,自大通驿而下,“江面阔三十余里,上游之险莫过于此,又兼汊港丛杂,戍守切矣”[2]5455。无为州繁昌县段,“江面阔二十余里”[2]5456。南京段,“南北两岸阔四十里”,“江流险阔,气象雄伟”[2]5457。镇江段,“渡瓜洲,江面不过七里有奇”[2]5457。常熟、通州段,福山、狼山“二山隔江相对,江岸阔几八十里,……江流浩淼,风帆倏忽”[2]5458。入海处的海门段,“波涛汹涌,与海相接”[2]5458。这些记载,既扼要地说明了各段江流的水文特点,也揭示出不同的交通形势及军事地理特征。
总之,顾祖禹对长江总体情况的概括,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长江的河性特征,对不同河段具体特点的描述,有助于从微观上把握长江各段的水文差异和军事防守策略。
(二)注重记载长江支脉之汇散分合及名称之歧出变化
长江流程最长,沿途吞吐湖沼,吸纳百川,支脉众多,顾祖禹对此多所留意。长江在成都府内支汊较多,有南江、北江、内江、外江之分。顾祖禹云:“今大江自松潘叠溪而入茂州界,西南历威州转而东,经汶川县南,又东南经灌县西北,又东南流出灌口,过崇庆州新津县而入眉州境者,此汶江之正流也。成都人名之曰南江。其自灌县西北离堆薄灌城而东北注,历新繁西南,郫县南及府城南而会于新津之大江者,此秦李冰所凿石犀渠也。成都人谓之北江。北江又分为两:出灌县东北宝瓶口,又穿三泊洞而北注,经崇宁、彭县、新繁、新都而入汉州雒水,东南流为金堂河者,所谓湔水也。成都人名之曰外江。其自宝瓶口直东入五斗口,东北经崇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界内,过府城北折而南,会府城前江,经双流入眉州合于大江者,成都人谓之内江,此成都府境之内江、外江也。”[2]3132
再如,长江在宜都县至松滋县之间又多有分流。顾祖禹云:“大江自宜都县北,东流七十余里而经枝江县城北。江流至此分而为二,间以大洲,谓之百里洲。洲之北曰北江,南曰南江。《禹贡》‘东别为沱’,即此地也。又东南流七十里而经松滋县城北,江流至此复支分为三派,名曰川江。”[2]5451长江在岳州府境接纳了澧水及洞庭湖之水,形成三江汇流之势:“大江经岳州府城西北十五里之城陵矶。洞庭之水自南而北由此注于大江,谓之荆江口,亦谓之西江口,又谓之三江口。以洞庭及澧水与大江并会于此也。”[2]5452
长江接纳百川,流经不同地域,由此产生了诸多异名俗称。如,长江在重庆府境内有南江、内江、外江之分,其名亦多有异称。长江正流在威州、茂州之间称为汶江,而成都人俗称之为南江;石犀渠成都人俗称之为北江、前江,北江亦曰郫江;湔水成都人俗称之为外江,内江亦曰流江。长江正流经崇庆州西北五十里,又南称为味江,又东南流经新津县城南,亦谓之皂江。长江在彭山县东北二里,其支川自灌县分流,经成都南境者于新津、彭山之间又依次流入汇合,经县城东者谓之武阳江,南流经眉州城东者谓之玻黎江。长江流经嘉定州城东,亦谓之通江;至城东南而大渡河合青衣江之水自州西南流入汇合,又兼有合水之称。长江在泸州府境,又有外水之称。长江江流异名纷繁众多,大体而言,“自汶川县而南,往往随地易名,不可更仆数也”[2]5447。
(三)择要记述沿江的重镇要地,阐发江防之险易变幻
长江江流浩荡,素为天堑,沿江重镇要地星罗棋布,顾祖禹择其要者提纲挈领地叙述,意在突出长江之军事地理价值,同时也竭力阐发江防之险易变幻。长江流经威州北三十里的高碉山下,这里是唐代维州城故址所在,“三面临江,号为险塞”[2]5447。长江流经汶川县治西,“曲折环流,蜀境西北之保障也”[2]5447。重庆府“居内、外二水之间,凭高据深,为全蜀之襟要”[2]5449。三峡为长江沿途所经最为奇险之地,顾祖禹综合多种文献资料,做了十分精彩的记录。
长江荆江段亦为险要之处、战略重地。顾祖禹云:“大江自松滋县东北流百二十里而至荆州府城南,府翼带江沱,称为都会。府东二十里曰江津口,江水支分于枝江以东者,至此洲尽而流合,势益盛。昔时滨江置戍,为江陵重地。”[2]5451荆江口“控据要津,为湖南、北之喉吭”[2]5452。汉阳府城与武昌府城相距不过七里,二城隔江相对,“为矜束之处。天下有事,无不注意于此者”[2]5453。武昌府至黄州府江段,“南北纷纭,江滨多故,此皆烽火之区矣”[2]5453。九江段之江流浩瀚,战略地位亦显赫,顾祖禹云:“又东南五十五里即九江府城也。江流至此,阔二十余里,波涛浩瀚,谓之浔阳江。……亦谓之九江。古称湓口重镇,中流矜带,盖府城当吴、楚之要会,不特江右安危视九江之缓急,而上游之势,淮南、江左祸福与共,所谓地有常险者非欤?”[2]5454湖口为江西之噤吭,湖口以下的彭泽县段,江心有小孤山、马当山,均为“江津之险”[2]5455。安庆府有皖口之险,“特立江滨,江环三面,屹为形胜,盖南畿上游之屏障矣”[2]5455。池州段梅根港以上江流狭窄,为南下福建、广州及北上徐州、汴州的捷径,梅根港以下的大通驿段江流开阔,汊港丛杂,“上游之险莫过于此”[2]5455,为戍守重地。仪真县“控临江津,南北往来,亦利涉之所也”[2]5457。镇江府的金山、焦山,“皆控扼江津,并称形胜。然金山近在津途,尤为要会,扬帆击楫,必以金山为表识矣”[2]5457。常州府西北之孟渎口,“为戍守要地”[2]5458。常熟县福山和通州狼山隔江相对,“滨江置戍,恃为门户之险”[2]5458。
顾祖禹在记述沿江险隘要地时,秉持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审视其军事攻防形势和战略价值。他指出,“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2]1,但山川形胜并非恒常不变,“险易固无定形”[2]5459,社会政治形势也一直在变,因而江防“安可一律论欤?”[2]5459他举例说,采石江面狭窄,江滨旧有沙洲,横列矶下,这里自古为渡江重地,但后来由于江心洲的发育演变,新洲沙渚越来越多,横亘绵延,采石已“非利涉之道矣”[2]5456,取而代之的是京口。这种变化,既有采石交通条件恶化的因素,也是国家漕运粮饷和防范倭寇的现实需要。这些客观形势共同促成了京口与采石一升一降、一起一落的联动关系。顾祖禹指出,京口战略地位的崛起,符合事物发展变化之常理,“昔日之采石比京口为重,而今日之京口比采石为切,消息之理也”[2]1250。京口地位的变化,进而影响东南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再如靖江,原在江心,孤悬江中,与京口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但后来由于沙洲变迁,北面湮为平陆,与如皋、泰兴连接起来,而东西南三面屹立江滨,这使得靖江与江北的如皋、泰兴成为一体,与江南的江阴、武进夹江而峙,“为唇齿之势云”[2]5458。
长江固然为天堑,沿江的重镇、要塞、险阻堪为军事堡垒,但顾祖禹指出,江防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如长江南岸常熟县北四十里之福山镇与长江北岸通州南十五里之狼山镇,隔江相对,虽然沿江置戍把守,“恃为门户之险”[2]5458,但由于江面辽阔近乎八十里,“江流浩淼,风帆倏忽,欲却敌于江中,未易言也”[2]5458。可见这里虽为重要防守门户,但防守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易言也”暗示了其中的无奈与玄机。号为江、海出入之门的海门因海陆变迁,形势为之一变。崇明岛环海孤悬,沙渚迂回,是长江口的天然防御屏障,但也仅是“自守则有余,制敌或未足”[2]5459。有鉴于此,顾祖禹特别强调指出,悠悠长江,重镇要隘所在皆是,“然用之得其当,则节节皆险,失其宜,亦处处可渡,险易固无定形矣”[2]5459。江防之险易变化,不可一概而论。
二、顾祖禹的江防军事思想
长江作为我国一条悠长宽阔的大川,其重要的军事防御价值素来为人们所称道,“或称为南北之限,或恃为天堑之防”[2]5459。然则究竟如何防守长江,长江的防守应该放在怎样的战略视野下展开,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布局,采用何种作战方式,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分析和评论。顾祖禹在深入分析历代争战、政治纷争和攻守形势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前贤的思想认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江防思想主张,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从军事战略看,守江必须守淮、汉,注重长江上中下游之间的战略联系
三国时吴国大将陆抗云:“议者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此守国之末务,非智者所先也。”[2]5459顾祖禹对陆抗的主张深表赞同。他从更为开阔的军事战略视野出发,指出长江的防守不能仅仅依凭长江之险,以江防江为守国末务。顾祖禹认为军事防守需要保留较为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并举例论证说:“譬之御盗者御盗于垣墙之内,垣墙一坏,而举家之人心胆堕地,何能复与敌战哉?然则守剑阁者不以剑阁,守瞿塘者不以瞿塘可知也。”[2]3096由此他强调守江必须守淮、汉,且需注重长江上中下游之间的战略联系。
长江上游的汉水和下游北部的淮河是江防最重要的两条外围防线。在中国古代南北对峙时期,淮河始终是东部重要的政治、军事分界线,成为江防的一条天然屏障。顾祖禹云:“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2]887长江阻隔南北,而守江莫如守淮,建都南京的政权,“必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2]918。汉水为长江中游最大支流,汉水之险虽不及长江,但其对江防的意义十分重大,“汉亡江亦未可保矣”[2]3500。江与淮之间、江与汉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战略关系,“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2]3500。淮河防线的战略意义在于将北方来敌拒于淮河以外,江淮之间成为军事缓冲地带,从而为南方争取战略主动,否则弃淮不守,“则与敌共长江之险”[2]887,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可被敌人用作潜师之地,其可相机渡江,成为江南政权的心腹之患。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淮南的得失成为江南地区政权盛衰存亡的关键,顾祖禹举例说:“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所并。唐末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能度淮,杨氏遂能以淮南之境与中原抗。五代周取淮南,而李氏之亡不旋踵矣。”[2]887可见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南政权危矣。
淮防、汉防对江防意义巨大,淮防、汉防之间亦需紧密配合、齐头并进,才能取得最佳的防守效果。与淮河防线相比,汉水防线位于长江中游,其以居于江南政权“上游”之战略优势,发挥着对江南政权的屏蔽保护作用。汉水防线一旦失守,敌人便可沿江顺流而下,高屋建瓴,直捣南京,淮河防线不攻自破。汉水防线的得失,关系着南北政权的战略发展方向。北方政权控制汉水,可以吞并东南;南方政权控制汉水,可以进图西北。因此建都江南的政权,无论是消极的东南自保,还是积极的问鼎中原,均需将保淮与保汉、用淮与用汉结合起来,所谓“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问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2]3500-3501。淮、汉的防守控制,也可起到均衡南北政权军事势力的作用。如三国时吴国不敢涉淮而攻取魏国,魏国不敢绝江而攻取吴国,重要的原因在于“吴据荆、扬,尽长江所极而有之,而寿春、合肥、蕲春皆为魏境,……盖其轻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2]916。淮、汉之间的战略联系,在南方政权内部的争斗中也有所体现。顾祖禹云:“自楚武伐随,军于汉、淮之间,自是汉上之地渐规取之矣。”[2]3500吴国讨伐楚国,与楚国夹汉水而对峙,楚国便处于危险境地。顾祖禹指出:“楚之失始于亡州来、符离,其再失也由于亡汉。”[2]3500可见楚国战略上陷于被动,一是因为失去了淮河防线,二是因为失去了汉水防线。
长江的防守,除了要处理好淮防、汉防与江防的关系,还需注重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之间的战略联动关系。长江浩淼悠长,上中下游地区的战略地位不尽相同,但其间存在着密切的战略联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江防必须将上中下游视为一体,互相支援配合,联防联控,增强整体防御功能。顾祖禹指出,长江上游的蜀地为“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取之先资也”[2]3095,蜀地的得失关系着南方政权的盛衰存亡,“欲取江南,宜先取蜀,取蜀而江南可平”[2]3095,因此古来争夺天下者,“莫不切切于用蜀”[2]3094。譬如,曹魏欲灭吴,则先攻打蜀,等到蜀国攻破,“而王濬楼船自益州下矣”[2]3094,通过“经略上游,屯寿春,出广陵,则吴以亡矣”[2]916,由破蜀而灭吴成为自然之势。隋人以巴蜀之资为平陈的根本,“杨素以黄龙平乘出于永安,而沿江镇戍,望风奔溃”[2]3095。南宋张浚担心金人据陕窥蜀而东南不可自保,于是全力加强蜀地守备。顾祖禹云:“宋人保东南,备先巴、蜀,及巴、蜀残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2]3128-3129“终宋之世,恒视蜀之安危为盛衰。”[2]3095上游的蜀地对于下游江左的军事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顾祖禹特别强调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上游”,“国之安危,系于上流而已”[2]3517。长江出重庆、夔州后进入湖广地区,湖广居于八省之中,“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2]3516。长江中游所在的湖广,一则位居江南政权的上游,二则有襄阳、武昌、荆州形胜之地,因而战略地位至关重要。长江在湖广境内自西而东回环曲折长达一千八百里,在南北相争时期,“沿江上下,所在皆险,盖不特楚地之襟要,又为吴会之上游也”[2]3500。对于江左政权而言,湖广实为国之西门,因而六朝立国格外增重上游,“江左大镇,莫过荆、扬。扬为京畿,财赋所资;荆为阃外,甲兵所聚。……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此立国之大要也”[2]159。顾祖禹指出,武昌水要,荆州路要,襄阳险要,“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2]3484。湖广“三要”在不同的战略视域中地位都十分显赫,势必成为争夺的焦点、防守的关键所在,“六朝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耳”[2]159。
总而言之,长江上中下游的防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策应和联动的,只有将长江上中下游视为整体,呵成一气,江防的威力和效果才能很好地显现。
(二)就江防本身而言,需加强沿江重镇门户的防范
悠悠长江,道里悬远,虽称天堑,而沿江津梁渡口,抑或不少,长江的防守诚非易事。“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2]887对此顾祖禹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引孙吴光禄大夫纪陟语云:“长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处,犹人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2]885应该说,纪陟的这几句话道出了防守长江的若干秘诀,即大江虽然浩荡悠长,全面防守力不从心,但善守者关键在于守其门户,所谓“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处”,“其护风寒亦数处耳”,即是指此而言的。顾祖禹对沿江一带险要必争、堪护风寒的渡口、要隘、重镇格外重视,在“历代州域形势”、各省的总叙、各府州的小序中扼要概述其战略价值、军事形势,在各府州的小序之后又具体叙述发生于此的战争。他再三强调,旨在说明这些重镇要害在江防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
县级思想宣传机构发展缓慢,更有甚者举步维艰,公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县级传统媒体快速流失用户,受到新媒体猛烈的打击。短视频可谓是更为彻底的手机原生态产品,流量大规模从传统媒体倾泻般涌入短视频,俨然已是当今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时,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5G大规模商用之后,用户观看视频时长还将大幅度上升,大概率会出现视频APP使用时间多于社交通信APP的情况,而社交通信类APP也面临视频化和三维化的发展压力。基于此,短视频建设将是县级融媒体建设不可或缺的战略重镇。
大体而言,沿江一线最为关键紧要的渡口主要有七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云:
古来都建康者,以大江为要会。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十郡之间,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2]885
这七处津渡都在大江之南,属于今长江中下游,可分为三个区段,即上流的公安、石首、北津,中流的武昌、采石,下流的宣化、瓜洲。这几个渡口沿江散布,控扼着一方局势,成为防范北方来敌涉江南渡的必守之地。顾祖禹引王应麟语云:“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据武昌之津,使自汉水者不得进;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据瓜步之冲,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守江之策也。”[2]885-886
沿江地区的重镇、险隘亦数量众多,其中最为重要者约有如下数处。长江上游重庆府的江州、夔州府的瞿塘关,中游荆州府的江陵、武昌府的夏口和武昌、襄阳府的襄阳,下游南直隶的东关、京口和广陵。
江州城扼“内、外二水”“控瞿唐之上游”[2]3271,为水路要冲、咽喉重地,经由长江水道攻伐蜀地者,无不首先以攻克江州为要务。占领江州,“御利、阆,蔽夔峡”[2]3271,既可防御来自嘉陵江流域利州、阆中的军事威胁,也能屏蔽扼控夔州府三峡之险,从而为保全蜀地获得根基。瞿塘关亦即江关,在夔州府城东八里,以瞿塘峡而得名,“瞿唐峡为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2]3122。瞿塘关依瞿塘峡而设,地势险要,居于荆楚上游,扼控蜀东门户,既为巴蜀之喉吭,又为荆楚之襟带,对于上游的巴蜀和下游的荆楚具有双重的军事意义。
荆州、武昌、襄阳为湖广形胜,荆州为全楚之中枢,武昌为东南之锁钥,襄阳为天下之腰膂,这三地既有突出的战略价值,也是中游江防的要害所在。荆州府城江陵,“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2]3652。顾祖禹指出,江陵位居江右上流,为江东之屏蔽、巴蜀之门户,与襄阳、武昌、长沙构成辅车相依之势,关系着四方军事政治局势,“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2]3652,因此江陵为江防必争之地。对于武昌,顾祖禹云:“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曰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2]3484东南政权上流之形胜在武昌,因此武昌成为孙吴以后历代江南政权江防的重要门户。夏口亦称汉口、沔口、鲁口,在武昌府城西,适当江、汉之交,位置冲要,素为兵争重地,“六朝之际,上流有事,夏口为必争之所”[2]3520。武昌、夏口均为扼江险要,二者形成犄角之势,里应外合,缺一不可,顾祖禹以具体史实论证说:“刘表使黄祖守此,孙策破之,霸功始立。孙权因之,筑城夏口,建都武昌,屹为重镇。及晋人南下,使王戎袭武昌,胡奋袭夏口,岂非以地居形胜欤?自东晋以后,谈形势者未尝不以夏口、武昌为要会。”[2]3520
汉水为长江中游最大的支流,襄阳位于汉水之滨,虽不在长江干流,但其对江防的意义重大。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2]3701,地形四通,为水陆之冲。襄阳控扼汉水门户,由襄阳可直抵大江重险夏口。襄阳以其上流门户之势,与江左的建康在军事上形成左右臂的战略关系。
京口和广陵夹江而峙,一南一北,密迩京师,在在为建康之门户,东晋以来皆为重镇。广陵为江南政权的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2]1113,把守住广陵,既可保守淮东,也可屏蔽江南。京口因山为磊,凭江为险,控扼大江,为建康之东门,南北对峙时期京口为必争必守之地,京口的防守形势直接关系着建康的安危,顾祖禹指出:“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门户,锁钥不可不重也。”[2]1249
对沿江各个津渡、险隘、重镇的个别防守诚然格外重要,但其间的相互配合与支援也不可轻视,否则会出现一地失防、门户洞开的局面,江防陷于被动。如陈末隋军兵临大江,樊毅分析当时形势说:“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2]882采石、京口犹如唇齿,唇亡必齿寒,采石失守,京口失防。后来韩擒虎率五百士兵连夜从采石渡江,陈朝大势已去,随之灭亡。“缘江上下防扞”道出了江防内在的战略联系,应该成为江防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因势而变,形成合理的战略防御格局
一般而言,长江的防守,主要是指南方政权针对来自北方政权南下进攻而展开的防御,表现为南北方向上的江防关系,这在南北对峙的历史时期尤为典型。南北向的江防,在防御格局上重要的特点是屯兵据要多在江南,而破敌制胜多在江北。顾祖禹引张栻语云:“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2]916这种格局决定了江北沿江重镇要隘对江防的重要意义。江北的防守,中游重在守汉水,下游重在守邗沟和巢肥一线。汉水为长江中游之门户、下游之屏障,保汉水则中游无患、下游无虞,失汉水则中游失控,敌可以建瓴之势顺流而下,往往所向披靡。长江下游江、淮之间有两条重要防线,东线邗沟和西线巢肥一线,北方南下一般走东线,自当加强防范,但西线亦为重要通道,不可轻忽。在实际的防守中,须根据客观军事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防守策略,中下游配合、东西线并重,加强联防,大江庶几可守。
除了南北向的江防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东西向的江防。顾祖禹云:“嘉靖间倭寇充斥,东南糜烂,于是江防、海防之议益起,沙洲浦渚,节节为防,详且密矣。”[2]886明代由于倭患兴起,充斥东南沿海一带,如何防范倭寇溯江而上祸乱沿江地区成为当时江防的重要内容,江防形势发生变化。防范倭寇,虽然可以充分利用沿江沙洲浦渚等地利条件节节为防,防守据点既详且密,但顾祖禹仍然指出,江防形势多变,不可守株待兔,“然而机变无方,风帆迅疾,未可绳以守株之见也”[2]886。顾祖禹赞同唐顺之的江防观点,从宏观的江防战略出发,提出分层设防的江防思想。根据长江的江流广狭及地形地势特点,江防有三重门户,“江口蓼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海面阔百四五十里,此江防第一重门户。江北周家桥与江南岸圌山相对,江中有顺江洲为两岸分界,周家桥南至顺江洲江面止六七里,顺江洲南至新洲夹江面止七八里,新洲夹至圌山江面不过十四五里,此为江防第二重门户。京口、瓜洲南北相对,江面不过十八里,此江防第三重门户也”[2]886。“三重门户说”本身,虽非顾祖禹提出,但为顾祖禹所认同,也是其分层设防江防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防御将重点防范和全面防范结合起来,有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形成了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的空间防御格局,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实践上具有战略成效。
江防门户的防守,在具体防御中,须利用微观地形条件,把守战略据点。顾祖禹对此作了细致分析,他说:“唐、宋以来,滨江洲渚日增,江流日狭。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渡口与江心金山寺相对;自瓜洲而东十八里为沙河港,其东南与江心焦山寺相对,亦谓之沙坝河,旧与白塔、芒稻二河俱为泄水通江处;又东五里曰深港,俱东面设防处也。又东五十余里曰宝塔湾,为盐盗渊薮,其南岸汊港可进圌山。又东南四十五里曰三江口,亦曰新港。又东至周家桥四十里,正与江南圌山相对。中有顺江洲,江面稍狭,水流至急,此处扼守,则瓜、仪可保。此为金陵门户,江心要会。有一字港,上接圌山十里,下接三江口十里,官兵可以驻扎。贼繇通州狼山而西,宜于此泊守。若一入新港,登岸为卞家坟、周家坟,稍西则扬州矣。此新港为可以登岸可以入海之要口,江防最切处也。”[2]1117-1118这里所谓的“俱东面设防处”“此为金陵门户,江心要会”“江防最切处”,均是指江防必须扼守的关键要害所在,只有占领了这些军事制高点,江防才能得心应手,否则便会受制于人。由于京口至建康沿线高冈逼岸,宛如长城,不容易登犯,因而第三重门户“江岸之防惟在京口”[2]1250;京口以东至孟渎的七十余里间,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港汊之地众多,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因此第二重门户“江中置防则圌山为最要”[2]1250。
(四)因地制宜,选择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
在冷兵器时代,行军作战无不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就江防而言,如何结合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身优势选择合适的防御策略和作战战术便显得格外重要。在顾祖禹看来,江防的基本策略应该是全面防御与重点防御相结合,注重平时的巡逻预防与战时各据点的配合,坚持战守并用的基本原则。《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引宋人汪立信语论证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三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江,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互相形援,以为联络,率然之势,此上策也。”[2]885这是说,长江的防守需在沿江部署防御据点,配置守将,在尤其关键紧要处须增加兵力作为重点防御基地,平时加强沿江巡防,战时各据点齐头并进,相互支援配合,如此可取得防御的最佳效果。顾祖禹指出,以守为战、以战为守有机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防御策略。
由于江南江北地理条件不同,江防作战的方式也应因地制宜,或以战舰扼控,或以战车抵挡。就长江下游而言,江南水势浩瀚,须用战舰,江北地势平坦,须用战车,“建康自古用武之地,然必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夫大江以南,千里浩邈,决欲控扼,非战舰不可。大江以北,万里坦途,欲扼长驱,非战车不可”[2]918。
以水代兵是利用水泽之地的特殊条件,筑堰蓄水,以水漫淹,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吴大帝筑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王凌请攻讨,而司马懿不许。诸葛恪一城东兴以遏巢湖,而魏之三将数十万之众皆覆没于堤下”[2]896。以水代兵是古代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战方式,“堰水以固圉,未为非策也”[2]896。顾祖禹对此颇为留意,《读史方舆纪要》中亦多所载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