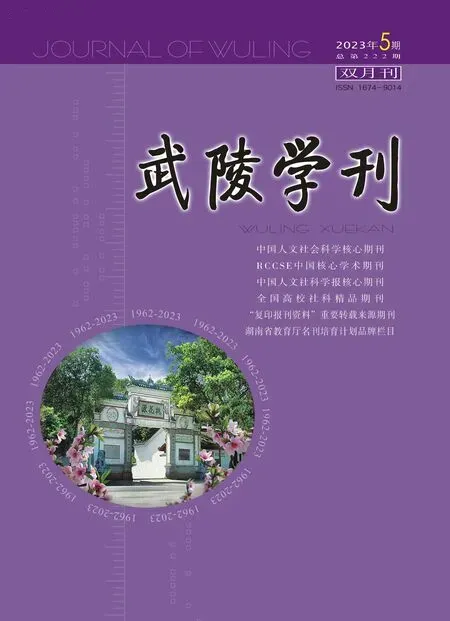清代乡规民约的道德审视
——以《圣谕广训》为核心
韩 金,严蓓蓓
(南京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正式乡规民约为北宋关学代表吕大钧创立的《吕氏乡约》,属于村民自治行为,与官方无关。明朝时期,王阳明作为地方官员,订立《南赣乡约》,乡规民约被纳入官治范畴。至清代时,顺治帝开始提倡乡约,康熙、雍正两皇帝分别作《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正式推广乡约,乡规民约从此成为御治工具,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
一、清代乡规民约的发展脉络
清朝入关后,为了迅速稳固政权,积极借鉴中原政权社会治理的诸多办法,在广大乡村以乡规民约治村,创造了乡规民约发展的鼎盛时期。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可以将清代的乡规民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清朝初期乡规民约的御用化
顺治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九年(1652)清廷在直隶各省乡村颁行《六谕卧碑文》。“六谕”的内容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1]291,其中虽有普适性的道德义理,但它明确指出了颁布“六谕”的目的是和睦乡里,可见《六谕卧碑文》制定的初衷是指向乡村的,具有乡规民约的属性。七年后(1659),清廷“设立乡约,申明六谕”[1]291,强调“其六谕,原文本明白易晓,仍据旧本讲解。其乡约正、副,不应以土豪、仆隶、奸胥、蠹役充数……每遇朔望,申明六谕”[1]291,可见清朝对乡规民约的重视。其实《六谕卧碑文》的“六谕”实质上是直接搬用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这也说明清统治者虽然十分重视乡规民约治村,但是对乡规民约的认知还处在跟风模仿阶段。所不同的是,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只作了令行乡约的宏观要求,没有像清代初期统治者那样勒令在广大乡村制度化、程序化地宣讲推进。也就是说,清代在执行层面开创了乡规民约御用制度化的先河。
(二)清朝中期乡规民约的泛化
清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华大地的战乱纷争大幅减少,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迅速增长创造了条件,而人口的激增导致伦理道德问题凸显,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在广大乡村出现了“或豪富凌轹孤寡,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良善”[1]291等现象。圣祖康熙帝认为治理这些基层乱象,道德教化是最根本的方法:“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2]于是康熙九年(1670)颁布《圣谕十六条》,以明礼醇化风俗、务本定立民志。《圣谕十六条》不仅丰富了《六谕卧碑文》的内容,而且行文上以严格对仗句式进行表达,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增强了感染力。《圣谕十六条》从形式到内容都超越了《六谕卧碑文》,只是《圣谕十六条》虽然起到了乡规民约的作用,但康熙在颁布“十六条”时并没有明确将之定义为“乡约”,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礼部颁布政令要求广大乡村遵行“十六条”,“通行直省督、抚,照依奏进《乡约全书》刊刻各款,分发府、州、县、乡、村,永远遵行”[1]291,从此正式确定《圣谕十六条》为纲领性的乡规民约。《圣谕十六条》刊刻至地方后,各地官员为获得良好的宣讲效果,纷纷对其进行诠释。为规范执行《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清廷对其进行了逐条详解,最终形成万余言《圣谕广训》。各个地方为了方便广大村民理解《圣谕广训》,他们或不停地对其进行二次加工,或翻译为地方语言,由此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圣谕广训》通俗注解版本,这标志着清代乡规民约真正进入繁荣鼎盛阶段。
(三)清朝晚期乡规民约的回归
清朝晚期各地起义频繁,太平军攻克金陵(今南京)后,江南地区危机四伏,咸丰四年(1854)江阴县令广集绅士商议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团其身必团其心,练其力必练其气……若仅讲团练,不以文教治之,练丁即有勇,悉能知方……若与宣讲乡约,练丁则忠义明而果敢气作矣”[3]216。为鼓舞士气,江阴常大元兄弟等人报请官府设立乡约局,以推广乡约,教化乡村团练。次年(1855),常熟、无锡、金匮等地也纷纷设立乡约局,由此清朝乡规民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乡约局由地方官吏设立,不是依皇权意志而立,宣讲内容不再是单一的清帝圣谕,而拓展为儒家的各种善治思想,将乡规民约恢复至宋明时期的自治样态,不再唯圣谕而行。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朝堂主张君主立宪,在地方倡导地方自治,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以及清廷控制力的下降,乡规民约开始突破皇权圣谕的禁锢,且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阎锡山的山西村政、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等运动均延承了乡规民约的进路。这样,乡规民约的发展经过兜兜转转后,再次回到乡民层面,回归乡规民约的本真样态。
二、清代乡规民约的内容
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以武力征服天下建立自己的王朝,因此清朝的建立带有“野蛮战胜文明”的先天不足。为顺应大一统发展趋势,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置于正统地位,继续用“三纲五常”思想来教化百姓。历代清帝颁布的乡约圣谕,体现了其重视儒家道德教化的伦理思想,其中以注解《圣谕十六条》的《圣谕广训》最为典型。
(一)道德主体关系:宁厚毋薄,宁亲勿疏
研读《圣谕广训》可以发现,其对道德主体的规约是从个体、家庭、宗族三个层次逐级推进的。《圣谕广训》指出,作为道德个体应严格遵守儒家的孝道之礼,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开篇便指出孝乃“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4]198,论证了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着,他论证了如何尽孝的问题:“方其离怀抱,饥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4]186“自当内尽其心,外竭其力。谨身节用,以勤服劳,以隆孝养。”[4]186该书言简意赅地论证了道德个体应遵从孝悌伦理,充分体现了乡规民约简洁实用的特色。
在传统熟人社会,道德主体除以个体方式存在外,更为主要的存在方式是家庭与宗族。因此《圣谕广训》指出,孝道并不局限于孝父母,还要敬兄长,“众子弟皆当咨禀焉。饮食必让,语言必顺,步趋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4]186,作为家庭一员既要做孝子又要做悌弟,“不孝与不弟相因,事亲与事长并重”[4]186。为保证家庭和谐安乐,《圣谕广训》强调了良好家治的重要性,既肯定了家训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家训秩序。家训使道德个体“端其本,明大伦”,家训秩序是“教万民训子弟,党正、族师月吉读法,岁时校比”[4]193。此外,《圣谕广训》还阐述了家长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可模可范,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见闻日熟,循蹈规矩之中。”[4]194这样,《圣谕广训》从多个视角完成了对家庭道德主体的道德规约。
《圣谕广训》认为宗族的出现是人类群居的本性和必然,“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4]187,所以宗族内的每一个道德个体都要“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4]187。宗族内各家庭之间虽然亲疏远近不同,但均为同一血缘,宗族之人不能罔顾骨肉之亲,《圣谕广训》主张宗族共睦,为此还列举了“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的宗族共睦案例来佐证。至于宗族不睦的原因,《圣谕广训》列举了种种导致宗族不睦的现象,作出了“富者多吝”“贫者多求”“贵凌贱”“贱骄人”“财货相竞”“意见偶乖”等具体分析。但《圣谕广训》最后将导致宗族不睦的原因概括为人伦道德的偏颇:“盖宗族由人伦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未尽。”[4]187就是说,宗族不和睦一定是族内之人未能恪尽血缘人伦本分,为此宗族成员“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勿疏”[4]187。可见,《圣谕广训》将人伦孝悌推广至更大的范围,旨在透过血亲人伦孝道规则营造宗族雍睦、乡静人和的底层社会氛围,从而有效巩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概言之,《圣谕广训》作为乡规民约首先强调的是对人伦关系的认知和规约,认为人伦关系和睦是乡村秩序稳固的基本前提。
(二)经济生产伦理:各付一业,节俭犹水
清初兵灾不断,广大乡村土地荒废,百姓生活艰难,统治者虽然采取了富民休养等措施,但是康熙时仍是官吏腐败、国库空虚。雍正继位后,用《圣谕广训》注解《圣谕十六条》,对乡村经济生产从务本、劝课、节俭三方面进行了重点规约。
有恒业才有恒产,《圣谕广训》主张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要务本,“幼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4]193,认为“各付一业”是平民百姓的立身之本。为使百姓清楚自己的本业,雍正皇帝还重新划分了行业类别,他在士农工商四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行伍兵士,共五业,认为五业虽殊异,但恪守本业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不能见异改本,因为“朝夕营营,不恒其德。资生寡策,历久无成。而志遂以荒,而业遂以废矣”[4]193。《圣谕广训》还对如何务本五业给出了明确规定:士者谨身、农者守时、工者审材、商者通有无、兵者行阵且屯田守汛,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工利器用,商通货财,兵资捍卫”[4]193,只要各行各业恪守本业,则可“富庶丰亨,游于光天化日之下”[4]193。
五业并列,并不意味着五业地位相等。《圣谕广训》虽将兵单列,但认为“农为最贵”,天下衣食皆依赖于农,若“一夫不耕”或“一女不织”,则整个社会便会遭受饥寒之苦,“故农为天下之本务”[5],因此《圣谕广训》中用较多笔墨劝课农桑。为有效劝课农桑,《圣谕广训》还煞费苦心地分析了全国各地的自然条件,指出江浙四川湖北适宜种桑养蚕,其他省份虽不适合种桑养蚕但“与树桑一也”,也有适合自己耕种的麻棉等作物,不能见异思迁。皇帝如此注重劝课农桑,实质上是告诫各地官吏要劝课农户积极耕种,“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勿夺民时,勿妨民事”[4]189。与此同时,《圣谕广训》对军兵的农事作用也进行了规定:“多方捍卫,使农桑俱得尽力”[4]189,军兵为农业活动保驾护航,以保农事兴旺、国库充盈。
农有所耕,则农民的基本生存便无问题,但是若想富民,还需要教民节俭持家。《圣谕广训》中用蓄水规律阐述了节俭富家的道理:“夫财犹水也,节俭犹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则一泻无余。”[4]190至于如何节俭,《圣谕广训》从服饰、饮食、婚丧、器具、宴宾等方面进行了规约:戒奢,“衣服不可过华,饮食不可无节,冠婚丧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务取素朴。即岁时伏腊,斗酒娱宾,从俗从宜,归于约省”[4]190。此外,《圣谕广训》还认为“兵丁钱粮有一定之数,乃不知撙节,衣好鲜丽,食求甘美”[4]190,告诫兵丁要知耕种,因为丰灾无常,军队要厉行节俭,排除奢侈之风。
概言之,《圣谕广训》作为道德规范,其内容没有局限于人伦范畴,还涉及广大乡村的其他领域,经济生产就是其除人伦关系之外的重点规约对象。
(三)社会秩序伦理:里仁为美,比户可封
由于人口激增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清代加强了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圣谕广训》中有大量关于乡党秩序约定、乡村意识形态建设、刑礼跟进等社会秩序伦理的内容。
清代乡村社会底层政府组织的架构形式为乡党,《圣谕广训》指出,乡党和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缓急可恃者,莫如乡党”[4]188,乡党、邻里之间关系至关重要,如若乡党不和,则会“举动相猜”,甚至“报复相寻”。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乡党和睦,《圣谕广训》认为待人接物需“温厚”、处理事情需“谦冲”,不可“恃富侮贫”“挟贵凌贱”“饰智欺愚”“倚强凌弱”,不但要“小忿不争”,还要有“包容之度”。此外,《圣谕广训》还规定“民与民和”“兵与兵和”“兵与民交相和”,旨在通过教化构建“里仁为美,比户可封”[4]188的理想乡村秩序,进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从国家层面看,维护社会稳定必须统一意识形态,但是明末以来士风奢靡、学术倾颓,再加上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引发华夷之辨,人们对儒家思想失去信心,而广大乡村封建迷信盛行、思想混乱,成为清初统治者亟须勘正的大问题,因此《圣谕十六条》提出了“黜异端以崇正学”“隆学校以端士习”的主张,而《圣谕广训》既详细阐述了清朝尊崇儒学历史传统的主张,又详细论述了兴办学校罢黜异端邪说、“崇正学”、“端士习”的举措。《圣谕广训》认为“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异端之害,害及人心”[6]290,同时指出,非圣之书“皆为异端”,“习乎异端曲学而不知大道”[6]269不可以为士,所以要“隆学校”以授孔孟之学,使人明辨伪道、远离异端。事实上,雍正皇帝比较热衷于兴办社学、义学、义塾,希望通过社学、义学、义塾系统化地传授儒家伦理思想来匡正基层百姓行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
雍正皇帝深知道德教化的软性功能,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固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其实效性不佳,所以《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讲法律以儆愚顽”“诫窝逃以免株连”“联保甲以弭盗贼”等条款作了详细注解,但因其内容与本论题关联性不强,在此不赘述。总而言之,清代乡规民约不但延承了以往乡规民约的道德教化功能,而且与以往相较,其内容更明确、针对性更强。
概言之,《圣谕广训》将道德教化和刑罚相结合,保证了乡村社会的常态化运转。
三、清代乡规民约的特色
乡规民约在清代的御用化特色鲜明,虽为政治统治工具,但是其本质是一种“礼”不是法,其规约体现的是它的伦理道德意蕴。当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清朝乡规民约的道德功能发生了异化,这从《圣谕广训》中可以管窥一二。
(一)教化功能减弱,规范功能增强
吕大钧设计《吕氏乡约》,其目的是想凝聚乡村内外各种力量,应对乡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乡规民约的制订主体是乡人而不是官人,主要解决的是乡村之事而不是国家大事,所谓“乡人相约,勉为小善”[7],实质上是乡村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到明代,由于国家的介入,乡规民约开始与保甲、社仓、社学结合,具有了对外御敌、对内救恤以及教化的功能,乡规民约村民自治色彩变淡。但此时的乡规民约虽然开始与保甲、社仓、社学结合,却依然发挥着乡约的礼俗道德教化等核心功能,保甲、社仓、社学是实现乡规民约道德教化功能的辅助力量,所谓“一纲三目”,礼俗道德教化是纲,保甲、社仓与社学是目。可是到了清代,乡规民约在肩负道德教化功能的同时被赋予了更多功利属性。
无论是北宋《吕氏乡约》还是明代《南赣乡约》,它们不仅蕴含着保甲、救济等事功理念,而且保甲、救济等事功只是以道德理念的形式出现,以至于王阳明单独作了《十家牌法》来规范保甲制度,并没有将保甲的实体性规定纳入《南赣乡约》,而清朝《圣谕十六条》却以明确的条款形式将乡规民约的保甲功能展示出来:“联保甲以弭盗贼”,将保甲与乡约合二为一:“十家为甲,十甲为保”“甲有长,保有正”“吏则徒稽户籍,民则仅置门牌”“一家有失,击鼓为号”等,这些内容具有了制度规定性,不再像宋明乡约里的保甲一样只是一种道德理念了。如果将《圣谕广训》中的“联保甲以弭盗贼”单列出来,“十家为甲,十甲为保”“甲有长,保有正”“吏则徒稽户籍,民则仅置门牌”“一家有失,击鼓为号”等内容就是一种保甲规范,只是清朝时将之纳入乡规民约之中罢了。由此可见,清之前的乡规民约主要是通过道德观念、教化理念来引导村民自觉维护基层社会秩序,而清代则将乡规民约的道德属性、道德功能完全工具化,这是它的突出特色。
概言之,《圣谕广训》具有明显的道德工具化色彩,伦理道德本是抚慰人心、纯化心灵的,一旦工具化,便失去了它的本然属性,这是清代乡规民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二)例行公事,形式化痕迹明显
为了便于乡民学习和掌握乡规民约,从康熙《圣谕十六条》开始便有了宣讲制度,到了雍正时,针对《圣谕广训》,制定了详细的宣讲制度和宣讲仪式。清廷规定“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8]231,而且制定了褒惩制度确保《圣谕广训》得到广泛宣讲:“行至三年,著有成效……加旌异,以示鼓励。其不能董率、怠惰废弛者,即加黜罚。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该督抚据实参处。”[8]231据杨开道先生统计,“从顺治九年(1652)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239 年间,共颁布乡约谕旨32 道”[3]251。如此大力度宣讲、执行,使得乡间里下极为重视《圣谕广训》,且每次宣讲都要“行三跪九叩头礼”[8]250,“大约在清代各帝心里,在礼部各臣手里,乡约只是圣谕的宣讲,而不是什么乡民公约”[3]202。显而易见,宣讲乡规民约已经成为基层官吏的例行公事,被赋予了稽查、催科等公共职能,对学习乡规民约的程序性、形式化要求胜过了学习它的实质内容。清代因执行程序的严苛,乡规民约形式化的痕迹远胜于宋明两代。
导致清代乡规民约形式化的原因不仅在于执行程序,而且主要的是清代乡规民约内容的官方化。如前所述,宋时乡规民约是纯粹乡村自治的产物,明时变成了吏治的工具,而清代则变成了御治工具。明时的乡规民约虽然也有了官方化的色彩,但它是在地方官吏主持下根据本地乡村实际情况,以解决本地乡村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的,而清代的御治化使得各地的乡规民约内容完全一致,圣谕的固定范本消解了乡规民约的地方特色,乡规民约解决的不再是各个乡村的具体实际问题而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这就使得清代乡规民约偏离了乡村实际,远离了乡村道德主体的实际生活,机械地重复圣谕内容,对民众缺少吸引力,最后只能流于形式。正如学者所说,清代乡规民约“以提倡乡约的办法去提倡乡约,已经嫌其单纯,不能兼顾;以提倡县约的办法去提倡乡约,更觉城乡辽远,官民隔阂,无怪乎清代乡约费力多而成功少了”[3]221。
概言之,清廷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将潜隐在乡规民约中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以圣谕方式确定为乡规民约的主要功能,缺少了乡规民约的专有属性。随着清朝圣谕宣讲制度的完善,清代乡规民约的乡村道德建设功能日渐式微,直至太平天国时期乡约局的出现,才重新开始结合地方乡村实际宣讲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才再次发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功能。
四、清代乡规民约的当代启示
清朝之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还能延续近三百年,创造出康乾盛世,其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在乡村道德建设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可资借鉴的地方。
(一)乡规民约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清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暴增,清初人口由0.9 亿左右暴增至清末的4 亿多,“中国人口一度占世界人口总量的37%,但是中国城市人口却只占世界城市人口的11.5%,城市人口的增长远低于总人口的增长”[9],这说明清代人口激增主要是在广大乡村地区。面对人口激增以及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动荡,清政府不得不重视广大乡村地区的意识形态建设,加之此时的中央政权已经具备了管控地方的能力,因此清代的乡规民约必须以体现国家意志为宗旨。换言之,清代乡规民约的“御用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样,清政府也用事实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出台与推广,与“康乾盛世”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乡村人口的剧增推动了国家层面的乡村治理,国家层面的乡村治理又带来了“康乾盛世”。
当今中国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村出现了“空巢化”“空心化”“撕裂化”的现象,乡村治理难度增加。因此,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单靠村民自治是解决不了广大乡村存在的问题的,必须依靠基层政权和国家的力量进行乡村治理和乡村道德建设,因此当今的乡规民约也应以体现国家意志为主。
(二)乡规民约内容必须体现乡土文化特色
清代独具特色的乡规民约的出现虽然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清代的乡规民约毕竟过多体现了国家意志,存在将道德工具化、伦理形式化的弊端,因此清代乡规民约饱受研究者的诟病。多数学者认为,清代乡规民约虽然名为乡规民约,但是实质上已经背离了乡规民约的本质,它既不是乡规也不是民约,而是国规官约。因此,在肯定清代乡规民约强化国家意志的同时,更要注意其将道德工具化、伦理形式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合理规避其不足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乡村道德建设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城乡一体化、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从器物到精神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承载乡土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在逐渐消失,代表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城市文明正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乡村道德主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认同,乡村道德主体在情感归依和价值认同上出现了摇摆,产生了困惑。对于这些困惑,应该大力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乡村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确立新的坐标,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巩固乡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从而建设更加和谐有序、美丽健康的新农村。在乡村,我们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在涉及具体的乡土事务上应尊重村民的意愿,发挥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体现地方特色,使广大农村成为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促进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总之,当代乡规民约建设既要克服清代乡规民约工具化、形式化的不足来体现国家意志,又应以村民日常生活为载体,满足村民的特殊情感需求,确保乡村道德建设在国家意志的宏观指引与规范下,充分展示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以各具特色的乡规民约辅助乡村道德建设和乡村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