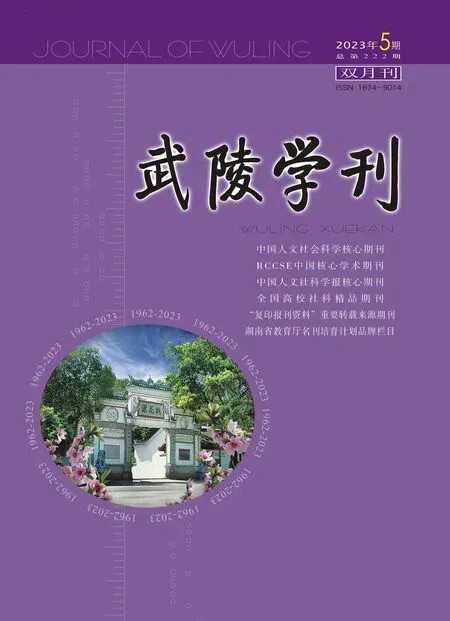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的经济改革举措及启示
杨天奇
(1.南通大学 张謇研究院,江苏 南通 250100;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引 言
19 世纪末欧洲工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得到前所未有之发展。工业高度发展逐使资本走向垄断新形态,新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亦渐次形成,诚如英国政治经济学者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在《帝国主义》中所论:“帝国主义致力于为工业巨头寻求销售国内剩余产品的国外市场与增殖国内剩余资本的国外投资场所,以便扩大能够容纳他们剩余财富洪流的渠道。”[1]欧洲帝国主义的兴起,是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的最核心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1881—1882 年,法国人占领突尼斯,英国人占领埃及;1911 年欧洲人将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的非洲所有土地瓜分殆尽;1914 年英帝国领土是其本土面积的140 倍,荷兰是60 倍,比利时是80 倍[2]。中国等亚洲国家均不同程度受到欧洲帝国势力的侵噬。
“古典帝国主义”风行于重商时代,它希望通过殖民建立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而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新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于此。制造业和运输业的惊人增长,使各帝国普遍意识到寻求新的投资市场以增加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原料和市场资源由政府直接控制才是最安全的[3]。早在1902 年,日本农商务省农业事务司司长佐古光起与日本政府官员若松兔三郎在中国、朝鲜考察时,就对扩大东亚区棉花种植一事展开过深入交谈。两年后,朝鲜棉花种植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in Korea)的成立,可以说是对若松兔三郎经济设想的成功实践。该协会由日本帝国议会和贵族院成员及制造商联合创建,彼时日本业已深刻意识到政府有效控制资本的重要性[4]293-294。前所未有的巨额收益使越来越多的帝国视棉花为“白色黄金”,中亚的塔什干和浩罕汗国很快便成为俄国重要的棉花种植出产区,俄国工业协会(Russian Industrial society)也不断加强了对中亚棉花资源的干预。直至1902 年,俄国的棉花产业可以完全不再依附美国,并以脱离美国为明确目标。由此,“棉花帝国主义”开始逐渐形成,并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4]296。然中国纺织业的收益自清末洋务时期始就不尽如人意,如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局、李鸿章翼下的上海织布局等,皆因过度依赖帝国过剩资本的放款而常处负息的状态[5]。
是以,张謇“棉铁主义”方案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方略其实是在世界新帝国主义体系下寻求本国经济摆脱境外资本侵蚀并能获得一定程度修复的权宜之策。1913 年7 月,袁世凯任命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但他对熊氏荐举的财政总长候选人梁启超不甚满意,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最后只好勉强应允司法总长一职由梁担任[6]。或碍于旧日的师生之谊,袁对熊氏荐举的农商总长候选人张謇表示赞同,不但敦促熊氏电请张謇促就农林工商之职,并于9 月1 日亲自致电张謇,劝其北上组阁[7]。张謇对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遗教恪守不渝,以张氏之见,唯有实现富民,国家才能稳固,“弱则宜无事安民命”[8]3。通览张謇赴任农商总长前与袁世凯、熊希龄的往来书信不难发现,张謇对官衔爵位并无多少兴趣,他所关注的是饱受战乱的百姓、民力的恢复,以及中国实业的前途[9]378-393。1913 年10 月,张謇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农商总长,任期虽只有一年余[10],但在此期间主持编订、颁布经济法规和条例20 余种。直至1928 年,南京政府所颁布《公司法》基本仍是对张謇编订的《公司条例》的照搬,1946 年国民政府才对其做出调整[11]269-276。因此,他被后世誉为“系统制定中国近代经济法规的第一人”[12]。他对经济战略布局有通盘而详细的筹划,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现代转型亦有以启山林的贡献。自今反观,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而非后世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儒商”。
有关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的经济改革研究论者已多,主要有王翔于2000 年所撰《张謇与民初经济法规建设》、虞和平于2001 年所撰《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朱明于2003 年所撰《张謇的法律意识与经济立法实践》等。2023 年是张謇诞辰170 周年,若要厘清张謇植根于中国自身土壤经济改革方略的当代意义,应当从“古今”和“中外”不同视角并结合张氏所处历史语境给予再检视。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共分三节阐而论之:第一,基于传统的现代经济立法与改革;第二,理财救国语境中的金融改革;第三,生态与经济的相协调。不求面面俱到,仅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基于传统的现代经济立法与改革
“经济法”一词始于法国摩莱里的名著《自然法典》,但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形成却在“一战”前后。其时魏玛共和国直接以经济法命名颁布《煤炭经济法》与《钾盐经济法》,经济学家遂将这两部法典视为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干预与调节的“现代国家经济法”。现代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到新帝国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旨在帮助政府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化解经济危机[13]。而中国经济领域内的立法,亦有数千年的历史。战国时期,魏相李悝认为王者之政应始于惩戒贼盗,为此他著成中国第一部法典——《法经》,以推行其“法治”主张,维护封建领主私有财产不受到侵犯[14]。李悝谏言“尽地力之教”,力倡“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15]。显然,他是一名特具“重农”思想的改革者。迨至商鞅,农业仍为其变法的重心。商鞅认为农为国家之本,其重农计划凡十六纲要,说之精密,意义深远,然商鞅重农却未尝“轻商”,其重农思想主要是在考量秦独特之地理、自然、历史等现实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16]。自李悝至晚清,“重农”与“农本”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中心议题。依英籍学者邓钢的观点,中国的农业原教旨主义并非政府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农民是重农思想的主要决定因素。从农民的角度看,重农主义和民本思想是公众评判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一把标尺。而从中国精英的角度看,农业关乎天下太平,他们充分意识到大规模农民武装叛乱的危害[17]。
19 世纪末,中国农业商品化的程度继续加深,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取决于国内市场,而是由列强借助通商口岸加强对华资本扩张导致的[18]。此时土地兼并的风气并未消减,加之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使得农民无力改进生产,生活日益落伍[19]。因此,自然经济在农业领域仍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农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显著,但农业领域内尚未出现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很多农牧垦殖公司的创办人不乏军阀、官僚,如孙传芳、吴佩孚、冯国璋等都是这一时期垦殖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此外,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虽有所发展,但比重很小,且常受到土地和高利贷的双重束缚[20]。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亦很关心农业的命运与前途。早在1897 年,张謇就已深刻认识到:“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8]27其时江苏濒海盐场、濒江州县,闲地荒滩,或被公家所弃,或被豪右所占,或为战后所遗,为此他谏言光绪明降谕旨饬各级官府仔细理查,将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种植葡萄果木之类,或仍用旧法,推广桑棉畜牧之类,或集公司,或借官款,通力合作,官民一心,逐件经营”[8]27。张謇对中国农业发展迟滞的状况深感担忧,就任总长后立即展开了关于兴革农业之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以他之见,民国肇建,凡关于土地事宜,俱应厘定规条,俾资遵守[8]310。民国三年(1914)3 月,他拟定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正式颁行。《条例》凡四章,首章总纲即指出所谓荒地,即“江海、山林新涨及旧废无主未经开垦者”,后三章详列承垦实施细则,如垦荒者须具书呈请官署核准,经核准后须按每亩纳银作为保证金,并由官署颁发正式的承垦证书。如此既能维护开垦者合法权益,又可按各地税则拓宽税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8]310-314。
张氏于1914 年4 月拟定《观测所官制》,并建议政府采用现代器械观测气候变化,设置观测所及分所,并聘用气候调查与预报职员协助农民及农会展开农业生产[21]。他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另其同期所拟《征集稻麦种规则》《关于征集植物病害及害虫给各省民政长训令》《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劝农员章程》等条令,实际也都指向了这一点[22]304-331。
但必须指出,张謇并非一农业原教旨主义者,他期望借助现代立法改变以往“重农抑商”的观念及政策传统,认为“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8]222。此处的“完备之法律”不止面向农业,亦应嘉惠工商业,他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重申并明确了此观点:“窃维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纂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工商政待举百端,一切均无从措手。为此夙夜图维,惟有将现在农工商各业急需应用之各种法令,督饬司员从速拟订。”[8]263-264他援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之论意在说明:实业者须兼本末而不能重本抑末,农虽为工商之源,但无工商则农困塞[23]82。他在《通州兴办实业章程》中同样指出:“中国人待农而食,虞而出,工而成,商而通。工固农商之枢纽矣。”[24]“本”对于“末”义有先后而无轻重[23]82,直至晚年他仍持此见解:“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者也;商为之绾毂,而以人之利为利。”[25]560此处的“绾毂”语出《史记·货殖传》“栈道千里,唯褒斜绾毂其口”,其本意为“扼其要冲”[26],张謇虽未明确提出类似康有为倡言的“以商立国”论,然他将商譬喻为“绾毂”的做法,足已表明“商”在其心中的地位与权重。
历史表明,儒、商并非相互抵牾、卒难调和,“儒与商同源不仅可以从殷商亡国时说起,甚至还可以上溯至商族诞生之时,商族人的起源就是儒的起源”。契是商族人的祖先,也是儒家的思想祖先,儒与商其实是一体同源的[27]。孔子弟子中子贡最擅经商,从孔夫子对其“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的评价亦不难看出,儒家殊无轻视抑制商业之意[28]。而以儒者自居的张謇,其构想的实业是“大农大工大商”[29]。他任总长伊始,即建议北洋政府解散农林工商两部,合其为农商部,并主张农商部设三司,分别为农林司、工商司、渔牧司,左列矿政局管理矿业事项[22]1-4。所以说,“划地为界,琢钉其中”式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他所乐见的。
不容否认,张謇的经济改革方略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世界化”,然他绝非全盘之西化派,无论其改革观念还是实施举措洵能考虑到自身国情,因而有很强的本土特征。如在制定《商人通例与商人注册规则》时,张謇就注意到传统商号的商业注册问题,他在通例指出:公司之商号应各视其种类分别表明,并可按传统以其姓名为商号注册公司[22]155。中国商号常有添设支店的习惯,就此张氏主张支店商号亦须遵照总店之商号。此外既注册之商号他人不得仿用,商号与营业需一并转让,且转让人十年内不得于同一乡镇再开设同类营业商号[22]156。又如盐业改革方案,亦是他在精研《盐铁论》《两淮盐法志》等古代盐政书籍的基础上拟成的[23]92。中国盐政承千百年以前之旧法,若使旧制一扫而空,并不可取。以他之见,“施行必有次第”,更须明察吾国盐政之现状[23]212-216。他出任农商总长期间派专员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淮北各地,制成调查报告,并召集全国盐政专家于北平,由盐务顾问景本白厘定,一起讨论并制订了《盐专卖法》《盐税法》《制盐特许条例》《私盐治罪法》等条例[30]。显然,张謇经济领域内的立法及改革是基于国情与传统逐步展开的。章太炎曾言:“法律者,因其俗而为之,约定俗成,案始有是非之剂,故作法者,当问是非,不当问利害。今夸以改律为外交之弊,其律尚可说哉。”[31]照搬西方法律并不可取,因其俗而为之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张謇在农商领域的立法及改革既能立足于自身土壤探寻适宜本土的可行路径,亦能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传统与现代经济政治制度间的内在关系。他之种种努力,对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理财救国语境中的金融改革
清季以降,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以救国富民,渐成为诸多有志之士的共识。维新派先驱者郑观应于《盛世危言》中曾谓:“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32]钞票、银行、商部是现代金融的主要构成,泰西国帑皆存银行以为根柢,凭纸券出钞,如此既可避免官吏私自侵挪国库,又能集合商股、取信于民。梁启超则认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谓财政枢机,于兹焉丽,国民生计命脉,于兹焉托也。”[33]改革币制应效仿欧美诸邦成立中央银行,流通金融,使吾邦尽早成为现代货币之国,才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关键。1908 年,康有为撰成《金主币救国议》,康所言金主币论即是“金本位制”。所谓“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是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于19 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其最早形式是金币本位制(gold specie standard),始于1816 年的英国,其主要特点有:用黄金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间根据其含金量有一个固定的比价;各种银行券和金属辅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黄金是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结算货币,可自由输出输入[34]。康氏称其币制主张为“金主币制”而非“本位制”,因在他看来“本位二字不文”,而以主币、助币阐释则更妥帖。康曾举例,若英金镑为主币,则银币诗令、铜币编尼是为助币,主币与助币即母与子的关系。然现今世界诸国大多行金主币制,金银两主币并行的时代已成刍狗,因此当早定金为母币,银、铜为子币,此即大势所趋,不可易也[35]30。以康之见,吾国物质未兴,机器未盛,如不改定金币本位,必导致诸多“大害”:银价日降,物价日腾,供求失衡,市场紊乱,民商愈困,金价日涨,外债无力偿还,金融权也将被外国掌控。若此,“全国人宛转匍伏于外人财权之下”的局面亦不远矣[35]43-44。
张謇早年亦为“金本位制”支持者,癸卯东游之际,在西村等陪同下参观了日本的造币局。他对日本造币工艺之精湛印象尤为深刻,认为其“精制场之平量轻重机为最新式,至精极准”。他进而指出,日本货币虽分金、银、铜三种,却明确以金为本位。反观吾国,苦货币之困久矣,虽有改银、铜币之说,然不造金币,且无本位,以致黄金日流于外而日贵[36]。民国肇建,对于货币本位制的讨论被正式提上议程,北洋财政总长周学熙认为,“币制之定本位为先用银之说,既非天演界中之所宜;舍银而金,又非我国实力之所能。无已,择其最适宜我国情形者,其唯金汇兑本位制度乎。……在国中仅以银币、纸币作金之代表,其随时与金兑换,专为国际之需。”周氏赞成的“金汇兑本位”即是任公所言“虚金本位”,然周氏认为“虚金本位”或“假金本位”的称呼多有不当,因国内交易并不真正使用黄金,只是在国际汇兑时以黄金为核算标准,故当以汇兑本位命名之[37]。诚如周氏所言,舍银而金为吾国力所不逮,故梁氏早年虽力主“金本位制”,后又改弦易辙,主张率先实行“银本位制”,以梁氏之见,“今虽以无念之故,未能行金本位制,然此虚金本位制,苟得其人而行之,则亦与金本位同一功用。故为中国计,今日惟有急变用银块之习,以成为银本位制”。银本位制后乃可实施虚金本位制,虚金本位制后,币制基础已定,将来遇有机会,如本国开得金矿,战胜他国而得偿金,或可实施金本位制,此乃先后之序,不可易也[38]。
无论周学熙还是梁启超,其时都已深刻认识到:金本位制固然上乘,然因中国实业欠发达,加之黄金储备有限,国内亦不流通金币,只能暂行“银本位制”。1914 年2 月,张謇会同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共同制定的《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正式颁行,《国币条例》主张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母币,以“元”为基本单位。面对清末发行货币混乱及民间私铸屡禁不绝的现状,《条例》第一条即指出“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币种类共有三种,分别是银币、镍币、铜币,其中银币四种:一元、半元、二角、一角。第四条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元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此外,对于国币铸造、磨损、毁坏等均有相应之施行条例。另外《条例》后附《施行细则》,尤其对新、旧钱币的折算、使用作了详细规定。《细则》明确,“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对于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一元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市面通用之旧银角、旧铜元、旧制钱,政府以国币收回改铸之,但于一定期限内,仍准各照市价行用。对于民间债项以及旧银角、旧铜元、旧制钱或他项钱文计者,均依规定折合国币改换计算[22]280-282。《国币条例》颁布不久后,立即遭到持不同币值意见者的反对。如币制专家刘冕执认为,银本位制会使金价奇低,国人亦会乘机大加囤积黄金、金饰,甚至购外国金纸存于国外金融机构,以致国库黄金无可储蓄,终而坐失实行金本位制的绝佳机遇[39]276。刘氏被强行卸职后,多有不满,直至数年后,他对这段遭遇仍记忆犹新,“其时所谓名流内阁,不用余策……而硬订二十年来所用之银本位制”,遂“愤而著一《银本位制亡国论》”。他对当时情形也作了客观描述:“世界各国多用金制,我国独用银制,必感不便而受损失,但素未储金,骤改金制,势所不能。”[39]276至今反观,此段回忆录颇值玩味,其中“势所不能”四个字可谓一语中的,这也难怪《国币条例》颁布二十年后,刘氏本人不得不承认当年行为之鲁莽,并坦言曾含愤撰写的《银本位制亡国论》“语固过于偏激”[40]3。
事实上,银本位制并非中国所独有,中世纪时期,欧洲许多国家曾实行银本位制,这实际是由当时欧洲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贵金属生产情况决定的[41]。只有国内经济走向发达,对外经济交往密切,才具备放弃银本位的条件,如英国于18 世纪末放弃银本位,美国于1873 年放弃此制,其余如俄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等于19 世纪末才相继放弃此制[42]。
因此,《国币条例》中的银本位制并不是贸然提出的,而是综合考虑本国商品经济状况及其它现实客观因素后得出的方案。1935 年11 月3 日,民国政府正式废除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骤然实行法币本位制[43]。法币制的强制实施,实为通货膨胀即滥发纸币开了方便之门,抗战胜利后,恶性通货膨胀终未得到抑制,法币制最终崩溃[44],此后蒋介石又颁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其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45]。与蒋氏有所不同,张謇奉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它不仅稳定了当时的物价、惠及百姓大众,同时新旧钱币折算等细则的实施也为有效降低民间资本的融资风险提供了可靠保障。《国币条例》颁行后,供求得以平衡,民生得以恢复,信用得以拓宽,进而为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宝贵的“黄金期”,这一切很难说不是得益于张謇等金融改革者的揆时度势、审慎而为。
张謇出任农商总长之际,康有为所撰《理财救国论》正式刊行。康称此书数年前业已完成,只因民国初建,政府财政困绝,生计尽绝,因不能忍,才将其刊发,以备采择[35]384。以康之见,“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善用银行者,无而能为有,虚而能为盈,约而能为泰,必有实金而不以实金行”[35]386。事实上,依靠银行等现代金融手段解决民初的财政危机,业已成为当时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除上文提到的梁氏所撰《余之币制金融政策》外,再如章太炎“惩假币”论[46],孙中山《钱币革命论》等,皆是在理财救国这一语境中展开的。张謇于1914 年4 月建议北洋政府成立“劝业银行”,以他之见,吾国地大物博,然农林、垦牧、水利、工矿等皆囿于小成,难有规模,推其缘故,完全是因资金匮乏所致[22]283。劝业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将外国资本引进中国,给农工商类企业以基金贷款[47]。是年12 月,张謇拟定的《证券交易法》正式颁行,第一章总则即指出:“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分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22]29118 世纪初,全球首家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在伦敦交易巷(Change Alley)开业,旨在通过股票交易帮助企业筹资[48]。金融是货币流通、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它不仅指资金融通,还包括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时至今日,金融仍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49]。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时期所制定的金融方案,涉及货币、银行、证券、股票、税则等诸多方面,他试图建立的是一套健全的金融体系,并希望借此调控经济,解决商业衰敝、财政困竭等现实难题。他的金融改革方案无疑有很强的“凯恩斯主义”特征,然而,他亦希望通过立法等手段为民营经济创造广阔自由的空间。恰如章开沅、田彤所言:“(张謇)试图在‘抗争’与‘依靠’中把握平衡。”[11]379概之,张謇绝非一自由经济主义者,而是倾向在国家调控的机制中振兴民营经济,实现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的相协调,这亦为其理财救国方案的创新之处。
三、生态与经济的相协调
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 这一概念形成于上世纪60 年代,最先由美国经济学者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提出。鲍氏在其专文《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中指出: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是有限的,伴随人类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必然会与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产生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为命运共同体[50]。国内经济学者许涤新则认为,生态经济学“不是生态学与经济学一般相结合的科学,而是在现代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一体化的科学”[51]。所以,生态经济学研究重点应放在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之间发生的经济现象和体现的经济关系上,而研究这些问题,旨在调节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使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够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中虽未直接提出过生态经济学理论,但自先秦起就主张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下,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与“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和谐统一。前已述及,儒家殊无抑制经济发展之意,然必须承认,儒家又十分注重生态保护,劝诫世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又如儒家学派代表者荀子,不但强调“天道自然”,更言“制天命而用之”,这里的“天命”指自然规律,即言顺应自然规律而造福人类。至于如何顺应,荀子亦有详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张謇早年对荀子情有独钟,曾撰文专论荀学。在他看来,荀子“喜于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而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25]214。
张謇不但崇尚荀学,亦为“制天命而造福百姓”思想之践行者。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倪文蔚出任河南巡抚,八月黄河于郑州决口,倪氏自责疏于防范,请求朝廷议处,因倪氏到任不久,朝廷暂免其处分[52]24。张謇不忍倪氏因此而革职,特撰书信五份,陈言治水方案请倪参酌,以他之见,治水不能一味靠堵塞,因黄河河身宽通深远,河水顺势而下,若决口浅涸,可采堵塞之法,然遇决口险绝,堵塞即不能挽制。为此,张謇主张“疏塞并举”,以“塞为目前计,疏为久远计”。他并指出“泰西能于水中挖泥之法,实中国从来所未有”[9]33,故建议倪氏从德国购买平地、开河之器,借平地器穿瀹淤滩,用浮水器乘流施工[9]34。在他建议下,倪氏组织民工抢筑水坝的同时,又次第开放引河分散水势,此一疏塞并举方法使其治水终见成效,嗣后,倪氏亦因此得朝廷封赏[52]24。甲午恩科殿试时,张謇曾谏言光绪帝:“治水肇于《禹贡》,畿辅之地实唯冀州,而因水利与农事相表里之故,此诚今日之先务也。”[25]239-240
迨至民国,他对水利事业的热衷,亦未稍变。1914 年,他在《淮与江河关系历史地理说》中讲:“豫计之次第,先计淮、沂、泗、沭如何泄泻入海之路,路分几道,方能有利无害。”[23]321禹之治水,顺地高下之势,导西北高山、平原之水,汇入大海。而中国地势无不西北高、东南下,故应复淮、沂、泗之故道使其入海,并疏通沂、泗、沭入海之支路,淮水入江之支路,此即为他一再主张的“七分入海、三分入江”之治淮方略。江、淮既通,既利于舟楫交通,亦能利于江淮地域如淮安、宝应、高邮、兴化等地的农田灌溉[23]322-324。张謇任总长时曾撰《请设全国水利局呈》,并借此再度申言:“水利为农田之命脉,农田之利弊当为全国计,则水利之兴废亦当为全国计”[8]254,他建议政府尽早设立全国水利局,管理导淮事宜。又其《条议全国水利呈》指出:“除害之大者,莫如导淮而兼治沂、泗二水;兴利之大者,莫如穿辽河以达松、嫩二江。”[8]302此外,政府宜从国外引进水利人才,开设河海工程学校,并设立农业地产银行,以济疏浚之款[8]302。他任总长时的导淮方案详见于《复勘规画导淮豫计之报告》,此报告完成于1914 年。是年四月,他偕同荷兰工程师贝龙猛从南通启程,昼夜前行,沿途依次复勘清河、惠济、安东、陈家港、淮阴等地的水位标准,并测量地形、探测水势,最终预算出淮河水利工程之工价。以他之见,水灾犹如病人腹胀胸闷,即便经费不周,亦当先泄其小水,徐排其积痞、疏通其经络[23]309-315。
事实证明,张氏不止为生态保护之提倡者,更是名副其实的为生态立法者。1914 年11 月4 日,他主持制定的《森林法》正式颁行,此即为中国的第一部森林法[53]。《森林法》主要有总纲、保安林、奖励、监督、罚则、附则六部分组成,其中保安林章明确提到保安林之作用为预防水患、涵养水源、保护卫生、利于航行确定目标以及防蔽风沙等。另《森林法实行细则》对森林法的具体实施如关于森林之监督、罚则及保安林管理等皆有详细规定的呈现[54]。张謇对“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童山濯濯,所在皆是”的现象深表忧虑,他指出黄河、扬子江、珠江岁屡为灾害,洪水骤发,势若建瓴,端在于无森林以涵养水源。若一味筑堤防水,则水益高而患益烈,因此,只有在水源区栽种大面积保安林,含蓄水源、防止沙土流失,才是解决水患的根本之途[8]335。总之,在他眼中,生态对于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均甚重要,而他强调保护生态不止为营造良好自然环境,亦在调节国民经济活动、改变旧有之生产结构,实现人与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张謇希望塑造一产业树,使企业与企业间形成一循环系统,进而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促成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发展[55]。循环经济是建立在生态学规律之上,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旨以减少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为主要目的[56]。张謇不但为循环经济之早期实践者,更将这一构想运用到城市建设之中。其所构想的“一城三镇”之规划布局,既有效避免了工业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也使主城区的金融、交通、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南通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亦因此得以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近代第一城”[57],这一切很难说不是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
温铁军曾谓:“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58]张謇主张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营造生态城市,并能从循环经济的理路入手思考构建新型产业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树立国民生态价值观等现实问题,这足以证明,他已经开启了对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新形态文明的探索之路。他之所以将其纱厂取名“大生”,是因在他看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59]。曾繁仁先生认为,《周易·易传》所说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生生”一词是动宾结构,即意谓着使天地间的万物获得旺盛的生命,“生生”美学的关键词“生生”,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之东方生命论本质[60]。“生生”亦为张謇经济思想之主旨,不但祈愿在“天人合一”结构中实现自然之生生、百姓之生生、社会之生生,亦祈山美水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美丽中国”的梦想早日实现,此即为张謇经济思想的价值旨趣与最终目标。
结 语
安东尼·吉登斯曾谓:“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的具体特征。”[61]经济建设亦复如是,如罔顾其民族性,则现代性必如空中楼阁,毫无根基可言。康有为曾言:“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62]387又言:“但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62]552对此,李泽厚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总结为“点点滴滴乌龟式的改良主义”[63]。但必须清楚,历史上但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艳羡“躐等之进”,唯有循序而行的方案才是最可行的。张謇经济方略的意义便在于他能对来自西方与日本的成功经验给予“批判地接收”,因而他的经济改革的特征是渐进式的,也是稳健式的,特别是他的生态经济思想,洵能立足于儒家生态观思考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既做到了不失固有之血脉,又能紧跟世界时代之潮流、与世界共经济。他的这一改革路径无疑是“援西入中”式的,虽有诸多不足,然在今天来看,不仅有益于保存传统既有优势、激活本土旧说的现实效能,亦能为儒学如何开出“新外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