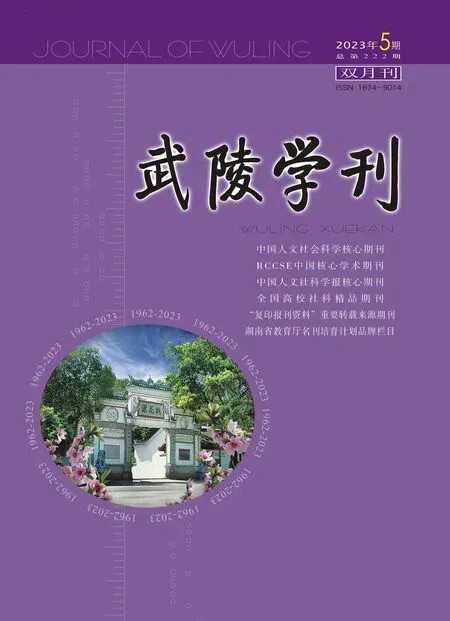宋代乡村道德建设解析
——以《吕氏乡约》为例
章云峰
(三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相较,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其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较之工商业人口仍具压倒性优势,因而宋人的社会生活仍未跳出以乡村道德生活为主的范式,其乡村道德建设的最大亮点便是乡规民约的正式出场。
一、乡规民约的内涵与源起
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规”为“有法度也”[1]216,“约”为“缠束也”[1]272。所谓乡规民约,是指在特定的乡村地域内,乡民们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共同商议制定的以维持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为目标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宗法社会和熟人社会乡民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实质是乡民的自教、自劝和自治。乡规民约是乡土社会乡村治理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抓手。乡规民约属于非国家层面的上层建筑,主要是通过封建宗法思想与儒家伦理纲常对民众实行道德教化,维持以传统道德为导向的乡村社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乡规民约遵行儒家的“先富后教”之道,在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帮助乡民解决灾、病、死、窃等实际生活难题,从物质上夯实道德教化的根基。由此可见,乡规民约不但打造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利益共同体,以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为基层社会道德教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乡规民约是传统社会乡村道德建设的基础和保障,至于在中国历史上何时、何地率先采用乡规民约的方式治理传统社会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关于乡规民约的起源问题,杨开道先生在《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进行了深度分析,他认为乡规民约起源于《周礼》,学界大多认可此观点。作为儒家百科全书的《周礼》,其设计的制度规范体系涵盖了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涵盖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在乡村社会管理架构中,《周礼》明确指出:“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2]《周礼》关于比、闾、族、党、州、乡六级乡制框架中,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的规定凸显了《周礼》以礼乐为依归,引导邻里互相劝勉、互相扶助、互相沟通、共同趋善的教化功能。可以认为,《周礼》对乡规民约作了最早的顶层设计,因此,它是中国乡规民约的雏形。为此,杨开道先生指出乡规民约由《周礼》发源[3]。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周礼》只是明确了乡规民约的内涵与功能,其实质并不是一种自觉性质的乡规民约,因为它是以国家典章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是适应具体乡村的专门的乡规民约,中国历史上最早以专门形式出现的乡规民约是宋代的《吕氏乡约》。
二、《吕氏乡约》出台的背景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考证,中国封建社会成文最早且较为系统的乡规民约,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以吕大钧为首)在其家乡试行的《吕氏乡约》。《吕氏乡约》在此时诞生并非偶然,是当时特定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一)乡里制度的变革
自唐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古代乡里制度更迭逐渐频繁起来,乡官制开始向职役制转变。至宋代,乡官制和职役制虽然并行不悖,但此时的“乡”已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演变为税籍所在的财政区划,此时的“里”已变成政令执行的政权机构[4],职役制逐渐成为主流。乡里领袖的职权因这一转变而逐步缩小,乡里领袖的待遇渐轻渐低,威望亦大不如前,其原有的乡官身份,逐渐转化为差役的角色,州、县官可任意调遣乡官。同时,乡官主导乡村教化与管理的功能逐渐丧失,此种情况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之后更加突出。乡官转为职役,使原来统一管理教化乡村社会的机制异化,乡民逐渐变为乡村事务的管理者,“以民治民”的色彩日益浓厚。朝廷对乡村社会的管控力量减弱,乡民的政治空间扩大,为基层自治提供了便利,为乡村社会的重塑创造了条件,《吕氏乡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的。
(二)宋代知识分子往基层的下移
北宋开国后,凭借科举考试实现身份跨越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取代了世袭门阀阶层。宋初的“右文政策”使得无论富家贵胄抑或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加入文官队伍。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知识精英人格尊严的提升与政治地位的高涨,极大增强了知识精英的使命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积极参政议政,针砭时弊。当然,也不是所有知识精英都可以通过科举制进入官僚体制,其原因在于不断膨胀的考生人数远远大于官职数,有限的官位将不少知识精英排除在官僚队伍之外,而这部分被排除在官僚队伍之外的知识精英留在了基层乡村社会,逐渐转化为乡绅,成为基层领袖。随着新兴乡绅的崛起,重构儒家礼教、重整乡村秩序的呼声高涨,乡绅因此成为乡村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吕大钧四兄弟订立《吕氏乡约》,生动反映了知识精英实施乡村管理教化的使命意识和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道德自觉,显示宋代知识精英已经成为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关学思想的影响
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宋代建立之初,廉耻道缺、礼崩乐坏,儒家道德礼教遭受巨大破坏,重建儒家道德礼教成为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与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士人“尚名节”“矫激”之气不同,宋代知识精英关注的焦点既包括“庙堂之高”,也包括“江湖之远”,仰视要盯着皇帝能不能推行仁政,俯视要观察民间能不能坚守礼义[5]。宋代理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的理学思想流派——关学(又称“横渠学派”)由此诞生了。关学注重“经世致用”,关注民生现实,维持礼教秩序,提出了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圣人理想。关学将道德礼教与富国安民、扶危济世紧密相连,鼓励知识精英勇于担当,以道德伦理淳化乡村。张载就是关学的典型代表,在其传世典作《西铭》(原名为《订顽》)中,他对宇宙大地、社会万家、生逝人生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将《礼运》中的大同理想具体化,旨在构建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理想社会,认为在这一理想的宗法社会里,依托宗法血缘,长幼相助,强弱相扶,人们不会感到孤独与无助,人与人可以和谐相处。他在任职期间,尽心复古礼、教民众、训子弟,对吕大钧乡村管理教化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吕大钧、吕大忠等都曾受教于张载,尤其是吕大钧因其深研张载思想,“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7]。虽然张载致仕后未能实现其理想抱负,但他的学说对他的学生吕大钧的影响甚大,也就是说,《吕氏乡约》既是吕氏兄弟的创新之作,又是对张载关学思想的传承。
三、从《吕氏乡约》看宋代乡村道德建设的特点
乡规民约虽不具有国法性质,但其核心主旨尽显儒家礼教化民成俗的特质,全文不过两千字的《吕氏乡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吕氏乡约》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篇,附“罚式”“聚会”“主事”三篇,由七部分构成,体现了儒家教化治人的理念。
(一)惟善崇德的教化方案
《吕氏乡约》首篇就提出“德业相劝”,“德”与“业”各自具有独特内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乡村道德建设。
所谓“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与利除害,能居官举职”[8]105。在《吕氏乡约》中,“德”的解释就是尽力做善事,闻过即改;能修身也能治家;能孝侍父兄,也能培育子弟;能管束仆人,也能尊奉长者;能与亲朋好友和睦相处,也能谨记慎交往来;能廉洁不贪腐,也能行善好施;能承担他人托付之事,也能救助遇到困难之人;能及时指正他人的错误,为其出谋划策,也能为大家做事;能化解纠纷,也能决断对错;作为官员能兴利除害,恪尽职守。总而言之,《吕氏乡约》认为乡村治理要以“德”为先,“德”能解乡村一切涉及道德之事。
至于“业”,“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8]105。“业”体现的是营家济物的道德要求,是对“德”的再强调,同时还要求研习理论知识、劳动技能、持家经营等方面的学问,不做对学习、生产、生活无益的事。由此可见,“业”实质上是“德”在乡村生活、生产领域的具体落实,“德”属于抽象义理层面的要求,“业”属于具象操作层面的要求,二者虽分工不同但实属一体。
《吕氏乡约》不但对“德”和“业”进行了明确界分,还对道德实践及效果进行了界分:“德业相劝”。在道德建设中,“德”与“业”是道德主体道德素养提升的两翼,《吕氏乡约》反对单靠刑罚来威慑乡民,认为刑罚既不能使村民明白什么是耻辱,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指出只有普及德化教育才能使乡民从根本上反对不良行为,进而自觉遵守乡村道德规范,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安宁,而对广大乡民德化教育的方式就是“德业相劝”。因此,《吕氏乡约》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规范乡民的行为,勾画了以道德为本位的和谐乡村蓝图。
(二)礼俗并治的实践机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意味着规则、礼制,由传统习俗汇集而成,“礼”是道德的外显形式,承担着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等级、协调关系等社会职能。“法”体现着公正与权威,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侧重于制约与惩处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乡民的知识水平有限,对“法”不甚了解,他们主要依据传统习俗来规范自身言行,而贯穿于习俗的主线是“礼”,因此“礼”是吕氏兄弟进行传统乡村治理的实践策略。
《吕氏乡约》“礼俗相交”篇中指出:“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当众议一法共行之……凡助事,谓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则借助器用,丧葬则又借助人夫及为之营干。”[8]106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婚姻、丧葬、祭祀的礼仪,已载于典籍的,按相关规定办理;若不能立即推行,则可以暂时按照传统规矩办理,不合规的应逐步修正、去除;同乡之间的交往礼仪,应当由众人商议确定,共同遵守执行。《吕氏乡约》中对婚嫁、丧葬、祭祀之礼的着墨不多,因此相关学者认为它比较空洞,但是,“礼俗相交”约文在乡民实际生活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宋代婚嫁好厚奁厚聘,讲究排场体面,仪式繁琐;人死讲求厚葬,家中有人去世丧葬仪式所耗费的酒、食开支很大,这些对普通家庭而言经济负担沉重,为此,《吕氏乡约》对婚姻丧葬仪式进行了规范,主张仪式从简、节约开支,规定了婚丧贺吊时财物或礼金的大致数额,并且规定若婚丧时确有难处,同约乡民要尽可能扶助,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保障措施,避免乡民因此致贫。这样,《吕氏乡约》不仅尊重了乡民的风俗礼仪,也避免了因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社会不稳定。
《吕氏乡约》中对互助的规定,既有利于集乡村之力解决乡民个人生活难题,又传承了中国传统美德中风雨共济、互帮互助的仁爱之礼。同时,《吕氏乡约》还认为仅靠“礼”的正向规约是不够的,任何制度规范都应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作保障,因此《吕氏乡约》中有“罚式”篇,其规约如下:“犯义之过,其罚五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8]107“罚式”的规约明显具有外在强制性,其针对的是三类不同过失,并给三类不同过失规定了相应的量刑处罚:记录在册、财产罚乃至除名,惩罚程序透明,议罚机制民主,凸显了《吕氏乡约》的司法干预功能。
总而言之,《吕氏乡约》将传统儒家礼仪转变为乡民日常生活礼俗,并辅以“罚式”,对规范邻里乡亲的行为、转变粗犷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引导乡里社会的道德生活,塑造亲爱和谐的邻里关系,推动了乡土文明和善俗社会的形成。
(三)官民相得的道德自治
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特色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9]2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的。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0],这种乡村治理的“双轨模式”到宋代已完全形成。宋朝建立后,朝廷逐渐取消了直接派遣乡官对乡村社会实行集中管理的做法,官僚体制在乡村社会日渐式微。对于乡村基层治理粗放而又柔弱乏力的朝廷而言,默许乡绅参与乡村治理,使其承担乡村道德建设责任,扮演礼教权威角色,实现中央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与乡村自下而上自治体制的接驳,有利于实现国家对乡村的间接控制,缓解中央与地方的龃龉冲突,为以村民自治为特色的《吕氏乡约》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吕氏乡约》的发起者是以吕大钧为首的乡绅,具有非官方背景。吕大钧以乡约治村,与同时代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不同,保甲法是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强推的,完全是官方行为,而《吕氏乡约》于官治外另立乡民自律约文,具有乡民公约的意味。首先,从入约条件看,吕大钧曾明确表示“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11]568,这意味着加入乡约接受道德教化并无高高在上的门槛条件,财富多寡和权势大小与入约无关,完全遵循乡民自愿原则。其次,从《吕氏乡约》的组织规范看,“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8]108。《吕氏乡约》中关于“主事”“直月”以及奖惩、轮换规则等方面的规定,显示其规则的公正与平等。最后,从《吕氏乡约》的运行方式看,“聚会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8]107。这些“聚会”规约体现了乡民协商机制的形成与常态化,确保了同约之人参与乡村道德教化的话语权,使《吕氏乡约》具有了村民自治的民主雏形。
由此不难看出,《吕氏乡约》是一个兼备地域性与自愿性的乡民道德公约,体现了“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9]2的官民相得愿景。换言之,《吕氏乡约》的出场充分体现了宋代乡村道德自治的政治统治意图。
四、《吕氏乡约》的现代性审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先治村、治村先教化的农村工作思路,可以看出全面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在国家工作中的重要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挖掘创新乡土文化,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作用”[12],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强调要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吕氏乡约》作为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蕴含了大量乡村道德建设资源,在团结民心、教化民众、淳化民风等方面对新时代乡村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团结民心
传统乡村社会乃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礼为核心按差序格局排列,乡规民约在这样的道德舆论场发挥着乡村建设的作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族体系逐渐瓦解,人与人的血缘、地缘联系逐渐淡化,以道德礼教为核心维系的乡村社会逐渐向以利为主导的多元社会转变。传统的道德秩序和伦理秩序已经破坏,新的道德秩序和伦理秩序还未建立起来,乡村出现了道德滑坡和伦理失序现象。传统道德礼仪的规范作用不再,乡民的道德认同感降低,乡民之间的交往以利益为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疏离淡薄,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广大乡村“空心化”,留在乡村的多为鳏寡孤独者和留守儿童,“空心化”与“空巢化”叠加,乡村社会更要传承传统道德守望相助和互相帮扶的精神,而《吕氏乡约》中“患难相恤”等规约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在《吕氏乡约》“患难相恤”篇中,规定了乡里之间的互助之法:“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8]107同约之人的生产生活物品乃至仆人皆可相互借用,遇到紧急事态时,应通知同约乡邻,大家出谋划策,共同应对;即使非同约之人遇到困难,也应该帮扶支持,对那些困难较大的人,还要团结同约之人共同救助。因此,《吕氏乡约》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美德画卷。“一切道德义务都源自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13],《吕氏乡约》将乡村道德主体的相互依赖关系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使乡村道德主体之间具备了道德义务关系,这种道德义务关系既能帮助同约的孤寡羸弱之人化解生活难题,又能凝聚大众形成仁者爱人的道德共识。由此可见,《吕氏乡约》中的“患难相恤”规约闪耀着“乡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本”光辉。在新时代乡村道德建设中,我们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要根据乡民的真实需求和合理利益诉求制定政策,以此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从而凝聚民心。
(二)文明以止化民成俗
无论古代社会还是当代社会,乡村场域中村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是我们进行乡村道德建设时应关注的重点领域,而《吕氏乡约》为当今广大乡村的民众教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样本。《吕氏乡约》规定对民众彰善纠恶的情况要进行记录,而且主要以彰善引导为主,以礼制的方式完成纠恶,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了乡村规约的道德教化作用。
《吕氏乡约》坚信“见善必行,闻过必改”[8]105,认为提升村民对善恶是非的识别能力是教化村民的关键,所以它主张对村民“德业相劝”。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广大乡村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加速期,广大村民还处于从传统乡土伦理向现代乡村伦理转型的过程中,道德伦理观念的转型还未完成,价值真空和道德标准不清晰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因此在进行乡村道德建设时还必须“文明以止”,即通过讲解现代乡村道德的义理让广大村民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现代乡村道德建设要求,尽快形成现代乡村道德伦理认知体系。当然,新的道德认知体系的建立不能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吕氏乡约》采取的惟善崇德的教化方式,历史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为今天乡村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范式,加大新时代乡村道德教育力度,使广大村民文明以止、化民成俗。
如前所述,《吕氏乡约》不但找到了惟善崇德的教化路径,还主张礼俗并治;它不仅对婚丧嫁娶等进行了规约,还对三类不同过失的惩戒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并以此规范村民的道德行为,保证其德化方案的有效落实。当代乡村虽然与传统乡村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以及国家法律在乡村实施已无障碍,但是广大乡村依然是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广大村民的道德自觉性有待提升,因此《吕氏乡约》关于“礼俗相交”的规定对今天的乡村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以新乡贤引领新民风
在古代,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多远离政治中心,“蜂窝状”的乡村社会分布使得中央政府对乡村社会的管控相对松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间组织就成为稳定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四民之首”的乡绅便是众多民间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乡绅集知识、财富、身份要素于一身,不但发挥着治理乡梓、服务乡民的作用,还主动承担诸如赈灾捐助、造桥修路、兴办水利、祭祀迎送等乡村公共事务,成为乡村社会的“稳定阀”。乡绅因为没有官方正式授予的对乡村社会的管控权,他们更多通过传统且符合乡民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方式来强化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因而他们也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捍卫者,发挥着道德榜样的力量。《吕氏乡约》的主要创立者吕大钧去世后,乡众“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11]612,凸显他在维护乡里和谐中的表率作用和道德影响力。
在当下,乡绅这一概念逐渐被新时代乡贤所取代。新时代的乡贤不再是像吕大钧那样仅仅依靠血缘、地缘关系联系乡村社会的传统乡绅,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致富回乡创业的企业家,有的是从海内外返回家乡投身乡村发展建设的精英人士,有的是基层乡村优秀党员、劳模,有的是退休回到乡村安家的知识分子、海归人士等,他们德才兼备,以振兴乡村为己任,深得乡民的敬重,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新时代乡村道德建设一定要发挥新乡贤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人才回流机制,为新乡贤发挥作用提供配套政策支持。具体而言,各级政府应组织搭建类似“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室”等具有服务性、互助性、公益性的基层乡村社会平台,以弥补乡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为不同专业知识背景和才能各异的新时代乡贤提供良好平台,将新乡贤的道德精神植入乡村社会,调解乡村道德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此外,各级政府还可借鉴传统乡贤文化的建设范式,如仿效古制设“公德册”、建“公德堂”、行“命名制”,把乡贤们乐善好施、造福乡梓的事迹记录下来并大力宣传、推广,让乡民走近乡贤、了解乡贤、信任乡贤、学习乡贤,进而推动乡村公序良俗的形成。有了政府的引导,更能“保障践行目标的实现”[14],也更易于让乡风文明之花开遍淳朴的乡村大地,使农村成为山美、水美、人更美的新农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不仅为社会的整体转型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着最大的实践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道德标高,很大程度上取决定于乡村道德建设状况,所以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古代乡规民约的具体内容有些已经过时,但乡规民约中蕴涵的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义理与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