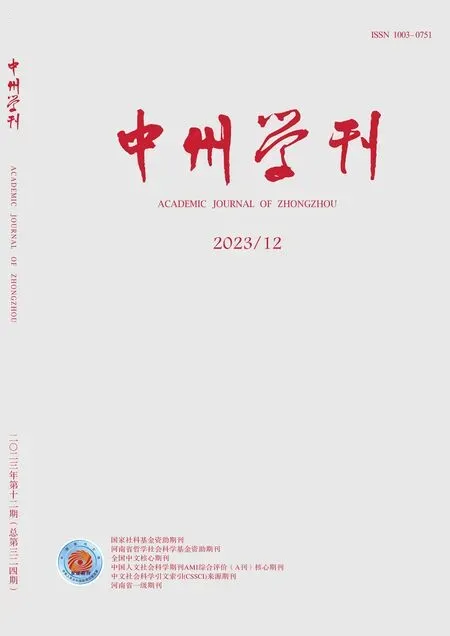厉祀、殇祀与《国殇》《礼魂》的祭义
曹胜高
《九歌·国殇》的祭义,王逸注为祭祀死国事者:“谓死于国事者。《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1]83死于国事乃为国牺牲,无主之鬼则为无后之人。《国殇》作为祭歌,无论是祭祀死国者,还是祭祀无后之人,皆用于特定的祭礼。要确定《国殇》的祭义,应该考察其施用的礼乐制度。
据《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其五为泰厉;诸侯为国立五祀,其五为公厉;大夫立三祀,其一为族厉[2]1305。厉为强死者、兵死者,王、诸侯、大夫分别祭祀泰厉、公厉、族厉,形成厉祀制度。《礼记》又载殇祭,将殇死者附祖,使其得食享,使之成为有主之鬼。《九章·惜诵》中亦载屈原向“厉神”求占而欲登天,厉神掌管众厉,与周制中的三厉之祀相应。楚简亦有攻解强死者之类的祷辞,表明楚地有厉祀制度。由于传统学说并不认同神灵魂魄分离之说,这就否定了王逸、洪兴祖等人所谓的“送神曲”之说,使得《礼魂》是《国殇》的附歌还是《九歌》的附歌充满了争议①。若结合厉祀、殇祀的制度设计,分析《国殇》的祭义,并结合早期中国的魂魄观念,细致地辨析《礼魂》的乐义,可以更为周全地理解《九歌》的祭义。
一、厉祀、殇祀的制度形态及其祭义
《礼记·祭法》载天子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皆用于祭祀前代无后者,意在使其有所归而不再作祟。孔颖达疏:
“曰泰厉”者,谓古帝王无后者也。此鬼无所依归,好为民作祸,故祀之也。……“曰公厉”者,谓古诸侯无后者,诸侯称公,其鬼为历,故曰“公厉”。……“曰族厉”者,谓古大夫无后者鬼也。族,众也。大夫众多,其鬼无后者众,故言“族厉”。[2]1306
厉为死而无后者,因其得不到祭祀而精魂游荡。天子、诸侯、大夫分别祭祀同级别之厉,以祈其不作祟:“五官皆有所食,无所食而有功者谓之厉。‘泰厉’有功于天下,天子立之。‘公厉’者有功于一国,诸侯立之。‘族厉’者有功于一家,大夫立之。”[3]天子、诸侯、大夫祭祀泰厉、公厉、族厉,实际是无后之鬼,即《小尔雅》所谓的无主之鬼②。
《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曾梦见大厉复仇,可见时人对厉的认知: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4]742—743
杜预注:“厉,鬼也。赵氏之先祖也。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故怒。”[4]742晋景公杀赵同、赵括,后梦见赵氏先祖以厉鬼的方式追索复仇。晋景公恐惧而问巫师,巫师居然能说出晋景公所梦的场景,并据此对其死生进行推断。可见早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知识系统来解释厉鬼。晋国史官将这件事记录在册,表明晋国君臣对此深信不疑。《左传》将之录入,亦信此事不虚。在时人的观念中,厉鬼能够报复、惩罚在世之人。故郑玄注:“厉,主杀罚。”[2]1305厉既能保佑本族后代不受侵害,更能报复他人。
《左传·昭公七年》又载伯有被驷带所杀后,“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4]1247。果然,壬子日驷带卒,壬寅日公孙段卒,郑国百姓皆恐惧。子产遂立伯有之子良止为大夫。据周制,大夫可立宗庙祭祀先祖,这就使得伯有之魂有所归,而不再作祟。人问其故,子产言:“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4]1247厉鬼得到祭祀,便不再为厉。由此来看,厉祀的用意正在于使无后之鬼得到祭祀,使其“有所归”而不作祟。子产聘晋时,赵景子又问及此事,子产解释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4]1248—1249人得精气魂魄而生,精气魂魄散则死。杜预注:“强死,不病也。”[4]1249强死者死于非命,其未散之精气、未安之魂游荡于世,依附于人而作祟,是为厉。只能采取措施使其得到祭祀,方使其有所归而不再作祟。
韩宣子听闻子产精通厉祀之道,私下宴请之,言及晋平公寝疾三月,泛祀众神,疾病却日益加重,请子产予以辨别:“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子产言:“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4]1244—1245子产认为晋平公所梦黄熊,乃鲧被杀后所化。鲧治水被杀而为厉,夏人郊鲧,使其魂魄有所归。周王立泰厉祀之,鲧不为祟。东周王室微弱,不祀前代泰厉。晋主盟诸侯,应当代替周王祭祀古帝王中有功而失祀者。晋遂以董伯为尸郊鲧,晋平公之病有所减轻。《国语·晋语八》亦载此事,子产有更详细的解释:“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5]由此可见,言鬼神是吉是凶,关键在于是否为其族类,本族祀其先祖为神,其能护佑子孙;他族不祀则为厉,便作祟于人。
这样来看,厉祀实际上是对无主之鬼进行祭祀,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作祟。殇祀亦如此,《仪礼·丧服》言:“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6]因此,二十以下者死亡者皆可称为殇。《礼记·檀弓上》载周人分别以殷人之棺椁、夏后氏之堲周、有虞氏之瓦棺来安葬长殇、中殇、下殇与无服之殇,由此形成殇葬制度[2]178。《礼记·祭法》讲述对殇鬼的祭祀:“王下祭殇五: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适士及庶人祭子而止。”[2]1307王、诸侯、大夫、士、庶人皆祀本族的殇死者。《礼记·丧服小记》言殇葬之法:“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不祭殇者,父之庶也。不祭无后者,祖之庶也。此二者,当从祖祔食。”[2]965由此可见,殇者由宗子祀于本族宗庙,从其祖食享,使其魂有所归。
楚简载楚有殇祀,殇者常随其父祖得到祭祀。葛陵简乙四109所载“乙未之日,就祷三世之殇”[7],即是对三代夭殇者进行祭祀。包山简222记载:“又敚见新王父殇,以其故敚之。与祷犆牛,馈之。殇因其尝牲。”[8]34王父为父之考,在祭祀新王父时,一并祭祀其庶子庶孙中的夭殇者,正是祔祖而祀。包山简225记载:“殇东陵连嚣子发。”[8]35从包山简201—202、221—222中所载祭祀顺序可以推断,东陵连嚣当为昭佗叔父或者伯父[9],其无后,便由家族祀为殇鬼,从祖祔食。包山楚简227记载:“以其故敚之:举祷祠一全豢;举祷兄弟无后者卲良、卲乘、县貉公各冢豕、酒食、犒之。”[8]35卲良、卲乘、县貉公无后,是为殇鬼,兄弟中有后者在祭祀时祔祀之。
由此来看,厉祀、殇祀的祭义,皆用于祭祀无主之鬼。泰厉、公厉、族厉祭祀有功于世而没有得以祭祀者,王、诸侯、大夫对其公祭,使其有所归,是为厉祀。殇祀为家族祭祀本族无后之殇者,使其从先祖附食,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
二、《国殇》为厉祀之歌
楚地设专门之神管理兵死者。九店楚简《日书·祷武夷》载武夷掌管兵死者:“□敢告□绘之子武夷:尔居复山之基,不周之野。帝谓尔无事,命尔司兵死者。今日某将欲食,某敢以其妻□妻汝,聂币芳粮,以量犊某于武夷之所:君昔受某之聂币芳粮,思某来归食故。”[10]这里言及武夷为神,掌管所有兵死者。兵死者之妻在某日要祭祀之,请求武夷准许其夫就食。换言之,也就是让兵死者的魂灵暂时离开武夷所司,归于家族享祀。
无论《祷武夷》是个别文本还是通用祷辞[11],都足以表明楚地设有专门之神掌管兵死者。兵死者不再归于家族祭祀,而是进行专门的祭祀,由武夷掌管。《史记·封禅书》载武夷君位次太一、山神、地主之后,在阴阳使者之前:“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史记索隐》引《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12]1386—1387这里言武夷为武夷山所居仙人,实误。武夷为司兵死者之神,其所居复山之基史载不详,不周之野则为幽都所在。《淮南子·地形训》记载:“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15]336不周之野为幽都郊野,正是武夷掌管兵死者之所。《楚辞·招魂》言:“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1]201幽都为冥界,武夷居于幽都之野,守护冥界,掌管出入。《汉书音义》云:“阴阳之神也。”[12]457阴阳使者掌管往来阴阳之事。
兵死者为厉,武夷掌管兵死者,当为屈原所谓的厉神。屈原《惜诵》云:“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屈原曾梦见自己登天,魂在中途失去凭借无法飞升,于是请厉神占卜。王逸注:“厉神,盖殇鬼也。《左传》曰:晋侯梦大厉,搏膺而踊也。”[1]124王逸认为厉神与晋景公所梦大厉类似,其有能力作祟。洪兴祖补注则引《礼记·祭法》“王立七祀有泰厉,诸侯有公厉,大夫有族厉”之说释之[1]124,以厉祀制度重新观察厉神。笔者认为,王逸将厉神解释为“殇鬼”,文意难以疏通。一是厉神当掌管楚所祀泰厉、公厉及族厉者,当为掌众之神,而非厉鬼。屈原向厉神求占,并得到指点,可见厉神具有比厉鬼高得多的法力。屈原是在自己魂灵无法升天时求助于厉神,可见厉神当掌管灵魂升天之事。二是子产言厉之作祟,在于其精气强而魂魄不散,厉为魂无所归者,立庙或祭祀能安抚之。屈原所言的厉神,恰恰能解决“魂中道而无航”的困境,通晓魂何以无法升天并能给予指点。因此,屈原所言的厉神不可能为厉或鬼,只能为掌管厉鬼之神,才能引导其魂灵升天。
楚人将被杀之人视为强死者。《左传·文公十年》载,楚范巫矞似预言成王与子玉、子西“三君皆将强死”,孔颖达疏:“无病而死,谓被杀也。”[4]530后来,楚成王赐诛子玉,成王又被太子商臣和潘崇逼而自杀,子西为白公胜所杀,三人皆死于非命,是为强死者。楚简中记载大量与强死者有关的祭祀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某种法力厌服,使其不作祟。天星观竹简中,常见“思攻解于盟诅与强死”“思攻解于强死”“思攻解于不”之类的祷辞[13],此乃借助祝祷、法术使强死者或不辜者无法作祟[14]。《淮南子·说林训》亦言:“战兵死之鬼憎神巫。”高诱注:“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杀之。憎,畏也。”[15]1198兵死之鬼亦为强死者,由神巫采用厌胜之法,使其不再作祟。二是对其进行祭祀,使之成为有主之鬼。包山简中多见以祔祖祭祀的方式来化解不辜者、兵死者之厉。如包山简217记载:“与祷楚先老僮、祝融、鬻酓,各一牂,思攻解于不。”[8]34包山简240—241记载:“与祷……各戠豢,馈之。思攻解于诅与兵死。”[8]36这里通过向楚国先公先王、先祖、社神祷祝,使枉死之不辜者、作战而兵死者,祔祖得以祭祀,以安其魂。楚简所言的“强死”“不辜”“兵死”者,皆为周人所言之“厉”,都可以通过祝祷、祭祀的方式以安其魂,使其不作祟。
据周制,兵死者不入祖茔。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杜预注:“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4]1089齐庄公为崔杼所杀,杜预言其死于兵乱而不入先王墓地。《周礼·春官宗伯·冢人》言其制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16]不入兆域,是在祖茔之外另行安葬。有功者居前,表明其为集体安葬,以功勋序次。这与在祖茔中安葬时以长幼序次不同,乃另立陵园以祀之。《左传》又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晋大破秦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被俘。秦穆公听闻后“素服郊次,乡师而哭”[4]476,以战败之礼哭秦军,迎接三将被释回国。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兵伐晋取胜后,“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杜预注:“封,埋藏之。”[4]499言秦穆公亲至殽地,安葬兵死者。司马迁对此这样记载:“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12]193—194秦穆公集体安葬曝尸荒野三年的兵死者,哭之三日,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秦穆公殽谷封尸的行为,一则证明兵死者不入兆域,就地集体安葬;二则表明当时确有安葬兵死者之礼。集体安葬兵死者之礼,于史有征而乏详载。其祭义主要是追述兵死者的英勇不屈,颂其忠于国家,告慰其英灵,祝祷其继续护佑国家。
在屈原时代,楚与秦作战多次,皆失地丧师。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春,秦斩楚甲士八万,虏屈匄、逢侯丑等七十余将,并占领汉中。“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12]1724,楚精锐皆出而大损。此后,楚国既无善战之将,也乏精锐之卒,只能被动防守。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联合攻楚,杀唐眜,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攻楚,楚死二万,景缺战死。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秦攻取楚八城。楚国无力与诸雄抗衡,只能退却。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楚国彻底失去自卫能力,任秦宰割。
兵死者不入兆域,则由国家进行集体安葬,举行祭祀仪式,安抚兵死者的英灵,使其得到祭祀。《国殇》先以追述将士作战场景赞美其壮烈:“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这表明祭祀的对象,是大战中的兵死者。
《国殇》的祭义体现在最后两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身既死兮神以灵”之句,是祝祷兵死者精魂升天为英灵。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临终时,提及鄢陵之战中战殁的大夫,《左传》中这样记载: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4]910—911
楚共王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大败,中箭于目,公子茷被俘。他深以为耻,以为罪责在己,于临终时所言的“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是希望大夫在天之灵,保护自己得以脱身。可见楚人认为兵死者有灵,在生前死后皆能保家卫国。
“子魂魄兮为鬼雄”之句,则为安魂之辞。王逸、洪兴祖对此这样解释:
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
〔补〕曰:《左传》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疏云:……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人之生也,魄盛魂强。及其死也,形销气灭。圣人缘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与神,教之至也。魂附于气,气又附形。形强则气强,形弱则气弱。魂以气强,魄以形强。《淮南子》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注云:魂,人阳神。魄,人阴神也。[1]83
洪兴祖引经据典讨论魂魄之义,试图阐明魂魄何以为鬼雄。我们认可补充其义。《礼记·郊特牲》言:“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2]817人合阴阳,阳为魂,阴为魄,魂魄聚则生,魂魄散则死。《韩诗外传》亦言:“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17]人死之后,魂飞而升天,魄散则入地③。兵死者精气刚毅,魂魄不散,因而需要对其祭祀,由阴阳使者引导其魂升天、其魄入地,魂魄各归其所方能安息。
因此,从厉祀制度来看,《国殇》用于楚国为公祀兵死者举行的国厉之祀,为安葬兵死者之歌。其名为殇者,在于伤祷兵死者其寿不永,使其得到祭祀,成为有主之鬼。其虽然名之为殇,祭义却为厉祀。
三、《礼魂》为安魂之歌
自王夫之《楚辞通释》言《礼魂》为送神曲后,学界多然之,亦有学者存疑。如蒋天枢《楚辞校释》便指出,太一、湘君、河伯、司命之属“乌有所谓魂者”[18]?认为诸神皆为神灵,神灵魂魄不散,不必用礼魂的方式送之。然《礼魂》位次《国殇》之后,多以其为《九歌》通用的送神曲。但其题名为《礼魂》,我们应该结合早期中国的魂魄观念,辨析其所礼之魂究竟为何,方能更准确判定其祭义。
从中医理论来看,魂魄相生相依。《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概括了早期中国人对魂魄的理解:“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魂随神往来,魄随精往来。魂体气能升降,魄存形能聚散。《类经·天年常度》这样解释:“阴主藏受,故魄能记忆在内;阳主运用,故魂能发用出来。二物本不相离,精聚则魄聚,气聚则魂聚,是为人物之体,至于精竭魄降,则气散魂游而无所知矣。”[19]59魂飞魄散则人死,魂魄长存则长生,故“凡人之死,魂归于天,今人云死为升天者,盖本诸此”。[19]1人死则魂升于天,魄入于地。
从道家学说来看,魂魄存于肉体之中,超越魂魄约束方能体认大道。《庄子·在宥》言及体道之法,在于摆脱肉体体验,而合乎自然大道:“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20]心为人体的主宰,魂寄托于肉体,只有坐忘,才可以体认自然之道。《淮南子·主术训》亦言:“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15]608—609只有天地相合,魂魄若无,才能黜形离知,不劳不损,体道通神。《淮南子·览冥训》又言:“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绌聪明,大通混冥,解意释神,漠然若无魂魄,使万物各复归其根。”[15]497体道者要摆脱魂魄对人的约束作用,才能体察天地大道。
道家修炼认为魂魄合一,才能长生。《周易参同契》卷中言道家修炼之术,在于合和阴阳,使得魂魄永固:“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魂魄不离不散,以求长生。《道枢》载诸多养魂制魄之术。如《阴符篇》言及修道总则时云:“阳为魂,阴为魄。魂者欲人之生,魄者欲人之死。故圣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含真抱一以归于太阳,养阳之魂以消阴之魄,神仙之道其尽于斯矣。”[21]道教修炼的核心,是魂魄相依,魄不散则阴存,阴存而阳守,魂永存则长生,采用合魂营魄、养魂制魄、拘魂制魄等法,可以长生,可以成仙。因此,在道教传说中,常有固守魂魄而长生者,如山世远“使人魂魄自制炼。尝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22]254;尹喜“道德虚凝,魂魄固守,形一神万,道乃成就”[22]294;钟离权亦言成仙之术:“若能全阳而聚其冥魂,以合阴魄,使阴阳相合,魂魄成真,是谓真人。”[22]1044只要养魂制魄,就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显然神仙不存在魂飞魄散,自然也不存在礼其魂之事。
由此来看,《九歌》中所祀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等皆为楚地所祠神灵。如云中君“与日月兮齐光”[1]58,湘君能够“令沅湘兮无波”[1]60,湘夫人可以“将腾驾兮偕逝”[1]66,山鬼能“东风飘兮神灵雨”[1]80,皆精爽无贰,来去自如。屈原在《惜诵》中登天不得,又向厉神求助,厉神可以直接让屈原升天。可见,楚地神灵皆精气不散、魂魄永存,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不必以礼魂的方式送其升天。只有常人去世后,魂升天、魄归地,方能得以安息。因此,《礼魂》不应当是礼送众神的送神曲,其只能是告慰逝者的安魂曲。作为厉祀结束后的安魂曲,《礼魂》在《国殇》之后演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礼魂》中以会鼓、献花、歌舞祝祷兵死者安息,这些正是礼魂的方式: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1]84
成礼,乃言祭祀兵死者之礼完成后,以会鼓送其魂灵升天。鼓以动阳,春秋时以鼓救日、击鼓进军,春日以鼓激发阳气。会鼓以多种鼓、多面鼓齐奏,鼓荡天地阳气,以助阳魂升天,实则祝祷兵死者之魂升天,使有所归而安息。春兰生阳,秋菊滋阴,二者为礼魂所用香草,意在使魂魄分离,各有所归。《神农本草经》言,兰草“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23]45,其能助阳气升腾。《韩诗》亦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24]这里言春日采兰,以养魂营魄,可以使诸病不侵。祭祀用春兰,在于其可以鼓舞阳气,助阳魂升天。《神农本草经》又言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23]11。九月采菊入药,用其阴而养血,足以营魄。秋菊能安魄,因此后世常用秋菊纪念逝者。由此可见,《礼魂》中以春兰礼魂,以秋菊安魄,以击鼓歌舞致敬兵死者,使其魂有所归,魄能安息,从而完成对兵死者的祭祀。因而,《礼魂》当为厉祀之后的安魂曲,用于《国殇》之后,而非《九歌》通用的送神曲。
综上所述,将《国殇》置于楚国乃至周代的礼乐制度中,就可以清晰看到其祭祀为国牺牲者的祭义;由此观察《礼魂》的祭义,分析其所在时代的魂魄观念,从思想史上可以看出其作为歌辞,是对《国殇》的延续,而非对所有神灵的礼赞,应称为《国殇》的附歌。从制度史、思想史重新观察《九歌》的创作,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不同乐歌的祭祀对象及其祭义,为重新研究《楚辞》提供更为宽广的路径,使其在文学意味之外,更具有制度史、思想史的意味。
注释
①王逸、洪兴祖认为《礼魂》为《九歌》的送神曲,汤炳正、李大明等注《楚辞今注》则认为神灵不需要送魂,《礼魂》仅为《国殇》附歌而非《九歌》送神曲,从而使得《礼魂》的性质存在差异,参见潘妍《〈九歌·礼魂〉各注本归纳分析》(《名家名作》2019年第12期)对《礼魂》性质的分析。②《潜夫论·巫列》:“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于民者,天子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觋之谓独语,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七神,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参见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6页。③龚自珍《释魂魄》言:“浑言之,人死曰鬼,鬼谓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无知者也。……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东西北南以游。招魂之礼,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亲也。屈原、宋玉之词,则求之上,求之下,求之东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状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义也。魂有知,故礼有招魂,楚巫有礼魂;魄无知,故周礼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属善,以魄属不善,求之孔、墨,具无其义。小说家言人遇鬼于墟墓,然则魂有恋魄而悲死者矣。孰达孰悲?吾弗知。”参见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