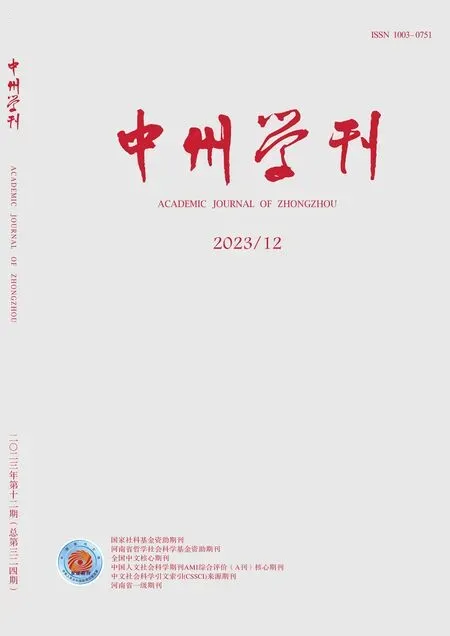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郭卫华
“情”和“理”均为人性,二者在人的精神生命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对情理关系进行文明设计,成为中西方精神文明之异的重要标识:西方文明形成以理为本的情理二分传统,中国则侧重以情为本的情理融通,即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并形成了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在Kant哲学,理性至上而神圣;在中国传统,理性只是工具,人的生存、生活、生命才是至上和神圣(它的前提又是整个自然界的生存),从而人的情感才是根本或至上。”[1]113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情”与“理”融通的中国化表达就是“通情达理”。“通情达理”既是中国人价值世界的生活化表达,也是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凝结,并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境。
一、“情”据“理”而“通”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情”被赋予情实、情境、情绪、情欲、情感等多种内涵。“情”在被赋予多种含义的基础上,还被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成为“天—命—性—情—道—教”中的一环。同时,在这一本体论的逻辑中虽无“理”字,但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由“天道”向“人道”的落实,无不彰显着情理融通的文明智慧。
从人性发生学的角度看,“情”的初义为人性接物而感通生成欲望、情绪、好恶等自然之情,并在道德哲学中凝炼为两种含义:反映人的生物性需求的自然情欲以及物我感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好恶之情的情感义。“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礼记·乐记》)在人性论角度,无论是自然情欲还是好恶之情,都具有自然必然性,都属于人性,因此情欲与情感同源并具有相通性。当然,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的文化设计中,二者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又截然不同。自然情欲成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规约的对象,好恶之情经由理性提升而成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的精神动力。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首先肯定满足人的自然情欲的客观合理性,并把自然情欲的满足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即使儒家极为重视“大体”对“小体”的超越、弘扬“舍生取义”的道德精神,但在普遍意义上,仍始终坚持适当满足人的自然情欲需求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本前提,如宋明理学高扬“存天理,灭人欲”,反对的也只是过度的人欲,并不否认满足自然情欲的客观必要性,甚至认为满足人的合理欲望本身内含于“天理”之中。道家更是从天道自然的哲学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然之情的满足,乃至产生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贵生”思想。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受肯定自然之情价值取向的影响,其佛法中“不杀生”“普渡众生”的理念也得到凸显。但是,人作为拥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在追求自然情欲的满足时,与物相感应,又产生好恶之情。“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行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2]在这里,人的自然欲望虽然有客观必然性,但在满足自然欲望需求的过程中又会产生主体意志自由渗透其中的好恶之情。“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好恶之情因与物感通而产生,具有自然性,但因交织着自由意志的好恶之情,其已不同于本然的天然之性,而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于是,“性”接物感通产生的自然之情虽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在物我感通中如何满足自然情欲便具有了善恶意义,好恶之情也随之处于善恶的临界点:好恶之情如果得到道德理性的引导就会成为扬善抑恶的精神动力,反之则会激发恶,“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3]。
于是,好恶之情因与自然情欲相通而具有自然必然性,不可否认,不可抹杀;同时,因其交织了意志自由,又成为“自然人”走向“道德人”的基础和逻辑前提,正所谓“礼因人情”。那么,好恶之情如何由自然之“情”升华成为具有伦理普遍意义的道德之“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诉诸“通”的哲学智慧。“通”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内涵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总体上讲,‘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超过一百余种训诂方式,大体可归纳为十一个方面:1.达、至;2.行;3.顺、畅;4.共、同、举;5.开;6.连;7.深;8.知可;9.道;10.卷;11.辄。按其内容可归为‘变通’‘会通’‘贯通’‘感通’四个层次。可见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通’不仅是一个哲学观念,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代表一种高明的精神境界。”[4]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正是基于“通”的哲学方法,化“通”的理性智慧为“通情”的伦理道德智慧:在“天—命—性—情—道—教”的本体建构中,“情”上通“天—命—性”而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和神圣性,下通“道—教”的理性引导而取得了人化的形式,并交织着人的意志自由。由此,自然之情与“道—教”(道德理性)相关联后,“情感”与“情欲”相区别开来,情欲因其生物性而成为道德哲学的规约对象,“情感”因交织着意志自由经道德理性引导而成为道德哲学发挥伦理教化功能的精神动力。
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是:“情感”和“道—教”如何关联?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文化逻辑就是通过人伦秩序之“理”(“礼”)对血缘亲情进行文化塑造,赋予血缘亲情以伦理本性成为“通情”的起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当然,基于“天—命—性—情—道—教”本体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之追求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抱负来看,血缘亲情虽然具有直接性和绝对性,但是“情”的普遍形态如果仅仅囿于血缘亲情,就仍有其局限性和道德风险。“儒家在血亲主义架构中陷入的上述伦理悖论,构成了它内在固有的一个最根本最致命的深度悖论……说它最致命,则是因为始终高调地以弘扬伦理道德为己任的儒家思潮,恰恰在这个悖论中违背了‘不可坑人害人’的正义底线(亦即孔子自己倡导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居然公开赞美那些为了维系血缘亲情而不惜坑人害人的道德邪恶行为。”[5]由此,如何突破血缘亲情的局限性,使千千万万囿于家庭的私情贯通为具有伦理普遍意义上的“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基于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一体关联,诉诸推己及人的情意感通,通过发挥忠恕之道的理性能力,以己之情推扩至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通过“尽己之理”与“推己之情”等“通”的哲学智慧,个体通过发挥自身主体性自由使“己”之“情”在伦之“理”的秩序安排中与他人之“情”相通,乃至与天地相通,于是,“情”便具有了伦理普遍性。“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之理,我与人同乎其情,则又同乎其道也。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由此思之,则吾之与人相酬酢者,即人人各得之理,是即斯人大共之情,为道之所见端者也。”[6]与他人之“情”相通相合后,个体便能从一己偏私的陷逆中挺拔出来,使彼此间在身、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最终打破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彼此隔绝,通过自身道德之行与他人之好恶、情义相通相合,进而在彼此的情意感通中达至心灵顺畅而无碍的精神自由之境界。
总之,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情通则理得,以精神的方式凝结为“天理”或“天道”。由此,“情”也从自然之情的封闭性据“理”而“通”,从而获得开放性,自然之情进而升华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情。关于中国这一情理智慧,孟子以“经验变先验”(李泽厚语)的方式,通过“不忍人之心”的情感体验进行了“通情”表达:“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二、“理”由“情”而“达”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关于“情”的本体意义建构中,“情”虽然被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但在人类实际的道德生活中,“通情”最终的文明归宿是“达理”,因为“通情”只是为个别性通向普遍性提供了现实根据,“通情”本身还无法形成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和道德原则,“通情”还需走向“达理”,从而获得精神哲学意义。
在文字学意义上,“通”和“达”可以互训互证,如《说文》辵部:“通,达也。从辵,甬声。”但从通情达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看,“通”和“达”又有相区别的一面:“通情”更重于过程,侧重于言说人与物的感通、人与人的情意感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而“达”更侧重结果,在道德哲学意义上体现为个体应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应达到的至善,具有开放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如老庄所讲的“虚”、佛学讲的“空”和理学家所求的“廓然大公”,都是主张破除一己私欲和主观任意性,以开放的心态和超越现实世界的意义追求,求得无私至善之通达。因此,“达理”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又是一种伦理抱负,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当然,基于“通情”与“达理”的内在关系,“理”无“情”则不达。
第一,从道德的角度看,“达理”展现为个体的德性修养。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既有物质之维,也有精神之维。对于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本质属性而言,精神之维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更具根本意义。因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人性前提虽然奠基于人的自然之“情”,肯定自然情欲的满足对于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其关注点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因此,“达理”的首要道德目标便是“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这种转化既关乎作为理性凝结的伦理准则的引导,又关乎个体内在情感世界的价值追求。从现实的形态看,“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是在道德实践中完成的。而道德实践的发生既出于“我应该做”的道德认知,也出于“我想做”的道德意愿。“我应该做”主要展现为理性的自觉意识,而“我想做”则融合了意志和情感。具体而言,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视域中,“自然人”向“道德人”转变的核心要点就是自然之情(也即好恶之情)经由理性的引导、教化升华为涵容理性和意志的道德情感,如儒家的“仁”、道家的“慈”和佛家的“慈悲”都是“情”与“理”互融又互渗。在这种转化中,个体超越自然情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呈现出以善为目的的与他人、社会、天地的伦理互动的自我开放中,由此成就了“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道德人”与“自然人”的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拥有了理性、意志、情感相互融摄而形成的道德品格,并在反复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为中化为人的第二天性,习惯成自然,并彰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如儒家所言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在这里,“见”展现的是对人伦之理的理性自觉,“自然”包含着情感(爱亲之情和恻隐之心)的体验和感受,凸显出情感由知到行的直接性,所以这里的“知”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和认知,而是融合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道德行为,在“知孝”“知悌”“知恻隐”的道德实践中,人就超越了动物性而成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的“道德人”。
第二,从伦理的角度看,“达理”体现为追求人伦和谐的伦理能力。在道德哲学意义上,“达理”不仅体现为道德上的理性认知,还包含着付诸道德行为的实践智慧。对于“伦理优先”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而言,“达理”价值目标便是“人伦本于天伦”的伦理和谐。那么,如何实现伦理和谐?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源于中国血缘文化,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伦理精神。由此,在实现伦理和谐的这一价值追求中,“达理”展现为一种以伦之理涵育的道德之情为内在精神动力,并在践行伦理准则的反复磨炼中形成的伦理能力。这种伦理能力基于人的类本性。人作为类的生命存在,其意志自由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尽管人的意志自由在抽象形态上与人的类本性相冲突,但在现实性上,人的意志自由落实于实践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展现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理上。这种外在关系从与人的生存发展最切近的关系逐步外推而形成,既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包括自然界的整个宇宙在内。因此,“达理”所体现的基本能力就是维护家庭这一伦理共同体的伦理能力。家庭作为以血缘为本位的伦理共同体,其维系的主要力量便是情感。“血缘本位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的重视,因为情感是家庭生活的绝对标准,血缘关系的绝对逻辑,而家族血缘又是情感培养的母胎,这种双向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绝对意义。”[7]当然,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不再是自然性的情感,而是经由伦理的理性引导、意志自由参与其中的道德情感,如孝和悌不仅仅是出于子对父、弟对兄的一种自然亲情流露,而且成为涵容理性认知上的“应当”和意志参与其中的“意欲”的情理或义理。这种基于家庭自然性的情理只是培养人的伦理能力的起点。人作为类的生命存在,其伦理能力不能仅局限于家庭之内,而要突破家庭的局限,向外、向具有更大普遍性的伦理共同体延展,即“治国”和“平天下”。伦理意义上的“治国”和“平天下”就是发挥道德情感的超功利性和合同性,以“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胸怀实现“天下一家”的充满温情与平和的伦理抱负。
第三,从“道德”—“伦理”统一为“精神”的角度看,“达理”为“致中和”的自由和谐境界。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主要是通过人追求善的行动构建以自由与和谐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生活世界,并展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所谓自由和谐,在个体层面,意味着人人作为拥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能够超越自然情欲的束缚,进而实现个性的自由伸张;在群体层面,意味着道德主体在与他人、社会、国家、世界乃至自然宇宙的关系处理中能够“伦理地在一起”,即在人与世界的共在共存中追求幸福美好生活。那么,以人之性情为基点的“达理”该如何实现自由和谐的精神境界?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达理”在经由“道”之“德”的性情锤炼和“伦”之“理”的实践智慧引导后,其终极价值追求便是“致中和”。何谓“中和”?《中庸》对此进行了明晰阐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从人的性情的角度看,“中”和“和”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性情”之未发与已发的区别,但是“已发”是否“皆中节”,则关涉到“情”的发育流行是否符合“理”和“道”的理性要求,因此,源于“情”的“达理”本身既是“理”引导“情”的过程,也是“情”之“达理”(“皆中节”)的精神境界追求。具体而言,人作为情理交融的生命存在,其生存于世不仅需要主动地建构理性秩序以获得彰显人的主体性自由的生命情态,即“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需要遵循以和谐为终极目标的情感逻辑,进而追求宇宙万物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在道德哲学意义上,“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就是“达理”,“达理”既需要理性秩序(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礼”)的约束引导,更需要和谐情感的精神支持。“我们伦理地在一起”的终极追求不仅是一种理性秩序,更是一种情感逻辑。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理”据“情”而“达”正是在“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情怀支持下追求与万物共生并育的自由和谐境界,即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能够彼此成就并在相互成就中获得各自顺从本性的发展。
三、通情达理开启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哲学逻辑是:“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由此开辟了不同于西方情理二分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中国哲学的旨归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传统伦理思想是以情理融通为特质的心灵境界。在物欲泛滥、精神疲软、心灵失序、精神家园荒芜的现代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和优势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8]
第一,“克己”。在中国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己”具有两种内涵:一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对生物本能、自然情欲的克制;二是以伦之“理”的心灵秩序建构把好恶之情提升为向善之情。在“克己”的情理结构中,“理”虽然源于“情”,在以伦理道德的方式化解自然情欲、好恶之情等“私欲”的基础上凝结而成,但对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而言,“理”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的“克己”精神中“理”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而不是主宰地位。因此,关于如何对待自然情欲,中西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明理念:西方宗教型文化中,理性居于对自然情欲的主宰地位,“信仰—情感”结构不但与人的自然情欲无关,而且基于理性纯粹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自然感性遭受折磨甚至牺牲而建立对上帝的信仰与服从。以理性绝对主宰自然情欲导致的文化后果就是:低于上帝的信仰和服从以斩断与此岸世界的一切情义关系为前提和代价,这种文化模式在现代性中一旦遭遇到“上帝死了”的文化挑战,如何对待自然情欲就成为西方文明之痛;中国的情理精神则坚持“道始于情”,承认自然情欲的自然必然性,以道德的方式适当满足自然情欲本身就是“理”,并且理性化的向善之情正是从人的自然之情中升华而来的。“情理之所以为情理,就在于有情斯有理,无情必无理;理从情出,情通理得。”[9]由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在此岸世界的生存、生活、生命中,以构建有情的生命观,在“克己”的生命展现中“理”源于情、引导“情”,却又最终融于“情”中。同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神不仅展现为消极意义上的对自然情欲的克制和引导,而且因涵容道德意志的“理”对自然之情的主导和规范,在积极意义上还展现为由“克己”到“舍己”的人性崇高和圣洁,如儒家的“舍生取义”,道家以“清静为天下正”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命智慧,佛家以“治心”破除贪欲的出世情怀,都展现了人所具有的崇高的道德力量。这些道德力量在面临利与害的重大冲突时,能够激励人类强化自己作为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渗入关切他人、社会利益的人道情怀。“个体离不开群体,每个社会群体为维持其生存、延续都要对个体做出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有时并要求个体做出各种牺牲包括牺牲生命,这就是社会的伦理秩序。”[1]156中国这一展现道德崇高性的克己精神,对有效化解当代中国面临市场经济逐利性、自利性等引发的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和价值范导功能。
第二,“爱人”。与“理”主导的“克己”精神相比,“爱人”展现为以利他为本质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正面价值关切,“情”(确切地说是向善之情)居于主导地位,是契合人的类本性的伦理精神形态。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己”与“爱人”虽然表现出“理”与“情”的不同关联,但二者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贯通的。“克己”由消极层面克制自身私欲向“舍己”的过度和升华,在现实性上表现为对他人同情、关怀的“爱人”精神。二者在道德哲学意义上都体现着人性的崇高和精神力量。当然,二者在形式和侧重点上也有所不同,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伦理与道德、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克己”致力于反求诸己,侧重于挺立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力量,有助于培育个体坚强的道德意志,以理性凝聚的意志力量升华人的自然之情,为克服个体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而形成“爱人”精神提供了主体条件;“爱人”精神则强化了人的类本性,凸显了人在关系中的价值和意义,肯定了人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应当被关爱和关心,人的尊严是在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实现的,人类种族的绵亘、延续更需要“爱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一己私欲,帮助人类克服一切生存和发展困境。在此种意义上,“爱人”在维系人与人之间情义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克己”甚至“舍己”的理性意志力量,“情”的精神凝聚力也进一步凸显。“爱”的情理融聚力量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尽管在中西方道德哲学中属老生常谈,但从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挑战看,这一精神在今天仍需要强调。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化社会的变迁,个体自由、个性伸张在现代民主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和实现,但是人作为类本性的生命存在,个体始终处于与家人、朋友、同事、同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倡导个性独立、彰显个体权利的现代都市文明虽然对传统熟人社会带来颠覆性冲击,但是人类会始终处于人与人、人与社会极为紧密的关系网中。而且与以往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需要坚定的情义力量支撑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乐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爱幼等彰显“爱人”精神的道德规范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凸显。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的慈爱精神、佛家的慈悲情怀在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依然熠熠生辉,并具有世界意义,就是源于“爱人”的情理融聚力。
第三,“万物一体”。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基于“天—命—性—情—道—教”的本体建构,“通情达理”中的“通”和“达”不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可以相通,使“我”能够成为“我们”,而且还追求人与万物相通而融合为一体的极致境界,即“万物一体”。“万物一体”的境界追求既源于“克己”和“爱人”,同时也是对“克己”和“爱人”的超越,为“克己”和“爱人”内化为人稳定而持久的德性品质提供着本体性根据。之所以说“万物一体”源于“克己”和“爱人”,是因为在“克己”与“爱人”的道德实践中,个体既认识到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生命不可逆、人固有一死等有限性),同时作为有精神的生命存在,个体也体悟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何为“无限”?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的回答就是“万物一体”的境界追求,并且这一境界追求是在情理融通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现实性。“情”据“理”而“通”的前提是万事万物相通而不相同,这种“相通”意味着世间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如何把这种联系纳入人的主体在世结构中,并且在这种在世结构中使人能够追求美好生活?根据通情达理的精神逻辑,就是以“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责任感使万物相通而成为“一体”。这种责任感的极致表现就是人在体悟到“万物一体”时所产生的一种令人敬畏、仰望和崇拜的激情和热情,这种激情和热情能够激励个体超越有限追求无限,通过对“克己”和“爱人”的超越而仁爱万物。诚然,在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大肆流行的当今时代,对自然宇宙的科学探索固然重要,人作为生物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有机统一的生命存在,功利追求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人还应当超越功利而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生在世,既不能离开大地,又总爱仰望上天;既要讲科学,以求获得自然物为我所用的实际利益,又有根本不计较任何利害的对真善美的追求(科学不仅有实用价值,其本身还有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方面),甚至有至善、至美、至真的纯真理想和目标的敬羡、向往和崇拜之情;既有‘人之去禽兽也几希’的非神圣方面,又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佛性’的神圣方面。”[10]当今时代因缺乏对精神境界的文化认同,在对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迷狂之下过于执着对人、对世界的“主宰”,以至于战争、生态危机、科技异化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万物一体”宇宙情怀所彰显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智慧不失为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