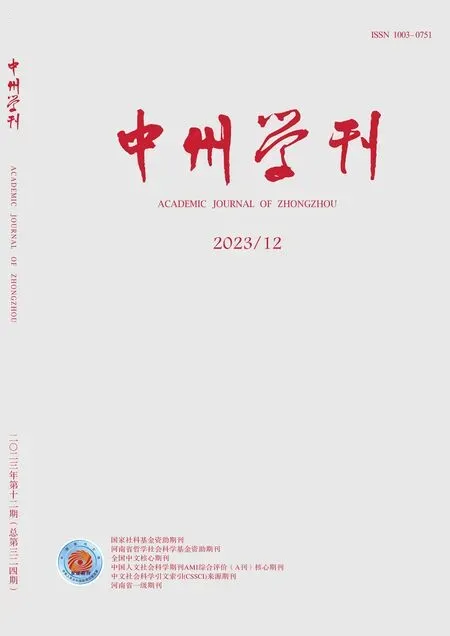《七略》之“略”再释
——兼论《公羊传》之“甚恶”
李若晖
《别录》《七略》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图书总目,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但是《七略》一名之释义,有章太炎与姚名达二先生之说歧出,学者往往依违其间,有如触蛮相峙。这需要学者不惮烦琐,仔细审察古代文献,对这一问题给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一、《七略》之“略”章姚二解
章姚二说各有拥趸。右章者如孙显斌曰:“《说文》:‘略,经略土地也。’‘略’有分界之义,在‘七略’之名中则有分类之义,所以‘七略’为七‘略’之合称。姚名达、吕绍虞以‘略’为简略之义,这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对‘辑略’的解释必然牵强。”①左姚者如董广文,以之为姚名达的学术贡献之一[1]。曹慕樊《目录学纲要》则未引章、姚之说,自出己意,将“略”释为“要”:“刘歆把各类书编在一起,只存刘向叙的大要。大要叫‘略’……及到后期,成果多了,就得编个简要的书目,以备查阅。这工作由刘歆去做。做这项工作,只能以刘向奏进叙的内容做根据。省文存要,所以叫做‘略’(略即纲要的意思)。”②之所以二者难分轩轾,孙振田的分析可谓到位:“大致言之,衡之以《七略》文本上的特点,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单纯就《七略》的确分为七个板块而衡之,章先生之论无疑是能够成立的,而再就《七略》确为据《别录》而来且较为简来看,姚名达之论当然也能成立。”[2]也就是说,二者各有其长。章说与《七略》之名若合符契,所谓《七略》就是七个“略”合为一书,故名《七略》。将“略”释为“简略”显然无法解释作为篇名的“略”,如《六艺略》之“略”的意义。姚说则注意到《别录》《七略》内容与名称的整体性,也颇有见地。
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章、姚二说的立论依据,以推鞫其是否成立。
二、章姚二说之辨析
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序》:“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所以标别群书之际,其名实砉然。”③《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则讲得更为明白:“略,本义为略取(画界限而占领之曰略取),引申为劫略,汉律有‘略卖’。经略与经界谊近,《七略》,言七种书分界部居也。”[3]“略”有疆界义,乃古之常训,可毋庸置疑。《小尔雅·广诂》:“略,界也。”莫栻《广注》:“《左氏》庄公二十一年,惠王与郑厉公‘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又‘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杜注:‘略,界也。’”[4]是则章说可谓有理有据。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然则《七略》何以名略欤?斯可引古义以明之。《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5]42
姚说的全部根据,即“录”“略”相对,“录”有“详细”义而“略”有“简略”义。由于姚说成立与否,完全建基于对《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一语的理解,故而有必要廓清“《春秋》录内而略外”之义。详审《公羊传》之文,其所谓“《春秋》录内而略外”的具体做法是“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即对于鲁国的大小之恶都要记载,只是具体的书法不同:小恶直书,大恶曲笔;对于诸夏的记载,却是只直书大恶,小恶则不予记载。韦昭《国语叙》“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董增龄注:“录者,记也。隐十年《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6]5《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7]171意谓史官于君主行为,有闻必录,无论大小善恶,皆予记载。《国语·吴语》:“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韦昭注:“录,第也。敢问先期乱次之故。”[5]311韦氏以“第”释“录”乃随文释义,意谓吴王未能依照双方事先约好的行事次第在日中会面,而是提前在昧明即来至晋垒。此“录”当指吴晋会盟程序列表,于会盟中之大小事件靡不记录。至于“详”,《说文》:“审议也。”段玉裁注:“审,悉也。”[8]这是指记载一件事情的细节之完备,与“录”指对于不同性质事件均予记载显然不同④。如是,相应地,“略”之义也当不同。
《春秋经》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公羊》何休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徐彦疏:“鲁得尊名,不与外诸侯同文,即是尊鲁为王之义。”[9]28《公羊传》何休《解故》“隐公第一”下徐彦疏引何休《文谥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9]7王鲁则当以王文述鲁事。但如是则在现实中僭越了周天子,因此只能将外诸侯贬一等,以大夫之文述之。这样鲁仍述以诸侯之文,既未僭越天子,又高外诸侯一等,可谓两全。可注意者,何休此注之“贬外”,杜预乃径言“略外”。《左氏》杜预注:“称卒者,略外以别内也。”孔疏:“诸侯曰薨,礼之正名。鲁史自书君死曰薨。若邻国亦同书薨,则与己君无别。国史自在己国,承他国赴告,为与己君同,故恶其薨名。虽赴称薨,皆改赴书卒,略外以别内也。《释例》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7]50可见“略”之义,即是在礼制上贬低一等。《穀梁》范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至于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两通其义。”杨士勋疏:“何休称死而异名者,别尊卑也。葬不别者,从恩杀略也。”[10]所谓“葬不别”,即仅仅在外诸侯死时“略外以别内”,在该诸侯下葬时,就不再区别内外,完全依照其臣子之辞。杨疏解释之所以如此,是“从恩杀略”,也就是恩义减低了。此处“杀略”乃同义连用。《汉书》卷八十五《杜邺传》:“《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师古曰:“杀谓减降也,音所例反。”[11]《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7]631《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引作“降杀以两”[12],即每降一等礼数减二。可见“略”也正是减一等之义。而宋穆公之“卒”也仅一字,在字数上与“薨”相同,可见并不存在记载内容“详略”的问题,而应是礼制上的降等。《春秋经》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杜预注:“称妇,有姑之辞。”孔颖达疏:“桓三年‘齐侯送姜氏于欢’,注云:‘已去齐国,故不言女。未至于鲁,故不称夫人。’然则往逆当称逆女,入国当称夫人。此时逆则卿不行,入复不告至。其礼轻略,异于常文。徒以有姑,故称‘妇’,以齐女则称‘姜’,直云‘逆妇姜于齐’,略贱之文也。”[7]305-306言“轻略”,言“略贱”,皆礼制降等之谓。
《春秋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公羊传》:“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录,下士略称人。”徐彦疏:“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来归脤’,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录之,故以为难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来归脤’是也。云中士以官录者,言以所系之官录之,即此是也。云下士略称人者,即僖八年春,‘公会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9]13-14依何休之说,天子之上士要加一等,以大夫之礼待之,故而以名氏通,即定十四年的“石尚”;中士“以官录”,就是如实记录其官称,不加一等也不减一等,即此隐公元年之“宰咺”;下士略称人,则为减一等,既不称官也不称名,此即僖公八年的“王人”。此处何休恰恰以“录”“略”对言,此“录”“略”也绝不可以“详细”“简略”来理解,只能是在礼制上加减一等。
由此数例也可知《春秋》学中所用的“录”“略”实为礼学术语,即在礼制上加减一等之义。《仪礼·士丧礼》:“设盆盥于馔东,有巾。”郑玄注:“为奠设盥也。丧事略,故无洗也。”贾公彦疏:“云‘为奠设盥也’者,谓为设奠人设盥洗及巾。云‘丧事略,故无洗也’,直以盆为盥器也。下云‘夏祝及执事盥,执醴先酒’,即是于此盥也。但诸文设洗篚者,皆不言巾,至于设洗篚不言巾者,以其设洗篚,篚内有巾可知,故不言。凡不就洗篚皆言巾者,既不就洗篚,恐挥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丧事略,不设洗篚,皆见巾是也。”[13]424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十《丧礼通故》三:“经‘设盆盥不设洗。’郑玄云:‘丧事略。’以周案:礼,设盥洗有不同者,洗礼繁,盥礼简,丧事略,故不设洗,此一义也。洗有定处,盥就近为之,丧事遽,故设盥不设洗,此亦一义也。礼有以之优尊,洗盥并设,如《公食礼》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诸礼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故既设洗,又设盥,此又一义也。凡盥洗皆有巾,诸文设盥言巾,设洗不言者,巾在篚也。”[14]黄氏此处之“洗礼繁”乃谓洗礼加一等,“盥礼简”为言盥礼照正常礼制规定不加(不减),“丧事略”则是丧事较正常礼制规定减一等⑤。正常之盥礼用洗器。《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郑玄注:“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士用铁。”[13]8洗设于庭。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二《通例》下“凡庭洗设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诸侯当东霤,卿大夫士当东荣,水在洗东”条,引《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乡饮酒》《乡射》:“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所谓卿、大夫、士之礼也。《燕礼》:“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大射仪》:“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公食大夫礼》“设洗如飨”,注:“必如飨者,先飨后食,如其近者也。《飨礼》亡,《燕礼》则设洗于阼阶东南。”郑氏以《燕礼》证之,是《公食大夫礼》之洗当亦在阼阶东南也。此皆当东霤之洗,所谓天子、诸侯之礼。卿、大夫、士两下屋,故云“当东荣”;人君殿屋四向流水,故云“当东溜”,其实设洗皆在阼阶东南,异其文,不异其处也[15]91-92。故盥礼需由堂上下阼阶至庭就洗,可参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二《通例》下“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让升”条[15]87-88。尊者不降级就洗,即在堂上行盥礼。故黄氏云:“如《公食礼》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诸礼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是庭虽设洗而不用,在堂上另用盘承弃水,此即黄氏所言“故既设洗,又设盥”。是则黄氏所谓“洗礼繁,盥礼简,丧事略”,是尊者设洗用盘,常礼用洗,丧事无洗用盘。“丧事略”即较盥礼设洗,降一等用盘。
由上所论,可知姚名达完全不明白礼制上“录”“略”的真实意义,就草率地滥用其义。因此其依据《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对《别录》《七略》书名中之“录”“略”做出的新解也就绝不可信。
姚名达《目录学》第一章第二节《录是什么》,据《殷虚书契类纂》“彔”字,认为:“这就是录字的前身。牠的本义只是表示用刀锥在木版或铜片上刻字的形式。古代初有文字,没有纸笔,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叫做史;他这种刻字的动作,或叫做‘书’,或叫做‘录’。这本是我的臆见,不料古人已有先得我心的。”接下来,姚氏引用了俞樾、章太炎师徒的著作。俞樾《儿笘录》卷四“录”条:“录者,彔之或体也。《说文·彔部》:‘彔,刻木彔彔也。’刻木必用刀,故或从金。隐十年《公羊》‘《春秋》录内而略外’,盖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谓之录,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⑥章太炎《小学答问》:“凡言记录者,藉为刻木彔彔之录,古者书契本刻木为之也。”⑦姚氏据此论曰:“所以录字本来是一个动字,例如:《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礼记·檀弓》:‘爱之斯录之矣。’”[16]可见姚氏在写作《目录学》时尚无“录”详“略”简之说,其于《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之“录”之义,仍本旧说释为“记录”。鉴于姚氏《目录学》出版于1933年,《中国目录学史》则写作始于1935年[5]自序1,出版于1937年,故可以推测,姚氏在写作《中国目录学史》时,翻阅旧著《目录学》,目及曲园所引《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忽然灵光一闪,遂创为新论如彼。设使姚氏著书之时,倘能深入考察“录”“略”之礼义,自可明白决断。惜于其考察工作仅限于抄录《公羊传》之整段原文,再无寸进,而后之学者又慑于其大名,以止步表尊仰,遂使“录”“略”之义,暗而不明,悲夫!
行文至此,本当告终。然何休对于隐公十年《公羊传》之解释,仍须一辨。
三、《公羊传》“甚恶”考
《春秋经》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何休注:“明取邑为小恶,一月而再取,小恶中甚者耳,故书也。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小恶不讳者,罪薄耻轻。”[9]41何休乃是将传文严格理解为“内大恶讳”和“内小恶书”两个等级,然后推论,既然《春秋经》对于“一月而再取”之恶“书”了,那么就必然属于小恶而非大恶。因此得出此“一月而再取”乃是“小恶中甚者”。何氏并由此再进一步推论,“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这就等于说,无论君父做了何等伤天害理的大恶之甚者,臣子都必须曲为之讳。此绝非《春秋》之大义。
详阅《春秋》,获地而讳之者,如《春秋经》隐公二年:“(夏五月,)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9]24-25《春秋经》昭公四年:“九月,取鄫。”《公羊传》:“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9]276此皆一次性之灭国,故书以取邑讳之,可见此为大恶。《春秋经》昭公三十二年:“(正月,)取阚。”《公羊传》:“阚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何休注:“与取滥为亟。”徐彦疏:“取亦作受字者。二年之间,比取两邑,故以为亟而讳之矣。”[9]309此处“以为亟而讳之”,则确系大恶无疑。“二年之间,比取两邑”已为大恶,“一月而再取”焉得为小恶!
《春秋经》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庚寅,我入邴。”《公羊传》:“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难也。其日何?难也。”何休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礼也。当沐浴絜齐以致其敬,故谓之汤沐邑也。归邴书者,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录使者,重尊汤沐邑也。入者,非已至之文,难辞也。此鲁受邴,与郑同罪当诛,故书入,欲为鲁见重难辞。”[9]39《春秋经》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公羊传》:“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易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9]46此二邑皆未使用武力,但是《春秋》仍然讳之,《公羊》且以为郑伯鲁公皆“背叛当诛”,显然是为大恶。
由此五事观之,皆获土而讳者。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其罪无疑重于“入极”“取鄫”“取阚”,更重于“入邴”“假许”。既然此五事为大恶无可置疑,那么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就绝不可能归类于小恶,“小恶中甚者”也不行。何休所谓“明取邑为小恶”,断然与此五事显相抵牾,绝不可从。细读传文,言“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便是在问,《春秋》于内大恶当讳,此处为何不讳?则《公羊传》将此“一月而再取”视为大恶,明白无疑。否则当问“内小恶书,此其言甚之何?”若然,《春秋》于恶之等级,应分为三等,“内小恶书”与“内大恶讳”二等之上,还当有“内甚恶繁”一等。亦即,倘若鲁国内为恶太甚,超出于人性与正义所能容受之极限,是则已非夫子所得为之曲讳。于是夫子势不得不超出《春秋》成例,对于此“甚之”者,不唯不讳而直书,抑且在书之之例上,踵事增繁,以见其已超出大恶。就此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之例而言,则是突破“取邑不日”之成例,在“取邑”之例上加上取邑之日,以示其“甚之”而不得讳。《春秋经》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何休注:“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春秋》公子贯于先君,唯世子与母弟以今君录亲亲也。今舍国体直称君,知以亲亲责之。”[9]127《左传》孔颖达疏引《公羊传》之后云:“言父子相残,恶之甚者。”[7]204此为《春秋》甚恶之例。《春秋繁露·玉英》:“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⑧可见董生明确以“甚恶”高于“大恶”。《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成帝赵皇后等残杀成帝嗣子,成帝崩,哀帝即位,司隶解光奏请惩治。但是哀帝即位已大赦天下。解光奏言:“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不当所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鲁严公夫人杀世子,齐桓召而诛焉,《春秋》予之。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帏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谊示四方也。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18]意谓赵氏所为乃悖逆已极,即便天子也不得赦免,并举元帝故事及《春秋》经义为据。此悖逆已极者既不得赦,自然更不得讳⑨,正可见《春秋》于甚恶不讳之义。
《春秋经》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公羊传》:“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何休注:“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下书归是也。礼,男不亲求,女不亲许。鲁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来请己,与禽兽无异,故早鄫子使乎季姬,以绝贱之也。月者,甚恶内也。”徐彦疏:“正以遇例时,即隐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庄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之属是也。今此月者,甚恶内也。”[9]137此即内甚恶之辞。《春秋经》僖公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何休注:“日者,杞属修礼。朝鲁虽无礼,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当乃入之,故录责之。”[9]151杞来朝鲁,乃是修礼。纵使礼数不备,入之太甚,故书日以“录责”之。此“录”字乃对“讳”而言,恰见《春秋》之不“讳”。不讳方可“责”之,斯正见夫子之不得讳。苏舆注《春秋繁露·俞序》曰:“略人容天下,所谓恕也。详己而先治其国,自厚之谓也。己不自治,则无以治人,何容之有?”[17]正是其义。
《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9]明确主张对于残暴已甚的君主,哪怕贵为天子,也必须坚决诛杀。检《荀子·议兵》:“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20]此“诛独夫”即孟子之“诛一夫”,可见孟子之义有本于《尚书》所载武王伐纣。《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1]孟子“诛一夫”之义上承《尚书》,下本《春秋》,乃早期儒学之真精神,惜乎为何休所蔽,今乃特表而出之。
综上所述,《七略》之“略”的确切意义应为“边界”,引申为“部类”。章太炎的解释是对的,姚名达释为“简单”是误解了《公羊传》“录内而略外”的意义。《春秋》“录内而略外”,是指对内如其所是地记录其礼制等级,对外则在礼制上降一等。何休基于此认为《春秋》于内恶只有大小两个等级,由此取消“甚恶”之等,是对《春秋》之义的篡改。
注释
①孙显斌:《〈七略〉与〈别录〉释名》,《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4期,第123—125页。按: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仅有“《别录》详而《七略》简”一语,是对于两书状况的客观描述,并未将此与《别录》《七略》书名之“录”“略”相联系,不能认为吕氏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了姚说。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也言及“《别录》详而《七略》略”,同样也没有以之与《别录》《七略》书名之“录”“略”相联系。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27页。②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此后孙振田在没有提及曹说的情形下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说:“概言之,合以‘略’有‘要’‘梗概’之含义,及针对《七略》之产生、渊源、命名、注释等所做之分析,《七略》称名之‘略’不当以表分类或详简之‘简’解之,而当以‘要’(或‘梗概’)义解之。”孙振田:《〈七略〉称名新释》,《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年第1期,第108—112页。③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章太炎全集》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按此序修改后收入《訄书》重订本,为《征七略》第五十七。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页。《检论》仍之。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8页。④《春秋繁露·俞序》:“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苏舆注:“略人容天下,所谓恕也。详己而先治其国,自厚之谓也。己不自治,则无以治人,何容之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1页。此乃谓《春秋》欲正天下,先自鲁始。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四《释九旨例》下《贬绝例》曰:“《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诸侯大夫之不可正,则托义于其贤者以正之。”刘逢禄:《刘礼部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是其义。此“详”之义,《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列传》附子恺传“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李贤注:“《尚书》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详刑。’郑玄注:‘详,审察之也。’”范晔:《后汉书》第5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9、1310页。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引《俞序》此文以释“《春秋》录内而略外”。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又或以为:“《春秋》为鲁史,故详于鲁。记别国事则较鲁为略。苏注以略人为恕,未洽。”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上册(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皆非。参下引《春秋经》僖公二十七年“入杞”。⑤《公羊传》哀公五年“丧数略”,何休注:“略犹杀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第344页。⑥今核对俞书,“刻木必用刀”作“刻本必用刀”,意谓刻木本来必须用刀,义本可通,姚氏误以“本”为“木”之讹而径改。俞樾:《儿笘录》,《春在堂全书》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93页。⑦今核对章书,浙江图书馆校刊余杭章氏丛书本《小学答问》作“耤为刻木彔彔之彔”。《章太炎全集》作“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姚名达当是将“耤”改为通行字。章太炎:《小学答问》,《章氏丛书》第5册,民国六年至八年浙江图书馆校刊本,第44页a。章太炎:《小学答问》,《章太炎全集》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⑧《春秋繁露义证》钟哲标点原以“讥”字属下句,断句于“是为甚恶”,今改为“是为甚恶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3页。⑨《春秋经》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杜预注:“不言齐人杀,讳之。书地者,明在外薨。”孔颖达疏:“实齐人杀之。讳,故不言杀也。夫人之薨,例不书地。书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齐人乃以其丧归耳。”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第197页。此处所讳者乃是齐杀鲁夫人,至于哀姜之恶则未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