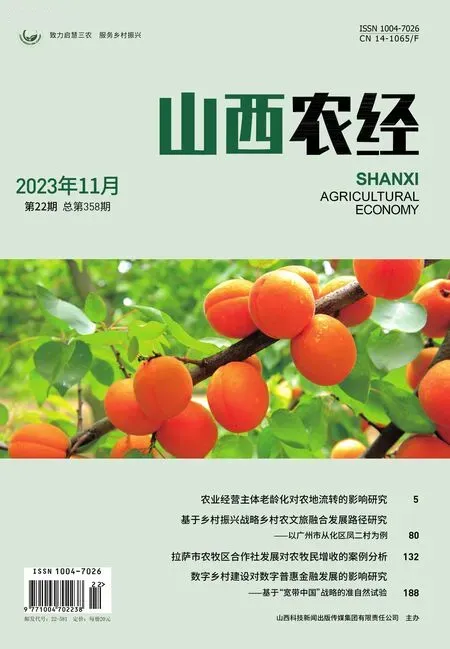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试验
□逯鹏飞
(吉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当今,我国正处在乡村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交汇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颁布以来,全国各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我国初步建成了适用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广大乡村也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基本实现宽带进乡入村,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5%。联合国在2005 年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我国在普惠金融的推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日益成熟,但是我国在金融和数字乡村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体现为普惠金融和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精细程度不够,究其原因是受农户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乡村建设与“三农”问题、数字乡村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数字乡村的内生发展模式等方面[1-4]。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传统金融的对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化发展影响方面[5-6]。
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研究了数字乡村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为我国今后乡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双重差分法等前沿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1 数字乡村建设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的模型设定
1.1 模型设定
本研究以我国285 个地级城市2011—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准,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一项准自然试验,虚拟变量的设置依据是将“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赋值为1,而将非试点城市赋值为0;时间虚拟变量的设置依据是将试点设立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参照刘传明和马青山(2020)[7]的相关研究,将多期DID 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Fia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市i在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DIDi,t为数字乡村政策的虚拟变量;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消费水平、人口规模城市、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ηt为时间固定效应,u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1为研究的核心固定参数,代表数字兴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净效应。
1.2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1.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 可以看出,各变量的观测值都为2 565 个,除了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标准差较大外,其他的各个指标的标准差都比较小,各地差异不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2 数字基础设施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2.1 平行趋势检验
如图1 所示,通过比较数字乡村政策实施前后普惠金融的变动趋势发现,在数字乡村政策实施之前,试验组和控制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之后,试验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越来越大,这说明DID模型通过平行趋势检验,适合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2 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3 可以看出,无论将4 个控制变量加入与否,在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基础上,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政策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着显著促进效果。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一),数字乡村建设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385,且在5%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模型二),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890,且在1%水平上显著。

表3 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
2.3 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
在应用DID 模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先处理VS 后处理”的情况,“先处理”的个体尽管已经存在处理效应,但在分析过程中仍然可能会被当作处理组。若“先处理VS 后处理”所产生的加权平均值的权重过大,会使双向固定回归估计产生偏误,影响TWFE估计量的回归结果;反之,则生成的偏误相对较小,对最终的估计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Andrew Goodman-Bacon(2021)[8]提出的诊断偏误方法有负权重诊断、培根分解以及同质性处理效应的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DID 进行实证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影响效应,涉及到多期多组数据。为防止结果出现偏误,此处借鉴学者提出的方法,以Bacon 分解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方法。Bacon分解将双向固定效应的DID 估计量分解为各部分的加权平均值,具体见表4、表5。本研究涉及到三类数据组,即未处理组、早期处理组和后期处理组,根据前文分析,一般认为未处理过的对照组为好的对照组。

表4 DI D估计量

表5 Bacon 分解结果
表5 中,数字乡村建设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中有90.5%的影响来自于处理组和未处理的对照组,有4.0%的影响来自早期处理组与后期处理的对照组,有5.5%的影响来自后期处理组与早期处理的对照组。可见大部分影响都是未处理组作为对照组来进行反事实检验得到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本研究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为正,进一步进行Bacon 权重分解。
图2 中,横轴表示权重,纵轴表示单个水平DID估计量,水平横线代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真实估计量。可以看出在水平横线之上的估计量所占权重比较大,下方的三角点效应为负,权重基本为0,对于估计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图2 培根分解权重
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随机抽取某一年作为城市i被设立为试点的时间,将该过程重复1 000 次,进行安慰剂稳健性检验。结果见图3,随机分配的估计值的P值在0附近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大多数系数对应的P值均位于显著性水平0.1 之上,也就是说伪政策系数在10%的水平上都不显著,进一步证明本研究回归结论稳健可靠。

图3 安慰剂检验
4 异质性分析
近年来,东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人才培育和普惠金融机构等方面有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会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异质性。因此,本研究按照“东中部、西部”划分样本城市[9]。
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时间起始于1986 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东中部地区有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西部地区有9 个省(自治区),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东中部地区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但西部地区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升了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即促进了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西部地区的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会阻碍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缺乏良好的金融发展基础有关。

表6 各区域基准回归分析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促进效果,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精细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改善以往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粗犷化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对于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普惠金融正在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鉴于此,文章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一是规划制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线图。我国目前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应尽早完善现有制度,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方式和路径,并尽早出台相关细则,做好规划和及时应对措施。
二是推进普惠金融精细化转型发展。尽早解决以往粗犷化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各种弊病,使得普惠金融体系早日成熟。
三是提升数字乡村建设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水平。从内部、外部两方面同时保证普惠金融和数字乡村建设的良性发展,保证两者在同步发展中共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