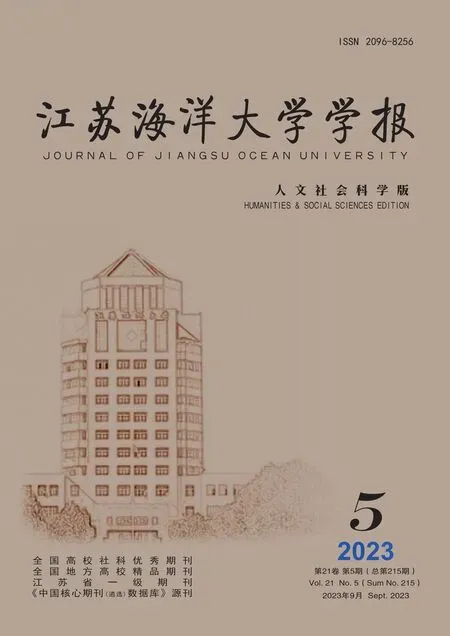学问何以用:纪昀试律诗学新论*
谢冰青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学问化是清代诗学的重要议题,而试律与学问关系匪浅,清人余集即以学人之诗目试律,曰:“顾有骚人之作,有学人之作。……学人之为诗则不然。或献之朝廷,或成于明试。”[1]学界已经关注到了学人之诗的性质(1)王兵与蒋寅均引清人之说,提出试律当属学人之诗。参见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294页。蒋寅:《清代诗学史:学问与性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59页。,已有学者将之列入清诗学问化的宏观背景之中,认为试律诗博采经史子集的诗题是推动清诗学问化的重要因素(2)参见宁夏江、魏中林:《论清诗以学胜》,《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也有学者将之纳入思想史视野,探讨了试律诗学问化特征与特定学术思潮之间的关联(3)参见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r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546-558.梁梅:《清代试律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13-131页。。这些研究对于解答“清诗为何学问化”与“试律为何学问化”的问题都大有裨益。由此也引申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试律引入学问是否有其自身的诗学意义?第二,试律在书写学问时又有何特殊的书写策略?第三,除了知识性与思想性的内容之外,作为学人之诗的试律对于古近体诗是否还有其他影响?
被清人视为试律典范大家的纪昀或可为以上问题作出解答。纪昀在清代试律诗学理论建构上有突出贡献,而其古近体诗学与试律诗学均颇重学问。学界对纪昀试律诗学的研究,多倾向由其试律诗学本身出发,论其试律诗学对于试律诗学史的意义(4)相应研究有:邱怡瑄《纪昀的试律诗学》,台湾政治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徐美秋《纪昀评点诗歌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彭国忠《〈唐人试律说〉:纪昀的试律诗学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蒋寅《纪晓岚试律诗学论述》,《阅江学刊》,2016年第2期;梁梅《清代试律诗学研究》,第144-203页。其中邱怡瑄论文对纪昀古近体诗学也有论述。。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之上,以纪昀的古近体诗学体系为立足点,以他的试律评点著作《唐人试律说》《庚辰集》与试律别集《我法集》为主要研究对象(5)纪昀试律诗著作尚有《馆课存稿》,惜其无纪昀个人评点,姑暂搁置不论。邱怡瑄对纪昀试律诗学著作版本考证甚详,参见《纪昀的试律诗学》。,尝试解答学问在他的试律诗学中的作用,厘清其试律对于学问的书写策略,以求进一步探讨试律学人之诗的性质对古近体诗的潜在影响。
一、由诗之本原论试律之体卑
纪昀对于试律有一个论断,即“诗至试律而体卑。虽极工论者弗尚也。然同源别派,其法实与诗通”[2]271。“体卑”不仅是对试律文体尊卑的定位,也可能包含了对于试律艺术审美的评价,因为他在诗歌评点著作中亦时以“卑”论诗歌审美价值,两者之间或有共通。而“同源别派”则折射了其对试律与古近体诗关系的认知。因此,要理解纪昀的试律诗学,有必要先厘清两个问题:第一,既然试律与诗同源,那么在纪昀的诗学理念中诗歌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从诗歌评点角度而言,“体卑”的含义应当如何理解?
从同源而论,纪昀标举“发乎情,止乎礼义”为诗歌的本质,他将诗歌视作创作主体心灵的产物,反映了其对于创作主体的重视。《挹绿轩诗集序》云:“《书》称‘诗言志’,《论语》称‘思无邪’,子夏《诗序》兼括其旨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之本旨尽是矣。”[3]365带有鲜明的儒家诗教论的色彩。不过,纪昀在实际论述中采取了情志并举的态度,亦以“志”“性情”等论诗。《冰瓯草序》云:“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怀。举日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以宕其性灵。是诗本乎性情者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之至;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3]352可见,他颇为看重诗歌情感的真挚,是以其特为强调至情至性是“本天而动”,在高扬诗歌“鸣国家之盛”功用的同时,也对偏向个人情感的“抒愤写怀”的抒情呈现出了一定包容。
不过,“发乎情,止乎礼义”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诗歌应该“写什么”,还涉及到诗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在《云林诗钞序》中,纪昀对诗歌的表现内容与艺术审美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诗歌不仅要具备情感内容的雅正,还要具备文学的形式之美(6)张健认为“纪昀的诗学带有非常突出的折中特性”。杨子彦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体现了纪昀注重诗歌抒发性情的功能,《云林诗钞》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了对于审美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并重。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4页。杨子彦:《纪昀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0-78页、第88页。。他认为后世出现了对于“发乎情,止乎礼义”各执一义的谬误,是以皆误入歧途,曰:“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3]361-362结合纪昀对于苏轼《芙蓉城》的评点更可见此意,苏诗前小序声明此作有“止乎礼义”之意:“世传王迥子高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乃作此诗,极其情而归之正,亦变风止乎礼义之意也。”[4]178诗歌铺叙渲染了与仙人同游的种种瑰丽奇幻的景致,结尾却忽然转折以收束:“春风花开秋叶零,世间罗绮纷膻腥。此身流浪随沧溟,偶然相值两浮萍。愿君收视观三庭,勿与嘉谷生蝗螟。从渠一念三千龄,下作人间尹与邢。”[4]178由刘辰翁评点可见其旨:“谓彼自堕落,勿效尤也。”[5]807纪昀对于苏轼的处理颇为赞赏:“《序》所谓极其情而归于正,若无此一结,便是传奇体矣。尤妙于庄论而非腐语,所以为诗人之笔。”[4]178称许如此作结既具备思想的醇雅,也符合文体法度的优美。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可资借鉴以为阐释:“‘发’而能‘止’,‘之’而能‘持’,则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tte gehen)’矣。”[6]58
可见,在纪昀的诗学中,诗歌不仅关乎抒发什么样的情志,更是在于如何抒发情志。在这一过程中,学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情志需要学问陶钧方能转化为诗歌,《清艳堂诗序》云:“帝妫有言曰:‘诗言志,歌永言。’扬雄有言曰:‘言,心声也;文,心画也。’故善为诗者,其思浚发于性灵,其意陶镕于学问。凡物色之感于外,与喜怒哀乐之动于中者,两相薄而发为歌咏。”[3]364他所说的“性灵”较为偏向强调个人天生的内在特质,诗歌创作过程的起点是先天的性灵被激发,再由后天的学问加以组织安排。另一方面,诗歌是个人情志的直接产物,而学问则可在诗歌中间接显现,从而呈现出艺术审美的差异。《郭茗山诗集序》云:“盖志者,性情之所之,亦即人品、学问之所见。”[3]356此论是针对赵执信与王士禛的诗学观点而言,赵执信为批评王士禛诗学,力倡“诗中有人”,强调“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7]7。纪昀对二人的争执报以折衷的态度,主张他们的诗学理念其实都有对于创作主体重视的一面:“阮亭先生论诗绝句有曰:‘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岂非柳州犹役役功名,苏州则扫地焚香,泊然高寄乎?饴山老人持诗中有人之说亦是意焉耳。”[3]356王士禛认为韦柳二人诗风相近,韦又胜于柳,纪昀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二者心境不同。可见学问人品会造成心境差异,所以即使诗歌表达了相同的旨趣,也会呈现出微妙的审美品格区分(7)张健指出纪昀有“人品即诗品”的观点,而诗品既包含道德之品格,也包含审美之品格。参见《清代诗学研究》,第596页。,这正是创作主体个人气质在诗歌中的体现。
简言之,纪昀认为诗是创作主体情志的表达,尽管情志应当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但是他也认可无关政教的个人情志书写的正当性。纪昀还强调诗歌的表达方式需遵循一定的法度,使之具有形式之美。学问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陶钧情志的作用,并且也是创作主体在诗歌中的间接呈现,从而造就诗歌独特的艺术美质。
在厘清了纪昀诗学中的诗歌本质之后,则可论试帖何以体卑。首先,“体卑”包含着对文体地位尊卑的判断,如《四库总目提要》(8)虽然《总目》撰写者众多,但“集部提要与纪昀的见解是密切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个人的文学观和论诗文的折衷立场”。参见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学术界》,2015年第7期,第189页。有言:“惟歌词体卑而艺贱,则从马氏之例,别立《词曲》一门焉。”[8]4550试律之所以被认为地位卑下,其一或是因为它缺乏主体情志的自然抒发,这也是试律与古近体诗最明显的差异。作为功令文体,考场试律之作虽多为颂扬之词,有关政教,但囿于文体形式,多缺乏写作主体个人情志的呈现,清人也因试律缺乏真情实感,视之为俳优之词,戈涛乾隆二十二年所作《杜律启蒙叙》云:“今时场屋所用之诗,不过如唐试帖,犹时文之闱墨耳。韩子所目为俳优者之词。”[9]1013纪昀也指出“坊刻试帖,往往互易姓名”[10]15。
一种文体地位的高低还往往与其审美特质密切相关(9)参见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 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体卑”也涉及到对艺术审美的评判。纪昀曾批评许浑诗“体卑”:“许浑诗体卑而味短,虚谷排之最公。”[11]82一则因其机械化与模式化,纪昀对许浑“体卑”的评价出自《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方回指许浑登临之作则多为套词:“如许浑《登凌敲台》‘湘潭云净莫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不过砌叠形模;而晚唐家以为句法,今不敢取。”[11]82纪昀对方回的评价深以为然:“论许浑二句最是。”[12]40纪昀批评许浑诗亦指摘其“套熟”:“浑诗病在滑调浮声,如马首之络,处处可用。不病于哑,又病于填用熟调,自落窠臼。”[13]51纪昀谓试律常有“甜熟”[10]67之病。袁枚曾指试律有落套之病,云:“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14]13二则因许浑诗虽工于修辞却艺术格调不高。纪昀指其“格意凡近”:“‘体格太卑,对偶太切。’八字评用晦切当。……用晦之病在格意凡近,不尽在句法也。”[12]510他也曾以“体卑”评李商隐的《泪》:“卑俗之至,命题尤俗。问:此诗亦有风致,那得云俗?曰:此所谓倚门之妆,风致处正其俗处也。”[15]93“体卑”正因其“俗”。纪昀明确意识到试律的艺术审美评判标准与古近体诗不同,一些在古近体诗中格调不高的表现手法却适用于试律,如评唐人马戴《府试开观元皇帝东封图》云:“‘粉痕’二句以诗法论之,点缀纤巧,所谓下劣诗魔也。在试律则不失为好句。文各有体,言各有当,在善读者别择之。”[2]279宋人葛立方论其时科举所用省题诗云:“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16]43此语也适用于论清代试律。纪昀也指出,试律写作存在“刻意敛才就法,反而浅俗,不为佳作”[12]750的现象。
由此可见,试律体卑既是因为主题内容的书写缺乏创作主体的真挚情志,也是因为其艺术审美的缺陷,易有程式化与艺术格调卑下之病。
二、情志的补足与形式的陶钧:学问对试律体卑的双重补正
从“本原”论试律之体卑,可见在纪昀的诗学理论中,试律与古近体诗在主题内容与艺术审美上皆有龃龉。对此,纪昀自言以“意格运题”,曰:“试帖多尚典赡。余始变为意格运题,馆阁诸公每呼此体为‘纪家诗’。”[17]83意格强调的是写作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意格是以意统其格,在评点李商隐诗时,纪昀也曾拈出“意格”这一概念,评《楚宫》云:“意格与《陈后宫》一首相似,彼不说破,此说破耳。”[18]144二作的主题皆是讽刺历史上帝王的无状之举,在表现手法上都是先铺叙昔日宫苑繁盛,结处忽作一转折点明主旨(10)《李商隐诗歌集解》对二作论析甚详,参见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第764页、第11-12页。。
同样,纪昀也颇为看重学问对于试律的作用。他在《庚辰集序》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学问对于试律的重要性:“虽试帖小技,亦不可枵腹以成文。”[10]4《庚辰集》注释颇为详尽,以致纪昀自言:“故此书之隘与冗,微人知之,吾固知之。”[10]4但冗长琐碎的注释实则包含着使初学者“以知诗家一字一句必有依据”[10]3-4的期许。从狭义而言,学问主要指向各类知识性内容,如《怡轩老人传》曰:“顾昀于文章,喜词赋;于学问,喜汉、唐训诂,而泛滥于史传百家之言。”[3]459而从广义而言,学问还指向对于前人文章的学习体悟。冯武认为:“盖‘江西诗’可以枵腹而为之,西昆则必要多读经、史、《骚》、《选》,此非可以日月计也。”[13]6纪昀对此则批驳:“西昆须胸有卷轴,江西亦须胎息古人,皆不可以枵腹为也。如以粗野为江西,以剽窃为西昆,则皆可以枵腹为之。”[13]6冯武以经史与《骚》《选》并举以论作诗之道,不仅强调要掌握其中知识性的内容,更是强调对于行文的研习。纪昀所言“胎息古人”也可见此意,他主张掌握前人行文的思维模式以为我所用,是以他特别提倡“我法”这一概念(11)杨子彦对纪昀“我用我法”的创作理念有详尽论述,可资参考。参见《纪昀文学思想研究》,第110-127页。。在评点苏轼《次韵子由岐下诗》时,他特别批判了“辗转相摹,渐成窠臼”[4]28的风气,提倡“虽非佳作,要是我用我法”[4]28-29。其标举编选《庚辰集》是采用了“我用我法”[13]3的态度,他将晚年所作的试律别集命名为《我法集》,足见其意。
学问与意格运题关系密切,学问既主导了对题意的理解,决定了试律的主题内容,也影响了试律的艺术表现。从题意解析而言,对于题意的理解往往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从这一层面而言,学问首先可以弥补主体性缺失的遗憾。虽然当时的试律很难表现个人的情志,但如前所言,个人的学问可以在诗中间接显现,因此,学问可以被视作创作主体“主观的投入”(12)此处借鉴了龚鹏程的观点: “所谓‘文体的规范普遍而独立自存’,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投入。因为者就像索绪尔所说‘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言是社会习惯所形成之语言集体契约,言语则是人在语言中经由自己的选择和处理所表现的个人用法。所以语言和言语的辩证关系,是必然存在的。”参见《论李商隐的樱桃诗》,《书目季刊》,1998年22卷第1期,第45页。。试律诗题多是寻章摘句而来,对于一些诗题的知识性阐释使得学问也可以成为诗歌所直接表现的主题。在纪昀的创作中,这一倾向颇为明显。《我法集》有《赋得镜花水月得花字》,题源自《沧浪诗话》论诗之妙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19]26纪昀以为严羽的诗论是针对宋季“四灵一派刻画琐碎,江湖一派鄙俚相疏”[20]卷二的状况,但后人奉为圭臬,未免忽视诗教,又生其他弊端,故其试律专为驳正世人对严羽诗论的误解:
诗以禅为喻,沧浪自一家。水中明指月,镜里试拈花。
圆魄千江印,欹枝两面斜。蟾疑浮浪縠,蝶讶隔窗纱。
对影虽知幻,摹形反虑差。其间原有象,此会本无遮。
六义轻东鲁,三乘转法华。别传归教外,珍重辨瑜瑕。[20]卷二
此作意在说明严羽诗论当被视为教外别传,后来者还当谨慎辨析。纪昀自言此处用“压题格”,压题是源自八股文的批评术语,刘熙载《艺概》卷六《经艺概》云:“衬法有捧题,有压题。捧题,以低浅;压题,以高深。”“衬托不是闲言语,乃相形相勘紧要之文,非帮助题旨,即反对题旨,所谓客笔主意也”。[21]730-731两相结合可见,“压题”是一种针对题旨的阐释思维,即“打压主题”[21]731,往往是要对题旨进行一定辨析。纪昀在试律评点与创作中曾多次提及对“压题格”的运用,如《庚辰集》评赵青藜《学然后知不足》云:“起四句压题得法。”[10]60《我法集》作《赋得西园翰墨林》,称“此压题之格”[22]。作《赋得斧凿其言》“以压题法结之”[22]。
由纪昀对“压题格”的频繁使用还可见,学问在辨析题意时不仅提供知识背景,更形成一种思辨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面对一些琐碎纤巧、格调不高的试律诗题时就成为写作的突破口,体现了学问的“陶钧”之用。《我法集》有《赋得池水夜观深》诗,此题源自赵师秀《灵隐寺诗》,赵师秀千锤方得此句,但纪昀并不欣赏这种锤炼之功,提出此为“隔日疟也,于诗家为魔道”[20]卷二。对于此种诗题,他也承认不得不“琐屑刻画以还之”[20]卷二,但认为具体刻画要遵循一定的逻辑:“火日外影,金水内影,晴昼则水面浮光,与外面日光互耀,光在水上自不能下视;夜则四面皆黑,内影自明,昏暗中视若深者以此。又星月极高,其倒影入水亦必极深,上面相距之差数,即下面相距之差数,星月下视若深者又以此。”[20]卷二虽就一“深”字刻画,但也要阐明池水为何深,夜影为何深,钟楼观池水又为何深数端,这种对前人诗句细致把握也正是体悟学习的过程。
而对于试律程式化的艺术缺憾,无论是作为知识内容,还是作为文章体悟,学问均可对此进行一定补正。从知识内容而言,纪昀认可试律写作有其诗法套路,但是其强调试律的诗法套路也要“关合本题”,而精准理解题意,在写作之时活用典故以阐明观点本身就是对知识性学问的考验。他评价唐人韩濬《清明日赐百僚新火》:“结寓祈请,唐试律类然,亦一时风气如是,今则不必。又如颂圣作结,固属对扬之体,然亦须关合本题。若以通套肤词,后半篇支缀三四韵,非诗法也。”[2]277韩诗最末一联云:“应怜萤聚者,瞻望及东邻。”[2]277此句用典自喻之时也考虑了题意,发祈请之意亦妥帖契合,纪昀所引朱琰评论可见此意:“末联‘萤聚’者,指聚萤之人。此诗无萤可聚,则瞻望‘东邻’,希其凿壁分光也。若作‘萤聚夜’,清明之夜,安得聚萤?”[2]277从文章体悟而论,纪昀在承认模式的同时,亦强调“拟议之中自生变化”(13)梁梅对纪昀试律诗学中的拟议与变化有详细论述,参见《清代试律诗学》之《纪昀的试律诗学理论及影响》,第145-157页。,其以为:“善为诗者,当先取古人佳处,涵泳之,使意境活泼,如在目前,拟议之中自生变化。”[2]279模拟最好能够达到“夺胎”的效果,以求“得悟门又变化之”[22],即使对不同的写作主题亦可应对自如。纪昀也在写作实践中遵循了这一准则,其有《赋得以风鸣冬》,虽为咏物候之题,而写作之法却袭李商隐咏史《筹笔驿》而来,自言:“此诗又是一格,起四句先完题面,次四句作一大开,次四句作一大合,末四句推出题后作结。纯以气焰挟题而走,《庚辰集》中香树先生《春从何处来》诗即是此格,均夺胎于玉溪《筹笔驿》诗。”[22]
相应的是,纪昀的试律评点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博学取向,这在其亲自注释的《庚辰集》中最为明显。他的注释不仅是考据学的学理阐释,更是一种诗学解说。以《庚辰集》卷四对沈启震《三月桃花水》的注释为例,一方面,纪昀对诗题出处详加辨析,以助后学理解题意。注释除了标明诗题源自杜甫《春水》诗,还对“桃花水”作出一番考释:“《汉书·沟洫志》:‘春来,桃花水盛。’注:师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判,众流猥集,故谓之“桃花水”耳。’”(14)纪昀:《庚辰集》卷五,刘金柱,杨钧主编:《纪晓岚全集》第4卷,第381-382页。按:查《汉书》作“来春桃华水盛”。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689页。言明何以春水有“桃花水”之谓。另一方面,纪昀对诗中典故详加阐释也有助于后学厘清诗中意脉,从而理解前人诗句。沈诗首四句为“水面縠纹生,桃花照眼明。乱红吹不断,新绿涨初平”[10]382,其中“縠纹生”三字,纪昀特别引《宋景文笔记》论“生”字当何解:“晏丞相尝问曾明仲曰:‘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其说好奇而无理,究以作‘生灭’之生为是。”[10]382此处因题中“桃花水”描述的是春日桃花开放、川流溪水聚集的情态,“縠文生”之生作“生灭”解,则表现了流水的动态,方切合题意,以下“新绿涨初平”亦顺承其意,自然通畅,全诗也由此展开。
由以上可见,学问可以从主题内容与艺术表现两方面补足试律“体卑”之病。纪昀基于试律因题命意的特性,以学问丰富表现内容,补足创作主体缺失之憾。以学问积累所蕴含的思辨性思维模式疗愈试律的琐碎刻画之病,以知识内容与文章体悟双管齐下,从而打破程式化的窠臼。他的评点还呈现出一定的博学取向。
三、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表达:学问入诗与诗歌艺术审美的平衡策略
诚然学问入试律对于“提升试律体格”[22]确有裨益。但是在诗歌批评史上,学问入诗的争议也由来已久,当中折射了言志抒情与学问说理的冲突。严羽的观点影响深远,其以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10]26,“非关书”,意在鄙弃直接在诗中堆垛学问,“非关理”,旨在说明诗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质,是针对宋人以理语入诗的弊病而发(15)此处借鉴了郭绍虞先生的相关论述,参见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3-47页。。
纪昀认为严羽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论《沧浪诗话》云:“讲学家肤浅粗疏,江湖派雕锼细碎,因标举盛唐之兴象以救弊补偏。”[23]713“讲学家”云云,说明纪昀也意识到过度在诗中堆垛学问、说理议论会对诗歌艺术审美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他的试律诗学固然推崇学问,却也在竭力调和可能产生的弊端。先就“非关书”而言,对于试律诗来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辨体”,即根据题意以选择“相应的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24]247。以堆垛学问而言,对于有超妙自然之意的诗题,他提出不必一味拘泥故实,其评锺辂《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云:“‘盈谷’,似用‘黄帝张乐,在谷满谷’意,‘入云’似用‘秦青之歌,响遏行云’意,皆乐事也,此亦未必不然。然作诗、说诗,俱不必如此沾滞。”[2]290题本自仙人王子晋故事,颇有出尘之意,锺诗云:“初闻盈谷远,渐听入云清。”[2]290若强以“盈谷”“入云”比附典故,反不能表现出仙人音乐的缥缈之态。而对于说理议论之题,纪昀就颇为赞许言有根柢之作。如《庚辰集》有卫肃《如石投水》,题出自李康《运命论》,言张良“及其遭汉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10]254。卫作既简练地抉历史原典,云“千秋明主遇,一卷老人书”[10]254,又巧用《诗经》与《三国志》之典,以阐发得遇明主之幸:“诗咏他山石,欢同得水鱼。”[10]254纪昀评点云:“妙无一字无来历。”[10]254
再就“非关理”而言,严羽的理论在清代也引发了回响,其中,沈德潜的“理语”“理趣”之论颇有代表性。严羽所论之“理”或是针对宋代理学而言(16)钱锺书:“窃疑沧浪‘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谈艺录》(补订重排版)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44页。,但清人诗论中的“理”又非仅就理学而言,而是可以被泛化理解为知识性的内容与思辨性的思维。据钱锺书先生考证,沈德潜先是在乾隆三年(1738)提出“禅理禅趣”的概念,乾隆九年(1744)其在《说诗晬语》中又以“禅理禅语”与“理语理趣”并举(17)参见钱锺书:《谈艺录》,下册,第645-646页。。可见此时“禅”“理”本身的具体学说内涵已经不是沈德潜诗论所关注的重点,他更为关注的是各类思想所蕴藏的理性思维与诗歌的感性表达之间的关系。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作的《清诗别裁》之《凡例》中,他阐明了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25]2“所谓有理趣者,就是使理感情化、形象化,使其具有美感。而下理语者,就是将道理直接说出来。”[26]681沈德潜认为诗歌需要基于一定的内在理路进行组织排布,但又不是以诗为道理的附庸,以致丧失诗之艺术美质。自后清人也不乏以“理语”“理趣”论诗者,足见沈氏理论的余波。
纪昀的试律诗学也承袭了沈德潜的学说,他又更进一步注意到了试律因题命意的特性与说理议论的关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书的《唐人试律说》中,其论卢肇试律《澄心如水》云:“诗本性情,可以含理趣,而不能作理语。故理题最难,存此一篇以备体。”[2]286纪昀也意识到了性情与说理之间存在矛盾,他推崇理趣的审美趣味,试图化解理性议论与感兴抒情之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理题”这一概念,由于试帖诗题多寻章摘句而来,不乏需要说理议论之题,说明纪昀意识到“理”是其试律诗学建构中不可避免的概念。他不仅推崇阐发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无理”之题,也欣赏能作出妥帖安排的作品。《庚辰集》有边继祖《梭化龙》一作,其诗首四句云:“恍惚谁能测?神龙变化多。偶同鱼在藻,幻作凤衔梭。”[10]203纪评:“此与剑化为龙不同:剑本神物,可以变化;梭则无当化之理,难以措词。先抉明龙之为梭,然后折入梭之为龙。解铃系铃,原归一手。解题有识,自然挥洒纵横。”[10]203此处又与“压题”格有所差异,压题格意在有意反驳题意,而此处则是将题旨合理化。
除了试律本身因题命意的文体特性,如前所言,纪昀个人的试律诗学具有注重思辨思维的特点,这也使得他在审题构思时会立足于题所反映的事物规律进行思考,注意背后蕴藏的事理物理(18)此处对周裕锴观点有所借鉴,“事理”包括“包括伦理规范、历史规律、政治准则和生活常识等等”,“物理”即“客观事物的特性规律以及其中蕴含的哲理性内涵”。其对宋人“文理”的相关概念亦有探讨。参见《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5-100页。。如《我法集》有《赋得能使江月白》,题本自常建《江上弹琴》,虽是写景,实际上折射出演奏者在弹琴之时的心境变化,诗句并非直接写出心境澄明,而是藉由观月以言心境,纪昀评点亦由此入手:“月岂待听琴而白?江岂待听琴而深?而神清心净之余,实有此意,此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本不可以言说。然既已命题作诗,还须他解说。”[20]卷三在写作之时更是以直白的语言将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调古心弥淡,缘空念不兴。性情皆荡涤,耳目亦清澄。”[20]卷三此处微有下理语之嫌弃,不过纪昀评点苏轼诗的评语也可用于试律:“本是理题,遂不嫌作理语,言固各有当也。”[27]170
此外,纪昀在命意之时还会立足于“文理”措语,“文理”是基于行文的内在意脉理路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综合考量。当纪昀试图平衡二者关系时,又往往会采用议论作结的方式。以《我法集》中《赋得日高花影重》为例,题本自杜荀鹤《春宫怨》,纪昀指出此题之难在于表现“高”“重”二字:“则非用算法测量,断不能清出。此种花香草媚之题,忽然请到句股角线,更成何文理?此又作诗之难也。此诗亦不能不用算法,故从本题春宫怨入手。以昼长引出倦绣,以倦绣引出看花,以看花引出看花影,即以‘闲检点’引出‘细形容’,得‘细形容’三字作脉,则以下接入测量日影。”[20]卷一然而正因以春宫怨入手,最终又仍要符合试律体裁,是以最终纪昀选择以“驳题作收”:“地尽栽珠树,人如坐玉峰。云何杜荀鹤,更遣忆芙蓉。”[20]卷一化用杜荀鹤原诗“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28]7925句,却极言宫苑内富丽堂皇的景象,从而驳正杜氏借宫怨自怀身世之语。
至此可见,在纪昀的试律诗学中,试律与说理议论密不可分。不过,理趣”固然是纪昀所推崇的审美范式,但在实际写作中要达到“理趣”的境界也十分难得。所以,他对待“理题”又发展出独特的审美范式。其一是推崇意脉清晰、结构分明的作品。《庚辰集》有金甡《大衍虚其一》,题本自《周易》,纪昀欣赏金甡之作以多种方法层层递进,将题旨清切明畅地表达清楚:“‘乍验’二句用旁比,‘理从’二句即从正面推阐之,‘戴九’二句用平对,‘岂缘’二句即用开合挑剔之。反正虚实,浅深疏密,一笔不苟。理题须如此清楚。”[10]127其二则是欣赏“清浅显豁”的语言风格,即将复杂之理以明白晓畅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法集》有《赋得性如茧》,题本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以蚕茧为喻论“性善”,因是比喻之题故有二层,一是“茧”的喻体,二是“性”的本体。纪昀认为与其强行兼顾二层旨意,反不如各自论述,将题中隐含之旨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譬喻最切,然作诗则两边字面太不比附,强作双关之语,必至牵凑支离。故只好首位点正意,中间但作题面,以意思作关合。此种是沉闷理题,须以清浅显豁出之。”[20]卷一试帖十至十二句云:“傥曰求文绣,而慵转缫车。材良徒坐弃,质美待何如?”[20]卷一其中“倘曰”二句就纺织而言,“材良”二句微带说理之意,近乎理语,但他并不以此为意。
通过上述梳理可见,纪昀一方面欣赏试律中所体现的自然超妙的一面,推举“理趣”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由于试律因题命意的文体特性与个人学问化的诗学理念,理性思维在纪昀的试律诗学中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以他又为之另立审美范式。
四、结语
由纪昀的诗之“本原”论出发可见,试律体卑一则因为其往往缺乏写作主体情志的呈现,二则是由于试律存在程式化与格调卑下的艺术缺陷。学问一方面可以弥补写作主体情志缺失的遗憾,因为学问的显现也是创作者的一种主观投入,另一方面,可以疗愈试律一些审美弊病,譬如思辨性的写作思维可成为琐碎纤细之题的写作出路,而知识内容的精准运用与对前人文章的灵活体悟则可打破程式化的窠臼。不过,学问入诗也存在着理性思维与感兴表达的冲突,对此,纪昀在试图以自然、理趣的审美理念调和二者关系的同时,又别有创见,建立了针对于试律的独特审美范式,即理脉清晰与言语清浅。
综上可见,学问对于纪昀的试律诗学来说不仅是“写什么”,更是“怎样写”的问题。他以学问为基点建构了一套具有思辨性的写作思维模式,正如其门人梁章钜所言:“以平易之笔,写真实之理,不特为作试帖之准绳,即凡诗文皆可从此隅反。”[29]54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纪昀将试律视为别派,并且在评点之时有意援引一些古近体诗学原则以建构其试律诗学,但以时间线性梳理又可见,一些先出现于纪昀试律评点的概念也逐渐渗入到其古近体诗歌评点之中。以前文所举“理题”为例,纪昀是在乾隆二十五年成书的《唐人试律说》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一开始他的态度仍然是标举“理趣”反对“理语”。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间,纪昀开始评阅《庚辰集》,这一时期,他对于一些“理题”的“理语”表现出了一定的包容度,集中不乏此类作品。而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纪昀开始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此时他做出了“本是理题,遂不嫌作理语,言固各有当也”[27]170的总结。时人也注意到了纪昀诗学批评的这一特色,王文诰评点《苏轼诗集》有言:“晓岚多以较馆后进试帖法绳此集。”[5]156所以,从纪昀这一个案可见,试律对于古近体诗的影响可能并不仅仅是书写知识与内容的开拓,或许还存在着创作思维与批评思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