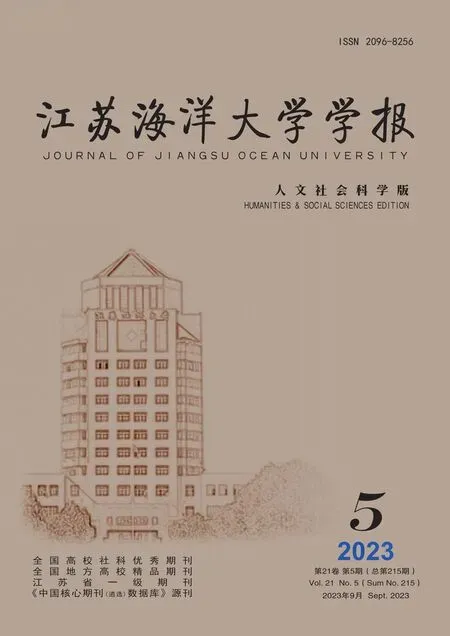青年恩格斯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思想研究
——基于不来梅时期的文献考察*
陈仕伟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1838年至1841年,带着文学梦的恩格斯来到不来梅学习经商,但是最终有选择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不来梅是恩格斯第一次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就业的地方,“是一个繁华的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德国最大的商港之一”[1]24。巧合的是,他的出生地巴门是德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被誉为“小曼彻斯特”[2]3。虽然如此,当时整个德国还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并正在逐步推广,李比希学派的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但另一方面,德国还是一个地理名词,处于封建的四分五裂状态,并笼罩着虔诚主义等宗教思想,完全不能满足当时的发展要求。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青年恩格斯一直关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并就其中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思考。因此,有必要基于不来梅时期的文献,深入分析恩格斯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的成长历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青年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
一、乐观与悲观: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虽然恩格斯就读爱北斐特理科中学时深受虔诚主义影响,但他学习了地理、数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素养:在地理方面,“拥有相当明晰的知识”;在数学方面,“恩格斯掌握的知识是令人满意的,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与数学相似”[3]548。正因为如此,考察恩格斯最初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发现,他的重要理想是自由与真理。《献给我的外祖父》体现了对古希腊神话英雄的崇拜;《我看到远方闪烁着光芒》赞美了浮士德等英雄;《海盗的故事》崇尚反侵略英雄;《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希望上帝是“拯救人类”的英雄;《贝都英人》直接表达了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因此,当时的恩格斯崇尚英雄、追求自由与真理,实际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带领人们追求自由与真理的英雄。但是这一理想该如何实现呢?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考察,恩格斯陷入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境地。
(一) 乐观:在理论上,通过编译《咏印刷术的发明》,恩格斯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1839年1月初至3月底,恩格斯编译了西班牙著名诗人、政治活动家、法国启蒙学派追随者曼·何·金塔纳的诗歌《咏印刷术的发明》。该诗歌主要表达了科学技术在反对封建主义中的积极作用。首先,该诗歌认为历史上的伟大发明都能极大地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而“足以显示它的伟力”,发明者因此为历史所铭记而获得“永生”[3]30-31。古登堡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并“进行发明创造”[3]31,特别是充分运用真理而发明出来的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反封建事业。发明创造能够发挥出巨大社会作用的关键,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理性、理智和真理,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及其科学成果就是佐证,因此“英才”即科学家能够“征服太空”“发现规律”[3]34,能够帮助人们从封建社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其次,该诗歌强调,布鲁诺会被烧死,但是真理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人民群众必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实现自由的王国。最后,该诗歌强调古登堡“击溃了专制政权下的蒙昧势力”,是“真理促使他乘胜前进”[3]38。
该诗歌不是恩格斯的创作,而是他改编和翻译的作品。但是,如果不认同该诗歌所表达的观点,恩格斯肯定就不会去专门编译,可见,该诗歌直接表达了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思考。通过对全诗十三节内容的深入解读,或许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乐观倾向。第一,科学技术即重大发明能够促进人们的解放,该诗歌例举了“巨犁”和“印刷术”;第二,科学技术对人们的思想解放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科学技术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科学技术将促进人们获得自由。
但是,恩格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仅仅是认同了这首诗歌所表达的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毕竟他还没有认清科学、技术与真理、自由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更没有考察科学技术发挥社会作用所需的制度环境,更多的是考察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上,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持积极乐观态度。
(二) 悲观:在现实上,通过回忆伍珀河谷状况,恩格斯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
几乎在编译《咏印刷术的发明》的同时,恩格斯就撰写了《伍珀河谷来信》,认为造成伍珀河谷悲惨状况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3]44。如果说《咏印刷术的发明》重点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促使恩格斯对科学技术抱有信心而具有一定的乐观倾向,而《伍珀河谷来信》则重点论述科学技术的运用给伍珀河谷沿岸居民带来了悲惨生活,促使恩格斯对科学技术持怀疑态度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悲观倾向。
虽然《伍珀河谷来信》是在不来梅写成的,却是关于恩格斯故乡巴门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政论文章。作为当时德国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工业革命成果已经在该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基本确立。因此,科学技术已在巴门得到较广泛的运用。如果按照《咏印刷术的发明》所表达的观点来理解,运用科学技术必将会把人们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现实却相反。伍珀河谷虽然工厂林立,特别是染布业发达,表面上看完全是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地区,但是实际上还处于封建社会,到处都是教堂、监狱、赌场和酒馆等,特别是教堂众多,伍珀河谷呈现出一幅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同时并存的画面。虽然科学技术本身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还处于封建状态,尤其是虔诚主义笼罩,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不仅没有体现出来,消极作用反而得到充分展现,即伍珀河谷居民的生存处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悲惨境地,因此恩格斯预言:“用不了3年,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就会被毁掉。”[3]44
虽然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运用给伍珀河谷居民带来了悲惨生活,但是他对其中的原因认识还是感性的,没有抓住根本。因为他认为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工厂劳动”[3]44,即工厂组织形式下的劳动。所谓“工厂劳动”,应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就生产力而言,是运用科学技术的劳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进步,正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就生产关系而言,“工厂劳动”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该说,造成伍珀河谷居民悲惨生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为生产关系最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但当时的恩格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他提出“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之后,就开始论述工厂中的环境、条件如何恶劣,可见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太了解。因此,当时的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感到悲观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找不到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虔诚主义。虔诚主义一直宣扬逆来顺受——“人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期望得到幸福,更不能说创造幸福”[3]50。这导致中下层劳动人民处于精神颓废状态,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幸福。由于工厂劳动已经使中下层劳动人民处于悲惨的生存境地,而虔诚主义又使他们习惯于精神颓废的生存状况,因此就出现了酗酒、疾病、赌博、卖淫等令人颓废沮丧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恩格斯来说,显然难以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保持积极乐观态度。
(三)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恩格斯难免陷入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境地
基于文献考察,刚到不来梅的恩格斯,深刻体会到了自由与真理的“空气”,阅读了大量在巴门阅读不到的报刊和书籍。因此,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从接触社会现实的方式来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就难免会让恩格斯陷入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境地。
恩格斯编译《咏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他一开始就认同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必然会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乐观。但是,当他反观自己的出生地时,却发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从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悲观,这实际上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咏印刷术的发明》从理论层面论述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并且指出通过科学技术人们完全可以实现自由,这肯定会让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充满憧憬。而伍珀河谷居民的生存现实不得不引起恩格斯的悲观深思,毕竟与《咏印刷术的发明》的描述相差甚远。如果照此发展,伍珀河谷的人们就无法实现自由,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也就根本无法发挥。
从根本上说,恩格斯之所以会处于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境地,是因为他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认识还停留于感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因而无法真正寻找到伍珀河谷居民走出悲惨生活困境的出路,也无法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海涅就曾指出:“从自然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进步以后,奇迹便完蛋了。亲爱的上帝受到物理学家怀疑和严密的监视。”[4]43因此,伍珀河谷居民的出路还在于科学技术。并且工厂劳动也并不是一无是处,1844年10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强调:“自从我离开以后,伍珀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50年都要大。”[5]321但是,当时的恩格斯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认识,仅仅指出“那里有同样的工业和同样的虔诚主义精神”[3]53。因此,恩格斯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否则就只能陷于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
二、科学与宗教:宗教经不起科学的理性追问
怀有文学梦的恩格斯刚到不来梅时,除了广泛阅读和创作文学作品外,还与格雷培兄弟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起初,恩格斯主要是向格雷培兄弟吐露心声,讲述自己在不来梅的所见所闻,同时也了解他们在柏林大学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但是随着通信的深入,他们就宗教信仰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因为此时的恩格斯正在努力清算自己的宗教信仰以摆脱宗教世界观的影响。诚如罗燕明所言:“《伍珀河谷来信》仅仅是恩格斯摆脱宗教世界观的起点,其着眼点放在虔诚主义对伍珀河谷造成的社会恶果上,还不是对神学理论和整个宗教的批判。”[6]90而格雷培兄弟是虔诚的宗教徒,并在柏林大学神学系就读。因此,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争论不可避免。根据200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收入的书信分析,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共通信19封,第一封信写于1838年9月1日,即恩格斯刚到不来梅的时间,最后一封是写于1841年2月22日,信的最后是“再见”[5]279,而在此前的信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字眼,这意味着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彻底决裂。而正是通过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恩格斯完成了对神学理论和整个宗教的初步批判,转向了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即恩格斯初步完成了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
(一) 在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交锋中,恩格斯开始了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
格雷培兄弟出生于正统的宗教家庭,且他们的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就立志于成为一名牧师,他们在大学学习时也选择了神学系。虽然恩格斯也出生于正统的宗教家庭,但是他不仅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还苦口婆心地劝说格雷培兄弟放弃宗教信仰。很遗憾,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最终导致他们走向决裂。恩格斯之所以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母亲。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就曾回忆指出,恩格斯“背道而驰”地成长,由家庭希望的“丑小鸭”成长为“天鹅”;恩格斯自己也承认,这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7]160。恩格斯母亲出生于语言学家家庭,很有教养,特别推崇歌德及其作品[8]32,这对青年恩格斯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收入的书信中有18处提到歌德,特别是在与他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两次通信中提到歌德的作品,1838年10月9日—10日,恩格斯要求玛丽亚·恩格斯提醒妈妈在圣诞节前将歌德的作品寄给他[5]105;恩格斯在1840年12月21日—28日的书信中特别提到:“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寄来了《歌德全集》领书证,昨天我就拿到了先出的几卷,而且昨晚我就读《亲和力》一直读到12点钟,感到极大的满足。”[5]269因此,正是有母亲的积极引导,恩格斯从小就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否则就无法喜欢歌德的作品,更何况歌德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博物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较高造诣。如果说《伍珀河谷来信》是恩格斯批判“神学理论和整个宗教”的现实起点,那么,这就应该是重要的理论起点。
正因为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宗教徒,所以生活在宗教笼罩的普鲁士的恩格斯总是感到迷茫。在罗素看来,“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最近几年为止,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获得胜利的”[9]1。而在当时的德国,科学对宗教的胜利还没有最终实现,但是科学对宗教的冲击早已开始,即科学与宗教正处于激烈的交锋之中,并且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还占据了不小的主动。1839年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信中描述道:“我对巴门越来越感到失望:这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毫无希望的城市。那里所发表的东西,除了说教以外,起码都是些胡言乱语;宗教上的东西通常是胡说八道。难怪人们都把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称为朦胧的和神秘的城市;不来梅的名声也是一样,它和这两个城市十分相似;市侩习气同宗教狂热相结合,在不来梅还要加上卑鄙龌龊的宪法,这些都阻碍着人们精神上的发展。”[5]128因此,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抵制宗教的消极影响,恩格斯就难以进一步成长。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1839年11月13日,恩格斯在致威廉·格雷培信中就承认:“我渴望找到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激情燃成熊熊的火焰。”[5]218可见,恩格斯一直在苦苦追寻能够实现彻底批判宗教的理论武器,但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处于迷茫状态。
恩格斯正是在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交锋中,使自己的宗教信仰处于持续的自我革命中,并逐渐走出迷茫。1839年4月8日—9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5]139此时的恩格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超自然主义者,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果然,大概过了半个月,即1839年4月24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信中就承认自己正处于变化之中:“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5]143大概又过了三个月,即1839年7月30日,恩格斯在致威廉·格雷培信中说:“我可能还会长时间地保持一些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5]190但恩格斯作为保持一些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者的时间同样也不长,大概两个月。1839年10月8日,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就宣布自己属于斯特劳斯派:“大局已定,我是施特劳斯派,我是个可怜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5]205这时的恩格斯可谓信誓旦旦,认为“大局已定”,自己将是永远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而实际上,施特劳斯思想也仅仅是他成长过程中非常微小的一个中间阶段。1839年11月13日—20日,恩格斯在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再次迅速发生重大转变:“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5]2241840年1月21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信中确认,“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5]228,并且“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5]230。在不来梅,恩格斯最终选择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
总之,在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交锋中,恩格斯的宗教信仰一直摇摆不定。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实现着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最终选择了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结合恩格斯后来的成长说明,恩格斯的自我革命还在继续,最终实现了对“神学理论和整个宗教”的彻底批判。
(二) 通过认清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恩格斯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
之所以会摇摆不定,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恩格斯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科学与宗教是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根本对立。因此,正是在与格雷培兄弟的激烈通信交锋中,他逐渐认清了其中的根本性对立,进而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最终转向了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
一方面,无论是虔诚主义、神秘主义,还是正统论,都充满着独断论,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对宗教教义提出任何质疑。1839年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信中就指出,无论是巴门还是不来梅,宗教上的“胡说八道”“阻碍着人们精神上的发展”[5]128;并且还“咒骂任何一个并不怀疑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解释与他们不同的人”[5]129。1839年4月24日—5月1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再次强调:“正统派所讲的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5]143因此,当时整个宗教界都要求每一个信众只能盲目地接受教义,而不能提出任何怀疑,即对于宗教教义只能无怀疑地相信,而不能进行任何理性分析。这与恩格斯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要追求自由与真理就意味着必须进行理性探索,绝对不能盲目相信任何绝对权威。特别是在1839年4月21日,克鲁马赫尔竟然还公然宣扬“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违背基本科学常识的观点[5]174-175。这是恩格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时距离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已经过去了近300年。因此,恩格斯总结说:“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做神的学说。”[5]184
另一方面,宗教不仅经不起理性的检验,也经受不起科学的检验。当时宗教界对科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凡是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与《圣经》所描述的内容相一致,就会拿来论证《圣经》,凡是与《圣经》相悖,则会遭受宗教界的诋毁,其中典型表现就是正统派在处理地质学与“摩西的创世史”之间关系的态度上[5]187-188。这显然不是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可见,宗教与科学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在恩格斯看来,宗教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就意味着宗教根本就不是一种学说;宗教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就意味着宗教根本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1839年7月12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凡被科学屏弃的东西……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5]188其实此时的恩格斯是在做抉择:要么盲目地相信宗教,要么坚持理性而相信科学!最终的结果是,1839年12月26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相信科学、相信理性,因为基督教根本就拿不出任何科学证据来驳倒理性主义,并且“害怕纯科学领域的斗争而宁愿去诋毁对手的人格”,特别是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进行纯科学的讨论[5]190-191。以此分析,在恩格斯看来,必须相信科学而放弃宗教,因为当时宗教界对待科学的态度,就表明宗教完全以非理性的、实用的、诋毁的态度对待科学,这与恩格斯追求自由与真理所需的态度完全相悖。因此,1839年12月26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强调:“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仅仅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不能承认你们的真理是永恒真理。”[5]192-193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分道扬镳也就成为必然。
因此,恩格斯与格雷培兄弟进行宗教争论不是就宗教谈宗教,而是与理性、哲学、科学、真理等紧密结合起来釜底抽薪式地否定宗教,因而促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宗教的非理性、反动、虚伪、荒谬,与科学完全对立。诚如朱传棨所言:“当恩格斯从理性、科学与现实来重新考虑耶稣的生平和《圣经》的故事时,也发现了其中的许多矛盾。因而他着重考察了宗教教义同理性、科学之间的矛盾,他认识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10]8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实现了自身宗教信仰的自我革命,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现代泛神论。
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
无论是《伍珀河谷来信》,还是与格雷培兄弟的论战,恩格斯都在苦苦地追求着自由与真理,且具有一定的悲观倾向。虽然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之后所撰写的《致敌人》《书的智慧》《诗稿一束》等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十足的信心,但是这仅仅是文学领域的豪言壮语。《伍珀河谷来信》表明科学技术发展并没有给伍珀河谷居民带来任何幸福;而恩格斯在与格雷培兄弟论战中,不仅使自己处于理论的迷茫状态,而且对宗教也表现出了彻底的失望。虽然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初步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但是主要是在理论领域得出的结论,而在实践领域,恩格斯并没有深入分析。而要实现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领域,必须与生活、现实结合起来。大概写于1839年12月初至1840年1月底的《时代的倒退征兆》就强调:“可以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3]110即恩格斯强调了科学技术与生活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虽然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但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保留,因为他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存在,并不像黑格尔极端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自由的概念。”[3]151
(一) 通过“触碰”英国工业革命,恩格斯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强大生产力功能
或许是为了摆脱思想上的迷茫,1840年5月,恩格斯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从不来梅启程,“经过威斯特伐利亚,奔莱茵河方向而来。在科伦坐上轮船沿莱茵河来到下游的鹿特丹市,从鹿特丹渡海到英国,在伦敦作了短暂的停留,然后乘火车继续向利物浦方向前进”[11]35。在这次旅行中,恩格斯应该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触”工业革命:不仅他乘坐的轮船和火车是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成果,也是他第一次去英国切身体会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对此,恩格斯在《风景》中进行了论述:“鹿特丹绿树成荫的码头、运河和舟楫,在来自德意志内地的小城市居民看来就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了。”[3]174“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你们这些从未见过火车,却抱怨火车单调乏味的人,现在就请坐一坐从伦敦开往利物浦的列车吧。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可以乘火车穿越全国的国家,那就是英国。”[3]177英国的发达也深深刺痛了恩格斯的爱国心,毕竟当时的德国与英国并不在同一档次上,“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自己的祖国吧!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威斯特伐利亚对自己的儿子弗莱里格拉特大为恼火”[3]178。因此,恩格斯强调:“年轻的一代才会同吮吸母乳一起吮吸新事物,新事物的胜利才会到来。”[3]179鉴于此,这次长途旅行促使恩格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向英国学习,并不是简单地学习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照搬英国的社会制度,而是应该学习英国如何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好互动状态。而这一思想重点,体现在恩格斯自英国回来之后对蒸汽轮船在德国发展的特别关注。
正因为有了这一次“触碰”英国工业革命的旅行,恩格斯更乐于从现实层面关注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显然,特雷尔·卡弗就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曾指出:“恩格斯在伍珀生活了很长时间,而在文中(指《不来梅港纪行》,引者注)所描述的不来梅港仅仅只是做了短暂的停留和了解。然而,在他的分析中有了一个新的东西,即对海运技术进步表现出的热情。他在文章中预言新设备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并结合人类、技术和解放做了如下概括总结。”[12]15显然,特雷尔·卡弗对恩格斯突然关注起海运技术即蒸汽轮船感到不解,并且对恩格斯突然重点强调以蒸汽轮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更是感到难以理解。毕竟此前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悲观,而此时他的悲观情绪不仅突然消失,还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以至于麦克莱伦认为青年恩格斯具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青年)恩格斯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印象深刻,谈论的更多的是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的经济结果……恩格斯具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发展观念。”[2]101通过这次长途旅行,恩格斯不仅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强大生产力功能,而且还深刻感受到德国与英国的巨大差距,并希望通过向英国学习来实现德国的发展,这就必然促使他更加关注英国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德国的具体运用。这就不难理解,恩格斯在结束这次长途旅行后,马上就在《不来梅通讯》上相继发表了10篇相关文章。
概言之,恩格斯是从现实的生产领域具体关注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恩格斯在《剧院。出版节》中对古登堡号轮船的首次航行进行了报道,表达了赞赏之情。《不来梅港纪行》则记录了恩格斯在乘坐了英国的先进蒸汽轮船之后,在德国乘坐轮船进行短暂旅行的情况。显然,恩格斯对自己祖国的轮船交通运输业不是很满意,因而希望积极发展德国的轮船交通运输业,“这位贤哲竭力向自己身旁的一个人证明,把威悉河河道加深,让大型船只也能通过,要比建设不来梅港更加明智,遗憾的是,在这里反对派的不断出现……”[3]194这段论述表明,恩格斯因当时德国对这项先进交通运输技术无动于衷而感到不安。在随后的《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应用》一文中,恩格斯不仅充分肯定了对阿基米德号轮船的改进,而且还强调“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3]243,并且再次呼吁,“我们应该赶快把这项新的发明用于我们的横跨大西洋的交通航线”[3]247。在《航运规划。剧院。军事演习》的通讯文章中,恩格斯通过具体数据说明,运用新型的阿基米德号轮船可以极大地缩短纽约与不来梅之间的航运时间,并且“来往于德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蒸汽邮船一旦通航,这种新设备无疑会被迅速采用,并且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3]253。终于,1840年11月5日,恩格斯非常高兴地撰写了《不来梅港同纽约的轮船航运》的通讯报道:“我很高兴向你们报道,为不来梅同纽约之间的定期航线建造一艘排水量为1 000吨级轮船的决定,现在已经通过。”[3]263这意味着,恩格斯一直呼吁将新型轮船技术运用到德国交通运输业中的愿望已经实现。
综上分析,恩格斯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一直关注这一项重要技术发明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时偶然,毕竟他一直关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这就不能不促使他关注工业革命及其成果在德国的具体运用,而英国旅行又让恩格斯切身体会到工业革命重要成果之一的蒸汽轮船对交通运输的重要变革作用。因此,恩格斯总结认为:“自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范畴从思维着的精神的直观形式中独立出来,人类便力图在物质上也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3]253在恩格斯看来,蒸汽轮船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是简单地缩短交通运输时间进而加强两地之间的联系,而是不断地实现人的解放。显然,这样的认识视角不是文学的,而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意味着,恩格斯通过对交通运输技术的关注,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
(二) 恩格斯对科学技术持乐观态度,但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虽然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于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恩格斯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恩格斯也充分认识到,如此先进的交通运输技术之所以在德国迟迟得不到广泛运用,根本原因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社会制度。恩格斯在《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应用》中强调:“但愿我们那些富有的人们和船主们关心这一重要事业,而不要让心胸狭窄的和目光短浅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妨碍他们对这一事业的支持。诚然,乍看起来,这种事业似乎不利于航运企业,因为帆船当然要被夺去一定数量的走这一航线的移民旅客。但是,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由于船主们的忌妒而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3]247-248可见,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封建社会,害怕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会冲击某些集团的利益,但是科学技术的巨大生产力功能必然会突破这种狭隘眼界,广泛地运用于生产中。恩格斯的这个预言很快在1840年11月5日转化为现实。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落后的德国就举步维艰,显然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制度。但是落后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能限制科学技术的强大生产力功能,并且科学技术强大生产力功能必将会突破社会制度的限制而逐步改变社会制度。因为蒸汽轮船技术虽然由于落后的封建制度而导致在德国迟迟得不到充分运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强大生产力功能的日益发挥,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要在德国得到运用,否则,德国就会远远落后于世界,特别是无法进行工业革命。根据迪特尔·海因的研究,德国“早在19世纪40年代爆发工业革命之前,交通和贸易领域的革命就已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非比寻常的机遇”[13]33,“道路的改扩建与蒸汽船只的出现,1834年关税同盟的形成,最后则是铁路的兴起”[13]34;“市民阶层的人数与重要性不断上升”[13]34;“在个人自由、法律平等和个人成就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13]35。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强大生产力功能促进了落后的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因此,当恩格斯已经认识和体会到科学技术的强大生产力功能时,此前所具有的悲观情绪就基本一扫而光。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能够通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尤其是生产力功能而逐渐实现。因此,恩格斯在大约写于1841年7月底至11月底的《漫游伦巴第》中,就表现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情:“自然力量对于人类精神的这种对抗,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巨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即使在这里也是精神战胜了自然。”[3]318-319特别是在该文章的最后,更加体现了当时恩格斯的心情:“我从未见过而久已向往的大自然的魔力,使我陶醉激动,我一边想着即将出现在我眼前的种种壮丽景色,一边愉快地入睡了。”[3]322
四、青年恩格斯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恩格斯从小具有的文学梦在不来梅已基本破碎,在认识到青年德意志的局限性[14]而最终选择黑格尔哲学后,恩格斯撰写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明显递减,但是他从小就树立的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却从来没有改变。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要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对于当时的恩格斯来说,就不能不受到理性、真理、科学等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从中学起就开始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因而促进了恩格斯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迈进。
第一,恩格斯坚信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坚持朝着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奋进。基于文献考察,此时的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密互动关系。他不仅认识到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文学创作,而且必须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作用。此时的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要实现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就必须不断改变世界,即要不断发挥出科学技术的积极社会作用。因为无论是要彻底消除思想领域的困惑(典型表现就是与格雷培兄弟的宗教争论),还是要彻底解答现实的社会问题(典型的表现就是运用蒸汽轮船技术改变德国的交通运输问题),都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换言之,如果不是这样,不仅不能认识世界,还无法改变世界,那么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就永远无法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就遥遥无期。因此,正因为恩格斯一开始就关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促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才能不断地实现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理想,才能不断促进人类的解放。
第二,恩格斯在认清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的关系后,坚定地朝着唯物主义方向前进。通过与格雷培兄弟的争论,恩格斯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与宗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毫无疑问,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了宗教就意味着坚持了唯心主义,而选择了科学就坚持了唯物主义,恩格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在与格雷培兄弟争论期间,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理论领域摇摆不定状态中实现自我革命,根本原因就是他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当理论不能解答现实问题时,毫不犹豫地放弃理论,而不是修改现实来适合理论。即使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最终选择了黑格尔哲学,也是更看重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于他的唯心主义则从一开始就持批判态度。或许正因为黑格尔哲学存在着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后来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黑格尔哲学,在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的基础上与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认清了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关系,就表明他将会朝着唯物主义方向前进,而不是相反。
第三,恩格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撰写奠定了前期基础,进而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初基础。由于恩格斯更早地关注社会现实,因而比马克思更早地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恩格斯编译的《咏印刷术的发明》就强调“巨犁”在改造自然中的巨大作用;恩格斯在英国的长途旅行中就切身体会到交通运输技术能够提升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期认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会明确提出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这个精神要素的观点[15]67。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应该列入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思想,后来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同时也为现代生产的蓬勃发展所证实。”[16]277-278而孙伯鍨认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7]146-147。
第四,恩格斯辩证地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打下了前期基础。正因为恩格斯在坚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希望从现实社会发展状况中来寻找到其中的理论,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理论来修正现实。因此,恩格斯一开始就拒绝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保留了辩证法,这意味着他在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后就会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比如恩格斯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就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历史发展:“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丝,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3]107因此,恩格斯肯定会将辩证法运用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分析中,这样就必然会得出关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科学辩证发展的科学认识。后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撰写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对18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各技术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辩证分析,这显然为恩格斯创立自然辨证法打下了重要的前期基础。诚如张云飞研究所言,《伍珀河谷来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著作具有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奠定了前期基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