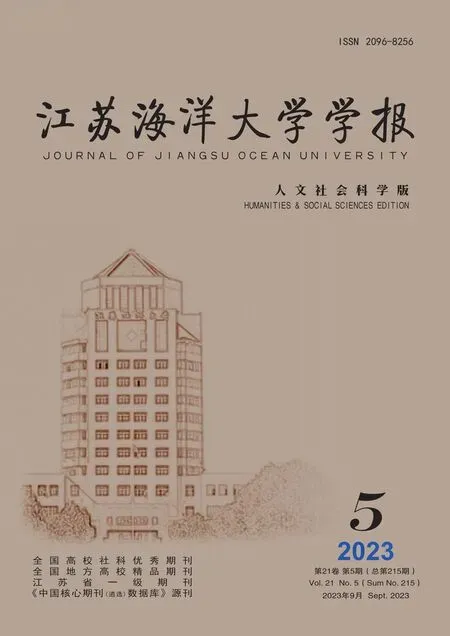否定与超越: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生发的逻辑论析*
李少霞,王文东
(1.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天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不同,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发展视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英国学者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中指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暂时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他并不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运动即使有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暂时的”[1]2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是暂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的界限与自反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秉持辩证否定的原则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对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剥削、无产阶级生活状况、人口相对过剩、阶级斗争等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理论剖析和批判。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剖析资本主义自反性的同时,发现了其中内含的“新世界”,继而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
一、限度与域度:资本逻辑自我运行的界限及其自反性
资本逻辑的本质是增殖,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无限度地吸取工人的血汗,“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69。但是,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它在确立自身特有的界限时,却追求无限增殖企图超出任何界限;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生产力时,却随处潜藏着倒退的萌芽;在推动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历史进步时,它自身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体制”[3]35。
(一) 资本逻辑自我运行的限度
资本逻辑是一种强大的、自我增殖和自我膨胀的同一性力量,为了增殖,它必然会将现实中的一切变为服务于自己的手段和工具。资本只有吮吸活劳动才能生存,因此,资本要实现增殖,就必然要剥削工人,通过占有工人的劳动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增殖,一旦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就只能是一个僵死的抽象物。但是,当资本无限制地追求价值增殖时,其本身必然会遭到人的身体、自然、道德和法律的限制。
第一,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实施剥削时,必然会受到人的身体的限制。对于工人来说,一天只有24小时,工人只能在小于24小时的时间内支出自己一定量的生命力,其他时间则需要用来休息和吃饭,以维持和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不可能24小时都处于不眠不休的状态受资本家支配。此外,人的身体、器官、体力和智力等都是有限的,这决定了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空间也是有限的,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这一能力的影响面也是有限的。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中还是机器大工厂中,无论是资本家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还是要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都必须承认以下事实:一方面,就工人的劳动时间而言,虽然工作日是变动的,但是,其变动的范围和幅度都要受制于人的体力;另一方面,就工人的劳动强度而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越强,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就越大,但是,无论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多大,都要受制于人的体力。
第二,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实施剥削时,必然会受到自然的限制。自然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和约束,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活动更不例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增殖欲望是无限的,满足资本增殖欲望的物质资料均来源于自然,资本的无限增殖必然受到有限自然资源的制约。资本借以增殖的物质资料均处于生态循环的链条之内,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资本家的视野中,他们看到的只是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被资本增殖逻辑所切割的孤立的物质实体,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为资本家眼中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财产,从根本上贬低了自然界的实际价值。当资本家盲目追求价值增殖时,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必然会无限制地剥夺自然资源,从而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性,损坏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制约生态系统的存续和发展。
第三,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实施剥削时,必然会受到道德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所衍生出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专制的统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利用各种政治的、文化的手段,将这一状态宣告为一种永恒的、终极的状态,肆意鼓吹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使其成为支配现存世界的“精神枷锁”。因此,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这一“虚假的观念体系”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道德阴谋,悄无声息地抹杀了工人对资本统治的批判和反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批判,而是立足于工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和生活状况,将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作为批判的着眼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作时间的深入观察,马克思提出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即让工人“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2]269,深刻透视了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背后工人的生活状况,规定了资本增殖逻辑实施剥削的道德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强度。
第四,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实施剥削时,必然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维护统治,资产阶级总是以国家政权为中介,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和框架。而作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主要场所,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厂也不例外。但是,“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2]322。马克思指出:“资本终于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2]282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体现在:一方面,迫于工人的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构对于工厂法做出一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使工人的劳动强度稍微有所降低,以缓和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性和永恒性,使资本增殖的方式更具合法性。资本主义大工厂中的一切立法均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管是工厂法规定的工人全天候工作还是换班制,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的大工厂中,一切“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2]320,只要工人还有一滴血和一块肉可以榨取,作为“吸血鬼”的资本家就不会作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去争得一项法律。
(二) 资本逻辑的自反性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一种“在批判性和具体人道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的逻辑”[4]184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资本逻辑,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分析,深入地把握了资本逻辑的秘密,即资本逻辑内含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的必然趋势。
第一,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逻辑使人摆脱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的统治,将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从表面上看,工人付出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生产产品,资本家给工人支付工资,这是一种表面上“平等”的关系。但是,从深层意义上看,资本逻辑就是现实的形而上学,其本质就是“‘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时空中的展开”[5]1171。资本逻辑虽然使人挣脱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又给人套上了新的枷锁,使人受物的束缚。在资本逻辑中,物的发展取代了人的发展,资本作为一种强大的、同一性的社会力量,将人创造出来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反面。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这种人受物的抽象统治的现存状况宣告为一种永恒的、终极的形态,成为束缚人的一种“枷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历史就是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所衍生的物对人的占有和统治。因此,人类解放的旨趣就是要颠覆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将人从“物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将资本主义社会“物”所占有的独立性和个性赋予于人。
第二,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枢轴,其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需要通过不断地生产和消费来充实自己。但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自反性日益凸显,走向自我否定和瓦解。立足于资本增殖的生产,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资本家总是把获得的剩余价值以资本的形式不断地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本的增殖和积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的存在,使资本处于永不停歇的增殖运动中;再加上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资本家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扩大生产规模、加大投入等方式,变相地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但是,当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被应用于生产后,工厂中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也会相应缩短,与之相对应,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会随之降低。当工厂中生产出的产品日益增多而工人的消费能力日益降低时,必然会带来生产的过剩和产品的积压。在资本增殖逻辑的主导下,资本家生产得越多,工人的支付能力就越弱;积压的产品越多,经济危机爆发的机率就越大。经济危机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弊病,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就是资本自身。
第三,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与生产关系的停滞不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作为统治现存世界的统一性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一切事物都必须在这一权力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因此,资本追求增殖的本性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均处于动荡和变革中。资产阶级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革命使一切旧的、僵化的观念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均被瓦解,建立了普遍的世界性交往。资本增殖的逻辑将一切民族国家均卷入资本的洪流中,一切分散的生产资料、劳动力、财产等也在资本强大的辐射效应之下聚敛,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当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它所创造出的财富时,社会生产力便开始反抗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阻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洞见了其发展的历史趋向:走向瓦解和灭亡。
第四,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其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一切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以及产品等均“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6]996。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均不断得到提升。同时,一切小规模的个体生产都集中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需要各部门的集中参与才能完成。但是,资本家想尽可能地获取高额利润,在这种盲目获取高额利润欲望的驱动下,一切价值规律都不过是一种内在的规律,只是“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6]996。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以及市场运行的刺激下,一切生产以及消费的社会联系均只是“表现为对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6]941。伴随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以及垄断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逐渐显露。由此,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反性,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二、辩证的否定: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与其他的唯心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以辩证的否定原则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等“内在否定”因素的全面考量和批判,发现了新世界,确证了新世界的美好图景。
(一) 无产阶级:旧世界的掘墓人和新世界的建设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在经济上以科学技术的革新不断变革生产方式,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比以往一切社会创造出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文化上形塑了资本逻辑背后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拜物教意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确立商品、货币和资本在商品交换中对人的总体性统治,实现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的奴役,并使工人能够接受剥削和奴役、接受这种永恒的终极状态,抹杀了种种批判反思的可能性。通过对资本增殖运作规律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马克思发现,资本能够无限增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控制和占有了工人的“活劳动”,资本的增殖和积累与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是相伴相生的。资本的一切使命就是增殖、谋取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关注物,不关注人自身。这种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压缩工人的发展空间,从而“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7]289。工人的付出和所得成反比,工人体力耗费得越多,他占有得就越少。不仅如此,面对物的残酷奴役和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单个工人无力摆脱这种境况,只能“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任由资本家摆置,成为随时都可以被替换的机器附属物。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工人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就越大,在资本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野蛮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734。
对于工人而言,肉体受到摧残、精神遭到折磨、未老先衰、疾病缠身、过早死亡等均是难以避免的宿命。在所谓“公平”的交易市场中,资本家“笑容满面”“雄心勃勃”,工人却畏畏缩缩,任由资本家肆意蹂躏。在资本逐利本性的主宰下,资产阶级以一种无声的经济关系强制统摄着工人的生产生活空间,压榨工人的血汗。虽然机器的应用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的生产能力的显著提升,但也日益加剧了劳动的碎片化和人的身体的机械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状况的深入接触以及对劳资关系对抗的全面审视,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劳资关系的对抗是资本增殖逻辑运演和资本权力运作的必然结果。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事物都要被资本的同一性逻辑对象化且受其控制和占有。当工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阶级关系的两极对立和革命的到来。
马克思的任务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透过人的生存境遇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马克思深入到工人的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揭示了资本家利用工资抹除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界限,掩盖资本家剥夺工人的假象;另一方面,通过区分可变资本与不可变资本,计算出剩余价值率,以一系列详实可靠的数据既直观又量化地展现出资本家剥夺工人的程度,使工人更明确地知晓自身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会更加尖锐。随着工人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将被激发。马克思通过对否定辩证法的演绎,提出“剥夺者被剥夺”的号召,积极引导工人认识当前的生活现状,旨在充分调动和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使工人能打破外在的“他者”对自身发展的规约和束缚,突破资本逻辑的枷锁。只有当工人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姿态变革现存社会制度,从资本逻辑的裹挟中解放出来,才能把支配工人的异化权力归还给人本身,使工人摆脱“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可以说,“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9]43。
(二) 资本主义所有制:自我否定
所有制即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和占有,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地位。当马克思将研究的视角从哲学批判转变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后,他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也更倾向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并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自我否定性,伴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代替它的必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但是,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对原始公有制的复归,而是一种双重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超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之后,马克思又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9]592,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最后一个对抗阶段,破除了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所宣扬的资产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非历史性。依据所有制的社会性质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资本主义以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体现的是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制度,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基础。这些自由的劳动者可以借助自身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进行生产,并占有劳动成果。这种以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意味着“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聚,也排斥协作……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8]872。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分散的生产资料逐渐集聚到少数人手中、小生产者转变为大生产者,人民的土地、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等被剥削时,这种私人占有的所有制便解体了,随之而来的是“被资产阶级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8]873。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这种个人的分散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这种否定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对私有者进行剥夺,是对个人所有制的一次“自我摧毁”,它使一切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都被资本家占有,原来的小生产者由于失去生产资料,被迫转变为自由民,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在这一私有制中,各个资本家均是独立的、互相竞争的个体,为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每个资本家都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高额利润,以大企业吞并小企业、以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当“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8]873,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日益深重时,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瓦解。此时,必须要对私有制进行第二次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彻底的扬弃,而是建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的新陈代谢。“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874这种“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否定和重建的有机统一,体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人的自由个性”的转化。并且,从分散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再到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一种复归和倒退,而是在更高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对私有制的第二次否定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对私有者进行剥夺,是因为:(1)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均归资本家占有,体现为一种“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8]873;(2) 相对于第一次否定,第二次否定的范围更宽,它否定的是一切剥削工人的资本家。
(三) 生产力发展:开辟通向自由王国的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683这里的“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指的就是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在这一社会形式中,任何人将不再受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的约束和宰制,人将从自然、社会关系以及时间中获得自由,可以享受真正的、全面的、普遍的自由,人的自由个性将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通往自由王国的基本路径。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仍旧深受物化的社会关系制约,人的自由时间也被剥夺,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它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迈入新的发展进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通向自由王国的一个重要路径。
一方面,资本家在追求利润增长的过程中不得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必然会创造出剩余劳动,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10]69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切劳动都是必要劳动,只能维持人自身的生存。而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劳动。所谓剩余的劳动,是指“劳动产品逐渐积累以供个人和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劳动”[5]1137。特别是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将先进的大机器引入到工厂中,使机器代替人力完成繁重的劳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人节约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使人可以在闲暇时间内依据自己的喜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剩余劳动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人能够在普遍的交往中实现个人才能的普遍化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剩余劳动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充裕的自由时间,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不同于传统学者,马克思赋予时间特殊的功能,认为时间代表着人的自由程度。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其存在必然要占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时间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和事物存在的必然属性。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时间均被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时间是人创造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所必须花费的时间;自由时间则是人在劳动之外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即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人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参与人际交往等,从而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施展自由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价值增殖,因此必然会衍生出一个基本的逻辑,即“资本的规律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产生了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趋势”[10]83。当资本主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会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指出:“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0]197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当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增殖的最大化时,它必然会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王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缩短工作日,为人创造出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
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都只是为人的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机器大工业的推广、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式的采用等,一切都加速了劳动的社会化,在导致资本主义自我灭亡的同时,也使人从“物的依赖关系”中挣脱出来,走向发展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三、共产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文明面”的历史性超越
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孕育的新社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文明面”对旧社会的历史性超越。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9]259资本主义只是“生产方式有规则链条中的一环”,并不是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普遍的、永恒的和固定不变的,也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短视地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而是倡导无产阶级要充分认识并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面”。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超越,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克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 共产主义社会是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根据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当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否定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时,这是第一次否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生活于普遍的异化和受压迫之中。这种私有制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它必然会经过否定之否定进入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将不复存在,而是重新获得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这种所有制虽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是,这种所有制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分散的、无序的个人所有制,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马克思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1]96在共产主义社会,“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10]386。不仅劳动者可以以主体的地位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而且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与劳动者的个人占有之间是不冲突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不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生产,一切生产均只是围绕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展开。并且,由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充沛的物质财富,能够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一部分会归社会所有,用来扩大再生产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部分则归属个人所有。因此,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占有与个人所有并不矛盾,它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状况的科学描绘,既不是对私有制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公有制的简单实现。这种重建个人所有制具有以下内涵。
首先,个人所有制的重建依赖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874。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重建个人所有制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紧密相连,只有保障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才能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奠定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之分,一切人均是平等的社会主体,因此在产品分配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整个共同体中的所有人,不会偏袒任何特殊的个体或群体,有效确认了所有个体对社会总产品的占有权。同时,也正是因为每个个体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它更关注个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从而切断了生产资料向个人所有转变的可能。
其次,重建个人所有制体现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12]582,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现状的摒弃和推翻。从字面意义上看,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对劳动者个人所有的重建,这种重建,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的社会化不断扩大和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当资本主义被消灭后,生产资料就不再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是转变为为大多数人谋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成为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当生产资料与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有效结合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无政府的状态、相对贫困、经济危机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均被消灭和解决。这一结合体现的社会效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当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特殊利益均会转变为普遍利益、对使用价值和质的关注将会代替对交换价值和量的关注、一切产品的生产活动均服务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赋予正向的物质激励和精神内涵。(2) 当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人吃人、人奴役人的相互对立的状态将会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是开放、包容和共赢的。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所塑造的人的个性和独立性丧失的状态将一去不返,人将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富有个性和独立性,成为差异化的个体。(3) 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强调的是社会生产与个人消费、社会占有与个人占有之间的统一。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即生产资料归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则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所有,绝大多数人处于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地位,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共产主义社会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多数人对少数人剥夺的基础之上,是对个人劳动的社会回馈和成果确证,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所创造出的共同财富。
最后,重建个人所有制内含对劳动所有权平等的肯定。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其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的政治合法性,保障了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占有的经济权利。因此,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追求,相对于经济制度的变革而言,重建个人所有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的变革。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如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言是永恒的和非历史的,而是暂时的,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限制;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愿景来看,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的一极,资本的席卷摧毁了无产阶级生存空间的完整性,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均被改写,陷入生存困境。争取自由和解放是无产阶级毕生的追求。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推翻任何形式的剥夺与压迫,满足了劳动者可以自由使用劳动条件占有社会产品的意愿,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二)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将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是当代哲学的根本使命。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挣脱出“虚假的共同体”,实现自由人的联合,构建起“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挣脱异化的枷锁,实现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一切特权、终结了资本逻辑抽象统治的理想王国。在这一理想的自由王国中,人的精神将得到极大充盈。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2]571要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必须使人能自发地联合起来,使物质交换处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彻底摆脱物的力量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生活于其中的人将真正占有人的本质,从一切片面、固定、单一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有机统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人与集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中,资产阶级往往通过“国家”压制多数人的利益,扼杀个体的自由个性,以共同的利益掩盖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自由人的联合体”关注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置于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保障了个体鲜活的自由。
第二,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不存在阶级,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参与共同体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使阶级斗争简单化,但是,它却史无前例地加剧了阶级斗争,“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题,任何一个个人,他总是依附于某个阶级。而“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阶级之间的联合,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均摆脱了阶级压迫,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个人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有序的,人的“类特性”得到彻底激活。
第三,生活于“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每个个体均可以充分地享受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等。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12]571,而对于广大的被统治阶级而言,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居住权和发展权均被剥夺,一切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人作为主体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隐。与之相反,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阶级差别、分工和异化等均会被消灭,生存权、发展权等将不再是统治阶级的禁脔,而是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
第四,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将不再对立,两者之间将实现有机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建立在普遍利益之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阶级的消亡使得国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也会随之消失。
第五,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由发展、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不再是被资本逻辑所主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性手段。马克思曾对其进行了描述:“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2]232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均将成为和谐、正向、充盈人的精神生活的交往。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对原始社会传统共同体中的那种平等和谐状态的复归,而是一种超越性的社会存在,它不仅超越了狭隘的自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超越了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义,而且也超越和扬弃了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确保社会全体成员有效控制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消费和分配,为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新道路的开辟指明了方向。
(三)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审视,提出要在推进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进程中改变现存事物,“推翻那些使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2]11,勾勒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人被资本奴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丧失的现状,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才能使人摆脱身上的枷锁,使人的自由发展不再是幻想。
首先,工人是“完全没有任何财产的阶级”[12]677,只能将劳动力以商品的形式出售。资本家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想尽各种办法压迫和剥削工人,资本家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2]306。同时,资本逐利的本性也决定了资本家只会从抽象、空洞的自然属性方面理解人的存在,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多样化需求,仅仅是将人视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被资本逻辑所压抑和统治,资本被赋予个性和独立性,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却被剥夺,人被异化。资本对人的身体空间的统治使物的关系遮蔽人的关系,人的逻辑被淹没于物的逻辑的总体性发展之中。除了为资本家服务、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之外,工人没有任何消遣和任何获得自身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像一头载重的牲畜。残酷的剥削和生活状况的窘迫使工人意识到,必须要联合起来,以自由人联合的空间拓宽人的生活和生产空间,在克服地域空间局限性的同时也加速对资本逻辑物化之谜的破除,摆脱“虚幻的空间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随着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加深,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也日益强烈,资本主义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意味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变革现存社会的重任。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仅生活窘迫,而且尊严尽失,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被遮蔽在物与物的关系当中,物奴役了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旨在揭示诱发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矛盾的肇生源,推翻物奴役人的社会关系,改变人的生存境遇。他深入到经济学的视域中,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劳动异化问题进行揭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18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人挣脱了“圣神形象”的自我异化,但是又陷入“非圣神形象”的自我异化中,建立了一个包围着自己的“第二自然”[13]200。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从各种生产关系中、从他自身和自然中克服异化,从而占有自己的本质,“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14]69。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将从受物质力量所遮蔽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不再受资本逻辑和资本权力的支配和控制,人可以在共建共享的氛围中理性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自觉构建起以和谐、正义为主要特征的共享格局,劳动也不再是束缚人发展的外部力量,而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彰显。在这一彰显人的主体力量的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展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和一致性。
四、结语
当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均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固定不变的社会状态时,马克思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物质生产和资本社会运动的客观形态中,洞悉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本质,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谎言。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机理”与“外在症结”的诊断,在资本主义的“病因”中管窥到“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资本的增殖意愿是无限的,但是这种意愿受自然、人的身体、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当这些限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本身就成为限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91,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调整,它都潜藏着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批判和否定,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的工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考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面”及其进步意义——孕育共产主义社会的发源地。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在推进自我建构的同时也趋于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走向自己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