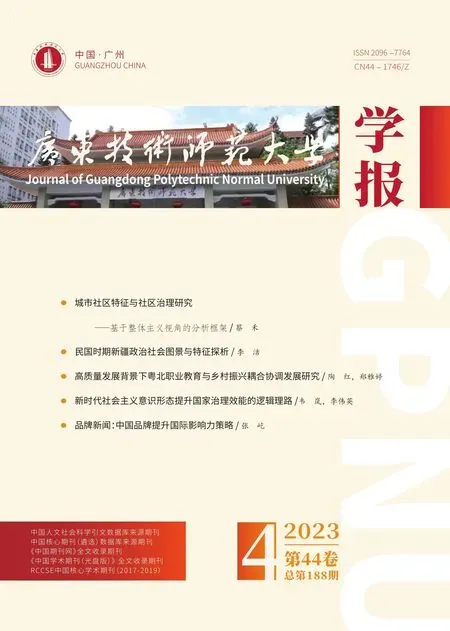场域、文学与绘画:岭南行商园林的空间想象
邹晓霞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
目前学界对岭南行商园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物质实体空间,从建筑学视角探讨造园手法及园林美学艺术,但面向超脱于园林实体之外的精神文化空间的考察则不够深入,尤其是文学、绘画这两种媒介对园林的空间文化建构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挖掘和解析。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想象的角度对岭南行商园林文化作出进一步的考察。在当今的研究语境中,空间的定义已经突破了现实物质层面,被赋予了浓重的社会文化意蕴。美国学者王敖在《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一书中提出空间想象是“构造意象的过程”,而意象乃是指“将现实通过各种媒介呈现出来的精神图式或表现。意象可以是影片式的、图像式的、语言的或心理的。”[1]意象的构造对于空间文化场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而意象可以是跨越媒介的多种形式的呈现。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岭南行商园林由现实地理场所转换为具有浓重文化意蕴的空间场域,文人们的空间想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行商园林空间想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彼此协同乃至相互转换。绘画和文学作为最主要的两种媒介,共同展开对岭南行商园林的重新书写,生化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美学画卷和空间意象呈现。
通过跨媒介的考察和空间理论的引入,探讨行商园林如何由物质的空间转化为文化的场域?此一场域所生产的诗文与绘画怎样构筑起这些美丽花园的空间想象并赋予其文化的生命力?对于这些问题的探寻,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园林空间文化增值路径的理解,同时对园林、绘画、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更加深入的探索。
一、园林文化场域的形成
物质空间能否转换为文化场域,人的交游与活动是关键因素。布迪厄提出场域是由行动者和客观空间共同组成的网络构型,没有人的行动便没有场域的形成,并将场域划分为“文学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等大大小小的空间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行商园林能够突破建筑实体和私人居住空间的藩篱,建构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场域,人的活动与行为发挥了关键作用。行商构筑物质空间基础,出入官员为之灌注政治的力量,文人及文人化的园主引入高雅文化因子,外商带来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些参与者及其活动共同推动了园林功能结构的嬗变和文化场域的形成。
中国古典园林本具“可游可居”之特质,但向中外游客同时敞开怀抱,将游览性和娱乐性之场域功能发挥至极,行商园林则属首创。行商后代颜嵩年曾回忆昔年磊园作为游赏场所的盛况:“时城中各官宦皆悉此园美观,常假以张宴,月必数举。冠盖辉煌,导从络绎,观者塞道。”①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对于行动受限的外国商人来说,游览行商园林成为他们中国城市生活的重要节目,被邀请到行商的美丽住宅中去游宴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难得的宠遇。作为向西方开放的休闲游赏空间,行商园林成为公认的美丽超凡的城市象征物和“中国符号”,对晚清中国城市形象的对外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行商园林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游赏场所,还是晚清中国重要的政治场域之一。在与政治联系的紧密度上,行商园林远超徽商、晋商园林。鸦片战争后,颇通夷务的行商成为政府外交谈判的倚重对象。伍家庭院两次作为荷兰使团与两广总督的会面地点,海山仙馆甚至充当了清政府一处非正式的外交场所:“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人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②威廉·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章文钦、骆幼玲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潘仕成参与了两广总督耆英与法国使团谈判的全过程,多次邀请使团代表参观海山仙馆并于园中安排下榻之处。美丽花园中的宴请和谈判打上了个人感情的亲善意味,作为严肃政治的润滑剂,行商园林成为晚清政府对中国南方经济和外交进行控制的柔性权力场域之一。
除了观赏宴游的休闲功能和外交往还的政治、经济功能,行商园林更是诗文酬唱、书画收藏等文化传授的场域空间。这些私人园林因其优美的景致和园主的影响力,往往成为文化雅集的胜地。张维屏曾有诗《甲寅(1854)三月三日,卢柬侯比部福晋、许星台水部应鑅、伍荫亭郎中长樾、许筠庵太史应骙,招同金醴香员外菁茅、桂蓉台广文文炤、沈少韩太史史云珠江修禊,遍游花埭翠林、花市、馥荫、芳村、杏庄诸园,即事有作》,从中可见当时广府文人将园林游玩、修禊雅集与诗文酬唱密融为一的文化交流方式,这样的文学活动促使行商园林由地理空间转换为重要的文学场域。
将诸如书画、茶香、琴石等各种无关生产的“长物”纳入园林生活范围是行商精神文化追求的重要部分。潘仕成海山仙馆收藏的古帖、古画、金石等堪称“粤东第一”。伍氏的万松园“收藏书法名画极富。嘉道间,谢兰生、观生、张如芝、罗文俊……时相过从。”③[清]黄佛颐:《广州城坊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园林书画收藏不仅是以此来营造作为个人生命寄托的生活之情境,更多的是通过文人间的书画鉴赏和互动活动来维护一种知识上的“共同体”,获取文化身份上的提升。
书籍的收藏和刊刻是显示行商博学和文化涵养的重要手段,这种“亦商亦儒”的产业有时直接设置于私家园林中。潘仕成曾集刻《海山仙馆丛书》《佩文韵府》《尺牍遗芬》等大量书籍,受邀参观海山仙馆书坊的法国公使随员赞叹中国商人的高雅学识,称扬其对地方性知识保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间广州的印刷所被用来拓印古代的铭文和愈来愈稀少的古代箴言,它们的复制品向来很受读书人的青睐。”④伊凡(Dr.Yvan)著,张小贵、杨向艳译:《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随着大量书籍的收藏和刊印,行商私家园林成为文化传受的空间和岭南文脉传承的重要链条。
“原生的地理空间,因有文人的到来而成为文化场所……文化活动越多,文化创造越丰富,地理空间越有文化意义。”[2]与余荫山房、可园、梁园等其他岭南园林多属于归隐居住府第不同,行商园林因交游、政治、外交和文化活动的丰富,便由私人领域空间转换为开放性的文化场域。伴随此一场域中文人活动的丰富,相应的图绘文记随之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文人和画家利用文学、绘画媒介展开创造,进而构筑起精神图式中的园林空间想象并赋予园林以文化和生命的意义。
二、园林文学的空间想象
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的历史往往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有形的园林与无形的文学之间存在着往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园林作为雅聚酬唱的舞台和物质空间,构筑起文学创作与传播的文化场域。另一方面,园林中的醉人美景,主客的交际往还,往往会触引文人的创作情思,进而展开“再现与想象意义上的二次建构”①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页。。文人以语言为媒介参与了行商园林的空间想象和诗学重构,而这些想象和重构则反向赋予园林以精神的生命,实现了超越建筑实体藩篱的文化延续。
如果以空间的视角去关照文学与文化,其所指应是“文学与文化如何呈现外在的物理空间和内在的精神世界”[3]。行商园主“业商而好文”的价值追求使得园林成为演绎士大夫情结的理想空间。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被描述为“世外桃源,人间之仙境”,可见园主超然于世俗之外的意趣追求。伍崇曜所建远爱楼“半生嗜好,神仙端合楼居。七宝庄严,城市别开诗境。”②黄任恒编篡:《番禺河南小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在城市世俗的园林中寻一方心灵的理想居所,正是园林营造背后的精神诉求。这种精神诉求在园林文学书写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现。检视文本,我们发现不少行商园林诗文呈现出类似的叙写模式,那就是自然物理景观与精神文化空间的双重呈现。试举几例:
伍崇曜西园:“竹洲花坞,王摩诘之所往来;书库琴亭,白太傅于焉啸咏;洞房连闼,半郭半郊。傍山带江,饶水赋竹。”
伍元华听涛楼:“大海风涛气,苍茫一当胸。万签搜逸竹,四面种乔松。黄木几湾水,白云何处峰。爱君论座帖,半日作书傭。”
潘正亨万松山房:“河洲卜筑园林胜,一路松荫到画堂。花竹微云清自媚,琴樽小雨澹生凉。高朋偶聚盟鸥鹭,古帖闲评重汉唐。十亩芙蕖尘隔断,不知身在水云乡。”
潘正炜清华池馆:“小筑清华傍茂林,笙簧隔水奏佳音。敢夸墨妙供幽赏,赖有松涛惬素心。文字留题钗股折,水天同话酒杯深。”
潘仕成海山仙馆:“修梧密竹带残荷,燕子帘栊翡翠窝。妙有江南烟水意,却添湾上荔支多。萧斋旧制多藏画,吴舫新裁称踏莎。万绿茫茫最深处,引人幽思到岩阿。”
在诗的世界中,精神性的关照将日常园林生活经验提升为文学空间中的人生体验,展露出晚清岭南士商雅致悠闲、怡然自得的生命哲学追求。行商园林文学的自然景致大多为竹木亭台水榭,傍山带江,饶水赋竹,松涛阵阵,万绿茫茫,充满文人化的审美情致。当文人们用心灵之眼去感知这些园林景观时,常常关联着“赖有松涛惬素心”“引人幽思到岩阿”的山水共情。“此中境界涤尘俗,此外何处娱幽情”,当世俗名利缠绕撄身却不足凭藉时,寄情于园林山水成为心灵的皈依处。谭莹《听涛楼歌为伍春岚作》:“勳华何者足千古,山水真能移性情。顾我独嗟尘网撄,行窝隔江还隔尘”。当人远离复杂喧嚣的世界,“近睇遥瞻,仰属俯映”于这宁静致远的园林空间中,便超越了世俗物质的空间而进入虚静的诗意空间,文学赋予了园林以生存论的文化意蕴。
除了乔松逸竹等传统意象,荔枝和荷花作为具有岭南地方文化色彩的物象景观成为行商园林的审美喜好。万松山房“十亩芙蕖尘隔断,不知身在水云乡。”南雪巢“门外陂塘数顷,多种藕花。张维屏有句云:半郭半村供卧隐,藕塘三月脊令飞。盖纪实也。”海山仙馆万荔环植,红蕖万柄,“荷花世界,荔子光阴”是文学书写中频频出现的最得人欢心的地方文学意象。荷花世界的闲静淡雅与荔子光阴的热闹华妙自洽而又圆融,世俗生活的富足与性灵世界的舒展在岭南行商的生活经验中并行不悖。“士商两个群体的文化特色,如清净淡雅的文人园林所体现的精英文化与奢华功利的商贾园林所体现的世俗文化,各自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变化所反映出的融合趋势是不容置疑的。”[4]
“空间不仅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场域,还是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对象化载体。”[5]行商园林文学书写因文人情感和想象的介入,成为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生活美学、精神追求、审美意趣的对象化载体,赋予了冷冰冰的园林以生命的细节和精神向度的表征,将业已亡佚的地理物质空间提升转化为心灵的诗性空间。
自然的园林空间虽能一惬素心,却远不能满足文人雅致的精神追求,行商们更加热衷于将园林打造为文化雅集的互动场域空间。潘恕“所居双桐圃,春秋佳日,觞泳无虚。君好佛、好客、好书、好画、好笛、好花,力勤性朴,乌衣子弟,居然名宿。”①黄任恒编篡:《番禺河南小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雅集文化场景作为文人集体风流忆念的承载,不断呈现于园林文学文本的书写中。伍崇曜的西园中“书库琴亭,于焉啸咏”,伍元华的听涛楼内“爱君论座帖,半日作书傭”,潘正炜的清华池馆中“文字留题钗股折,水天同话酒杯深”,潘正衡的菜根园中“高朋偶聚盟鸥鹭,古帖闲评重汉唐”,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内“萧斋旧制多藏画,吴舫新裁称踏莎”,在美丽清雅的园林空间中,水天同话、诗文啸咏、鉴画论帖、登览游赏等雅集活动安顿着焦灼的精神世界,重现晚清广州文化交游活动的盛况和荣光。这些雅集赋予园林空间以文化的意义,“使一个原本寂寂无闻而拥有美景的地方,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甚至名留青史的胜地。”[6]
园林书写不仅是文人意趣和精神情结的承载体,同时发挥了以文存园的文化价值。在行商园林中,文学书写最为集中的当属潘氏家族花园。潘氏家族崇尚文化的风雅传统让历任园主多致力于园林文化场域的营造和文学的书写。潘有为所居六松园“擅园林花竹之胜”,“画善设色花卉,诗名藉甚”,他的诗集以其园林书斋“南雪巢”命名。潘正亨“弱冠能文,以善书名,尤工诗”,其诗集名为《万松山房诗钞》。潘正炜建听帆楼收藏法书名画,自命为“听帆楼主人”,一时名流群集于此,其诗集则命名为《听帆楼诗钞》,以心心系念的园林书斋、楼亭等作为诗集的命名。这些园主以其自身的文化声名提升了园林的传播效能,他们的文学书写让园林剥脱了商人的铜臭味而拥有了更多的文人气质、文化资本和声名传播力,潘氏园林历经百年而传承弥新与此有莫大的关系。除了园主自身的书写,潘氏花园雅集频仍,吸引了大量的名士为之作文,翁方纲、张维屏、谭莹、黄培芳等均是热心的园林咏赞者,这些访客群体的诠释与推崇为园林形象的传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谭莹作为行商园林雅集和文化建设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对园林的文学书写不遗余力。《粤雅堂记》《远爱楼记略》《春晖池馆春禊序》《还石轩记》《题听涛楼为伍春岚作》《万松山房夜宴赠春岚》《春日过潘比伯临万松园赋白秋海棠》等园记园诗以难以忘怀的口吻记录了他所参与的园林雅集活动,在称扬园主们的个人魅力和秀美的园林景观之外,尤为突出这些园林在岭南文人交游和文化建构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笔墨文章因为不朽,其生命长度远胜于园林本身。”[7]行商园林实体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文学的空间想象发挥了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作用,将园林的精神图示历历呈现,让业已消逝的园林以鲜活的姿态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并逐渐固化为地域文化系统的重要符号。
三、园林绘画的空间建构
中国古典园林与绘画作为姊妹艺术,具有密切的天然联系。园林常常以画图为蓝本,有意创造出具有绘画范式的景观来,营造“尽日楼台住画中”的诗意栖居意境。作为诗画雅集的重要场域空间,园林往往成为绘图的重要素材,从而创造出空间感知和视觉形象的美妙交叠。与园林的文学书写相应,绘画以其独特的观看视角再现园林的审美文化要素,二者共同展开了对园林的空间想象与呈现。
行商园林是晚清岭南绘画生产和传播的重要空间场域。不少行商具有较高的书画素养,或精绘事,或精鉴藏,且与岭南知名书画大家往来频密,这些文化活动大多展开于美丽的园林背景中。伍崇曜回忆“先伯东坪观察,归田后留心著撰,兼工绘事。故与谢里甫太史、退谷上舍、张墨池孝廉三先生,交谊特深。”①黄任恒编篡:《番禺河南小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页。“东坪先伯”即伍秉镛,其人能诗善画,时相过从者谢兰生、冯敏昌等人皆是粤中绘画名家。潘氏家族后人潘飞声的回忆同样充满精英式的荣耀感:“先曾祖分转公,向慕黎二樵先生。购其诗书画,悬之一室,颜曰黎斋……海外名士游岭南者,靡不知黎斋。一时文宴,五羊称盛。”①黎斋的海外声名广播得益于绘画这一生产方式对园林空间的文化型塑。
岭南士商的园林雅集往往伴随着园林诗与园林画的同步实践与生产。画家陈务滋曾经画过两幅唐荔园图,图卷上收录有四十多位文人的诗与题跋。伍元华所筑听涛楼,著名画家谢观生为之绘图,伍有雍、颜元任、吴荣光、黄德峻等25 人作有题画诗。海山仙馆的贮蕴楼更是频繁上演着图与诗的互动:“道光壬寅七月廿九日,宴集海山仙馆之贮韵楼。熊笛江孝廉绘图,叶庶田农部作诗先成,诸友次韵题图上。”②同①第259页。后潘仕成邀夏銮作海山仙馆图,图中附有多位诗人政要的诗文题跋。诗画雅集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能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比较真切地还原不同阶段、不同情境里中国士绅们社交性文艺活动的实态”[8]。这些活动示现了文学与绘画文本的互文交织,同时真切还原了晚清广州主流文化圈园林诗画雅集交往频繁的文化特质。
在传统书画的鉴赏和生产之外,行商园林以其文化场域的开放性和巨大的吸引力,与晚清外销画产生了密切关联。行商园林作为广州城市的标志性景致,成为外销画最受欢迎的素材之一,其中西融合的情调和奢华富丽的装饰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及富商生活的认知需求,甚至一度影响了西方的造园设计风格。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物,外销画拓展了岭南园林的传播空间场域,赋予了传统园林以现代性的内涵。
高居翰提出园林绘画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作为视觉记录和美学再创造”[9]。超越于视觉记录的记忆功能之外,画家们对行商园林展开了富有意趣的空间呈现和美学再造,丰富了园林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广州现存的岭南名园比之江南园林、华北皇园,规模上显得娇小,其价值地位也容易被低估,但绘画媒介下的行商园林却突破我们的认知局限,在空间营造上呈现出自信大气、富丽堂皇的审美观感。夏銮所绘《海山仙馆图》乃海山仙馆全景图,绘画镜像中的这座冠盖岭南的园林池广园宽,风廊烟溆,迤逦十馀里,宏规巨制,炫人眼目。此种空间观感在美国人威廉·C·亨特的笔下得到了印证:“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③威廉·C·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
除了规模的宏伟,奢华富丽是行商园林带给西方人的普遍感觉,这种审美观感在外销画中尤为凸显。庭呱所作外销画《清华池馆》乃海山仙馆局部图,画中建筑不同于夏銮《海山仙馆图》中朴实的竹木构筑,转而变为富丽堂皇的雕梁画栋。虽因中国画与西洋画技法有异,但这样的空间呈现无疑迎合了西人对于行商园林的审美想象。这种审美想象可与亨特的《旧中国杂记》形成图文互证:“住房的套间很大,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③亨特笔下的海山仙馆拥有东方式的华丽,且具西方异域情调,与庭呱插图中的想象是一致的。传统绘画中的行商园林于大气中包裹着优雅的文人气质,外销画中的行商园林则在大气中流露出世俗的富贵风华,它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人们对行商园林的审美认知。
不同于传统的园林山水写意手法,行商园林绘图尤其是外销画在园林景观的展现上,多忠实于真实自然,显露出具有写实性的地域文化特征。行商园林绘画中的景观要素极具岭南风味,建筑物、植物、水体完美融合,自然天成。建筑布局多呈迂回曲折、迤逦多姿的雄伟之势,轩窗敞宇,大气四开,长廊跨湖,水榭回绕,将台池楼观之丽尽现于前。时人黄恩彤对海山仙馆的自然景观有这样的描述:“跨波构基,万荔环植,周广数十万步,一切花卉竹木之饶,羽毛鳞介之珍,台池楼观之丽,览眺宴集之胜,诡形殊状,骇目悦心,玮矣,侈矣!”①广州市荔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荔湾区政协之友联谊会、广州市荔湾区荔苑诗社合编:《历代名人咏荔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与上述文字相应,荔枝、芭蕉、圆柏、松树等地域植物以及让西方人啧啧称叹的盆栽花卉构成行商园林绘画的主要景观要素,它们长势苍郁、错落有致,与台池楼观、山水跨波形成虚实、动静的互补,营造出岭南园林水乡的地域景观特点。
在行商园林绘画中,景观空间中时有人物活动耦合其间,向人们展示着园林空间是如何被体验和使用的。夏銮的《海山仙馆图》中,有士人或在窗前读书,或在游廊漫步,或有人骑马来访,或宾主间拱手相送,充满着中国传统文人化的身份标榜和欢愉雅趣。相较于传统园林画的高雅清逸,外销画则热衷于展示行商的家庭世俗生活和日常交际场景,女性成为园林空间的活动主角。《清华池馆》《亭阴赏荷》《故园旧事·夏·对弈》《中国阳台风景》等外销画深入到行商园林曲径通幽的生活空间,女性们游园、雅集、对弈、弹唱、聚会等家庭生活场景成为最常见的表现题材。这种对私密空间进行窥探的审美视角显露出西方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浓厚兴趣,也为我们留下了作为时代符号的文化表征,从而构建起起鲜明的地方感:“画作中的地理标志物与象征性符号,会唤起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情感记忆,也能满足尚未游历中国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10]
图像作为“视觉表述”的形式之一,并不被动地反映现实世界,一如镜子映照出来的影像,而是主观整理后具有视角呈现的某种“观点”。透过画家们的主观思想滤镜,园林变形成为绘画镜面上具有独特视角的影像。行商园林绘画的空间营造方式,所选取的景观、主题与情境,何尝不是画家对于岭南园林富有意味的审美呈现与文化建构。相较于文学文本,绘图的图像化诠释方式更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外销画对西方世界的敞开更是增加了传播的受众面。行商园林的真实空间几乎无一保存完整,园林绘画以视觉记录的方式再现这些花园的当年辉煌并赋予其意义与价值,发挥了实现园林文化增值和不朽延续的鲜活效应。
结语
社会空间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互动近年来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透过对岭南行商园林空间转向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园林、文学、绘图互相激发,彼此增益。园林为这两个领域的文本提供生产场域和表现话题,文学和绘画作为行商园林文化生产的主要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语言和视觉媒介的方式介入对园林的空间想象,共同发挥着作为文化表征的空间建构作用。经过文人之感受力的独特加工,文学和绘画赋予了自然景观以生命力,使行商园林的精神、审美、文化意义得以彰显,从而实现文化的增值和声名的传播。
岭南行商园林的真实物质空间已基本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文学和绘画作为园林场景记录和空间想象的承载物,持续唤起人们对园林符号的情感和历史记忆,以实现地方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延续。对于业已消失的行商园林文化的复原,诗画艺术的价值和潜力是不应忽视的研究面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