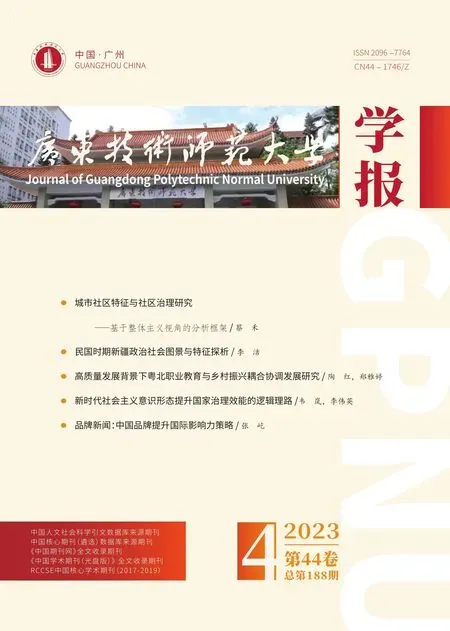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图景与特征探析
李 洁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民国时期的新疆偏安一隅。在1943 年1 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并真正影响新疆时政之前,自主政者杨增新起至盛世才统治后期,均着力于维持新疆“独立王国”的局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既保持联系又并未深入,与周边帝国势力则保有微妙联系。政治经营中,不同执政者的理念既有承继又存区别,新疆彼时虽较内地军阀争斗而言相对平静,但动乱亦时有发生,地方社会运行中既有一些通弊,也存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层面的弊端。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的专门探讨与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研究多从某一层面论及新疆政治,如从地方各级参议会的成立、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探讨民国时期新疆政治近代化问题①贾秀慧:《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近代化述评》,《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或就乡约的职能转变探索基层政治运行②赵丽君,黄林辉:《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新疆地方志》2018年第1期。;一些研究从学校教育着手,如王顺达聚焦于留学生与新疆政治进程、政治体制变革的关系③王顺达:《赴外留学生与民国新疆政治》,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或就国际因素透视民国时期新疆政治运行及边疆问题④段金生:《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聚焦于民国时期政治的整体性研究,则见于买玉华对于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政治与社会的系统研究⑤买玉华:《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政治与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版。、姜刚以军阀政治为主线对于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变迁的整体性梳理与研究⑥姜刚:《军阀时代——清末民国新疆的政治变迁》,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其中个别研究已涉及考察文本资料,而当我们将视角转向以考察文本为资料主体的民国新疆政治社会探讨时,文本对政治格局某一事项或层面相对集中的书写,使得历史镜像中的民国新疆政治更为具象化,考察家的个人体会与思虑也一并添入其间。
本文拟利用考察文本的各类记载以呈现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图景,藉考察家的深描与个体认知把握这一时期各方势力的交错、博弈,进而析出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运行特征。考察文本可循的政治图景脉络大体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类军阀政治的掌控
依据学界对于军阀政治的界定,姜刚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时期的特征归纳为:“无一例外地都依托忠于自己个人的军队掌控政权,统治着新疆这片辽阔的地域,并且与虚弱的中央政权呈现出一种游离的态势”①姜刚:《军阀时代——清末民国新疆的政治变迁》,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页。,将之视为一个军阀政治的时代。以“军阀政治”理解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为我们审视民国时期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政权更替及政治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维度,也是探讨政治社会运行特征的要素之一。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位历任主政者,前两者均为文臣,仅盛世才可称之为武将。若论私人军队,则杨增新时期的弱兵政策似乎与之相悖,然而各执政时期的即有军队力量却均掌握于三位手中,虽与彼时甘宁青马家军阀有所区别;就三位主政者的行事准则而言,执政期内无一例外地由一人决定新疆之一切民政,任何策略均以保全新省与个人专政为基准。基于以上,笔者暂以“类军阀政治”这一概念作为梳理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主线。民国时期新疆无论是处于相对稳定且迟缓发展,抑或如盛世才统治时期一度获取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均于其中清晰体现着军阀政治所特有的地域社会个人专权本质,这就必然造成地方与中央的分离性,以及与政治近代化的背离。
(一)类军阀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杨增新执政时期的新疆时政多通过当时的档案、文史资料、回忆录及杨增新本人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等获取相关信息与脉络,而当我们聚焦于考察文本时,所现信息既是对传统资料的回应,也可见其延伸与深化。林竞于1918 年第二次入新考察,记有“旧地(迪化)重来,城郭无恙,人亦无恙。念内地屡遭乱离而新疆独能晏然,羡望之情,又曷能已也。”②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彼时内地军阀混战,而新疆维持着至少表面上的平静,杨增新彼时对外之于边境、对内与内地之间交通信息的严格封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动荡时代新疆的安定。又有徐旭生于1928 年带领西北科学考查团于哈密见餐馆“座前贴有‘莫谈军政’字样。吃了不少东西,价只七两多银子,若比北京,可谓价廉。”③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无论是“莫谈军政”,还是“价廉”,均是对杨增新时代政策及其影响下新疆时局的呈现。刘文海1928 年途经哈密,有感于“奈地方当道,一味疑忌国内较有知识之分子,而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先驱如所谓科学考查团,基督、天主教传教士,反不敢有所留难。言念及此,诚觉灰心”④刘文海:《西行见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一方面回应了杨增新执政时期对于内地尤其知识、信息泄入新疆的戒备之心,一方面则显现着边疆面对帝国势力的无奈之举。上述三位考察家的记述与感受,大体描绘了杨增新执政时期的统治特征:严控疆内,隔绝外界,维持较为平静且缓慢的社会发展。对于杨增新本人,则存有对其强硬政治手腕下维持一方稳定的赞赏,与对于治新理念“固守”“守旧”的否定这两种观点。
金树仁执政时期因较短暂,后期又逢战乱,致使东向自内地进入新疆的星星峡关卡设防严密,西向之于外国考察家探察活动的阻隔亦较多,所以这一时期鲜有考察及相应记载。
1933 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得以上台执政。在其长达十年的治新期间,与国民政府、西北地方军阀、苏共、中共等各方势力的联合、虚与委蛇或决裂使之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也影响了民国中期以后的新疆政局与社会发展进程。盛氏执政时期恰与抗战重合,新疆成为大后方转运来自苏联方向的国际援助物资,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以及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激发了这一时期国人考察新疆的热情,旅行书写遂载有盛氏执政时期的一些时政要闻与印象。如时任《申报》记者的陈赓雅于抗战时期赴西北各省考察采访,有感于“二十二年‘四一二政变’后之新省府,其行政系统,除改组原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外,并添设一农矿厅”①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49页。,对于这一时期盛氏政府运行给予肯定。当时新疆在财政、实业、教育等事业方面的发展成绩,亦有张大军所书《新疆风暴七十年》中引用的一系列统计数字予以佐证。此后李烛尘于1942 年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工业、矿产开发,抵新时恰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及大批军政要员进入新疆之际,因而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多方政治势力:先载盛氏政府与苏共之关系,“为与苏联取得密切关系,故其一切政治作风,不能不有所袭取,而中共以往在新疆活动者,或亦不乏其人,然均未尝根本影响其形态”;其后是与国民政府之关系,“当考察团到新之日,适为新疆政治与中央打成一片,……乃于党部成立之日,全省无论何处,均飘扬党帜,同时三民主义,与建国方略者,汉、回文书各数千册,即于同日发布出来,分送党员,可见其用心之深细”;最后谈及盛世才执政时期的时政印象——“新疆当局,因于政治上之警觉性,特别提高,故对于反对之主张及言论,决不相容。……又其各级政府组织,似为各机关绝对对领袖负责,而相互间之联系,比较清闲,故新疆当局之命令,可以贯彻到底。……总之新疆自得盛世才督办十年苦心经营,确已将西陲一片土,保持住了。”②李烛尘:《西北历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在现有国内考察家相关记述中,《西北历程》是较为详尽呈现盛世才执政时期政治特色及权力博弈的文本。对于盛世才治新,李氏从边疆视角给予充分肯定,并突出这一时段严控言论、绝对权威的特征。总体上,考察文本显现着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在财政、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绩,认为这与政府组织结构的改组、发展实业有关,权力博弈则凸显为盛氏与国民政府、苏共、中共三方势力的周旋。对于盛世才的评价,兼具对于其勤恳、敏锐、力兴工业的赞赏,及国外考察势力对于盛氏“亲苏”、摇摆于各种势力之间的贬斥。
(二)关于时政的整体认知
对于民国时期新疆时政的整体认知,主要呈现于民国末期最后一任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的夫人戴安娜·西普顿经由长期观察的回忆录中。其于国民党实质性接管新疆后在喀什噶尔生活了短暂的两年,她如何看待自己到来之前的新疆?其中《古老的土地》回顾了民国不同时期新疆社会的情形:“从1911 年中国改制为共和国后,一直到1924 年,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一直有名无实。而只有一些汉族人作为个人在这个地区掌握着权力,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对新疆的治理归功于中央当局。总督杨增新对新疆的治理极为严格但也非常高明,很有谋略。……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像杨增新这样的人的独裁治理方式,僵硬但有效,精明而强制,是治理一个简单的农民社会的最好政府形式。我想,他们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事实上,就是在杨的统治下,新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繁荣,都要安宁。杨增新死后,新疆就一直处于叛乱蜂起的状态中,局势非常复杂。内战不断,各方割据,各自为政,是这一段时期历史的特征。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苏联苏维埃政府的作用却日见增长和强大。……后来,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一位汉族将军盛世才,开始控制整个新疆省,新疆才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在一个新式独裁者的统治下,这片土地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安宁和繁荣。……然而,取得这一切,他和这个省都付出了代价。不管盛本人的意愿如何,他都处于俄国人的强大影响之下。”③[英]凯瑟琳·马噶特尼、戴安娜·西普顿著,王卫平、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页。以上戴安娜的印象、见闻与亲历,与前述国内知识精英的认识相印证,且有所拓展:一则展现了民国时期新疆与中央政权的疏离——“有名无实”,无论是边疆的实际运行,抑或执政者的认知均如是;二则凸显杨增新、盛世才治理新疆不同路径下的有效性,“稳定”与“繁荣”殊途同归;三是强调盛世才时期苏俄势力影响之强势及盛氏政府付出的“代价”。
关于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史载大体涉及两个层面或称之为“问题”:一是新疆与中央政权的若即若离,于周边国际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并被牵制;二是新疆内部政治经营中的强权政治、派系权力倾轧及时局动荡。现有考察文本主要聚焦于后者。刘文海于金树仁执政时期入新,在其考察日记《西行见闻记》感叹道:“新疆迄今克保卧病状态,并非士兵训练有方、为政用人得当,乃此漫天弥地大沙碛之力也。新疆当道,一味泥古专制,故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亦受直接影响。教育不堪过问,工业并未进步,……又如商业为人民经济生活与省政府岁入所赖,竟亦自加摧残,令人莫名其妙。……总而言之,新疆之专制固蔽,可谓今世独一无二之区域。”①刘文海著:《西行见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无论是刘氏的政界身份,还是其体察新疆政治的视角,均为立足于中央政权看地方政治,强调新疆政治的症结在于历史专制的延续,与已处于相对“民主”“现代”的南京国民政府、内地政治存在差别,革命的烈火燃至边疆却未有实质性效果,致使各项社会事业均无进展且日渐衰败。新疆政治问题的核心在于专制,刘氏论及相应策略:其一,“铲除专制魔力”,“保障邮电交通,遴派忠实人员,举发枉法虐民恶吏”;其二,“严防帝王思想之野心家”,直指类军阀政治。其于考察文本中的策略延伸至社会发展层面,提出“注意维持次序”与“提倡殖民实边”。关于民国末期的新疆,戴安娜·西普顿在《古老的土地》中记有:“在这里政府没有给人民修建医院,盛世才修的学校已经渐渐破败不堪。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在交通和工业方面新疆全省都是大大地落后了,情况非常不好”②[英]凯瑟琳·马噶特尼、戴安娜·西普顿著,王卫平、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为什么民国末年的新疆破败不堪?这位最后一任喀什噶尔总领事夫人从他者视角看中国及新疆,认为主要在于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控制与影响力不足,忙于战事的南京政府无暇他顾,也源于边疆社会发展基础的薄弱制约了现代化进程。上述两位考察家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将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的症结归于不同之处,所论“区域专制”“中央政权不力”而致使“社会发展迟滞”等确为这一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弊端所在。
考察文本的具体描绘,让我们得以从微观视角透视宏观历史,从地方窥视整个时局的特征与变化。上述民国时期新疆时政特征,是中央政权治理边疆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既显现了新疆与中央政权的疏离,又有边疆地方运营的有效性,同时边疆还处于外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无论中外考察家,均有上述较为一致的体认。关于时弊,国内考察家着重关注地方“专制”、帝王野心,外国考察家则聚焦于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控制与影响力不足,及边疆社会发展迟滞。从文本所现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运行及弊端来看,边疆地方的自在运行及与中央的疏离,历任统治者的专制,均反映着军阀政治特色,凸显的割据性是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的症结所在,也是政治近代化失败的根源。
二、与内地的疏离与协作
民国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联系程度如何,相应的道路网络建设是否畅通,与前文所论类军阀时代主政者的政治理念有关。意在“孤悬塞外”还是与中央保有一定程度的沟通,呈现为新疆与内地之间于杨增新时期的“隔绝”及此后主政者的逐渐“开通”,实则关乎中央势力是否通达边疆的治理实质。
民国前期至中期赴新考察的国内外考察家,均以各自的观感记述了杨增新时期新疆与内地联系的阻隔及此后的变化。1919 年林竞因勘测路线抵新,与杨增新论及交通,“相与谈中央计划交通事,渠数年前,对于新省交通颇为冷淡。盖以交通便利,则内地不安分之徒,来者愈多,而新疆亦将投入旋涡。故不如暂抱闭关,使其无法前来。同时又将不安分者驱逐出境,庶几乱源减少,治安适易实现。”③林竞著:《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以此显现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与内地交通阻隔的主要缘由——偏安一隅,“闭关”以避乱,即杨氏所谓“不开恩怨之门”,“不开奔竞之门”,“不开争夺之门”,“不开祸乱之门”,只有“天下之人皆塞其兑闭其门则天下太平”①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四,第五十二章。。林竞认为此法于“无外患而有内乱”时确有成效,但一旦出现外患则“无异自绝”,“故自俄乱发生以后,伊、塔各处,纷纷告急,新疆颇有呼应不灵之感,而杨督之态度,亦因之而变。视余之来,甚表好意,云中央苟不办,新疆亦将自办云。”可见遭遇伊塔边境危机后,杨增新对于交通开发的态度有所缓和,这一变化依旧源于维持新疆稳定。上述记载显现了杨增新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对于新疆内外交通发展的区别认识与变化,这有别于以往史料中对于杨氏“ 闭关”思想始终如一的相关记述。1926-1941 年间修女三姐妹于西部行走,记有“由于欧洲大战(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及俄国革命的反响,中国的新疆省长甚觉不安,恐惧感促使他实行严厉的边界管制。护照、许可证、地方通行证,以及其他数不尽的书面文件,开始困扰旅行人……接着,在叛乱和革命震撼中国及其‘新疆域’的几年当中,边境的规定益形严格,沙漠商队往往必须在猩猩峡难以形容的破烂旅店中待上十多天,等候当地驻军司令和远在乌鲁木齐的省长交换信息,因为每一个行经猩猩峡的人皆须获得省长亲笔批准。”②蜜得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著,黄梅峰、麦慧芬译:《戈壁沙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谈及杨增新时期出入新省境管制严格的几个因素:一战与俄国革命,内地的叛乱和革命,即以一切乱源为由。彼时星星峡作为内地与新疆之界,商队、旅人均被阻拦于此,等候获准方可入境。1930 年代入新的天涯游子记载了时人对于杨增新执政时期内地与新疆交通阻隔的认识,“据当地人民传说:新疆在前任杨省长任内时,完全同外界隔绝。”伴随着新疆与内地交通的管制与阻隔,与外界信息通讯闭塞,报刊、电报等一应被列入严查范围内,一并导致彼时新疆的闭塞与隔绝,而“现在随着这位闭关政策的杨省长的去职,新疆已换成为一个新面目了。”③天涯游子著:《人在天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在政权由杨增新向金树仁过渡的一段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基本延续杨氏执政时期的导向,刘文海于《西行见闻记》记有“十六七年交,新疆当道借口防止乱源,毒井塞道,断绝交通,一时繁荣商业,遂命运中断。”④刘文海著:《西行见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与前述一致,阻隔的缘由在于“防止乱源”,新疆“孤悬塞外”之状清晰可见。具体至星星峡处的通关条例,规定“凡骆驼入新疆境,均须在哈密挂号听差,驮过两次军粮,方准其驮货出境。”⑤同④,第95页。将驼队作为暂时的军需运输力是哈密当地劳动力欠缺的表现,也是星星峡关口处理入疆商队的一种策略,是地方对杨增新时期严格管制边境的变通。
萨空了于1939 年运输新疆所需文化建设物资至星星峡,在《由香港到新疆》中详细描绘了过境情景:“新省入境的限制比较他省为严,目的在防范汉奸的混入。过去新省曾捕到过化装日人潜进边境,当局遂决定了凡是甘肃逃来的老百姓必须在星星峡留住三星期,作为考察时期,在这期间,有钱的人,新省合作社可以卖米粮给他们;赤贫的老百姓,星星峡也有赈济机关可以施赈,同时还可以在星星峡作临时的劳工。新省人力缺乏,在星星峡作一日的散工,像担水挑泥,全无技术可言的工人,工资为新省法币一元五角,这个数目足够他们在当地吃饱肚子还可有些余剩!三周之后准予入境,但仍不能到哈密以西,只能在哈密以东居住,……政府所以限制他们西移,是因为哈密以东人烟稀少,劳力最缺,希望移殖民众在这一带定居,可使地方建设进步较速,但因为哈密以西工资更高,迪化可有二元半一天,他们都希望更向西移。”⑥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158页。可见,盛世才执政时期尽管整体上放松入境管制,但至抗战时期因防止汉奸潜进与难民大量涌入,于特殊时期收紧了出入星星峡的政策,论其本质,与杨增新时代基于新疆“完整性”的“避乱”缘由一脉相承。星星峡作为一个临时的入新集散地,集身份查验、补充劳动力、鼓励移殖等各项功能于一身,既与前述民国中期的过境地方策略相似,又更为多元、精进,其中鼓励难民就近移殖的目的更为明确,与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国家整体战略、边疆策略一致。除省际交通阻隔之外,在萨氏文本中还呈现了这一时期内地与新疆的沟通联系——省际交通协作。其一为萨氏行前曾请新疆省政府通电沿途各省政府予以保护及准免过境捐税,行至南宁时,“从厚厚的档案中,他们找出了广西省府的一个照转新疆省府通电准予照免各税的电令,於是我没有用一个钱就过了这个关。”①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5页。其二为抵重庆后,“西北公路局答应借给我们五辆汽车,自重庆拨给,一直帮我们把东西运到新甘交界的星星峡为止。汽油机油,则答应我们自川陕边界广元站起借,沿站供给直到星星峡为止。将来全数由新省在星星峡拨还。”②同①,第57页。可见,当时新疆与内地各省之间以电报通讯可达成一定协作。以往研究多论及新疆“孤悬塞外”,此间省际联系相通与配合协作,或源于抗战期间的区域通力合作,却为我们打开了认识民国时期内地与新疆交流沟通的另一扇窗。
至1942 年末李烛尘抵新考察时,正值新省传统政治势力——盛世才倒台、国民党政治势力进入新疆,新旧势力交替、中央与地方势力交接之时,李氏一行将至星星峡,“过十余里,即入新疆辖境。公路至此较劣,而路旁全无路标,令人发生一种‘两不管’之感想。下午五时至猩猩峡,新疆省之检查所在焉。”③李烛尘著:《西北历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由此可见,星星峡于民国时期一直作为省际过境的关卡,即使至民国末期。所载情形既呈现了甘新两省经历战争灾难的凋敝与省际差异,也用“两不管”透露了作者视野中省际联系的疏离。
以上考察文本所现民国不同时期新疆与内地联系的表象与特质,意味着联系畅通与否的关键在于新疆统治权威的“避乱”、保证新疆“安定”思想,因而杨增新的“孤悬塞外”与“闭关”策略得以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延续着。地方策略在国家内部区域协作中突显,地方权威所确保的“地方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国家内部区域间的连续性,当然也由此奠定了其于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可能性及地位。同时,文本所载抗战时期新疆与内地交通的一定联系与协作,无论是特殊时期的区域协作亦或省际策略,都意味着区间协作的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得以增进。
三、城镇景象中的二元性
外国考察家文本深描下的城镇景象较为多见,或为南北疆重镇,或为商贸街市。城镇风貌在呈现小型社会发展进程与特征的同时,又是区域政治社会运行的映射。
瑞典突厥语语言学家贡纳尔·雅林于1929-1930 年随瑞士传教团进入喀什噶尔,其考察文本《重返喀什噶尔》呈现了民国中期南疆重镇喀什噶尔的影像。关于喀什噶尔,先有清末最后一位及民国首位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夫人凯瑟琳·马噶特尼记录了清末景象:“喀什噶尔有两座城,一座是旧城,也称之为回城,……中国的行政机构就在回城。……提台是地方军事长官,他驻在汉城,……喀什噶尔新城在旧城以南7 英里处,面积比旧城小。那里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汉族。”④[英]凯瑟琳·马噶特尼、戴安娜·西普顿著,王卫平、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显现了清中期以后汉回隔离政策下的“分离”镜像,对此林恩显评述“于清朝统治利益而言,于治标上不失为一可行方策;在新疆地方言,有保护之利,闭塞之害,利害各半;在整个中国、大中华民族而言,阻碍了国家统一、国族团结,实百害而无一利也。”⑤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3页。凯瑟琳于文本中呈现了喀什噶尔传统城池的格局与功能,“城墙”“城门”“护城河”等中国传统城市格局的建设规制因其形制与彼时世界城市发展形象格格不入,令外国考察家格外注意。
贡纳尔·雅林亦论及上述城镇印象,只是时间流转至1929-1930 年民国中期:“在那些年代,喀什噶尔城被大约10 米高的结实的城墙环绕着,……与外界的交通是通过4 个巨大的城门进行的,城门暮闭晓开。……中国政权机构在城外,在城外的还有英国和俄国领事馆,瑞士传教团以及它开设的医院和其他福利机构。城外绿茵处处、阳光灿烂,而在城里却总是半明半暗。”①[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译:《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上述描绘更具象化,可见汉回隔离制度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在贡纳尔·雅林眼中,缺乏“内核”的回城日益没落而仅余传统,汉回二城分别对应着时代新气象与老旧传统。然而,当贡纳尔·雅林深入老城(回城)内部,却非死气沉沉,传统社会的运行、人群流动及经济运行因增添了外部元素的影响而呈现着另一番气象:“喀什噶尔老城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安集延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欧洲货,大部分都是在俄国制造的,但经常也有印度出产的东西。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信号,也是喀什噶尔会很快现代化的标志,但暂时还只仅仅是一种迹象而已。一般来讲,那时喀什噶尔的人们还不完全了解现代文化的优越性。所有那些无法理解的技术性产品都被称作shaita(撒旦),即与魔鬼有牵连的东西。有一次,一个汉族人带了一辆自行车到喀什噶尔,当地人把它叫作Shaitan arbcsi,意思是‘魔鬼车’。而那个流动出售图书和古董的商人肉孜·阿洪第一次听我带去的唱片时,他把唱片音乐叫做‘Shaitan naghmasi’即‘魔鬼音乐’。……安集延区是喀什噶尔的现代部分,它指向近在门前的未来。”②同①,第69页。以上对于喀什噶尔老城日常的描绘,呈现了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的边疆重镇:传统的一面是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的,相较当时内地传统日常生活更为陈旧与滞后的文化印记,较传统更为边缘;现代的一面,则源于安集延区贸易的繁盛与“现代”元素。对此,凯瑟琳·马噶特尼在其回忆录中对于民国初期的喀什噶尔亦记有:“我刚到喀什噶尔的时候,巴扎上几乎见不到外国货。……想一想这座城市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老样子,它的街道,它的巴扎,都古风依旧,让人感到这一切真是妙极了……但是,我到这里不久,这座城市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里的裁缝们也开始用上了‘辛格’缝纫机。但是,在黑糊糊的狭窄的巴扎街上阴暗的小铺子里,一个人跪在那里使用这种缝纫机,却让人感到有点不对劲。”③[英]凯瑟琳·马噶特尼、戴安娜·西普顿著,王卫平、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相关记载是外国势力渗透南疆的鲜明佐证,喀什噶尔作为英俄势力在南疆盘踞的重镇,所受影响与冲击无疑在南疆诸城中最为深刻。外国考察家记录中的喀什噶尔,在散发现代气息的同时伴随内部的传统与陈旧,城市运行与发展的模式透露着矛盾与风险,国家影像于其间并未产生波澜。
此外,三位修女一路西行至塔尔巴哈台所见所闻也留有类似记载:“在楚呼楚(即今塔城),俄国移民引进一些对生活较便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划分出东西世界的不同。……在这个地方,西伯利亚的面包师傅不但会做普通面包,有时还会烘培出一盘小甜圆面包或奶油蛋卷,或制作西伯利亚蜂蜜、山草莓果酱,还有水果口味的甜点供人购买。”④蜜得蕊·凯伯、法兰西丝卡·法兰屈著,黄梅峰、麦慧芬译:《戈壁沙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沙俄在北部边疆重镇塔城的长期渗入,使城市呈现着俄式风貌,俄式道路规划建设、建筑风格及饮食元素,让我们看到了民国中期苏俄势力在北路边疆重镇影响之深刻。
上述城镇风貌既是外国势力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持续渗透的结果,也是对于渗透作用下城镇差异发展路径的阐释。边疆城镇既延续着陈旧滞后的传统、边缘印记,又因英俄势力渗透而呈现现代性,城镇运行与发展模式透露着地方传统与外部现代性渗入的交织,亦为地方政治与外国势力的绞缠。外国考察家描画着边疆城镇印象,字里行间不乏对于异域风情、东方传统的渴望与怀念,以及对于现代元素渗入的不适,然而这种感知与惋惜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投射。
结语: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运行的特征
对于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认知与探讨,传统上多聚焦于新疆的“孤悬塞外”而与中央疏离,间杂着英俄势力渗透,以及主要探讨不同执政时段的特征。依据考察文本的深描及整体刻画,结合上述三方面,笔者大致将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运行及其特征进行下述不同类型的归纳:
其一,基于地方社会政治运行的主体性因素,主要呈现为:既有各执政时期政治经营格局基于军阀政治特色的延续与变革,又有社会进程中的传统延续与现代性的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前者的弱控制与后者的若即若离并存;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显现为强分隔与弱协作;国家政权与外国势力聚焦于边疆的角逐,前者艰难维系对应着后者的强势渗透。总体上,突显了多方主体的交错与博弈。
其二,政治社会运行图景的特征,体现为基于差异的多元复杂性,与内外危机的一致性。一方面,区域政治格局内部呈现个性与差异,类军阀政治赋予各执政时段持续的专制特色与特定时段的调整变革,城镇因战略地位、交通所在、国外势力渗透等存有不同发展路径,这些使得民国时期的新疆政治社会呈现多元化、复杂性。另一方面,由差异多元的各个局部窥视整体,又具有一定共同性,表现为:不同执政时段的差异性汇聚为民国时期边疆整体的政治状况——孤悬塞外,稳定与危机并存,以及中央对于边疆治理传统的延续、内地与边疆隔阂、国外势力盘踞等;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差异性的显露,则是外部势力渗透与边疆危机的普遍结果。若将多元化的特征予以追根溯源,则透露着一致性,即内部治理危机与外部势力渗透下的边疆危机。
第三,若追究政治社会运行弊端的根源,则在于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一为分离性,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新疆各区域之间,城市内部的汉回城之间,不同层次均存在疏离与张力,且与国外势力影响无法撇清。二为二元性,即区域间、城市间显露着发展变革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边疆城镇在发展中隐藏着深重的边疆危机。基于结构的分离性与二元性,回溯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运行的明显弊端,就在于中央权威建构不力、地方传统权威延续及类军阀政治本质、外部力量渗透三者交错并存,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复杂多元,这显然是民国时期边疆政治社会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