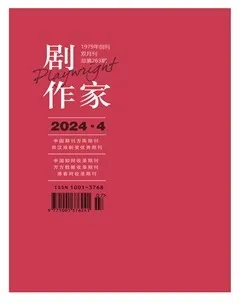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摘 要:上海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春秋二胥》对传统京剧中的伍子胥故事进行了重构,创作者希望通过对其进行改编来引发观众对于复杂人性的思辨,呼唤仁爱和善良。然而,他们对于传统戏剧情节的改编落入了道德绑架的圈套,对剧中主要人物的情感处理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于原故事中伍子胥面临的情感矛盾难题,新作不仅没能做到有所突破,反而体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性”理解的庸俗和浅薄。
关键词:《春秋二胥》;新编历史剧;上海京剧院;现代性
中国有两句古语,一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一是“睚眦必报”,明明都是复仇,仅仅因为怨恨大小就在句意上有着如此明显的褒贬之分,实在是让人费解,不过这两句话也从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胸襟坦荡的君子还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但凡有冤仇都会寻求报复。与之相对应的,无论古今中外,以复仇为题材的故事始终能够牵动人们的心弦,激发观众的肾上腺素,从而拥有众多拥趸。一夜白头的伍子胥自然是流传最广的复仇故事的主角之一,也正是因为他本身的经历足够传奇、足够热血,所以不停地被搬上舞台。京剧中更是衍生出一套完整的“系列剧”,从《乱楚宫》《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到《战郢城》等,讲述了伍子胥受冤逃国、借兵复仇的全过程,尤其《文昭关》向来是京剧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剧目。可当代的创作者们似乎并不满足于传统戏中伍子胥以一个“刚正、忠直、隐忍而又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出现[1]P71,为了表达所谓对复杂人性的“思辨”,新编历史剧《春秋二胥》被搬上了舞台。
这出剧目由上海京剧院创排,冯钢编剧,续正泰、白云明导演,对传统京剧中的伍子胥故事进行了改编创作。在表演上最大的改动便是让传统戏中由老生应工的伍子胥改为了风格更为粗犷狰狞的花脸应工,且延续了上海京剧院近年来成绩斐然的新编剧目的风格,像《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一样以花脸和老生应工的两个主要角色的对手戏为主。但同样的模式,同样是改编自传统故事,不同于前两出佳作所营造的悲剧氛围和表现出的人性挣扎,这出《春秋二胥》却让观者感到深深的不适。
剧中的第一个小高潮出现在伍家受冤十九年后,满腹怨恨的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势如破竹直杀向楚都郢城。面对兵临城下的窘迫,刚刚继位的新君昭王正一筹莫展。王后孟嬴不得已讲出当年平王丑闻和伍家冤案之始末,并举荐申包胥出面劝解伍子胥。因为当年义释伍子胥而被关押了十九年的申包胥痛陈当年往事。楚昭王则颇明事理,决定下诏书平冤案,并为伍家冤魂举行祭祀。于是乎,申包胥出城面见伍子胥以“人死百怨消”劝阻于他。后者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但一来感恩于申包胥当年的义释之举,二来悲悼父兄心切,便答应入郢城祭拜家人。来到楚国宗庙面对父兄灵位,伍子胥痛哭一番。楚昭王趁机宣读为伍家洗冤的诏书,并恳求伍子胥“开释前嫌,重修旧好”。得知楚平王已死且正“金棺盛敛”,伍子胥只好请求昭王归还他父兄尸骨,可“太傅蒙难,弃尸荒野一十九年”,早已无迹可寻。对于这一段情节,曹树钧教授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伍子胥索要父兄尸骨是一个“过分的要求”[2]P94。笔者不禁感到惊疑:试问一个人全家被害无辜惨死,仇敌尚且被金棺盛敛,亲人的尸首无有一口薄棺,希望冤死的亡魂入土为安竟然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吗?尽管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这个要求难以被满足,但于情于理也都算是伍子胥最低限度的诉求了吧。既然这个要求无法满足,伍子胥接着提出要鞭尸平王以泄恨。听到这话,楚昭王竟然无法置信,双手颤抖地言道“你的恨如此之切,竟不放过已死之人”,似乎全家三百口被冤死之恨不应该“如此之切”一样,也全然不顾这三百无辜之人正是死于这个金棺盛敛的“已死之人”。紧接着,伍子胥又提出或可以平王宗亲三百口偿命,自然得到昭王的拒绝。他便发誓要“攻取郢都,驾战车踏破平王棺柩”。曹树钧教授写道:“至此,戏剧矛盾已由伸张正义转化为伍子胥报私仇与申包胥、楚昭王誓死保卫楚国的尖锐矛盾,伍子胥也已从一位伸张正义的英难转化为一个引狼入室的罪人。”[2]P94-95读到这里,笔者不禁发问:首先,伍子胥由“伸张正义”到“报私仇”何来“转化”之说?两者之间从来就是不相矛盾而是同为一体的,况且为屈死的家人“报私仇”又难道是什么品格低下的行为吗?其次,楚昭王誓死保卫的不是楚国,只是他先王的遗体、宗亲的性命、王室的尊严。伍子胥在这三次的诉求中是不断试探、不断升级的,而即便是要求最高的第三个也算不上苛刻和过分——一命偿一命,这是最简单粗暴的,但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中也都或许是合法的处理方式。而当这些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伍子胥又能如何呢?他只能宣战,即成为了所谓“引狼入室的罪人”。吴春集先生认为伍子胥此举是“为攻打郢都寻找师出之名”[3]P30而非单纯的报仇。这么一看似乎伍子胥确实不那么正义凛然了。但这只是吴先生主观的揣测,因为至少编剧和导演并没有在舞台上展现或者哪怕是暗示这一点,至少从演员的表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心只为报父兄之仇的伍子胥,攻打郢都最多只是吴王阖闾利用伍子胥所想达成的目的而非伍的主要目的。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为了呼应编剧的创作意图便主观臆断地为伍子胥添加如此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更不能以此来批评他“人性沦丧”[3]P30。
在谈判破裂后,伍子胥便回到军营发兵夺城却久攻不下,无奈之际只好决定决堤淹城。下令前又特地唤出申包胥与之苦口相劝。可申包胥对伍子胥痛失家人、吹箫讨饭的遭遇视而不见,只一味地感叹“当初子胥如今何在呀”,劝现在这个“怨毒偏狂”的子胥能够“暂息过往仇,当念百姓忧”。伍子胥当然不肯作罢,坦白少时便要决堤淹城。得知此噩耗的申包胥质问伍子胥:“这千千万万的百姓们又置于何地呢?”怒斥这个曾经在他心里“悲天悯人的仁义丈夫”从“大英雄化禽兽”,便急匆匆返回都城。马上城破国亡之际,“悲愤痛惜萦满胸怀”的申包胥悲哭“忍叫这芸芸苍生浊浪盖”,这位嘴上爱民如子的道德圣人竟然选择“面对着哀哀子民深深拜”,决定留下百姓蒙难,安排昭王逃走。说到底,所谓的不忍生灵涂炭不过是用来阻拦伍子胥的道德盾牌,当对方不肯妥协时,百姓便成了存续楚国王室血脉的牺牲品,成了伍子胥千秋骂名的判罪书。讽刺的是,伍子胥分明承诺只要昭王“开城纳降,自裁军前”,百姓们便可免于一难,而开口百姓闭口子民的申包胥和楚昭王却从未想过牺牲自己。
很快郢城被攻破,伍子胥见到了当年平王父纳子妻的受害者孟嬴。他自以为这个同病相怜的女人会对自己感恩戴德,却不料对方掏出匕首意欲刺杀自己,幸而未果。伍惊魂未定之际,孟嬴便指责他“任意杀戮,无视他人丧亲之苦,与当年平王一般无二”。此刻的她已然“无意苟活,死不足惜”,便自刎而死了——俨然是一位深明大义、心怀天下的奇女子!可让人纳闷的是,既然她心里清楚“当年平王父纳子妻,满朝文武俱都装聋作哑,只有伍太傅直言谏君,可算我的恩人”,当年伍家满门因她丧命之时,她怎么就没有如此之勇气去刺杀真正的始作俑者楚平王呢?如今“眼睁睁母子难团聚,可怜我形影单此心何寄”了,还要在临死前喊出那些道德口号来责难伍子胥。同样是失去亲人,她就没有想过伍子胥曾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吗?更何况昭王并没有死而是安然逃走了。伍子胥的痛苦正是因为当年伍家替她抱不平。说到底其关键不过是“丧亲之苦”在他人还是在己身罢了。尾声处,二胥再次相逢,面对申包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冷言冷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楚国故地,伍子胥瘫坐在地上怅然若失。
显而易见,这出新编剧目不是仅仅增删人物、改动情节来重新敷演这个故事那么简单,从剧情设计和人物对白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道德指向,故事的主题也不再是复仇,而是编剧要借申包胥为代表的楚国上下之口来呼唤“人性中的善良、纯真、柔软和爱”[4]P1,希望通过善良和仁爱来劝解伍子胥放下仇恨,而当这个被劝解者没有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泯恩仇、释心怀时,就被斥为了人性扭曲的怪物。正如编剧冯钢在其创作漫谈中所说的那样,他希望通过这出戏引出这样的思考:“仇恨及其报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性,是人性复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类始终难以摆脱的心理困境,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蕴育,人类应该有勇气去思考和避免因为仇恨而带来的更大的人道灾难和人性摧残。”[1]P72在剧中,他借申包胥之口对伍子胥说“铁骑到处,满目破败,太傅若见,也要泣血,此情此景,望君自省”。看到这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忽然涌上心头,相信有不少人在年少时和我有过类似的经历:遭受了某同学没由头的欺负,去向老师讨要公平却被反问: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人家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在这部剧里,我为伍子胥感到深深的委屈和不公。
当创作者借角色之口不断地指摘伍子胥涂炭生灵、批评家们也纷纷附和着谴责伍子胥丧失人性时,我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伍子胥的复仇行动是有完全充足的理由的。楚昭王继承王位时是那么的心安理得、合情合法,需要他承担责任时却又各种推脱,伍子胥家破人亡时遭人追杀,手掌兵权了就被要求悲天悯人,这是何等的双重标准?且伍子胥不是一开始就要颠覆整个楚国的,在攻打郢城之前他就提出过多相当合理的条件,可楚昭王自始至终除了嘴上道歉,从没有付出过实际的补偿。正如吴春集先生文中所写的孟嬴:“先赞赏和感谢伍家仗义执言,又以舍生取义刺杀伍子胥作结,给了伍子胥的人性沦丧以强大的刺激和反讽。”[3]P30没错,口头上的赞赏、感谢和道歉都给予了伍家,仿佛十九年前命丧刀口的三百条冤魂听到这些口头上的赞赏、感谢和道歉就能安息一样,在实际中给予伍家的却是车裂、长刀和匕首,却又反过来指责伍子胥人性沦丧?编剧冯钢说:“楚平王的突然死亡,伍子胥失落之下的大肆杀伐,‘存楚和复楚’进入到了是‘灭苍生还是保苍生’的问题。”[1]P72我想说这个问题不是抛给伍子胥的,而应该抛给合理继承了平王王位的楚昭王。最终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这悲剧的责任承担者不应该是伍子胥,至少主要不是他。
我们一直在呼唤当代戏曲应该具备现代性,该剧创作者所力求表达的仁爱、善良、对人性的思辨当然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可真正的仁爱和善良是一切恶行得到惩治而非冷眼旁观者一句轻飘飘的“人死百怨消”,对人性真正的思辨是设身处地地考虑到每个人所处的困境,看到他在大是大非和个人私情间的挣扎,而非没有条件地充当理中客。在这出现代人创作的现代戏曲中,当申包胥一遍遍以各种大仁大义逼迫伍子胥放弃复仇时,我仿佛听到了经常遭受批判和鄙夷的传统戏里“娘子不必太烈性”的当代回响。
那么伍子胥对楚国的情感处理是否是戏剧构造的一个无解局面呢?且看拍摄于1996年的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剧中伍子胥攻下了郢都,挖出楚平王鞭尸三百,楚国百姓在旁围观人心惶惶,众人都劝他不住。就在局面无法收拾之时,不远处的江上传来一段歌谣:“芦中人,芦中人,渡过江,谁的恩?宝剑上七星文,还给你带在身,你今天得意了,可记得渔丈人?”听到这段歌谣,伍子胥沉默良久,跪倒在地上痛哭起来,心中积怨自此化开。这位乘舟而来的渔丈人便是当年助伍子胥过江的老翁,歌谣中的芦中人便是指伍子胥。渔丈人的一段歌谣便能化开伍子胥的心结,阻止了他继续报复下去,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有恩于他的老丈出现在面前时,伍子胥才恍惚意识到生他养他的是楚国人,灭他满门的是楚国人,对他穷追不舍的是楚国人,渡他过江的也是楚国人。且同样是有恩于他,相对于被灭国还能奔赴千里外去哭秦庭的申包胥而言,这位老丈更能代表与伍家冤案毫无关系却被牵连受苦、无处喊冤的普通百姓。正是这样的复杂交织的情感被勾起,伍子胥才没有继续酿造悲剧。这位自在行舟于江上的渔丈人咏出的歌谣,要比那些高高在上、连篇累牍的春秋大义更加触动人心。电视剧里的这一段小情节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咏出了《春秋二胥》所要追求的仁爱和思辨。《春秋二胥》的创作者们所想要阐述的那些东西当然是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的,但关键是它以什么样的戏剧安排表达出来,至少仅凭那一段段正义凛然的西皮二黄是无法感化伍子胥的。
司马迁评价伍子胥为“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没想到几千年后自诩为现代人的我们竟然在一出现代戏曲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伍子胥放弃他那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复仇行动,这实在是悲剧。笔者不禁联想到了西方那个著名的谚语,但我想说,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不仅要狠狠打回去,连那个在一旁不明所以就劝你把右脸伸过去的人也至少也要挨一口唾沫。
参考文献:
[1]冯钢:《行与思》,《剧本》,2020年第6期
[2]曹树均:《别开生面的两个舞台艺术形象——喜看历史京剧〈春秋二胥〉》,《艺术评论》,2014年第9期
[3]吴春集:《好一出人性的生死拷问——〈春秋二胥〉》,《艺术批评》,2020年第1期
[4]苗春:《〈春秋二胥〉:刻画人性 以情动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3月第11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戏曲生态现状与传承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D2405。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