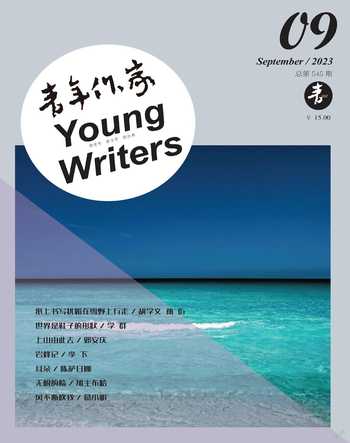理想人间
张象
报到那天,我在酒店办入住,巧遇路魆和贾若萱。放好行李,他们喊我去喝东西,顶着大太阳,走了两条街,都没找到地图上的咖啡馆。群里通知说,五点二十集合去吃饭。我们原路返回,进便利店买水才发现,那个咖啡馆竟然就在隔壁。若萱问我,返程是不是也从天府机场出发。活动营结束当天中午,我和鲁院同学吕峥,还有青年作家写作营认识的兄弟加主布哈在一起吃火锅。此刻人还没多起来,店里绿意盎然。火锅不算太辣,表面红得大江东去,吃起来却晓风残月,让我不禁再次感叹起吕峥的周到。去年在鲁院学习时,我们没有私下聚过,同学之间感觉还没有处够就蓦然四散。毕业后,但凡有机会,大家都要聚一聚。我每次和同学吃饭,都感觉吃的不是饭,而是遗憾,仿佛每吃一次,那些遗憾就少了一点。席散,和两位兄弟挥手,天巧合地阴了一小会儿,落了几点雨。
这几天前锋村的大鱼,尤安村的水蜜桃,荷桥村的悠然岛,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但我已上了出租车,去看望舅舅。我的舅舅姓李,我妈却姓高。因为一些说来话长的原因,我和他已经三十多年没见了。我们约好活动结束后第二天,我就去他家。我拎着一瓶二十年的汾酒和一箱平遥牛肉,以及两本书,远远地,就看到他在大门口等我。他的头发很稀疏了,两鬓斑白,眼含笑意,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边走边说。我说:“您身体还挺好啊。”舅舅说:“其他还好,就是动脉硬化,容易引发脑梗,或者心梗。”我说:“千万要注意,外婆当年就是心梗去世的。”舅舅说:“是的,我记得她那时候有一点胖。”
我换上拖鞋,放下东西,坐在浅咖色的皮沙发上,和另一头的舅舅舅妈聊天。舅妈给我泡了一杯茶,又端来苹果、枇杷等放到茶几上。茶几是米黄色的,大理石,边上横着几个蓝白相间的积木玩具。
聊了快一小时,两边的亲戚近况知悉,我看看表,打算告辞。舅舅站起来,说他一早就去菜市场买了鱼、猪肝、小龙虾,必须喝一点。我赶紧站起来解释,“晚上和朋友还有约,这次就先不喝了,认了门,以后再来。”舅妈也帮忙说,“他明天早上的飞机,朋友那儿离机场近。”舅舅这才作罢,一转身去了地下室,提了一大盒茶叶,命令我拿上。
回到酒店,我看那一大盒茶叶不好带,就想把茶叶拿出来,盒子扔掉。茶叶盒很高档,密封很好,我好不容易打开,却发现轻得像鹅毛。我试着打开一看,竟然,都是空的。我把盒子夹壁都检查了一遍,也是空的。
但我没有跟舅舅说,这两罐茶叶是空的。我没有跟他说,因为痛风,他买的美味我无福消受。我也没跟他说,其实我是第二天下午飞机,晚上没约朋友。我更没跟他说,本来我留了一整天时间,准备和他好好聊一聊。因为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舅舅对我的情意是实的、重的。我就把舅舅给我的两罐心意,装到行囊里,背走了。
夜风浅凉,暮色苍茫。当沱江两岸的灯火,再次点燃我的眼眸时,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简阳。前两日,海底捞火锅、简阳羊肉汤等“餐饮九绝”,都尝得差不多了,此时一个人,我只想去体验一下市井快餐。就在酒店楼下,吃了一份宫保鸡丁饭。果然是简阳,盖饭都好吃。
次日上午,看着沱江美景吃过早餐,我打车去葫芦坝。七八分钟,车子就穿过了“周克芹故里”牌楼,停在三岔路口。下车看见两个店铺紧挨着。画着美女头像的“新农村美发”,卷闸门关着,门外停一辆蓝色三轮。画着另一个美女头像的“新农村理发店”则开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给一个白发老爷爷推头。我上前问路,年轻人摇头。老爷爷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我只听懂几个字:走大路,不要走小路。
顺着老爷爷指的方向前行,我心想,不愧是文学之乡,连老人说话都这么有哲理。说得多好。文学不也是这样吗?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边想,边走,边看。茂林修竹。碧水蓝天。枇杷榆钱。空中电线。笼中的鸡。冬季用气安全须知。小手拉大手共筑防火墙。恪尽职守站在门口的狗。没有行人。偶尔一辆电动车飞过,戴头盔的少年,掀起身后一阵风,将鸡鸣声和犬吠,送得更野更真更辽阔。
不知走了多久,路过一户人家,青砖耸立,爬了半墙紫红色的热情。那花我认得,此前在深圳见过,叫做三角梅。只是当时忙于创业,无心欣赏,直到此时,一个人偶遇,才觉得她开得那么好,那么恰当,那么活泼而不失稳重,那么坚韧而不计得失。野风吹过,压着她,她不悲。蝴蝶飞来,绕着她,她不喜。她就那么不悲不喜地开着。有人看,她开得热烈。没人看,她仍然开得从容。
转角遇到一位大姐,戴着帽子,手里提个篮子。一问,大姐惊呼:“你走过了,多走了两公里。”普通话我听明白了,忙说感谢,再走回去。大姐说,“坐公交吧,两块钱。”几分钟后,果然有一辆绿色公交驶过,遂上车。车上都是戴着草帽的大爷大娘。坐了约三四站,大姐叫我,“到了。”下車一看,这地儿很熟啊。就是最初那个三岔路口。这难道是在呼应我和路魆、贾若萱第一天去找咖啡店吗?顿时喉咙也呼应着渴了起来,我去理发店对面的小超市买水喝,这才知道走得不对。
走大路是对的。但是,什么是大路?大路是相对的,不是笔直延伸跑公交的马路,而是拐个弯进去,无数岔路小路中间的一条水泥路。
路走对了,就很快。踩着枯叶和苔藓,上了一个似乎鲜有人至的石阶。没多久,周克芹先生的雕像就出现在眼前。接着看到繁体的“小說家周克芹之墓”。碑上刻着一副挽联,据说是诗人流沙河的手笔,写的是:“重大题材只好带回天上,纯真理想依然留在人间”。我给先生,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一抬头,又看到先生用以自勉的文字,这次是简体:“做人应该淡泊一些,甘于寂寞……只有把个人对于物质以及虚名的欲望压制到最低标准,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的开放。”我又想起了那半墙紫红,不悲不喜,热烈从容地开着。
下午,我抵达天府机场。起飞的刹那,窗外树影挥手,花皆点头。风吹过大地,吹过岁月,吹过薛涛停马的人间,吹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吹过了每一个蒙尘又被擦亮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