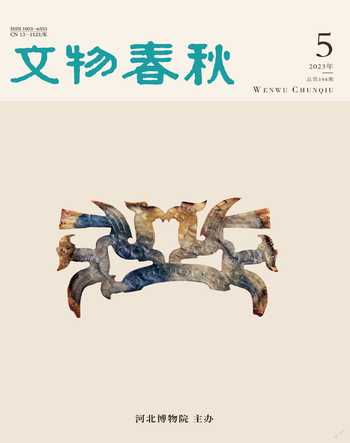学术史视角下考古学文化名称撮议
郭荣臻 张鼎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郑州地区;公共考古
【摘要】在已确认的中国史前—夏商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有一些文化的命名不但与河南郑州地区遗址地名关联密切,而且属于考古学研究中的高频词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在考古学界对相关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学科背景下,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以郑州地区相关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概况,并在此基础上重温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针对发现的同一支文化存在不同名称及文化名称中有与现地名不一致等现象,认为不必在既有文化命名已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刻意“制造”新的文化名称来取代旧名,也不必因循守旧对具备条件的文化不予命名,并纠正错别字现象以与今地名相符。通过总结与梳理,提出对普及郑州地区公共考古乃至公众历史教育知识和书写郑州本地考古学史的思考。
————————
*本文为郑州兴文化工程2023年度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郑州地区史前农业复杂化进程研究”(项目号:xwhyj2023193)、郑州师范学院大创训练计划项目“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房屋建筑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号:DCY2021002)、郑州师范学院定向研究招标课题“郑州地区博物馆群建筑选址比较研究”研究成果
引言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显示,以河南郑州、洛阳等地区为代表的“郑洛文化区”[1]或“嵩山文化圈”[2]在史前—夏商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该文化区或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郑州地区有多支史前—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当地地名相称,甚至个别大的“考古学时代”概念也因当地遗址得名,不同学者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与内涵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本文在回顾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学术史的基础上,就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为便于讨论,本文暂依考古学文化相关人群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而非学术史上讨论的先后顺序对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梳理;同时为保证表述的连贯性,暂以“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简称之。囿于个人学力,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简史
1.李家沟文化
以郑州市新密市来集镇李家沟村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10000年前后。2009—201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认识到该遗址存续时间较长,文化序列相对清晰。在所刊简报和发掘纪要中,发掘者对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裴李岗文化层位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以“李家沟文化”称[3]。考古发掘资料公开后,有学者就其环境乃至生计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但对李家沟文化遗存以“李家沟时期”称[4]。鉴于李家沟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有学者曾建议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概念约当的“前裴李岗时代”以“李家沟时代”称,作为考古学时代名称的“李家沟时代”专指距今约12000年或更早阶段至距今9000年左右的时间范围[5]。
2.裴李岗文化
以郑州市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8500—7000年。需要说明的是,对这支文化的年代,学界另有其他测年数据。关于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学界有过较长时期的讨论,主要纠葛在于其同磁山文化的关系。在裴李岗遗址发掘之前,文化面貌与其存在相似因素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已发掘,但当时对这两类遗存的发掘皆少,有学者将二者视作同一类文化。如陈旭先生将二者统称为“裴李岗文化”[6],严文明先生则建议将裴李岗遗址纳入到“磁山文化”组成之中[7],夏鼐先生总结新中国30年成就时所持大抵也是将二者视作一体的认识[8]。李绍连先生在梳理磁山、裴李岗、莪沟北岗遗址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将这些遗存统称为“磁山·裴李岗文化”,认为可分作磁山文化类型、裴李岗文化类型两部分[9]。总体来看,上述学者虽然都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但更倾向于认为共性是主要的,不同仅是同一文化内部的类型或地域差异。
早在新鄭裴李岗遗址发现伊始,作为发掘者之一的李友谋先生便已审慎地认识到此类遗存可以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而不是将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纳入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中,并较为坚定地认为就当时已有发现而言,仅新密莪沟北岗遗址的遗存与裴李岗遗址遗存相似[10]。随着河南境内考古调查、发现、发掘的增多,李友谋先生又与陈旭先生合作撰文,讨论了裴李岗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磁山文化的异同,再次提出两者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混为一谈,并提倡以“裴李岗文化”称河南境内已在多处遗址发掘到的此类遗存[11]。此后这一认识逐渐得到考古学界的认同。
鉴于裴李岗文化在相近时期诸文化中的领先性[12,13],栾丰实先生提出了“裴李岗时代”的名称,特指距今9000—7000年左右的时间范畴[14]。此后,张松林先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以“裴李岗文化时代”称此时期[15]。这一概念的提出,较过去学界一度流行的专指这一阶段的“前仰韶时代”的笼统称谓更为精准、科学。以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部分师生为代表的不少考古学人认可并使用了“裴李岗时代”的概念,在过去20多年间这一概念在考古学界的普及率相对较高,但在学界的认同度不及后续“仰韶时代”“龙山时代”等概念。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过去并未接受“裴李岗时代”话语体系的学者在研究中逐渐认同栾先生首倡的这一基于裴李岗文化的史前时代概念。
3.秦王寨文化
以郑州市荥阳市高村乡枣树沟行政村西秦王寨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内涵与后述大河村文化同,以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群体的组成部分。在早期的研究实践中,以秦王寨等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曾被划归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6]。20世纪60年代,杨建芳先生提出了与之相异的认识,将其作为不同于庙底沟类型的遗存看待,并论述了仰韶文化及其不同类型的内涵。在杨先生的话语体系下,仰韶文化存在西阴村、三里桥、秦王寨、半坡、后岗等具有早晚关系的类型[17]。杨文问世未久,方殷先生针对杨先生的部分论证方法、结论予以讨论,提出了并不一致的看法,认为即便发现较早,但在没有发掘工作支持的背景下,“秦王寨类型”命名的提出尚乏条件,甚至存在问题[18]。
时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其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有学者在对秦王寨遗址考古调查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命名,认为其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19],这一年代数据明显晚于现在所公认的大河村遗址三、四期遗存。巩启明先生认可秦王寨类型的提法,并将其作为仰韶文化诸类型的一种[20]。虽然前述类型、文化名称皆以秦王寨遗址为基本点,但对此类遗存的内涵却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有学者将以大河村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遗存视作秦王寨类型[21],但在另一种话语体系下,此类遗存指的则是与大河村遗址三、四期相当的遗存[22]。近年来,作为考古学文化类型名称的“秦王寨类型”仍在继续使用,如戴向明先生将其称作豫中地区“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23],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将上述遗存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看待且予以专题系统论证的学者可以孙祖初先生为代表。在分析诸遗址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孙先生将秦王寨文化分作六期,判断了其渊源与流向,比较了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22]。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在后续的学术实践中,以秦王寨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或类型的名称在部分学者话语体系中被更具代表性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所取代。但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种取代,新近仍有年轻学者在研究中以“秦王寨文化”称此类遗存[24]。
4.大河村文化
以郑州市金水区北部连霍高速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南隅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遗存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亦属于仰韶文化群或仰韶文化群体文化之组成。鉴于该遗址考古发现较多、内涵丰富,而秦王寨遗址则未开展过系统工作,安志敏先生提倡以大河村类型取代秦王寨类型[25]。该认识提出未久,王震中先生在通過考古资料重建上古史的研究中即以“大河村类型文化”称此类遗存[26]。不过,学界更常见的操作则是将上述遗存以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称。在考古学界堪称典范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编著者认为过去将仰韶文化划分为二三十种类型的方案过于繁杂,明确提出使用“仰韶文化群”中的“大河村文化”概念[27]220—221。就日常实践来看,这一观点获得了一定的学术认同。
上述以外,有学者研究视域下的“大河村文化”所指不仅包括豫中地区以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为代表的遗存,而且将河南北部、中部、西南部介于裴李岗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的大多遗存都纳入其中[28]54—81。与此种偏广义认识相异,另有学者笔下的“大河村类型”则偏于狭义。如在李昌韬先生看来,大河村类型(距今5000—4800年)晚于秦王寨类型(距今5500—5000年),两者具有确凿的承袭证据[21];廖永民先生亦将二者视作同一文化系统的组成,强调二者的独立性,秦王寨类型与大河村类型前后相承[29,30]。嗣后,韩建业先生将大河村遗址第四期遗存归入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31],虽所用名称与前述诸多先生有所不同,认识大致可归入一类。由此可见,对大河村文化或大河村类型、秦王寨文化或秦王寨类型的见解,学术界虽有主流声音,也存在不尽一致的观点。
5.大河村五期文化
以郑州市金水区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遗存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发掘报告中称其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32,33],认识到其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的差异。随着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学界研究的深入,学界或将其纳入庙底沟二期文化,或视其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中的考古学文化[34]。靳松安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大河村五期文化”的名称,对此类遗存予以系统研究,视其为与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抵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为豫中地区嵩山北部、东部,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000—4500年[35,36]。得益于靳先生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具有郑州大学考古系学习背景的学人认同并使用此概念。对于此类遗存,另有学者以“大河村五期类遗存”称,认为其年代距今约4900—4600年,上承大河村文化,下启王湾三期文化[27]525—526。虽然将大河村五期文化作为独立遗存甚或专门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在学界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却也具有一定认可度。
6.新寨文化①
以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绝对年代约为距今3870—3720年[37],主要分布于豫中地区。关于此类遗存乃至新寨遗址的性质,学界至今仍存歧见,阶段性认识远多于共识性结论。就现有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来看,此类遗存属早期夏文化的可能性颇为不小[38]。
就此类遗存的命名情况而言,学界争讼已久却无定论,已有学者作过繁简不等的学史回顾[39—42]。要而言之,承认该遗存特殊性而非将其向上归入王湾三期文化的学者们对此类遗存的称谓,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新砦期”[43]、“新砦二里头早期”、“新砦二里头早期文化”、“新砦期文化”[44,45]、“新砦期”[46,47]、“新砦文化”[39]66—72,[41,43,48—53]、“新砦文化亚态”[54]、“新砦期遗存”[55]、“新砦期文化遗存”[56]、“新砦二期文化”[57,58]、“新砦类遗存”、“新砦现象”[59]、“新寨期文化”[60]、“新寨文化”[61]等等。就已有研究来看,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罕见有类如新寨文化命名这般曲折、持续时间如此久却仍无定论的现象。关于该文化,笔者将有小文《学术史视角下的新寨文化命名省思》(待刊)作详细论述。
回顾学史,学界不但对此类遗存能否以考古学文化称存在歧见,而且即便在认可其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学者中,对于何种遗存属于新寨文化也存在不一样的见解,如杜金鹏先生认为新砦文化包括新砦二期及二里头一期[48,49],高江涛、庞小霞伉俪话语体系下的新砦文化则系以新砦二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39,41],魏继印先生文中的新砦文化则包括新砦二期、新砦三期遗存,并认为新砦三期早于二里头一期[50,51]。笔者认同庞小霞女史、高江涛先生所倡的“新砦文化”,惟近年将其名称改作“新寨文化”。
7.洛达庙类型文化
以郑州市中原区洛达庙村的考古发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基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主持发掘了该考古项目。在此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认识到,该遗址的“商文化层”与二里岗文化下层、二里岗文化上层、郑州人民公园期商代文化遗存皆存不同,虽然将其判断为商文化,却已清晰认识到该遗存早于二里岗文化[62]。鉴于其内涵较登封玉村、洛阳东干沟的同类发现更具代表性和知名度,学者们一度有过将其称之为“洛达庙类型”[63]或“洛达庙类型商文化”[64]的研究实践。此后,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65]及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工作的开展,学界认识到二里头遗址在同类遗存中的典型性远超其他遗址,“二里头文化”[66]命名被提出后,这一新的学术名称接受度更高。以洛达庙遗址命名的“洛达庙类型文化”便完成了其学术使命,终结了其短暂的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历史。
8.二里岗文化
以郑州市管城区二里岗街道命名的商代早期文化,亦可以早商文化称,距今约3600—3300年。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等君主的都城所在地[67]。郑州地区的早商文化被分为二里岗下层一期、二期,二里岗上层一期、二期(或曰二里岗文化一、二、三、四期)。鉴于二里岗文化在当时诸文化中的领先态势和强势地位,有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了“二里岗时代”的名称[68],可以认为该概念意指商代早期或早商时期的时间范畴。
综上,根据国内考古学界乃至历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多达8种,这一多种文化以同一市级行政区地名命名的情况在国内其他地市并不多见。从地域来看,被命名为文化的遗址既有分布在郑州市区者,也有分布于下辖县级市者;从时代来看,这些文化涉及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前期和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时代前期、二里头时代后期、二里岗时代。
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功用
论及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功用,不妨再对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加以回顾。此概念系西方学界首倡后传入国内,在早期倡导者戈登·柴尔德先生看来,稳定且共存的多种文化因素复合体可以文化集团或文化称[69]。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学界对考古学文化的误解,夏鼐先生专门撰文论述了考古学文化问题,认为文化是“某一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这群东西即学者们在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70]。严文明先生论定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为“存在于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特征的实物遗存的总和”[71]。安志敏先生所撰写的词条影响也较深远,称考古学文化为“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72]。其后张忠培先生也有类似表达,视考古学文化为“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73]。
通過对上述定义的学习,可以发现,考古学文化以文化特征为基础,兼具一定的时空特征。虽然西方学界有研究者倡议不再使用考古学文化概念,代之以其他名称如“风格”甚至其他方法其他理念等[74],但就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初“仰韶文化”的名称提出以来,经一个世纪的发展,此种概念、此类方法已深入学者内心,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乃至底色,不但没有摒弃的必要,而且在未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而言,抑或从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文化概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提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不但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公众考古的开展与公共历史教育的普及。提到一支考古学文化,学界便能联想到其所处时代、所在地域、所具备的有别于其他人群遗存的特征。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时代虽有不同,但在广义的层面,可以作为今人认知、理解古代社会、古代人群的一个代名词与切入点。设若没有这样的概念及在此概念基础上生成的一系列名称,无论学术研究抑或公众知识普及,都会平添诸多不便。
专就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而言,除上述功用外,它们的提出,还有利于提高郑州地区相关历史文化的知名度。在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河南特色、郑州特色传统文化建设与传承的历史进程中,有效利用这些考古学文化,有利于紧扣时代主题,讲好郑州故事、河南故事、黄河故事。在今后的公共考古活动中,可以在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基础上,充分利用相关文化的相关遗迹、遗物,让文物活起来,用考古学的手段和研究成果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自信。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都有作用,但不能为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宣传与推广刻意缔造不必要的“文化”,否则将会事与愿违,不但不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而且会使严谨的学术流于主观化。
一支考古学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根本就在于其所具备的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征,是在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基础上所获结论。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史的重要组成,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不但对郑州地区历史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理解学界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或原则、对今后如何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有借鉴意义。
三、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名称评议
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讨论持续已久,尤以张国硕师对命名方法的总结最为全面[75]。在张先生总结的11种中外学术界存在过的命名方法中,至少有6种存在于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里,如最初发现地命名法(秦王寨文化)、典型遗址命名法(大河村文化)、地名加分期命名法(大河村五期文化、新寨二期文化)、类型文化命名法(大河村类型文化、洛达庙类型文化)、双名命名法(磁山·裴李岗文化)、时代命名法(夏文化、早期夏文化、早商文化)等。
此外,另有两种情形出现在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中。第一,同一支考古学文化存在不同名称。前述秦王寨文化、大河村文化名称存异,但在部分学者话语体系中两者内涵相同、异名同指。此类情形也存在于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中,如黄河上游地区裴李岗时代的“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李家村文化”“白家文化”等名异而实同,再如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名异却指一,另如“尹家城二期文化”的称名被“岳石文化”取代,等等。第二,命名中的错别字现象或笔误现象。新密新寨村名被误作“新砦”遗址后,“新寨期”“新寨文化”皆被误作“新砦期”“新砦文化”;二里岗文化命名缘起郑州二里岗地名,但在研究实践中亦有学者将其写作“二里冈文化”。此种情形在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中也不罕见。
常见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中,无论首次发现地命名法抑或典型遗址命名法,皆基于现代地名。相关遗存、类型、文化会存在错别字现象,与地名的误写有关,如“新砦”即是真实地名“新寨”的误写,新近已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该错别字问题[76]。其实早年调查简报中“新寨”“新砦”两种写法并存,到21世纪初开始有学者改用“新寨”[60],另如2021年河南大学第四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上赵春青先生所作学术报告即题为《新寨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此外所用新密市文物工作者近年編纂当地文物资料时亦使用“新寨”的遗址名称(尚未正式出版,据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杨建敏先生告知)。
河南信阳地区的孙寨遗址也存在相似情况。在早年的发掘报告及研究中出现的皆是“孙砦遗址”[77,78],新近发布的资料中则称其为“孙寨遗址”[79]。将遗址、类型、文化纠正为与现今地名相同的写法,既是对现今正确地名的尊重,也是严谨的学术规范使然,不但极具必要,而且十分可行。
在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诸考古学文化中,有一些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考验,不断为后续的考古发现所验证,而且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如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二里岗文化等,另有一些虽有部分学者提倡并坚持使用,但尚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如大河村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新寨文化等。这一研究现状并不意外。事实上,赵辉先生早已指出,考古学文化概念仅系“考古学家为把握考古学文化客体历史意义所借助的一个中介”[80];许宏先生也曾认为,考古学文化概念“只是考古学者对其研究对象所做的聚类解析,它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而并非客观实体本身”[40]。这些见解对理解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地位,评估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学术研究是学者以个人为代表的成果产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便面对同样的文字史料,学者们也可能会得出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遑论具有一定主观性的文化命名问题。在学术史的视角下观之,研究实践中的某某遗存、某某类型、某某文化都是相关学者学术努力的产物,无论其是否成为学界主流认知,在学史上均有重要意义。即便在时过境迁以后,相关认识不再为学界所认同,也不能忽视它们被提出的初衷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怀抱理解态度看待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陷入偏狭而不自知。
四、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相关问题
综观国内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认可度最高的无疑为最初发现地和典型遗址命名法两大类别,前缀+地名、地名+后缀、省略个别字等方法皆属于前两者的变体(王芬先生回顾学术史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命名的文化已经基本摒弃了添加前缀或者后缀的做法[81])。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大体不出上述范式。
在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中,大河村文化或类型对秦王寨文化或类型的取代、新寨文化命名的接受历史与现状尤其值得关注。
一方面,何以出现文化名称的变更,新文化命名对旧文化命名的取代是否极具必要性值得深思。如果说秦王寨文化的命名与秦王寨遗址发现最早相关,大河村文化的命名与大河村遗址所做的发掘及研究工作更多且更具代表性相关,那么究竟遗址、遗迹、遗物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典型,这是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然而,有些新遗存在最初发现时或者未被辨识出来,或者虽然辨识出与以往遗存的不同,但因是初次发现而未认定为新的考古学文化,以至于当此类遗存有了较多发现并确认为新的考古学文化时,“冠名权”已不属于首次发现地。如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就是以更典型的遗址取代首次发现地(登封玉村)及曾命名地(郑州洛达庙)并获得学界一致认同的案例。如何更好地平衡首次发现遗址与典型遗址的关系,甄别和选择更加适宜、更加妥当的文化命名,仍是值得讨论的。
另一方面,何以一支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范围、延续了一定的时间阶段且有着一定自身文化面貌的考古学遗存作为文化的存在长期未能得到学界认同,也是学术史梳理与回顾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如新寨文化。在可以预见的不短的时期内,关于新寨文化命名成立与否的认识分歧仍将持续下去。
回观学界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前辈学者不乏精辟思考。早在20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便已指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有一群特征、多处发现、学者有相当充分认识,并提出了用群众路线选择文化名称的建议[70]。张忠培先生赞同典型遗址命名法,并对典型遗址的内涵加以界定[73]。时至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关注骤增。前述张国硕师文则肯定了首次发现地命名法的客观性,认为典型遗址的标准不好把握,而且不赞同群众路线在文化命名中的实践[75]。安志敏先生认为,考古学文化名称适用于史前共同体,在评述诸种命名方法的基础上,重申了夏鼐先生所提倡的三原则[82]。王仁湘先生在肯定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建议成立相关机构,经由一系列程序申报通过后方可使用相关文化命名[83]。赵春青先生认为可先对首次发现地以“某某遗存”称,待研究深入后再按照典型遗址予以正式命名,并反对权威机构仲裁抑或群众路线定夺的原则[84]。
这些讨论皆系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不但对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有所反思,而且对将来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应注意到,前辈学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分歧。不同的学习者、研究者可能会有自己的认同,不必强求统一,但与学界情况不同,在公共考古实践工作中还是应当谨慎地寻求更为稳妥的处理方式。
虽然获得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权”有利于向在地公众开展公共考古宣传教育,但为了地方文化宣传而放弃既有考古学文化名称,并缔造另外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则大可不必。以新密莪沟北岗遗址为例,其发掘时间与新郑裴李岗遗址相近,曾有学者认为以北岗作该文化名称更合适,但在学界普遍认同裴李岗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变更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便未能获得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权,也未获得相关类型的命名权,也并不妨碍莪沟北岗遗址作为裴李岗文化重要遗址的地位。
虽然任何考古学研究在学术史上都有其位置与意义,每一位学者所提出的观点都值得被尊重,但问题是:随着全国各地诸时期考古发现的增多与研究的多元化,学界和社会公众是否真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指代同一文化的不同名称?这种名称的增多对考古学界学者们而言尚能区分和认识,只是增添了些许麻烦,但对于非考古专业背景的学者来说则会增加认识的难度,更会导致社会公众的无所适从。我们认为,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在既有文化命名已经深入人心的前提下,着实没有必要標新立异,不断因种种原因刻意“制造”新的文化名称来取代已深入人心的命名;另方面,针对学界过去没有命名但的确具备称其为考古学文化条件的遗存,也不必因循守旧而不予命名。虽然不必强求学界每位学者都遵循唯一的命名,但在公共考古宣传与公众历史推广时,应尽量避免使用不同的名称指代同一内涵的文化,或者在使用自己认同的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同时,注明该文化的其他别称,以免公众误以为该文化和异名同指的遗存是不同内涵。
结语
综上梳理不难发现,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有大有小,层级有高有低,分别涉及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末期前段和青铜时代早、中期诸时段。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称名既有为学界广泛认同者,亦有至今仍存争议者,甚至有为以其他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所替代者,但作为考古学研究史上的重要组成,从考古学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不但有利于加深对郑州地区史前—夏商时期社会演进与文化格局的认识,而且对思考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方法也有助益。
郑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郑州地区先民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及其命名历程亦应引起重视。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诸名称兼具主观、客观双重特质,可以之为案例省思国内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道路上,如何寻求更符合中国考古学实际、兼具研究特色与历史底色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可以作为问题持续讨论。正如许宏先生所言:考古学有其残酷性,新发现不断完善、订正、颠覆既有认知[85]。适时对考古遗址、类型、文化命名中的失误予以修正,不但不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与抹杀,反而有利于将这门学科推向更加确切的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本文并非是对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未涉及各种文化的代表性遗迹、遗物特征,虽然对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命名简史作了回顾,但并未将学界所有先生对上述文化的全部研究予以提及,由此造成的疏漏,恳请前辈、同辈及更加年轻的学者海涵;另一方面,前述梳理仅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为案例。除此之外,以郑州地区地名命名的诸文化下的类型(如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王湾三期文化王城岗类型,新寨文化新寨类型、花地嘴类型,二里头文化洛达庙类型或先商文化洛达庙类型,先商文化南关外类型,等等)也是本地乃至全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组成,对认识和理解郑州地区的重要发现、考古学相关方法论皆有助益。然而囿于文章篇幅及个人学力,本文未予全面回顾,可留待将来再加梳理,以便更加系统地认知相关问题。
后记:本文酝酿于2020年,时有提笔却迟未完结。2022年5月,因疫情封城,得以居家办公,总算了却夙愿将其定稿。文中存在的失误与不足,恳请相关学者批评。写作过程中,曾就大河村五期文化相关问题请教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学友张建先生,郑州师范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谢祥蕊同学提供了信阳孙寨遗址名称存疑的线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学友王豪先生予以确认,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
[1]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J].华夏考古,2002(1).
[2]周昆叔,张松林,张震宇,等.论嵩山文化圈[J].中原文物,2005(1).
[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1(4).
[4]张俊娜,夏正楷,王幼平,等.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古环境分析[J].中原文物,2018(6).
[5]郭荣臻.考古学视域下的史前“时代”概念简说[J].文博,2018(1).
[6]陈旭.仰韶文化渊源探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4).
[7]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J].考古,1979(1).
[8]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J].考古,1979(5).
[9]李绍连.关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从莪沟北岗遗址谈起[J].文物,1980(5).
[10]李友谋.略论裴李岗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4).
[11]李友谋,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J].考古,1979(4).
[12]李友谋.论裴李岗文化在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中的领先地位[J].中原文物,1988(4).
[13]栾丰实.试论裴李岗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关系及其发展去向[C]//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市文物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论裴李岗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57—68.
[14]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J].考古,1996(4).
[15]张松林.裴李岗文化与裴李岗文化时代[C]//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市文物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论裴李岗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15—118.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7]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J].考古学报,1962(1).
[18]方殷.从庙底沟彩陶的分析谈仰韶文化的分期问题[J].考古,1963(3).
[19]李昌韬.秦王寨遗址与秦王寨类型[J].中原文物,1981(3).
[20]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J].史前研究,1983(1).
[21]李昌韬.试论“秦王寨类型”和“大河村类型”[J].史前研究,1985(3).
[22]孙祖初.秦王寨文化研究[J].华夏考古,1991(3).
[23]戴向明.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10.
[24]朱雪菲.大河村遗址秦王寨文化彩陶再研究[J].中原文物,2015(2).
[25]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J].考古,1979(4).
[26]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J].中原文物,1986(2).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1952—1992[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9]廖永民.关于大河村四期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命名问题[J].中原文物,1986(1).
[30]廖永民.关于秦王寨类型与大河村类型的划分问题[J].中原文物,1986(4).
[31]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7—118.
[3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3).
[3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95.
[34]罗新,田建文.庙底沟二期文化研究[J].文物季刊,1994(2).
[35]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D].郑州:郑州大学,2005:49—50.
[36]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54—55.
[37]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J].考古,2007(8).
[38]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N].中国文物报,2001-06-20.
[39]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D].郑州:郑州大学,2004.
[40]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46—158.
[41]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0—96.
[42]赵春青,耿广响.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4-20(10).
[43]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C]//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17.
[44]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J].考古学报,1986(1).
[45]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C]//《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37—48.
[4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78—80.
[47]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J].中原文物,2002(1).
[48]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2).
[49]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66—72.
[50]魏繼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J].考古学报,2018(1).
[51]魏继印.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J].考古学报,2019(3).
[52]郭荣臻.新砦文化农业综论[J].农业考古,2019(6).
[53]魏继印.新砦文化时期的大洪水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J].南方文物,2020(2).
[54]顾问.“新砦期”研究[J].殷都学刊,2002(4).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9—51.
[56]赵春青,顾万发,耿广响.河南新砦遗址发掘再获重要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7-06-02(8).
[57]闫付海.新砦二期文化性质新论:上[J].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18(6).
[58]闫付海.新砦二期文化性质新论:下[J].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18(7).
[59]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83—191.
[60]陈星灿.何以中原?[J].读书,2005(5).
[61]郭荣臻,曹凌子.新寨文化动物器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22(2).
[6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7(10).
[6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43—44.
[6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J].考古,1961(2).
[65]徐旭生.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1).
[66]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J].考古,1977(4).
[67]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J].文物,1978(2).
[68]秦小丽.中国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域关系: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陶器动态研究[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54—163.
[69]V GORDON CHILDE.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
[70]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J].考古,1959(4).
[71]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J].文物,1985(8).
[7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53.
[7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C]//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97—110.
[74]焦天龙.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J].南方文物,2008(3).
[75]张国硕.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J].中原文物,1995(2).
[76]李维明.河南密县“新砦”“双洎河”称名辨异[C]//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院刊: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132—134.
[7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89(2).
[78]黄克映.从河南信阳孙砦西周遗址谈我国人工养鱼的起源[J].古今农业,1994(3).
[79]王豪,武志江.河南信阳孙寨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到周代遗存[N].中国文物报,2016-09-27(8).
[80]赵辉.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J].考古,1993(7).
[81]《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63—164.
[82]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J].考古,1999(1).
[83]王仁湘.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J].文物季刊,1999(3).
[84]赵春青.论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原则[C]//赵春青.史前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97—406.
[85]许宏,俞钢.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J].世界历史评论,2021(1).
〔責任编辑:成彩虹〕
————————
①“新寨”学界此前多称“新砦”,实系地名的误写,已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该错别字问题,参见李维明:《河南密县“新砦”“双洎河”称名辨异》,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博物院院刊》(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20年,第132—134页。
——探访酿名斋郭勇孝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