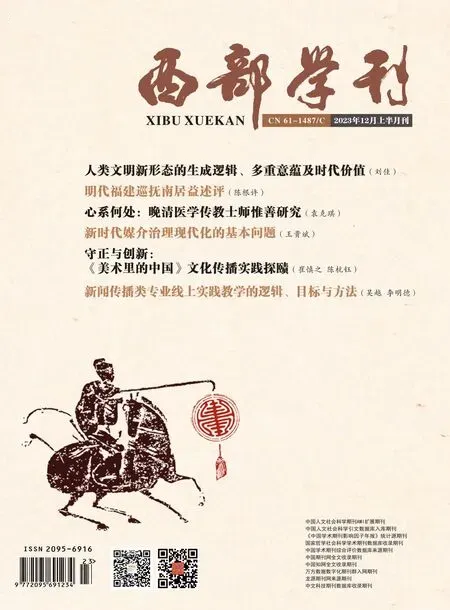心系何处:晚清医学传教士师惟善研究
袁克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3)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各传教团体不断扩大在华的文化教育医务事业,传教士分工则更为精细[1]。此时,医疗传教亦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手段,师惟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便是这一时期来华医疗传教士中的一员。1864年5月17日,他受英国基督教卫斯理会(Wesleyan Mission,后中译名循道会)派遣,以传教医生身份抵达汉口,在华中地区医学传教七年。虽在华停留时间较短,但师惟善是汉口乃至华中地区第一位医学传教士,他不仅创办了湖北第一家西医院——汉口普爱医院,还对湖北一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师惟善的关注范围包括中国传统医疗实践、中国草本药材的释疑和应用、中国地理与物产、中国人生活习惯与地方习俗、地方俚语以及中外关系等方面。他在上述领域著述颇丰,有大量文章发表于当时国内的主流外文刊物。由于师惟善在华居留时间较短,其文章多刊发于外文刊物,当前学界对其研究相对不足。目前已有学者在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近代湖北医疗事业发展以及近代中西医药交流等研究中对其在华经历有所提及,但关注点多集中在师惟善在汉口地区的医疗实践,对他医生之外的诸多活动挖掘并不充分,这使一个医生身份的师惟善形象被固化下来。但师惟善在汉口期间的生活是多元且丰富的,除医疗服务外,还包含诸多对华探索,在期刊上实时发表的文章,不仅反映了他在华期间的心路历程与思想感受,亦是研究晚清湖北风物的重要记录。本文以师惟善在华著述,尤其是其在华期间发表的刊物文章以及期刊读者对其文章的回复为中心,考察他在汉口期间对中国的调查与认识、其在华期间的思想感受与不足,力求展现一个全面、立体的师惟善形象,并以此为切入点讨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普遍关注之问题。
一、善于思考的医生
师惟善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医学系,于1855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此后直至1863年来华,师惟善行医于欧洲大陆与英国本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其来华时他已是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会员和伦敦国王学院预备会员[2]。观其来华前履历可知,师惟善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医疗训练,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这为其在华期间可以熟练应对各种医疗问题做了准备。
师惟善在汉口的首要工作是完成医疗服务任务,这是为学界讨论最多的一点,但以往学界关注的多是医疗工作的具体事功,即每年收治多少患者、医治了哪些疾病、进行了多少台手术,在这种描述下师惟善成为平面的“医匠”。除了机械的医疗工作,师惟善热衷于思考其在华遇到的医疗问题,尤其注重立足于本地环境考察当地病例,避免将教条的医学知识带入到治疗之中。以在晚清发病率较高的眼病为例,师惟善将引发眼病的原因归纳为:“1.强烈的太阳光;2.来自北方的剧烈风沙;3.清朝人的发型导致眼睛没有头发的保护;4.当地人对眼部健康不重视,在轻微发病时没有处理;5.营养不良。”[3]此种结合汉口一地特殊地理环境进行疾病原因思考的案例还有许多,诸如霍乱、结石病等,这反映出师惟善在医疗工作之余,积极调查思考,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此种善于思考的态度亦随着普爱医院年度报告的出版发行而备受好评。例如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对包括普爱医报在内的医院年报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通过医院年报可以获取当地医疗卫生情报:“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与印度医学领域的有趣信息,或者是从医学角度看到的社会情况。”[4]
师惟善虽然是受过系统教育的专业西医,但并非挟技自傲、闭门造车之人,他更乐于与中国本地医生进行交流。师惟善通过交谈、演示以及互赠书籍等方式与当地医生取得联系,并日趋频繁[5]。一方面,师惟善会观察当地医生的医疗实践。例如,他曾对当地民间治疗方法“白水神符”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报道,将其定义为“奇怪的医疗实践”(curious medical practice),并通过教务杂志询问在华传教士,可见其对中国当地治疗手段的好奇[6]。同时,师惟善从当地医生治疗中分析中医理论与西医的差别,把当地医生描述的“以毒攻毒”“以热制热”的治疗手段与西医中顺势疗法与对抗性疗法做比较,在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本土的医药实践[7]。另一方面,师惟善与中国本地医生的交流体现在双方交换药材[5]。此方法不仅可以增进双方信任,亦可使中国本地医生对欧洲药材更加青睐。通过与中国当地医生的交流,师惟善加深了对中医药的认知,使其能够结合自己的西医知识给中国传统医药“他者”建议,即中国医生将自身积累的医疗经验与西方解剖学知识相结合,并配以中国充分的本土药材,这会取得巨大的成就[8]。
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其最引以为傲的医生身份的范围内,师惟善常常寻求自身认知外的知识,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身边与医疗主题相关的事物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思考。这反映了师惟善善于学习、研究的特质和对中国的满满兴趣。
二、忠诚的传教士
作为医学传教士,师惟善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即救死扶伤的医生和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亦是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所具有的共同身份。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发轫之初,传教士与之是一对绑定的“双生子”,二者相互促进,繁荣于各条约口岸。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医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沟壑,医学传教士在使用医学这一手段时逐渐发现,其传教士与医生的双重身份愈发难以调适,在此背景下“传教”与“行医”之争贯穿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直至二十世纪,“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意义在世俗的浸淫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9]。那么师惟善是如何调适医生与传教士的双重身份呢?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探究。
师惟善在华活动处于教会医院进入条约口岸的初期,这一事业仍在蓬勃发展的初生阶段,行医与传教的矛盾并没有过于激化,师惟善自不用二选一式地取舍,但其对这两项任务是有所偏重的。师惟善更偏重医学传教的宗教属性,认为教会医院的传教属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教会医院的更高目标是将上帝的品格和启示展现在中国各阶层面前,其在医报中宣称: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this work of philanthropy with the higher aim of bringing the character and revelations of the Divine Being before the Chinese of all classes.”
“the hospital is not set up as a trap to catch the weak and the suffering, but to teach them that humanity and sympathy are essential parts of the gospel of mercy.”[10]
师惟善认为在诸多传教手段中,医疗传教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人利益和信仰,呼吁人们注意医院的宗教目的。他的这一倾向亦得到了当时一批在华传教士的支持,故虽然普爱医报所记录的传教成绩差强人意,但他在其他传教士中得到了声援与支持。如W.T.M.在评价师惟善医报时认为虽然通过医疗手段进行传教的结果有些不尽人意,但医疗传教在消减中国人敌意、促进传教方面作用匪浅,故不能因此而停滞放弃,应该在其真正见效之前怀着爱、耐心与信仰坚持这一工作,以实现其中华归主的最终目标[11]。
师惟善对基督教宗教活动在中国开展充满关切,这是当时在华传教士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安息日问题[12]。在此问题上,师惟善更倾向于从中国文化习俗中寻找答案,致力于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而其此类倾向,亦不仅限于宗教方面。他对数字“7”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关于数字“7”的民俗到俚语、成语等文化现象,皆被纳入其讨论范围,但其发现,虽然数字“7”在中国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与计时意义,但与安息或休息并无关系[13-14]。为了更好地在华传教,师惟善对于早在唐朝便在中国存在的各种带有基督教渊源的宗教及分支予以批判,认为它们的存在以及在中文中冒犯性的称呼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传教事业产生不好的影响,应该对其予以放弃[15]。可见师惟善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研究。
师惟善积极参加传教团体,注重以团体的力量推动医疗传教事业。他不仅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汉口支会的书记,亦和汉口其他的传教士组成了“汉口医学传教会”并担任书记。由此可见,师惟善在履行医生职务的同时,亦不忘其传教士的身份,甚至在主观倾向上更偏向于传教职能,这为研究医学传教中宗教与医学之争提供了很好的个案视角。
三、中医药专家
随着师惟善对中医药兴趣渐浓,他开始研究中药并调查当地的药材市场,这项工作的开展方式为文献研究与实物研究相结合。首先,师惟善翻阅了大量中西文献。中外文材料包括大量欧美汉学家、博物学家、医疗传教士关于中国、印度植物和药材的专著、文章以及未刊手稿,中国海关有关这一内容的出版物;中文材料包括中国古代百科类书籍和药物文献,包括《尔雅》《广群芳谱》以及《本草纲目》,其中师惟善尤重《本草纲目》[16]V。其次,结合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如汉口的霍布森(Hobson)曾赠予师惟善许多药材标本[16]V,以供其将实物与文献对照。汉口是当时重要的药材集散中心,师惟善有机会收集到更多药材,其在文章中坦言汉口是一个巨大的药材市场,这里聚集了来自四川、河南、山西、湖南、河北等省份的药材,为其查询药材以及进一步测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7]。再次,运用近代西方生物学和化学知识进行中药鉴定研究。例如师惟善曾使用显微镜来鉴别区分“猪苓”和“茯苓”,并通过化学式来确定“猪苓”不含有淀粉[18]。由此可见,师惟善对中药的研究称得上全面。最后,在医疗实践中使用中药。例如在汉口普爱医院中“高良姜”被用作健胃滋补的药品,师惟善评价其有极佳的效果(excellent effect)[16]10。在认识与实践多层面上对中医药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他对中医药的认识,也为其在中医药领域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础。
师惟善利用自己闲暇时间研究中医药并非孤军奋战,他注重将自己的疑问与研究成果通过期刊、报纸分享给西方在华群体,其与中药相关文章主要发表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上。师惟善的投稿热情很高,且并不是单方面分享,亦注重在报刊上与志趣相投者交流,是这些报刊上讨论中医药话题的热点人物。笔者将其在期刊、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归纳为询问相关中医药知识、介绍中药、回答有关中医药的询问与质疑三类。
第一类文章是师惟善对研究中医药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分享和询问。虽为医者,但面对中国这块陌生土地上完全不同体系的医药知识,师惟善难免会有疑问。报刊则提供了一个互助平台,解决外国人在华遇到的问题。此类文章包括:询问其观察到的奇怪医疗现象,如师惟善于1868年12月在《教务杂志》上介绍并向在华群体询问了“白水神符”现象;求助有关中医药的书籍,如其1868年12月在《教务杂志》上介绍自己研究中药的进度并向在华西方群体求购有关中医药书籍[19];询问中国境内相关药材信息,此类询问多发布在《中日释疑》中,包括女贞、冬青、甜槠、曼陀罗、冬虫夏草、木槿、暹罗根、Sumbal root[20]、硫或锑相关物质[21]、郁金香[22]。虽然是询问,但师惟善的问题往往可以引起他人兴趣与回复,如医疗传教士德贞就“白水神符”问题在《教务杂志》上回复师惟善[23],并以此为引子,写了八篇关于中医药的系列文章[24],可见师惟善的询问增加了在华西方人对中药讨论的热度。
第二类文章是师惟善分享有关中医药的研究成果,对中医药的推介或分享对中医药的思考。据笔者统计,师惟善先后在《教务杂志》《中日释疑》《字林西报》与《北华捷报》上相继介绍过黄连、红茶、佛手柑、中医实践中的顺势疗法、腊树与蜡虫、猪苓、肫皮、菖蒲、石菖蒲、野菊花、广木香、苍术、蚊烟、皂矾、青矾、绿矾、胆矾、蓝矾以及大量药材的中西译名。一方面,这些文章带有科普性质,师惟善对多数药材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包括中英文名称、外形、产地、自然属性、药用功效以及如何分辨。以黄连为例,师惟善连发两篇文章对其进行推介,不仅指出前人(Morrison,Hobson,and others their copyists)将都带有苦味的黄连(Hwang-line)与龙胆(Gentian)混为一谈,还在植物学意义上指出黄连即金合欢的根(It is really the root of the Justicia paniculata/Acanthaceoe),并与几种带有苦味的药在植物学上做了区分,还叙述了黄连的外形、产地、市场,同时指出黄连具有镇热、治疗痢疾等药用[25]。另一方面,师惟善推荐中药的行为包含其对西方在华群体的关心,希望给在华西方人提供便利。例如鉴于殖民地居民苦于夏日炎热、蚊虫以及瘟疫困扰,师惟善在《字林西报》上向在华西方群体推荐菖蒲、石菖蒲、野菊花、广木香、苍术等药材来消灭虫害、抵抗瘟疫[26]。
第三类文章是师惟善对有关中医药话题的回复。首先是回应报刊上其他学者关于中医药的提问,此类文章有师惟善在《中日释疑》上的答复文章“The Chinese Words for Opium”[27]和“Hernia in China”[28],即是回复该刊上有关中国鸦片和疝气情况的询问。其次是回应其他学者对他有关中医药研究的质疑与建议,其间文章往来还引起了有趣的误会。起因是1869年7月16日,师惟善在《字林西报》上刊发了一则中国关于外国人的谣言,即传教士诱拐儿童,以人体器官入药。师惟善从医学的角度为中国人辩护,认为中医药中有以人入药的传统,以及西方医生在华的解剖行为易使中国人误解,呼吁在华西方人尊重东方传统[29]。1869年12月7日,师惟善在《字林西报》上刊文抗议洛杉矶药品检验员伍斯特(Dr Wooster)在《伦敦中国报》(London and China Express)的言论,即声称中药是可怕且难以形容的混合物(indescribable mixture and horrible substance),他基于中药的有效性对中药进行辩护并第一次以黄连举例[25]。这场争论引起了医学传教士德贞的注意,他于1870年3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On the Disgusting N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30]一文,指出中药以人入药的恶心,并指出师惟善7月16日文言中医以人入药与12月7日文为中药辩护相互矛盾,并指出师惟善所介绍的黄连知识中的错误。师惟善在1870年4月5日的《字林西报》上刊文,解释其前两篇文章并非矛盾,同时再次强调应该尊重中医药,反对以偏概全、笼统地对中医药进行否定[31]。师惟善又在1870年6月的《教务杂志》上发文,对德贞所指出自己中医药研究中的错误表示欢迎,甚至愿意将手稿交出,一起完善这项工作[32]。可以看出,对于学术上的建议,师惟善是乐于虚心接受的,但是对于中医药的无端指责,则是坚决反对。
正是在这些研究的积累上,师惟善完成了《中国药物学和博物学新释》(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一书,这是他在华期间对中医药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一经问世,便备受好评,如博物学家汉璧礼称赞该书是中国药物学的最佳作品,伦敦《柳叶刀》杂志亦对其评价很高,该书十分畅销,甚至在印度和欧洲大陆亦有不错的销量[33]。除了商业上的成功,该书在学术上亦有深远影响,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医药的重要参考材料,如《西药释略》曾在前言中感谢该书对中国本土药材的整理[34]。至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师图尔(George Arthur Stuart)在此书的基础上增订药物,写成《中国药物学(植物王国)》一书,可见其在学术上的传承及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师惟善对于中药材的研究称得上全面,且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这一特殊时期研究中医药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医药的研究不仅吸引当时西方人对中医药话题的关注,亦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四、充满热情的汉学家
除从事医疗实践与中医药研究外,师惟善对其所处的中国充满关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他的本质身份是在华传教士,其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反映着传教士以宗教人身份在中国的生存状态与诉求取向。陶飞亚在其《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初论》一文中,将“圈内人”即传教士在报纸杂志上的声音归纳为中西语言的翻译、基督教活动在中国的开展和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礼仪宗教等方面的介绍。经过笔者梳理后发现,师惟善对中国调查研究的文章几乎涉及上述的每一个方面,可见其在华活动的代表性。以上主题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如何让中国人接受自己,另一则是如何更好地了解其身处的国家。
传教士进入中国首要目的是传教,语言不通则是其要面对的首要挑战,故中西语言翻译成了传教士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师惟善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其对中国语言的掌握愈加熟练。他虽以英文写作,但凡文章中涉及重要名词,都会标注汉译以及音译,这让读者不仅可以识其字,又可以知其音,方便了传教士在中国对这些词汇的使用。师惟善对此类词汇的翻译涉及医疗名词、中草药、地理名称、中国日常物用、宗教名词等,可谓是十分广泛。师惟善对地方俚语充满兴趣[35-36]。其对地方俚语的研究范围多在湖北地区,对不同俚语的含义、适用范围做了详细的阐释,可见其对地方社会的细致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师惟善并不只局限于对中文的翻译介绍,而是深入讨论中国语言背后的文化与社会现象。例如,在调查地方俚语时,师惟善对中国人讲话时好引用经典贤文这一现象进行探讨,认为中国人习惯将语言蒙上神性化的光环,这种现象使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具有优良的道德。这种论述反映了晚清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道德形象进行解构和重构的一种趋向,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对于中英翻译,师惟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当前西方科学、艺术等思想传入中国与希腊文化传入罗马做比较,认为虽然在一些专业词汇上汉语需要暂时屈从于西方语言,但最终汉语仍会占据主导地位。他希望中国人可以在这场文化交流中更多地吸取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呼吁西方人亦要摈弃私利而致力于在中国各行各业留下真理的伟大原则[37]。此种看法显然与其传播宗教的目的同向。
除了上文讨论的对于基督教有关活动的探究,师惟善对中国的研究还扩展到风俗文化方面,他认真观察眼前不同文明下的中国社会,对汉口丧葬习俗、中国人初一十五斋戒、寺庙武僧等带有宗教色彩的风俗进行了调查[38-40]。对于这些习俗,师惟善会将其与基督教观念相比较,以此分析基督教与中国的联系。同时,对于有悖于基督教理念的社会习俗,例如汉口地区的儿童葬礼中为防止去世的孩子感到孤独而用稻草给其作伴,师惟善并未从宗教上对其表示批判,而是对此行为表达了同情。但仍需注意,虽然师惟善对中国的调查研究中无一不显示其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我们对其所精通程度不宜过于乐观,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始终是处于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在文章中,可以见到有关中国典籍的询问与讨论。如师惟善曾询问孔子“roast pig”这一典故[41],而同期他正在回答湖北地方俚语“烧猪”,此实风马牛不相及;又如他曾对庄子《逍遥游》一文中的“大鹏鸟”进行讨论,却在文中寻找现实中的对应物[42],这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不通透的。
最后,师惟善对中国及其周边地理情况颇感兴趣,许多文章皆围绕此主题。在他的文章中,师惟善对这些地理名词及沿革进行辨析、翻译,尤其是一地多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配有中文名音译[43-45]。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中英对照中国、日本、韩国、安南、暹罗、缅甸、海峡及临近国家地点人物、部落和教派名称词汇表》一书。在1869年12月刊登在《教务杂志》的信件中,师惟善对出版该书的计划做了介绍。该书主要涉及中国及周边地区地名、人名、朝代、部落、宗教,尤其是对那些困扰读者和翻译者的别名进行了厘定,此后其在期刊上所发表有关地理文章也多限于此范围。师惟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热情,起源于西方人对中国地理认识不足的不满,尤其是西方人靠发音的相似性去猜测辨别中国地名造成许多误解[46]。不难发现,师惟善对地理的兴趣亦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地理超乎寻常的关注,据统计,《教务杂志》历年刊发汉学研究文章中地理地域类文章共有138篇,其数目仅次于宗教[47]。
由此观之,师惟善对中国研究不仅涵盖较多主题且成果亦丰硕,其作为近距离接触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近代汉学家之风。
五、仍是一个外乡人
身处异国的师惟善对中外关系颇为关切,不仅关注外国人在华形象与地位,还十分关心当时在华外国人的生活。同时,他对在华外国人群体的态度是有等差的,从其文章中可见对俄罗斯似乎抱有成见,该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吵。
首先,对于其自身的在华地位与形象。师惟善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中国人可以平等以待包括他在内的在华传教士与其他外国人,他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人用轻蔑的语言称呼外国人这一现象表达不满。例如,在翻看汉阳县志时,他对上面将外国人冠以“夷”这个称谓进行抗议[48];在论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称谓时,亦对这些俗语化的名词表达不满[15]。正因为渴望被平等对待,师惟善对中国人的偏见亦较同时期在华西方人更少。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师惟善亦在一些方面为中国人辩护,例如其从中国中药传统入手,对中国人盛传的关于外国人将中国小孩迷晕至教堂然后以其器官做药的谣言表示理解[49]。此外,他呼吁西方人应该放下对中国的傲慢无礼。但是,他的根本立场还是站在殖民者一边,未能摆脱其作为西方人固有的傲慢与偏见,面对天津教案,主张将天津摧毁以祭奠这场事件中遇难的外国人[50]。
其次,在文章中体现了对在华西方社区的关心。例如,对于影响在华外国人心情的教案问题,他会派助手远赴河南去进行调查澄清[51]。作为医疗传教士,他对在华西方群体的医疗卫生与健康情况都格外关注。他在医疗实践中所积累的生活经验,诸如夏日的解暑、驱赶蚊虫、保存衣物以及消毒等方法,都毫无保留分享给在华西方社区。对于西方国家在华政策,他积极建言,如建议使馆颁发在华登记证时要配上中文,以便减少实际中遇到的困难[52]。
相比于对传统意义上西方群体的关怀,师惟善对俄罗斯的态度却偏向负面。在多篇文章中师惟善对俄罗斯专制传统、在华传教毫无贡献等进行抨击,其对俄罗斯的看法在读者中引起颇多反响。许多读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反击其观点。例如德贞曾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俄罗斯的历史,以此反击师惟善的观点。由二者交锋来看,师惟善对于俄罗斯的看法是带有个人偏见在其中的,但其观点亦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基督教传教士对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批判与不满。
六、结语
本文以师惟善在国内英文期刊上实时刊发的文章以及著作为中心,试图在其医生身份之外,展现一个更为丰满立体的师惟善形象。通过研究可知,师惟善不仅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医生,亦是一个忠诚的传教士、中药材大师、汉学家。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究在华基督教群体与师惟善在期刊上的互动,以及将师惟善的研究与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群体的关注热点比较,力求将师惟善的个人轨迹,融入到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群体中。从中可见,师惟善所关注的医疗实践、中医药、中西语言翻译、基督教在华活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礼仪宗教以及中外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亦是在华传教士群体所关注的重点。师惟善之研究成果,亦非无根之木。从师惟善对中医药和中国地理的研究可知,其认识的形成是立足于西方已有之积累、中国传统之典籍以及个人实践活动之上的。师惟善对中国的诸多研究,既是自身兴趣的所在,也是在华传教士所面临的实践需求所致,即努力了解脚下陌生的国家,以使自己可以更好地适应异国的生存环境,更好地被当地人民所接受。随着师惟善对华了解的深入,其对中国人有关于西方的谣言与恶意多了一份理解,并试图从文化角度去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师惟善终是一个外国人,其仍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之上,当中外发生冲突时,果断站在西方一边,并妄言对华实施惩罚,故仍不可过度高估这一群体对华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