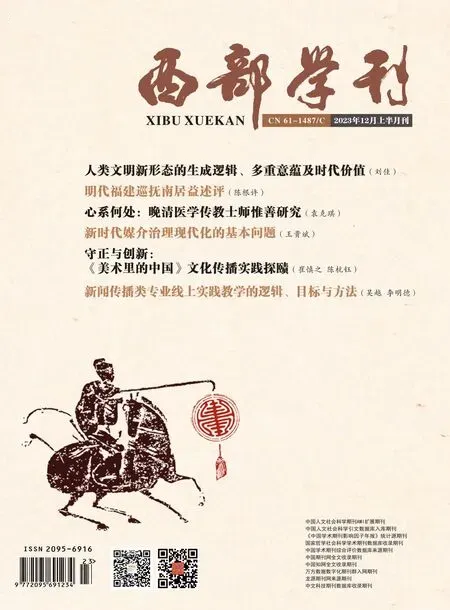明代福建巡抚南居益述评
陈根许
(渭南市临渭区政协,渭南 714000)
南居益(1566—1644年),字思受,号二太,陕西渭南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辛丑科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三迁广平知府,擢山西提学副使、雁门参政,历任山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等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仕劳思休,回归故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被起用为太仆寺卿,次年擢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改任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时魏忠贤当道,“衔居益叙功不及己,格其赏”[1],又诬其依傍门户,将其削籍为民。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南居益被起用为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十月春,后金兵分三路进攻京师,因南居益在通州守城戒备有方,升工部尚书。不久,又因疏救郎中王守履试炮而炸失职,被崇祯以徇私之名罢职归籍。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南居益被攻陷渭南的李自成义军所拘。次年春,被以炮烙之刑拷饷,不从,绝食七日而死。本文现就南居益巡抚福建的有关史实作一探讨。
一、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
南居益的主要功绩是其在任福建巡抚期间,率领军民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正在老家修建宅园的南居益“蒙熹宗皇帝擢臣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地方”[2]30,皇帝明确要求南居益“地方有事,不得过家迁延”[2]31。接到皇命的南居益不敢怠慢,“星驰至海上,审视情形,料理戎事”[2]31。
南居益所任福建巡抚,正式官衔为“巡抚福建地方兼提督军务”[3]。他任福建巡抚时,正值“红夷”猖獗。据《明通鉴》记载,“红夷即和兰国,其地在西南海中,近佛郎机。其人深目长鼻,发须皆赤,时谓之红毛番”[4]。在南居益任职福建巡抚前,荷兰人已盘踞澎湖,以互市为名,屡犯厦门、漳州等地。
南居益的前任,福建巡抚商周祚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二十四日曾上奏朝廷,“红夷自六月(天启二年)入我彭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鳌”,“遂犯中左,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察海澄。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5]1。面对荷兰人的反复侵扰和欺诈,福建当政者踌躇无策,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便听其择便抛泊”[5]1。当地“闽人或言战,或言抚,相持未决”,“海上奸民多为夷耳目,以我情输夷,又馈之食”[6]369。
甚至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四月初三日,福建巡抚商周祚上报的“红夷遵谕拆城徙舟”[7]1奏折中还为荷兰人辩解,称荷兰人是因求市不利,“疑吕宋截留其贾船也”,“先攻吕宋,复攻香山澳,俱为所败,不敢归国,遂流突闽海,城彭湖而据之,辞曰自卫”“又其志不过贪汉财物耳,即要挟无所得,渐有悔心。诸将惧祸者,复以互市饵之,俾拆城远徙。故弭尔听命,实未尝一大创也”[7]1。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福建当局对荷兰人的迁就忍让甚至纵容到了何种程度。
不仅福建地方对荷兰人姑息纵容,就连朝廷在商周祚再奏红夷“所约拆城徙舟及不许动内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测”[8]3,提出集兵筹饷备战时,朝廷还下旨“上以红夷久住,着巡抚官督率将吏,设法抚谕驱逐,毋致生患”[8]3。朝廷态度暧昧,福建当政者犹豫不决,影响到前线将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荷兰人进侵旧浯屿、中左所等地时,虽有“总兵一鸣冒矢石督战”,但“中左所副总兵张嘉策闭城自守,不肯应援,身不至海上,诡言红夷恭顺,欺罔旧抚。甚有言其通夷,必欲迁延以成互市”“纵敌观望,不止一嘉策,彭湖、中左、浯屿、铜山各处守汛将领皆有失事”[9]4-5。
荷兰人对漳、泉沿海的不断骚扰,导致闽地沿海战乱不断,商船停运,民心浮动,米价腾贵,也逼得沿海居民或通夷或为盗。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南居益作为一个足不涉江南、目不睹沧海波涛的西北人,临危受命,以身许国,慷慨赴难。他一到福建,就义无反顾深入漳、厦抗夷前线,了解夷情民情,走访官商士民,共商拒夷之策。
南居益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受命,七月到任(天启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商周祚还有奏疏,以此推测南居益实际到任最早应在天启三年七月)。经过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实际考察,八月二十九日,他上呈奏章条分缕晰后,以忧国忧民之心提醒朝廷,如不迅速扫除红夷,“浸假而数年之后,根穴日固,扫除更难,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左抚顺城也”[2]31。明确提出“狡夷之反复必不可理谕,互市之要求必不可以苟从”,“羁縻之术已穷,天讨之诛必加”[10]。他在与前线将士反复商讨后,果断提出集兵筹饷、选练兵卒、举贤任能、排兵布阵的具体措施。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国事为重,“疏劾南路副将嘉策蓄缩不堪,所当革任”,认为“闽海利害,唯闽人能谙”,大胆举荐“于俞咨皋、陈文扬二人内推一人代之”[9]5。
南居益的奏疏直击夷乱要害,既有入情入理的形势分析,又有有理有据的应对策略,促使朝廷改变了对“红夷”以抚为主的策略。天启帝下旨“红夷狡诈,为患方深,巡抚官着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一切安攘事务,但听便宜行事”[11]。接到朝廷谕旨后,南居益运筹帷幄,开始筹备收复澎湖的战斗。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秋,南居益巡视漳、泉,荷兰人派奸民洪燦、池贵携书信并明珠、珊瑚、番镜等珍玩,企图贿赂他。南居益慷慨陈词:堂堂中国,岂贵此物。随即招集文武官员及士商百姓于演武场(戚继光练兵地)焚毁宝物,将奸民洪燦、池贵枭首示众。他赋诗明志:“明月珊瑚贵莫言,番书字字逛军门。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将献至尊。”[12]以实际行动激励将士警示奸民,回击犹豫不决者,向士民表明“版章一寸地,亦是我门庭”,“有再模棱者,请看刀头斑”[13]35,宣示与荷兰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月二十六日,被激怒的荷兰人在首领高文律(荷兰人称法尔森)率领下,进犯厦门海域。南居益亲至海上观敌料阵,与谢弘仪等将领商议,设计诱使荷兰人进入内港,用火急攻荷兰人船舰,烧毁敌舰一艘,重创一艘,活捉高文律等60余人(1)见周凯:《厦门志》卷16《旧事志》,乾隆《泉州府志》卷56《武迹》亦载,生擒夷酋是在厦门鼓浪屿海战中。,荷兰人死伤无数。捷报传到朝廷,熹宗皇帝下旨:“该省剿夷奇捷,南居益运筹制胜,懋着勤劳,总兵官用心督率,并有功文武将吏,俱候事平优叙。”[2]31-32
这次战斗荷兰人“精锐略尽,气势始衰”[2]31-32,但他们依然盘踞澎湖,筑城待援,伺机反攻。南居益不以小胜而止,誓收澎湖,随移驻漳州,亲自“浮海至金门,乘小艇出没波浪中”[6]369,观察敌情,部署兵力。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正月初二,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准备,南居益利用春汛之机,命守备王梦熊率3 000余人,驾木船突袭澎湖镇海港,一面与荷兰人激战,一面筑城为营,荷兰人退守风柜城。正当荷兰人困窘之际,其统帅牛文来律率援兵赶到,荷军锐气又生。见此情形,南居益调都司顾思忠赶赴澎湖镇海港与王梦熊会合。到四月,南居益担心师老财匮,亲至海面巡视后,命令巡海道孙国桢等率兵第三次增援澎湖。孙国桢等率兵勇于五月二十八日赶到娘妈宫前,在观察敌情、地形后,确定了先攻敌舟、后攻敌城的策略。六月十五日,孙国桢等誓师攻敌,南居益现场亲授攻敌策略,调集火器接应。王梦熊、顾思忠等分兵把守陆路要害,阻止敌人弃船登岸。一时明军水陆齐进,荷兰人无招架之力。七月二日,荷兰人派使者赴镇海营谈判,求放开一条生路。七月初三日,明军分三路直逼风柜城,荷人首领牛文来律竖白旗降,哀求“乞缓进师,容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14]。
七月十三日,荷兰人拆城运米下船,只有风柜城东门大楼三层,是荷兰人原首领高文律的居所,荷兰人留恋不愿拆除。南居益命令王梦熊等直抵风柜,尽行拆毁。最后,荷兰人乘十三艘船只逃向台湾。南居益命令明军以犄角之势扎营,防止荷兰人返回偷袭。至此,南居益收复澎湖战斗胜利结束。“是役也,曾无亡矢遗镞之费、血刃膏野之惨,而彭湖信地,仍归版图,海洋商渔,晏然复业。”[15]
捷奏朝廷后,熹宗皇帝下旨,“红夷屡败,俘获酋目,余众遁逃,地方宁靖。一应善后事宜,还加意料理”[2]32。并采纳南居益意见,“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2]32。
南居益总结这次与荷兰人战斗的过程,以自己的观察、思考向朝廷上报了善后十策,从增兵、设将、筑城、驻营、添饷、屯田、用人、赏功、备战等方面对坚守澎湖、保漳泉海靖地宁提出了建议。当时魏忠贤阉党当道,因忌南居益叙功时未提及他们,不仅搁置南居益善后建议,还百般诬陷,阻止为南居益等人赏功。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南居益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南居益又被免官还乡。
二、治理地方,举贤劾奸
南居益在驱逐“红夷”、收复澎湖的过程中礼贤下士,广纳各方意见;不计个人得失,直言敢谏;拒贿锄奸,严治军民;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不顾安危,身先士卒。这些都展现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事不避难,果敢担当、舍身忘己的士人品质和文武兼备、智勇双修的安邦之才。闽人将其比于周之南仲、汉之张良,称南居益“德业品望,柱海撑天。建人所不能建之功,守人所不易守之节,爱民则赵公之冬日,接士则程子之春风。兹膺高擢,公论允符”[16]。
南居益在福建的短短三年时间,除平夷靖海、建立不世之奇功外,还履行巡抚职责,举贤劾奸,宣教化民。南居益甫到福建,在了解夷情民情,广泛听取士民意见后,就举荐平倭名将俞大猷之子俞咨皋为副将。平夷备战之暇,他与当地名流贤达游历品茗,折节下士,亲自拜访漳州名人、隐士张燮,上书朝廷,希望委其以重任。在澎湖海战关键时期,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七月初十,南居益又特意疏荐海道孙国桢、水利道葛寅亮。平夷战后,南居益在奏捷议功疏中,对上至前巡抚商周祚,下至州府县官、游击参将,乃至捕盗、掌号官等文武官员各叙其功,提议朝廷表彰晋职。
举贤任能,不仅使南居益得到了福建士民的拥护,树立了他在士民心中的威信,也为他取得收复澎湖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举贤可以赢得人心,但纠劾就需要勇气。作为巡抚,南居益刚到任,在了解以前战况后,毫不留情疏劾已拟提任徐州总兵的南路副将张嘉策“蓄缩不堪,所当革任”。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二月十八日,南居益疏纠当时的文坛名流、福建提学副使钟惺“百度踰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17]788。他参劾兵备道曾舜渔“耳目如壅,精神似愦”[17]788,显示出嫉恶如仇、不趋炎附势的性格特点。
任职期间,南居益还在福建广交贤士名流,一方面与他们赋诗唱和,切磋励志,以文化俗,因诗宣教,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抗夷主张,争取士人的支持和理解。现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玉屏山虎溪岩及福清石竹山、福庐山,福州乌山就有南居益题诗摩岩石刻七处。其中日光岩题诗《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寤之池直夫》,是在厦门海战、智擒高文律后,南居益与谢隆仪、池显方登临鼓浪屿的唱和之作。南居益诗曰:“野人惊问客,此地只临鸥。归路应无路,十洲第几洲?”池显方和诗:“虽小亦门户,如何不一登?新城盘曲折,古寺俯稜层。易服瞒村老,寻香妒墅僧。渡澎诸战舰,帆展候风乘。残石伐将尽,惟余一古丘。烟开生远岫,潮至乱平畴。去岁如遭虎,今年再狎鸥。全凭藩屏力,吾得卧沧洲。”[18]这两首唱和诗既有景色描述,也有对平夷时局的态度,更有收复澎湖的期盼和决心。
在福建期间,南居益与同安望族名士池显方交往甚密,池显方还拜南居益为师。南居益“获夷犹未喜,喜获一士奇”,并与池显方“舟中谈终日,语语吐肝脾”。经常对池显方“谆谆加切规”,“寄音再三慰”[19]30,以至于池显方经常夜梦恩师。两人之后经常书信来往,互寄问候。池显方誓言“某拟秋初,经建州一别,若不来则梦魂不安,纵师能容之,某志不能自容也”[19]30。
南居益与闽地名士蔡复一、徐兴公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诗文唱和,书信往来,互相交流,共议国事。他不仅资助徐兴公刊刻《鳌峰集》,还请张燮代为作序。尤当一提的是,澎湖之战后不久,南居益曾因叶向高的关系,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交集。虽因平夷之战刚刚结束,南居益担心艾儒略为荷人奸细,而未对其传教做出明确支持,但也未明令禁止,默许当时儒生、士人与其交往,这显示了南居益宽容开放的待人之道。这一不经意的举动,为天主教在福建传播开了方便之门。
南居益与士人交往只是他宣化谕教的一个典型事例,在他与当时平夷将领、地方官员书信往来、面谈交流中,也多循循善诱以启心智,谆谆教诲以化风俗。闽人称他“修政、修教,即须臾间已纤毫毕照、振举靡遗;八郡从兹脱汤火而就枕席”[20]。
三、对南居益任职福建的评价
南居益在福建任巡抚短短三年时间,平“红夷”,收澎湖,建不世之奇功;举贤纠奸,廓清吏治,除官场积弊;以文辅政,宣教化民,引领时风世俗。其生前身后,闽人在福州、泉州、漳州、澎湖等处为其建祠以祀,文人雅士称颂其功绩的诗文更是不绝如缕。尤其是平靖“红夷”,与荷兰人战斗取得的胜利,震动朝野,给当时内乱不断、辽战屡败的明王朝争得了颜面,提振了朝野、将士的信心。正如他的学生池显方在《平红曲》中所说,“一方息征战,半壁欣恬澜”“边将皆如此,复辽亦何难”[13]35-36。
收复澎湖“为国家复得一块疆土,为闽人除却百年隐祸”[2]33,不仅挫败了荷兰人占据我国沿海的图谋,也对其他殖民者以警示,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讲,南居益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澎湖一战的胜利,改变了当时闽人长期对外夷或畏或倚的态度,极大地激发了闽地士民的家国情怀。作为北方而来的官员,南居益为福建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风气。他举贤劾奸,整肃官场因循畏难、相互掣肘的陋习,凝聚了八闽士心。同时,在与文人士大夫交往中,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影响了当地的世风民俗。
南居益“清正不染,兼饶才略”[21],闽地士民称赞其“体貌温而不类北人,意气重而不类今人。风雅优而不类仕人,韬钤娴而不类文人。真一代之杰,而社稷之臣欤!朝廷报之,当凌烟麒麟;国士报之,当吞炭而漆身也”[22]。由此可见,南居益在福建的巨大影响和积极贡献。
----论戴·赫·劳伦斯的哲学随笔《天启》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