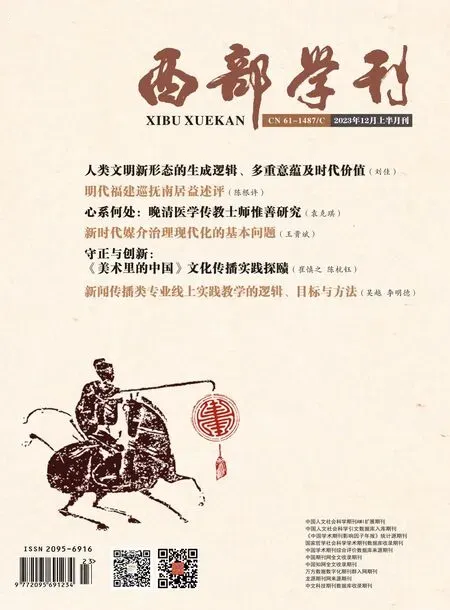新时代非遗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
康 璇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乐山 614000)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数字化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算升级,其发展与应用能为非遗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更多元的发展路径、更广阔的传承空间、更生动的体验场景、更丰富的传播业态和更深厚的价值内涵。据此,本文就新时代非遗数字化发展路径作一探讨。
一、我国非遗发展历程回顾
(一)以抢救性保护为主,数字化单向助力发展
早期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1]。二十一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并先后发布了相关的保护宣言或公约,各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及时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方针。通过系统性抢救及时地记录、整理、保存了大量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这一阶段非遗的保护属于本真性保护。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运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保护。同时,《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要求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品的数字化、网络化。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对数字化记录、保护非遗做出了具体的安排。2010年,文化部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则是非遗数字化的具体实践。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非遗数字化进行了规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由此看来,数字技术对非遗的支撑是一种“线性融合”的路径,即科技以技术的形式单向赋能非遗,并且这种技术支撑集中在那些技术更易于介入的领域。
(二)向全面性保护转变,数字化与文化双向融合
非遗的活态流变性与脆弱性决定了保护是其精神内核延续和文化价值呈现的前提和基础,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的再生产实现形态演进和价值转化[2]。第一是向生产性保护拓展。2012年,文化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出,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遗领域实施非遗生产性保护,并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100个企业或单位。第二是向活化利用拓展,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也包含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有力地践行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有效地坚守住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好中国文化基因。基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这一时期我国更加重视非遗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加重视释放非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既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的“采取措施”“振兴”的精神,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的“合理利用”与“开发”的规定[3]。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时期发布了较多的文化数字化政策,促进了文化与数字化进一步深度融合,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保护在政策鼓励下得到了较大发展。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同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标志着文化数字化正式以国家级工程项目的形态起步。2016年底,《“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其中,提出“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文化数字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此后,关于文化数字化的文件密集出台,给非遗数字化发展创造了契机。2019年,《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数字化已经从粗放式发展迈进系统化、体系化建设的阶段。2018年至2020年,中央多次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5G网络和数据中心建设等,在架构端为文化数字化提供了物理支持。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提出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两个数字化目标,标志着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迈入了新阶段。2021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非遗保护规划》《“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不同角度明确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路径。2022年3月,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目标。10月,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意味着文化数字化从部门层面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联合发布的《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利用渲染处理、感知交互、近眼显示等多项关键细分领域技术推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化,为文化沉浸式和交互式消费提供了更切实的实现路径。
非遗数字化政策的数量逐渐增加、专业性日益增强,体现着国家对包含非遗在内的文化数字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另外,非遗和数字化呈现双向融合的趋势。基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数字化赋能非遗发展,同时非遗反哺数字经济。非遗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非遗的文化内核与历史积淀让数字经济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更有趣的灵魂。
二、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特征
(一)延展性:从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
非遗数字化政策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时代发展的必需。我国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从“物质”层面延展到了“非物质”层面,非遗工作从“靠政府投入”层面转变到了“靠市场自身发展”层面[4],非遗数字化也从“静态保护”层面延展到了“活态保护”层面。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所拥有的聚合性特征,非遗呈现散点性特征,非遗数字化在本真性保护阶段实施的抢救性保护从数据著录和数据库搭建开始,侧重于采集、记录、存档等基础性工作。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技术的限制与传统介质的弊端,通过图文扫描、立体扫描、全息拍摄、数字摄影、运动捕捉等采集技术和数据库、磁盘阵列、光盘塔、光纤和网络连接等存储技术更好、更完整地保存了非遗的基础性数据。非遗数字化应用则向数字化链条后端的利用、传播延伸,侧重于“活态利用”。非遗数字化立足非遗的资源属性,充分利用新载体、新媒介,将非遗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推动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产生,实现非遗价值的延续、转化、确认、传递与增值。
(二)人本性:从关照遗产向关照传承人转变
延续一直以来的文物保护思路,非遗保护在开始阶段更重视对遗产本身的保护,比如对于口承文学的载录、对于剪纸艺术的审美关照等。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深入让人们逐渐认识到,非遗是一种言传身授的“人体文化”,其较高的人体依附性决定了“人”才是保证非遗守正创新的关键要素,因此政策重心转向非遗“传承人”,建立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2013年,文旅部利用录像、录音、照相及多媒体等现代技术,全面、真实、系统地对1300余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拍摄口述史影像。2022年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与腾讯微信联合举办“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人数字技能专题培训,助力提升非遗传承人的数字技能。2022年,抖音直播增加了非遗传承人与大众的接触面。
(三)立体性:从时间节点向空间构建转变
非遗的传承具有时间的线性特征,其时间性体现为“世代相传”。综观非遗保护的思路演变和政策演进可以发现,早期的非遗数字化基于抢救性保护目的而开展的数字化只能记录某一时间节点“在场”的非遗样态,并不能记录、保存非遗产生的环境、历史的演变等要素。突破时间线性的局限需要向空间借助力量。2010年,《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以保护非遗为核心而进行整体性保护。截至2023年1月,全国已设立2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数字化技术在场景营造、场馆构造、区域建构方面的运用,把现时横截面下对某一非遗的关照进一步拓展到关注非遗项目及其所处的文化与自然生态空间,为研究非遗的产生、发展、壮大、衰落等提供了新路径,有效地推动了非遗的立体化保护,表明了未来非遗数字化的发展重点。
(四)交互性:从单向传递向多向互动转变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一种单向传递,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数字技术在非遗的应用中不仅起到保护、传承、记载、交流、传播的作用,而且结合当下新人群、新需求、新技术、新场景,采用新方式在新的知识生成、经验传递上发挥作用。比如,非遗馆借助VR、AR、NUI技术和3D全息投影技术等数字化手段,达到“再现+参与”的目的;传统工艺技艺数字化利用多媒体虚拟教程与实物制作实现交互体验;传统节庆仪式类数字化借助多媒体展示实现场景营造与氛围营造;传统手工技艺数字化以奇幻的视觉和交互体验形成现代科技辅助下的新型传统文化展示空间,在互动游戏体验中达到知识传播等目的,最终让非遗的内容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多向传播,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新的创造者、分享者。
(五)共享性:从局域认知到广域共创
前期非遗数字化的主体集中在研究机构或专业领域。国家级非遗保护专业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建立为数字化提供了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持,同时如天津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参与了非遗数字化工作。随着非遗数字化的传播与普及、数字化企业的兴起与发展,非遗数字化从早期的政府、研究机构扩展到广大群众、市场主体。新兴的新媒体数字传播平台、数字经济创新企业借助自身优势介入非遗传播、销售等领域。另外,无线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公众参与消费非遗数字化成果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需求侧文化大数据为非遗数字化提供了海量数据信息。
(六)规范性:从临时抢救向建章立制转变
随着意识的觉醒与认知的转变,非遗数字化始于抢救、兴于制度。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诸多促进非遗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各地出台非遗保护条例,自上而下贯通的体制机制为非遗数字化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建立了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5],进一步推进着非遗数字化建设。
三、非遗保护的发展路径优化
(一)稳步增强物理连接,实现文化资源数据化
现阶段,非遗数据种类繁多、数量宏大,归集难度较大,且大量非遗数据处于最初样态、素材化程度低,物理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防范数据安全问题的现状特征,要求我国加强数据库建设,形成主体多元、规模多样、内容多彩的各类非遗数据库,需要主动对接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要求,尽快确立统一的文化数据标准,实现专业资源分类和系统资源整合,并在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的国家文化专网的框架下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原则把现有零散的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数据关联,展现中华文化整体风貌[6]。
(二)大力激活数据价值,实现关联数据资产化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华文化数据库关联下数据资源的有意义交换和整合为数据资产化奠定了基础。非遗供给侧数据和需求侧数据以表单、图形、语音、数据库、代码等各种数字形态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资产。要推动文化数据资产评估与管理形成行业规范,激活非遗数据价值,要从供给侧到需求侧、从资源端到生产端再到消费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工程化方法对非遗数据进行采集、解构、关联、重构、呈现,萃取、提炼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所囊括的非遗记录成果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建立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用于新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6]。
(三)利用好文化新基建,实现创新创造智慧化
数字技术丰富了文化存储介质、革新了文化演绎形式、开辟文化传播渠道[7]。科技创新是推进非遗数字化的技术底座,它促进技术从“选择性介入”文化走向“整体性融合”。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融合算力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基础设施与国家文化专网、数据超市、区域性集群式智能计算中心、具备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的文化计算体系等文化领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要求非遗数字化推动全环节与全链条的数字化,加强“非遗+”系列融合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
(四)逐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数字消费场景化
发展新场景,激活新业态,数字化的发展和应用给非遗提供了更多样的呈现方式、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和更具创造力的想象空间。因此,可以运用全息呈现、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新型体验技术,增强非遗的体验感;运用智媒体、电竞、直播、短视频、云游戏、数字人/虚拟偶像、智慧文旅等新业态,增强非遗的参与性;利用移动互联、数字传播、智能终端、自媒体等“大屏”“小屏”无缝切换,增强非遗的便携性;运用元宇宙的3D建模技术,增强非遗的虚拟仿真化。数字技术推动了非遗空间格局重构和价值体系重塑,非遗数字化能更好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更多地共享保护发展成果,更有利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坚实底气和强大动力。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