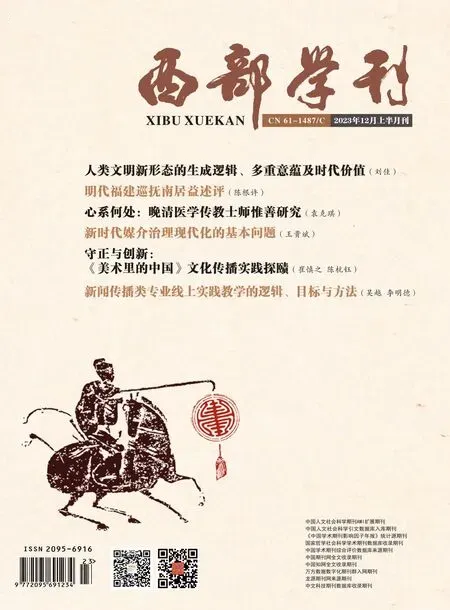齐格蒙特·鲍曼对大屠杀的伦理批判
李广博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家庄 050024)
伴随工业化的推进,人类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文明、和谐的社会之中,然而进入二十世纪这种梦想破灭了,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大屠杀(1)“大屠杀(Holocaust)”特指二战期间(1933—1945年)由纳粹德国政权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对欧洲数以百万计犹太人实施的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运动,纳粹党提倡一种极具恶意的种族反犹主义,在此期间他们通过有规划性建造集中营或隔离区,以大规模枪杀和毒气窒息的方式残忍屠戮了约600万犹太人。事件。在此之后,众多哲学社会学家都对大屠杀产生之根源做了深刻反思,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至2017年1月9日,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以下简称鲍曼)将大屠杀这种群体恶性事件的产生归结为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1]5。
一、现代工具理性的膨胀
理性肇始于人类对自我的确证,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人的主体意识逐渐挣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和压抑,逐步走向觉醒,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确定特质的“先天性”受到了世人的贬低,人们将其看作是一种不完美的非理性遗留物,一种可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麻烦,开始转向追求一种完美的、充满确定性秩序的理性之路。时至今日,伴随着理性力量的逐渐壮大,现代社会经济日益增长、政治日益民主、文化日益繁荣,然而理性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导致了个体道德责任悬浮,最终酿成大屠杀等悲剧。
现代性大屠杀的萌生源于理性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按照个体行为中手段和目的的不同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指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56,即价值理性强调个体行为动机和手段的正当性与否,重视情感与精神层次的需求;“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56,即工具理性强调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漠视个体情感与精神价值。鲍曼所批评的正是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1]24。他指出,这种无冲突的状况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即以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工具理性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湮没,造成全体间普遍的道德冷漠或道德败坏,最终导致大屠杀的发生。
二、理性片面膨胀的后果:剔除即创造的“现代园艺文化”
受理性的影响,现代性所追求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充满秩序、规范、确定性、整齐划一的社会,鲍曼将其概括为“园艺文化”。“园艺文化”就是要剔除杂草,呵护人工培育的植物,因此在“园丁”看来,清除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园艺文化”的现代文化,它以追求完美有序的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为目的,而在这些异类中犹太人因其“历时的连续性和共时的自我认同”之双重意义的分离变得尤为突出。
鲍曼认为,作为“杂草”的犹太人的特殊性在前现代社会就有根深蒂固的基础。首先,犹太人的特殊性表现在与基督教的张力之中。犹太人既是基督教的先驱,同时又对基督教心存不满和怨恨,“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基督教实质性的他我(alter ego)”[1]49。因此,犹太人既是基督教自我认同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基督教所极力驱除的内容。其次,犹太人的特殊性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犹太人作为“流动的阶级”(mobile class)在前现代社会一直扮演着“中间人”角色,他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联系下层阶级的纽带。对上层阶级而言犹太人是肮脏粗鄙、野蛮无知的下等人,对下层阶级而言犹太人是高高在上的剥削阶级,因此犹太人就成了“两种互相敌对和矛盾的阶级仇恨的目标”。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阶级间交流的提升,犹太人原本由于时空因素影响而被分隔的形象相互遭遇,受到社会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共同唾弃,并演变为一种“元不协调性”(meta-incongruity)。最后,犹太人在历史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3],是一个处于成长中的或现存的各民族的世界之中的无民族的民族。由于犹太人分布地域广泛且具有明显的、难以同化的犹太特征,因此对每一个民族而言,犹太人都是打入其内部的敌人,他们的存在抹杀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对追求普遍确定性秩序的现代生活的打破,因此必然要将其“剔除”。
总之,伴随着理性膨胀引发的“剔除即创造的园艺文化”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犹太人这一“三棱镜群体”成为现代园艺文化中的“杂草”,对犹太人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彻底消灭变成了一种创造性行为——创造一个具有永恒秩序、充满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世界,由此产生了现代种族主义,为现代性大屠杀的产生埋下隐患。
三、工具理性与科层制的合谋
现代种族主义认为某些群体存在着不可消除或矫正的缺陷,试图采取极端的方式将这些群体消灭。但是种族主义仅仅为大屠杀的发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现实操作中,“为了实现有效性,现代灭绝性反犹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官僚制度联姻”[1]104。只有在科层制与现代理性的合谋之下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筹集大量资源、对各部门统筹协调以及进行细致劳动分工等任务,实现设计者、实施者、旁观者和受害者这四者之间的密切配合。
首先,大屠杀的产生离不开纳粹高层官僚和专家不遗余力的精密且准确的设计。现代科学由于受到“将理智从情感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1]143等主张的影响,已然变为一个不存在任何道德规范的价值无涉领域。德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目标仅仅是追求更高的知识或纯粹的理性,在他们眼中只有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4]。因此,当纳粹官员下达研制更快速、安全、高效的“剔除”方式时,专家们迅速地提供了精确的设计方案,如奥斯维辛集中营、高效的毒气室等。
其次,个体道德责任的悬浮——现代官僚制度运用细致劳动分工方式使执行者与自身行为结果脱节。鲍曼指出,细致劳动分工的存在导致人们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产生距离,个体仅仅以角色面目出现在生产链条中,由此导致责任的悬浮,造成“责任依赖于角色,而不依赖于完成任务的人”[5]22。每一项成果背后所依靠的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协作的整体,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造成最终结果的直接原因。因此,劳动分工就造成了在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之间的距离,这意味着在现代官僚体系内的官员眼中对结果只有一种抽象、孤立的认识,他们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命令所造成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并执行命令;同样,细致劳动分工最终造成个体的道德关注只会是更好地完成自身工作,所谓“道德”只能归结为努力做一名高效、专注、勤劳的人的戒律,这就造成了个体责任消失,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
再次,现代官僚制度充分利用“异类恐惧症与种族教化”,导致民众变成了道德冷漠的旁观者,甚至为大屠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大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1]100。鲍曼指出,个体与他者之间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到我们对他者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纳粹分子试图将犹太人隔绝于德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外,以期望民众对大屠杀保持道德中立态度。在生活上,纳粹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犹太人做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分,并强制性地将他们驱赶出德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排斥、贬损并拒绝他们;在精神上,充分利用民众对犹太人的“异类恐惧症”,即在普通民众看来,犹太人是“无民族的民族”,他们的存在是对自己完美、幸福平静生活的打破,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已经变成了超越人类感情的一个‘非个人化的’、抽象的和外来的实体”[1]103。这样,伴随着精神层面与生活层面中亲密性的消失,就导致德国民众自身的责任归于沉寂,道德冲动被淡化,他们变成了道德冷漠的旁观者,造成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时千百万人毫无异议地坐视暴行发生。
最后,现代官僚制度诱使受害者基于自身理性与加害者展开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大屠杀的发生。为了实现使受害者积极配合屠杀行动的目的,纳粹分子采取了一系列充满理性而有序的策略。一方面,纳粹分子努力诱使犹太人社区中的传统精英与之合作。为此,纳粹政府将犹太社区完整保存下来并让犹太人的传统精英仍旧保持领袖地位,借此利用犹太委员会的势力消弭犹太民众反抗力量。另一方面,纳粹利用犹太人个体谋求自我保全的理性思维诱使大多数受害者与之合作。在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之下,理性玩起了“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文字游戏,这样犹太人经过理性思考后出于自我保全的利益或牺牲少数人以寻求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解救而主动与纳粹政府进行合作。通过一系列举措,纳粹政府造就了在屠杀过程的每一阶段(除最后阶段)都有个体希望被拯救的现象,因此犹太人出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就会选择与纳粹进行合作。
鲍曼通过以上分析提出,现代社会通过以工具理性作为精神支撑,以现代官僚制度作为手段,使大屠杀中的设计者价值无涉、实施者责任悬浮、旁观者道德中立以及诱使受害者理性合作等方式将这四者紧密结合起来,共同造就了惨绝人寰的现代性大屠杀。
四、唤醒个体道德责任与良知
在大屠杀事件背后充分显示了现代理性与科层制的合谋造成了个体道德责任与良知的缺失,使大量不道德的行为在民众眼中变得合理。在鲍曼看来,使大屠杀产生的这两个因素——理性与科层制——在现代社会仍未消失,因此绝不能把大屠杀看作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特殊的、绝不再发生的群体恶性事件,应当对其充分警醒,避免再次出现普遍性个体道德泯没现象。那么,在现代性进程中究竟应当怎样避免类似于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在鲍曼看来唯一的解救途径就是唤醒个体的道德责任与道德良知。
唤醒个体的道德责任与良知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要承认道德之先验性。与涂尔干将道德本质归因于社会性的强制力量,认为道德源于多数人认同的观点不同,鲍曼指出道德具有无可救药的先验性,道德的来源是前社会性的,“道德上的先在不是通过本体的缺席,而是通过本体的降级和废黜来制定的。道德是对存在的一种超越,更精确地讲,道德是这种超越的一个机会”[5]83。因此,个体的道德能力先于社会产生,它存在于社会交往范围之内,产生于自我对他者负责的社会关系之中。只有重新确立道德之先验性才能够明确道德源于人类本身所固有的、不可磨灭的自然情感,而非源于社会中掌握权力的个人制定的或少数服从多数的道德规则,重新唤醒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二是要重新确立个体对他者负有无条件的、绝对的责任意识。在自我与他者之关系上,鲍曼区分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将他者看作是个体行动的阻碍,行动者的任务就是确保忽略他者,在这种相处情境中道德是一种外来侵扰;第二种类型是萨特式的“他人即地狱”,在这种相处模式中,将道德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和约束;第三种类型是列维纳斯式的“为之存在”关系,即在“亲近”(proximity)的道德律令领域当中作为交互主体的我——你之关系是不对称的,个体对他者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邻居的面孔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责任,优先于所有自由的允诺、所有的合同和所有的签约”[6]。
鲍曼显然赞同列维纳斯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理论,他指出,道德的内容就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这种责任并非出于任何契约性的义务亦或是对自我利益的计算,它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我们必须实现由人与人之间冷漠状态的“与之共在”到个体主动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与义务的“为之存在”的转变,道德责任与良知的唤醒不在“我是我(I am I)”中,而在“我为……(I am for)”中[5]89。只有通过自我向他者无条件的伸展,在对他者负责的过程当中,我才能够如我所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我,进而克服自身的“蛋白质恐惧(proteophobia)”,以包容之心同“陌生人”(包括同犹太人)和平相处,承担对他者的道德责任。三是承认个体道德之多样性。鲍曼提出,现代社会所追求的“道德普遍主义”其实质不过是通过压抑个体内在道德冲动来引导个体朝某一社会既定目标前行。“道德普遍主义”是在个体的本质或本性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但是真正的道德是难以捉摸的,它具有非目的性、非互惠性和不可签约性等特点。鲍曼认为,“道德责任仅仅单独存在于对个体的质询中,并且要由个体来承担”[5]63,所以只有当个体顺应自身的道德冲动倾向,主动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才能够避免成为道德冷漠的旁观者、价值无涉的设计者乃至责任悬浮的实施者。
五、结语
鲍曼通过对现代性大屠杀产生的原因进行细致分析,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要将道德主体从由理性建构的、追求绝对秩序的僵硬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承认道德之先验性,实现个体与他者关系由“与之共在”到“为之存在”的转变,让个体重新直面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后现代社会中避免类似大屠杀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