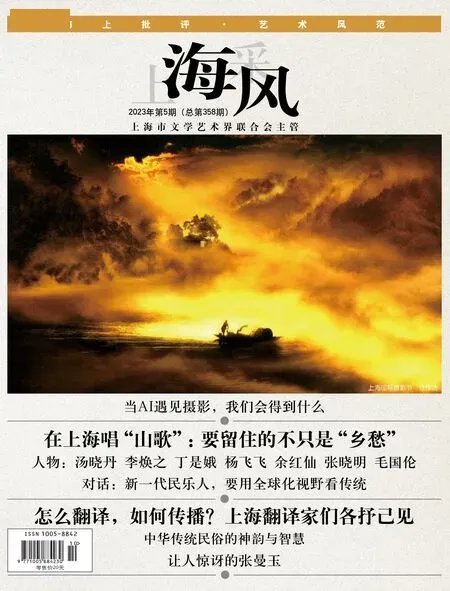林文月教授的上海望月
■ 张 凤
林文月是华语世界的散文名家,我非常喜欢她的文字。她是台大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在这三个领域中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当地时间2023年5月26日早上9时许,林文月在美国加州过世,享年90岁。
1990年她的儿女已留美,先生郭豫伦也退休,多住在加州。1993年夏,她从台大中文系荣退,即移居旧金山团聚。深居简出的林教授,2002年应燕京学社杜维明社长邀请来哈佛演讲。哈佛燕京楼午餐会演讲会场,学者文友纷纷慕名而来,林教授谈文学、说艺术、论翻译,似质而自有膏腴,似朴而自有华彩。优雅的作品与她的姿容一样,收放都饱含高风的韵致,是我们散文界经典,传颂不歇。
本人因协助举办负责伴同参与,而能亲炙获得赠书,日后还幸能得到她的指教联系。后微信盛传,她在沪日故居,文友纷纷热心询问,由此得知林教授与上海的一段情缘。
林文月教授1933年生于上海日租界,精通中日双语。她虽祖籍彰化,但都没住过彰化,从小在上海生长。
林文月教授出身名门,《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是她的外祖。外祖伉俪生男名震东,为其舅。连横弥留之际对震东说:“日本侵华野心明显,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就在此一战。”为孙取名连战,寓意自明:自强不息的意思。舅舅连震东是外祖的独子,表弟连战是连氏二代单传,妹夫为曾任台北市长的黄大洲……在林文月的作品中,不少谈及连家的种种。
林教授父亲林伯奏,学商,曾任华南银行首任总经理,继创新亚实业。原生台湾溪州刘姓,后被北斗林家领养,小时刻苦自强。1916年,考取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分校商学系,受板桥林熊征资助,并担任林夫人盛宣怀五女盛关颐的秘书。其父为毕业于该校的首位台籍留学生。毕业后,任职日租界,林府八个儿女,六位诞生在上海,父亲在江湾路540号自建了第一栋住宅。
林文月勾绘这幢房子的内外:客厅壁炉地毯摆设精美,饭厅有专供宴客的大圆桌,楼上是卧室,穹形小阳台在二楼中央部分,幼年她常喜欢坐在这里,看小火车定时驶向江湾,夏天居高临下看斜对面游泳池入口处的人群。战胜时偷窥街上的紧张混乱。
母亲在前院种了桃树,后院有供孩子玩耍的秋千、单杠和沙坑。篱笆围起的住宅,生活平静优裕。家里不缺帮佣,女佣苏州人珊妹最疼她,三餐间有两顿点心。父亲出入以汽车代步,周末去江湾打高尔夫球,归家时带来五颜六色的棒冰或新鲜玉蜀黍。后院有孩子秘密探索内心的迷园。
江湾路往闸北的上学路上,她每天走过花园坊,父亲和新感觉派台籍作家刘呐鸥合伙在此建造有33栋红砖小洋房,再往前是运河,河上有船,有舢板。
其父曾遥遥回忆:留沪同文书院读书时,台湾总督长谷川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谈,要找位既通国语、沪语、日语,又晓悉闽南语及台湾情况的人做通译,学校便派其父担任。同文书院二战后日人自上海撤出,即迁返日,于爱知县复校,改称爱知大学。
她外祖连横晚年,并未如诗所写移家西湖上。十里洋场的虹口一带,比较安静,外祖外婆住闹中取静的公园坊,两层楼的小洋房,安享比在台湾更清静的老年生活。她家住在江湾路,与外祖隔着草坪,方便往来。林文月的出生给了外祖含饴弄孙的安慰。其母曾说:别看你外公写起文章来笔力犀利如剑,抱着你的手,可是小心翼翼抖抖颤颤的啊。她学步不久,外祖带去对面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散步,她总是顽皮地跑在前面,身着白府绸衫裤瘦高的老人,不得不辛苦弯腰来牵她的手。
她上学时,先跨过窄窄的铁路,沿着虹口公园,下去是整洁的北四川路。马路中是有轨电车的终站地段,她常和同学围看检票员颇具英雄气度地拉接电缆将电车掉头。人行道由方块石板铺成,这段路是她最喜爱的。她说很少规规矩矩走这段,不管有无同伴,总顺着那石板跳行,有时也踢石子跳移。夏天高大梧桐树遮蔽了半条街;秋天常有落叶追赶在脚步后。
路的中心点,靠近学校边,有一排两层洋房。前是果菜市场和杂货的店面,其母常去购物;后段是她爱去的文具店和书店。早晨因为太早和赶时间上学,店门总是锁着,只能从那沿街大玻璃窗望进去。夏季,常碰到朝阳晃朗反射耀目,不易看到店内的景象;冬季,窗上结了冰霜,只见白茫茫的一片,禁不住会用戴手套的指头在薄冰上随便划道线,或涂抹个字什么的。
就读国校一年级时,功课既少又轻松,通常十一点半就放学。要等父亲吃午餐,不会太早开饭,她几乎每天都在归途溜进那书店,去看不花钱的书。那时的学生不作兴带钱,她家更有不成文的规矩,要等上了中学才可领零用钱,身上当然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倒也可以天天在那书店里消磨上半个钟头,入迷地看带图的《伊索寓言》等书。
她最喜欢嗅闻那印刷精美的新书,那油墨真有特别的香味!边看书边闻书香,小小的心里觉得快乐而满足,若不是壁上鸟鸣钟声,真忘了肚子饿回家。
朋友考据说是内山书店,她觉得书店十分大,四壁全是书,但那时她个子矮小,无法衡量。进出口处有柜台,轮流坐着中年男子和老妇人,大概是母子吧。经过柜台,她却是永远不付钱的小顾客。其实那样溜进溜出,倒真有点儿像进出图书馆一般自在,母子从来没有显出厌嫌;那中年人还常常替她取下伸手够不着的书。老人弯着腰坐柜台后,她每回礼貌地鞠躬,老人都把眼睛笑成一条缝,叫她明天再来玩。日子久了,他们都变得有些熟稔,偶尔伤风感冒有事请假,甚至还会关怀问:昨天怎么没来一类的话。
后遇倾盆大雨她一身湿透,老少店主以热食干衣救助照顾。电话告知其母雇了包车来接回惊心的她。
她从小喜欢读书,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生读书、教书,也写书、译书。始终做着与书本文字相关的工作结下了深缘。什么原因变成这样子呢?她不明白。只有一点可能:在幼时好奇的那段日子里,如果那书店的母子不允许她白看他们的书,甚至把她撵出店外,她对书的兴趣可能会大减,甚至不再喜欢。读书写作不可能只受单一影响。
她的文章常在小学作文比赛后被张贴公告同学阅读,但班长总不是她。五年级夏,因抗战胜利日本同学回乡留书家中,她读了不少日译名作:《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悲惨世界》《罪与罚》《茶花女》等,还有夏目漱石《我是猫》等岩波文库袖珍版的书。
零零星星的小事情,也点缀着生命的五线谱,经常在她不经意回头的时候,便会听见叮当作响,只是那些声音微弱得只有自己听得到。
1946年2月,全家在黄浦江的寒雾中搭船离沪。
总之,上海始终是她记忆中的故乡,强烈怀念。近年曾有几次可以回去的理由和机会,但她心中近乡情怯地步步迟疑,不敢贸然面对她童年许多珍贵记忆所系的地方。
阔别半个世纪,她才鼓起勇气到上海寻家访故居,林家旧宅那时还在,现已改造了。
但无论如何,这次回沪寻访,多多少少抚慰了她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