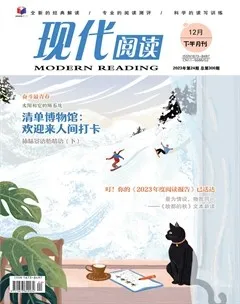寄海内兄弟(节选)
支线任务:请朋友李修文喝好酒
清单主人: 泥瓦工马三斤
在陕西汉中时,我住在城郊的一家小旅馆里写剧本,因此认识了终日坐在旅馆楼下等活路的泥瓦工马三斤,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听他说,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三斤重。
活路实在难找,打我认识他,就没看见什么人来找他去干活,但他跛着一条腿,别的苦力更加做不下来,也只好继续坐在旅馆外的一条水泥台阶上等着有人问津。
马三斤实在太穷了,在我送给他一件自己的羽绒服之前,大冬天的,从早到晚,他穿着两件薄单衣,几乎无时无刻不被冻得全身上下打哆嗦:他有两个女儿,而妻子早就跑掉多年了,所以,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也仅仅只够让两个女儿穿上羽绒服。
天气越来越冷,有时候,当我出了旅馆去找个小饭馆喝酒,便总是叫上他,他当然不去,但也经不住我的一再劝说,终于还是去了,喝酒的时候却又迟迟不肯端起杯子,我便又要费去不少口舌接着劝,劝着劝着,他端起了杯子,他一杯,我一杯,却总也不忘记对我说一句:“哪天等我有钱了,我请你喝好酒!”
没有等来他请我喝好酒的那一天,我便离开了汉中。原本我想跟他告个别,却接连好几天都没在旅馆楼下看见他。可是,等我坐上长途汽车,汽车马上就要开了的时候,却看见马三斤踉跄着跑进汽车站,只一眼便知,他显然生病了:胡子拉碴,头发疯长,一整张脸都通红得骇人。
等他跑到汽车边,刚刚看见我,虚弱地张开嘴巴,像是正要对我说话,汽车却开动了。隔着满溅着泥点的玻璃窗,我看见他刹那间便要落下泪来,只是在瞬时里,他就像是被什么重物击垮了,一脸的绝望。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下意识地对他吼叫了一声,吼叫声被他听见了,见我吼叫着对他举起了拳头,他先是怔住和呆滞,继而,也像我一般下意识举起了拳头。等汽车开出去好远,待我最后回头,看见他仍然举着拳头,身体倒是越站越直,越站越直。
自打与马三斤分别,又是好多年过去。我们二人一直都不曾断了联系。有时候,他会给我打来近乎于沉默的电话,有时候,他又会给我发来文字漫长的短信,每一回,在短信的末尾,他总是会署名为:你的朋友,马三斤。
我当然知道,那些无端与变故,好似蝮蛇一般在噬咬着他,可是,除了劝说他忘记和原谅,我也找不到别的话去安慰他。好在是,他终于将日子过好了起来:虽说谈不上有多么好,但总归比从前好。
去年夏天,他又给我发来了短信,说他的大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无论如何,他都希望我能再去一趟汉中,一来是为了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二来是他要兑现他当年的诺言,请我喝上一顿好酒。在短信的末尾处,他的署名仍然是:你的朋友,马三斤。
其时,我正步行在湘西山间,置身在通往电视剧剧组的一条窄路上,头上满天大雨,脚下寸步难行,但是,看见马三斤发来的短信,我还是一阵眼热。于是,我飞快地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去躲雨,再给他回复了短信,告诉他我一定会去汉中,去看他的女儿出嫁,再去喝他的好酒。在短信的末尾处,我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你的朋友,李修文。
结果,等我到了汉中,还是在当年的汽车站里,等马三斤接到我的时候,我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苍老像蝮蛇一般咬住了他:他的头发,悉数都白尽了,从前就走得慢的步子,现在则更加迟缓,乃至于一步步在地上拖着自己的腿朝前走。
可他不由分说地抢过我的行李,自己拎在手中,为了证明自己还能行,他甚至故意地走在了我前面;走着走着,他又站住,回头,盯着我看,看了好半天,这才笑着说:“你也老了,也有不少白头发了。”我便也对着他笑。
走到半路上,在一片菜园的篱笆边,他突然停住,先是亏欠一般告诉我,尽管他老得不成样子,但女儿要结婚了,他的老,还是值得的;说完了,再担心地看着我问:“你呢?你值得吗?”我沉默了一会,再请他放心,我想我活到今天也是值得的。听我这么说,他竟哽咽了,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
这时候,一天中最后的夕光穿过山峰、田野和篱笆照耀着我们,而我们两个,站在篱笆边,看着青菜们像婴儿一样矗立在菜园的泥土中。此时情形,唯有元人韩奕所写《逢故人》里的句子如影随形:
相逢喜见白头新,头白相逢有几人?
湖海年来旧知识,半随流水半随尘。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来见我》,有改动)
深度解读
以“蝮蛇”意象解读马三斤的苦难
文章中两处出现了“蝮蛇”——“那些无端与变故,好似蝮蛇一般在噬咬着他”“苍老像蝮蛇一般咬住了他”。
蝮蛇喜隐蔽潜行,暗处出没,伤人时非一击毙命,而是一圈圈缠绕、收紧,用毒液浸入人的躯体,以蝮蛇隐喻马三斤的苦难是非常贴合的。马三斤的苦难不具备戏剧性,而是如蛇噬咬一般磨人。文中对马三斤苦难的叙述,亦如草蛇灰线,隐约可见。马三斤出生只有“三斤重”,或可推测其原生家境贫苦;他跛足,为泥瓦工,“活路实在难找”,可知其生计艰辛;偏偏他又要担起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重担,生活更是捉襟见肘。这些苦难不是重大事故、不是天降横祸,它们只是躲不开的繁琐俗事。普通人的困窘,是沉默的隐痛。
作者没有刻意渲染马三斤的艰辛,避免了套路化的“苦难展览”,而是如话家常、顺笔道出实情。读者需细读、需联想,结合实际生活体验,才能领会马三斤生存之不易,才能明白为何“苍老像蝮蛇”让马三斤的头发“悉数都白尽了”。而只有读懂了马三斤的苦难,方可读懂马三斤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
思考:
汽车站离别之际的“举拳”行为有何深意?为什么马三斤短信结尾皆署名为“你的朋友,马三斤”?为什么重逢时马三斤会“担心地看着‘我’”?品读全文,寻找答案。
技法课堂
呈现电影般的画面感
“喝酒”寓意着马三斤与作者的情谊,是一条贯穿全文的明线。“女儿”则是马三斤人生的另一条隐线,故事情节围绕着两条交织的线索向前推进。随着故事的开展,“旅馆”“汽车站”“菜园”等场景的转换和“酒”“蝮蛇”“短信”“白头”等意象的反复出现,作者的情感在时间的往复和空间的叠映中得到充分的渲染和强化,整篇文章呈现出如电影一般时空切换、镜头交叉的画面感。不同时空的镜头和画面,被贯穿全文的两条线索紧密串联着,因此并不显得散乱无序,反而给读者一种现场观影的亲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