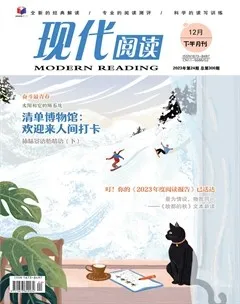景为情设,物我同一
同步统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
统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将《故都的秋》与《荷塘月色》组合在一起,大概因为这两篇现代散文都是情景交融的名篇佳作。但同是情景交融,《荷塘月色》的诗意世界与日常生活是格格不入的;而《故都的秋》则是情在景先,景为情造,景与情是高度统一并相互作用的。
“有我之境”:中国文人传统血脉里的秋天
透过《故都的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自然风物,还有作家郁达夫的性格禀赋、审美趣味和精神气质。这里的秋天,是他的生命安顿之地;这里的秋天,是他的心理投射之所。郁达夫深爱的故都的秋天,是真正的“有我之境”,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传统血脉里的秋天。
之所以被称为是中国文人传统血脉里的秋天,是因为这里的景总是与观赏者强烈的情感反应联结在一起,郁达夫的感知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细腻,清静是那样的让人享受,悲凉是那样的让人沉醉。北国之秋,固然有它与江南之秋在色、味、意境与姿态上的差异,但同时又未必不是郁达夫的那一份秋的情结,将北国之秋推向了极致的结果。郁达夫没有去寻找和选择故都具有代表性和具有标签意义的秋景,他对“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也只是一笔带过,他精描细绘的,是北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的寻常巷陌、秋晨院落、一碗浓茶,这里的树影蝉声、雨后斜桥、都市闲人,会让读者在行色匆匆中抽离出来,并以深度介入的姿态,体味到实实在在的秋意以及生命的自由与舒展。清静、悲凉、闲适、写意,这些由绚烂归于平淡的东西,只有在不急不躁的生活中,在时光的自然流转中,才能让人结结实实地感觉到;而那些声闻遐迩、车马纷沓的风景名胜,大则大矣,却并不是作者的情感倾向和审美意趣所在。
也正因为是中国文人传统血脉里的秋天,这里的“悲凉”便有了它不同于一般人眼里的悲秋情结。“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紫黑色比淡红色好,蓝色或白色又比紫黑色好,因为秋不应该是热烈的、鲜艳夺目的,而应该是淡远的、冷色调的、笼着轻愁和薄怨的。其实,这哪里是秋花的颜色呢?分明是辛苦而孤高的生命的颜色啊。这哪里是衰颓的秋草呢?分明是自然的美化与生活的艺术化啊。“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些亲切而熨帖的、半是欣喜半是忧郁的句子,更是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幽远而萧索的情愫。尽管“尘世难逢开口笑”,毕竟“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里的秋花与秋草,以及落蕊的寂然、微细、柔软,帚纹的细腻、清闲和落寞,都凝聚了作者的生命自觉与世俗关怀,说到底不过是中年心境与文人雅趣的情感投射。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无处不在的秋蝉的“啼唱”和“嘶叫”,似乎模糊了昆虫与人的界限,或许正是因为它的“衰弱”,它的行将告别,才与秋的况味和人的心绪高度自洽。
“一椽破屋”也好,“破壁腰”也罢——虽在闹市,宛如远村——我们都不难看出作者为情用景的心理倾向和审美态度。正如文章标题为“故都的秋”而不是“北平的秋”,大抵是因为旧时光更具稳定性,与清静和悲凉的氛围更加契合,也更能寄托遐思与幽情。而落蕊、衰蝉、凉风、冷雨、淡绿微黄的枣子,还有在秋实盛景之后接踵而来的西北风和尘沙灰土的世界,与其说这是秋天的常见物象,毋宁说这是作者情感的精微和巧妙的外化。秋天,这样一个盛极而衰、万物凋零的季节,最容易引发文人“向死而生”的感喟和“一岁一枯荣”的叹惋。而对这种残破的、感伤的、隐忍的美的欣赏,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对一般读者特别是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相对不足的学生而言,或许是一种挑战,但这也恰是我们在深度解读这篇作品时应该努力抵达的地方。
“真诚表白”:体悟直抒胸臆之“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大都会关注情景交融之“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抒胸臆之“情”,总觉得那些明白浅显的句子没有追问的必要。实际上,因为直抒胸臆完全没有遮拦和隐藏的缘故,更容易让我们把握北国之秋的特质,也更容易让我们看到郁达夫对北国之秋一往无前的痴情,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让我们在触摸作品感性的宽度的同时体悟其知性的深度。“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让我们体会到了作者“便下襄阳向洛阳”般的急切与兴奋;“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沉醉不知归路”般的痛快与喜悦。至于“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更是把对北国之秋的热爱与挽留推向了极端,甚至到了可以拿生命去交换的程度。
应该说,这些直抒胸臆之“情”是有助于我们完整地去理解和把握情景交融之“情”的,也是有助于我们去感受和体味作者对“清”“静”“悲凉”的那一份由爱作为底色的痴迷与偏爱的。
《故都的秋》不单是郁达夫对北国之秋的描绘、怀念与赞颂,更是他审美取向与人生态度的真诚的表达。“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每一处秋的画面之中,都能隐约看到“我”心醉神迷的影子。物我交融,神与物契,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相互渗透,浑然一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话语方式,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我们不仅可以由人窥景,同时也可以由景知人,在景与情的相互作用下得到情感升华和美的熏陶,而融情于景、情理结合的独出机杼的表达,也充分印证了郁达夫“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