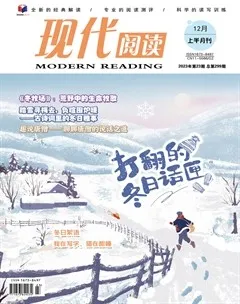迷人的月色与可疑的悲凉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一文的思想感情集中体现在“闲人”一词上。“闲人”之“闲”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内容?语文界似乎有着普遍的共识,即“闲人”既指苏轼的政治处境,也指他夜游时的心境;“闲”既有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又有贬谪的悲凉和人生的感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建议”中,更是作了特别的提醒:“要让学生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只有在了解作者被贬黄州、多年闲废这一写作背景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在分析文本与揭示主题时,都会给出“乌台诗案”以及苏轼的生平、作品等相关背景,然后顺势引出这里的“闲”不仅有悠闲自在,更有无可排遣的悲凉的结论。
那么,《记承天寺夜游》是否真的表现了“贬谪的悲凉”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它究竟写了什么。
记承天寺夜游
[宋]苏轼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是妙手天成、意味隽永的文言文典范,尽管只有85个字,却把事、景、情、理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让读者在月色无边、情韵悠长的绝美境界里流连难舍。
细写月之空灵境界,畅抒“闲”之乐趣
作者开篇即点明了具体的时间,将读者带入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直接写到了这次夜游的缘起:“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教学中,个别教师往往对“月色入户”缺乏必要的注意,却喜欢为“欣然起行”的动机随意加戏。事实上,每一个内心丰盈的人在月色入户的时候大抵都会生发感物寄兴之意,何况苏轼这样的“月光诗人”呢?所以,什么百无聊赖,什么愤懑不平,都落入了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的陷阱,我们没有必要离开人情之常和文本事实而在想象中寻找答案。“起行”且“欣然”,只能是因为月色,只能是因为月亮这个古往今来所有文人骚客永恒的朋友。不然,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2700 余首苏轼诗中,咏月诗居然有300 多首。“欣然起行”与“念无与为乐者”并不是先后相属的关系,“念”字隐藏着这样的信息:一个人赏月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如果此刻能有人与自己分享这一份闲适和喜悦就好了。这样,才有了接下来“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的行为。苏轼的“遂”是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轻描淡写间,暗示了他们心意相通的关系。而“怀民亦未寝”中,“亦”字可以理解为心有灵犀的惊喜,也可以理解为不出所料的欣然。
以上是叙事的部分,这部分最重要的句子“月色入户”是作者欲睡而未睡的原因,也是作者和朋友“相与步于中庭”的理由。尽管这里没有对月色进行具体描摹,但我们不难想见它给作者带来的美妙而强烈的诱惑。
接下来的写景部分用了18个字,可以说是无一字写月色,而无一字不在写月色。我们可能会特别注意“积水空明”“藻、荇交横”这些漂亮的语句,却忽略了“如”“盖”这两个与具体描写无关的虚词。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两个字,那种如真如幻、惝恍迷离的境界就完全呈现不出来。明明不是积水,却用一“如”字;明明是竹柏,却用一“盖”字。作者似乎始终处在将信将疑之中、欲明未明之间。这里的写景好似与月无关,却是对月光如水最生动的诠释。
上文所描绘的空灵境界正是为下面的抒怀张本的。“但少闲人”以“但”字转折,表达了一种超拔于常人之上的自得与旷达之情。这里的“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心无挂碍;是处境,更是心境;不是看清了一切,而是看轻了一切。“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作者的情感抒发始终围绕着月色和月色下的竹柏展开。是的,没有迷人的月色,何来这份悠然之情与自得之趣呢?
误读“贬谪的悲凉”,游离文本之外
毫无疑义,在《记承天寺夜游》的文本之中,我们是感受不到作者的任何“悲凉”的。这“可疑”的悲凉,不应该属于月色撩人的夜晚,更不应该属于浑然忘机的闲人。那么,所谓“贬谪的悲凉”是从何而来的呢?
应该说,它来自我们对“知人论世”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简单机械地运用。如前所述,“贬谪的悲凉”这一结论是在介绍苏轼生平之后“直给”的,而不是通过文本分析水到渠成地得出的。所谓“贬谪的悲凉”这一结论游离于文本之外,是把苏轼的人生际遇直接转化为此文蕴含的思想情感了。试想,即便在贬谪之中,作者的心就一定每时每刻被悲凉所笼罩、所左右吗?在苏轼夜游承天寺前的半个月,侍妾王朝云为年近半百的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使他欣喜若狂,“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他为这个儿子写的。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背景”而认定他的“欣然起行”与此有关呢?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同样,将苏轼的月下感怀和他四年前被贬谪的经历捆绑在一起,这种“知人论世”也是武断的。
背景的意义更多的是给文本解读提供线索和支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决定文本的主旨。换句话说,不能用背景的“有”来推断文本的“无”,不能用背景的“实”来改变文本的“虚”。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背景的介绍是为了使“他终于忘却了我的不好”的那根暗线更明晰—“我”与“父亲”的矛盾冲突在文本中若隐若现,“我”的许多表达是隐晦的,而这一切都可以在背景中找到答案。质而言之,不加分析地从背景导向主题,是一种简单机械的,甚至是凌空蹈虚的方法。《记承天寺夜游》中的“悲凉”之所以不足信,是因为它直接从背景中被剥离出来,并没有得到文本的支持。当我们引导学生在“闲”中读出悲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强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文本中移开,而让背景与主题建立起了无视文本而存在的抽象关系。这种用“知人论世”代替文本细读的倾向恰恰是当下的阅读教学中要特别警惕的,因为它会给学生一种暗示,似乎走进文本的精神内核,并不需要在字里行间去倾听作者的呼吸与心跳,而只需要对文本主旨做简单的对应和概念化的图解就可以了。
所以,众口一词的“贬谪的悲凉”,很可能只是一些人一厢情愿地强作解人而已。在一般人看来,贬谪总是一件不堪的事,但在苏轼那里,在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那里,这或许是不幸之幸—他远离庙堂,死里逃生,自食其力,终于成为一个心可以不为形所役的人,一个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
在同样作于贬谪黄州期间的《临皋闲题》中,苏轼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我们解读《记承天寺夜游》时,这一通达而潇洒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鉴与启示呢?
(注:链接《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