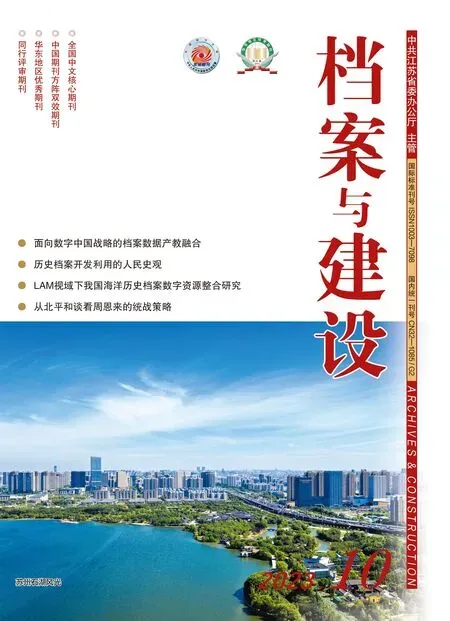曾三档案思想研究30 年(1992—2022):回顾与展望*
苏筱红 王闫芳 唐 蕙
(1.桂林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6;2.全州县档案馆,广西桂林,541500;3.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曾三(1906—1990)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理论的开拓者,作为国家档案局首任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首任馆长,他始终致力于建设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档案工作的经验和规律,形成了由其档案形成观、档案价值观、档案利用观、档案编研观等所构成的较为系统的档案思想。笔者希冀对三十年来曾三档案思想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回顾和展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继续发展和档案学理论的拓展研究提供启迪和借鉴。
1 研究的发轫:1992—2005
曾三于1990 年11 月28 日逝世,此后一年间,与曾三并称为“档案三老”的裴桐、吴宝康分别在《档案工作》(现《中国档案》)和《档案学通讯》上发表《追悼曾三同志》《沉痛悼念曾三同志》等文,既体现了对曾三的深情怀念,也表明了对曾三档案思想的高度认可。同时,地方省市的档案工作者也纷纷发文回忆曾三,以此追忆他对当地档案工作的要求和指导。从1992 年起,一批关于曾三档案工作经历、曾三档案思想内容及地位的专题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曾三档案思想研究的序幕正式拉开。
1.1 传记类成果
早年在曾三身边工作过的田真、赖世鹤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起就对曾三进行采访并获得了大量访谈材料,二人以此为依据着手撰写长篇传记性文章《曾三传》。曾三逝世后,《北京档案》分十六期对《曾三传》(上卷)进行了连载。其中,1992—1993 年的载文详细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曾三带领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中央档案大转移”的历史过往。通过这次档案转移,曾三对“如何进行档案分类”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其一,他提议除绝密文件外,其他档案可不按照以往的“中央”“地方”两类分法,而改为“总类、党务、政权、军事、民运、国民党区(包括海外)、党内刊物”等七种类型[1];其二,各类型档案应再按照其内容、地区分纲分目,并分别交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整理、研究和保管。考虑到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田、赖二人认为曾三这个提议非常有利于保持文件的历史联系。[2]从后来的档案工作实践来看,曾三关于档案分类的思考,既适应了战时背景下保管档案的实际需要,也为后来新中国确立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思路。
1.2 关于曾三档案思想主要论域的研究成果
档案学家陈兆祦认为曾三所提出的“由文书部门或有关人员立卷归档形成档案开始,经过档案室,最后集中到档案馆”这一内容包含了档案的形成和运动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与欧美档案界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似。[3]同时,从我国档案工作的一般流程来看,档案室工作是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有学者据此指出,健全归档制度是曾三创建机关档案室工作的成功之道,集中统一管理机关档案是曾三创建机关档案室工作的基本原则。[4]在这一研究阶段,王传宇着重对曾三关于科技档案管理的相关论述作了分析,认为其深刻揭示了科技档案工作同科技、生产活动的本质联系,对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有巨大的指导作用。[5]霍振礼也指出,曾三等档案前辈的努力使我们能够区分科技档案与科技资料的不同,从而为我国科技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6]
曹喜琛等依据曾三关于档案馆“要做研究工作,要参加历史研究”等论述,指出曾三的档案编研思想体现了我国优良的历史文献编纂传统,为全面理解和开展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7]在裴桐看来,曾三之所以如此重视档案编研工作,是由于档案常常是零散细碎的史料,并且可能存在内容失真的情况,因此需要进行整理和考证。[8]
1.3 关于《曾三档案工作文集》的研究成果
1990 年7 月,由国家档案局编撰的《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正式出版,曾经分管过国家档案局工作的习仲勋为此书封面题签并作序,认为其反映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许多情况,是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好书”[9]。《文集》收录了曾三在1951—1986 年期间所作的71 篇文章、讲话、报告等文献,既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历程和宝贵经验,也直接体现了曾三关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核心观点和主要方法,可谓是曾三档案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面对《文集》极为丰富的内容,吴宝康从“建立档案制度”“培养档案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科技档案问题”“注重档案利用”等角度对《文集》内容作了概括和解读。[10]同时,王德俊和陈普元分别对贯穿《文集》内容背后的理论主线进行了梳理,前者认为书中提出的“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作出总结”体现了曾三档案学思想的灵魂和核心[11],后者则指出《文集》所体现得最为基本和突出的思想是曾三科学全面的档案价值观[12]。也因为如此,有研究者提出《文集》作为我国档案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结晶,已经阐述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和中国档案学的基本思想。[13]通过上述观点多元、认识深刻的研究成果,可以预见对曾三档案思想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阶段即将到来。
2 研究的深入:2006—2022
一项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在于研究论题的多元化、成果类型的多样化等。以2006 年纪念曾三百年诞辰为契机和起点,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旨趣,对曾三档案思想的历史地位、重点论题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
2.1 曾三档案思想历史地位的确认
曾三诞辰百年之际,国家档案局原局长冯子直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曾三领导档案工作之初即已开始研究档案工作的规律,其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思想、观点应是一个完整、系统和科学的理论体系,且这一理论“是超越时空的,今天对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4]。2009年,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刘国能从九个方面总结了曾三开创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卓越贡献,认为曾三对“从芬特到全宗”“档案与资料的区分”等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学术思想。[15]吴宝康在《中国档案》发文指出,曾三的贡献涵盖了档案事业中的教育、科学、学会等所有领域。[16]其中,针对档案学理论基石之一的档案形成观,宗培岭认为对档案形成规律作出最具代表性论述的当属曾三[17],而徐拥军、闫静在回顾曾三档案思想的内容演变历程后,也指出曾三尊重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和工作规律,对“中国式档案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18]。丁海斌则通过梳理曾三、吴宝康等老一辈中国档案学者所注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认为曾三在领导建立档案工作体系的过程中所探索出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是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成果。[19]
2.2 重点论题研究的逐步深化
“什么是档案”是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曾三档案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厘清了档案的基本概念。王景高对曾三关于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三次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曾三对档案的定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即“档案是本机关在工作和生产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技术文件、影片、照片、录音带等经过一定的立卷归档制度而集中保管起来的材料”[20]。这一概念既明确体现了档案的社会性、原始性、客观性等重要特征,又完整地反映了曾三对档案形成以及档案工作规律的认识,不少研究者也因此将其称之为“档案自然形成论”[21-23]或“档案自然形成观”[24],并把它确认为曾三档案思想的基础性理论。
在曾三为档案事业所做的诸多贡献中,他对科技档案工作的开创是一个主要亮点。在这一研究阶段,吴宝康认为科技档案工作的开展以及科技档案管理学的创立既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重大特色,又是“曾三同志档案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5]。霍振礼在上一阶段研究曾三科技档案观的基础上,将曾三在1980 年全国科技档案工作大会中的一段讲话称之为“三纳入”思想,即“科技档案工作纳入科技管理制度,纳入生产科研计划,纳入科技人员职责范围”,并认为这是曾三关于科技档案工作的一条“健全的思想理论和法规”。[26]此外,刘前程[27]、张诗敏[28]等在其学位论文里也对曾三的相关论述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2.3 研究论域边界的不断扩展
档案因其原始性、可靠性等特点而具有独特的信息价值,曾三在领导和开展档案工作期间就档案的利用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学界也因此对曾三的档案利用思想给予了较多观照。马仁杰等研究者认为曾三等前辈的努力为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奠定了基石[29],徐拥军等在这一阶段系统梳理了曾三从重视收集保存档案到将档案利用作为中心任务再到有条件开放档案的思想演变历程,并指明了曾三对待档案利用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作风[30]。罗吉鹏在其学位论文中则全面分析了曾三档案利用思想的形成基础、具体内容、主要特点,并对其历史地位和基本精神进行了细致的总结。[31]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曾三主张档案馆应积极地开展档案编研工作以做好档案服务,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看法。邓君通过分析曾三关于档案馆应开展档案史料汇编并参加历史研究工作的相关论述,总结了曾三提出的“边整理,边研究”“先急后缓”等四条原则[32],这一成果可谓是在上一阶段曾三档案编研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曹建忠基于曾三关于档案馆要积极参加编史修志的思想,提出了成立档案、史志、党史三部门“档史合一”工作机构的建议,他结合贵州等地已开始施行的做法,认为这一模式是对曾三“档案与地方志结合起来”观点的大胆创新和成功实践。[33]
进入21 世纪以来,以云南大学华林、杨毅为代表的学者为推动民族档案事业和研究的发展,以曾三关于做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工作的相关论述为基础,阐述了加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保护开发[34]、加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档案挖掘力度[35]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
3 研究展望
尽管业界、学界三十年来对曾三档案思想这一主题始终抱有较大的学术关切,且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目前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向依然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3.1 考察曾三档案思想形成发展的哲学根基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应当有自己的哲学根基。冯子直认为曾三始终较好地运用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来解释档案工作与其他事务的关系。[36]马婷婷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里则是将曾三档案哲学观的主要内容总结为“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观”“走群众路线”等三个方面。[37]上述表明,研究者们已经对曾三档案思想中的哲学元素做出了十分可贵的理论探索,但既有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哲学方法论层面,如果不多从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哲学根基角度进行思考,就难免会有“碎片化”的观感,使人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曾三档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从曾三关于档案形成的相关论述来看,档案本质上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原始信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一种现实活动,因此,档案的形成应该是人们的一种实践活动,档案的内容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的一种认识。基于这一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考察曾三档案思想的哲学根基:一是在认识论维度上,这一思想是如何客观反映档案活动这一社会实践的;二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这一思想是如何有效指导档案实践活动的。除此之外,如何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问题导向和价值实现相统一”等角度思考曾三档案思想形成发展的哲学成因,有待业界、学界进一步发力。
3.2 拓展曾三档案思想的研究内容
如前文所述,目前关于曾三档案思想中的档案形成、档案利用、档案编研、科技档案等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纵观曾三领导和开展档案工作的完整历程,仍有较多的研究内容尚待拓展或深化。譬如,曾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档案工作的特点和重要性:“如果其他同志不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他解释。”[38]他的这些大力宣传档案的做法以及强调档案宣传重要性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社会对于档案的了解。因此,加强对曾三档案宣传工作论述的研究,对于今天继续破除“档案神秘”的误解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曾三关于农业档案、档案研究、档案教育、民族档案等论域的思想和观点同样需要学界深耕,他对地方省市档案工作指导的一些新史料也需进一步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