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之个体自觉
苑天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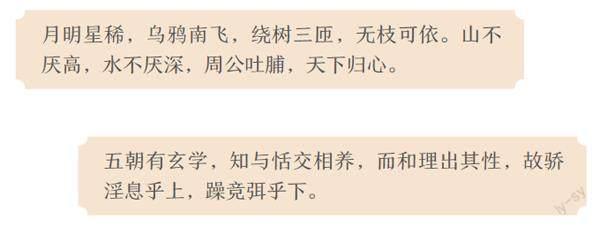
众所周知,魏晋名士的性情与意气可谓淋漓尽致。与魏晋名士相比,三国时期的军政人物则具有博大襟怀和深刻智慧的英雄意气。
三国时期的曹操,被称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虽然是以“权术相驭”,但也以精神情感丰富著名,《曹瞒传》里说他“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操曰:“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以大事小是至德,不管曹操是否甘愿以大事小,但他终生没有僭越却也是事实。曹操《短歌行》曰:“月明星稀,乌鸦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三国志》记载了张昭与孙权意气冲撞而相投的一件事。公孙渊称藩,孙权欲遣使去辽东,张昭以使者必然会被杀为由阻拦。君臣激烈争辩,孙权不能容忍,握刀怒道:“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敬君已极。而多次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张昭看了孙权好久,才说:“臣虽知言不用,每尽愚忠者,实因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遣诏顾命之言犹央耳。”说完涕泪横流。孙权也感动了,“掷刀于地,与昭对泣”。但最终孙权还是派使者去了辽东,张昭气愤称病不上朝。孙权恼火,派人用土堵了张昭家大门,张昭则在门内也用土封堵。后来公孙渊果然杀了使者,孙权醒悟,多次去向张昭道歉,张昭拒绝出门。孙权以放火烧张昭家大门恐吓,张昭更加紧闭门户。孙权让人灭火,站在门外很久很久,张昭的儿子们这才扶张昭出来,君臣和解。
与军政人物英雄意气相比,魏晋名士们的意气是高标独立的,形成了“善言虚胜”“谈尚玄远”,“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贵无”“崇有”,“超言绝象”地为天地万物、政治人伦寻找存在理由的魏晋玄风。章炳麟先生说:“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
錢穆先生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李泽厚先生对“人的觉醒”曾有解释:“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余英石先生指出,相比之于中国汉代的“士之群体自觉”,魏晋时期的人之自觉是“士之个体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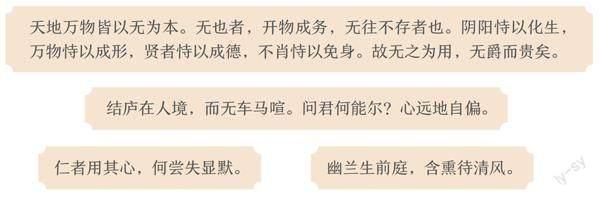
魏晋的“士之个体自觉”,体现为魏晋名士风度。
何晏与王弼是魏晋玄学正始时期的开创者,祖述老庄,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何晏与王弼皆贵无,认为“无”是世界万有之根本,但是,何晏与王弼在“圣人有情无情”上有分歧。《王弼传》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圣人因其“应物而无累于物”(应对事物但不为事物羁绊拖累),从而有“体冲和以通无”(冲和为道,体悟道的存在从而通向自然无为)的能力。
由此可知,王弼贵无,但是并不追求虚无的人生理想,理想境界并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之外去追求和寻找,而应实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虽然力图用道家思想改变或者补充儒家思想,但是他并不认为圣人应该超世尘外,圣人不应该离开现实人生,圣人的人格德行并不表现在无喜怒哀乐之上,而是表现在“智慧自备”“道同自然”上。这样,“圣人有情”就带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内容:性与情。
“情性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题目,我们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细说。但这个重大话题,引出了魏晋士人关于生命意识觉醒与生命安顿方式的探寻,从而具有了一种怀疑、否定、反思、解构性质的中国式、带有人情味与美感的哲学思潮,这是在魏晋士人生命意识觉醒时期应运而生的。
阮籍、嵇康与何晏、王弼生约同时,而晚死十余年,被称为“竹林名士”。他们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从魏晋玄学的历史进程来看,阮籍与嵇康表现了“玄学的浪漫”。阮籍主张:四海九州、普天之下,万事万物都顺应各自的本真自然之性,完满自足,达到一种平和、和谐的理想境界,所谓“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
嵇康的浪漫风度,见于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自我写照。公元263年,嵇康获罪于司马昭,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无果。临刑前,嵇康顾视日影,索琴弹奏《广陵散》,弹罢弃琴而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应物而无累于物,是大多魏晋士人的基本处世态度。这是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物我关系,真正能够走向超脱,而不是在思想和口头上追慕。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名士倡导玄学、高谈理念;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纵情任性、率真脱俗;以裴頠(音同伟)、王衍、郭象为代表的中朝名士妙于谈玄、容止灿然。此后的东晋,陶渊明可谓这一时期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这是陶渊明弃仕归田,大隐于酒的生命之安顿。
魏晋风度是“士之个体自觉”,体现出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精神境界与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