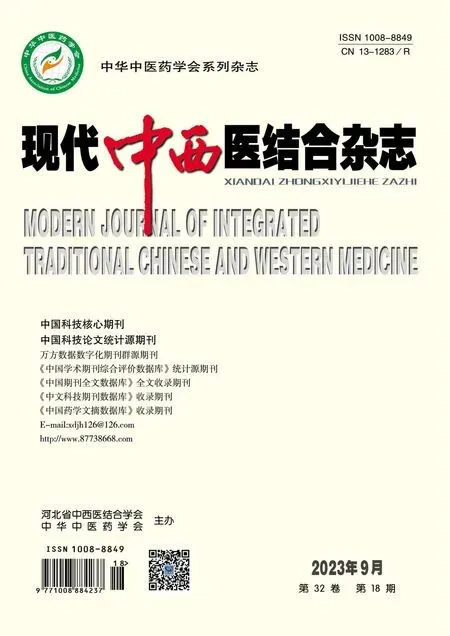糖尿病肾病蛋白尿中医研究进展
李明侠,李小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00)
糖尿病肾脏病(DKD)也称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慢性肾脏病和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要病因。DKD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蛋白尿,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最终导致终末期肾病。现代医学认为DKD的发病多与糖脂代谢紊乱、慢性炎症反应、免疫机制激活、细胞焦亡及自噬、氧化应激的加速、表观遗传等有关,具体发病机制仍不明确。目前临床治疗中多采取控制蛋白质摄入,调节血压及血糖,或采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系统抑制剂(ACEI或ARB类药物),但并不能有效延缓DKD进展至肾功能衰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损伤的敏感指标,也是肾功能持续恶化的危险因素,可预测临床期肾病及肾功能的进展[1]。因此早期、积极控制尿蛋白对于延缓肾功能恶化十分重要。中医药基于整体辨证观在控制蛋白尿,延缓肾功能减退,改善临床症状方面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且疗效显著。现将历代医家关于中医药治疗DKD蛋白尿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
1 DKD中医病名及病机的认识
DKD依据其症状及病因病机,可将其归于为“肾渴”“下消”“尿浊”等范畴。DKD发生在消渴病基础上,后逐渐出现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以及肾功能减退等,中医也称其为“消渴病肾病”。《外台要诀》有描述三消者,久见“小便浊淋如膏之状”“浮在溺面如猪脂”,这与DKD蛋白尿的表现非常相似。中医认为DKD蛋白尿的产生与机体先天禀赋薄弱、六淫邪气侵袭、情志过极、饮食不节、房劳过度等有关。消渴后期气阴两虚,真阴耗伤,肾元亏虚,气化失常,邪气壅滞肾络,肾体受损,封藏失司,精微下泄,出现蛋白尿[2]。张大宁[3]认为DKD的主要病机为肾虚血瘀,肾虚为本,血瘀为标。杨洪涛教授认为DKD蛋白尿的病机以脾肾亏虚为本,加之风、热、湿、瘀、毒等邪气阻滞肾络,经气外溢,下遗而成蛋白尿[4]。张喜奎教授指出DKD病机总以脾肾亏虚为关键,湿热、瘀血等贯穿病程始末,使蛋白尿顽固难消,痰瘀浊毒痹阻络脉,肾络受损,致肾功异常[5]。DKD蛋白尿的病机总以本虚标实立论。笔者认为,DKD蛋白尿的病机主要以脾肾亏虚为本,瘀血阻络为标,风邪是其缠绵难愈和疾病不断进展的关键因素。
2 病因病机
2.1血瘀论 《太平圣惠方·三消论》载:“消肾也,斯皆五脏精液枯竭,经络血涩,荣卫不行,热气留滞,遂成斯疾也。”说明了消渴肾病与瘀血的密切联系。消渴日久,气虚瘀阻;阴虚火旺,津液受灼,易生痰、生瘀;痰瘀阻滞肾络,肾络不通;久致络息成积,肾络瘀阻,肾体失用,则精微下泄,发为消渴病肾病[6],进一步损伤肾络。肾络窄小,病邪易居,外邪侵袭易停滞在内,损伤肾络,加重病情。DKD多虚多瘀,痰瘀互结,瘀阻肾络,加剧蛋白尿的产生,更是导致DKD病情进展的重要病机。吕仁和教授创新性地提出了DKD“微型癥瘕”病理学理论,认为肾小球基底膜及系膜基质经历了从增厚、增生,到肾小球形成结节硬化,实际就是由“瘕聚”渐至“癥积”的过程,即先聚为“瘕”,后积为“癥”[7]。肾络癥积,久而致肾用失司,精微下注,形成蛋白尿。DKD患者肾脏肾小球膜细胞增殖,肾小球簇瘢痕形成,导致肾小球呈现弥散性和结节性肾小球硬化,最终将导致肾小球毛细血管的闭塞,形成血栓[8]。这似乎与中医的“微型癥瘕”理论不谋而合。仝小林等[9]认为糖尿病肾病瘀是核心病机,而瘀阻络脉为主要病理改变。现代研究发现随着肾络瘀阻程度的逐渐加重,血液黏度、脂质代谢、内皮素的异常愈发明显,肾功能也呈现进行性下降趋势[10]。这也与消渴肾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瘀血内生、阻滞肾络的病机符合。因此在DKD治疗过程中,活血化瘀法应该贯穿始末。张大宁教授提出了肾虚血瘀论和补肾活血法,认为肾虚是导致慢性肾病肾小球硬化的始动因素,血瘀是其形成的病理基础[11]。认为应将补肾与活血化瘀相结合,并贯穿慢性肾病治疗的始终。多项研究显示DKD患者凝血功能亢进,而活血化瘀药可改善血液循环,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液高凝状态,修复组织损伤。可见,活血化瘀药可有效延缓DKD的进展。
2.2风邪论 《灵枢·九宫八风》言:“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说明风邪伤人可以直中肾脏,且与肾水关系密切。《诸病源候论》所云“风邪入于少阴则尿血”。DKD患者脾虚失运,咽部干燥,风邪循经妄入,直中肾络,风邪扰肾,肾失封藏,精微下泄,故见蛋白尿。以上都描述了风邪与肾系疾病的关系。DKD后期病程进展迅速,症状多样,病机复杂。其病情演变的迅速性及并发症的多样性,皆反映了风邪善变、易行的特征。有学者认为风邪与现代医学的免疫炎症相关[12],并认为免疫炎症反应与DK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基于吕仁和教授的“微型癥瘕”理论,结合临床上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常表现有头晕眼花、肢体麻木、皮肤瘙痒等类似“风”的症状,赵进喜教授提出“肾络伏风”的理论,认为消渴病日久,机体阴虚燥热,热蕴成毒,致热盛生风;肝肾阴虚,日久生风;久病络脉不通,易血虚生风[7]。这诸多因素致风邪内扰,伏藏肾络,形成“肾络伏风”[13]。风邪伏藏日久,致肾失封藏,精微下泄。张建平教授认为DKD后期病机复杂,风邪易兼加水湿痰浊瘀血等为患,壅滞肾络,肾络不通,血脉滞涩,精微不固,蛋白难消,则肾病缠绵难愈[14]。DKD后期可见大量蛋白尿、尿中泡沫及颜面手足水肿等。临床上DKD患者一旦外感风寒或风热后水肿、蛋白尿症状加重。风邪扰肾,肾气化失常,清浊不分,精微下泄,见蛋白尿。这都是风邪为患的表现。外风引动常是DKD发病的起始因素,内风伏藏则是DKD病程迁延反复的关键[15]。因此治疗DKD常需内外风兼顾。杨辰华[16]从“玄府”理论出发,认为DKD肾中玄府失养,虚气留滞,导致气液代谢障碍,精微外泄,出现尿浊、水肿等症。在DKD病机及玄府理论中,风药能开玄府、胜湿、升阳、活血。风药开发了玄府郁结,使气液运行畅通,津液敷布正常,肾脏循环改善。因此在DKD治疗中适当加上“风药”能起到减少尿蛋白、改善水肿、缩短病程等作用。
2.3脾肾亏虚为本论 《景岳全书》指出:“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体现了脾虚对于肾系疾病发生的重要性。故肾脏有疾,求之于脾,也是应有之理。人体之精微,化生于脾,封藏于肾。脾之生化依靠肾中内寄之元阳以鼓舞,肾之封藏又赖脾所化生阴精以涵。胰腺分泌胰液消化食物与脾运化水谷的功能极为相似,胰腺又是糖尿病发病的中心器官,故而中医认为胰归属于脾,故有“脾胰同源”学说,认为从“脾”论治DKD正对其本。因此脾虚为DKD病变的始动因素。脾土亏虚,下不能充养于肾,久致肾气虚损,络脉瘀滞,致肾用失司;或脾气亏虚日久,湿浊内生,变生浊毒,损害肾络,致肾用失司,精微下注现蛋白尿。张喜奎教授依据六经辨证理论认为消渴日久,燥热久存,正气耗伤,必先累及太阴,致太阴脾气亏虚,加之少阴肾阴亏虚,脾肾两虚,则精微下遗,而见蛋白尿[5]。脾肾两脏虚损的基础一旦形成,机体的水液代谢便愈加紊乱。在DKD的治疗过程中,应始终把握“脾肾亏虚为本”这一基本病机,以健脾益肾法为基本治疗原则。在DKD的不同发展阶段,脾肾亏虚和痰湿、瘀血、浊毒等病理产物轻重表现不一。应根据实邪的性质、轻重,及时予除之、泄之、解之。疾病后期,肾阴亏损及阳,可见少阴肾之阴阳双亏之证。赵玲教授认为脾气虚为DKD始动之因,肾虚为DKD发病之本,肾阴阳两衰为其最终归宿[17]。既往亦有“补肾不如补脾”之说,认为治脾可以治肾。因此在DKD治疗中则注重补脾固肾涩精,结合逐瘀通经、解毒降浊,以补虚泻实恢复脾脏生理功能。
3 辨证论治
3.1化瘀通络-贯穿始终 张宗礼认为活血药的应用宜早不宜晚,早期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肾病进展,减轻肾损伤[18]。赵进喜教授[19]则将DKD以气血阴阳为纲,按早、中、晚三期分型为气阴虚血瘀证、阳气虚血瘀证、阴阳俱虚血瘀证以分期辨证论治,分别以益气养阴化瘀、温补脾肾化瘀、补肾培元固本化瘀为治法应用于临床。常以选左归丸、肾气丸等加减而固本,桃红四物汤等活血化瘀方加减合用。用药上可予杜仲、肉苁蓉、山萸肉等补益,以香附、丹参、郁金、当归等行气活血。治疗时应结合不同分期的病机特点,辨证论治,灵活用药[20]。DKD日久病邪入络致瘀、络息成癥积,形成陈年宿邪,久而深入脉络细微处,交织痼结,必藉虫类药深达肾络以搜风剔络,破积消癥、攻毒化痰。李明权教授在治疗DKD 时常以僵蚕、地龙、蜈蚣、全蝎等搜风剔络,以水蛭、地龙、土鳖虫、蜈蚣等化瘀破积,以五灵脂、全蝎、僵蚕等化痰软坚[21]。虫类药物的功能各有侧重,临床应用需辨证应用[22]。仝小林等[9]治疗DKD络脉瘀滞,以失笑散加减以通络滞;以抵挡汤加减通络瘀;方以大黄虫丸加减,治疗后期络脉闭塞,血行瘀滞等。徐晶等[23]发现活血化瘀通络中药具有降低尿蛋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ACE2-Ang-(1-7)-Mas轴的活化,对高糖高脂饲料联合STZ注射造成的糖尿病大鼠的肾脏发挥显著的保护作用,且效果优于ARB类对照药物的干预作用。吴健等[24]发现百令胶囊、大黄蛰虫丸联合西药基础治疗用于改善DKD蛋白尿,其效果优于西药治疗基础上单用百令胶囊,特别是在改善早期DKD的β2微球蛋白、尿微量白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上效果显著。可见活血化瘀法对控制DKD蛋白尿疗效明显。
3.2巧用风药-疗效显著 DKD治疗宜通补结合,将风药与补肾药配伍,可使其补气而不滞气,畅气而不耗气。风类中药已被证明大都具有免疫调节,抗炎、抗过敏及变态反应、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稠度的作用。DKD治疗中应用虫类药、辛味药、风药可以达到“通玄畅络”的效果。赵进喜团队从风论治DKD,常以蝉蜕、僵蚕、穿山龙、鬼箭羽、川芎、牛蒡子等风药应用于治疗中[25]。朱良春认为虫类药不仅具有“虫蚁搜剔”之性,而且因其含有动物异体蛋白,对人体也有补益的特殊疗效[26]。现代研究表明虫类中药具有抗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抗氧化应激及变态反应等作用,还可以保护肾脏,延缓DKD的进展[27-28]。叶传蕙教授对于一般性蛋白尿,常先选用僵蚕、地龙等;对比较顽固的蛋白尿,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加用全蝎;对于病情缠绵难愈、日久难消、大量蛋白尿患者,提倡在前三者基础上,加用蜈蚣、水蛭[29]。临床中常以苏叶、乌梢蛇、蝉蜕三药治疗肾性蛋白尿,以调气机,通肾络,祛风邪。对于DKD日久的顽固性蛋白尿,可在辨证基础上配伍防风、羌活、荆芥等,一方面使清阳得升、浊阴得降,同时还可以鼓舞正气。藤类药如雷公藤、海风藤、络石藤等,因其藤蔓延交错,状如经络,故取类比象。雷公藤提取物雷公藤多苷[30],可以改善氧化应激、抑制炎症因子及相关通路,改善肾间质纤维化,降低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雷公藤还可以稳定足细胞的细胞骨架,保护和修复足细胞损伤,对于消减蛋白尿疗效突出。黄为钧等[31]在应用益气活血、祛风通络法及二者结合的方法治疗DKD大鼠的实验中发现,祛风通络法降低尿蛋白疗效突出,二者结合的方法可明显延缓肾间质纤维化,比单独应用两种方法更有优势。说明在活血化瘀、通络散结的基础上,若加用祛风通络的药物可以提高疗效。
3.3健脾益肾-基本治则 DKD病机核心为脾肾两虚,由本虚继发之瘀血、水湿、痰浊等病理产物导致该病迁延难治、不断进展。DKD早期以微量蛋白尿为主,常见气阴两虚证为主。刘喜明教授认为补气同时佐以养阴,气不独失,阴不独养,阴足则缓缓而化气,生化无穷[32]。杜小梅等[33]发现以参芪地黄汤加减可降低尿蛋白,保护肾功能,另一方面可以改善DKD 患者微炎症状态和肾脏病理损伤,恢复肠道菌群平衡,观察组效果优于单纯西医治疗的对照组。DKD中期出现持续性尿蛋白,常见水肿、困倦、纳少腹胀、尿有浊沫、腰酸膝软、肢冷尿少、脉沉缓等一系列脾肾气虚证,此阶段强调健脾助肾,固涩精微,运化水液,常以八味肾气丸或水陆二仙丹加减治疗,兼加补脾肾固及利水渗湿之品。若出现明显脾肾阳虚证,方用济生肾气丸合实脾饮加减治疗。DKD后期脾肾衰败、浊毒泛溢,出现持续大量尿蛋白,并见纳差、呕恶、畏寒肢冷,水肿、心悸等症,临床常选用真武汤、五苓散、金匮肾气丸等加减治疗,以温肾助阳,化气行水。因后期常兼夹虚、痰、瘀、浊毒之邪,若邪气不除,正气不复,则蛋白难消,疾病缠绵难愈。张宗礼在此期常佐以通腑祛浊之品,常以大黄、大黄炭、蒲黄炭、海藻炭等药物吸附浊毒,使邪有出路[34]。崔雅斌等[35]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治疗组应用温补脾肾结合化瘀利水法治疗脾肾阳虚夹湿瘀型DKD时患者24hUTP、Cr、BUN明显下降。DKD后期处于消渴向水肿发展的过程,与脾肾功能障碍更加密切。李小健等[36]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实验组以四君子汤作为基础方,加用补肾气、化湿浊等药物化裁而成益肾健脾汤用以治疗Ⅳ期DKD患者,与单纯西医治疗相比,中医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尿蛋白、肌酐、尿素氮等水平且整体疗效更佳。
4 特色对药
在名医荟萃的历史中,众医家总结出了灵活、有效的运用于DKD的药对。戴恩来教授治疗DKD常以黄芪配山药,黄芪偏补脾阳,山药偏补脾阴,二者伍用,阴阳相合,健脾固肾,则精微下泄能止,适用于脾肾气阴两虚证[37]。现代研究表明,黄芪、山药能降低血糖,减少尿蛋白排泄,降低血清尿素氮、肌酐水平,还可以改善肾脏病理损害。施今墨教授在治疗DKD 时以苍术伍玄参,使二者润燥相济,以“敛脾精,止漏浊”,适用于脾肾不足、湿浊阻滞者,具有显著的降血糖及降尿蛋白的功效[38-39]。名方水陆二仙丹,以芡实配伍金樱子,具有健脾利湿、益肾固精的功效,临床上能改善DKD患者的症状,降低尿微量蛋白,调节糖脂代谢等。张大宁教授常以升麻伍金樱子,寓“升清兼固涩之用”,加强了金樱子固涩收敛之力,减少精微下泄,降低蛋白尿[40]。其他历代的医家药对更是繁多,如水蛭配地龙,水蛭引地龙入血,地龙携水蛭达肾,共奏逐瘀通经之效;葛根伍丹参,活血化瘀,通利经脉。这两药对均能改善肾脏微循环,有助恢复肾功能。再如仙茅伍淫羊藿,温补命门之火,除湿消肿,改善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水肿等症状;熟地黄配山茱萸,功在补血养阴,强阴益精,大补元气,适用于DKD之肾阴阳两亏证者。
5 经验方
张建平教授自拟“搜风摄白汤”,该方以补气敛精,搜风通络,针对DKD早期患者,目的为减少精微物质的流失[14]。该方由黄芪、蝉蜕、白僵蚕、地龙、乌梢蛇、黄芩、柴胡、半夏、五味子、紫菀、乌梅、鸡内金、百部组成。方中黄芪的用量最大可达60 g,寓滋阴与补气的功效,加强对精微物质的升提固摄。该方标本兼治、上下同调,通补结合,以调畅全身气机。刘爱华认为DKD的病机为脾肾亏虚、浊毒下陷。遂自拟糖肾升清降浊汤,以益气固肾,升清降浊[41]。该方以六味地黄丸、四君子汤合升降散加减而成,加用当归、怀牛膝、黄芪、黄葵、黄连、鬼箭羽、积雪草等,以使浊毒得泄,脉络通畅,具有攻补兼施、升降并用的特点。刘晓云[42]在治疗DKD气阴两虚型患者时,运用黄芪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加减,以太子参易人参,加用白术、泽兰、丹参、芡实、金樱子组成。该方在益气养阴的基础上,兼有固精缩尿、利水消肿、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蛋白尿等。李济仁教授从脾肾论治DKD,自拟蛋白转阴方,该方由黄芪50 g,党参、石韦、白茅根各20 g,茯苓、炒白术、车前草、萆薢、续断、金樱子、墨旱莲、诃子肉、乌梅炭各15 g组成,具有补脾益肾、收敛固涩、分清泌浊之效,临床应用疗效显著[43]。
6 中成药
百令胶囊具有补肺气、益精气、扶正固本的作用。其主要成分是发酵冬虫夏草菌丝体干粉制剂,现代研究认为其可以调节免疫、降低炎症反应,减轻肾间质损害及延缓肾小球硬化,减少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和坏死,从而延缓DKD的进展[44-45]。尿毒清颗粒中有效成分为大黄素、黄芪甲苷等活性物质,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减轻系膜细胞的增生和细胞外间质的沉积,以延缓肾小球硬化,改善肾功能[46]。孙守萍[47]在尿毒清联合百令胶囊治疗早期DKD临床观察中发现,尿毒清联合百令胶囊实验组血糖相关指标、BUN、SCr、UAER和24 h尿蛋白定量比单用百令胶囊的对照组下降更显著。大黄蛰虫丸长于祛瘀生新,缓中补虚,主治正虚瘀血内结之症。研究表明大黄蛰虫丸可以抗炎、调节脂质代谢紊乱,还可减轻肾间质纤维化、保护足细胞,延缓DKD的进展。吴健等[24]研究发现,在应用西药基础上联合百令胶囊和大黄蛰虫丸治疗早期DKD患者,可明显减少超敏C反应蛋白,提高血清蛋白,改善尿微量白蛋白及24 h尿蛋白,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及西药联合百令胶囊组,但其具体机制仍不明确。黄葵胶囊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主要成分为黄蜀葵花,其提取物能有效抑制免疫反应,抑制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减轻肾脏炎症损伤,降低尿蛋白,改善肾功能[48]。蒋婷婷等[49]在临床观察研究中发现,在西医治疗基础上联合黄葵胶囊胶囊治疗DKDⅢ、Ⅳ期患者,能显著促进其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改善,同时有益于恢复DKD患者肾功能,并指出其机制可能与调控肾组织内MDA、SOD、8-OHdG表达水平有关。
7 结 语
DKD病程漫长,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随着中医药对DKD治疗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医药体现出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首先,中医药治疗能提高DKD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现代研究表明中药可抑制DKD患者肾脏病理损害,延缓肾功能不全的进展速度。其次,中医药不良反应少,成本低,应用前景广阔。然而中医药治疗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譬如中医强调辨证论治,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标准和疗效评价体系;缺少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数据,且研究结果不易推广应用;疗效显著的经验方的作用机制阐释得尚不深入;药理研究和分子机制缺乏深度。这些都需以后继续深入研究,需要加大对中医药人才和队伍的建设,加大科研人力物力的投入,使中医药和现代科技结合,探索挖掘出中医药更大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出中医药的优势,使中医药DKD诊疗迈向更高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