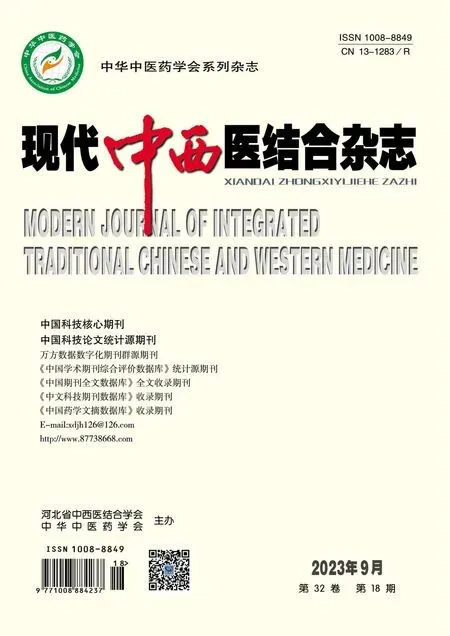赵泉霖治疗糖尿病心肌病的诊疗经验
于珊珊,赵泉霖
(1.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2015—2017年在全国31个省进行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社会人群糖尿病患病率高达11.2%,其中2型糖尿病占91%。作为基础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除临床共识的会引起肾脏、视网膜等器官病变外,对心血管的损伤破坏也不容忽视,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4倍,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临床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心肌病(diabetic cardiomyopathy,DCM) 是指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发生心肌病变,起初发病隐匿,特征为心肌能量代谢异常、心肌纤维化、心室重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的心肌舒张功能障碍,最终发展为症状明显、难治愈、射血分数下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1]。DCM的心力衰竭和心脏肥大是心肌结构异常和功能障碍所导致的,其发病机制复杂且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主要与心肌细胞糖脂代谢紊乱、钙稳态失调、高血糖及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等炎症反应、心肌细胞自噬与凋亡、心肌纤维化、心室重塑等有关。传统西药治疗DCM主要使用降糖药、胰岛素和促胰岛素分泌剂、β受体阻断剂等,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反应和药物依赖性。而一些新型潜在的西药治疗方法,例如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Vaspin)、褪黑素、辅酶Q10(Co Q10)、非编码RNA等,则需要进一步临床试验研究的证实[2-3]。并且传统西药治疗乃是针对症状进行诊疗,仅能缓解和改善临床症候,难以从根本上帮助患者康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而近几年大量临床研究发现,中医药在治疗DCM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又可改善此病发病的病因病机,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充分发挥了中医药标本同治的特色。赵泉霖教授是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中医院名医堂知名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现任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山东省科学养生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赵泉霖教授对于治疗DCM有着丰富而独特的临床经验。笔者现将赵泉霖教授运用标本兼治法及芪归药对(黄芪∶当归=2∶1)治疗DCM的临床诊疗思路整理如下。
1 病因病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
纵观中医古籍,关于糖尿病心肌病的病名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其病因病机及症状可归为“消渴病”并“心悸”“胸痹心痛病”“怔忡”的范畴。关于DCM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如《灵枢·本脏》云“心坚,则藏安固守;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阐述了心弱则心火易动,从而伤津耗液、阴虚内热,终致消瘅热中,易患消渴病。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亦记载“消渴重,心中痛”,阐明了消渴病久或消渴病重可引起胸痹心痛,即认为心中痛是消渴重症的临床症状。当代国医大师周仲英总结归纳消渴的病因主要为禀赋不足、五脏柔弱、精神过极、劳欲过度、过食肥甘、形体肥胖等原因致使肺、脾胃、肾脏受损[4]。消渴病的病机关键在于阴津亏损,燥热偏盛;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两者互为因果[5]。DCM是在消渴阴虚燥热病机之上,久而伏邪入络致气血运行失常、津液输布失调的病变。其主要病机为气阴亏虚,耗伤津液,内热炽盛,进而气阴两伤,气虚则血塞,阴涸而脉枯,致使心脉不畅,血脉瘀滞,损伤心体,终发为“心悸怔忡”“胸痹心痛”之病。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有云“心脉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赵泉霖教授从医30余年,总结归纳临床经验认为DCM基本病机为消渴本病导致的气血失和,本以气虚阴伤导致心脉失养、心脉瘀滞;兼以气滞、痰浊、瘀毒痹阻胸阳,阻滞心脉,涉及心、肺、脾、肝、肾诸脏,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
1.1气阴亏耗为本 赵泉霖教授总结多年临床诊疗经验认为:消渴病病程缠绵难愈,病机复杂多变,DCM作为病程进展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其病因病机主要分为阴虚内热-气阴两虚-阴阳俱虚三个阶段。DCM以阴虚燥热为始,由于消渴病久,阴虚伤津耗液,进而津液化生血液不足,难以濡养和滑利血脉,血液黏稠,运行涩滞,阴虚燥热炼血为瘀,而致心脉痹阻不通[6]。气津同源,相辅相成,津液亏损,使气虚加重,《难经·八难》云“气者,人之根本也”,气是维持人体基本生命活动的物质,血液的运行需气的推动。气充则血足,气虚则血不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素问·调经论篇》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消渴病久,心脾肾等五脏六腑功能的失调,脏腑精气亏损严重,阴津内耗严重,气虚难以推动全身气血津液运行,进而内生痰浊、瘀毒等病邪,又值正气亏虚之时,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所凑,其气必虚”,外感六淫及内生邪气毒邪炽盛,循络入里,使气耗过多、阴液亏虚加重,燥热结聚,致气阴两伤,致心肌不得气血津液濡养而加重病情进展[7]。DCM后期心之气阴耗伤严重,日久伤及阳气,心阳受损,阳虚气化无力,水饮上溢,凌射心肺,致心悸、憋喘、水肿、少尿之重症,更甚者可见阴阳两绝之危重症:四肢厥逆、大汗淋漓、脉微欲绝[8]。
赵泉霖教授认为DCM的主要影响脏腑为心肺,涉及脾肝肾。①心主血脉,肺主治节,心气推动和调控血液运行及心脏的搏动,肺气助心行血,推动血液的运行,两者相互协调,气血运行自畅,心血畅通。赵泉霖教授认为若心气或肺气不足,则生血之源匮乏、化生血液不足或无力推动血液的运行、血液运行不畅,则致心气不足而心血失荣、心脉失养或心亏气虚而血瘀,痹阻心脉,不荣或不通则痛发为DCM。②心肾上下交济,君相安位,心血充荣,脉道滑利,血液畅通。赵泉霖教授认为若心阴、肾阴亏虚,阴虚燥热, 热耗营阴, 津亏血少,则不能濡养血脉,脉道失于柔润,血液黏稠,运行不畅,血行涩滞为瘀,瘀滞心络,心脉痹阻,则发为DCM。③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水谷精微经脾转输至心肺,贯注于心脉而化赤为血[9]。而血液的正常运行既有赖于心气的推动,又依靠脾气的统摄。赵泉霖教授认为若脾气虚损,统摄无权,则血行失常致气虚血瘀而心脉瘀滞或脾失健运,化源不足,可导致血虚而心失所养。消渴患者过食肥甘厚味,或嗜烟酒而成癖,或忧思过虑、劳欲过度,易致脾胃受损,运化失常,聚湿化生痰浊,从而上犯心胸清旷之区,阻遏心阳,胸阳失展,进而气机不畅,痰阻血瘀,心脉闭阻,而成DCM。④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气条畅,促进血行,使心主血脉功能正常。赵泉霖教授认为郁怒伤肝,致肝失疏泄,肝郁气滞,甚则气郁化火,灼津成痰,而无论气滞或痰阻,均可使血行失畅,脉络不利,进而气血瘀滞,或痰瘀交阻,胸阳不运,心脉痹阻,不通则痛。如《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 曰:“总之七情之由作心痛。”七情失调可致气血耗逆,心脉失畅,痹阻不通而发为DCM。
1.2瘀滞浊毒为标 赵泉霖教授认为DCM本属于“久病入络”致气阴两虚,标以病久易夹瘀毒,亦常兼痰浊、气滞。瘀血既可为导致DCM的“死血”又可为DCM疾病进展中形成的病理产物[10]。近代医家总结归纳提出“外毒”和“内毒”的概念。“外毒”为外来六淫邪气。“内毒”为因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化失常,机体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排除体内积聚而成的内生之毒。痰浊则为脏腑功能失调所致气化不利,水液代谢障碍停聚而形成的,阻碍气血运行,瘀滞心脉,发为DCM。
赵泉霖教授总结归纳认为瘀血在DCM中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其一燥热煎熬阴血成瘀,其二阴虚火旺炼血成瘀,其三久病耗气,气虚运血无力,血行不畅为瘀,其四阴损及阳,脉管失于温煦,寒凝为瘀。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也明确提出了“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的观点。“瘀血”积久为“毒”,瘀毒内生,循络入里,脏腑亏耗,心气受损,心肌不得濡养,发为DCM。
痰浊为DCM发病的另一重要因素:消渴患者多素体肥胖,脾虚湿聚,留滞体内;或现代人忧思过极,七情伤脾,脾运失健,津液不布,聚为痰浊,或气郁化火,炼液水停化为痰热之浊;或恣食肥甘厚味,或嗜烟酒而成癖,致脾胃损伤,运化失常,聚湿生为痰浊;或劳神过度,耗伤脾气,脾气虚转输失能,不能运化津液,化生痰浊。如《景岳全 书·杂证谟·痰饮》指出:“盖痰涎之化,本由水谷,使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随化,皆成血气,焉得留而为痰。唯其不能尽化,而十留其一二,则一二为痰矣;十留三四,则三四为痰矣;甚至留其七八,则但见血气日削,而痰证日多矣。”机体痰浊积聚日久,生为浊毒,易阻滞心络,阻塞气机,使心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发为DCM。
2 治则治法——标本兼治,分清缓急
DCM的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故赵泉霖教授认为治则治法应主以扶正固本,益气养阴以补虚;兼以祛除病邪,邪去正复以泻实。必要时应扶正求本与祛邪治标同时进行,以发挥中医药治疗的最大优势,达到最优疗效。又因DCM基本病机为消渴本病导致的气阴亏耗、心脉瘀滞,兼有气滞、痰浊、瘀毒。则治法相对应为益气养阴活血为要,辅以行气化浊解毒,两者相辅相成,病邪去则正气复。
2.1本以益气养阴活血 《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 气血对于人体基本的生命活动有重要意义,气与血生理上相互依存,病理上相互影响。消渴病久,耗伤脾肾,气阴亏虚为主[11]。因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之源匮乏,心脉气血不足失养;又因脾肾阴虚,内生燥热,耗液伤津,血脉运行涩滞,痹阻心脉致DCM。因此赵泉霖教授在治疗DCM时不仅注重药物之间君臣佐使的配伍,同时也更加注重药物配伍的剂量比重。故选用出自《内外伤辨惑论》中的经典配伍药对芪归药对,即黄芪∶当归=2∶1,此药对为补气生血效方,此比重可更好地发挥补气生血的作用[12]。黄芪甘温入脾经,为补中益气之要药。《本草经解》记载:“人身之虚,万有不齐,不外乎气血两端。黄芪气味甘温,温之以气,补益气血。”当归甘温质润入脾经,为活血行瘀之良药。《医学启源》记载:“当归,气温味甘,能和血补血,尾破血,身和血。”黄芪补气又生血,使阳生阴长,配以当归养血和营,使阴血渐充,《得宜本草》云黄芪“得当归能活血”,两者相辅相成使气血阴阳调和,《本草新编》中记载“使气生十之七而血生十之三,则阴阳有制,反得大益”,心血得以滋养温润,心脉得以通畅条达。同时现代药理学表明:黄芪多糖可以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抑制凋亡靶基因蛋白的表达,增强SOD2、MAPK蛋白的表达,当归多糖可以通过上调VE-GFA和抑制大鼠心肌细胞凋亡来减弱糖尿病大鼠的缺血/再灌注(I/R)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 从而改善氧化应激,延缓心肌纤维化的过程,改善心脏的功能,达到治疗DCM的作用[13-14]。
2.2标以行气化浊解毒 赵泉霖教授认为DCM病程日久,病机复杂,兼证繁多,故用药时应灵活多变,根据兼证要点辩证用药。气滞甚者应加用辛香走窜之药,能行能散以行气通络,如桂枝、细辛、柴胡、枳壳等疏肝理气,使气行则血行[15]。痰浊甚者应加用茯苓、泽泻、半夏、陈皮、竹茹、山慈菇、延胡索等健脾祛湿、解毒化痰、软坚散结,以理气使气顺痰消、燥湿助化痰之力[16]。而瘀毒贯穿始终,从瘀论治是目前防治DCM的主要研究方向。正如刘斐述在《临证指南医案·三消》认为消渴病久迁延,则气阴耗伤易合并痰瘀互结等,主张益气养阴、活血化瘀合用以辨证治疗消渴胸痹。故血瘀甚者应以血府逐瘀汤加减,加用化瘀通络之药,如川芎、红花、桃仁葛根、丹参等搜经通络、活血祛瘀。
3 验案举隅
患者,男,54岁,2021年12月20日首诊入院治疗。主诉:血糖控制不佳伴心慌胸闷7 d。患者糖尿病病史2年余,2年前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查体发现血糖升高,空腹血糖(FPG)为7.2 mmol/L,未予系统治疗。半年前因FPG升高至9 mmol/L,餐后2 h血糖(2hPG)升高至20 mmol/L,自行口服二甲双胍治疗,疗效一般。期间不规律服药控制血糖,2hPG控制在15 mmol/L左右。近1周因血糖控制不佳伴心慌胸闷,就诊于内分泌科门诊收入院治疗。高血压病史25年余,血压最高140/110 mmHg(1 mmHg=0.133 kPa),口服拜新同30 mg每日1次治疗,平素血压控制在120/80 mmHg。高血脂症病史9年余,口服瑞舒伐他汀钙片20 mg每晚1次。入院症见:口干口渴,心慌胸闷,头晕,周身疲乏,双下肢麻木疼痛,纳可眠差,小便淋漓不尽,大便调,舌红苔少,脉细数。入院糖化血红蛋白10.6%;住院生化:FPG 10.67 mmol/L,总胆固醇2.09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64 mmol/L;心脏彩超示:二尖瓣反流(轻度),三尖瓣反流(轻度),LVEF 61%,FS 33%。中医辨病:①消渴;②胸痹,辨证:气阴两虚,心脉瘀阻。西医诊断:①2型糖尿病;②糖尿病心肌病;③高血压病1级(中危);④高血脂症。治法: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治疗方案:盐酸二甲双胍0.5 g每日2次口服,达格列净10 mg每日1次口服,中药以芪归药对合血府逐瘀汤加减。整方如下:黄芪30g、当归15g、生地黄15g、葛根30g、丹参30 g、炒苍术15 g、玄参15 g、桑枝30 g、石斛15 g、川芎15g、红花15g、莪术12g、百合30g、炒酸枣仁30 g,水煎服每日1剂(300 mL),早晚饭后温服。嘱患者低糖低脂饮食,定时定量进餐。适量运动定期监测血糖谱。2021年12月23日血糖谱:早餐前6.6 mmol/L,早餐后2 h11.6 mmol/L,午餐前6.4 mmol/L,午餐后2 h 10.1 mmol/L,晚餐前7.2 mmol/L,晚餐后2 h 8.1 mmol/L,睡前7.3 mmol/L。2021年12月27血糖谱:早餐前5.2 mmol/L,早餐后2 h 7.2 mmol/L,午餐前5.4 mmol/L,午餐后2 h 7.2 mmol/L,晚餐后2 h 7.7 mmol/L。血糖控制平稳,心慌胸闷有所改善,周身疲乏改善,双下肢麻木疼痛减轻,纳眠可,二便调,于2021年12月28日出院。出院前带14剂中药继服,嘱继用盐酸二甲双胍、安达唐、拜新同、瑞舒伐他汀钙片。嘱注意饮食,适量运动,监测血糖。出院后2周于内分泌科门诊复诊。2022年1月10日门诊复诊:自述血糖控制可,心慌胸闷头晕好转,口干口渴乏力好转,双下肢麻木疼痛好转,纳眠可,二便调。测得FPG 5.2 mmol/L,降糖方案继用,中药去炒酸枣仁、百合,加枸杞15 g、菊花15 g。2022年1月28日门诊复诊:自述血糖平稳,FPG控制在5~6 mmol/L,餐后血糖7~8 mmol/L。偶有心慌胸闷,无口干口渴乏力,无双下肢麻木疼痛,纳眠可,二便调。继用降糖方案,停用中药。
[按] 患者为中年男性,体型肥胖,脾主运化,为胃行其津液,胃主腐熟食谷,患者长期过食肥甘、醇酒厚味等辛燥之品,胃火炽盛,燥热损伤脾胃,积热内蕴,耗液伤津,津液输布失调不能上乘于口,则出现口干口渴;脾主运化失职,水谷之气亏虚则周身疲乏。心主血脉,《渎医随笔·承制生化论》云“气虚不足以推血,则血必有瘀”,气行则血行,血液的运行不息、血液的濡养须依赖于气的推动和津液的濡养,流布周转至心脏及全身[8]。气虚气滞则血液运行不畅,心脉瘀滞,津液耗伤则血行瘀涩,心失所养,故出现心慌胸闷、头晕。血脉瘀滞不能濡养四肢故双下肢麻木疼痛;阴虚火旺不能纳阳,阴阳不和则眠差;舌红少苔,脉细数为气阴亏虚血瘀不畅的表现。治以芪归和血府逐瘀汤加减益气养阴,活血化瘀。黄芪∶当归=2∶1出自于李杲的《内外伤辨惑论》,为补气生血之要方,是“甘温除热”的代表方,甘温以补气,阳生阴长以生血,药简效宏。血府逐瘀汤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为治疗胸中血瘀证之代表方,本方活血与行气相伍,祛瘀与养血同施,升降兼顾,气血并调,后世皆以此方加减治疗瘀血诸证。本医案中:黄芪为君药补益脾气,生津养血,行滞通痹;当归为臣药补血活血,祛瘀不伤正;二者相辅相成,补益又活血,阴阳调和,使心血滋养心脉畅通。葛根、丹参、莪术活血通络;川芎、红花温通血脉,既活血祛瘀又行气通滞;合以生地黄滋阴养血,使祛瘀不伤正。玄参、石斛滋阴生津润燥;炒苍术、桑枝健脾燥湿,通经活络;四味药为降糖常用药。百合、炒酸枣仁安神助眠。全方共奏益气养血、活血化瘀之效。理法方药,药证合一,患者服药效可,症状好转。
4 小 结
赵泉霖教授基于自身多年丰富临床经验,结合DCM疾病特点,归纳总结出其“气阴亏耗为本,瘀滞浊毒为标”的病机特征,并提出“本以益气养阴活血,标以行气化浊解毒”的标本兼治之法,同时灵活运用“芪归”药对配伍论治,临床验之甚效,为DCM的临床诊疗提供了依据,更深刻体现了中医药理论“治病求本,标本兼顾”的特色优势。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