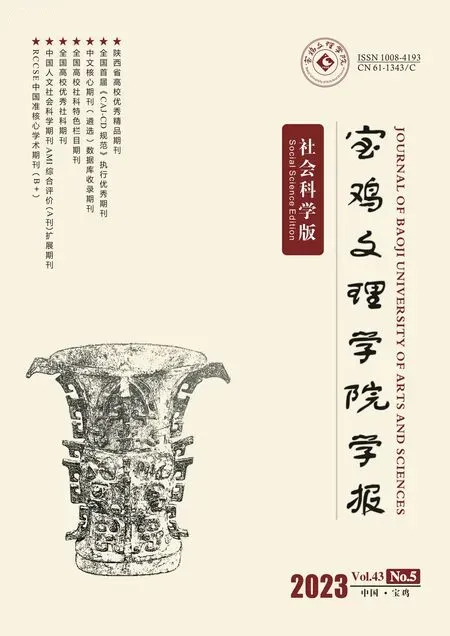《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董 飞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2)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密切相关,关于秦国墨学,蒙文通、李学勤、臧知非等学者均有所论及。①史党社先生亦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比较工作。[1](P187-206)沿着前辈学人的思路,将新见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进行比较、对照,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无论是对《墨子》“城守各篇”的校勘、整理,还是对里耶秦简中一些简牍性质的确定、语汇的考释等,均有所裨益。此外,由于汉承秦制的缘故,一些问题同样可以在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及《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找到解决线索。将相关考证写成札记五则,还请方家指正。
一、《墨子·迎敌祀》篇所见“弟之”考
《墨子·迎敌祀》载:“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举屠、沽者置厨给事,弟之。”[2](P85)
关于“弟”,毕沅云:“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孙诒让认为:“弟疑作豒之省,豒与秩同,言廪食之,毕说未允。”[3](P575)岑仲勉云:“毕解‘次第’,较得其意,即言分别其能力而为之品第,使互相统属也。贤大夫、方技士及百工为一类,屠宰及沽酒人为一类。”[2](P85)
按:毕沅言“古次第字只作弟”,其说可从。里耶秦简中“弟之”通常写作“第之”,这些简牍可丰富我们对于“弟之”的理解。可知“弟”确有“次第”之意,但既非“次第居之”,亦非“互相统属”,而是依据能力大小确定等次,按次第登记造册。
为方便讨论,现将里耶秦简中与“第之”相关的简文誊录如下:
廿九年四月甲子朔戊子,田虎敢言之:御史书曰:各第官徒隶为甲乙次。·问之,毋当令者,敢言之。
四月戊子水下十,佐安以来。ノ气半。安手。9-699+9-802[4](P179)
廿九年四月甲子朔辛巳,库守悍敢言之:御史令曰:各苐(第)官徒【粼】者为甲,次为乙,次为丙,各以其事易次之。·令曰各以□
上·今牒书当令者三牒,署苐上。敢言之。(正)
四月壬午水下二刻,佐圂以來。ノ槐手。(背)(8-1514)[5](P342)
里耶秦简9-699+9-802缀合简与8-1514简分别来自于“田”与“库”两个官署,内容均与“第官徒隶”相关,是它们接到御史下达的文书后,根据自身情况上报的反馈。推测“田”和“库”上报的情况将与其它拥有官徒隶的官署上报的情况一起,经迁陵县汇总后上报洞庭郡,层层上报至御史。两简均书写于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四月,书写日期分别是四月二十五日与十八日。可见“田”与“库”接到的应是同一件“御史令”,之所以日期不同,主要是由于两个官署距离县廷的远近不同,因此“御史令”传达到官署的时间便产生了偏差。因此,这两枚简上“御史令”中关于“第官徒隶”的规定,可相互参看。前引缀合简言:“各第官徒隶为甲乙次。”8-1514简:“各苐(第)官徒【粼】者为甲,次为乙,次为丙,各以其事易次之。”其中“”,与“易”相对,为“难”之意。[5](P342)按照从事工作难易程度“次之”,即按照能力大小排列,能力最强的为甲,居第一;其次为乙,第二;再次为丙,第三。[4](P179)
简8-1514简“今牒书当令者三牒,署苐上”,可见“库”的官徒被分为甲等、乙等、丙等各写在一枚简牍上。这三枚简牍是作为文书的附件,随着一封与8-1514简一模一样的文书一同上报洞庭郡的,8-1514简作为文书副本,出于备案之用留在了迁陵县。而“田”则上报“毋当令者”,这很可能是因为“田”的官徒单纯从事耕种,其劳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技术含量,无法区分高下;而“库”有一部分官徒从事手工业,可以分出水平高下。如8-1069+8-1434+8-1520缀合简是“库”的作徒簿,其中提到始皇三十二年五月,“库”的十五名官徒隶中有“十二人为舆”,即制作车辆;一人织,即纺织[5](P272-273);9-172简是“库”的“库工用计”即生产原料清单。[4](P81-82)可资为证。
秦汉时期,有关部门常常依据各人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势力背景等要素,将名单制作为簿籍,按次序排列,编订成册,作为人事任免的重要依据。如《汉书·五行志》:“德不试,空言禄,兹谓主窳臣夭”,孟康曰:“谓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为夭也。”[6](P1460)可知依据德行高下等因素,将人员名单编订成册,按次第任用。再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壹违之,便忿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7](P2336)如李傕、郭汜、樊稠三人所保举之人便依李、郭、樊三人势力大小排列、编订成册。汉献帝依次任用。基于此,我们便可以推测里耶秦简御史要求“各第官徒隶为甲乙次”的性质了,当然,这不会是选拔徒隶们去做官。而是在中央需要劳动人手时,将此簿籍作为征发劳动力的依据,如始皇时的骊山工程,势必会征调“甲等”的官徒前往。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对“第”的性质做一个总结。“第”与品第评定有关,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品第的评定;第二,将不同品第的人分别书写在不同的簿籍上,将这些簿籍按照次第排列,予以编联,作为人事任免或者劳动力征发的依据。因此,《墨子·迎敌祀》中“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举屠、沽者置厨给事,弟之”应该是将“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屠、沽者”按照能力强弱评定等级,名单次第排列予以编联,并将名单上交官府备案,在敌人逼近城池、需要劳动力时,按照名单予以征发。
二、《墨子·旗帜》所见“菌旗”考
《墨子·旗帜》:“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棋,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竟士为虎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姊妹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物足而下旗。”[2](P90)
此处提及“食为菌旗”,大意是说如果城墙上的守军缺乏饮食,则要举起“菌旗”, 城下人员看到后便要向城墙上补给饮食。但究竟什么是“菌旗”,学界尚存在争议。孙诒让《墨子间诂》:“自仓英旗以上七旗,并以色别,‘菌’非色名,疑当作‘茜’,说文草部云‘茜,茅搜也’,茅搜可以染绛。字或作‘蒨’,左定四年传‘綪茷’,杂记郑注引作‘蒨旆’。[3](P579-580)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菌是食品,故食为菌旗,孙疑作‘茜’,按茜,赤黄色,异与‘赤’混,且常言未见有取‘茜’与五色并列者,孙说不确。”[2](P90)孙诒让以“菌”为颜色,岑仲勉以“菌”为食品,此两说对我们都有启发,但仍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
按:岑仲勉对于孙诒让关于此处“茜”误为“菌”一说的商榷之处已较为完备,兹不赘述。岑以“菌”为食物,其说是。如《汉书·艺文志》录《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颜师古注曰:“服饵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闵反。”[6](P1779)据《汉书·武帝纪》“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应劭曰:“芝,芝草也,其叶相连。”[6](P193)可见周秦两汉之时,“菌”确为一种与“芝”并提的可食之物。由于传统医学“药食同源”的缘故,“芝”“菌”又被用作药物,如徐福在为始皇帝配置长生不老之药时,便加入了“芝”:“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8](P257)可见无论是“菌”还是“芝”,在当时都被视为不老之药。
无论“芝草”还是“菌桂”,其生长地点多为潮湿、阴暗的木质物上,秦汉时人一般将“芝菌”称之为“寄生”,直至唐朝,关中人仍以“寄生”称呼此物。《汉书·东方朔传》中则提到“芝菌”的另一个名称:“窭薮。”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6](P2844)
颜师古对“寄生”为何称之为“窭薮”做了注解:“窭数,戴器也,以盆盛物载于头者,则以窭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类,淋潦之日,着树而生,形有周圜象窭数者,今关中俗亦呼为寄生。非为茑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叶者也。故朔云‘着树为寄生,盆下为窭数。’明其常在盆下。今读书者不晓其意,谓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辄改前‘覆守宫盂下’为盆字,失之远矣。”所谓“窭数”,指的是一种盛放物品的器皿,盛物品后,顶在头上行走搬运。由于“芝菌”等“寄生”的形状与“窭数”相似,故名之。此外,颜师古亦提及“窭数”在唐代时亦为“卖白团饼人”所用,可见这种器皿可以用来盛放食物。[6](P2845)
由此可见,“菌”确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常与“芝”并提,称之为“寄生”;由于其形状与圆形器皿“窭薮”相似,故汉代文献中有以“寄生”指代“窭数”的文例。因此,《墨子·旗帜》所言“食为菌旗”中的“菌”,指的是形似“菌”的盛饭器皿“窭数”。在城墙上守城吏民士卒需要饮食时,举起画有食器的旗帜示意,也是符合逻辑的解释。
此外,《墨子·迎敌祀》有“涂菌”者,今附于此小议。
《墨子·迎敌祀》载:“城之外,矢之所逮,坏其墙,无以为客菌。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狗、彘、豚、鸡食其肉,敛其骸以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内薪蒸庐室,矢之所沓皆为之涂菌。[3](P576-577)
关于“无以为客菌”之“菌”,孙诒让《墨子间诂》:“菌,犹言翳也,周书王会篇有菌鹤,孔注云‘菌鹤可用为旌翳’,是菌有翳蔽之义。苏云:‘菌疑与棞义通,意言城外有墙,是令敌人得障蔽以避矢,宜急坏之。’”认为此处“菌”有遮蔽之意。其说是。[3](P576)
关于“涂菌”,孙诒让《墨子间诂》苏云:“涂菌所以避矢涂、塗同。”[3](P577)岑仲勉曰:“涂同塗,涂菌即子篇二四所云积薪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2](P87)二位前辈均认为此处“涂”通“塗”,且“涂菌”之目的在于“避矢”,其说可从。只是岑仲勉指出“涂菌”之主要目的在于防备火箭引发大火,其说似更为完备。可知“涂菌”之“菌”与前文“城之外,矢之所沓,坏其墙,无以为客菌”一句中的“菌”含义相同,当取“翳蔽”之意。
三、《墨子·号令》注释商榷一则
《墨子·号令》载:“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辄人随,省其可行、不行。”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注解:“此泛言号令既出,须遣人察视其可行或不行,使能有所督促及改正也,由此见古人之慎重将事。”[2](P108-109)
按:岑说误。令之“可行、不行”与令的可行性无关,而在于其是否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若令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则会对“受令”者予以处罚,借此督促他人;并不会改正令文,更不会给予受令者以改正的机会。
《二年律令·兴律》中记载了当事人接到“戍”的命令之后,“已受令而逋不行”当受的惩罚:
当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盗去署及亡盈一日到七日,赎耐;过七日,赎为隶臣;过三月【日】,完为城旦。[9](P243)
在这条简文中,命令是“戍”。官府下达“戍”的命令,也就是《墨子·号令篇》所言的“令出”,官府“令出”的同时伴随着黔首吏卒的“受令”。受令者会以书面形式签署较为正式的“受令”文书,此类“受令简”,里耶秦简中多见。如里耶秦简9-1130号简:“东成不更朱发受令。”[4](P266)再如里耶秦简9-2263号简:“安成罢臧受令。”[4](P441)简言之,此类“受令简”应是黔首吏民接受命令的备案记录,上级据此便可按图索骥对相应“受令者”执行命令的情况予以考核。
可见《墨子·号令》篇“令出辄人随”,乃是遣人察看受令者是否坚决执行了命令,与令的可行性无关;若是命令执行不坚决,即“不行”,则要予以相应的处罚,借此督促、警示其他受令者。并非岑仲勉先生所认为的督促受令者本人,更不会由于令不可行便对律令有所改正。
四、《墨子·备城门》补说一则
《墨子·备城门》篇载:“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秠、马矢皆谨收藏之。”岑仲勉注曰:“康今作糠,粃者秕子,秠者谷皮,与马矢数物,皆乘风于城上扬散之,以眯敌目,故谨其收藏。”[2](P19)吴毓江《墨子校注》并未突破岑说。②
按:岑说不误。但是,在实际城池守备中,“马矢”亦用作涂墙、涂薪,在房屋修缮保温、防火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不局限于“眯敌目”之用。
居延汉简《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中记载了“侯史广德”的十六条错误,其中便包括“亭不涂”“马牛矢少十石”“亭不马牛矢涂”。甘肃居延汉简整理小组指出:亭,泛指烽燧。按发掘的遗址,坞壁、烽台,经常在维修,都有涂壁现象。先敷一层薄泥,然后面上涂以白粉,残余的涂壁层有十数层之多。可见涂亭是有制度的,如不及时涂治,也为一大事故。[10](P70-71)《墨子·杂守》篇载:“涂茅屋若积薪者,厚五寸以上。”岑仲勉注曰:“此言涂泥之厚度;积薪须涂土,见子篇二四等节。”[2](P153)结合《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可知,“涂”的原料,很可能是混杂了牛、马粪便的泥浆。之所以这样做,推测是牛、马粪便中有未消化干净的植物纤维,将其混入泥浆中,有增加泥土黏合力的作用。此外,“康、秕、秠”等亦可以代替马矢混入泥浆,作涂墙之用。
此外,前引《墨子·杂守》中的“涂茅屋若积薪”,应是出于防火的目的。《墨子·备城门》:“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也。”[2](P13)《墨子·迎敌祀》:“城之内,薪、蒸、庐、室,矢之所逮,皆为之涂菌。”[2](P87)可见在城池防卫作战中,城内的薪柴、草庐、房舍等易燃之处,皆要“蒙涂”“涂菌”,以防备敌方火箭。
简言之,古代军事城池防卫时收集“马矢”之举,其目的不仅仅限于“乘风于城上扬散之,以眯敌目”。亦与泥浆参杂,作涂抹至墙壁、薪柴之上,作房屋修缮、保暖、防火之用。《墨子》“城守各篇”是周秦之际重要的军事著作,其内容多与城池守备有关。但对其进行理解时,亦不可“墨守成规”囿于兵法成说,亦要结合其它史料,充分考虑到明文规定之外的各种情况。
五、《墨子·备城门》与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
此简应是对迁陵县木材保有情况的统计,里耶秦简中与物品统计情况相关的简牍还有很多,譬如9-1571简:“□弩廿。”[4](P330)9-770简:“弩臂完可用者百卌九。”[4](P202)以上两枚简的内容均在物品名称与数量书写完毕后戛然而止。加之9-1588简在“七”字至残断处至少留有三至四字的空白,故我们认为9-1588简的残断部分,似不应再有其他内容。这枚简牍统计了当地“五丈长、径三围”这一尺寸的木材数量:七个。
按:《墨子·备城门》中有将官署、民宅建筑中的木材登记造册,以备战时征用的记载:
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为薪樵挈,壮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称其任。[2](P37)
寇近,亟收诸离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即急先发。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谒,勿听。入柴,勿积鱼鳞簪,当队,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积木,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城四面外各积其内;诸木大者皆以为关鼻,乃积聚之。[2](P147)
木材是守城战中重要的战备物资,备战时,要“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悉举民室材木、瓦若石数,署长短、小大”。所谓“举”:查报也;所谓“署”登记也。[2](P110)可见《墨子·备城门》篇所言“必数城中之木”便是将城中官署、民宅木材的长短、大小情况登记造册。而9-1588简中“长五丈、大三围”恰恰是木材“长短、小大”的内容。
关于征用这些木材的用途,除了“无令寇得用之”,避免资敌外,也有将这些木材积聚城上,用作滚木雷石的考量。《墨子·备城门》在记录“城上之备”[2](P19)时提到:“木大二围,长丈二尺以上,善耿其本,名曰长从,五十步三十。”[2](P21)此处言守城时,城墙上每隔五十步,便要堆放三十根“大二围,长丈二尺”的木材,疑为“滚木”之用。“悉举民室材木、瓦若石数”,亦可印证这一推测。
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注意到《墨子》“城守各篇”中确实有一些语句在里耶秦简以及基于秦律制定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找到对应的简文。一方面,通过讨论解决了一些以往不甚清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墨子》“城守各篇”确与秦墨有关,将出土秦简牍与《墨子》“城守各篇”参照阅读,可以更好地促进两者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重视法家对于秦国、秦文化的影响,而通过对秦简牍与《墨子》“城守各篇”的参照阅读,我们也注意到墨家守城术对秦帝国军事、行政等方面的深刻影响。诚然,《墨子》“城守各篇”中的墨学是经历了法家思想规范、改变后的墨学,但这种影响一定不会是单方面而是互相的。因此,墨家与法家的关系、以及墨家对于秦国的影响等,是值得继续挖掘的问题。
注 释
① 参见蒙文通《儒学五论·论墨学源流与儒墨合流》,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587页。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335页。 臧知非《〈墨子〉墨家与秦国政治》,载于《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
② 吴毓江《墨子校注》认为对上述物品“谨收藏之”的目的在于“眯敌目”。参见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