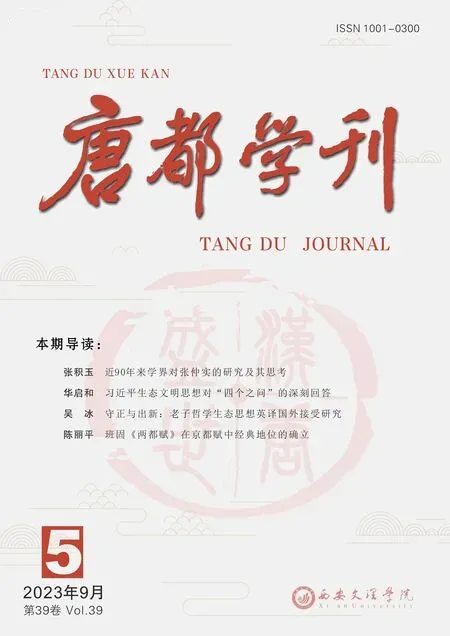论阮籍赋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兼与前代赋对比
刘 宁,高 榕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阮籍赋现存六篇:《鸠赋》《猕猴赋》《东平赋》《亢父赋》《清思赋》《首阳山赋》,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籍集》中。近年来随着专家学者对阮籍赋进行细致的整理、校注,学界对其研究也日益全面、深入。马积高先生《赋史》称阮籍是“讽刺赋最有成就的作者”;程章灿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对阮籍赋的特点做了详细的总结;韩传达先生的《阮籍评传》对阮籍赋的风格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赋风格一般都比较清新,不以冗长的事物刻画取胜,而以隽永的感情抒发争长”。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对阮籍现存赋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阮籍赋的分类
依照阮籍现存六篇赋的内容及主旨,参考中国历代文学选集中对赋题材的划分,笔者将阮籍赋分为三类:鸟兽赋、都邑赋、述志赋。
(一)鸟兽赋
鸟兽是中国古代文学很常见的描写对象,在汉魏六朝赋中,鸟兽赋是体物赋中的一种。阮籍的《鸠赋》《猕猴赋》可以算是鸟兽赋的代表作。
1.《鸠赋》
“鸠”是鸟类的一种,它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历代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1];《庄子·逍遥游》:“蜩与学鸠笑”[2]。“鸠”在赋中首次出现便是阮籍的《鸠赋》。《鸠赋》序中写道:“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之旨。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之赋。”[3]9郭光在《阮籍集校注》中注释道:“嘉平,魏少帝芳的年号。嘉平中,指嘉平年(251),是年五月,司马懿杀太尉王凌,六月杀楚王彪。《鸠赋》当作于此时,以狗杀两鸠影射司马懿对王凌、楚王彪的杀害。”[4]34在此期间,司马氏集团正逐步强大,司马懿为铲除异己而大杀名士,导致社会出现“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的局面。受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故等因素的影响,作者在行文时笔法含蓄曲隐,大量采用象征手法,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他以鸟兽抒怀、托物刺世的主旨。“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发蒙。有期缘之奇鸟,以鸣鸠之攸同。……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于微躬。欲残没以麋灭,遂捐弃而沦失。”[3]9-10赋中命途多舛的“鸠”象征弱者受到来自强大势力的摧残和迫害,同时也暗示曹魏政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凶猛狰狞的“狂犬”象征着残暴的司马氏集团,表现出作者对司马氏集团的愤恨与不满,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对司马氏忌惮、畏惧的心理。
2.《猕猴赋》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猕猴以其凄凉怪异、悲哀婉转、连续不断的长啸声为人所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猕猴的记载,如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西晋傅玄的《猿猴赋》。阮籍的《猕猴赋》对猕猴形态刻画栩栩如生:“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呻兮,似巧言而伪真。”[3]11韩格平指出:“文中对猕猴形态的描写,可能包含有作者对历史与现实中某些人物的嘲讽,亦不排除作者对自己身为人臣受羁于世的感慨。”[4]62笔者认为,阮籍正是通过对猕猴的批判表达对魏晋时期所谓的礼法之士贪求利欲、献技逞巧、人面兽心的辛辣讽刺,意在撕开他们虚伪的面纱,揭露他们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丑恶面目和卑鄙行径。从外表看,他们俨然是一副道貌岸然的形象,“整衣冠而伟服”,然而骨子里却结党营私,最终落得“伏死于堂下,长灭没乎形神”的悲惨下场。作者在批判的同时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和悲悯之情。
(二)都邑赋
都邑赋是汉魏六朝赋的又一门类,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以赋为首,而赋中又把京都赋放在第一卷,可见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阮籍之前的都邑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旨在通过描述都城来揭示社会问题。例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另一种则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主要是描摹某座都城山水形胜、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代表作品有扬雄的《蜀都赋》、刘桢的《鲁都赋》等。阮籍的《亢父赋》《东平赋》虽是由都邑赋发展而来,但他敢于突破传统,另辟蹊径,大胆创新,一改前代都邑赋“铺张扬厉”之风,代之以犀利的笔锋,借对普通小城邑的批判,反映当时社会的混乱,抒发自己愤世嫉俗之情。
1.《亢父赋》
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著述中“亢父”均作“元父”,在《历代赋汇》后附考证中称其应为“亢父”,据陈伯君考证:“诸书无‘元父’一地名,断为‘亢父’无疑。”[3]19古代确有亢父城,故应为亢父,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南部。阮籍在小序中言明自己的写作目的:“吾尝游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赋以诋之,言不足乐也。”[3]18诋,即诋毁、贬低之意,明确表达了写这篇赋的目的是评判与抨击。
其区域壅绝断塞,分迫旋渊,终始同贯,本末相牵,畴昔迄今,旷世历年。钜野潴其后,穷济尽其前,甽浍不畅,垢浊实臻……故其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怀私抱诈,爽匿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3]18-19
《亢父赋》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亢父的不足与问题,赋末发出疑问:“先哲遗言,有昭有聋。如何君子,栖迟斯邦?”[3]19君子们是否了解亢父的情况?如果了解,为什么还要逗留在这样一个城郭里呢?这就委婉而意味深长地把讽刺矛头指向了所谓的正人君子,细品便可觉出全篇深沉的愤世嫉俗之情。
2.《东平赋》
《东平赋》所写东平故城在山东省东平县,“《汉书·地理志》注:故梁国,景帝十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5]《晋书·阮籍传》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即拜东平相。”[6]1360据此可以得出,《东平赋》当作于阮籍出仕东平相之时,约正元二年(255)。
阮籍此次去东平,真的是乐其风土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为了摆脱司马氏集团的纠缠,躲避政治祸乱。这篇赋里,阮籍描写的东平是“西则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所庐。三晋纵横,郑卫纷敷。豪俊凌厉,徒属留居。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是以其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向气逐利,罔畏惟愆。”[3]3-4作者所描写的东平实际是司马氏集团专政时期社会状况的缩影,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司马氏集团残暴统治的不满,也流露出他想在乱世中归隐山林、躲避祸患的想法。综上,批判现实与超越现实是阮籍都邑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
(三)述志赋
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类型, 述志赋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它强调“志”,具有说理色彩;另一方面,注重抒发个人情感,体现个性特点。
1.《首阳山赋》
阮籍《首阳山赋》序说:“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3]8从序文可以确定该赋作于正元元年(254),这一年司马氏废齐王芳而立高贵乡公,改年号为正元,此时社会动荡、朝政剧变,阮籍正担任司马师之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6]1360但面对如此动荡的局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所想,感情喷涌而出,写下《首阳山赋》。该赋首写离开官场后的孤苦伶仃,然后写面对首阳山所生发的吊古情怀。
阮籍父子崇尚儒学,他的父亲阮瑀曾为了纪念伯夷、叔齐两位儒家圣贤而作《吊伯夷文》,阮籍也曾在《咏怀诗》中提及伯夷、叔齐二人,表达了对他们的敬重,如《咏怀诗》82首其五:“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首阳山,相传是伯夷、叔齐隐居处。伯夷、叔齐是商代孤竹君的儿子,他们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这是群臣弑君,以暴制暴的不义行为,所以他们拒绝仕周,为表示自己不向周政权妥协的决心,他们也拒绝吃周朝的粮食,在西山采薇而食,最终被饿死。此诗中阮籍之所以说要到西山隐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意与当权者合作,他想走伯夷、叔齐的老路,由此可见阮籍对于伯夷和叔齐的所作所为发自心底的赞同。在《首阳山赋》中,阮籍指出伯夷、叔齐二人“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比进而不合兮”[3]8的行为是不得“称乎仁义”的,并发惊世之语:“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3]8。批判伯夷、叔齐的行为是“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3]8。最后笔锋一转提出“清虚以守神”的处世思想,矛盾背后的深意值得探究。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7]而阮籍却说“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3]8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其用意何为?
张建伟在《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中谈到,这里的夷、齐实际上是阮籍自我的一种暗指,他是借对夷、齐的评价,来反思自己的仕途之路,借对夷、齐囚于周,自身难保,不可能谏言武王伐纣之事,来隐指自己囚于司马氏之朝廷,自身难保,不敢言司马氏篡魏之事。表面上是对夷、齐妄发评论的批判,实则是对自己身处黑暗社会,不能像夷、齐那样评判时政的怨恨,表现出他对司马昭以“名教”治世的不满和自己的自责悔怨之情。阮籍在赋末连用三个反问句“何称乎仁义?”“何美论之足慕?”“焉子诞而多辞?”表面上是对伯夷、叔齐做法的质疑,实质上是对“秽群伪之射真”[3]8的黑暗现实的抨击,隐晦曲折地表明自己“宁高举而自傧”[3]8的生活态度。阮籍深谙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对魏晋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了然于心,这使他意识到在复杂时代背景下说话不当易招致祸患,所以他避免直接抨击时政,而采取婉转隐晦的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孤愤之情。
2.《清思赋》
《清思赋》是阮籍思想由儒入道之后的作品,它摒弃了对女性的爱慕崇拜,否定了世俗的女性之美,追求一种真正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理想状态。赋中作者神游于“清虚寥廓”[3]13的世外之境,遇见了理想中容貌秀丽、清雅高洁、超凡脱俗的佳人,可正当阮籍“观悦怪而未静”[3]15时,佳人却“翻挥翼而俱飞”[3]15。眼看佳人的远去,他无力挽留,只能“临寒门而长辞”[3]15,独自在外漂泊、逍遥四方。阮籍在赋末劝勉、宽慰自己:“既不以万物累心兮,何一女子之足思!”“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伊衷虑之道好兮,又焉处而靡逞。”[3]13
阮籍继承了老庄的虚静思想,“恬淡无欲”表达出作者摆脱了苦苦追寻的忧思。在没有了对女性美色的狂热追求后,佳人的清雅、高洁虽然与阮籍的审美理想相吻合,但从他追求安逸、恬淡的理想境界来看,追求佳人还是被世俗的束缚羁绊所致的不当行为。《清思赋》反映出阮籍由热切追求理想到平淡无欲的转变,与赋中所描写的空灵逍遥无牵挂的意境相呼应,反映出阮籍摒弃尘世的“清思”意旨。
二、阮籍赋的艺术特色
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盛赞阮籍赋作:“大言小言,清风穆如,间览赋苑,长篇争丽,两都三京,读未终卷,触鼻欲睡。展观阮作,则一丸消疹,胸怀荡滌,恶可谓世无萱草也。”[8]由此可见,阮籍赋的艺术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对其艺术特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阮籍的作品。
(一)比兴象征,含蓄隐晦
阮籍赋含蓄隐晦,究其原因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唐人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害,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9]322阮籍内心的愁苦、哀怨只能通过委婉隐晦的方式,大量运用比兴和象征等艺术手法来表达。
阮籍赋沿袭了前代赋大量使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如在《东平赋》中,阮籍用“鹿”“猪”等象征司马氏的党徒,用“松”“骏马”“礼服”“彩绣”象征自己的才华和远大抱负,用“风雨”“严霜”“变幻的云彩”等象征险恶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在《猕猴赋》中,以“猕猴”象征魏晋时期争名夺利、人面兽心的所谓世俗礼法之士;以“鼷”象征试图远离政治、躲避祸患但又无可奈何的人;以“夔”“熊狚”象征生活在偏远荒凉、远离尘嚣之地但仍然无法逃脱迫害的人。这篇赋通过刻画各种动物,隐晦地把阮籍对世俗社会的嘲讽表达了出来。阮籍内心那些不能直接表达的绝望与痛苦通过象征、比兴等艺术手法的运用表现了出来。
(二)想象丰富,意境寥廓
魏晋之际,以“竹林七贤”为首的一批文人墨客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阮籍是其中一位。阮籍推崇庄子的寥廓之谈,其赋的叙述对象多为寥廓虚幻的想象及内在精神体验,加之他想象丰富、才思敏捷,凭借自己的感情之需表达自己的情绪,故而能够挥笔成文且自然洒脱,毫无修饰痕迹。
阮籍《东平赋》有“请王子与俱游”的想象,幻想自己远离尘世纷扰。“漱玉液之滋怡兮,饮白水之清流。……忽一寤而丧轨兮,蹈空虚而遂征。扶摇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显兮,喜太阳之炎精。凭虚舟以遑思兮,聊逍遥于清溟。”[3]5描写虚幻情景时,作者的笔法如行云流水般灵动,给人以恢宏寥廓的感受。《清思赋》中,当追寻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佳人时,阮籍“载云舆之奄霭兮,乘夏后之两龙”。他改变了前人以细致笔法描摹美人容貌娇态及思慕美人的传统,从大处入笔:“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3]13作者增添了翱翔于广阔空间的神游情节,在此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对美感、心理特征的表现上,呈现出思绪飘渺、意境寥廓的艺术特点。
(三)化用典故,自然巧妙
阮籍赋善于引用、化用典故,使得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厚而富有深意。
阮籍在《东平赋》中引用了大量古代神话,如“伶伦游凤于昆仑之阳,邹子翕温于黍谷之阴,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羡门逍遥于三山之岑。”[3]3以伶伦、邹子、伯高、羡门四个传奇人物为例,向世人展示了“奇伟谲诡”的世外之地,与东平的鄙陋卑劣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鸥瑞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3]5他借《列子·黄帝》中的鸥鸟故事,歌颂了海鸥的一往情深,感叹它们最终被落空的纯真朴实之心。《猕猴赋》中“整衣冠而伟服兮,怀项王之思归”[3]11中的“项王思归”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将项羽沽名钓誉、刚愎自用又残忍野蛮的性格特征表露无遗,讽刺他像猴子一样虚有其表,目光短浅。
三、阮籍赋与前代赋对比
阮籍赋既有对前代赋的继承,也有自己的独创,因此在“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下面将阮籍赋与前代相关作品进行对比,探讨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以便对阮籍赋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阮籍鸟兽赋与祢衡《鹦鹉赋》对比
1.表现手法相同之处
阮籍鸟兽赋与祢衡《鹦鹉赋》都运用了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两汉三国时期的鸟兽赋大多只是简单地铺陈体貌,缺乏深意寄托,少数作品虽有寄托,但多在感情的抒发中融入个人身世之感,有物我一体的创作风格。祢衡的《鹦鹉赋》正是如此,祢衡对鹦鹉细致入微的描述与他个人的生命经历相融合。
《鹦鹉赋》用精致的文辞对鹦鹉进行了刻画:“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11]942这只色泽明丽、机灵聪慧、情趣高洁的鹦鹉其实就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他借对鹦鹉的美貌和“殊智异心”的高度赞扬,含蓄地展现了自身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情志。但因这只鹦鹉具备的美好而导致被捕,它从抗争到顺从,最终落得“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10]942的悲惨结局。借鹦鹉凄惨的际遇嗟叹自身悲惨的生存状态,抒发了他生逢乱世,颠沛流离、漂泊沦落、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痛苦历程,以及当时下层知识分子深感命运无奈、徒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绝望和痛苦的心情。这篇赋物我交融,看似写鹦鹉的遭际,表达对鹦鹉的同情,实际上是对自我遭遇的同情,鲜明地体现了托物言志的写作特点。
阮籍在祢衡《鹦鹉赋》托物言志的风格上向前开拓。《鸠赋》中,阮籍以狗杀两鸠影射司马懿对王凌、楚王彪的杀害,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司马氏政权及其党羽的痛斥与怨恨;《猕猴赋》则是借对猕猴的刻画讽刺那些贪求利欲、虚伪世故、人面兽心的礼法之士,表现出对其的憎恨和厌恶。阮籍鸟兽赋借对动物的描写,表现司马氏集团的凶狠残暴与弱者的悲惨命运,阮籍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混乱的社会,使得赋的社会批判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后世的刺世之作起到了引领作用。马积高先生认为,阮籍是曹魏正始前后讽刺赋最有成就者,这说明阮籍赋的批判性在“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这是祢衡《鹦鹉赋》所不能达到的。
2.表现手法相异之处
祢衡《鹦鹉赋》注重铺陈,阮籍鸟兽赋注重白描,这是祢衡《鹦鹉赋》与阮籍鸟兽赋在表现手法上最明显的差异。
《鹦鹉赋》开头就运用了铺陈的手法,从多个方面表现了鹦鹉的不凡。首先,作者用“金精”和“火德”来描述鹦鹉的明辉鲜丽,用“能言”和“识机”来描述它的智慧,然后用想象来描绘它“嬉游高峻,栖踌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11]942的高洁情趣,又直接描绘其容貌美丽,最后通过“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11]942的对比,衬托出鹦鹉的丽容奇姿,聪颖机智。
阮籍鸟兽赋注重勾勒,他深受建安抒情小赋的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前代鸟兽赋进行了大胆创新,减少了对物大量的铺陈描写,转而以白描手法进行粗线条式的勾勒。
3.意象创造
意象创造方面,祢衡《鹦鹉赋》和阮籍《鸠赋》都刻画了“囚鸟”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文人通过刻画“囚鸟”意象来表达他们怀才不遇、有伟大抱负却无施展之地以及受仕宦羁绊的苦闷感受。正如祢衡《鹦鹉赋》中,鹦鹉被困笼中,感叹不已:
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10]942
鸟兽赋抒发的最广泛的情感是对自由的渴望。祢衡在《鹦鹉赋》中也多次表现出这样的情感倾向,如:“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10]942。“昆山”与“邓林”本指能使鹦鹉纵情任性、放飞自我的地方,这里通过暗指表达作者对“昆山”与“邓林”的向往之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
阮籍《鸠赋》也是“囚鸟”,但该赋中“囚鸟”的结局是被狗所害,这种结局与《鹦鹉赋》中所描绘的“囚鸟”形象有区别,这是“囚鸟”意象在创作上的突破。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时期,《鸠赋》的寄寓意味不言而喻。
(二)阮籍都邑赋与班固《两都赋》对比
班固的《两都赋》是汉代散体赋中的名篇,也是都邑赋的代表作品。
下面从写作目的、表现手法、思想情感、作品内容四个方面将班固的《两都赋》与阮籍都邑赋进行对比分析。
1.写作目的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写道:“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他认为写诗作赋为君王歌功颂德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法则,能使国家的美名得以流传,所以是必不可少的。加之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9]37在班固看来,当时天下太平,朝廷安宁,京城洛阳发展迅速,设施制度日益完备。然而长安的老年人却很不满意,他们想让皇帝多关注一下长安,夸赞长安的规模制度是何等宏大完善,同时也对如今洛阳的简陋和落后嗤之以鼻。作者为了消除“两都”在民众心中的疑虑和不对等的错误观念,用必须建都洛阳的道理说服他们,所以作此赋来反驳。
与班固《两都赋》的创作目的不同,阮籍都邑赋的创作目的则在于表现对专制统治、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生活、人生的困惑和迷惘,表现了他受羁于世不甘无为却只能无为的痛苦悲愤之情。
2.表现手法
班固《两都赋》采用雍容铺陈、华丽夸张的艺术手法,其中尤以《西都赋》表现突出,如对宫室进行描写:“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虎贲赘衣,阉尹阍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9]37作者用大量笔墨,将西都的繁华、琳琅满目、无所不有用华丽的辞藻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夸张的笔调竭力刻画长安形势之优越险要、贡物之珍奇贵重、物产之丰饶充裕,展现出一幅琼楼玉宇、琳琅名贵、富丽豪奢、动静有致的华丽图景。
而阮籍的都邑赋一改前代对都城大邑的详细描写的传统,洗去汉大赋的极尽铺排,以简略的文字、大笔勾勒了普通小城邑地理环境恶劣、社会风气低俗,且更加注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
3.思想情感
班固在《两都赋》中对帝王的描写过于理想化,如曹道衡先生所说:“但从强调‘讽喻之意’这一点来说,班固的主张并不错,而他的写作实践,却只是加强了说教部分,而在实际并未真正摆脱司马相如、扬雄作品的弊病。”[11]80这是指他的讽谏意图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而阮籍两篇都邑赋均具有讽刺意味,寓有深沉的愤世之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展示了阮籍对魏晋易代之际现实政治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拓宽了都邑赋的思想主题。
4.作品内容
《两都赋》所写内容广阔,从多角度、多方面描写了当时长安、洛阳都城的繁荣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反映了汉代空前的强盛。班固将京都题材与铺陈描写结合起来,形成了汉代散体赋中的京都赋这一门类,被后世许多文人借鉴、效仿。阮籍的《亢父赋》《东平赋》对于传统都邑赋的创新在于以犀利的笔锋,直陈两个普通城邑环境恶劣,市风粗俗低下,拓展了都邑赋新的写作内容。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阮籍创作的都邑赋与班固等人写作的京都赋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题材的写作上,阮籍开创了全新的领域。
(三)阮籍述志赋与扬雄《太玄赋》对比
两汉述志赋涉及玄学的寥寥无几,而扬雄的《太玄赋》就是一篇代表性作品。在思想方面,扬雄的《太玄赋》与阮籍述志赋《清思赋》都表达了超凡、脱俗、避世的道家思想,但主旨不同。
扬雄在《太玄赋》中写道:“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12]138贪图富贵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所以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是“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于中谷”[12]138,向许由、老聃学习,进入深山老林去清静自守。他期望作“圣典以济时”,却担心“身殁而名灭”,又希望“执玄静于中谷”,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游仙,希图求道纳静、自由自在,过上歌舞闲适、与仙同乐的美好生活。扬雄在赋末写道“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12]138他认为屈原投河、伯姬焚身、孤竹二子饿死首阳山等做法都是不值提倡的,他选择冲破世俗和传统的束缚而执守《太玄》。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玄学大兴,涉及玄学内容的赋作数量明显增多。阮籍的《清思赋》虽推崇道家思想,却又有不同于《太玄赋》的主旨。《清思赋》的开篇即是玄理:“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3]13这篇赋字面意思上写对清虚高洁、超凡脱俗的神女的追求与爱慕,实际上表达对“美”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它超越了世俗对佳人美色的追求,而强调对清虚逍遥、无所系累、幽适恬淡的理想心境的追求。此赋把现实的人生体验与玄学思考结合起来,展现了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与扬雄《太玄赋》相比,阮籍在《清思赋》中所表现出的崇尚老庄之学给人以超越自我的精神感受,他对于魏晋玄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阮籍是魏晋之际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对阮籍作品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了解阮籍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赋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