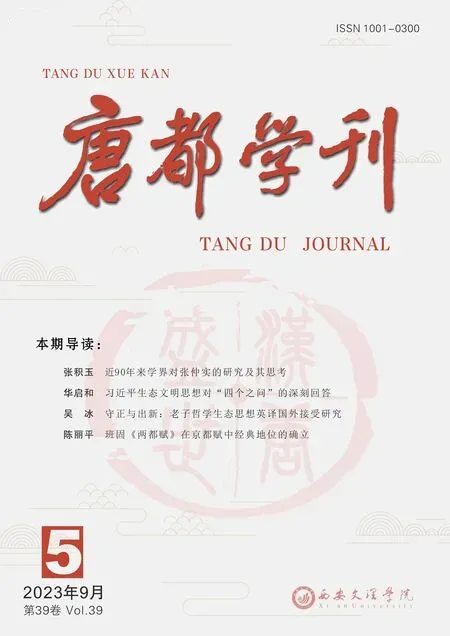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唐亚萍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康德构建的道德哲学体系是纯粹的,且不掺杂任何经验。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和目的王国的构建中,康德首先提出了责任概念,认为“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6,进而阐述了责任原则到意志原则的逻辑演进,责任最终指向的尊严。在目的王国中,一切存在者都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但目的王国中人有理性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一个按理性做事的人,因此理性是人被尊重从而过有尊严生活的条件。也就是人通过理性并按理性去做才能具备德性,最终获得尊严。在追求自由的问题上,康德从责任出发,责任是人实现自由的起点,而实现自由在于人要摆脱感性经验的束缚,自觉服从道德规律,即由责任的“他律”转化为“意志自律”。人作为主体在经过责任这种外在的约束过渡到意志自律,从而进入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有理性者自觉履行责任,自己为自己立法,且所立之法也是每一个有理性者所要服从的法,人基于理性并运用理性去赢得尊重,进而获得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尊严与人格,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一论证为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提供了依据。从“责任”到“尊严”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从准则到道德自律的过程,虽在这一过程的构建中存在不现实之处,甚至最终陷入悖论,但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这一逻辑关系的严密论证在其成功构建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责任作为一种行为必要性
康德指出:“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6,那么何为行为必要性?行为必要性又何以可能?
(一)何为行为必要性
康德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在于善良意志,其责任概念由善良意志推导出来。康德的善良意志是自在的善,是所有品质中真正决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原始力量。而善良意志仅仅是针对行动本身,是作为动机存在的。康德所追求的善是人如何按照普遍法则经常去做好事,去做该做之事,而不是根据做好事所带来的结果,导致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而使做好事成为不必然。康德在三个命题中对责任下了定义,即“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6。其行为必要性是指人基于何种要素经常去做好事,康德认为这个根本要素便是善良意志。而善良意志只是人做好事的起点,是一种行为的动机,但行动仅仅只有动机则远远不够,故而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了责任概念。责任概念属于关系范畴,能够引出可传达的命令,要求人必须去做一件事,这种必然的要求将行动上升到规范的意义上来,上升到命令的陈述上来,因而善良意志向责任概念的过渡是由行动的质料上升到命令的抽象上来,一个人如此行为才能使你的行为具有有效性。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实际上是由实体性的行动概念上升到可传达的普遍法则的表述问题上来。因此,责任概念是连接法则和行动的中间概念,是一种行为必要性。对于人来说,责任同义务一样,都是必须做的事情,那么责任对于人就有一种必要性,被称为“自我强制性”或“约束性”。可以看出,康德的责任概念不是经验世界的东西,其对于人的约束性主要体现为人心中的自我约束,“责任的戒律越是崇高,内在的尊严越是昭著,主观原则的作用也就越少”[1]6。因而不能将责任简单地归结于经验世界,更不能将其与爱好、任意相提并论,否则便等同于摧毁了责任的基础,更会损坏责任的尊严。
康德从行动问题引出了责任,通过行动而引起的行为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出于责任的行为,即我该做之事,必须做的事,如作为子女必须要孝敬父母,作为学生要尊敬老师。事实上,康德所强调的出于责任的行为并非是做一件事只有一个目的,而是做一件事当利己的目的与利他的目的并存之时,能将利他的目的放在其他目的之前,并非是将利他目的作为唯一目的确立下来,这便是康德所说的出于责任的行为。第二种是合于责任的行为,即我既对尊重法则有兴趣,又对尊重法则之后果感兴趣。第三种则是反乎责任,即为了自身利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康德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中,出于责任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道德价值。同时,出于责任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并非由其所要实现的意图来决定,而是由所规定的准则来决定,进而得出“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6。责任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东西,因此责任是一切行为的实践必然性,它要求每一个有理性者都从内心去尊崇责任,以责任为动机去行动。若行为仅合于责任,仅与责任的诫律相契合,其动机完全不同于出于责任的动机,并与爱好、任意无甚区别。如保存自己的生命是合乎责任的,这种行为或许出于某种情感,不具有道德价值。街头小店挂着“童叟无欺”的牌子,对于一切顾客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无论是白发老人还是黄口小儿,这样的行为并非是由于诚实,而是由于个人对利益的爱好,便不具道德价值。若一个处于逆境仍然意志坚定且不失活下去信心的人,体现出了其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这便具有道德价值。故而,“行动的一切道德性建立在其出于义务和出于对法则的敬重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建立在出于对这些行动会产生的东西的喜爱和好感的那种必然性上。”[2]责任作为一种行为必要性就体现在有理性的人怎样去遵从它,行为是出于责任还是合乎责任或是反乎责任是康德评判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标准。
(二)行为必要性何以可能
责任是基于尊重而产生的,要搞清楚责任作为一种行为必要性何以可能,就需要弄清康德“尊重”的意涵。康德指出:“尊重是一种情感,只不过是一种因外来作用而感到的情感,而是一种通过理性概念自己产生出来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与前一种爱好和恐惧有区别的情感。我直接认作对我是规律的东西,我都怀着尊重。这种尊重只是一种使我的意志服从于规律的意识,而不须通过任何其他东西对我的感觉的作用”[1]51,“所以,尊重是规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而不能看作是规律的原因。更确切一点说,尊重是使利己之心无地自容的价值觉察”[1]51。规律作为尊重的对象,是行为主体自身必须要尊崇的东西。同时,我们必须服从于规律,但这与恐惧的情感相类似而尊崇规律,其作为主体意志的后果,又与爱好的情感相类似。康德认为尊重一个诚实的人,可能是由于这个人在诚实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但这实际上是我们对诚实的尊重。能够看出康德所指的“尊重”的情感并非纯粹的,它偏向于爱好,但又出自于规律,因此康德又说道:“直到现在,我还说不清尊重的根据是什么,这可由哲学家去探讨,不过我至少可以懂得,这是对那种比爱好所中意更重要得多的价值的敬仰。”[1]53但责任是来自对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在责任面前一切其他动机都黯然失色,责任是善良意志的条件,责任也是“尊重”的基础。“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1]73在这里只有定言命令能够应用于责任,责任便成为对人一直有效的规律。尊重是行为主体加之于自身的,尊重即是作为一种纽带,致力于让有理性的东西超越责任的束缚而自觉遵守道德规律,从而实现道德规律与责任相统一。
责任是一种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就是让人们基于某种因素去做好事,并且持续做好事。在尊重的情感下,人们出于责任而尊重规律,便能使得“责任”这种行为必要性成为可能。康德提出人基于责任做好事的根源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是自在的善,所以康德将其定性为人按照普遍法则做好事的出发点。从康德对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尊重的重要性,尊重是作为人能遵守道德规律并能持续做好事的纽带而存在的,它在人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人履行责任是以善良意志为基点,以尊重为纽带,以目的王国为实现介质,以德性为手段,以实现人的尊严并最终使人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的。
二、从责任原则到意志自律原则
责任虽是一种行为必要性,但却不够纯粹,不能使人达到纯粹理性的状态。康德由定言命令推导出了责任原则、目的原则和意志自律原则。在责任原则阶段,责任只是作为连接法则和行动的中间概念,存于“此岸”世界中。从责任原则过渡到目的原则最终上升到意志自律原则,就是将准则上升到合乎道德的层面,将准则上升到了普遍的法则,将一般的道德理性知识上升到了道德形而上学,最终使人获得普遍的意志自律。
(一)“此岸”世界的责任原则
康德指出:“这样一种全然独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它不仅是责任的、全部确定可靠理论知识的根基,并且是责任诸规范付诸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条件。这种纯粹的、清除了出自经验外来要求的责任观念,一般地说,也是道德规律的观念,仅通过理性的途径,对人心产生了比人们从经验所得到的,全部其他动机都要强而有力的影响。”[1]61这种纯粹的责任观念鄙视那些来自经验的动机,并逐渐成为它们的主宰。康德通过实际的案例将责任分为“对自己的完全责任、对自己的不完全责任、对他人的完全责任以及对他人的不完全责任”[1]9,可以得出责任并非是在行为的对象上服从同一原则,而是在约束力的类型上服从同一原则。责任的制定不依从外在的条件,而在于其主体意志之中。在违背责任原则时会发现,我们不愿意自己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自己的准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如果从理性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在我们的意志中存在着矛盾。责任原则对个人的行为具有立法的作用,并通过定言命令表示出来。因此,责任是一切行为的必要性,它适合于一切有理性的东西,对一切人类意志都有效。与此相反的是,从人性的情感和嗜好中,或者从一种特殊只为人类理性所具有的经验主义的倾向中无法引申出规律,相反只能引申出准则和主观原则,责任的诫命愈发严苛,其内在尊严便愈发崇高,人的主观意志也就越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责任诫命的规律性也不会因此减弱,其有效性也不会因之受到影响。
在责任原则阶段,哲学面临一个危机,它需要一个固定的立足点,然而却在此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立足点。道德规律的实现在于有理性东西的自觉遵从,它存在于“彼岸”,而责任作为一种行为必要性却存在于“此岸”。在这一阶段有理性者还无法出于内心的自觉而摆脱责任的束缚进而达到“彼岸世界”的道德规律。因此,责任只是实现人类尊严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二)“彼岸”世界的意志自律原则
一切实践立法都能够按照责任原则而成为规律,并以目的为根据。在目的原则中,人是一切目的的主体,因而从此处引申出实践意志的最高条件的意志自律原则,“行动所依从的准则必定是以自身成为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准则”[1]101。意志自律原则是道德的至上原则,它由绝对命令推导出来。绝对命令要求有理性者主观所立之法能够成为普遍的客观的法则,这便强调的主观准则与普遍法则具有一致性。即是要求以行动者主观方面的原则在特定情况中对主体有效,并对所有的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在意志自律原则中,每个有理性者都作为普遍立法者,并在其观念中排除了一切无关理性的经验因素。人通过责任被规则所约束,所服从的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其所受到的约束就是按其自身所固有的意志去行动。如果人们由于一种关切或兴趣去服从某种规则,正是因为这种规律不是从其自身的意志产生出来的,而是被迫服从某种规则而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人们没有依据责任而行动,其行为仅是出于某种关切而产生的,这种关切可能是直接关切,也可能是间接关切。但归根究底,命令总是不足以成为道德诫命的,因此意志自律就是有理性者排除了经验,对自己的意志提出命令,自己成就自己的命令,无关责任,自己为自己立法。
康德认为,自由概念是阐明意志自律的关键,认为意志不受外力约束而独自起作用,这是对自由的消极阐述。而自由的积极概念是指通过因果性而呈现出来的稳定的规律,是具有不变规律的因果性。它不同于自然规律,康德论证了人何以自律,这便在于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作为因存在的,它是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因,它产生的果是按照其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就是说“意志所固有的性质就是它自身的规律”[1]101。康德从自由所固有的属性中引申出了道德,自由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所固有的属性,作为有理性的人能够享受自由,但这不足以实现意志自由,而道德作为规律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因而自由是一切有理性者所固有的属性。因为有理性者在目的王国中自己为自己立法,所立之法为所有成员共同适用,这正是通过道德自律来实现的。康德认为,道德观念就是自由观念,康德道德哲学所追求的就是有理性的人要获得德性,有德性的人才能在目的王国中为自己立法,成为自己的主人。
(三)从“此岸”世界的责任原则到“彼岸”世界的意志自律原则
有理性者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普遍立法,并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自身,这样就出现了“目的王国”。康德认为,在目的王国中,有理性者作为普遍立法者而存在,规律只能出自于其自身的意志,其行动也服从于这些意志和规律。正如伍德所说:“康德认为目的王国是理性存在者处于共同法律规则下的联合。”[3]在康德那里,意志自律原则就不仅是理性存在者为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并且应该成为所有有理性存在者都应该遵循的准则,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准则才能上升到合乎道德的层面,只有有理性存在者的准则上升为普遍的法则形式,我们才能获得普遍的意志自律。在目的王国中:“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24康德认为,意志自律是一个先天的道德命题,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受其约束,并自觉服从规律。马克思也充分肯定康德的道德自律,他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4]如果意志自律受到感性经验的影响,就会产生出他律性。他律性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其玷污了善良意志的纯洁性。不绝对的善良意志的行为不是出于对责任的纯粹尊重,是由于责任的约束性;相反,绝对的善良意志的行为是出于对责任的尊重,是基于人自身的本性、理性本身作为目的去行为。
在责任原则中,人只是出于责任去服从规律,这一阶段中的规律在“彼岸”,人在“此岸”。人无法摆脱经验世界的束缚,因此对于规律人无法达到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相统一。在目的原则中,康德强调无论在任何时候,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进一步将人从责任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人要走向自由,必须摆脱经验世界的束缚。在这一阶段,人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达到了统一,但规律还未从经验世界走向人的心中。因而,意志自律原则就是二者的高度提升。在意志自律阶段,规律完全被植入人的内心,在目的王国中,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同时通过准则而普遍立法。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既是首脑又是成员,人在这一阶段是完全出于意志,而不是将道德规律看成是外在的约束去服从规律,进而达到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统一。在康德那里,目的王国是理想中的王国,而意志自律却是唯一的道德原则。意志自律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自我约束,从理性出发,不依赖于外物,不基于责任的束缚,而形成的一种从普遍立法的观念出发,不以任何关切为根据,并在一切命令式中无条件地向目的王国过渡。因此,意志自律是使人能够真正达到自由的“手段”,也是最接近可能的目的王国的“手段”。
三、责任是人实现其尊严的基点
责任是一种外在约束力,是道德价值的根源,它是属于经验世界的行为,所以无法使人达到自由。责任最终指向的是尊严,尊严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只有当责任上升到意志自律的阶段,人才可能实现其尊严。
(一)尊严与道德价值
“目的王国中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1]87可见,尊严在目的王国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尊严是目的王国中每一个有理性者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1]88这里的“人性”就是指理性,明确表达出康德所说的有理性的东西通过理性并按理性去做便具备了德性这一条件,人便获得了尊严。在目的王国中,康德将价值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价值,与人的爱好与需要相关,可用于交换,既非是自足的,又非终极目的,故而不具有尊严;第二种是欣赏价值,取决于他人的兴趣与品位,这也不是人的最高价值;第三种是内在价值即尊严,尊严无法用价格来衡量,并且是自足的,因而是最高价值。基于此,无论是可交换、可替代的市场价值还是超越功利的欣赏价值都不是尊严,尊严是以内在价值作为行为动机的思想方式,它高于一切感性的物质东西,与权力、地位、欲望等一切的爱好都无关,是一种独立于一切感性价值之上的绝对理性。道德价值并非人所要追求的全部,尊严才是道德价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的,尊严来自规律,规律正是作为责任的基础。正因为责任以先天的道德规律为基础,并对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有效,其毫无利己之心且完全普遍,所以责任才具有强制性和必要性,才能成为道德价值的源泉。
康德强调,在目的王国中尊严是有理性的存在者自觉去服从道德规律获得的,而责任是人将道德规律看成是外在的约束,非发自内心地服从道德规律。责任是一种实践必然性,要遵从“任何时候都要按照与普遍规律相一致的准则行动,所以只能是他的意志同时通过准则而普遍立法”[1]87这样的原则来行动。在目的王国中对首脑并不施加责任,责任只以相同的尺度适合于每一个有理性的成员。目的王国中的每一成员都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责任必须基于理性,而经验世界中的责任由欲望、爱好以及情感所“掌控”,其中的人是“不道德”的人,不是理性的人。因此在康德那里,责任是基于尊重的理性的一种行为必要性,有理性的人最终追求的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我们在目的王国中追求尊严,尊严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而康德指出“唯有立法自身才具有尊严,具有无条件、不可比拟的价值,只有它才配得上有理性东西在称颂它时所用的尊重这个词,所以自律性就是人和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1]89。自律是行为主体自身遵从理性而为自己立法,并且每一个立法者所立之法对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具有效力,只有人达到自律的状态,达到出于本性去尊重规律,才能赢得尊严。
(二)从经验世界的道德价值到目的王国的尊严
康德构想的目的王国只是一个可能的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中,实践理性对经验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使经验世界合乎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这个经验世界成为理想的道德世界”[5]。但康德也提出:“目的论把自然当作一个目的王国,道德学则把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当作自然王国。在前一种情况下,目的王国是用来说明现存事物的理论观念。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然王国则是一个实践观念,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把尚未存在的东西变成现实,也就是与实践观念相符合。”[1]26并在这个理想的目的王国中,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应该将自己当作目的,而非工具。目的王国对于人只是可能的存在,人把希望寄于这个理想王国,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批判,也力求超越现实世界。在康德那里,目的王国也就是一个在人类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以道德律为根本律的人类的理想王国。人在现实世界、经验世界中生存,我们仅仅只能依据它是否符合规律的要求来对人作出评价,并且我们至多只能从责任这一层面进行分析。在动机意志层面,康德承认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到底是出于对责任的纯粹尊重还是出于对尊严的追求。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承认人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就在于其行为是否出于责任。因此,责任和尊严是不同的两个层面,出于责任的行为我们认为其具有道德价值,但出于尊严的行为,以尊严为目的,人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纯粹的自律。
目的王国中以尊严为最高价值,在康德看来,一切有理性的东西最终追求的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尊严,尊严是行为主体自身能够摆脱责任,摆脱经验的束缚,最终达到完全自律而去追求的东西。同时,在目的王国中,我们所要探寻的基点不只是出于责任或合乎责任的行为,我们要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对于责任,只是一种对规律的服从,但那些尽到了自己责任的人,依然是崇高的、有尊严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尊严是从责任中体现出来的,是由人的内心对规律的敬重而延伸出来的。康德一直强调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并不否定责任在目的王国中的作用。责任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是作为人以外的彼岸的道德规律,是一种“他律”。只有当人完全出于责任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康德看来才是有道德价值的。但也有打着责任的幌子,其本心并非真正出于责任,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当然更谈不上赢得尊严。
责任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力,作为道德价值的根源,这是属于经验世界的行为,所以不可能使人达到自由。责任指向道德价值,道德价值最终则指向尊严,而只有当责任上升到意志自律的阶段,人才可能实现其尊严,“作为自在目的,有理性东西的本性就规定它为目的王国的立法者。对一切自然规律来说,它都是自由的,它只服从自己所指定的规律”[1]88。自由是意志所固有的属性,意志所固有的属性就是其自身的规律,即自由就是道德自律性。一切与自由密不可分的规律都被认作是自由的,在目的王国中,有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的意志,并且“自由就是按照我们给予自己的法律而行动”[6],有理性的东西达到了意志自律,也就具有了尊严,最终能够实现自由。
四、结语
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这是康德提出的从一般人具有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康德提出了目的王国,目的王国的提出为责任找到了根据和伦理的基础。在目的王国中,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其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人必须履行责任的根据。康德提出实践理性问题来解决责任的来源和人如何履行责任的问题,他从生活实践进行论证,回到人如何才能履行道德责任的问题上,即绝对命令如何可能。因此,康德解决了责任的行为必要性问题,履行责任需要实践理性,这便将善良意志、实践法则、实践理性三个要素综合起来,提出理性世界和经验世界。康德认为,人的存在有两个世界——理性世界、经验世界,理性世界是原型世界,经验世界是模型世界,人的理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此,康德便从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了责任概念的问题。康德最终提出了道德自律即意志自由,从人的内在做论证,主要以德性的、自律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行为如何遵守法则的问题。
康德道德哲学最大的缺点是不能现实化,不能将形而上的法则转变为形而下的行为规定。康德完全将经验世界置于理智世界的支配之下,得出“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结论,同时否定人在面对情感、经验世界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个体呈现出的难以抉择的状况。其处理理性世界与经验世界的方法过于简单,为了达到意志自由的目的,牺牲了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之间异常复杂的纠结与冲突,牺牲了生活世界的底色与快乐和幸福对普通人的重要性,这是人所不能接受的。康德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是对人追求快乐、幸福和欲望的限制,或是说人在经验世界或感性世界应该过一种有限制的生活。康德的道德哲学给予人一种指向:人应该过一种基于物质生活但超越物质生活而达于至善的有尊严的、有人格的、自由的生活,即无限制的精神生活。因而,康德的道德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体系,也反映了康德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