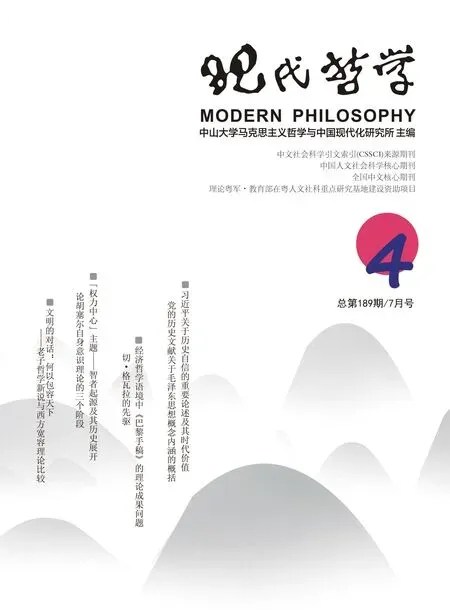极度痛苦论证与帕菲特的理由客观主义
李 红 陈 康
规范性理由(normative reasons)的本质问题是当代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s)研究的核心议题(1)规范性理由指的是支持、辩护行动和态度(比如信念)的理由。。与之有关的争论围绕多个问题而展开,其中之一涉及理由的内容或来源(2)See Ruth Chang,“Practical Reasons:The Problem of Gridlock”,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ed. by Barry Dainton &Howard Robinson,London:Bloomsbury,2014,pp. 474-475.。关于这一话题,目前存在两种主导理论,即理由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about reasons)和理由客观主义(objectivism about reasons)(3)下文分别简称“主观主义”或“主观理论”以及“客观主义”或“客观理论”。。大致来说,前者主张我们的实践理由依赖欲望,而后者认为我们的实践理由取决于价值。
在《论重要之事》一书当中,为了捍卫客观主义,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构造了三个论证来反驳主观主义。一般认为,帕菲特最看重其中的“极度痛苦论证”(the agony argument)(4)下文简称“痛苦论证”。另外两个论证是“全部或全不论证”(the all or none argument)和“不融贯性论证”(the incoherence argument)。。在他看来,这一论证决定性地反驳了主观主义(5)See 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 81.。一段时间以来,痛苦论证在学界引起不少讨论(6)See David Sobel,“Parfit’s Case Against Subjectivism”,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Vol. 6,ed. by Russ Shafer-Landau,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 52-78;Michael Smith,“Parfit’s Mistaken Metaethics”,Does Anything Really Matter:Essays on Parfit on Objectivity, ed. by Peter Sing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 110-118;Yonatan Shemmer,“Subjectivism about Future Reasons or The Guise of Caring”,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01(3),2020,pp. 630-648;Eden Lin,“Future Desires,the Agony Argument,and Subjectivism about Reasons”,Philosophical Review 129(1),2020,pp. 95-130;徐向东:《理性慎思与实践融贯性》,《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不过,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旨在表明:主观主义者能够回应痛苦论证的挑战。与上述讨论不同,本文试图阐明,即使痛苦论证成功反驳了主观主义,它也并不由此支持帕菲特的客观主义,一是因为帕菲特相信极度痛苦的本质(the nature of agony)给予人们理由想要避免这种痛苦,二是帕菲特认为痛苦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人们对痛苦感受具有一种享乐式的厌恶(hedonic dislikings)(7)相应地,快乐(pleasure)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我们对快乐具有享乐式的喜爱(hedonic likings)。对快乐和痛苦的这类态度合称“享乐式好恶”。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享乐式厌恶。。然而,以上两个方面并不兼容,因此帕菲特无法融贯地宣称人们有理由想要避免极度痛苦,这将导致痛苦论证无法支持他的客观主义。不仅如此,如果痛苦论证驳倒了主观主义,其范围也仅限于大卫·索贝尔(David Sobel)所说的动机主观主义(motivational subjectivism)。但根据帕菲特的核心信条,他实际上反对的是赞成态度主观主义(pro-attitude subjectivism)。一旦阐明了这一点,帕菲特关于享乐式好恶的观点最终将会削弱他的客观主义立场。
本文第一节主要论述帕菲特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刻画,同时阐明痛苦论证的内容及其对主观主义构成的挑战;第二节考察帕菲特对享乐式好恶和极度痛苦的看法,进而指出痛苦论证实际上并不支持他的客观理论;第三节表明帕菲特应当在赞成态度意义上来理解主观主义,鉴于此,他关于享乐式好恶的观点最终将会损害他的客观主义立场。
一、实践理由的两类理论与极度痛苦论证
理由主观主义者和理由客观主义者都认为,事实给予我们理由。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究竟哪类事实给予我们理由?根据客观主义,向我们提供理由的事实与欲望或目标的对象有关,或者与我们想要实现或设法实现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些理由属于对象给予的(object-given)理由。在帕菲特看来,对象给予的理由是基于价值的(value- based)理由,因为“仅当且由于我们所做之事或设法实现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或值得实现的,我们才有理由以某种方式行动”(8)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2.。而根据主观主义,给予我们理由的事实全部与我们当下(present)欲望的满足或目标的实现有关,或者依赖这些事实。由于这些事实和我们自身相关,所以这些理由是主体给予的(subject-given)理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欲望要做广义理解,是指“任何被驱动的状态,或者任何想要某事发生且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使之发生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9)Ibid.,p. 43.。而以上两类理论所涉及的欲望指的是目的性欲望(telic desires),即我们因其自身之故而想要它们。我们的目标则“常常是我们决定了要去设法满足的目的性欲望”(10)Ibid.,pp. 58-59.。
主观主义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如下:某个行动是我们最有理由去做的,仅当这个行动能最好地满足我们当下充分知情(fully informed)的目的性欲望,或者我们在理想的慎思(ideal deliberation)之后会选择去实施它(11)Ibid.,p. 64.。所谓充分知情,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相关的事实。对主观主义者而言,慎思指的是程序上合理的(procedurally rational)慎思,它涉及“充分想象我们各种不同的可能行动的重要后果,设法避免异想天开、正确地评估各种可能性和遵守某些其他的程序性规则”(12)Ibid.,p. 62.。充分知情且程序上合理的慎思就是理想的慎思。
帕菲特想要表明,理由主观主义具有不合情理的后果。为了揭示这种一点,他虚构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极度痛苦的情形:“我知道某个未来事件会导致我经历一段时间的极度痛苦。即使在理想的慎思之后,我还是不想避免这种极度痛苦。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欲望或目标,其满足会被这一极度痛苦或者被我不想避免这一极度痛苦所挫败。”(13)Ibid.,pp. 73-74.在上述情形中,我有理由想要避免且应该设法避免这一未来的极度痛苦。但主观主义无法蕴含这个符合直觉的判断,它允许我即便在充分知情且理想慎思的情况下依然缺乏这样的欲望。
那么,主观理论为何具有这种不合情理的后果?帕菲特主要给出两个理由。第一,主观主义者无法诉诸未来的欲望。帕菲特承认,当未来的我经历极度痛苦时,我会强烈地想要摆脱这种痛苦,但主观主义者不能主张这一可预测的未来欲望现在给予我理由想要避免未来的极度痛苦。一方面,我们对当下痛苦和未来痛苦的感知具有一种态度上的差别:“尽管我知道,当我后来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时,我会具有一种强烈的不想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欲望,但我现在或许不想避免这一未来的极度痛苦”;另一方面,主观主义者“没有宣称,且鉴于他们的其他假设,他们也无法宣称,关于我们未来欲望的事实给予我们理由”(14)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74.。帕菲特的意思是,就主观理论的主张而言,理由只能由当下的欲望来提供,要么是我们实际具有的欲望,要么是我们慎思之后将会具有的欲望。第二,从根本上说,主观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合情理的后果,是因为这些理论否认我们具有对象给予的理由,因此主观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基于他们的观点,“极度痛苦的本质并不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但客观主义者可以主张“极度痛苦的本质的确给予我们这样一个理由”。(15)Ibid.,p. 81.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帕菲特构造出他所说的极度痛苦论证,可以概要地表述为:前提一,我们所有人都有理由想要避免且设法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前提二,主观主义蕴含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理由;结论,主观主义是错误的。(16)Ibid.,p. 76.
上述论证的精髓在于,绝大部分主观主义者都接受前提一,即人们有理由想要避免且设法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然而,如果主观主义是正确的,这将意味着人们没有这样的理由(前提二)。这一不合情理的后果显示,主观理论是错误的。当然,主观主义者通常并不接受这一结论,为了表明主观主义并不具有这一后果,他们一般对帕菲特给出的第一点理由持有异议,认为主观主义者可以诉诸未来的欲望(17)See David Sobel,“Parfit’s Case Against Subjectivism”,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Vol. 6,pp. 60-66.,但并未关注帕菲特的第二点理由。较之主观主义者,客观主义者似乎可以正当地宣称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但基于帕菲特的痛苦观,他无法合理地说明这一点。
二、享乐式好恶与极度痛苦的本质
痛苦论证显示,主观主义蕴含了不合情理的后果,所以它是错误的理论。显然,帕菲特想借痛苦论证表明:鉴于主观主义无法成立,我们应该转而采纳客观主义。不过,痛苦论证能否达成这一目的,不仅取决于它是否驳倒主观主义,还取决于客观主义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前提一。如果无法说明这一点,那么即便主观主义是错误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转向客观主义。鉴于此,为了支持客观主义,除驳倒主观理论外,帕菲特还需要表明其客观主义能够合理地说明前提一。通过把极度痛苦的本质归为对象给予的理由,帕菲特似乎满足了上述要求。然而,他实际上并未做到这一点。即便痛苦论证成功反驳了主观主义,它也并不由此支持帕菲特的客观理论。
为了得出上述结论,首先要介绍帕菲特对某一类感觉的看法,再阐明他的痛苦观。我们发现,尽管在帕菲特看来,极度痛苦的本质能够给予我们理由,但这一观点实际上与他的痛苦观产生了冲突。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帕菲特无法融贯地主张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下面,先考察帕菲特如何理解包括痛苦(pain)在内的这类感觉(sensations)。帕菲特认为,存在一类心理状态,虽然常常被当作欲望,但最好被归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这类心理状态就是人们对某些实际的当下感觉(actual present sensations)的享乐式好恶(hedonic likings and dislikings)。比如,有些人喜欢吃牛奶巧克力、进行艰苦的身体锻炼和洗冷水澡时的感觉,有些人则讨厌这些事物和活动。
那么,人们为什么具有这种享乐式好恶?一种常见的回答是:这些感觉本身的特征或性质给予人们理由喜爱或厌恶它们。然而,帕菲特明确拒绝了这一说法:“有时候人们声称,这些感觉的内在性质特征(intrinsic qualitative features)或它们的感受性(what they feel like)给予我们理由喜爱或厌恶它们,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感觉本身就是好的或坏的。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理由。这些喜爱或厌恶既谈不上合理,也谈不上不合理。”(18)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53.帕菲特坦言,他就比较讨厌摸天鹅绒的感觉、家蝇的嗡嗡声以及大多数顶灯令人窒息的效果。尽管这些感觉特别奇怪,但它们不是对理由的回应,我们没有理由喜爱或厌恶它们。这些感觉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们是否令人愉悦或痛苦取决于我们的好恶态度:“这些好恶使我们具有的这些感觉是令人愉悦的(pleasant)、痛苦的(painful)或是以其他方式令人不适的(unpleasant),或者说,感觉是否令人愉悦部分就在于这种好恶。”(19)Ibid.,p.53.也就是说,对某些实际的当下感觉的喜爱或厌恶并不来自这些感觉本身的内在性质,这些好恶甚至不基于任何理由。帕菲特认为,尽管这些感觉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它们是有好坏之分的、复杂的心理状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经历疼痛(in pain)时,不好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感觉(sensation),而是我们的意识状态,即意识到我们具有一种自己所讨厌的感觉。如果我们不讨厌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意识状态并不糟糕(bad)”(20)Ibid.,p. 54. 帕菲特主要在身体疼痛的意义上来理解“痛苦”和“极度痛苦”。。
可见,按照帕菲特的理解,痛苦体验(experiences)包含一种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享乐式厌恶。其中,享乐式厌恶起决定作用,因为仅当我们厌恶相应的感觉时,我们的感觉体验才是痛苦的。可以说,正是我们的厌恶使得相应的感觉具有痛苦性,也是这种厌恶把糟糕性(badness)赋予这种感觉(21)See Sharon Street,“In Defense of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Ideally Coherent Eccentrics and the Contingency of What Matters”,Philosophical Issues 19(1),2009,p. 282.。或者说,我们的厌恶构成感觉的痛苦性(22)See Ruth Chang,“Can Desires Provide Reasons for Action?”,Reason and Value:Themes from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ed. by R. Jay Wallace,Philip Pettit,Samuel Scheffler &Michael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76.。“当我们具有某种我们非常喜爱或厌恶的感觉时,我们大部分人也强烈地想要处于或不想处于这种意识状态。”(23)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54.帕菲特把我们对此类意识状态的欲望称为“元享乐式欲望”(meta-hedonic desires)(24)Ibid.,p.54.。他认为享乐式好恶不同于元享乐式欲望,并列举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比如,我们厌恶的对象是感觉,但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不具有我们所厌恶的感觉;欲望有两种满足方式,要么不再具有这种感觉,要么具有这种感觉但不再厌恶它,但厌恶却谈不上满足与否(25)Ibid.,p.54.。据帕菲特的分析,许多人混淆了享乐式好恶和元享乐式欲望,把前者当成欲望。帕菲特之所以强调二者不同,是因为享乐式好恶能够给予我们理由,欲望则不能。不过,即便享乐式好恶不是欲望,“享乐式好恶能够给予理由”这一观点依然与帕菲特的核心主张格格不入。总之,帕菲特的痛苦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痛苦感觉的内在性质并不给予我们理由厌恶它;其二,痛苦体验不仅包括感觉,还包含我们对这种感觉的享乐式厌恶。后者在整个痛苦体验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即正是这种享乐式厌恶使得我们的痛苦体验具有痛苦性。
然而,从上述痛苦观出发,帕菲特无法融贯地宣称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因为二者无法兼容。主观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合情理的后果,根本原因在于其否认我们具有对象给予的理由,所以主观主义者无法主张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这种痛苦。帕菲特宣称,由于极度痛苦的本质属于对象给予的理由,客观主义者可以诉诸极度痛苦的给予理由性(reason-givingness)。但帕菲特没有意识到,如果极度痛苦的本质属于对象给予的理由,他便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极度痛苦的本质为何能够给予我们理由。要揭示这一点,就需要详细地阐明极度痛苦的本质。
截至目前,我们只知道帕菲特把极度痛苦的本质视作对象给予的理由。除此之外,对于极度痛苦的本质,帕菲特有没有更近一步的阐述?答案是肯定的。在评论主观理论时,帕菲特说:“准确地记住具有一种强烈的疼痛是什么感觉可能很难。因为某些糟糕性(awfulness)消失了。但我们还是可以足够好地记住这类体验。根据主观主义者,我们所记住的东西并不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再次具有这样剧烈的疼痛。”(26)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82.在另一处讨论主观理论时,帕菲特更明确地表示,当他宣称主观理论蕴含了极度痛苦的本质并不给予我们任何理由去避免未来的极度痛苦时,他的意思是“当我们记住经历极度痛苦是什么感觉(what it is like to be in agony)时,我们记住的东西并不支持我们想要且设法不再处于极度痛苦之中”(27)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 437.。这些论述显示,帕菲特似乎把极度痛苦的本质理解为痛苦感觉,即痛苦的感受性(felt-quality)或现象学(phenomenology)。但前文指出,根据他的痛苦观,感觉或感受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痛苦体验之所以是痛苦的,是因为我们对痛苦感觉具有享乐式厌恶。所以,帕菲特需要说明,如果极度痛苦的本质就是痛苦感觉或感受,那么鉴于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我们为什么要宣称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它?前文提到,客观理论主张,实践理由是基于价值的。在帕菲特看来,仅当我们所做之事或设法实现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或值得实现的,我们才有理由实施相应的行动。然而,根据他的痛苦观,痛苦感觉本身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基于此,帕菲特没有理由宣称,极度痛苦的本质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它。
鉴于帕菲特的痛苦观还包含另一个维度,关于极度痛苦的本质,帕菲特的真实看法也可能是:极度痛苦的本质并不在于痛苦的感受性,而在于我们对痛苦感觉的享乐式厌恶。但这一说法同样难以成立,首先并非所有人都厌恶痛苦感受(28)See Gwen Bradford,“The Badness of Pain”,Utilitas,2020,32 (2),p. 242.,而且根据帕菲特的客观理论,我们的实践理由是对象给予的。显然,作为对象给予的理由,极度痛苦的本质应当属于痛苦本身的内在特征。如果极度痛苦的本质在于我们对痛苦感觉的享乐式厌恶,那么它绝非对象给予的理由。毫无疑问,厌恶是一种主观态度,它并不属于对象,而属于主体。因此,极度痛苦的本质要想成为对象给予的理由,它就不可能表现为我们的厌恶态度。
可见,如果极度痛苦的本质属于对象给予的理由,那么帕菲特只能在感受性意义上来理解极度痛苦。如此,他便无法解释我们为何有理由想要避免且设法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由于帕菲特无法融贯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痛苦论证决定性地反驳了主观主义,它也并不由此支持他的客观主义。
下一节将表明,如果痛苦论证成功反驳了主观主义,其范围也仅限于动机主观主义。然而,帕菲特实际上反对的是赞成态度主观主义。一旦阐明了这一点,帕菲特关于享乐式好恶的观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和赞成态度主观主义形成交集,这不仅不符合他的客观主义,还会削弱这一立场。
三、理由主观主义与态度依赖
根据帕菲特的客观理论,所有的实践理由都是与欲望对象有关的事实所提供的,欲望本身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理由。但帕菲特承认,享乐式好恶能够给予我们理由,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喜爱快乐或厌恶痛苦,“但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具有并继续具有我们非常喜爱的感觉。我们甚至具有更强的理由不想处于由于具有我们极其厌恶的感觉而带来的极度痛苦之中”,“……是我们的厌恶使得我们的意识状态是不好的,也是它们给予我们理由去设法结束我们的痛苦或令人不适的状态”(29)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p. 56,67.。在他看来,我们对快乐的喜爱给予我们理由想要拥有它,而我们对痛苦的厌恶给予我们理由想要避免它。他把此类理由称为“享乐式理由”(hedonic reasons)(30)Ibid.,p.67.。
可见,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来自我们的态度。不过,帕菲特似乎认为,由于享乐式好恶不是欲望,所以上述主张并没有削弱客观理论。他表示,有些人混淆了享乐式好恶和元享乐式欲望,所以错误地认为享乐式理由是基于元享乐式欲望的。但享乐式理由基于享乐式好恶,而非元享乐式欲望(31)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67.。换言之,在帕菲特看来,享乐式好恶给予我们享乐式理由,但由于享乐式好恶不同于欲望,所以他并没有向主观主义者靠拢。帕菲特应该是想说明,“享乐式好恶能够给予理由”这一观点和客观主义并不冲突。但情况并非如此。索贝尔在讨论痛苦论证时指出存在两种主观主义,即动机主观主义和赞成态度主观主义,痛苦论证即便成立,最多只能驳倒动机主观主义(32)See David Sobel,“Parfit’s Case Against Subjectivism”,p. 68.。然而,从帕菲特本人核心的元伦理学信条出发,他应当是在赞成态度意义上来理解主观主义的。帕菲特关于享乐式好恶能够提供理由的观点将会削弱他的客观主义立场,也会带来相应的理论效应。
前文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涉及理由的来源问题。在帕菲特看来,这两类理论之间的争论,其要义在于欲望是否构成理由的最终来源。帕菲特在广义上使用欲望一词,它指任何被驱动的状态,或者任何想要某事发生且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使之发生的状态,这种广义的欲望反映了行动者的动机状态。帕菲特之所以把主观理论可用的资源限定为欲望,与他对主观理论的理解密不可分。按照帕菲特的阐述,主观理论认为,就某个行动而言,仅当它能最好地满足我们当下充分知情的目的性欲望,或者我们在理想的慎思之后会选择去做它,我们才有理由实施该行动。这意味着理由依赖于行动者的动机。所以,索贝尓把帕菲特所批评的主观主义称为动机主观主义。
然而,帕菲特对主观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围绕规范性理由的来源问题,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歧并不局限于欲望或动机是否提供理由。更恰当的理解是,前者主张理由来自对象,而后者认为理由依赖于主体。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的主张理解为:“主观主义者认为,行动者对某个选项的赞成或反对态度决定他是否有理由做出该选择。而客观主义者认为,做出选择的理由并不取决于行动者对该选择的意动(conative)态度。”(33)Ibid.,p. 67.按照这一理解,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争论表现为:规范性理由是依赖于行动者的赞成或反对态度,还是独立于这些态度?
就帕菲特所持有的核心的元伦理学信条而言,他应当是在赞成态度意义上来理解主观主义。在《论重要之事》一书中,他孜孜以求的一个核心信条是:存在着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normative truth)。顾名思义,《论重要之事》旨在探究“何事重要”这一问题。对此,帕菲特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事情重要,仅当我们有理由关心它们。”(34)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2,p. 269.他坚信在这一意义上,有些事情的确是重要的,比如我们有理由想要什么以及我们有理由做什么,“按照最好的客观理论,我们具有某个理由这一事实是一个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35)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109.。帕菲特相信,规范性真理不仅不可还原(irreducible),而且独立于行动者的反应或态度。要理解这里所说的独立的规范性真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帕菲特所反对的元伦理学建构主义(metaethical constructivism)进行比较。
元伦理学建构主义者主张,事物是有价值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作为行动者的我们认为它们具有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并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的评价性态度(evaluative attitudes)或实践视角(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的规范性真理(36)See Sharon Street,“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Vol. 3,ed. by Russ Shafer-Landau,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207.。价值是我们评价性态度的一种构造(construction)。对应到理由,按照莎伦·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的说法,价值的给予理由地位是由我们赋予事物的(37)See Sharon Street,“What is Constructivism in Ethics and Metaethics?”,Philosophy Compass,2010,5 (5),p. 371.。以斯特里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其主要的批评对象正是帕菲特这样的规范实在论者(normative realists)。根据后者,“存在着一个行动者如何最有规范性理由去生活的事实,独立于这个行动者的评价性态度,独立于这些态度和非规范性事实所蕴含的东西”(38)Sharon Street,“In Defense of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Ideally Coherent Eccentrics and the Contingency of What Matters”,Philosophical Issues,2009,19 (1),p. 274.。虽然帕菲特拒绝规范实在论这个标签,但他并不拒斥标签之下的内容。在《论重要之事》中,帕菲特在回应斯特里特时表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具有……对象给予的、基于价值的理由,在斯特里特的意义上,我们可能成为规范实在论者,相信存在着她所说的独立于态度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我的观点在斯特里特的意义上是实在论的,因为我相信存在着一些独立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它们绝不是由我们创造的。”(39)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 261,264.对帕菲特而言,规范性真理独立于我们的态度或反应。在他那里,规范性理由的来源问题属于规范性真理的范畴,不仅独立于我们的欲望或动机,而且独立于或不依赖于我们的态度或反应。
可见,帕菲特应当在赞成态度意义上来理解主观主义。根据他的核心信条,他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主观主义。因此,他关于享乐式好恶和元享乐式欲望的区分就不再重要。即使享乐式好恶不是欲望,它们依然属于主观态度。如果享乐式好恶能够给予我们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属于依赖于态度的理由。基于此,索贝尔认为,帕菲特并不反对依赖于态度的理由(40)See David Sobel,“The Case for Stance Dependent Reasons”,Journal of Eth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2019,15 (2),p. 155.。总之,帕菲特关于享乐式好恶可以向我们提供理由的主张,已然撼动了他的客观主义立场。他无法继续坚定地主张,规范性理由全部由对象所提供。
四、结 语
在谈及主观主义时,帕菲特指出:“理由主观主义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具有主体给予的理由……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主观主义甚至都不被说成是若干观点中最好的一个,而是被表现得仿佛它是唯一可能的观点。所以,这一观点是否为真极为重要。”(41)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1,p. 65.对帕菲特而言,这种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理由构成道德的基础,理由比道德更根本,因为“道德要求和其他的规范性要求一样,只有当它们给予我们理由时才重要”(42)Ibid.,p. 7.;其二,在各种元伦理学理论的冲突中,“理由提供了决定性的战场”(43)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 2,p. 269.;其三,存在着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这些真理主要指涉及理由的真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真理,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44)Ibid.,p. 465.。这样一来,等待我们的只能是虚无主义。鉴于理由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帕菲特必须确定究竟哪种理由理论能够胜出。借助极度痛苦论证,帕菲特希望表明,主观主义蕴含了不合情理的后果,因而是错误的理论,客观主义者才是正确的。然而,按本文的分析,即使痛苦论证成功反驳了主观主义,它也并未由此确立帕菲特的客观理论。尽管帕菲特对痛苦论证寄予厚望,但这一论证并未达成他的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