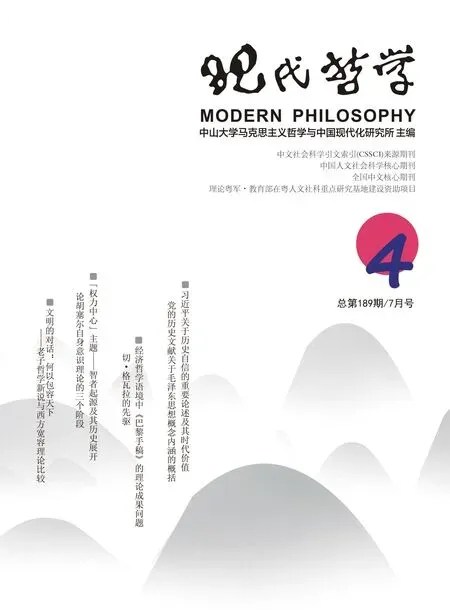儒家哲学中自我形态的探寻
——从文本分析到义理诠释
叶树勋
自我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1)本文所称儒家指先秦儒家。儒家所思的自我是伦理领域中的道德自我,其有关伦理生活和道德问题的种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自我这一基点来展开的。(2)一般印象中,自我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概念,它在西方哲学上比较显赫(尤其近代以后)。实际上,在儒家哲学里,自我也是一个颇为紧要的问题。自我概念的内涵比较复杂,在不同的场合里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儒家所思的自我是伦理领域中的道德自我,这不同于西方哲学上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原子式自我,也不同于心理学或神经科学领域所研究的自我。学界一直很重视对儒家自我观念的研究,但如何理解其义涵,大家看法各异。相比于那些事先立足于某种理论,或为了中西比较而进行化约的研究,笔者更倾向于先抛开立场、从文本出发的做法,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探寻其义涵。对此,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成中英提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方向:他们以“自”“己”“身”三词为线索,对其所涉文本进行分析,逐渐揭示儒家自我观的内涵和特点。(3)Herbert Fingarette,“The Problem of the Self in the Analect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29,No.2,1979,pp. 129-140. 中译版参见[美]芬格莱特:《〈论语〉中自我的问题》,《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43页;成中英:《儒家的自我理念——论儒家哲学中的修己与自由意志》,刘雪飞译,《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
人们得出儒家很关切自我问题的印象,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或源于对儒家心性论的重视,虽然心性问题不等同于自我问题,但此二者紧密相关;或源于对中西比较的关注,在比较的视域里自我问题在儒家的地位会越发地突显。而笔者得出这种印象,则是源于一种直观的文本现象。儒家典籍中存在大量的有关“自”“己”“身”“我”“独”的言论,这些频繁出现的语词在不少情况下都是表达自我观念的符号(4)观念是思想的基本单位,而语词则是表达观念的语言符号。同一观念可以由不同的语词进行表达。,其所在文本承载着儒家关于自我问题的深刻思考。如果我们选择从文本出发,那么这些关键词所涉的文本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
不管何种方式,哲学史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文本。方法的区别在于如何运用文本,是从文本出发不作预设,还是先有立场并为此去寻找文本,甚至是曲解文本。由于自我问题在西方哲学的显要性,人们论及儒家自我观时难免受西方影响,在研究中可能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预设,或遮蔽儒家思想的某些重要内质,或增加某些本来在儒家思想里不存在的内容。在此情况下,强调从文本出发,对议题相关的文本现象进行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可以让研究工作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便于找到理解义理问题的恰当门径。(5)曹峰主张,思想史研究中最好的方法是“无法之法”,即抛开预设、回到文本自身去。李巍强调,哲学史研究应遵循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的进路。这些见解给了笔者很大启发。笔者曾提出“哲理语文学”的方法,主张对文本进行语文学分析,为哲理之探讨提供基础。本文研究亦属此法之运用。(参见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0-288页;李巍:《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2页;叶树勋:《先秦道家“德”观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9-35页。)
如此来看,芬格莱特和成中英所用的方法便更能显示其价值。但他们的工作还存在推进和深化的需要。这不仅因为语词和文本的范围有待扩展,而且因为在分析方法上还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通过新的探讨,将会发现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形态比他们已考察的要丰富、复杂许多,并且还将看到这项研究不仅涉及如何解释自我观念,在更深层的地方还关乎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哲学。
一、语词、文本和分析路径
芬格莱特曾关注《论语》中的自我问题。他从“己”“身”两词切入,通过分析其文本认为,“己”指称自我时可能把自我当作主体(如“己欲立而立人”),也可能把自我视作他者的对象(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或者还可能把自我当作对自身起作用的行为者(如“行己也恭”“修己以敬”),最后一种具有自我省察的意味;而“身”字主要反映自我对自身起作用(如“三省吾身”“修身”),自我省察的意味更明显。从语法看,“己”的第一种情形是作主语,后两种是作宾语,包括作他人的宾语和作自己的宾语。当“己”作为自己的宾语时,语句中隐含了一个作为主语的自己。就“己”的直接意义而言,它指的不是芬氏所说的起作用的行为者,而是那个被作用的自身。“身”的用法有类似,如“修身”一言即省略了作为主语的自己,“身”指的是那个被作用的自身。
成中英以“自”“己”为线索考察孔子的自我观,认为“自”和“己”存在一定差异,“自”有自主、自动之义,彰显自我的主动性一面,“己”则主要反映自我的反思性一面;孔子的自我观包括主动参与和内向反思两个面向,但这不是指两种自我。在此基础上,他还洞察到孔子罕言“心”“性”,但其思想中的“自”和“己”分别包含着引发心智问题和人性问题的可能。成、芬两人的见解不无相通,成先生所言的主动参与一面,和芬氏所说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接近,而内向反思一面则类似于芬氏所说的自我对自身起作用。所不同者主要在于,成先生明确区分了两种面向,并且关注到孔子自我观和后世心性学说的内在关联。
两位学者的研究颇具启发性。诸种语词在表达自我观念时往往具有不同的特性,这和它们原来的语义、语法特点不无关系。由此展开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中的自我。沿此方向继续考察后,笔者发现这项工作还存在推进的需要。这不仅因为语词和文本的范围有待扩展,也因为分析的方法还有待调整。儒家学说中的自我语词比他们已做研究的更丰富,“我”与“独”也是重要符号。他们主要针对《论语》进行考察,典籍之范围也需要扩展。就如何分析来看,儒家都是在关系之中谈论自我,可以把关系作为分析的背景。这里说的关系是广义的,不限于通常所讲的伦理关系。两位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已带有这样的背景:成先生所说的主动性、芬氏所讲的“己”的前两种情形,均属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成论的另一面、芬氏所言的第三种情形,则属于自我和自身的关系。除此以外,儒家还经常谈论自我和某种特殊事物的关系,这既不属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也难以归入自我和自身的关系,此情形尚未进入两位的考察范围。
比如,孔子说的“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为仁”、《大学》的“德润身”、《中庸》的“君子之道本诸身”、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的“身服善以先之”、孟子讲的“此天之所与我者”,等等。这里讲的是自我和“仁”“礼”“善”“天”“道”“德”的关系。此情形不宜归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在探讨儒家自我观时,我们所说的他者是指和自我具有伦理交往关系的他人以及人外之物,而这些事物不在此范围内。再说,即便从广义他者(自我以外的一切存在)来看,其间也有不宜归为他者的事物,比如“仁”“德”,儒家是将其看作自我得以构成的内在之物。当然,也不能以此为由将此情形归为自我和自身的关系。“仁”“德”虽内在于自我,但它们并非直接指自我。若再考虑“礼”“天”“道”等,那就更不宜归为自我和自身的关系。
因此,为更充分地探察儒家自我观的形态,有必要补充一种新的关系视域。这不仅是为了安顿和自我有关的诸种特殊事物,更关键的是,此关系还涉及儒家自我形态的一个重要向度,蕴含着儒家对于自我的某些独特之思。另需说明的是,儒家言论里并不是每句话都只体现一种关系,并且诸种关系之间还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这些都不影响三种关系的各自存在。
从语词来看,“自”“己”“身”等词是儒家用以表达自我观念的语言符号(可将它们简称为自我语词),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和分析相关文本的线索。但需注意的是,这些语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表达自我观念,那么它们在什么时候能够表达呢?两位学者没有对此给出界定。笔者尝试提供一个方案。能够成为自我语词的符号,除了他们已关注到的三个,还包括“独”与“我”。在有关“慎其独”的研究中,“独”的符号已引起注意,而“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需要重视。此处即以“我”为例对自我语词的条件进行解说。
首先,该语词是用作类指,而不是特指说话者本人。如孔子说的“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论语·宪问》)、“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孟子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此中之“我”都是第一人称代词,特指孔子本人或孟子本人,不具有类指功能,故不属于自我语词。但在以下语句中,“我”具有类指功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所谓类指功能,是说这里的“我”可代表每一人。说话者是代表所有人进行言说,在他看来其所言之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在他身上成立,放在每一人都能成立。(6)古文中的“我”有时可指“我们”。但这里不宜理解为“我们”。此等语句强调每一“我”的意义。
语词的类指功能让它的所指具有普遍性,使它指涉抽象的自我观念成为可能。但并不是凡有此功能者即成为自我语词。这里涉及第二个条件,即该语词所在的文本乃是表达说话者关于自我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当满足这一点时,前面说的那种可能才会成为现实。比如,第1、3句,孔孟讲了一个人人皆适用的道理,但在其间自我问题并不突出;第2、4句则不然,它们反映的是孔孟对自我问题的某种思考,其中的“我”指抽象的自我观念。“我欲仁”一句强调自我作为“仁”之实践者的意义,“我固有之”一句则强调自我作为四德之拥有者的意义。由此再回看人称代词的用法,一则此中之“我”不具类指功能,二则此中所述无关哲学上的自我问题。我们只能说那些话反映了孔孟本人的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很难说它们表达了孔孟关于自我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
二、“自”“己”“身”的文本及其思想信息
本节将运用新视域考察“自”“己”“身”的文本。“自”“己”原是反身代词,但用法不尽相同,作为自我语词时存在一定差异,所在文本也表现出不同的向度。先来看“自”之言。“自”通常出现在“自V”(V指动词)的表达式中,意思是说“自己V自己”。如孔子讲的“自省”(自己省察自己)、“自讼”(自己责备自己),《大学》的“自欺”(自己欺骗自己),《中庸》的“自成”(自己成就自己),孟子说的“自暴”(自己残害自己)、“自弃”(自己放弃自己),荀子讲的“自知”(自己认识自己)、“自爱”(自己爱惜自己)。我们在理解时为简便计,可能会省略前一个“自己”,但这个“自己”依然存在,它的存在排除了其他事物让自己如何的可能。从语法看,“自”在“自V”中兼作主语和宾语,作为自我语词时则兼指起作用的自我和被作用的自身。为便于叙述,可将这两种角色不同的自我分别称为主我和宾我。(7)以此进行区分,可把语词的指谓看得更清楚。当然,这种简称会让人联想到詹姆斯(William James)关于主我和宾我的区分。詹氏从语法进行区分,以“I”为主我,以“me”为宾我,进而又论及纯粹自我和经验自我的问题。本文所称者各自对应起作用的自我(可以是对自身起作用,也可以是对他者起作用),和被作用的自身(可以是被自我作用,也可以是被他者作用)。这有点类似于“I”和“me”的区别,但内容上与纯粹自我、经验自我的问题无关。(参见[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方双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3-326页。)兼指性是“自”的一个特点,这使得其文本一般只体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8)“自”的兼指性在现代汉语的“自我”一词中还有保留,如“自我认识”是说“自己认识自己”。
“己”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一,所在文本表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如孔子说的“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孟子说的“反求诸己”(返回自身找原因)、《中庸》的“成己”(成就自己)。这里都隐含了主我,“己”指宾我。第二,体现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己”可指主我,也可指宾我。前者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后者如孔子说的“不患人之不己知”、《大学》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第三,少数情况下其话语可体现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如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9)此句亦体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自我克制自身),“己”指宾我,主我被隐含。如前所述,并不是每句话都只体现一种关系。这里关注的是“己”和“礼”“仁”的关系。“为仁由己”。以上为“己”之言的三种情形,比起“自”,其所涉的思想信息更丰富。需注意的是,“己”的第一种情形和“自”有所类似,但细究之又有不同。“己”不具有兼指性,当它指宾我时只能指宾我,正因如此,主语才会出现不同的可能(或是隐含的主我,或是他者)。而“自”则兼指主我和宾我,且首先指主我。因此,“V己”虽然也存在主我被隐含的情况,但它和“自V”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前者强调宾我,后者更体现主我。比如,“成己”是说自己成就自己(而不是成就他者),而“自成”是说自己(而不是靠他者)成就自己。前者强调自我也是应该被成就的对象,后者则着重体现在成就自身过程中自我的主动性和自发性。(10)“自成”和“成己”均见于《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己”强调被成的是“己”,和“成物”相对。“自成”是说靠自己来成就自己,与“自道”相应。“道自道也”相当于说“道者自导也”,意思是“道”要靠人自觉地以之为向导。
“身”是名词,原指身体。当它作为自我语词时,所在文本涉及自我的三种情形。第一,最常见的是自我和自身的关系,如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每日从三个方面反省自身)、《大学》的“修身”(修养自身)、《中庸》的“反求诸其身”(返回自身找原因)、“诚身有道”(让自身依循道而做到诚)、孟子讲的“反身而诚”(返回自身而做到诚),等等。在此,“身”意谓自身,指涉宾我,主我在句中被隐含。第二,体现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第三,反映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如《大学》的“富润屋,德润身”、《中庸》的“君子之道本诸身”、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的“身服善以先之”,这里涉及的是自我和“德”“道”“善”诸物事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身”作为自我语词时各有特点,所在文本的思想向度也不尽相同。“自”的兼指性让其所在文本只体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但同样是反身代词的“己”在用法上则比较灵活,这让其言论可涉及更多情形。“身”之言也关乎多种情形,但它又有独特之处。此词往往含有身心合一之意味,相比于“自”“己”,更体现自我的身体维度。比如,“修身”包含修养身体和修养心灵的双重意味,又如“德润身”中,“德”之于身、心都有滋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气象。
由此来看,芬氏关于“己”“身”之言的结论虽不够全面,但他关注到“己”之言的两种主要情形,同时揭示出“身”之论的重点。成先生从“自”“己”之言切入,洞察到自我的两个面向,这确实是高明之见。但他没有从提供明细的论证。前面关于“自V”和“V己”的考辨,即是论证上的补充。另需注意的是,“自”“己”和两个面向的对应也不能绝对化,比如“自省”“自讼”也能体现自我的反思性,而“己欲立则立人”也在反映自我的主动性。另外,两位学者主要是关心语词及其文本各自的特点,实际上它们也存在共性,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三、“独”“我”之文本及其思想信息
“独”与“我”的文本不在两位学者的考察之列。“独”之文本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已引起注意,但其间的特性还有待再探察。至于“我”,虽然和它有关的某些文本在心性论等领域的研究中经常被论及(如孟子说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但在自我问题的研究中,“我”的文本还未得到足够关注。
“独”作为自我语词集中见于“慎其独”之论: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
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子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礼器》)
“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郭店楚简《五行》)(11)此段亦见于马王堆帛书《五行》,文字略有差异。
君子至德,嘿(默)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荀子·不苟》)
“慎其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字面上看,这是说独处时要谨慎。但正如学者已指出的,此所谓“独”其实指向自我。(12)参见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320页;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48-249页;陈立胜:《“慎独”“自反”与“目光”——儒家修身学中的自我反省向度》,《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梁涛:《〈大学〉“诚意慎独”章新解》,《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在指自我时它还带上原来的独处、孤独之义,“慎其独”是说谨慎地对待独处时的自我。其类似用法也见于庄子的“见独”之说(《庄子·大宗师》),这是指发现独立真实的自我。“慎其独”之论只体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独”指宾我,主我被隐含。其语境中没有出现他者,并且恰恰要排除他者,这是“独”之语义所决定的。相比于“自”“己”“身”,“独”更能彰显自我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指与他者彻底无涉,他者只是暂时隐退,所谓独立性只是相对而言。儒家的一个理念是,当自我独处的时候,环境的约束力会降低,如果这时候自己能做好,那么不“独”的时候自然就更能做好。在某种意义上,“独”时之“慎”是为了给“不独”亦即交往提供修养的基础。《五行》篇说“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所谓“为一”正是强调“独”和不“独”之时其言行修养能够如一。
前文以“我”为例讨论了自我语词的成立条件。现把自我之“我”的主要言论分为三类:
(1)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郭店楚简《语丛三》)
思无疆,思无期,思无邪,思无不由我者。(郭店楚简《语丛三》)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
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荀子·天论》)
(2)自我和自身的关系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
(3)“我”指负面的自我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总体来看,“我”与“独”有所类似,语境中他者的在场性不强,自我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13)“我”的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在自我和他者的交往中得到实践。只是“我”的言论不像“自”“己”“身”之言那样,他者的在场性比较显明。“独”的独立性源于它的语义,而“我”的独立性则应该和它原来作为代词的特点有关。“我”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时,比起同类的“吾”“予”“余”等代词,更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对立。(14)如《论语·八佾》:“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孟子·公孙丑上》:“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尽心下》:“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这里的“我”与“尔”或“彼”相对而言,表现出较明显的对立性。当“我”成为自我语词时,这种特点一定程度上被带了进来。进而察之,“我”比起“独”又有不同之处:一则,“我”可指负面之自我,如第3类,“我”是指孔孟所反对的私我或小我;二则,“我”之言中最常见的情形是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而此关系在“独”之言里并无出现;最后,“独”只能指宾我,体现自我的反思性,而“我”多数作为主我出现,更彰显自我的主动性。(15)在“我”之言里,“求在我者”之“我”指宾我(隐含了作为“求”之发出者的主我),其他皆指主我。诸如“善日过我”“思无不由我”“凡有四端于我者”“万物皆备于我”“此天之与我者”,“我”在语句中虽然作宾语,但它依然指主我,这里不存在对自我起作用的自我或他者。若将语序调整,则可清楚看到此点,如“万物皆备于我”是说“我备有万物”。当然,原来的语气有所不同,它强调“万物”在“我”的完备性,调整后此意味变弱。
在先秦时期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予”“余”,它们在儒家典籍里都有出现。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我”,其余三者似乎都没有成为自我语词。以下几处可能比较特别: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第1句中,“予”指孔子本人。“天生德于予”反映的是孔子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他关于自我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当然,此言的内涵很重要,它是《中庸》所论“天命之谓性”的一个渊源。孔子就本人而论,《中庸》则把德性源于“天”此情况推扩到所有人。第2句中,“身”作为自我语词出现,但“吾”不是,它指曾子本人。芬格莱特把“吾身”解释为“我的自身”(my self),(16)Herbert Fingarette,“The Problem of the Self in the Analects”,p.132.颇为确当。此处的“身”具有普遍性(每一人都有自己的“身”),而“吾身”则指曾子所要表明的他的“身”。第3句会让人联想到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是,孔子此论具有一般性,而子贡之言则在表明他自己的心志。孔子后面回答的“非尔所及也”,也说明子贡之言只是就他本人而论。在子贡之言中,不仅“吾”,包括“我”,都不具有成为自我语词所需的普遍性。第4句的“吾”是类指用法,该言语并非反映孟子关于自我问题的看法,其情形类似于“鱼,我所欲也”。如此看来,在几个第一人称代词中,只有“我”比较明显地成为自我语词。前面曾言,“我”更强调彼我对立,更彰显行为者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儒家在选择语言符号以表达其自我观念时,“我”的这些特点也许会影响到他们的倾向。(17)由此顺带讨论下庄子言论中著名的“吾丧我”。通常认为这里的“吾”“我”俱有深义,代表自我的两种形态。笔者认为,此所谓“我”具有自我义,指庄子所否定的不良的自我;但“吾”不具有自我义,它是第一人称代词,指说话者(南郭子綦)本人。可借鉴曾子之言来分析。曾子之言的结构是吾-日三省-吾身。“吾丧我”的结构是吾-丧-我,可理解为吾-丧-吾中之我。“身”和“我”都是抽象概念,但“吾”不是。进言之,庄子此论确实含蕴关于两种自我的思考,“丧我”之后即生成一种新的自我形态,但此形态不是“吾”之所指。若要在其学说中找一个词来代表此形态,那么可以是“见独”之“独”。另外,庄子此论或沿自老子的“吾无身”思想。《老子》第13章:“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所谓“身”类似于“吾丧我”之“我”,指负面的自我。“吾无身”之“吾”也不具有自我义,但与“吾丧我”之“吾”不尽相同。后者特指说话者,而前者有类指功能。
四、自我形态的三种向度及其联系
在儒家思想中,自我作为道德行为者的存在和活动离不开他者的参与。王正曾强调,儒家的道德是人伦道德,必须在有对象的情景中才能真正完成;没有与他人相关联的人伦社会,就没有道德实践的可能。(18)王正:《先秦儒家道德哲学十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年,第119页。王正强调人伦社会,强调自我和他人的关联,其实还要扩展。儒家思想里自我所面向的他者还包括人以外的事物。根本上而言,儒家所思的自我是道德自我,此自我总与他者共在,离开了他者,自我就失去了呈现其意义的场所。但通过前论又可看到,在不同的语境里,他者的在场性有强弱不同的区别。总体上看,在“自”“己”“身”之言里,他者的在场性较强;而在“独”“我”之论中,他者变得有所隐退。这种区别不仅是语言上的现象,它涉及儒家关于自我的不同的思考方向。前者是把自我放在伦理关系网络中思考其种种表现,后者则是把自我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求索,它将导向更深层的自我之思。
“自”“己”“身”之文本都有涉及自我和自身的关系,自我反省是其间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来看,自我反省是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情,但实际上也涉及他者,且他者的在场性并不弱。所谓自我反省,是说自我在和他者交往的过程中要时时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比如,孔子说的“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是指在交往中如果发现自己有过错则要进行自我批评。又如,曾子说的“三省吾身”,其内容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些都是就己他关系而言。再如,孟子讲的“自反”和“反求诸己”,诸如“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都是说交往过程中如果出了问题,要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之,上述诸文本既体现自我和自身的关系,也涉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可以说,后者是促使自我进行反省的必要环境,被反省的自我是一个交往中的自我,是一个在伦理关系网络中不断展开的自我。
在“我”的文本里,存在一处可能会让人视同于自我反省的情形,此即孟子所讲的“求在我者”(引文见第三节)。它看起来与孟子讲的“反求诸己”同义,但实际上二者存在紧要差别。“反求诸己”之义,前文已述。所谓“求在我者”,是说追求那些潜在于自我之中的事物。(19)既然“在我”,为何还要去“求”?此等事物潜在于“我”,所谓“求”,是说反思到它们并在行动中实现出来。与“求在我者”相对的“求在外者”,是指追求那些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事物,虽然“求之有道”(按一定的方法去追求它),但能否得到,是自我无法掌控的,故而谓之“命”。在孟子看来,世上有些事情是自我能够做主的,有些事情则不在自我的掌控范围内。可自主的事情之所以可自主,是因为它们根源于“在我者”,根源于那种确实属于“我”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仅是可自主之事成为可能的依据,它在深层意义上也是“我”之所以是“我”的根据。无此“在我者”,“我”便无法成为“我”。联系前面说的自我反省来看,“求在我者”可归为自我反省的一种表现,但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自我反省。后者指省察自我在交往时的所作所为,而前者是指求索那些真正属于“我”的东西,探寻“我”之所以是“我”的根据。如此说来,儒家的自我反思理念应作两层观:一是以“反求诸己”为代表的对自我之所作所为的具体反思,二是以“求在我者”为代表的对自我之所以成为自我的抽象反思,后者代表着儒家自我形态的更深层次。(20)陈立胜注意到自我反省的多样性,并把它总结为四种类型,分别是针对一生经历、一天行为、心灵生活、当下一念的反省。这启发笔者去关注自我反省的不同类型,但笔者的理解角度不同。另外,“反省”一词在日常使用中多被用来指省察自我的不良作为,故用含义更广的“反思”来统摄两种类型。自我的抽象反思体现在儒家言论上,以孟子所讲的“求在我者”为典型,故以之为代表进行讨论。荀子也言及“在我者”(引文见第三节),其论亦含抽象反思之义,但所言不如孟子明确。(参见陈立胜:《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接下来讨论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儒家这方面的思考主要通过“我”之文本来表达,并且“我”之文本中最常见的正是此情形。当然,前文已指出,“己”“身”之言在少数情况下也涉及于此。结合来看,可将所涉的特殊事物整体上分作三类。第一,道义原则,如“克己复礼”的“礼”、“君子之道本诸身”的“道”、“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身服善以先之”的“善”。第二,自我的内在物,如“我欲仁”“为仁由己”的“仁”(21)孔子的这两句话似乎意味着“仁”是外在的对象,有待“我”去求、“己”去“为”。实际上,“仁”是自我所内有的德性。此两言是为了强调自我的行动对于实现仁德的意义。、“德润身”的“德”、“思无不由我”的“思”、“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凡有四端于我者”的“四端”(仁义礼智于心显现之端倪)、“万物皆备于我”的“万物”(22)对于孟子此论,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庄子所说的“万物与我为一”,从而把“万物”理解为天地万物。实际上,孟子所说的“万物”是指“我”之所以成为道德自我的一切根据。“万物皆备于我”是说,成为道德自我的一切根据在“我”皆是完备。(参见叶树勋:《道德自我与行动意志——孟子哲学中“万物皆备于我”的义旨新探》,《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的“志意”“德行”“知虑”。(23)直接来说,荀子所言的“在我者”是指“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这些取决于自我的事情,进一步来看,则是指“志意”“德行”“知虑”这些存在于自我的事物。“德行”之“行”非谓内在之物,但此所言之重点其实在“德”。孟子亦讲“在我者”,且明确强调“求”,强调反思而“得”之。但在该言语中孟子没有对“在我者”是什么给出说明。联系其他地方来看,他关于“我”固有“四德”、备有“万物”、源于“天之所与”的言论,都和“在我者”存有联系,在深层意义上它们构成了对“在我者”的解答。第三,形上本根,如“此天之所与我者”的“天”。
第一种事物指示自我在行动中所需遵循的原则,第二种涉及自我的内部构造,第三种则指向自我的形上之源。进一步看,后两种具有统一性,都关乎自我何以成为自我的问题:内在之物从现实生活层面进行回答,而本根之物从形上层面确立起自我的根基。在儒家思想中,自我的内在物以“德”为核心,即便是理论差异很大的孟子和荀子,在此点上亦无分殊(只不过他们对于“德”是否为先天固有看法不同)。这也是儒家所思之自我是为道德自我的根本原因。由此而言,自我何以成为自我的问题,更具体来说,乃是自我何以成为道德自我的问题,或者说道德自我何以成立的问题。前面讲过,“求在我者”所代表的抽象反思乃是指对自我之所以成为自我的求索。联系起来看,所要“求”的正是道德自我得以成立的依据。
通过前论,还可看到儒家哲学中“天”“道”“德”这些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这几个概念在儒家研究中是绕不开的紧要议题,但它们的关系又每每纠缠不清。以自我为基点,可以将其关系看得更清楚一些。“天”作为形上本根,是自我的根源(“此天之所与我者”);“天所与我者”的主要内容即是“德”;而“道”作为伦理原则,乃是源于自我而存在(“君子之道本诸身”),再具体点来说,乃是源于自所固有的“德”。由此可探察到“天-德-道”的内在逻辑。《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与“德”同谓。此语可谓是“天-德-道”逻辑的集中表述。以上所论以思孟一系的文本为据,论至荀子学说,则情况有所不同。其思想中“德”与“道”的逻辑先后是倒过来的。人性恶的判定决定了“德”不是先天固存于己的,它的形成有待“礼义”规则(即“道”)的“化性起伪”。并且,荀子所论的“天”是自然之“天”,他没有像思孟一系那样,把“天”推到形而上的层次、以之为自我乃至万物的依据。
在前两节基础上,这里对诸文本的思想信息作了进一步考察。现在让我们对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形态作一总结。自我所处的不同关系反映着儒家对于自我的不同的关注点,它们不是截然分开,而是错综复杂,彼此间具有内在联系。如果说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体现自我的交往向度,那么自我和自身的关系则属于自我的反身向度。(24)交往向度和反身向度都包含知与行两个层次。和他者的交往包括认识他者和成就他者,反身向度也包括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前面所讨论的自我反思的两个类型,都属于认识自我的领域。在自我和特殊事物的关系中,第一种事物作为塑造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规范,根本上来说属于自我的交往向度;第二、三种则关乎自我的内部构造和形上根源,它们都和自我何以成为道德自我这一前提性问题有关,可称之为自我的构成向度(此所言构成是广义的,包含形上之源)。此向度是交往实践成为可能的依据,后者是内在之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开展。
由此回视自我反思的两个类型,可知它们分别关联着交往向度和构成向度:具体反思是指对交往中之自我的省察;抽象反思乃是指对道德自我得以成立之依据的求索,所待求索之依据即是构成向度所涉之内容。总而察之,这三个向度在各自有别的同时又错综交会,共同交织成作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枢纽的道德自我。儒家伦理思想的不同方面,正依托于这一聚集多种向度的道德自我而得以展开。如果要在儒家的这种思想脉络中寻找一个出发点,那么它应该是自我的抽象反思,而此等反思所指向的“道德自我何以成立”问题,则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源问题。(25)“基源问题”此提法源自劳思光。他认为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在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此等问题可称为基源问题。(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儒家道德哲学的起点是什么?其基源问题是什么?不同的视角下会得出不同的看法。笔者之所以有以上论断,除了已论及的原因,也与杨泽波的启发密切相关。杨先生提出,儒家承认人具有内觉的能力,通过内觉我可以觉知到我在思考“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这个问题,因此在儒家的生生伦理学中只有“内觉”才能成为可靠的逻辑起点。(26)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4页。本文所称的抽象反思与杨先生所言之内觉有相似性,但抽象反思所觉知到的问题不同于杨先生所论者。如前所述,自我的抽象反思体现在儒家言论上,以孟子所讲的“求在我者”为典型。所要“求”的,所要反思的,乃是确实在“我”之物,而此物是“我”之所以成为道德自我的内在依据。由此来看,抽象反思所觉知到的问题是“我凭什么可以成就道德”,或者说“我成为道德自我如何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自我的抽象反思成为儒家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而“我成为道德自我如何可能”问题则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源问题。
五、对“关系性自我”与儒家伦理类型问题的回应
前文已对文本现象进行分析,并从中探寻到儒家哲学中有关自我问题的重要信息。接下来,笔者将据此对学界的两种常见观点做些回应。在当前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儒家所思的自我是一种“关系性自我”,此自我通过伦理关系中的角色和身份获得存在,与西方的“个体性自我”形成鲜明比照。(27)此所谓“关系”不同于本文用于分析自我文本的“关系”。它指的是自我和他者的伦理关系,相当于本文所说的交往向度中的那种关系。“关系性自我”的观点很常见,较典型的研究参见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4页;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增订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Henry Rosemont Jr.,Roger T. Ames,Confucian Role Ethics:A Mor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6,pp. 33-58;[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孟巍隆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15-128页。有学者据此进一步得出儒家伦理思想是“角色伦理学”的结论。(28)这是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所主张,见前引二人论著。其他以“关系性自我”进行定位的学者,也关注自我作为伦理角色的表现,但没有像安、罗那样明确提出“角色伦理学”。这类观点颇能反映儒家思想在某方面的特色,但在一种过于强调比照的视域里,它容易淡化那些更深层的实质内容。对此,廖晓炜提出了商榷意见:儒家固然突出关系、角色的重要性,但并未消解自我的自主性与个体性,以角色伦理学界定儒家伦理学,是基于对儒家自我的片面认识。(29)廖晓炜:《〈孟子〉中的自我观——兼及儒家伦理学的定位问题》,《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7期。在大方向上,笔者赞同廖先生的见解。笔者更关心的是,无论是角色伦理学,还是作为其依据的、同时被更多学者所主张的关系性自我,都把注意力放在儒家自我的交往向度,而忽视了作为自我存在之基础的构成向度。这类研究洞察到儒家自我之“流”(自我在各种伦理关系的表现)的特质,但对于儒家自我之“源”(自我之为自我的内在实质)则未免失察。另外,这类研究也注意到儒家关于自我反省的思想,但其所关注者是那种被本文称为具体反思的情形,这种反思恰恰是基于伦理关系网络来展开的,如此,得出关系性自我的看法就不足为奇。(30)学者们研究自我反省观念时所依文本是有关“自”“己”“身”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基本都是体现具体反思的。芬格莱特虽然注重文本分析,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是关系性自我,这与他所关注的文本是“己”“身”之言有关。如果注意到“我”“独”之言,那么就有可能探知自我形态的更丰富的向度。由此也说明,对文本的观照程度直接影响到义理上所作判断的准确程度。
廖先生用自主性和个体性来指示角色伦理学所忽视的方面。其所言个体性,自然不是指原子式或个人主义之自我的属性,但笔者依然认为此论有待商榷。角色伦理学,包括关系性自我的定位,根本上是消解了儒家自我形态中的构成向度。此向度所涉内容是自我之所以是自我的内在依据,对此可用“自身性”来概括。(31)海德格尔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曾谈过“自身性”。在海氏哲学中,自身性以及更深层的本己性是自身得以成为此在之本现的依据。利科对自身性的讨论源于自我同一性问题,他将同一性区分为相同性和自身性;此外,他强调自身性和他者性的辩证关系,即自身在具有自身性的同时必然包含他者性。相较于二人所论,儒家关于自我之“自身性”的思想在进路及内涵上皆有不同,但就自我之为自我的固有依据此点而言,其间不无相通。从利科观点来看,“关系性自我”之观点可说是只关注到自我的他者性,而忽视了自我的自身性。(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38-340页;[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9-206、461-518页。)儒家思考自我之构成,核心在于求索这种“自身性”。
儒家思想中自我的道德属性决定着,对其自我观的探讨根本上是对其道德哲学的研究,从关系性自我导出角色伦理学就是一个说明。角色伦理学的提出,源于学界多年以来关于儒家伦理思想属何种类型的论争。这是一个更广泛同时也更复杂的问题。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思想到底是美德伦理学还是道义论。照目前形势来看,美德伦理的定位越发成为主流。(32)以美德伦理定位儒家的学者比较多,陈继红的《从词源正义看儒家伦理形态论争》对此有简要回顾。近期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黄勇、唐文明等人。道义论的定位主要是李明辉的主张。另外,陈来、刘余莉、陈继红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兼含美德伦理学和道义论的内容。(参见陈继红:《从词源正义看儒家伦理形态论争——以德性、美德、德行三个概念为核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黄勇:《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唐文明:《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1-137页;唐文明:《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文史哲》2020年第5期;李明辉:《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刘余莉:《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陈继红:《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在如何判断其类型的问题上,唐文明和黄勇都强调,关键是看美德和规则(或原则)在儒家思想里何者优先。进而他们认为,儒家思想里美德优先于规则,要基于美德才能理解规则,因此儒家伦理思想是美德伦理学。(33)两位学者之论断还包括其他依据,但他们强调这一条是美德伦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参见前引唐文明著作及其论文,黄勇所著《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的第5-9页。)对于类型之判断,两位学者提出较有实质性的标准,倘非如此,就容易得出儒家思想既是美德伦理学又是道义论的结论,因为美德和原则在儒家思想里都很重要。
在笔者看来,如果回归儒家自身的话语,那么两位学者提出的判断方法可归结为看“德”与“道”之间何者优先。在儒家话语里,最能代表美德的符号是“德”,而最能体现伦理原则的概念是“道”。以二者关系为线索,能够使我们的考察更加集约。依前文所论,在思孟一系“德”确实优先于“道”,“道”的被理解要以“德”为前提,据此而言,思孟一系属美德伦理学。不过,这种关系在孔子思想里没那么明确。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论以“道”为原则,以“德”为德性。然而,我们难以看出“德”“道”之间究竟何者优先(语序不代表思想逻辑)。孔子还讲过“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但如前所论,此言不具普遍性。作为《中庸》所论“天命之谓性”的思想渊源,它或许可作为认为孔子思想具有美德伦理之倾向的一个依据。进而来看荀子,情况更加复杂。如前所述,在其思想中“道”优先于“德”,“德”不是先天固有的,它的形成有待“礼义”规则(即“道”)的“化性起伪”。以此来看,荀子伦理思想似乎更接近道义论。(34)黄勇还将美德伦理的视域延伸到道家,认为《庄子》所提出的规范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根据他在研讨儒家伦理时提出的标准来看,其实很难得出庄子思想属美德伦理的结论,甚至可以说庄子以及老子的伦理思想都更像是一种道义论。类似上述,我们也可回到道家自身的话语,以“德”“道”之关系进行考察。道家思想中是“道”优先于“德”,而不是反过来。“道家”的称谓已提示“道”的优先性,当然这还是笼统的证据。道家文本中有直接依据,如《老子》第21章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又如《庄子·天地》的“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参见黄勇:《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庄子〉中的道家美德伦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当然,这不代表笔者主张思孟一系和荀子各属美德伦理学和道义论。质言之,美德伦理学或道义论的定位,都是以西方伦理学类型为标准考察儒家思想。如同王楷指出的,这样的进路之于儒家思想,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35)王楷在其著作中对美德伦理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的研究进路有专门论析。(参见王楷:《天生人成——荀子工夫论的旨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4页。)在根本上,笔者并不打算在两种类型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里是想说,两位学者提出的判断方法可归结为看“德”“道”之间何者优先,进而可见先秦儒家中只有思孟一系能符合美德伦理学的标准,孔子的情况并不明朗,至于荀子则与美德伦理存在张力。照此来看,即便认为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这一结论也是局部成立的。王楷所言之得失,由此可见一斑。
儒家伦理思想类型的论争,直接来看是关于儒家伦理思想是什么的争议,但最后落实到结果,其实是研究进路的区别。就此来讲,笔者主张以自我问题为进路,对儒家伦理思想展开研究。前面可看到,三个向度共同交织而成的道德自我,乃是儒家开展其伦理道德思考之枢纽。立足于这一枢纽,可以让儒家伦理思想的不同方面及其机理脉络获得更充分的观照。这不是说笔者要提出一种“自我伦理学”。笔者关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研究,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儒家伦理思想是什么。
当问题从“是什么”转向“如何研究”时,可看到自我问题的进路和美德伦理的进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相比于道义论而言。美德伦理学和道义论之间还存在一种区别,即前者更关注行为者,而后者更重视行为。自我问题的进路虽然也关注行为(自我通过道德行动得以表现),但其基点在于行为者,由此来看,它和美德进路显得接近。另外,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乃是以“德”为核心得以构成的,这也是它作为道德自我的根本原因。这使两种进路显示出相似性。进一步看,自我问题的进路比起美德进路存在很大差异,它具有更强的统摄性,更能充分反映儒家道德哲学的内质。首先,作为各自聚焦的核心观念,“自我”的观念就比“美德”更周延。儒家思想中的自我是身心统一的道德自我。美德属心灵层面,而在此之外,身体也是儒家很重视的要素。关注身体维度,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特色。就心灵层面而言,儒家的思想也很丰富,在关心美德的同时还重视情感。当然,美德伦理学内部包括不同的子类型,比如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相对而言,后者更能体现儒家思想中情感的意义和地位,但它依然难以含纳前面说的身体维度。
以上就各自聚焦的核心观念来看,进而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两种进路的差异。从儒家诸子谱系看,不论是美德伦理不明朗的孔子,还是和美德伦理可能存在张力的荀子,都可以在自我问题的视域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观照。在关切自我、据之展开道德思考这一基本立场上,儒家诸子并无分殊。虽然就自我的构成问题他们的看法不同(尤其是思孟一系和荀子),这导致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思想出现差异,但这些都不影响自我问题在他们学说中作为枢纽的地位。横向观之,从儒家学理的内在构造看,自我形态中错综交会的三种向度,正能体现儒家道德哲学所涉的不同领域及其内在关系。总之,无论是从核心观念来看,还是从大局上的诸子谱系和学理构造来观察,比起目前常被采用的美德伦理进路,自我问题的进路更有可能充分呈现儒家道德哲学的机理脉络。
六、综论:兼谈作为方法的“言意之辨”
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来呈现过往的哲学思想,是哲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关于儒家自我观念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并且,面对这种容易受外部理论影响而产生主观先见的议题,从文本出发,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显得尤为紧要。沿着成中英和芬格莱特所提示的方向,本文梳理了先秦儒家典籍中与自我问题有关的文本现象,这既是为了探寻思想信息,也希望可以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材料依据和语义基础。尤其是“我”的文本,目前还没引起应有的关注,而儒家关于自我的某些紧要思考恰恰是通过这些言论来传达的。人们对儒家自我观中某些重要内容的忽视,和对“我”之文本的不够注意密切相关。
在对文本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可探寻到理解儒家自我形态的门径,从中获得基本的思想信息。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形态整体上包括构成性、交往性和反身性三种向度,此三者在各自有别的同时又错综交会,共同交织成作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枢纽的道德自我。儒家伦理思想的不同方面,正依托于这一聚集多种向度的道德自我而得以展开。据此,可以对目前学界常见的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回应。“关系性自我”的定位颇能突显儒家思想的某方面特色,但它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自我之“流”,对于自我之“源”则未免失察。伦理类型之论争的背后,其实是研究进路之别。比起目前常被采用的美德伦理进路,自我问题的进路具有更强的统摄性,更有可能充分呈现儒家道德哲学的机理。在一种多向而又集约的义理境域里,它可以更丰富地释放儒家道德哲学的意义。
思想义理和作为其语言载体的文本之间,如果借用魏晋玄学的话来说,即是“意”和“言”的关系。要探寻哲理之“意”,就文本之“言”进行分析是基本的路径,但这不代表“言”的分析就直接等同于“意”的追寻。“言”是“意”的载体,但“言”不是“意”,且“言”的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本身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性。(36)且不论此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的局限性,就本文的研究来看,其局限性便包括所考之文本只是儒家言论的某些部分,所探寻到的思想信息也仅涉及儒家学理的某些侧面。
正因为意识到“言”的有限性,王弼提出“得意忘言”的著名命题,认为要领会“意”则需超越“言”(“忘”指摆脱其限制)。耐人寻味的是,王弼在讲“忘言”之前,首先强调“用言”,强调需要通过“言”来追寻“意”。在他看来,“忘言”有个前提——得承认“言”作为“意”之载体的价值,得意识到“言”是领会“意”的必要工具。(37)在对“忘言”的聚焦中此层意思容易被忽视。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言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王弼还讲到“言”“意”之间的“象”,这和他提出此论时的一个背景(如何看待《周易》中的“象”)有关。我们这里不讨论“象”,就“言意之辨”来看,王弼其实首先强调了“言”的价值和作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表面上看,这和“忘言”有点矛盾,其实王弼正是洞察到“言”作为“意”之载体的“必要而有限”的特点:因为必要,所以要“用言”;因为“有限”,所以要“忘言”。“用而忘之”才是“得意忘言”论的要害。
论至今天的哲学史研究,这何尝不是在提示一种方法呢?“用言”是前提,是哲学史研究的首要工作,其基本路径便是对议题相关的文本进行系统分析,从中寻获思想义理上的信息。所谓“忘言”则提醒我们,目标在于“意”,“用言”过程中不能本末倒置而受限于“言”。(38)“用言”作为方法不限于文本分析,但这是必要的路径。论至作为方法的“忘言”,此间举个例子以稍作解说。前文讲到,孟子关于“我”固有“四德”、备有“万物”、源于“天之所与”的言论,在深层意义上构成对“在我者”的解答。实际上,孟子并没有明言这些话是在解说“在我者”。上述诸文本乃散见于《孟子》书中。但立足于孟子哲学之整体,我们可以推测这些话都和“在我者”存有联系,即便这种联系并无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在这个例子里,所谓“用言”和“忘言”指的是要充分利用文本所提供的信息,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此,同时还要去寻求文本之间可能隐含的某些思想脉络。另外,“忘言”经常被理解为追求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此等情况就不在可言范围内(前面说的“忘言”是在可言范围内的)。正如维特根斯坦说的:“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清楚地加以言说;而对于不可谈论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既然不可言,那就只好不言了。([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面向一种哲理,总有许多的“意”有待探寻和领会。“言”不是“意”,“言”的分析也不直接等同于“意”的领会,但这些都不代表可以一开始就越过“言”,也不代表可以根据自己先行设定的“意”去裁剪“言”。不管怎么“忘言”,都需要从“用言”出发,“忘”得好不好,其实取决于“用”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