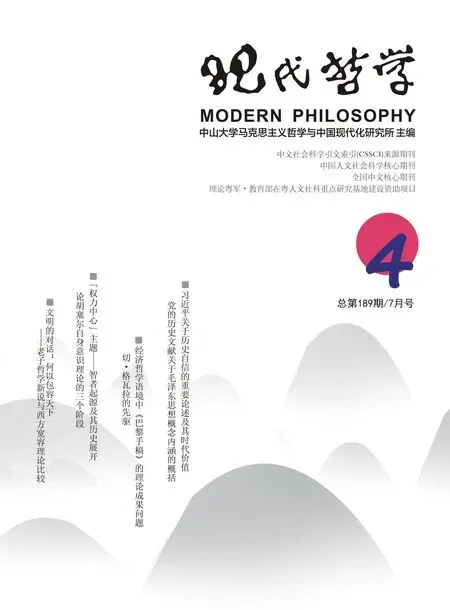何以报君恩
——《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李 曈
政教关系一直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议题。关于宋代禅宗与世俗权力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虽已十分丰富,但尚有不少未发之覆:以往研究多注重佛教政策、具体事件及具体人物等问题,侧重于历史层面的钩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宗教书写的隐喻特性,对禅宗内部关于政教关系的表达关注不够,未能从政教关系想象这一方面进一步揭示禅宗融入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就禅宗内部对宗教关系的想象,北宋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建中靖国续灯录》与《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以下分别简称为《续灯录》《传灯录》《广灯录》《普灯录》)并称为“宋代四灯”,它成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由云门宗僧人惟白所作,经驸马张敦礼引荐,由宋徽宗赐序并准许入藏流通。在《续灯录》中,惟白描绘了一幅和谐一致的政教关系图景,使禅宗作为一种统治术融入宋代的政治框架。分析这种政教关系想象的特点,并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其成因及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机制。
一、《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惟白在《续灯录》中描绘的政教关系图景由三方面构成,即施恩的皇帝、作为权力中介的臣子、积极“报君恩”的佛教僧人,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和谐一致的有机体。需要说明的是,因灯录文体及禅宗语言的特殊性质,《续灯录》中相关的表达大多出自其他禅师的法语,甚至来自弟子的发问,但由于这些语句经过惟白的拣选,故可说它们亦体现了惟白的政教观。
在这一三重结构中,首先,作为施恩者的皇帝是最为核心的,只有皇帝尊重佛教、运用世俗权力推动佛教在此世的传播,正法方可久住。正如佛陀德逊禅师言:“恢张祖席,创立丛林,岂一僧之能耳!必假国王大檀越与之护助,佛日乃可光扬。”(1)③⑥ [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第151页,第377页,第345、254、255页。《续灯录》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宋代皇帝对佛教的护持:“如昔仁宗皇帝,在宥四十余年,深穷禅理,洞了渊源。每万机之暇,常召大觉禅师怀琏、圆明禅师道隆于后苑升堂,交相问难,唱和偈颂;敷演宗乘,流布迨今,禅林取则。又元丰初年,神宗皇帝为求圣嗣,乃革相蓝律院,分为两禅,一曰惠林,一曰智海。召南方圆照禅师宗本、正觉禅师本逸领徒住持,开堂说法。”(2)⑦ [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下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602页,第510、511页,第502页,第463页。大觉怀琏为云门宗著名禅师,《续灯录》载其年过不惑,声誉便上达天听,奉诏住持净因禅院后,三次入禁中说法,仁宗对他尤为赞赏,赐号“大觉禅师”③。这是禅僧第一次入主汴京寺院。圆明道隆指华严道隆禅师,《禅林僧宝传》中说仁宗因梦中“见龙蟠地”而寻得道隆(3)⑤ [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第137页。,“皇佑二年,诏庐山僧怀琏至阙,演法于浚苑化成殿。上召隆问话,机锋迅捷”,即是此事。⑤另有哲宗皇帝“不忘佛记,克绍前芳”⑥,徽宗皇帝“度僧尼道,精崇法会;敕选禅众,举扬禅宗”,故能使“禅林讲肆,继祖传宗……天下禅门,孰不欣幸”。⑦这些都是皇帝礼遇禅僧的案例。在惟白看来,宋代禅宗得以发展兴盛,来自皇帝的支持是一关键因素,这便是“皇恩”。
在皇帝之下,皇室成员、官员大臣亦礼重佛教,助缘“皇恩”泽及僧众。《续灯录》提及的朝中外护有豫章郡王赵宗谔、恭王赵仲爰、驸马李遵勖、驸马张敦礼、王曙、夏竦、赵抃、王安石、章惇等数十人之多,但在对这些好佛的皇室成员、官员大臣的刻画上,与其先例《传灯录》和《广灯录》有很大不同。《传灯录》《广灯录》中多见居士与禅僧间的酬对互答,塑造了庞蕴、裴休、杨亿、李遵勖等极富禅机的在家众形象。《续灯录》中却鲜有此类禅语,在家的皇室成员、臣子最常见的礼佛表现,就是为禅僧奏请赐章服及师号。章服、师号是帝王给予僧人的极高荣誉。《大宋僧史略》言“赐人服章,极则朱紫,绿皂黄绶,乃为降次”,可知僧人之服章已成为世俗品级秩序的一种体现;又“师号,谓赐某大师也”。(4)⑩ [宋]赞宁撰、富士平点校:《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8、168页,第169页。汪圣铎指出,世俗统治者控制了紫衣、师号的颁给权,并通过赐紫衣和师号来引导佛、道教徒为国家、社会积极效力(5)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说明了紫衣、师号是在世俗政治框架内对僧人的肯定。由于皇室成员和臣子可以为僧人奏请紫衣、师号,如《大宋僧史略》说“每遇皇帝诞节,亲王、宰辅、节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荐所知僧道紫衣师号”,他们因此成为世俗权力延伸至僧人的中介。《续灯录》中大量表现居士为禅僧奏请章服、师号,进一步强调了佛教与宋代政治框架的融合。
对于来自皇帝、皇室及臣子的敬重,惟白认为佛教应“报君恩”。《续灯录》中有关“报君恩”的表达共出现四十余处,形式多种多样,如“为国开堂于此日,师将何法报君恩”“凭师一滴曹溪水,四海为霖报我皇”“恩大不知何以报,一炉香篆祝尧年”等,表现出佛教对君权的积极回应。
《续灯录》中禅僧报君恩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参加皇家法事,追荐亡故的皇室成员。《续灯录》共提及五场皇家法事,分别是元丰三年(1080)慈圣光献皇后上仙、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上仙、元符三年(1100)哲宗皇帝五七及百日、建中靖国元年(1101)钦圣宪肃皇太后五七。共有十位禅师参加了这些法会,哲宗皇帝百日时,更是出现“六院长老”(惟白、净因惟岳、慧林德逊、智海智清、褒亲有瑞、华严智明)共同说法的盛景。他们阐扬般若,深振宗风,祈愿亡者转生天道,早证菩提。如哲宗皇帝五七时,“问:‘大行皇帝上仙,未审即今居何报土?’师云:‘不居兜率陀天上,便在莲花世界中。’”。又净因惟岳在钦圣宪肃皇太后五七上祈祷皇太后“兜率天宫陪摩耶佛母一处逍遥,无垢世界共娑竭龙女同成正觉。回耀休光,昌明宗社”。禅僧以佛法为媒介在生者与逝者间建立联系,既让逝者进入更好的死后世界,又回向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命运,这是佛教对“君恩”的积极回报。二是祝太平,即在讲法时祷祝国祚长久、天下太平,这几乎成为禅师开堂时的固定内容。如法云法秀在说法时表示“即此举扬,上扶帝祚;仰冀聪明元首,芬芳万国之春;忠节股肱,弼辅千年之运”(6)[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第283页,第374页,第377页。;智海智清“上祝皇帝陛下,伏愿德光尧舜,道迈羲轩;资景运于万年,保瑶图于百世”。(7)③④⑤⑨ [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下册,第605页,第430页,第506页,第603页,第502页,第460页。三是祝圣寿,即祈愿君王寿命长久,如法云善本“师云:‘满庭嘉气合,匝地觉花开。’僧曰:‘若然者,炉爇宝香凝瑞剎,祝延睿算等南山。’”,等等。③
不难看出,宋代禅宗的“报君恩”行为有很强的现实性。虽然佛教被认为有超越性的力量,但以上种种方式,除了追荐亡者之外,无论是回向此土,还是祝太平、祝圣寿,其落脚点都不在于抽象的“福田”,而在于统治者在此世的利益。佛教接受世俗权力的帮助,又以佛法辅佐世俗权力的实现,在世俗世界中完成了“施恩-报恩”的闭环。
对于禅宗“报君恩”的行为,《续灯录》从佛教内部给出两点理论支持。首先,“王即是佛”,皇帝即是如来的化身。惟白曾云:“今上皇帝陛下,宝月智光如来示身为金轮圣王,登大宝位,布大恩庥。”④又智海智清曰:“我皇帝陛下是现在诸佛,以大悲愿力,顺天应人,覆育苍生,护持佛法……颂曰:‘佛有多身是处分,人间天上化凡伦。要知昔日灵山老,现作中华圣宋君。’”⑤既然“王即是佛”,那么王化即佛化,“报皇恩”即“报佛恩”。这种理论其实是中古《华严经》佛王传统的延续,即转轮王同时具有作为世俗统治者的转轮王与作为法的代表的菩萨或佛的形象。(8)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智海智清就说明了其“报恩”思想的《华严经》来源,给予僧人“报君恩”最正当的理由:
问:“华严教云:‘菩萨现身作国王,于世位中最无等,福德威光胜一切,普为群萌兴利益。’且道当今皇帝是什么菩萨?”师云:“荡荡莫能名。”僧曰:“大悲愿力为人主,日用佛心治万民。”师云:“知恩始解报恩。”(9)[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下册,第599页。
其次,中国禅宗有肯定经验现象的思想,《续灯录》就此进行发挥,为此土的政治秩序的价值进行合理性辩护。如牛头宗有“道遍无情”之说,认为道体遍布于世间所有现象之中,所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10)[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日]衣川贤次、[日]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惟白则说“玉池春水,澄湛法身。金殿香氲,含容妙体。龙楼耸峻,普贤家风。凤阁穹崇,文殊宝界。御沟柳绿,尽显真如。上苑花红,全彰般若”⑨,即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巧夺天工的亭台楼榭正是真如妙体在现实世界的体现。洪州宗有“性在作用”的思想,如马祖道一所言:“今见闻觉知。元是汝本性。亦名本心。更不离此心别有佛。”(11)[宋]释延寿集、杨航整理:《宗镜录》第1册,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因万法皆为清净自性的化现,所以主张全盘接受感官经验。《续灯录》则将此应用于政治领域,认为严整的君臣秩序亦是清净心的体现。如“问:‘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未审佛在什么处?’师云:‘万乘登龙座,千官列宝阶。’”“问:‘法无定相,随缘构集。有佛世界,以光明为佛事。有佛世界,以庄严为佛事。未审此佛世界以何为佛事?’师云:‘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从这两方面,《续灯录》为世俗权力与佛教间的施恩报恩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描绘出一幅“舜日与佛日高明,尧风共祖风并扇”的和谐一致的政教关系,将佛教完美地融入世俗权力的架构。
二、《建中靖国续灯录》成书的背景
《续灯录》之所以构建出这样一种政教关系想象,在于它是一部代表了京城禅宗(特别是云门宗)立场的、面向皇帝而作的作品,并且得到驸马张敦礼的支持。这三个因素的合力,使《续灯录》在选材和表现上有别于其他禅宗灯录。
北宋禅宗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逐渐走进京城、接近皇权,其中又以惟白所在的云门宗为代表。五代末至宋初,禅宗内部虽有沩仰、临济、云门、曹洞、法眼五家之分,但很快沩仰、法眼两家先后衰微,曹洞陷入沉寂,至《续灯录》成书时,已形成云门、临济二宗平分天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云门宗积极地向士大夫传法,率先在汴京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成为禅宗在政治权力中心的主要势力。据黄启江统计,北宋一代奉诏入京传法的云门宗弟子,由三世到八世至少有十四位。(12)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7页。他们往往落脚于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重要寺院,借此扩大了在皇室、士大夫中的影响,拉近了禅宗与世俗权力之间的距离,使“鹫岭传芳东震,云门列派皇都”(13)[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第259页。。
宋代云门宗在京城的兴盛始于云门文偃下五世的大觉怀琏。(14)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宋初汴京有律宗、华严宗、唯识宗寺院,却无禅院。皇佑元年(1049),内侍李允宁奏请,舍汴京宅第为禅院,仁宗赐额为“十方净因”(15)[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12页。,此为汴梁禅居之始。次年正月,怀琏奉仁宗之命入主十方净因禅院,成为宋代第一位在京中主持寺院的禅僧。未几,仁宗宣入化成殿,与之讨论佛法大意,赐号“大觉禅师”(16)[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第125页。。怀琏三入禁中对仁宗说法,使仁宗“皇情大悦”。仁宗共赐予怀琏问答诗颂十七篇,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17)同上,第126页;[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第151页。
由云门宗禅师担任初祖的还有大相国寺的慧林禅院和智海禅院。大相国寺是汴京最大的佛寺,最为宋王室所重视。(18)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第100页。元丰三年(1080),神宗皇帝为求圣嗣,同时感慨京城内禅居不多,将大相国寺六十四院改建为二禅六律。二禅院中东为慧林,诏宗本入主;西为智海,诏本逸入主。(19)[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第176页。“御制《建中靖国续灯录》序”作元丰三年,《僧宝传》《佛祖统记》均作五年,或误。(参见[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御制《建中靖国续灯录》序”第1页;[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第102页;[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第416页。)宗本为天衣义怀弟子,他初至慧林禅院讲法时,有若“弥勒从天而降人间”;翌日入延和殿面圣,神宗对宗本颇为认可,称赞其“真福慧僧也”。(20)[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第103、104页,第179页,第179页。宗本弟子净因惟岳后来成为十方净因禅院的第三任住持。宗本归隐灵岩后,慧林禅院的第三任住持若冲禅师亦是云门宗天衣义怀的法嗣。云门宗率先占据了十方净因、慧林和智海这三座重要禅院,其在皇室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云门宗由怀琏、宗本、本逸等人在汴京打开局面,临济宗紧随其后,净因道臻、慧林德逊、智海智清等人亦先后入主这三所禅院,另有褒亲有瑞、开元志添等人入京,渐渐呈与云门宗争流之势。但另一座由皇室成员请建的寺院——法云寺,一直由云门宗僧人担任住持,是云门宗在汴梁的一座重镇。元丰五年(1082),越国大长公主及驸马都尉张敦礼奏请复建法云禅寺于国之南;(21)[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序”第1页。元祐元年(1086)又为法云寺募捐得万斤钟一口,并请苏轼为之铭。(22)[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23页。元丰七年(1084),张敦礼夫妇奏请天衣义怀的弟子圆通法秀居法云寺,为第一祖。法秀曾因讲经“妙入精微,为众发挥”而声著京洛,后归心禅门,开堂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赐磨衲袈裟,皇弟荆王亲侍法筵。(23)[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上册,第281-282页;[宋]慧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第178页。法秀在士大夫中影响极大,据《禅林僧宝传》记载,他曾受王安石之请住锡蒋山,进京之后,又劝阻司马光抑佛,呵斥李公麟及黄庭坚,劝诱二人行佛行。这些轶事传说不免含有僧家自高身价之辞,但法秀使“云门宗风自是兴于西北,士大夫日夕问道”,当确定无疑。法秀入灭之后,他门下两位弟子分别接任了法云寺的第二、三任住持,一位是法云善本,另一位就是《续灯录》的作者惟白。
首先,禅宗用了半个多世纪逐渐占据京城的重要寺院,在皇都站稳脚跟,与皇室日渐亲密,惟白即置身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他嗣法法秀,又在法云寺这样一座由皇室建立的寺院担任师门中的第三任住持,必然也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自陈“两岁中三遇陛下诏阐宗风”(24)②③ [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下册,第836页,第836-837页,第838页。,这三次入内说法构成了《续灯录》中惟白条目的主要内容,可见是其极为重要的人生经历。另外,惟白还和越国大长公主、驸马张敦礼交往甚密,不仅惟白之入主法云寺、《续灯录》之入藏流通系由张敦礼奏请,当御旨下达时,惟白正是在张敦礼宅受付并讲法谢恩的。可想而知,皇权与佛教间的施恩报恩互动,是惟白所经历的佛教的常态。他在《续灯录》中描绘政教和谐一致的图景,强调佛教的报恩行为,实是代表不断世俗化的汴京禅宗立场进行的宗教书写。
其次,惟白在作此书时,已报着进上的目的。换句话说,他是明确以皇帝作为目标读者来编纂《续灯录》、构建这种政教关系想象的。在“上皇帝书”中,惟白先提及了宋初的《传灯录》与《广灯录》:真宗皇帝登基,改元景德,东吴僧人道原集禅门心要语句三十卷进上,真宗命翰林学士杨亿作序,更名为《景德传灯录》,入藏流通;仁宗皇帝即位,改元天圣,驸马都尉李遵勖亦集禅门语录三十卷为《天圣广灯录》,仁宗赐序并准许入藏。紧接着惟白说:“(臣)今遇陛下践祚改元,谨集禅门宗师心要语句三十卷,目为《建中靖国续灯录》,昧死上进。伏望陛下特降朝廷,依《传灯》《广灯》录例,赐序文,下印经院,编入大藏目录,随藏流行,使佛焰祖焰光明而无尽,则陛下圣祚国祚绵远而何穷也。”②事实上,《传灯录》上进于景德元年(1004),《广灯录》成书于天圣七年(1029),均非如惟白所述成于真宗、仁宗践祚改元之时。惟白此举,意在将禅宗灯录与皇帝登基改元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把皇帝赐序、准许入藏塑造为传统先例,并自觉地接续《传灯录》和《广灯录》,融入这一历史的轮回,利用真宗、仁宗对前两部灯录的垂青,使《续灯录》得到徽宗的肯定。可以说,惟白充分认识到徽宗皇帝作为世俗权力最高来源的特殊身份。他编纂《续灯录》就是要向这位特定的读者展现佛教助其“圣祚国祚绵远而何穷”的功能,这样,书中的种种“报皇恩”行为便得到合理的解释。
再次,在《续灯录》成书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驸马张敦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中所呈现出的权力结构。在引荐《续灯录》的“上皇帝札子”中,张敦礼同样提及《传灯录》和《广灯录》这两个先例,并引仁宗皇帝《御制广灯录序》中“法云滋荫”“续千灯而罔穷”等语句来论证宋朝皇室对禅宗的重视。③《广灯录》的作者李遵勖是真宗、仁宗时期的驸马都尉,与张敦礼有着一样的外戚身份。在《续灯录》中,李遵勖和张敦礼是两位最活跃的士大夫居士,似乎可以说明张敦礼有意以李遵勖为榜样,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位皇室中的佛教外护。但历史上的李遵勖是临济宗禅师谷隐蕴聪的弟子,于禅法颇有心得,禅籍中载有其与三交智嵩、石霜楚圆、杨亿等名僧、居士的机锋酬对。然而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未见张敦礼有过任何关于禅法的探讨、请益。在《续灯录》中,张敦礼的护法行为主要集中在请禅僧出世说法及为僧人奏请章服、师号,他共为十人请过章服或师号。由此看来,张敦礼的志趣或不在禅法,而在于功德。考虑到张敦礼与惟白的关系以及在《续灯录》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他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续灯录》中士大夫居士的形象。特别是李遵勖的形象,《续灯录》多次提及他为僧人请师号,而这些内容在他本人编集的《广灯录》中却没有表现,可见,张、李二人对士大夫居士作用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张敦礼及惟白看来,士大夫是皇权与佛教之间的权力中介,他们通过奏请荣誉奖赏的方式,使佛教融入到国家政治体制中。
这样,在佛教、皇权、臣子三者间的合力作用下,《续灯录》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其他禅宗文献的政教关系想象,这是进入汴京后的禅宗群体面向皇权进行的一次展示,本质上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三、“报君恩”是对“祸国短祚”的回应
《续灯录》构建的政教关系想象,是禅宗在世俗化过程中,对“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回应,应该将其放在佛教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理解。
美国学者魏雅博(Albert Welter)指出,面对儒家的复兴,宋初佛教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回应策略。一种以律师赞宁为代表,强调佛教与中华文化的一致性:在《大宋僧史略》中,赞宁梳理了中国佛教的制度史,并有意忽视佛教的印度传统,以此来说明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另一种强调佛教的文化异质性,其代表是禅宗的《传灯录》,它突出了禅宗神秘主义、反理性、反权威的精神特质,用独特的话语吸引在文化上主张兼收并蓄的士大夫文人,这种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25)Albert Welter,“A Buddhist Response to the Confusian Revival:Tsan-ning and the Debate over Wen in the Early Sung”,Buddhism in the Sung,ed. by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p. 21-61.此论的核心在于将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不同态度与特定的宗派联系起来,这或许值得商榷,因为《续灯录》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在《续灯录》中,惟白极力突显皇权与佛教间施恩报恩的互动,表现佛教对治理国家的帮助,正是使用了魏雅博所谓的“赞宁式”的回应策略。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魏雅博没有在佛教面对的世俗世界中细分出士大夫文人与世俗权力这两个多有重叠但又不同的对象。
《续灯录》中政教关系想象面对的对象不是思想层面的中华文化,而是皇权。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进入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之后,人们对其对国祚的影响,便有着各种判断和想象。如东汉时,黄老与浮屠未分,佛教便被视为延祚之方。(2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随着佛教日趋独立,反佛之声渐起,对其“祸国短祚”之指控,从未停歇。如南齐张融曾作《三破论》,指责佛教“入国破国”。(27)[梁]刘勰:《灭惑论》,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弘明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36页。唐代韩愈作《论佛骨表》引用大量历史经验说明好佛之国未能长久:“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反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28)[唐]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典藏本)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04页。而后宋儒对佛教的批判逐渐向哲学层面深入,但仍可见到此类批评。如欧阳修就另辟蹊径地指出,佛教的传入是王道不行带来的附加后果:“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29)[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11-512页。这种指控很难不引起君主的警惕,所以当僧人纷纷进入京城,频繁进宫参加皇家法事、与国王大臣酬作答对时,就必须面对来自皇权的凝视,不得不就佛教的社会功能与帝王之治的一致性展开论述。吴越国师、法眼宗禅师天台德韶曾说:“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患难。此是佛语,古今不易。”(30)[宋]道原撰、冯国栋点校:《景德传灯录》下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23页。赞宁在《大宋僧史略》“行香唱导”条中为官员行香辩护,称其为忠孝之举:“况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废之,如忠孝何?”(31)[宋]赞宁撰、富士平点校:《大宋僧史略校注》,第74-75页。又契嵩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说:“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岂不然哉?”(32)[宋]契嵩撰、纪雪娟点校:《镡津文集》(校勘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8页。可见,佛教对世俗权力的态度与宗派特质并无太大关联,而主要取决于史家与皇权的关系及所处的立场。
宋代高度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也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提出要求。(33)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261页。同时,宋代又是禅宗不断世俗化的阶段。《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正是禅宗在不断世俗化、渐渐接近皇权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答。禅宗本起于山林,但自五代十国开始,禅众逐渐向城市、都邑、大中寺院分流,同时结交士大夫,取代义学形成新的都市佛教。(34)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这一入世的进程在北宋得到加速。一方面,北宋整体上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数位皇帝对佛教颇为重视,如太宗曾为佛教设启圣院、译经院、内道场,真宗、仁宗分别准许《传灯录》《广灯录》入藏流通等。特别是仁宗诏怀琏入京及神宗改建大相国寺,直接使得禅宗势力在汴梁立稳脚跟。另一方面,禅宗一改山野语言,形成了意境深远的文字禅,在士大夫中掀起空前的参禅热潮,其中有就相当多的朝廷重臣和文坛领袖,(35)周裕锴:《禅宗语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页。这种现象进一步促进了禅宗在帝国权力中心的传播。《续灯录》正是北宋禅宗世俗化进程发展到巅峰的产物。在“上皇帝书”中,惟白说:“(臣)闻天地崇高博厚,所以覆载万物也;日月丽明而腾照,所以辉华万方也;孔孟本仁而祖义,所以教养万俗也;佛祖运智而含悲,所以开觉万有也。若此四者,古今罕有齐其功者也……(臣)窃原国朝祖宗已来,以圣继圣,未尝不以佛祖妙道资以周孔仁义而化成天下也。”(36)[宋]惟白撰、朱俊红点校:《建中靖国续灯录》下册,第836-837页。惟白认为,儒家和释家都是君王维持国家太平的重要手段,它们与天地、日月这些自然现象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便将佛教与王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诚然,后世作品对《续灯录》评价不高,正如魏雅博所说,“赞宁式”的融合路线遭遇了失败。如南宋悟明作《联灯会要》,直言“《续灯》所载,似无取焉”(37)[宋]悟明集、朱俊红点校:《联灯会要》上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原序”第1页。。雷庵正受自叙作《普灯录》因缘,是因其师阅《续灯录》,感叹帝王士庶求法之行“独是录未尝及之”(38)⑦ [宋]正受撰、秦瑜点校:《嘉泰普灯录》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页,第3-4页。。又晓莹在《罗湖野录》中赞叹怀琏于十方净因禅院归隐后“终藏而不出”,称其“足以羞挟恩恃宠者之颜”。(39)[宋]晓莹:《罗湖野录》,《全宋笔记》第五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以上种种,似乎都在批评《续灯录》过于强调禅僧与世俗权力的互动。但对这些批评,亦须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一方面,《续灯录》成书后不到二十年,徽宗倾心道教,转而抑制佛教;紧接着,宋廷南迁,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分散了朝廷的注意力;同时,理学渐兴,极大冲击了禅宗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诸多因素使得南宋佛教从整体而言,难以像北宋时那样接近世俗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北宋之后的禅史作家多志在山野,往往“杜门却扫,不与世接”(40)同上,“叙”第208页。,其与皇室之关系,比之惟白相去甚远。北宋之后的灯史撰作不代表京城佛教的立场,无需再经营这样的政教关系想象,故从它们的视角来看,《续灯录》的表述自然无从可取。但它们对于《续灯录》并非没有吸收借鉴。如正受在“上皇帝书”中同样说:“佛法于今正赖陛下举而振之……持此一毫善力,恭祝两宫圣寿无疆,国祚延鸿,天眷绵衍。”⑦这正是“报君恩”的延续。又《普灯录》设“圣君”“贤臣”两部分,将宋代好佛的帝王将相编入禅宗法脉,亦是佛王传统的另一种表现。由此可知,《续灯录》对政教关系的想象不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是佛教在接近世俗权力作出的必要回应,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结 语
惟白在《续灯录》中构建出了一幅“三位一体”的政教关系想象:皇帝以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人臣是权力的中介,佛教作为受者的同时积极地以各种方式“报皇恩”。在这一结构中,原本以出尘为志的佛教完美地与君王在此世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这种政教关系,是作为京城禅宗代表的惟白,特意展现给作为世俗权力最高来源的皇帝的一种想象;是宋代不断世俗化的禅宗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对“佛教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集中回应;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书写手段。这并不是说京城的僧人最后都变成了政治僧、权力僧,相反,与世俗权力保持和谐的动态平衡,是佛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能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中理解惟白等京城禅僧的所作所为,反而肯定其他禅史描述的禅宗固有的反传统特质和远离世俗权力的倾向,其实是不自知地倒向了另一种政教关系想象,进入了另一种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