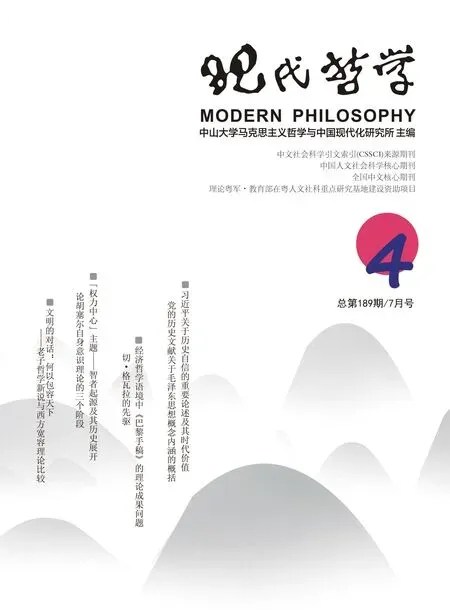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权力中心”主题
——智者起源及其历史展开
陈德中
学者约翰逊(T. J. Johnson)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关注“现实主义的智者基础”。约翰逊详尽追踪智者的思想,提炼出“智者三原则”(1)T. J. Johnson,“The Idea of Power Politics:The Sophistic Foundations of Realism”,Roots of Realism,ed. by B. Frankel,Abingdon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3,p.196.:
第一,相对主义,真理和正义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普遍可知或普遍可接受的真理;
第二,悲观主义,对于人性及其终极潜能抱着一种悲观态度;
第三,权力的优先性,承认权力——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压迫来使人信服——在理解政治互动中的优先性。
约翰逊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智者三原则”适用于后世所有的政治现实主义。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就其作为质询标准而非作为现成答案而言,“智者三原则”成为后世政治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三个必答题目。如何回答和处理“智者三原则”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成为我们区分不同思想家理论走向的核心参照。“智者三原则”所涉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智者运动,探寻智者的理智环境与现实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智者三原则”彼此之间在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解释。其中,“权力优先性”原则更是为后来的现实主义者所接受,并被发展为现实主义观察和解释政治的核心主题,此即现实主义的“权力中心”主题。
一、智者与“权力中心”主题的形成
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权力中心”主题如何脱胎于智者运动。“权力中心”主题牵涉到我们对权力作为政治的通货的理解。现代人对此业已普遍接受,但在思想史上,这一主题的独立并不那么必然。智者主张思考政治时权力具有优先性。从智者的权力优先性原则到后来的“现实主义”主张,这种转变依赖于后期智者在认识论等问题上的根本转变。但显然,现实主义主张不同于智者主张。
在人类思想史上,智者第一次真正开始主动以权力为中心展开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这一选择被当代学者称作“政治地思考政治”。“权力中心”主题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主张,历来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一种表现。因为人类本能地视权力为首恶,人们一直试图用真理、道路、正义、爱、救赎、大同、共同善、(历史的)发展规律等来刻画政治的目标。智者似乎努力在向其对手证明,这类目标其实都误解了政治、误识了政治得以展开的真正动力。
智者主张真理与正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早期智者的认识论支持这一点。早期的哲学智者,一头放弃神谕,一头放弃超越性哲学对人的认识的支撑。例如,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高尔吉亚说“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因此“无物存在”。(2)《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4、56-57页。认识论的主观主义导致了真理与正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交流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拥有的只有论辩术。智者的相对主义源自他们对实在的本性与感性现象的关系或者说实在与表象的关系(3)W. K. C. Guthrie,The Sophi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 3.这一问题的回答。高斯里(W. K. C. Guthrie)在《智者》一书中提出:“在道德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导致了一种‘情景主义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强调当下的实践,不相信一般的永恒法则和原则。”(4)Ibid.,p. 4.智者既质疑神圣律令的效力,也不再主张以超越性哲学作为社会规范的支持。在绝对主观主义的支持下,他们相信并且只能相信情景化的规范判断。极端而言,在人的论辩效力之外,不存在外在的、客观的独立有效的判断标准。在早期智者那里,力量原则围绕其绝对的主观主义认识论主张萌芽展开。
不过,早期智者的这种绝对的主观主义似乎并不为后世的现实主义所坚持。这里存在的疑问是:相对于早期智者的主观主义,后来的现实主义立场是什么样的?立场改变之后的现实主义,何以仍然持有一种相对主义?同样,对于约翰逊所总结的智者第二原则即悲观主义,阅读者也存在疑问。因为,早期智者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将人这个行动者从神圣秩序与宇宙秩序之中剥离出来,视其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早期智者并无对于人性的刻画,更谈不上对人性抱有一种悲观态度。从早期智者的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并不能够解释现实主义对于世界的看法。
针对上述疑问,约翰逊的回答是,早期智者强调人只能生活于法律、约定和习俗之中,而非生活于神圣秩序或宇宙秩序之中,因此人的德性是可教的。人必然地受制于法律、约定和习俗。早期智者虽无人性主张,但隐含着受制于法律、约定和习俗结构的必然性。这种理解接近于把人视为一种由结构性决定了的、被动的可塑造之物。早期智者即便并不拥有一种人性的悲观主义,也绝对不拥有一种人性的善的主张。
对于上述疑问的进一步回答,需要从后期政治智者安提丰、色拉叙马库斯和修昔底德主张的转变入手。(5)早期哲学智者更多关心认识论话题,后期政治智者更多关心政治话题。安提丰主张,我们要剥去不可见的东西,揭示实际的(the actual)东西,主体对事物的特殊归属并不改变事物的实际所是,因此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实在,即一个实际所是的世界(the actual world)。安提丰的政治理论注重实际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存在,代表着从早期激进智者向现实主义类型的转变。由于有着揭示事物实际所是的主张,安提丰得以开展对于人性既有特征的研究。主张“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的色拉叙马库斯的世界观与安提丰相类似:他关注事物的实际所是,而非名称归属;他认为存在着一个自然秩序和人性理论:人们依照其自身的利益去行动,约定的规则只是经过审视后的这种行动的结果;可见的人类行为事实优先于不可见的哲学理论。修昔底德作为智者的门徒则确信:存在着可被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深植于证据、拒绝神秘的理性方法或许可以有效地解释历史,获得与个人立场无关的真理;现实独立于观察者,只要严格忠于证据,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实。这里,修昔底德表现出对人类理智获知真理的能力(即对理性)的尊重,从而也使得修昔底德与相对主义拉开了距离。(6)关于安提丰、色拉叙马库斯和修昔底德的主张,参见J. Orton,“This is Not The Truth”:A Method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Classical Greek Origins of Political Realism, Durham University,E-Theses Online:http://etheses.dur.ac.uk/2434/,2007,pp.114-116,119-122,125-127.
总体来看,后期智者表达了对三个问题的关注:第一,事物的实际性(actuality)及其物质性;第二,独立的人性;第三,支配权力运行的一般法则。也就是说,后期智者关注实际性、人性和权力运行的法则,他们的主张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客观主义”。他们不追求神性,也不追求理性的超越性,其对现实的理解是现象主义的“实际性”。他们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从主观主义向看重实际性的转变。锚定于实际性,看重与强调实际性,也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区别于一般的理解,现实主义停留于从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转变的中途。现实主义不是主观主义,也不是客观主义。现实主义更倾向于是一种怀疑主义而不是智者的主观主义,对是否以人为尺度抱着一种冷峻的态度,其方法最终锚定客观准确、严格求实。由于早期智者是主观主义的,因此,力量原则要想独立就需要这样一个向着实际性的转变。只有立足于“实际性”,我们才能够实现力量原则的相对独立。在我们熟悉的晚期智者那里,力量原则具有了这样一种相对独立性。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智者对修辞术的强调,以及希腊人对互竞(agon)的强调。在一个民主竞争的时代,一个人的社会形象取决于他在城邦中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修辞术赋予城邦之政治家在政治事务中的形象。智者更是以打造城邦政治家为己任。智者的主观主义认识论切断了宗教事务与超验理想对世俗事务的支撑,人成了万物的尺度,外在世界的一切存在或其不存在都依赖于作为衡量尺度的人,因而依赖于人在城邦中间运用修辞术“说服”(persuasion)。智者既不关心超越的实在,也不关心经验的真理,他们只关注何者可以给出足够多的经验表象以说服或欺骗听众。在民主的雅典城邦,这种说服的能力就是一种动力和力量。极而言之,在一个竞争性的民主雅典城邦中间,依照智者的主观主义世界观,修辞术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获得的惟一通货。
晚期政治智者进一步把权力作为实际发挥作用的力量来加以看待。他们认为,在政治这个竞技场所,实际上真正运行有效的法则是权力法则。这一法则是自然的。其他人为的规范(法律、约定、习俗)要么是虚伪无效的,要么是会被权力法则所实际取代。其中,最能体现智者将“权力中心”主题显明化的,乃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然(physis)-习俗(nomos)”之辨,以及智者关于言与行关系的辨析。
政治智者声称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强力即正义”,均是“权力优先性”命题的表达。卡里克勒斯批评苏格拉底时说:
(在我看来,)自然(本性)自身表明,较好者比较差者、较强者比较弱者拥有更多,此乃公义。在很多方面它都表明,无论是在人和人之间,还是在动物和动物之间,抑或是在所有城邦和城邦之间、部族和部族之间,正义就在于优胜者统治卑弱者,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是的,他们依据自然(本性)的法则而行事,也许并不依据人为的立法而行事。(483d-e)(7)Plato,Gorgias by Plato,trans. by B. Jowett,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卡里克勒斯在这里强调,在政治生活中,权力或力量自然发挥作用,权力优先是倚重“自然正义”。智者坚持自然的强力具有优先性,而习俗以及法律是在后的。不但如此,凡是在人们声称法、约定和习俗优先的地方,其实际发挥作用的都是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自然本性通过人的“行”不断修正和改变人的言及其表现即法律、约定与习俗。行先言后,在人的真实的行动面前,习俗是相对外在的规定,不能够准确及时地把握行动者行动的真实动力。依照力量来行事,就是依照本性来行事,这是推动行动者行动的动力之所在。
智者贡献了对政治事务真实动力的洞察。权力优先即力量优先,力量优先即自然正当性优先。力量原则独立,是对于政治竞争中的人作为度量尺度的坚持。相较于早期智者,晚期的政治智者在朝着权力作为独立原则而出现的主张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在智者那里,自然是天性,通过后天的学习,人们可以获得第二自然。随后修昔底德用人的天性(人性)来指示人的社会和道德本性。晚期智者强调实际性、人性和权力运行的法则,这种主张已经使得晚期智者对政治的态度蒙上一层悲观色彩。但真正的悲观主义需要在晚期智者从主观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才会最终产生,最典型的是,它需要关联于修昔底德对于“权力中心”主题的鲜明刻画。
二、修昔底德与“权力的兴衰”主题
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简称《战争史》)对“权力中心”主题的提炼与升华。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第一次明确形成“权力的追逐以及权力的增长必然带来负面效应”这样一个悲剧性主题,即“权力的兴衰具有一种必然性”这一主题。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其相反方面的出现,这一主题附带引出了半个评价性的主题,那就是像雅典这样的城邦的兴衰呈现出一种令人惋叹的悲剧性特征。
在柏拉图作品中,出于话题论辩的需要,强调“权力中心”主题的智者们大都是以辩护姿态出现的。加之柏拉图有意将智者对于政治这种世俗事务的思考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进行对照,我们因而看到,智者对于“权力中心”主题的阐发是消极防御型的。我们从柏拉图以及其他人对智者的引述或转述中,看到的多是一种对这一主题的提出、辩护,或为反驳对立主张而进行的防御性辩护。
修昔底德生活于智者运动的环境之下,受到这一环境的巨大影响。不过,他的《战争史》在表达“权力中心”主题时相当正面。《战争史》的核心主题是“权力的兴衰”。该主题认为,权力的追逐与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其相反方面的出现。这一点既适用于政治家,也适用于不同人组成的政治行为体。修昔底德注重对实际的权力分配的分析,权力追求、权力分配与再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失衡,成为他分析政治动力的基本线索。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表明,权力不再是强者颁布命令(如相对主义者或色拉叙马库斯所宣称的那样),不是强者有能力将其意愿(意志)付诸实施,而是独立于强者和弱者的自身特性。权力运行的客观性得到彰显。这里无涉于主观主义和个人立场。权力政治不是某种我们认定的东西,而是某种实际所是的东西。“权力政治”这个术语乃是一个同义反复。
也有学者提出《战争史》另有一个主题,即作者对于战争等灾难的悲悯性主题。(8)参见[美]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王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3页。这一主张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战争爆发第一年中的伯利克里演讲,以及紧随其后的瘟疫的爆发对于伯利克里战争政策的影响。伯利克里在其演讲中骄傲地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其民主制是别人的模范。不过,修昔底德有意在描述瘟疫与战争之后,对照性地提出,战争是另外一个“苦涩的学校”。悲悯主题是权力兴衰主题的一个实际表现,其本身并不影响修昔底德将“权力的兴衰”作为一个特殊的“权力优先性”主题的提出。可以说,对照智者在历史上的出场,修昔底德的“权力的兴衰”主题更加冷峻、更具有现实感。
权力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权力的消长是必然的,权力具有一种回旋镖效用。后一主题已经开始为修昔底德所全面接受。耶格尔(Werner Jaeger)在评价《战争史》时说,在修昔底德这里,力量原则首次独立。“现在,力量的原则根据其自身的法则构建了一个自己的领域,它既不废除传统的礼法,也不承认其优越性,只是从中分离和独立出来。”(9)[德]耶格尔:《教化》,陈文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88页。在《战争史》中,力量原则独立出来的标志,就是其中几个著名的对话。对话双方清楚表达了实力(强力、力量、权力)优先的原则。这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对这一原则抱有信心的表现。作为与之竞争的神谕或道德考量,现在则只是作为对照而出现。
在古典现实主义那里,政治是权力之间永恒的竞争与冲突。在其典型代表修昔底德那里,权力竞争主题第一次得到正式总结。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主题被认为是“权力的兴衰”,或者是权力的追逐与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其走向其相反方向。伴随着权力追逐和权力增长,恐惧、荣耀和自利等要素既可能成为创造性的要素,也可能转化为破坏性要素。潜在地,权力结构将促成这样一种人性特征在后果上的负面转化。智者学派的第三原则逻辑地蕴含了第二原则,从而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悲观主义内涵。权力的优先性意味着,智者眼中的政治是自然强力竞逐表现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眼里,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与力量角力的舞台。如若谈论正义,那力量和力量的均衡才是正义。对于力量的习俗约束与真理性探索无涉于正义。这种互竞的世界观同时潜含着一种对权力的使用和权力的追求的悲观观察。权力运行的本性决定着,历史本身具有一种悲剧性。
修昔底德注重对于实际的权力分配的分析。权力追求、权力分配与再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失衡,成为修昔底德分析政治动力的基本线索。在修昔底德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关系必然遵从的自然法则,这一主张在整个希腊文化中并不陌生。宇宙的理性同时昭示了普遍的局限。自然的局限性也支配着人的行为,宇宙的局限性与人的局限性服从一个统一的单一原则。自然法则适用于对于权力关系的解释,安全问题由此而衍生。在修昔底德看来,政策的现实目标乃是获得权力优势,在现实政治中,道德乃是“一大堆无人相信的言辞”。道德掩盖了争论,让政策制定者丧失了其职分应该具有的真确与正直(accuracy,integrity)。
雅典的兴盛促使雅典人摆脱神圣限制和习俗正义的限制,雅典人在斯巴达不再提到神或他们行为的更高约束力。现在,他们明确宣称实力即正义。“修昔底德描述的世界乃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强者公然宣布且无情行使他们统治弱者的权利。”(10)[美]劳埃德-琼斯:《宙斯的正义》,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第221页。最终,我们看到,在政治这个竞技场所,实际上真正运行有效的法则是权力法则。这一法则是自然的。其他人为的习俗要么是虚伪无效的,要么会被权力法则所实际取代。权力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权力的消长是必然的,权力具有一种回旋镖效应。修昔底德的工作因而经常被看作对于权力兴衰的考察,而权力的兴衰的考察蕴涵着对历史发展的基本思考。修昔底德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权力(兴衰)观念。权力兴衰的主题认为,权力的扩张及其运用,将会导致权力使用者走向其反面。权力的兴衰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对修昔底德做整体界定的真正困难在于,事实上在人身上存在着真正的两间性(两难,ambivalence),尤其是事关权力的追求,权力运用所可能导致的滥用。修昔底德很少谈到,但是同样意识到,在其《战争史》一书中,他为这一两间性的每一面都预留了空间。”(11)P. R. Pouncey,The Necessities of War: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im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ix.
作为补充,伊梅瓦(Henry R. Immerwah)进一步主张,修昔底德《战争史》的首要主题乃是权力与苦难的关系。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正是权力的兴衰带来的苦难使得修昔底德有理由判断这场战争要比波斯战争更加伟大,因而将修昔底德的这一“权力与苦难的关系”主题称作修昔底德的“悲悯陈述”:“由此,权力除了在政治领域中产生影响,还具有人性方面的悲剧意义……修昔底德确实在叙述中刻画出一幅人类处境的绝望图景。”“《战争史》是在权力病理学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权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过程中经历的变化就是恶化的表征……这一恶化的重要症状就是权力施加的苦难。读者可以首先将‘病理学’看作是对‘权力之腐化的一种解释’,其次再将‘病理学’看作是对‘苦难的陈述’。”《战争史》“是对权力与苦难的双重强调”。(12)[美]斯塔特:《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第33、24、44页。所引译文译作《战争志》,本文统一改译为《战争史》。
经过发展了的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态度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层面,利益、自保、恐惧、攻击性、荣誉感等人性的基本特性;第二层面,理性和潜能上的悲观主义(这一点与第一层面交织);第三层面,历史观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古典时期的智者基本上只是表达了第一层含义。现实主义在其后来的演变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出第二、三层含义。第二层面的线索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思考中渐显。第三层面的“历史观”尤其线性历史观则有待于后世历史概念的展开。
为了避免对悲观主义作一般性的情绪性解释,彭西(P. R. Pouncey)严格界定说:“我只是在下述含义上论及悲观主义:相信人性的自身冲动会破坏其自身成就,事实上之前正是同样的冲动促成了这些历史成就,因而其兴也由此,衰也由此。”(13)P. R. Pouncey,The Necessities of War: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imism,p. xiii.权力的兴衰被视为修昔底德《战争史》的宏观主题,其间潜涵着对于权力使用的悲观主义的观察。对于权力兴衰的不可避免性的观察,构成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有的悲观主义,也成为修昔底德《战争史》的基调。对于这样的悲观主义,汉孟德(N. G. L. Hammond)提醒我们要从《战争史》叙述风格的整体转变中去体会把握:“修昔底德起初相信人的自主理性和勇敢的进取心……人的理性和进取心最终会占上风。”“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被证明为主导这场战争的不是理性和进取心,而是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命运女神的狡计。”“只有在前405年修昔底德才意识到智慧和进取心在结局上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14)[美]斯塔特:《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第75-76、76、78页。
实际上,悲观主义问题还与另一个问题关联:修昔底德(到底)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埃德蒙兹(Lowell Edmunds)的看法是:“那些更强调修昔底德的方法论及其对于理性的伯利克里的钦佩者,会得出结论说修昔底德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些看到大量理性计划未能实施,而非理性计划却屡屡成功者,就会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二者各具其半。”(15)L. Edmunds,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 213.埃德蒙兹区分行动者和史家,认为史家可以是理性的(我们据此也就能够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可以理性地、科学地加以研究),但权力运行的本性决定着历史本身具有一种悲剧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因而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后世的尤其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对于修昔底德有几种经典性的解读。第一种是基于人性论的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人性在此被作为一个常量。第二种是强调权力关系的结构主义,在此,权力结构的限制促使人的行动成为一个“必然性”,而权力结构造成的必然性又不同于命运。第三种是将修昔底德刻画为权力转移理论的开创者。这源于修昔底德的一个洞见,即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存在着转移现象。这个现象表明,权力是动态的,权力的动态性即权力的运用、追求及转移充满危险。第二种和第三种同属于“结构性现实主义”。第四种是新政治现实主义,将修昔底德解读为“政治复杂性的学生,在这种政治复杂性中,历史、道德心理学、政治行为的误判等创造了一个悲剧性的政治宇宙”(16)J. A. Schlosser,“‘What Really Happened?’ Varieties of Realism in Thucydides’s Histor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ucydides,ed. by P. Lo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3,p. 302.这里,施鲁瑟(J. A. Schlosser)的“新政治现实主义”指的是以威廉斯和高伊斯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当代流派。这一流派祖述尼采解读,并强调制度性因素。(Ibid.,p. 301-316.)。
三、韦伯与“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
修昔底德主题展开之后,权力政治的悲剧性色彩进一步彰显,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则在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中退居幕后。“权力中心”主题脱颖而出,该主题在20世纪之初的韦伯(Max Weber)那里再次获得一种全新的表达,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这一全新主题第一次正面关注人类合作的金字塔式结构,它仍然强调权力竞争和人类的永恒冲突,但是注意力的焦点更多转向了对人类合作组织或合作建制(如近代国家)的解释和理解。
一个有着凝聚力的政治单元何以产生?这是“主权”和“主权国家”理论讨论的核心。现代现实主义者对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的揭示,为上述理论问题贡献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解释版本。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的展开,得益于“尼采-韦伯-福柯”传统(模式)的存在。当福柯声称自己(作为其博士论文灵感)的理论工作源于他对尼采-韦伯的合理化主题的继承的时候,其思想旨归指向了将其本人也囊括其中的一个现代理论传统。这个传统贯穿了现实主义主题在近代的特殊展开。
尼采被置于首位,原因有二。第一,尼采是现实主义主题的点题者。他对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反思,促使他将自己对焦于以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他对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批评,对应性地回应了智者三原则中的第一原则,这也成为当代现实主义关注的核心与焦点。第二,尼采的“权力意志”主张为“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奠定了哲学基础。意志主题深植于西方哲学传统,而“求取权力”成为意志的目标对象,这一点始于尼采。福柯被置于末位,除了他对尼采-韦伯的合理化主题的继承之外,进一步体现在他对“治理术”的历史考察。福柯“治理术”的核心是关于权力的技术治理化,是统治他人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结合。福柯治理术主张的一个思想后效,就是极端的权力中心化和极端的治理技术化。
回溯地看,“尼采-韦伯-福柯”模式构成了对“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的一个完整揭示。韦伯是这一主题的清晰表达者和实际完成者,他对这一主题的真正领悟是在1910年之后,即其“权力支配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国家社会学”主题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韦伯明确认识到,我们可以用“支配-服从”(Herrschaft)关系来重新理解个人的社会合群现象。政治可作动态的理解,也可作静态的理解:动态地看,政治就是不同权力体之间的永恒竞争与冲突,静态地看,政治就是“支配-服从”关系的结构化。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这样来定义国家:“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惟一来源。”毫无间隔地,韦伯继续界定说:“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17)[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5页。有意思的是,在完成对国家和政治的动态界定之后,韦伯马上转身来谈论静态意义上的“国家”,并使用了“支配”概念:“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18)同上,第56页。
也就是说,动态地看,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是权力的争夺和分配的事业。静态地看,作为为权力而斗争的一种结果,就是具有支配结构的“国家”的出现。韦伯的视野,是抽象的永恒的权力斗争和具体的权力斗争的结构化并置。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一方面保留了政治的动态本性即权力和权力斗争在政治中的核心主线(我们这里称其为“权力支配”主题),另一方面承认和面对了权力支配结构化的制度现实(我们这里称其为“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韦伯的政治正当性的三种类型的划分,就是对于这一静态主题的考量核心。
和“权力支配社会学”所描述的双重主线并行,韦伯还描绘了两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一是不同生活方式所对应的价值域之间在终极价值设定问题上的永恒冲突,二是个人的价值选择意义上的价值冲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生活中所有领域莫不如此。”(19)同上,第40页。
无论是“权力支配”和“权力支配结构化”主题,还是价值域和个人在选择问题上的多元主义,这两个层面的主题均不正面地体现于修昔底德所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者那里。我们因而主张,以韦伯和随后的伯林(Isaiah Berlin)为代表的现代现实主义,乃是现实主义的全新阶段。韦伯为近代以来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诉诸权力支配及其结构化,而不是诉诸自然法、社会契约或公共理性。
事实上,权力结构的特性,以及权力运行的特性决定了个体自由与个体命运。权力结构化和权力的运行自有其规律,在结构化和支配化的权力结构面前,个体的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我们可以把韦伯政治观表述为:“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精英统治不可避免。”一种平等的价值观念何以在一个社会中潜滋暗长进而脱颖而出?这是另外一个严肃的话题。而作为对权力运行特性的反映,“精英统治不可避免”性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对于政治运行自身逻辑的深刻洞察。结构化的权力支配必然呈现出权力的金字塔式分布的特性。
被我们置于末位的福柯,其“技术治理”理论给阅读者造成一种技术治理具有不可避免性乃至不可逆转性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技术治理特性日益凸显的当代,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无奈感。好在权力的运行具有一种“回旋镖效应”。只要由着权力不受控制的增长,总会在某个时刻会出现掉头回转的现象。正是因为这种“权力运行的回旋镖效应”,使得权力的兴衰不断交替。这是修昔底德《战争论》的一个宏大主题,并且构成现实主义悲剧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好处就是“未来不可预期”。正是在这里,面对日益强化的“权力支配结构化”和客观化,个体自由仍然保留着其基本的可能性。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临近结尾处,针对现代性的铁笼已然将现代人套牢这一事实,韦伯用了三个“没有人知道”来表达他对未来的预言: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2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
韦伯这里的预言是针对着政治正当性的三种类型有感而发。“新的先知出现”对应着着魅力型权威的再临,“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对应着传统型权威的再次主导,而“这个废物”“机械的麻木僵化”的“铁笼里的生活”对应着法理型权威的全面宰制。但是面对历史,明天的人类政治到底会走向哪里,韦伯的回答乃是“没有人知道”。
在权力中心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中,个体需要在权力结构中,以及为权力而斗争的具体活动中获得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开辟自己对于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因此,个体自由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希腊智者的“权力即真理”的表述当然是张口即错(即现代人所说的“政治不正确”),但其初始意图乃是为了刻画人际互动模式中的“权力的优先性主题”,为了捕捉推动人类政治活动的真正动力。权力相对于什么具有优先性?权力相对于真理和正义观念具有优先性,相对于人的潜能的可能性具有优先性。现实主义主题得以确立并不断升级,源头正在于古代希腊的智者运动。清源正本,方知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