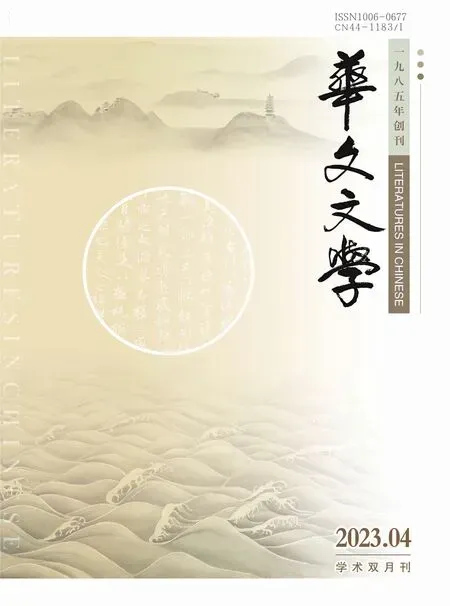欧丽娟《大观红楼》研究理路探析暨对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反思
施文斐
一、阶级分析之于红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行其道到现如今在学术领域中的淡出视野,“阶级分析”已然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变得颇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事实是否果真如此?“阶级分析”是否已然随着特定时代语境的逝去而毫无价值可言?台湾学者欧丽娟《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以下简称《大观红楼》)的批评方法论告诉了我们相反的答案。
面对着丰厚的红学研究成果,欧丽娟曾感言道,“唯个人深深感到,在如此之异彩纷呈的多样研究角度与丰富的研究成果中,似乎仍然缺乏一种比较切近于作者与作品之特殊阶级的视野。”①《红楼梦》“具有极其罕见的贵族阶级特性,许多情节中人物所言所行的基本意义,都必须在其特有的生活规范与意识形态下才能获得正确的判断。”②而意识形态正是由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并进而决定了成长于这一阶级中的人物的生活惯习以及心理感受、价值理念、思想信仰等精神世界的一切层面。诚如脂砚斋所评,“《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第十六回眉批)小说虽说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但同时也具有“文本的历史性”,是在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基础与阶级文化规制下进行的“合情合理”的艺术虚构。真正好的读者,当然也包括批评者在内,首先应做的就是借助于判定作者的阶级属性以把握作者所秉持的并进而贯通于作品中的意识形态,从而努力贴近作者与作品的精神世界。这是读者,尤其是批评者所应有的批评自觉。否则,一切解读都只能是“误读”。
那么,就《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而言,作者与小说的阶级属性又是什么呢?何以阶级分析在《红楼梦》的解读中变得如此之重要?欧丽娟认为,这是因为《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货真价实”③、“空前绝后”④唯一描写贵族生活的小说,其表现对象的极端特殊性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平民阶层的认知范围与生活经验。用我们今天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平民思维、平民视角轻易地加以类比解读,只会扭曲作者与小说的精神世界,而将这部伟大作品的复杂精神内涵加以简化与歪曲。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欧丽娟廓清了阶级分析之于《红楼梦》批评的重大意义。
在《大观红楼》的“绪言”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将《红楼梦》定位为一部“清代贵族世家的小说”⑤,认为“清代贵族世家”以及“他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正是“理解《红楼梦》的必要前提”⑥。为此,作者花了相当篇幅从外缘研究入手澄清了一般观念对于“内务府包衣”的错误认知,揭示了曹家的阶级属性,是“满汉融合又与皇室密切相关的旗人贵族世家”⑦,把握了“清代贵族世家”的种种阶级特性,包括“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⑧等等,从而建构起了理解《红楼梦》的基本认知框架。
脂批的价值也在确定作者与作品的阶级属性时得到了重估。脂砚斋的评点,如“余观‘才从学里来’几句,忽追思昔日形景,可叹。”(第七回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第十三回眉批)“实写幼时往事,可伤。”(第二十回夹批)“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第二十五回夹批)“况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第七十七回夹批)凡此种种,都在在表明了脂砚斋是与曹雪芹有着相同出身背景的人。当《红楼梦》最初以钞本的形式在以曹雪芹亲友为核心的北京旗人圈子里小范围流传时,因钞本的流通而连缀、建构起来的这一小众文化圈正是有着相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感的“精神共同体”。他们与曹雪芹所共享的同一阶级文化也正是脂批中一再标榜的“大家规范”、“大家风范”、“大家规矩”、“大人家规矩礼法”、“大家气派”、“大家势派”、“大家规模”、“大家风俗”、“大家风调”中的“大家”,亦即满洲旗人贵族世家。唯如此,脂砚斋才会对《红楼梦》中某些情节片段的素材来源如此了然于心,才会对弥漫于作品中的追忆、忏悔与幻灭感同身受,时时产生“今阅至此,放声一哭”(第三回眉批)的强烈共鸣,才会对崇尚诗书礼法的贵族精神性如此心心念念,时时跳出来对很可能并非同一阶层出身的读者耳提面命一番,提醒他们不可对某处某段的文字轻轻放过,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现代读者正确理解《红楼梦》而言尤为重要。
真正伟大的小说是表现的,而非表达的。诚如脂砚斋所言,“妙在此书不肯自下评注”(第四十九回夹批),《红楼梦》从不会像深受传统书场文化影响的话本小说那样,总是借说话人之口喋喋不休地自问自答、直接阐发观点,而是让文字自己发声。然而,受限于“时代”与“阶级”双重隔阂的现代读者却也因此而对小说中的关节处视而不见,或完全不明就里。此时,若有与曹雪芹有着“近似的生活背景与意识形态”⑨的脂砚斋作为小说家的代言人出场,将隐含于文字里层的专属于那个特殊阶层的意识形态的点滴表象提点出来并阐释清楚,确实有助于现代读者贴近小说所特有的阶级文化语境。也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欧丽娟认为脂批“具有文化内涵、阶级特性与意识形态等等高度的可靠性与权威性”,为现代读者“指点了正确理解红楼梦的宝贵视角”⑩,即从贵族世家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把握《红楼梦》的思想主旨。
站在贵族世家的阶级立场之上,从贵族世家的意识形态出发,当我们立足于这一研究视角重新审视《红楼梦》时,就会发现曾一度流行且现今仍具有相当市场的一些“权威”观点现出了穿凿附会、不堪推敲的荒谬本相。如所谓“排满”、“宫闱秘事”之类的政治寓意说,尽管曹雪芹在小说开篇就开宗明义地再三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11],“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12]。但这些宣言往往只被视为作者为了避祸文网而言不由衷的“烟雾弹”而已,而丝毫抵挡不住政治化解读的蔓延。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大肆风行于清末的“排满”说,欧丽娟认为这更是由于不了解清代旗人文化是立足于文化认同而非血缘认同这一基本文化背景而妄下的断言,不过是“以血统差异想当然尔地附会投射”。[13]
针对更具“权威性”,同时也更具影响力的“反封建”、“反专制”之类的主旨说,欧丽娟从富贵叙事、“受享”意识与乐园书写这三方面做了专门论述,以证明作者对其所属阶级的态度并非是“今天出于现代平等意识所以为的嘲讽和批判,而其实是渴慕与眷恋,以及失去之后的追悼与哀挽。”[14]在这里,借助于《红楼梦》与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类比,欧丽娟令人信服地追踪到了《红楼梦》“追忆文学”的基本特质。诚如普鲁斯特所言,“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并“以一千种方式重复这一想法”。[15]“失落”正是“追忆”、“追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而“忆”与“寻”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渴望复现昔日荣光的冲动。这种冲动无法在行动上付诸实践,便只能在虚构的重温中获得满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现实的痛苦,尤其是当此种“失落”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之时,如不肖子的逃避家族责任,“失落”所引发的痛苦更会转化为反躬自省的忏悔与自责,并最终生发出“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16]的幻灭与无常。诚如脂砚斋所评,“每阅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阅看完,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第二十六回夹批)《红楼梦》是在浓重的追忆与悲悼中写成的血泪文字,充满了对往昔贵族生活的无限眷恋,以及恋而不可再得的忏悔与自责。那么,《红楼梦》又何谈对于自己所属阶级的“叛逆”?又何谈所谓的“反封建”、“反礼教”呢?
在这里,欧丽娟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将小说人物的声音直接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曹雪芹必然会对贾宝玉偏离正轨的某些言行持肯定态度,不要上纲上线地认定贾宝玉偏离正轨的某些言行就是在“反封建”、“反礼教”。诚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言,“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只能是“一天一天地从所有选项中选择当下看起来是最好的一个”,而不能强求小说家,也包括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成为“回顾历史构建制度合理性的思考者。”[17]相反,我们应该说,“《红楼梦》非但没有反对封建礼教与贵族阶级,甚至恰恰是出于对贵族生活的眷恋,因此反过来对其末世光景深感痛心,并为其终究没落破亡而唏嘘叹惘。”[18]
二、主旨阐释与意识形态的结盟:从《红楼梦》的经典化谈起
《红楼梦》的主旨阐释中时常充斥着一些权威性错误认知,诸如“反封建”、“反礼教”,控诉压制青春与爱情的封建专制,为封建贵族阶级必将走向没落敲响了丧钟,贾宝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勇于反抗的林黛玉是封建专制下的牺牲品等等。然而,“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19],“以今证古”的逆推思维充其量不过是离题甚远的自说自话而已。即便如此,我们仍不禁要将问题进一步追问下去,即上述所说的这些权威性错误认知究竟从何而来?又何以具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我们将不得不从《红楼梦》的经典化谈起。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最迟从乾隆后期始,《红楼梦》就已然冲出了北京旗人的小众文化圈而在社会上大肆风行,“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20]虽风靡若此,作为小说文体的《红楼梦》却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文学等序中占据经典地位。即便在曹雪芹的亲友圈中,曹雪芹也是以其“诗才”而受到推崇。在其亲友的相关诗作中,丝毫不曾涉及到《红楼梦》这部旷世之作。
应该说,《红楼梦》的经典化要一直追溯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维新与革命的交替激荡之下,梁启超标举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西方小说观念的涌入为小说颠覆传统文体等序提供了时代机遇,“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仁学》)这一清末特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激烈立场也成为了此后社会革命思想的基本质素。“五四”继之而起,并进一步地以西方价值观为圭臬,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站在“二元对立”这一简单粗暴却也直截了当的认知观上,通过反“传统”以为“现代”赋值,通过反“社会/群体”以确认“自我/个体”的正面价值。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无价值化。
美国汉学家高彦颐认为,“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评本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21]正是在这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运动中,“反传统”、“反封建”、“反专制”、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婚恋自主、追求自由、崇尚叛逆等现代理念横空出世,在激烈地冲击着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深层地重构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语境,建立起了一整套与传统迥然有别的现代意义上的阐释理路与批评话语。也正是在这一新视域的关照之下,诞生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焕发出了颇具超前意味的现代性,其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开掘。从富于自然主义色彩的“写实”,如“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到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社会写实”,如作者“有意地应用写实主义”[22]以描写当时的世态,再到现实批判主义层面上的“社会批判”,如“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23]等等,《红楼梦》在“五四”史观的审视与重构下已变身而为涵盖了“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等“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24]的社会批判小说,《红楼梦》也因此而成为了在思想主旨上契合并成功诠释了“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
应该说,《红楼梦》的经典化得力于“五四”,《红楼梦》的主旨阐释更在“五四”史观的关照下实现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再度结盟,并因“五四”之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而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更因其在深层的精神内核上契合了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价值观而在现代社会根深蒂固、大行其道。
在《红楼梦》批评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如针对第六十三回贾宝玉给芳官改装并改名为“耶律雄奴”时发表的那一通歌功颂德的言论,如“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生平了”[25]。有评论者认为,这些言论不符合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如此看来,贾宝玉岂不成了美化清王朝的吹鼓手,哪还有一点叛逆者的影子?”[26]然而,与曹雪芹有着相同的阶级出身背景,共享着同一意识形态与文化记忆的脂砚斋却认为,“《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第十六回眉批)。欧丽娟也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并指出诸如此类或借叙事者之口,或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的“歌功颂德”之辞在《红楼梦》中远不止这一处。欧丽娟认为如果从贵族世家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会发现“此一恪遵君父伦理的心态不但合情,也十分合理”[27]。那么,通行于《红楼梦》世界中的“情”与“理”到底是什么呢?其“情”、其“理”应该“合”的是滋生于旗人贵族世家这一阶级属性下的意识形态呢?还是必然与深受“五四”文化洗礼,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人的现代思维保持一致呢?我想答案不言而喻。事理如此之显明,但吊诡的是,我们现代读者,往往也包括批评者在内,却总是直觉般地更倾向于认同后者并以此为据而轻下种种断言。当此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自省到我们其实很有可能是在毫不自知的情形之下就将现代价值观强行投射到了古人作品中,一厢情愿地认定古人应当以我们的价值观来写作,认定诞生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贵族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现代人的“反传统”加以生动注脚,于是将其中能拔高到“反传统”、“反封建”思想高度的经典人物、经典情节视为“有价值”,将无论如何也无法整合进现代价值观中的内容则一概简单粗暴地斥之为“封建糟粕”,并用“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之类似是而非的说辞轻而易举地一笔带过呢?试问此种解读方式本身难道就不是用平民立场对贵族叙事妄加断言的“阶级局限性”,用现代价值观对贵族世家意识形态妄加曲解的“历史局限性”的生动注解吗?
的确,“阶级”的概念在现今的平民社会中已然变得十分淡漠,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将“阶级”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唯阶级论”与无关阶级的“普遍人性论”都有着将文学“扁平化”“简单化”的危险。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则因滋养于现代平民社会的民主精神而趋向于认定“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并进而毫不迟疑地,同时也是毫不自知地径直以现代人的现代思维、现代价值观逆推古人。其实只要稍加思想就会明白,二百多年前生活在盛清时期的旗人贵族世家的贵族少爷的所思所想怎么可能会与现代人的现代思维保持一致呢?我们现代读者又怎么能够要求对自己的贵族阶级文化无限自豪且无比眷恋的作者其创作主旨应当符合、迎合、契合我们的现代价值观呢?
当然,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只怕也会有一千个《红楼梦》,这正是读者的阐释权力所在,原也无可厚非。而且,恰如读者接受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文学作品无法自动产生意义,只有在读者的阅读、思考与诠释下才会发出光芒。因此,读者的诠释与作者的创作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读者的诠释权在被合理化的同时,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弱点,即“人们只看到他所愿意看到的东西”也随之被合理化了,而这将会进一步地导致读者诠释权的被滥用。恰如鲁迅先生所言,“《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确乎如此。有多少读者在解读《红楼梦》时能自觉地站在学术立场上“充分估计《红楼梦》的作者生平、家世的复杂性”[28]呢?在一味地放纵个人爱憎好恶的同时,一千个《红楼梦》就这样被解读了出来。但,这一千个《红楼梦》是否都具有价值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而在现今的红学研究领域中似乎就有这么一千个《红楼梦》。尽管每年都会因各种意识形态的介入而层出不穷地催生出大量五彩纷呈、炫人视听的红学研究著作,但其中又有多少能够深刻地认识到《红楼梦》阶级文化属性的极端罕见,并以此自觉姿态真诚地切入到作者与小说的精神世界的呢?其中又有多少或出于习焉不察、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地将某种意识形态投射到《红楼梦》之上,并在因之而建构起来的新叙事层上自问自答、自说自话,在学术的外包装下自娱娱人、名利双收的呢?“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纵观红学研究领域中丛生之种种乱象,长此以往其结果只能是在自以为是的自信与毫不自知的无知中再一次地巩固自己既有的认知与偏见,再一次地偏离科学精神与文学立场,而无助于真正学术层面上的红学研究。
三、索隐本位?文学本位?——“实证红学”的价值重估
余英时先生曾就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做过专门论述,认为“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通俗化与歪曲”[29]。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进入传播领域,意识形态之于文学批评的介入就几乎是不可避免、无法阻挡的,尤其是现今消费文化与网络时代的双重催化更使得红学的学术殿堂变成了“人人都能成为红学家”的大众狂欢场所。意识形态阐释是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每经过一次意识形态的洗礼,就会生成新的阐释空间,从而使得诞生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古老作品得以在“新解”“新论”“揭秘”“闲话”“趣说”等名目下焕发出时代生机。而《红楼梦》似乎也天然就具备了“迎纳”各种意识形态阐释的巨大文化空间,从长盛不衰的政治意识形态到现如今诸如“职场红楼”之类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红楼梦》已然成为了一种具有强大号召力与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只要能将某种意识形态成功地编码进《红楼梦》并建构起一套自圆其说的阐释体系,那么,至少会收获到一段时间内的媒体关注度与网络热度,在为某“新解”、某“新论”带来社会效应与市场回馈的同时,也能让古老的《红楼梦》再度“翻红”,“常解常新”。但此种“双赢”局面下催生出的其实往往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红学,而绝非学术的红学。而所谓“意识形态化的红学”,则总是枉顾《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与思想艺术的完整性,而是“断章取义,按需截取,注彼写此,目送手挥”,其“对意识形态的兴趣超过了对事实、真理的兴趣”,其“功利性目的往往在于《红楼梦》之外”[30]。此种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的典型代表就是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就相伴相生的,虽逻辑荒谬,却总能翻空出奇、骇人视听的索隐红学。
因此,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者总是力求摆脱“意识形态的幽灵”,但从现当代红学的实际演进来看,我们却并不太惊异地发现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索隐红学往往总是与学术的红学/实证红学夹缠不清、难离难弃。如“整理国故”运动时期的胡适因不满于旧索隐派的穿凿附会而将文献学、考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红楼梦》研究中,其《红楼梦考证》因而被公认为“新红学”,亦即学术的红学的开山之作。但诚如学者陈维昭指出的那样,“新红学”在本质上就是“实证与实录的合一”[31]。其中,作为“新红学”核心理念的“实录”,却是史家意义上的,而非文学意义上的,信奉的是“如实记录”与“忠实还原”的传统注经学的学术理念,真诚地相信如果作者把历史本事写进了作品中,那么,读者当然就可以把“作品的历史本事析出,还原为历史”[32],且历史本事与历史事实二者绝然等同,可以互为依据、互证互换,如“贾曹互证”。当此种史学理念与学术路径应用于文学批评时,其实就是“索隐”,即“索解小说中隐藏的历史本事”[33]。胡适提出的“自叙传”说所依据的内在学术理路其实质就是深受传统注经学思维影响的“如实记录”与“忠诚还原”,并在“以实证捍卫实录”[34]的策略下获得了主要基于曹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外观,从而将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的旧索隐派成功地进化成了学术护航、实证保驾的新索隐派,使得索隐红学从此变得更为精致、更为隐秘,同时也更加危险。
继胡适的“新红学”后,当代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于上世纪80 年代初撰文并引发了关于“什么是红学”的广泛论争。周汝昌先生认为用一般的小说学研究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并不是“红学”,真正的红学研究应该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其实质也就是要求用学术的红学、实证的红学,或者说红学中的“实学”来纠正意识形态化的红学。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专注于对作者生平、家世、小说版本、小说评点的实证研究,是真正站在学术立场上的又一部经典力作。但其所秉持的《红楼梦》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35]这一观点依然是索隐旨向的,其所提出的“悟证说”则又巧妙地超越了文献有限性的制约,为红学研究再度滑向意识形态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周汝昌先生提出的探佚学,即《红楼梦》的佚稿研究,则更是在后世学者的继承与发展下变成了“实锤”,并进而催生出了红学研究的又一“分支”——秦学,旧索隐派的清史叙事、宫闱秘史得以在这一重构的新叙事空间中进一步文学化、小说化,踵事增华、发扬光大。
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索隐红学与学术的红学/实证红学之间的夹缠不清,似乎是现当代红学研究难以摆脱的“怪圈”。这引发了有识之士对于未来红学发展走向的严重忧虑,于是“告别实证红学”、“回归文本”、“文本本位”等各种呼声随之高涨,但这里仍有值得进一步辨析的地方,如“告别实证红学”一说。事实上,真正应该告别的并不是实证红学,而是以实证的研究成果为“技术支持”的索隐红学,尤其是索隐红学的核心理念,那种真诚地相信从文学虚构中可以反向逆推出历史真相的“实录”信仰。将实证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本事还原”的错误方向,非要在意义阐释的小说文本中还原出历史本事,这才是索隐红学的问题所在。因此,真正应当告别的是错误的研究旨向、研究路径,而不能归咎于实证的研究方法本身。
此外,“告别实证红学”的呼声在相当程度上也内含了对“以曹学等同于红学”这一研究取向的警惕。这是一种范畴思维上的警惕,展现出的是对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文本研究与外缘研究之间加以严格区分的一种学术自觉。诚然,由于习焉不察的思维惯习以及缺乏足够科学性、严谨性的研究理路,读者,也往往包括研究者在内,总是习惯于在小说人物与作者之间寻找可以使二者同一化的各种蛛丝马迹,与索隐红学夹缠不清的曹学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显现出了其对于红学研究的“危险性”,一些大众认知以及索隐派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曹学是否就因此而对红学有损无益呢?是否就因此而应将曹学,乃至于包括曹学在内的实证研究摒弃于红学之外呢?如若如此,那么,红学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学术研究的应有本色而不会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地通俗化、庸俗化、娱乐化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与“告别实证红学”相关联的还有“回归文本”、“文学本位”的呼声。每当红学领域中的繁琐考证令人无法忍受之时,就总会激发出回归文学立场的反驳。
但“告别实证红学”,尤其是曹学之后的“回归文本”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回归呢?诚然,一些文学作品,如《金瓶梅》,即便对其作者一无所知,也并不会妨碍对该作品的鉴赏与批评,但那仅仅是因为《金瓶梅》极力描摹的是与平民生活相距不远的“市井小人”,而非远远超出平民视野的“阀阅大家”。但《红楼梦》却恰恰相反,对于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贵族小说而言,真正贴近于作者与小说精神世界的意义阐释可并不是靠着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就能够实现的。诚如学者陈维昭所见,“红学的真正危机并不是没有回到文本,没有进行文学性研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这些意义阐释未能真正地建立在对《红楼梦》的作者生平、家世、成书过程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的基础上”,[36]而这一欲“回归”而不得“回归”的尴尬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告别实证红学”所导致的。
那么,曹学,以及包括曹学在内的实证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正确打开方式究竟是什么呢?欧丽娟的《大观红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示范。
通过欧丽娟的研究理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着重于曹雪芹家世背景研究的曹学在探析作者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进而贴近作者与小说的精神世界时发挥了多么重大的引领作用,具有多么重大的参考价值。诚然,建立在考证学、文献学基础上的曹学本身固然不可直接等同于小说文本研究,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红楼梦》确实又多方面内含了考据实证的巨大文化空间,曹学并不见得就比传统的小说学、文艺学更外缘于小说文本的意义阐释。因此,即便站在《红楼梦》的文学立场上,历史学的参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无曹学的指引与启发,采取历史学的路径以掌握《红楼梦》独特的阶级特性,又谈何容易?”曹学的引入,恰恰“在作者的考证上,让我们更能精确地掌握到其所在罕见的特殊阶级性”[37],而这正是曹学之于红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曹学应用于红学的正确路径,“只要不过度穿凿附会,实能对《红楼梦》的理解有很大的助益”[38]。
由此推演开来,“阶级分析”介入红学的路径也是如此。之所以引入“阶级分析”,为的就是更为精确地把握作者与小说的意识形态,从而努力贴近《红楼梦》的精神世界,而绝非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研究旨向;同理,“意识形态分析”同样应立足于小说文本本身,而不是将《红楼梦》加以意识形态化的发挥,使其成为某种思想或某次运动的生动注脚。
综上所述,对于《红楼梦》这部有着罕见阶级属性与浓重自传色彩的贵族小说而言,阶级属性、意识形态、曹学的介入都是理所必然、势所必需的,重要的是,当以何种旨向、何种路径被引入红学。将科学考证与实录还原剥离开来,以文学立场取代索隐旨趣,通过曹学等实证研究做尽可能忠实于作者与小说精神世界的意义阐释,而不是在小说文本之外再建构起一个耸人视听的新叙事层,这一研究旨向的确立虽相较于文学化、窥隐化、娱乐化的索隐红学缺乏足以激动传媒大众的种种噱头,但却有助于真正从文学立场与学术层面上深化红学研究。
一直在索隐旨向与实证方法之间纠结、苦恼,自称“愈研究愈糊涂”的红学大家俞平伯先生曾有言:“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迷,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迷,亦类乎迷,不过换个底面罢了。……有些问题,若换一个较聪明,较合理的看法去看,早已不了了之,不解自解了。”[39]这段发表于上世纪20 年代的自省文字对于今日的红学研究想必也同样地发人深省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时代主潮永远引导着《红楼梦》意义阐释的方向。《红楼梦》意义阐释的命运永远掌握在时代主潮的手中。”[40]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大批判运动、伴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主体性思潮、新时期的国学热以及网络时代催生的文化消费主义等等,各种流行或曾经流行的意识形态都曾在《红楼梦》的阐释史上拓展出了属于自己的阐释空间。与此同时,也无数次验证了《红楼梦》自身具有切入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说“阐释维度”的强大边界性。应该说,所有这些主导于时代主潮的文本阐释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显示了阐释者的阐释权力,也是小说文本几乎难逃的历史宿命,但意识形态的介入首先要以尊重作家的创作本意与小说的艺术完整性作为前提,否则难免就会有“六经注我”、“过度阐释”的偏颇出现。[41]正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欧丽娟《大观红楼》研究理路的深层解析,尝试探知如何突破现当代红学研究中的“怪圈”,即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索隐红学与学术的红学/实证红学之间始终夹缠不清的深刻启示与实践路径,以期有助于真正从文学立场与学术层面上深化红学研究。否则,红学研究终将在意识形态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3][14][15][17][18][21][27][37][38]欧丽娟:《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3 页,第46 页,第83 页,第44 页,第3 页,第4 页,第41 页,第4 页,第8 页,第8 页,第150 页,第150-151 页,第157-158 页,第19 页,第179 页,第16 页,第149 页,第59 页,第59 页。
[11][12][16][25](清)曹雪芹著,(清)脂砚斋批评:《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凤凰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页,第5 页,第4 页,第499 页。
[19][苏联]伊·谢·科恩著:《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佟景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版,第54-55 页。
[20]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57-358 页。
[22][23]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28 页,第49-50 页。
[24]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版,“写在卷头”。
[26]周中明:《强烈呼吁出版界:还曹雪芹的〈红楼梦〉好读易懂的真面目》“古代小说网”公众号,2018 年10 月3 日。
[28][30][31][32][33][34][36][40]陈维昭:《红学·学术·意识形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35 页,第7 页,第43 页,第85 页,第75 页,第157 页,第35 页,第53 页。
[29]余英时:《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明报月刊(第200 期纪念专号)》1982 年第8 期。
[35]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燕京学报》1949 年第37 期。
[39]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现代评论》1925 年第1 卷第9 期。
[41]施文斐:《京旗贵族族群视域下的“脂批”与清宗室评红文字探析——兼及〈红楼梦〉的主旨“还原”》,《满族研究》2020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