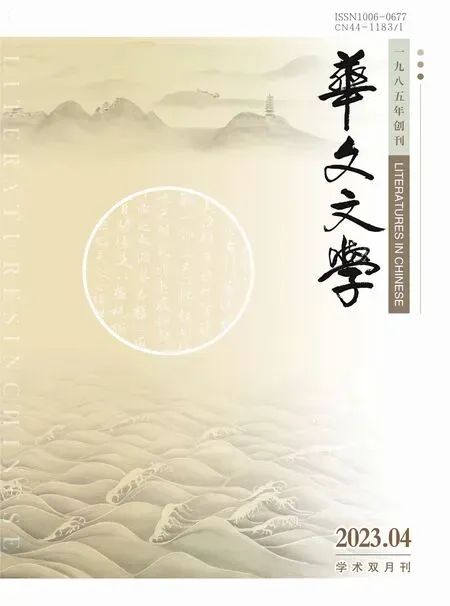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多种离散语境中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
黄万华
研究华文/华裔文学,常取的一个角度是“离散”,但离散的语境是复杂多样的;现在常谈的一个话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例如近年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涉及此话题。而这不应侈谈,文学与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文学创作实践的课题,要具体考察“共同体”(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非“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①,反映出其成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份认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产生、变化、发展。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就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对象。
一
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往往和离开家园迁徙、流落的经历密切关联,而族群、个体“背井离乡”迁徙状况不同和落脚(扎根)之地的离散环境相异,会产生多样的命运共同体认知。
首先是离散族群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华人作为离散族群漂流海外,往往会“以庙宇最先登陆上岸”,以故土的“神明”安定初涉异乡的心灵;之后,会以“会党的、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等等”组织聚合起散落的华族人员,以传统的人际关系重建异域环境中的华族社会;再后,会以创办华校、出版华文报刊书籍等方式来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香火”,以维系离散族群在异国他乡长久不“离散”的命运②。由此产生的华文文学承担起了表达这种进程及其心声的责任,诞生了大量异国他乡“灵根”落地生长的作品,离散族群命运共同体意识由此生发。而这种异国他乡“拓荒”之初安心托身的生存状态,正源自汉民族祖先“立国建邦”的历史。
不同于汉民族祖先“立国建邦”历史进程的,是作为离散族群的海外华人要参与的“立国建邦”,往往是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是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还是已有数百年现代国家制度历史进程的老牌国家,华人都面临与其他族群(原住族裔、主导族裔、少数族裔等)关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需要共同的价值认同才能同心勠力“立国建邦”,于是产生超越族群(政治文化)的命运共同体认知。
超越族群的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发生因时因地而异。华人离散海外,大多出于谋生、发展,也有产生于交流。离散之地,有原先生产力、商贸等较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也有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华人或与当地其他民族一起展开民族独立国家的创建(如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即便是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其建国也是华人与马来族、印度族等一起完成的),或侧重与其他少数族裔(如欧美等各国)一起表达诉求,健全、丰富所在国的制度、文化。超越族群的命运共同体认知由此产生,它依然包含民族意识,但它发生在华人参与所在地现代国家建立、发展的过程中,已“不是业已存在的民族表达的情绪,它是在创造以前并不存在的民族”③,从而发出的是与他族共同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心声。这在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就能听到。例如马华文学中,海底山(原名林其仁,祖籍福建,1910 年代就读新加坡华侨中学)的中篇小说《拉多公公》(1930)最早书写华人和马来人生活于同一块土地而产生的共同命运感,其引人注目的是将受中国1930 年代左翼文学影响的南洋新兴文学的革命思潮和“家南洋”的马来亚本土文学追求结合起来。小说在浓郁的南洋风情中展开浪漫主义想象,从马来领袖拉多公公的视角展开叙事,为了改变殖民地马来亚的命运,他与华人三保公结拜兄弟,马来人和华人都作为南洋子民,共同兴邦建国,华族和马来族被描述为反对殖民统治、建设马来家园的命运共同体。拉多公公曾和三保公一起创立了“相亲相爱,相助相勉”,无“内乱”,也无“外扰”的“仙乡”,后追随如来佛修炼百年,当他重回故乡时,当年的“诗样美满”荡然无存,浮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幅英、荷、法、日殖民者巧取豪夺的场景:资本的扩张,对“民族革命”的严厉镇压,让马来人、华人都沦为被奴役者。拉多公公终于明白,“这仙乡之破灭,人民之痛苦”的原因何在,马来族、华族都是被殖民者、被压迫者。他和三保公再次联合,开始第二次“开天辟地”。
当《拉多公公》从马来族人的视角展开叙事时,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英、荷、日殖民者纷纷向归乡的拉多公公报告他们的“伟业”时,一位“和三保公来至此地”的华人也“很自得地很快乐地”加入了报告者的行列。而恰恰是在他“正说得意高气扬时,忽然雷鸣似的骂声、怪叫声在人丛中发出,全座骚然”。这揭示了一个事实:东南亚华人与居留国“本地人”(原住民或比华人早抵达的其他族群)的关系。东南亚华人有经商传统,西方殖民者往往利用华商作为中介者,与“本地人”打交道。这种参与殖民帝国经济管理的活动,造成了华人社会内部身份的差异,形成殖民者与华人、华人与当地其他被殖民族群、华人之间等多重(反)压制/利用关系。当年的马来亚华族,一方面和马来族等具有反殖民的共同价值认知,另一方面又在经济活动中与其他族群发生复杂关系,其中包含现实政治、经济等冲突。在反殖民统治背景下形成的超越族群(政治文化)的命运共同体认知仍会面临种种族群间的利益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思想恰恰是在这种不乏曲折、艰难的过程中产生的。
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认为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的“精神共同体”④,有着文化、伦理道德的认同。没有文化层面、伦理道德层面等共同的价值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难免沦为空谈。海外华文/华裔文学正是在对人类共同的价值认同中表达出华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例如,自然生态文学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都发生得较晚,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1970 年代就初露端倪,1980 年代提出了“每天细细听听地球的声音”⑤的文学命题,从马来西亚的潘雨桐、田思、何乃健、陈慧桦、沈庆旺,新加坡的王润华、陈瑞献、淡莹等,到北美的非马、张让,大洋洲的胡仄佳等……都较早或持久地投入自然生态题材的创作,于其中推己及物,返物于人,反省自身,认同世界。这中间的线索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寻求。这里可以考察一下在海外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中最有成绩的潘雨桐,他是“华文作家中极少数长期关注婆罗洲雨林的生态破坏、原住民、非法移民、少数族裔妇女被剥削迫害等议题者,在地长驻”⑥,其作品被马华文学界视为“有资格成为经典文学”⑦。
作为马来亚本土出生的第一代华文作家,潘雨桐最早开始了“北漂”“南归”,1957 年开始留学、求职于台湾地区和美国,之后长期供职于马来亚农林界。马来(西)亚、美国都是多移民族群的国家,两地经历的呼应促成他对族裔关系、殖民后殖民等问题的思考。他1970 年代开始创作的取材于留美生活的小说,或写东西方不同的亲情、人际和不同族群间的友情,如《冬夜》《月落泽西城》等,或写不同国度(马、越、印尼)“卑微的被国家抛弃”的华人再离散的遭遇,如《乡关》《烟锁重楼》等……这些小说都充溢离散群体对命运共同体的渴望和追求。返马后,他长期在东马驻地写作,深入到马来亚社会内部的族群关系,如《野店》展示了“西马”人如何如“渡海过来的大白鲨”,吞没着东马富饶的资源,直面了诸多“东马”议题,从华人与原住民、少数族裔妇女,到乡土、殖民和后殖民创伤,从而表达出对不同族群边缘、弱势人们的深切关怀。而东马丰富的自然资源被疯狂掠夺,尤其是热带雨林被毁坏的现实,让潘雨桐在家园意识和专业背景双重影响下,开拓出自然生态的题旨。这一题旨,在海外华人离散的命运意识中有特殊重要意义。华人迁徙、飘落海外,往往出于谋生,其主要方式是索取自然的拓荒生涯,这对外来移民是严峻考验:他乡土地如何视同故乡,如何如珍惜故国家园般去珍惜刚踏上的异域土地,人生存中如何不逾越“戒杀”之限?当潘雨桐真切地探索这些问题时,他原先从马华社会的“内部眼界”去展开多议题(乡土、族裔等)“深度描写”的视野有了新的提升。
小说《热带雨林》中,回东马雨林养病的生物系学生叶云涛挣扎于叙事明暗双线的压力中:与菲律宾女子伊莉的雨林纠缠与开伐雨林家业的父亲冲突。叙事明暗线的汇合最终暗示出,他在雨林百年巨树树冠纷纷倒下的震撼中,要与父亲分道扬镳,告别传统“靠山吃山”、“养家富国”的人生哲学和持家、经营方式。《大地浮雕》在山林流浪儿阿祖为了生存,加入伐木者后的遭遇中,要寻找的是人的心灵对自然家园的敬畏之心。后来,他更是自觉创作了一系列东马沙巴京那巴登河岸热带村落的小说,《山鬼》《河岸传说》《河水鲨鱼》《沼泽地带》……一则则雨林传奇在他的长年在地体验中被讲述得极为真切,“生畜繁衍,五谷滋长,四时季令,天地阴阳,谁要是颠倒了,必遭天谴。”⑧人的私欲与雨林自然冲突的巧妙组织都指向了“林毁”必然“人亡”,无论是雨林原住民,还是外来经营者,都无法摆脱这一命运。只有克服人的私欲,抱有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才能拯救人类自身。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是海外华人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存之道。
潘雨桐这种创作轨迹,也留在不少马华作家的笔端下,“太阳底下,我们与万物共存共生,这么相亲的”⑨日常生活,成为马华文学描绘的最重要图景⑩。更多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将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谦柔、佛家的慈悲揉和而成的爱物思想扩展为在华族海外历史和作家自身生命经历中体验到的世界家园意识。而这也启发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人类在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生死与共,有了人类生存层面上的价值认同,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当今华人越来越多地迁居世界各国,中国也越来越多地需要世界各地自然资源来发展国内经济,此时,视他国土地为自己家园,以自由的心灵去感受自然,保护家园,异乡如同故土,惜物如同仁民,就是海外华文/华裔文学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最好的回馈。
二
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发生在近百余年世界历经一战、二战、冷战及其后的历史进程中,那是世界性离散文学多样性的年代。有种族迫害而流浪形成的离散型,如犹太离散文学;有奴隶贸易和劳动力流动引发的离散型,如非裔离散文学;有(大规模)政治流放而形成的离散型,如俄裔离散文学;有与国家政治、文化政策密切关联的离散型,如美国离散文学;有不同(东西方)文化自觉交流中发生的离散型,如欧洲离散文学。在此世界背景下大规模、多流向的华人海外迁徙兼有了世界离散性的多种情况,包括劳动力流动(其差异大,既有大规模劳工潮,也有不同时期的个人谋生出走),战乱、政局变动中的流放(既有群体性的迁徙,也有个人的自我流放),自觉的文化交流(既有留学潮那样的群体性交流,也有文化、艺术等的个体活动)等等各种情况。离散型的差异,影响着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寻求、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发生影响的是所居住国度(华人国籍加入国)对待华人文化的(国家)政策、(社会)态度。这使得华人(华文)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一是无国籍文化身份,这往往发生在华人受国家文化政策压制,华文被排斥于国家文化之外的国度和时期。二是少数族裔文化身份,三是国家文化身份,华人少数族裔文化如果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会和其他少数族裔文化一起,争取进入国家文化。
考察百余年海外华文/ 华裔文学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晚清—五四时期的华人留欧文学,二战时期的美国华侨文学、马来亚华文文学、战后时期的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文学、1960—1980 年代台湾、东南亚华人留美(再离散)文学、1980 年代后的新移民文学,分别提供了中西文化冲撞时期、大规模移民时期、外来侵略时期、独立建国(族群关系)时期、全球化和自然生态时期等不同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达,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乌托邦愿景,而是离散者(族群、个人)付诸于实践而寻求(到)的人与人、人与国家(族群)、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开辟出文学境界,甚至抵达了“真三”的境界。
我们以早期海外华文/华裔文学[11]为例,考察一下不同时代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
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最早也最持久地发生在晚清—五四时期的华人留欧文学中。从晚清陈季同开始,到五四后的盛成、蒋彝、熊式一等,直至战后的程抱一等,他们旅欧创作具有了华裔文学语境的三个要素:采用在地国语言(英、法、德文等)创作;面向欧洲(外国)读者写作,其传播、影响主要(或首先)发生在在地国及相关国家;融入了在地国的文化因素。在晚清开启的中西文化冲撞时代,他们抱有自觉、平等的文化交流意识。陈季同是最早旅欧写作的中国人,当时发生了中法战争,黑旗军的“可怖形象”还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而陈季同的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 年)、散文(《吾国》等,1892 年)、戏剧(《英勇的爱》,1904 年)都让法国人看到了“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12]。而到了五四前后,众多旅欧华人的写作使欧洲文化界人士对欧中文化交流的看法也变得自觉、积极:“十九世纪的末年与二十世纪的初年,我们见欧洲与中国最激烈的交锋,也可说东方与西方最激烈的接触,中国是东方的代表。这种冲突之后。我们可以期望有互相融解之一日。此日乃世界广含光明之一日,此日乃人与人非狼与狼相视之一日”,“这个伟大的民族维持一种千年来有统系无断续的文化”,“中国人与我们,各掌人类一半的历史,假如历史是一件不可埋没的事物!”[13]中欧双方都对文化交流抱有自觉、平等的心态,甚至超越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隔阂。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欧华作家“不断地在其本源文化积淀中最精华部分和‘他者’提供给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间去建立更多的交流”[14],从而获得的是民族文化生命“大开”的提升。一批成就了真学问、大创作的旅欧华人,尤其是程抱一,以持之以恒的努力,让直接承受的异族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转化成让中华文化传统中人类性、世界性的因素更多地显露、激活的力量,其作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把中国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15],在生命的本质、美的本质等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上把握了“本源”和“他者”两者的精华,并予以深度“交流”,极大地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人类性魅力。中西“异而不背”,让“异而不背”在互渗、互补、互通中揭示人类共同命运,成为早期欧华文学的主旨。
二战(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华人在多种不同地区(中国大陆正面战场、敌后抗日地区、日本占领区、欧洲战场、东南亚援华地区、太平洋战场等)参战,这些地区的华语文学所表达的灾难意识(对战争灾难根源的认识、对制止战争力量的寻求)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民族共同语表达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而对于海外华文/华裔文学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二战前,东南亚和北美都已有大规模的华人移民谋生活动,但华人移民或受排斥(如美国),或与当地社会关系缺乏“家园”纽带而“疏离”(如东南亚)。当二战蔓延于世界各地,此时的海外华文文学,和战争灾难中的祖国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指向了华人与在地国的关系。
在美国,华文文学是以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华侨文学”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历程。1940 年,正是在美国侨胞“比任何时期更为热烈、更能一致”地投身“抗日运动”的背景下,建立“以华侨生活为本位,以华侨社会做背景,用报告文学或小说体裁技术”的“华侨大众文艺”的主张[16]被正式提出。此后,“民族主义文学+西洋民主思想”的“华侨文学”,即全面抗战爆发后,“流亡海外,尤其是美洲”的中国文化人士,与当地“接受新兴的西方的民主思想洗礼”的华侨汇合[17],产生了“对于数千年世代相传的自己祖国、自己语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之热爱”,更“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时希望世界人类优秀的理想在自己国内实现,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18]的美国华人文学得以展开,其中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鲜明而强烈。1941 年美国对日宣战后,留美华侨纷纷参战,一些从军的华侨更是远戍于中、印、缅战区,他们创作的二战华人军旅文学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息息相通中书写了中美共同命运的篇章。
而在支持、参与中国抗日最积极的海外地区东南亚,尤其是马来亚,尽管开始华人社会还往往从“如果中国战败,会直接危及华人在马来亚的生存”来认识东南亚救亡文学和中国抗战的关系,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展开,不仅仅将“抗日”看作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更将其置于世界民主阵营和五四反封建传统中,将马来亚(东南亚)华人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紧密联系于世界和人类共同的命运,成为马华抗日救亡文学两种最重要力量——马来亚本土作家和中国南渡作家的共识。当时的报章主张和作家创作都表明了这一点。等到二战结束,华人更是从日军占领三年多的遭遇中“深深体验到”,“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才能“避免遭受另一次被侵害、被掠夺的灾难”[19]。华族作为一个整体清晰认识到与其他在地民族同一个命运,可以说始于此时期。二次大战打破了国家、地区、族群间的界限,将人类文明的危机、世界生存的困境推到所有人的面前,这种足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族群冲突等的语境促成了马来亚华人与其他族群共同的价值追求,马华文学才真正开始了它在“他乡”土地上的历史进程。
文化交流和经济谋生,是华人迁徙海外两种主要的动机和方式。从历史情况看,前者较多的是个体行为,后者多为群体移民。两者语境明显差异,但都会在与在地国他族文化相遇、对话中发生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前者的影响主要指向在地国他族,后者的影响主要指向在地国华族自身,由此生发的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互动有了多种形态。
三
华文/华裔文学的区域国别种族文化属性和他族文化相遇、对话,由此生发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互动,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华文明与他族文明两者中超越种族、跨越国度的核心价值(精华)的对话,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二是离散语境摆脱了现实政治文化、体制,尤其是现实意识形态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负面制约,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冷静、深度反省,由此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华”融入了世界潮流,也影响了世界。而这些互动不乏历史的曲折、艰难。
前面述及欧华作家在“本源”和“他者”两者的精华之间“交流”,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海外华人的漂泊性、混杂性、开放性、多元性等在旅欧作家中表现得更为广泛,这使他们的写作既最广泛地承受着种种现代与传统的危机,又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中西文化对话中人类文化发展的各种机遇。旅欧作家中,如最早留德的晚清秀才王家鸿“德文造诣一如其国学般高深”[20]那样学贯中西者众多。而回顾欧华文学,它的中华古典文化始终根深叶茂:一是多元而自由的选择中,中华古典文化的各种传统都得以传承,古典文化的各种学说相互照应,全面呈现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所在;二是无功利的诉求,传统的诠释完成于长期的潜心研究、体验中,古典文化传统得以提升;三是传统的传承成为中西文化相遇、交流的最重要内容,海外直接承受异族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压力的环境,使得中华文化传统中人类性、世界性的因素更多地处于显露、激活的状态,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既主动参照于西方文化传统,又积极汲取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种种成果,由此中华古典文化展开了既向现代“转化”,又深刻影响现代的丰富实践。总之,欧华文学中的中国古典文化处于一种不同文化“高度交流”的环境,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文化获得一种生命“大开”的机遇,“民族的灵魂”由此在提升中焕发出更多生命光彩。
陈季同晚清旅法,五四运动尚未发生,其海外“在地”写作表现出对中华古典文化的特别钟爱,甚至偏爱。但他自觉于之所以“对过去的传统保持着尊重”,是因为能“在传统中找到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最好保证”[21],而他着眼的“现在和未来”不仅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也是欧洲的“现在和未来”,甚至是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人的自画像》是陈季同在欧洲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就常常着眼欧洲的“现在”来讲述中国的传统。例如《宗教和哲学》一文,从“在人类努力向上帝靠拢的过程中,人性的弱点又致使宗教屡屡下坠”,工业革命、市场化让“喧嚷的世界充满了信仰的混乱”的欧洲从现实出发,强调人类的“智慧和宗教同样高深”,从而展开“教化人心”智慧的孔子学说的描述。在向欧洲民众介绍博大精深的孔子哲学时,陈季同突出“保持适度的理性是孔子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修己以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等“修身方法”是孔子“想创发一个贯通所有良知的普遍观点”的道德实践,其最终指向是“你的灵魂深处一定能体会得到万物平等的法则”的宗教境界[22],从而沟通了与欧洲民众信仰的宗教的对话,发出的是两种古老文明面向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出的“谁谓天下非一家哉?”的感叹[23]。
与陈季同不同,盛成是在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当年,以“五四运动嫡系的延续”勤工俭学[24]的身份来到欧洲。作为第一位双语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旅欧作家,盛成将他1920 年代旅欧写作的结集命名为《归一集》[25]:“归一”,即“人类是一体,人道无二用”,“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文化”,却“仍不能不归于一”[26],都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他的写作,就是要从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来表达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他写《我的母亲》(1928),是以“人人有的”“母亲”、“人人受的”“母教”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本来面目”[27],由此(天下母亲的“归一”)来探求人类的“大同”、世界的“归一”。他写《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932),是要“借英、法、德、意、俄、土、埃及、印度为镜,直照出中国的本来面目”[28],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揭示五四昭示的中国民众的解放之路与世界各国的平等、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意国留踪记》(1937),在“化合了神曲和十日谈的体裁”中,以一种深刻的“内心的介绍”走进“欧洲的精神”,从“知彼可以知己,借镜自照,或能复识”[29]中,寻求中华民族挣脱多重压迫的复兴、富强之路。这种寻求最终指向了欧洲文艺复兴以“生命意识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天地人合一”的生命整体观念的沟通:“以生命为意识以人为主脑而造成的”欧洲文艺复兴正是“天的这里,天的那里;地的这里,地的那里;人的这里,人的那里;都含蓄着”的“生命意识底全自然的大革命!”[30]海外语境使在国内投身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痛击孔子的牌位”[31]的盛成重新认识传统,将文艺复兴“人道的观念,以及人类归一的意义”视为“孔子人道主义的扩张”[32],孔子作为“初期儒家,原始孔教”(非后来的儒教),最应该为当今世界看重的是,“宽容一切的异端学说,以形成人类的仁,即人道。孔子的开明,不但光照出人世的大同,还要启示着宇宙诸神的和合”[33],即人类的“归一”。
陈季同与盛成的创作代表了当时两类中国知识分子,较为纯然的传统文人和经受了五四洗礼的现代青年的海外寻求。在西方世界尚处于殖民扩张,中国又受到列强侵略、掠夺的时期,他们都将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世界、人类的未来视为一体,在“世界大同,人类相通”中表达中国人对民族复兴、个体解放的追求。而他们的作品在20 世纪初的欧洲都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传播效果,为欧洲知识界,甚至欧洲一般民众所知,切切实实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古典文化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国内有过对传统文化激烈批判,乃至全面摧毁的时代,也有过大力倡导,甚至定于一尊的时期。批判时期,“矫枉过正”,传统“断裂”;倡导时期,被推崇的传统会受制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机制,显得单一而至尊,实际上也“断裂”了传统。而海外华文/华裔文学拉开了与中国国内现实政治、经济运作的距离,摆脱现实功利性的制约,其在中华文化与他族文化对话引发的反思中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融入了世界,也影响了世界。
例如,二战结束后,一批中国学子、文化人士陆续赴欧,之后国内政权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化,一些旅欧者难以返回中国,旅欧华文/华裔文学出现第一批定居欧洲的作家。欧洲战后重建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对峙,都使得欧洲社会较难顾及与中华文化传统的交流。而中国大陆与台湾1949年后对儒家等文化传统的态度相异,却都受到现实政治的严重制约。这样一种环境使得旅欧作家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没有任何现实功利性(这显然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旅欧环境),他们往往从内心生发“故国文化与欧洲、世界文化对接”的愿望。法国学者所形容程抱一旅欧后“在悄无声息中默默吸收着西方文化,与此同时,他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本土古代艺术、绘画和诗歌传统的意义”[34],正是战后定居欧洲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写作中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创作成就和影响大的,从1950 年代后的程抱一等到21 世纪的高行健等,都自觉延续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中培育的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即在自我本体的内在动力与外来文化相遇中互相涵化、转化,拓展、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与世界的联系[35],从中华民族历史境遇中提炼出世界语境中的价值精华。
旅欧作家所处的时代使得他们从中华文化传统出发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往往和西方作家从欧洲文化传统出发与“印度之外”“展示了另一种非欧洲语言”“范例”的中华文化[36]的对话,在同一个时空展开,他们的创作真正成了中国与欧洲(世界)双向影响的对话,两种文化的精华(核心价值)相遇,由此建构的价值认同自然指向人类共同的命运。当年,《与友人谈里尔克》(1961-1964)之所以成为程抱一异域创作的重要起点,是因为“里尔克是一位罕有的懂得亲近东方的西方诗人”[37],作为“一位伟大的西方诗人”,里尔克“以基督文化为出发点”,但“在其漫长的求索过程中,介入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了和许多中国伟大诗人相近的人生观”[38]。里尔克引导程抱一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相亲相近、相依相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是如里尔克“穿过死亡,追寻真生”的一生那样,在寻求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根本问题上展开:“人类只有在享受意义时才真正享受生命”[39]。之后,他在与拉康、雅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欧洲思想、艺术大师直接对话中,进入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溯源求本,在其本源文化积淀中最精华部分和“他者”提供给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间建立起生命感受的交流。他用多种方式,从唐诗法译、中国绘画,到中法文诗歌创作、长篇小说,直至美学、哲学建构,展开富有创造力的探求,每个领域的成就都誉满欧洲,乃至世界。这些文学、艺术的表达完美呈现了“中国思想所奉献的理想化的世界观”,如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的“三元思想”[40],在与西方哲学、艺术的对话中提升为一种人类的宇宙观,成为华文/华裔文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绝佳范例。
当以上论析在华文/华裔文学文本的淘洗中展开,多种离散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会成为华文/华裔文学经典性累积的一种进程。这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有意义的。
①④[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54 页,第65 页。
②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的《马来西亚的模式》一节中具体描绘了这一历史过程。
③[英]约翰·布鲁伊:《序言》,[英]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 版》,韩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 页。
⑤王润华:《白鲸之死及其他》,台北《中华副刊》,1989 年10 月14 日。
⑥黄锦树言,潘雨桐:《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版,封面。
⑦黄锦树:《经典非永世不变》,《星州日报》,1996 年6 月9 日。
⑧潘雨桐:《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版,第56 页。
⑨李忆莙:《年华有声》,《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01 年5 月20 日。
⑩马来西亚本土出版的一些文学论著都视“自然生态”为马华文学的重要课题,例如供“高中至大专院校马华文学课的师生”使用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将“生态文学”列为一章。
[11]海外华文/华裔文学的“早期”大致指海外华文/华裔文学发生至二次大战结束初期。
[12]原文载1929 年《巴黎文学新闻报》,转引自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2 年版,第256 页。
[13]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1932 年版,第10 页。
[14][法]贝尔托:《当程抱一与西洋画相遇——重逢与发现(达·芬奇,塞尚,伦勃朗)》,陈良明译,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2 页。
[15]晨枫:《中西合壁: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天一言》,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9 页。
[16]老梅:《华侨大众文艺》,原载《美洲华侨日报·新生》(1940 年7 月17 日)。收入李亚萍编《抗战中的文学崛起:20 世纪40 年代美华文学资料选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33 页。
[17]温泉:《广东文学论》,《华侨文阵》(美国)1944 年第1 卷第4 期。
[18]温泉:《华侨文艺十年》,原载1949 年版“华侨文艺丛书之四”《突围》,收入李亚萍编《抗战中的文学崛起:20 世纪40 年代美华文学资料选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5 页。
[19]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联合会1984 年版,第85 页。
[20]高关中:《推理小说家朱文辉》,《欧华导报》,2017 年1 月7 日。
[21](清)陈季同:《吾国》,李华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77 页。
[22](清)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陈豪译,金城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19 页。
1.人员素质低。基层队伍中,特别是村防疫员大多为临时雇佣人员,年龄偏大,不能独立完成移动智能识读器的信息录入和上传工作,严重影响畜禽标识数据库建设工作的落实。
[23]李华川:《陈季同编年事辑》,见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经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93 页。
[2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盛成文集·纪实文学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144 页。
[25]法文版《归一集》共5 卷,分别为《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与我》《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东方与西方》《归一与体合》。
[26][28]盛成:《我的母亲·叙言》(1933),《盛成文集·纪实文学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 页,第3 页。
[27]瓦乃理:《我的母亲·引言》,《盛成文集·纪实文学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 页。
[29][30]盛成:《意国留踪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7 年版,卷头语,第57 页。
[31]盛成:《我的母亲》,《盛成文集·纪实文学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99 页。
[32][法]弗利德门:《盛成之使命》,《欧洲杂志》,1930 年4 月15 日。转引自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61 页。
[33]盛成:《法译〈老残游记〉序言》,《盛成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65 页。
[34][法国]米勒·热拉尔:《诗与画——程抱一与克洛岱尔》,徐洁译,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2 页。
[35]最早多源流形成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就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同体有着广泛交流互动(可参阅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之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时期,由华夏民族共同体演化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与游牧民族文化、南亚次大陆文化、东北亚文化,乃至欧洲大陆文化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交流。
[36][法]岱旺(Yvan Daniel):《中译本序为何是中国?》,岱旺:《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化(1846-2005)》,叶莎、车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年版,第7 页。
[37]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0 页。
[38][39][40]高宣扬、程抱一:《对话》,张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6 页,第60 页,第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