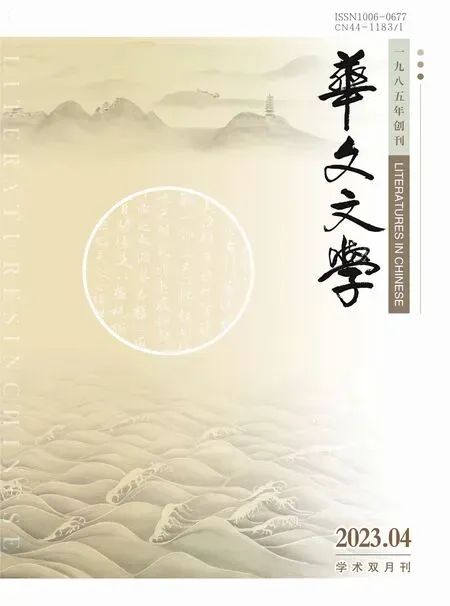从单性人格到两性同体:《瓦猫》中女性成长的现代困境
何琪
近年来,葛亮通过结集成册的“匠传”系列小说把离现代生活较远的一群匠人带到读者眼前,尤其是对几位女性工匠的书写引人注意。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成长经验的阐释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葛亮将女性与工匠身份联结起来,通过书写她们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为文化长河中较为匮乏的女性成长故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伍尔夫曾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①不同于生理性别以性征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心理性别往往表现为两性同体的存在状态。葛亮在《瓦猫》中从工匠、女人和人三个维度来书写矛盾割裂的单一性别气质对人物成长造成的束缚,进而主张融合协调的两性心理同体的性别行为规范,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完满人格也存在着游移不定和边界模糊的现实阻碍。两种性别气质的对立和对话,反映出女性构建性别自我的主体性生成过程,也展现出女性在这一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艰难。
一、束缚:单一的性别气质特征
正如伍尔夫所说,“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分别代表两性心理性别中的主导气质特征,并不存在绝对单一的性别气质。《瓦猫》中的几位女性工匠最初都是以强烈的单一性别特质出现,比如在父亲身边时温顺的女儿乐静宜以及具有“地母”式奉献精神的荣瑞红,二人的女性性别气质占据绝对主导,而凭借自身努力打拼事业的简则是用男性性别原则来追逐梦想的典型。但是,趋向单一的性别气质造成了她们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冲突,体现出单一性别规范束缚下女性成长的艰难与主体建构的困厄,进而产生个体价值的困惑、两性关系上的缺憾以及对命运的失控感。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下,她们展现出复杂痛苦的内心纠葛和悲剧境遇。
普里克认为,“当个体已经掌握了运用与性别相联系的规范的灵活性,容许个体为了成功地适应局面的需要,时而采取女性式的行为,时而采取男性式的行为。”②葛亮曾在文章中表示过对此观点的认同,相比之下,他认为单一的性别气质不利于构建完整的性别人格。在《瓦猫》中,葛亮在表现女性人物单性人格的阶段往往是采用回忆和插叙的方式,相对来说篇幅较小、叙事节奏较快。可以看出,葛亮有意表现《瓦猫》中的女性工匠从单性人格到两性同体的成长过程,前后对比之下更能凸显出单一的性别行为规范对女性的束缚。
(一)规训秩序下的女性性别气质
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③。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处于被动地位,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将对女性的期待转化为衡量女性的标尺,把女性气质归入“自然天性”之中。在这种规训之下,女性性别气质中的男性化部分被长期压制了,久而久之形成了女性天生就温柔、顺从、体贴、脆弱、感性、胆小等性别刻板印象。鲁迅将女性性别气质总结为女儿性、母性,还有被逼成的妻性三种。《瓦猫》中的古籍修复师乐静宜起初是以典型的“女儿”形象出现的,制陶者荣瑞红则是从母性上升为“地母”的化身。
1.“从父”的女儿:乐静宜
封建父权历史中对女性的第一道禁令就是未嫁从父。在“五四”时期,“父亲”权威象征着一种法规,也可以说是家庭和社会的制度④,比如冯沅君的《隔绝》中,女主人公试图用爱情来“弑父”。身为当代男性作家的葛亮则不同,他笔下的“女儿”往往服从性大于反抗性,较早的小说《朱雀》之中就有典型的“父之女”的形象出现。作为封建家族的大家长,父亲叶楚生始终以传统封建观念塑造女儿叶毓芝,在强权的灌输之下,叶毓芝本人也无意识地认同了父亲对自己人生道路和婚姻选择的限制,作为“父之女”的驯化与自我驯化令人悲哀。
《瓦猫》中第一个故事《书匠》里塑造的古籍修复师乐静宜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父之女”这一角色,不同于《朱雀》中父亲权威的直接表达,《书匠》中父亲的理想在潜移默化中移植给女儿,看似和谐温情的父女关系背后却是病态的亲子相处模式。小说中的乐静宜尽管出生在已经高度开放和现代化的香港,但是她骨子里却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气质,这和她的家庭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这里葛亮通过乐静宜的回忆视角切入,从阿妈每月固定“煲老火汤”、父亲“比客厅还大”的书房等只言片语中能够看出乐静宜是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知书达礼的家庭中,这样的环境自然而然将她调教成一个淑女。父母离异后,陌生的父亲更是成为威严的化身,让乐静宜产生本能的服从,于是想方设法地获得父亲的认可和怜爱成为她行为的驱动力。这一心理过程在波伏娃看来代表着女性主体性被剥夺:“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所以,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⑤小说中这一部分的叙述节奏较快,有关乐静宜个人理想的表露更是空白,她只是按部就班、被动地接受着父亲为她安排好的人生角色和道路规划。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说,乐静宜在成长过程中将父亲视作镜像中的自己,对父亲由畏惧产生的崇拜使她将父亲视作自我确认和追求的目标。童年时期与父亲在空间上的距离让父亲形象在乐静宜心中被神秘化和神圣化了,乐静宜最早关于父亲的记忆是他偌大的书房,因此对于父亲产生了强烈的崇拜;后来随着跟父亲的接触变多,父亲以老师的姿态向她传授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打开了她的视野,这时乐静宜对父亲的崇拜是持续加深的。但是这种相处模式也让乐静宜感到费解:“尽管这种亲密似是而非,并不很像父女,更类似某种师生的相处。”⑥父女相处之中的乐静宜处于失语的状态,然而在她生命中时隐时现的父亲却吊诡地决定了她的命运。
相比之下,葛亮在《飞发》中书写的一对父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亲子关系模式:父亲翟玉成是港式飞发师傅,但是儿子翟康然却坚定地拜父亲“对家”的海派理发师傅为师,一时间父子关系极其紧张。然而这种对立和分歧仅仅是在师承上,彼此间深藏于心的爱以及工匠之间的惺惺相惜在小说结尾达到了顶峰,冲突达成和解。葛亮在这一部分倾注了大量笔墨,精彩细腻的书写中能够看到男性人物的成长。相反,乐静宜与父亲则是处在被保护和保护的关系之中:父亲通过传授特定的知识“保护”女儿的思想,又用熟悉的事业“保护”女儿的未来;被保护的乐静宜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弱者的身份,放弃了勇敢坚韧、独立自主面对人生的成长过程。
2.“地母”的化身:荣瑞红
农耕时代的原始先民出于对土地的敬畏而信奉地神,又因其具有母德,于是“母神作为一切生物乃至无机物之母,是她生育出天地万物和人类。”⑦地母精神中所包含的宽厚、悲悯、包容、同情、善良、感性可以说是女性气质中“母性”的顶峰。葛亮的小说中也不乏这种带有救赎万物意味的女性形象存在:比如《朱雀》中的妓女程云和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曾在日军攻陷南京时负伤的洛将军,并且保护其躲过日军的搜查⑧。“匠传”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破题之作《瓦猫》中的制陶工匠荣瑞红,儿子形容母亲“身上是一种淡淡的温暖丰熟的泥味”⑨,这种“泥味”既是终日与陶土打交道的缘故,更隐含了“地母”本质。
《瓦猫》中的荣瑞红生长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南龙泉镇的农村,她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但勤劳朴实,她被葛亮塑造成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荣瑞红的地母精神主要表现为无条件地抚慰男性受伤的灵魂。在《瓦猫》中,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的荣瑞红女儿性是缺失的,与宁怀远始终不“对等”的爱情下妻性也是含糊的,相比之下的母性却被凸显和放大了,上升到“地母”的高度。荣瑞红的奉献和救赎精神主要体现在心上人宁怀远身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才子佳人”的叙事传统。进入20 世纪以来,张贤亮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延续和创新下形成了“落难文人”的新形态,《灵与肉》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许灵均直到与底层劳动妇女李秀芝的结合才走向了新生活。《瓦猫》中虚构的人物宁怀远是闻一多的研究生,而荣瑞红作为云南本地瓦猫工艺的传承人,二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可以说是“落难文人”叙事模式的变形。故事中,荣瑞红成为作者意图表现的精英文化传统和匠人精神之间融汇合流的精神容器,强大包容的地母性显露无遗。荣瑞红一开始被宁怀远吸引来源于农村女性对于知识的崇拜,在一次意外之中她得知宁怀远的孤儿身份,母性的同情与怜悯瞬间被激发出来,她“一把将宁怀远的头揽入自己怀里,紧紧地”,直到感受到“这男人毛丛丛地头发带来的温暖”⑩,她才好受了一些。此后,她对宁怀远“爱”得更深了,不仅仅有男女之间的爱慕,更多的是地母式的怜悯。在宁怀远从战场负伤归来后,她展开了“地母式”的救赎:她将眼前这个因残疾而丑陋的男子接到家里住,为他打石膏、买眼镜,为他生儿育女。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救赎,在她的感染下,宁怀远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葛亮在小说中对于荣宁二人爱情故事的书写远远比荣瑞红学习制陶的内容要丰富动人,因此造成少女阶段的荣瑞红个人成长部分的缺失。故事中“梨树”的意象也暗示了荣宁二人终将背道而驰。在生命的前半部分,荣瑞红把她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给予了这个男人,她也将快乐和幸福全部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两次被抛下的结果是她要独自承担生活中的苦难和精神上的痛苦。葛亮在故事中还嵌套书写了梁林夫妇二人的相处之道,荣瑞红看着“也像男人穿了衬衫和齐腰裤装,举止间是极飒爽的样子”[11]的林徽因充满了羡慕,相比之下,“地母性”却成为紧紧束缚自己的枷锁。
(二)生存需求下的男性性别气质
传统社会往往要求女性放大其女性气质,在看似包容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表面上弱化的规训实际上隐藏着对女性的更高要求。同时,单一的女性气质的确会束缚女性在社会秩序之中实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于是,一部分女性选择以男性性别气质武装自己,这是她们在父权制社会寻找自己定位的开始。但是这种趋向于中性的性别特质往往也会抹煞女性性别特质,有着模仿男性的趋势。比如《书匠》中的简和《飞发》中的郑好彩,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性别气质是在男权社会下与男性平分秋色、解决生存需求的必然选择。同时,这种男性气质的发挥也被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以保证男性话语的权威地位。
1.“灰姑娘”的翻版:简
德国童话《灰姑娘》讲述的是饱受后母和姐姐欺负的辛蒂瑞拉的故事,因为一直睡在火炉灰旁,所以她也被叫做“灰姑娘”。灰姑娘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直到遇到了解救她的王子,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华丽的公主,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灰姑娘”在当下被扩展为从坏到好、前后生存境遇有着明显反差的这一类女性。简在遇到郑先生之前也是“灰姑娘”的处境,她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没钱买书就只能在书摊借读;读书时期她拼命做兼职才还清买书的分期账单;后来她也在鞋业公司打拼、在电脑公司跑销售、也开过二手书店……简早期性格气质中的进取、竞争、果敢等特征是典型的“胆汁质”男性气质的显现,不同于灰姑娘是凭借神奇力量改变命运,简靠自己敢闯敢拼的姿态成为事业女强人的典型。
美国作家柯莱特·道林在《灰姑娘情结》中认为,女性气质有着回避独立的倾向。相比之下,简的奋斗之路看起来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不依附任何人的模范,但是究其背后原因可以看出,面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不景气以及父亲的突然离世,简不得不直面最迫切的生存需求,因此她只能压制自身的女性气质,以中性的身份来适应男权社会的丛林法则。这一点葛亮在书写简成为书匠这一关键情节中的无意识展现得更加明显。简本来只是一个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而失业、然后决定开二手书店的小老板,虽然爱书惜书,但是远远不具备接触到古籍修复这一职业的经济基础。这时,“男性导师”郑先生的降临才真正意义上改变了简的命运走向:郑先生不仅给了简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撑,而且还为她提供了资源渠道让她师从名师,才有了后来的古籍修复师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不了简自身的努力,但是郑先生的“从天而降”无疑起到了“王子式”的关键作用,因此葛亮在书写《书匠》的故事时,还是没有跳出男性解救并支配女性的神话,本质上也只是现代香港版的《灰姑娘》。
另一方面,简身上的男性气质也是作家加之在其身上的对于现代女性的多样化诉求之一。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开篇就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12]相比于对传统女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的规训,现代男性话语表达对于现代女性的要求更加复杂多样、游移不定。他们一边渴望女性能够独立潇洒、经济独立,一边又期望她们可以温顺贤良、回归家庭,两种要求同时加之在女性身上对于女性的自由成长造成巨大负担。正如简在拒绝毛果和欧阳教授的请求时被冠以“冷漠”和“令人尴尬”的形容时,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于女性身上的男性气质一方面加以肯定,但是这种肯定又是极其有限的,一旦女性表现出较强的进攻性,她们立马会受到较为负面的评价和回应,足以看出现代女性成长之艰难。因此,哪怕强大如简,女性身份还是使她跳脱不出女性整体在历史中所扮演的弱势角色,男性气质的展露本质上也是在威胁不到男性的范围内负重前行。
2.被遮蔽的妻性:郑好彩
《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可以说是父权制文化下理想妻子的典型:她聪慧又温顺,在婚后与丈夫沈复琴瑟相和,二人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创造情趣,精神世界也是充实丰富的。林语堂赞其为“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13]。葛亮在《北鸢》中也数次写到《浮生六记》,尤其是被芸娘身上的女性气质所打动。事实上,芸娘内心隐秘的苦楚和孤寂却是被历史的话语掩盖起来的:她在婆媳相处中所受的委屈、被泯灭的个性都被“识大体”一带而过,只剩男性修辞附加在芸娘身上的的幻想和要求。对于《飞发》中的郑好彩,葛亮是从美发助理的身份开始介绍的,她身形敦实、吃苦耐劳,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技满成师,但是葛亮却赋予她“他者”的身份,在拯救男主人公后立刻结束了她的生命。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郑好彩身上的男性气质可以说是生活所迫,她能够在众多漂亮女孩之中面试成功,跟她从小就培养出的“干活的身架子”不无关系。一直以来独自承担着生活重担的她,因为翟玉成的一句“留下吧”让她心底的归属感和女性气质被唤醒,从此她把翟玉成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洗头妹到翟玉成落魄时的救星,她把恋爱视作信仰,结婚是必然的结果,儿女降生后占据了她生命的全部,除此之外看不到郑好彩更为丰富的个人成长历程。就像翟玉成看着好彩,“她眼里满满憧憬,全是将来。此时,他心里却都是过去”[14],翟玉成的雄心和理想是郑好彩并不了解的,这也印证了郑好彩伪装的男性气质在本质上的虚无。葛亮在介绍人物出场的时候提到了她的名字:“好彩”在粤语中是“幸运”的意思,而郑好彩“无我”式的付出意味着她只能以工具性客体的形式存在。关于二人的婚姻,作者也并没有任何有关爱情的叙述,就像故事中插叙的“孔雀”旧事中提到的,翟玉成和一身侠气的霞姐才是真正的一路人,因此他爱的绝不是郑好彩这样的女性。同时,葛亮在《瓦猫》中对于性的书写一直是极为克制的,但是《飞发》这里比较特殊,写夫妻却不写性无疑是不完整的,被“阉割”的性导致描绘夫妻二人和谐关系时显得有些苍白。
闻一多说中国女子的妻性即是奴性[15]。翟玉成和郑好彩从最初的雇佣关系到夫妻关系,其实地位一直都不是平等的。虽然“乐群理发铺”是她一手张罗的,但是当翟玉成从往事的痛苦中走出来后,她立刻回归到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之中。相比之下,家庭对于翟玉成来说只是起点,延伸到家庭之外的世界才是他真正目标。因此,郑好彩实际上是将“她的未来交给一个拥有一切价值的人来掌握,这样她便放弃了她的超越,让这种超越依附于身为主要者的那个人的超越,让她成为他的附庸和奴隶。”[16]相比于走向世界的丈夫,身为妻子的郑好彩只能是依附者而无法得到成长。退回到家庭的郑好彩用生儿育女表达了她对性别的认知,她以自己的身体、性别为筹码来换取主体的生存,但这绝非是成长。“女性主义身体论认为,身体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有密切关系”[17]。但是,郑好彩用身体建构主体性行为换来的是失去生命的代价,葛亮通过悲剧结局来宣告郑好彩工具使命的彻底结束以及这种成长方式的岌岌可危。
二、游移:“雌雄同体”的性别行为规范
珍妮特·希伯雷·海登在《人类一半的体验:妇女心理学》中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气质,男女双性化听起来不错。因为,它使人们能显露他们的异性趋向。”[18]柯勒律治也表示,伟大的头脑是两性兼有。只有当这两种力量融洽时,我们的大脑才会得到充分利用。[19]事实上,这种“双性同体”的性别行为原则与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观念相通,这种思想也是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另一种诠释。面对女性自我与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女性如何填补自身的性别残缺、打破社会对女性“心理体验”的阉割、丰富秩序中的性别匮乏成为女性成长的关键。相比于单一的性别气质,葛亮无疑更认可两性心理同体的性别规范,他《瓦猫》中塑造的女性人物简、乐静宜和荣瑞红等试图使用灵活的性别行为方式,她们在建构主体性别自我的过程中努力突破刻板的性别角色和气质划分,但是这种“雌雄同体”的性别气质在具体落实中还是难以跳出理论的形式感。
(一)时代变迁下游移不定的诉求
在结集《瓦猫》中,葛亮塑造了叙述者“毛果”的形象来走进三个时期和地域的匠人故事之中,从《书匠》中的毛毛、《飞发》中的毛博士到《瓦猫》中的毛老师,毛果从少年到青年的年龄增长和身份变迁揭示出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女性匠人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变化路径。随着精神性别的成长和肉体奴役的解除,几位女性工匠身上浓缩了中国女性群体的处境。但是这种“被讲述”之中掺杂的几千年来男性对于女性的想象和诉求其实并未减少,“两性同体”对男女差异的削弱让女性寻找和建构性别自我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鲁迅早在上世纪20 年代讨论娜拉的演讲中就尖锐地指出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0]。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女性摆脱“他者”境遇的物质基础,葛亮有意书写多种性别气质在同一主体身上的闪现赋予了女性一种富有弹性的柔韧力。比如孤僻寡言但是心细如发的简在谈到古籍修复的工作时“眼睛里闪着晶莹的光,让整个人也明亮起来”[21],吃苦耐劳、感性真诚的荣瑞红多年制作瓦猫的经历让她变得处变不惊、“眼睛并不混浊,甚至很明亮”[22]。但是从简逐渐衰老到不能自理时的孤独和狼狈、乐静宜对于爱与恨的模糊界定以及荣瑞红只剩瓦猫陪伴左右的结局可以看出,这些女匠们事业之余的生活都是残缺而有遗憾的,这恰恰反映了两种性别气质特质同时作用在女性身上时所造成的割裂,灵活的性别行为方式难以落到实处。
首先是作为古籍修复师的简和乐静宜。《书匠》中简和乐静宜师徒的故事发生在新世纪以后的现代香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变迁,妇女解放的一个巨大标志就是从附属品的地位转变成自食其力者的形象,女性成为了与男性平等的另一半公民。在此之后,能够经济独立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标杆。《书匠》中的简就被塑造成这样一个“进取女性”的代表:修书事业上的成功使得简不需要为生计困扰,因此她可以坚持修书的原则不妥协;她也不需要通过婚姻来寻求安全感,经济上的独立让她可以自由随心地选择想要的生活;她可以在工作时全身心地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之中,在空闲的日子里去朋友开的餐厅享受美食、组织聚会来增进友情……葛亮在这里还插入了《查令十字街84 号》这一潜文本,以纽约女作家海莲·汉芙和伦敦旧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信之恋让这段爱情更具美好想象。但是葛亮这时却残忍地赋予了郑先生猝然离世的悲剧命运,同时他也让读者对于简应该会悲痛欲绝的这一预判落空,进一步凸显出简作为成熟女性的魅力。跟随毛果的视角所看到的简可以说是现代男性对于理想女性的欲望投射,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贤妻良母式的女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加大难度来获得观赏的愉悦感,简的孤独终老也印证了这种诉求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难以实现。对于乐静宜来说,在父亲的身边时的她一直扮演的都是女儿的角色,但是在简的感染下却成长为大方干练、业务能力强的现代女性代表。她可以在青年古籍修复师大赛上取得胜利,也可以毅然决然地拒绝志不同道不合的男友的求婚。这时的乐静宜打破了“父之女”阶段的失语状态,她可以在事业和两性关系中平等地与男性对话,但是与此同时她也产生了主体价值上的困惑。她对于父亲不知道有没有爱,对于简“恨不起来了,虽然也不可能爱”[23]。
还有瓦猫工艺传承人荣瑞红,生长于抗战时期闭塞的西南农村,她代表的是传统女性的坚韧力量。波伏娃曾感叹:“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24]传统女性无法成长和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男性经济的依附,根源是在男权制社会下,女性接受教育、从业的机会受到一定限制,即使才华出众也可能失去表现的机会。但是《瓦猫》中的制陶者荣瑞红继承了祖父的技艺,打破了传统技艺往往“传男不传女”的约定。相比于宁怀远对现实的逃避,荣瑞红面对生活时展现出坚韧而勇敢的男性性别气质。她一边从事瓦猫制作的工作、一边照顾儿子,葛亮笔下的这位女性把生活和事业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葛亮在具体展现这一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上较为空白,这一对于女性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书写被遮蔽掉属实遗憾。荣瑞红制作的一个个瓦猫也象征着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这些“似猫非虎”的器物伫立在屋顶为人民祈福挡灾,也永远只能形单影只。荣瑞红是被爱情抛弃后不得不选择让自己独立强大,这与两性心理同体这样一种流动、灵活、主动的性别行为方式本质上有着差别。
(二)男性凝视与女性情谊的抗衡
凝视是一种带有权力意志与主体欲望的注视,约翰·伯格用欧洲油画进行举例,“在欧洲裸体油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把女性视作及定为景观的标准和规定。”[25]虽然《瓦猫》中对于女性外形的描写不多,但是注视的目光从毛果视角投射出来与读者进行互动,使得这些女匠承载着男性凝视的目光。伍尔夫指出,女作家要克服男性价值标准的影响就必须杀死“房中天使”。所谓“房中天使”指的是按照男性价值标准虚构出来的理想女性形象,她们往往是纯洁、羞涩、优雅、自我牺牲,没有自己的欲望和思想。葛亮小说中的驳杂之处在于既有着男性主体欲望的投射,同时也书写女匠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削弱男性凝视。
《瓦猫》开篇是由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小诗《博物馆》引入的,辛波斯卡本人是一位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她的《罗得之妻》从女性视角探讨了罗德之妻在逃跑路上的复杂情感。《罗得之妻》作为《圣经》中一个悲剧故事,历史中的解读大多都是从男性视角表达对这个女性的同情和怜悯,但是辛波斯卡却从女性视角看到了罗得之妻从追随丈夫到独立自主的成长过程。在她笔下的罗得之妻“温和而不顺从”[26],代表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瓦猫》中以简为代表的女匠们的成长过程也是其性别自我的建构过程,她们有着不输于男匠的能力,同时也渴望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传递出女性的力量。以简的几个学生为例,她们的聚集并不是因为技艺上薪火相传的使命感和追求,更多来自于生活境遇和心理诉求。简发自内心地说她每一次收徒都有着非收不可的理由,这一理由可以说是一种松散但却强大的情感联结,她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也不需要任何仪式,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女性之间的理解和扶持。比如徒弟秀宁,简为她修好了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的书,让她重燃起生活的希望;与此同时,秀宁顽强的生命力让她从郑先生去世的悲痛之中走出来,两位女性因为修书的过程携起手来共渡生活的难关。就像简所说的,修书更是修身和修心,女性之间的情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弱化男性的凝视。
鲁迅先生的《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之间的裂隙除了经济问题以外,子君面对自身所指的匮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是我自己的”是以子君为代表的女性“开始了她们从物体、客体、非主体走向主体的成长过程”[27],也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之间从主客关系到主体间关系的转变,但是,女性在主体性生成中还是受到很大的阻抑,而填补自身意义的空白变成女性成长为主体过程中最关键也最复杂的一步。“爱情于女性而言,既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又是性别意识自觉的过程。”[28]由于简与郑先生之间的关系,导致简和乐静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葛亮并没有在小说中点明郑先生把女儿乐静宜托付给简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想要让女儿延续自己的梦想,或许是为了让两个自己爱着的女人能够结伴同行。首先不说简是怎样接受作为郑先生女儿的乐静宜,就拿简和郑先生一起瞒着乐静宜几年才告知她二人关系这一点也让乐静宜格外费解和委屈。乐静宜的一句“她只是被培养成第二个简”道出了极具欺骗性的男性凝视本质,郑先生一手塑造了简,然后又间接将女儿培养成另一个简,可见女性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始终难以跳出男性的期待视野。
相比之下,男性始终占据功能性的作用,在关键处是决定力量。无论是男性气质主导的简还是女性气质主导的乐静宜,二人注定只能是刻板化的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两位女匠看似在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但实际上还是逃不出“被看”的命运。正如戴锦华所说:“在急剧的现代化与商业化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正经历着悲剧式的坠落过程”[29],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往往会忽略女性的现实需求,而两性心理同体不应该是一个束缚女性的僵化框架,如何让它真正成为由女性自身来调度的灵活选择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完满性别人格构建之艰难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谈到,从前的人有三种性别,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还有一种一男一女的阴阳人。[30]柏拉图想说的是,人不是绝对的单面体,而是多面并存、完整合一的整体。传统中国社会以僵死的划分方式将性别气质设定在狭窄的界限范围内,事实上是对于生命百态的一种摧残。荣格认为两性间的和谐依赖个体内部双性自我之间的和谐。[31]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人类是有机的整体,那么两性的心理性别也应该是有机的统一体,个体内部两性特质的平衡才能促进个体健康发展和创造力的张扬。阎连科在《她们》中论述了作为女性之他性的“第三性”,这种他性体现在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的身份上。在阎连科看来,“女性中的他性是她们的一种疣赘物”[32],朱迪斯·巴特勒也提出疑问:“为什么这种性别差异的框架不能越过二元性进入多元性”[33]?但是,从超越性别的整体视野中来看待人性本身、在认同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对话以及个体内部的自洽这样一种两性乌托邦事实上是极度理想化的,容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
《瓦猫》中的几位女匠在爱情和婚姻上最终都是不圆满的:简与郑先生曾经“情书式”的甜蜜爱情却因为郑先生的意外去世而昙花一现;乐静宜与男友文森二人在理想追求上有着严重分歧;荣瑞红两次被宁怀远抛弃,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缺憾的命运暗示着两性同体论之下女性的成长之路依然步履维艰。尽管在郑先生离世时的简年纪尚轻、面容清秀而且事业有成,这样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追求者,但是简迟迟未能走出郑先生离去的悲伤;乐静宜在庆功宴上受到男友求婚,按照在场观众的预期应该是郎才女貌的美好结局,但是乐静宜无法认同男友的观念所以拒绝了这场求婚,拒绝后是无尽的落寞;说到荣瑞红,身为勤劳吃苦、模样标致的女子,她在漫长的后半生应该并不缺少可以共度余生的人,但是最终她还是孑然一身。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身能让她们静下心来反思自我、品味与咀嚼自我,为追问人生的精神追求提供了可能,但是她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孤独感和飘零感也是她们在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凄清和苦涩,两性心理同体使她们走向了另一种自我封闭。换句话说,孤独将女性成长指向自我的内在性生存,这可以是她们面对人生困境时反求诸己的能动行为,但更是现实人生的无奈之举。
凯若琳·G·赫布兰认为,男性和女性气质都是人性中必须的内在价值[34]。里尔克也表示两性人格更趋于完美,富有创造力的男性在女性化方面也会得分较高。在葛亮笔下,男性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也承担着引导者的角色,比如郑先生之于乐静宜和简、宁怀远之于荣瑞红。但是郑先生对乐静宜的“灌输式”教育以及宁怀远“抛妻弃子”的行为都显得有些粗暴和残忍了,如果这些男性能够承担起更多帮助女性成长的责任、两性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对话,那么这些女性的成长之路或许不会如此坎坷与沉重。
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里尔克写道:“大半两性间的关系比人们平素所想的密切,也许这世界伟大的革新就在于这一点: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而忍耐地负担那放在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35]里尔克的愿景是美好的,两性同体既是作为人对自身探索的责任,也是一种积极的潜能,是建构两性乌托邦的努力方向;但也不得不承认的是,两性本身就具有和谐中的矛盾,女性的成长道路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更是亟待解决。
三、结语
普兰·德·拉巴尔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36]葛亮以叙述人毛果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进几位女匠的成长故事之中,通过考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成长经验,既有利于对女性的成长困境有更全面和深入的挖掘,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男性主体欲望在女性身上的无意识呈现。女性的主体成长和精神突围并不是意味着将男性置于矛盾的对立面去敌视,而是通过突出人的心理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因素,进而从“人”的整体价值出发,挖掘人的最大潜能,促进人类整体朝着更加全面自由的方向发展。面对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与男性在性别气质上的巨大差异正是二者之间需要共通和互补之处,异性气质间的互相渗入和汲取有助于打破界限的束缚。但是,两性同体在目前来看更趋向于一种理想化的美好期待,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自身内部的和谐都难以做到。可见,女性的自我解放、成长之路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120 页。
②[美]达维逊、果敦:《性别社会学》,程志民、刘丽、宋坚之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第21 页。
③⑤[2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实际体验》,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9 页,第23 页,第449 页。
④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2 页。
⑥⑨⑩[11][14][21][22][23]葛亮:《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6 页,第314 页,第254 页,第231 页,第138 页,第74 页,第215 页,第90 页。
⑦叶舒宪:《老子与神话》,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74 页。
⑧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8-120 页。
[12][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吕澎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 页。
[13]沈复:《浮生六记》,苗怀民译注,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313 页。
[1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2 文艺评论·散文杂文》,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16 页。
[1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736 页。
[17]乔以钢、李振:《当身体不再成为“武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
[18][美]珍妮特·希伯雷·海登、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范志强、周晓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5 页。
[19][2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33 页,第29 页。
[20]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娜拉走后怎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7 页。
[25][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64 页。
[26][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我曾这样寂寞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6-148 页。
[28]梁小娟:《近30 年女性成长小说的性别书写》,《江汉论坛》2015 年第4 期。
[29]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1994 年第6 期。
[30][古希腊]柏拉图:《会饮篇》,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29 页。
[31][美]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62 页。
[32]阎连科:《她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年版,第207 页。
[33][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202 页。
[34][美]凯若琳·G·赫布兰:《双性人格的体认》,李欣颖译,《中外文学》1986 年第10 期。
[35][奥]莱内·马利亚·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版,第26 页。
[3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事实与神话》,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1 页。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