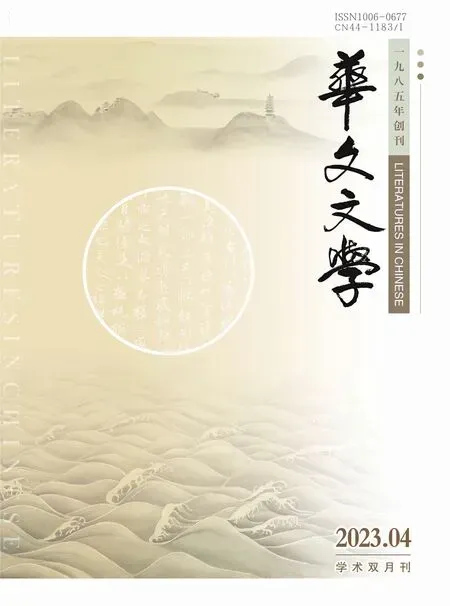多元交杂的混合体
——论葛亮创作中的“香港”构形
罗欣怡
“大家认识香港,往往是先看到许多有关香港的图像:比方有关香港的书籍的封面、明信片、摄影册、香港旅游协会对外的宣传图册等,这些图片展示维多利亚海港两边林立的高楼大厦,在画面中央老是见到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大厦高耸的建筑物,这些影像好似被公认作为这个城市和它的文化的象征。”①图像常以直观的形式为观者展示了一个城市的部分面貌,而一位作家则主要以文字来想象与构形一个城市。葛亮于21 世纪初赴香港求学,后定居香港,至今近二十年。葛亮的创作在香港开始,香港也成为了葛亮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经由早期的短篇小说《阿德与史蒂夫》到近年的长篇小说《燕食记》,葛亮笔下的香港已然展现出复杂而独特的面貌。
一、香港城市形象五种元素的书写
(一)香港的道路与边界
凯文·林奇曾将城市形象中物质形态的内容归纳与分类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认为“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的意象”②,其中道路作为居住者在都市中接触的最为密切的元素之一也被凯文·林奇认为是城市形象中的主导元素。具体到香港这座城市,笔者认为,由于香港的道路名称也许是整个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因此在葛亮的小说中,香港的道路首先可以帮助读者明确作品的“香港”身份,构建故事背景,在外部形式上对“香港”的构形有所帮助。香港许多街道的名称与香港被殖民的历史有关,即以历任港督命名,这是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如位于香港半山区的罗便臣道是以香港第五任港督罗便臣爵士命名。
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小说《地图集》在深挖香港城市地图方面颇下功夫,纪实的考据与虚构的小说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其中就有专门的“街道篇”。相比而言,对香港道路的描写在葛亮的小说中往往一闪而过,只成为人物生活的背景,如《燕食记》中写五举前往灯红酒绿的销金窟所在的骆克道找寻戴德,如《街童》中写男女主人公在轩尼诗道的行人路上漫步。葛亮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对香港的街道进行了评价,《私人岛屿》中男女主人公行走在窝打老道时这样写到,“她听他讲起香港街道的掌故。香港人翻译出的街名,都是别别扭扭的。诚心要你记不住。街道一路都是低矮的两层住宅,颜色阴暗,很不起眼似的。”③尽管葛亮在小说中并没有花太多笔墨来具体描写香港的街道,但他在散文中却对其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描绘,这种对香港街道的感受也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其个人南京经验的对比中。散文《拾岁》里葛亮提到了许多令他印象深刻的街道,如一条靠着正街的用石板铺筑的陡峭阶梯是“密集集地下落,几乎有点壮观的意思。”④如高街“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⑤
葛亮对香港街道的认知、感受和书写总体可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在街道名称方面。葛亮认为,香港街道名称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显得俭省而生僻,多少有些不着调。⑥正如笔者前文所提及的,香港的街道名称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是最为特殊的,这形成了香港的一大特色。二是香港街道的“形状”方面。葛亮认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天空显得阔大,因为道路往往也是宽阔的,相比之下,香港的街道大多逼狭乃至崎岖,以至于“太多逼仄而狭长的天空。”⑦这一街道特点也正是凌逾教授在概括香港城市文化时所提到的“挤感空间”的具体表现。立足于葛亮对道路这一元素的书写可以发现,葛亮在散文中通过个人的观察与体验将道路作为构形香港的重要因素,但在小说中却并未强调这一元素的价值和作用,其小说中道路主要作为人物生活的背景以及确认作品故事的“香港”身份而存在。
边界与道路的含义与作用是有些交叉的,凯文·林奇对边界的定义亦有些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边界是除了道路以外的线性要素,它们通常是两个地区的边界,相互起侧面的参照作用,并举出了河岸与铁路线的例子,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边界经常同时也是道路,将二者混淆乃至等同。笔者认为,这两个元素的确息息相关,对边界的认知应从其核心功能出发,即对两个不同区域所起到的分割或连接的作用。无论是人为的道路还是天然的湖泊,不论是线性或弧形,只要具备分割或连接不同区域这一核心功能都可称之为边界。正如葛亮笔下的香港中有两类边界值得注意,第一类往往是道路,分割出两个不同的区域,显示出两个区域的不同特色,如《书匠》中写到我与简开车穿过海底隧道去观塘区,简居住的半山区属于居民区,而观塘区则属于工业区,海底隧道就充当了人为边界的作用,显示出两个区域“功能”的不同。第二类边界是香港天然形成的边界,即海水与海岸线。现在通常所说的香港实际上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和周围的诸多岛屿,海水与海岸线作为分割岛屿的边界也自然形成了香港的边界。正如葛亮书写香港道路时会将香港的道路与故乡南京的道路做一番比较,葛亮对香港“边界”的认知同样有时以南京为对照,长江从南京的版图中流过,成为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天然边界,划分出了所谓的“江北人”,香港也不缺水,“来到香港,还有水,这回却咸下去,是海水。”⑧
通过对维多利亚港与离岛两种海水与海岸线的描写和对比,葛亮展现了其深厚的历史意识。维多利亚港位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成为了这两个区域间的边界,它是天然形成的良港,是香港重要的资源,港口附近的码头“整齐地排列着橘色和蓝色的集装箱”⑨,以繁忙的货物运输见证着香港的经济变迁。同时它也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葛亮所言,“乘坐天星小轮,往返维港两岸,渐成熟悉的经历。”⑩尽管维多利亚港在香港的历史与现实中如此重要,但葛亮却并没有对其海景进行夸赞,亦没有描绘其繁华,而是评价到,“其实不像海,窄窄的一湾,水声却不小。”[11]面对维多利亚港海岸线的变迁,葛亮充满了对历史的感叹和对香港过度城市化的反思,毕竟“这港曾经是广阔的,填海取地改变了天然的海岸线,造就了港内的风浪”[12],可未来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大概难以想象维多利亚港湾,也曾港深水阔,可以容纳五十艘万吨巨轮的历史。”[13]同样的深思也出现在香港作家陈浩基的笔下,他在小说《遗忘刑警》中借人物许友一之口感叹了维多利亚港附近海岸线的变迁:“现在所处的新海旁街,以前是海的中心,距离岸边至少一百米……工程车把泥土倒进大海里,那些愉快的时光只能变成回忆。”[14]
与维多利亚港的海水与海岸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离岛的海水与海岸线。葛亮在小说《龙舟》的开篇借主人公于野之口对维多利亚港的海景进行了点评并借此赞扬了离岛的海景:“于野的印象里,香港似乎没有大片的海。维多利亚港口,在高处看是窄窄的一湾水……于野是在海边长大的。那是真正的海,一望无际的。涨潮的时候,是惊涛拍岸,不受驯服的水,依着性情东奔西突。”[15]小说主人公于野也正是在对维港海景的“不满”中才来到了离岛,遇见了一片宜人的海景,“海滩宽阔平整,曲曲折折地蔓延到远处礁岩的脚底下,略过了一些暗沉的影。干净的白沙,松软细腻,在斜阳里头,染成了浅浅的金黄色。”[16]从葛亮对香港的天然边界——海水与海岸线的描写来看,葛亮的态度是鲜明的,褒贬皆有的,充满历史反思的。
(二)香港的特殊区域
“区域是城市内中等以上的分区,是二维平面,观察者从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因为具有某些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从内部可以确认,从外部也能看到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17]岛屿本身作为能够从外部被识别的特征是构成香港这座城市重要的区域因素,如小说家刘以鬯就有一部名为《岛与半岛》的长篇小说来描写香港。葛亮也曾在散文《拾岁纪》中写到,“还可说的,是香港的岛屿。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开始热衷于对离岛的探访”[18],并在《龙舟》《街童》《杀鱼》等多篇小说中描写了离岛。
葛亮不仅展现了离岛这一区域内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反映了离岛这一区域的物质和文化特色,如宽阔的海滩与漫天的火烧云等自然景观、赛龙舟及太平清醮等节日习俗、传统寺庙与祠堂等特色建筑等,还展现了这一区域内产生的变化与面临的危机。小说《龙舟》中随着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来离岛的人逐渐变多,“观光客,旅行团,在非节假日不断地遭遇”[19],海浪中携裹着游人丢下的易拉罐,离岛的海滩慢慢被改变了模样。《杀鱼》中主人公阿佑的阿爷在岛上以杀鱼为生,有着高超的杀鱼技艺,然而渔场越来越多地使用机械化杀鱼的方式,阿爷的传统技艺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小说中阿佑与阿爷的代际矛盾实际上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暗示着离岛年轻一代对传统的背离。更大的危机在于,小说中龙婆的房屋连同离岛上的整个村子都面临拆迁,拆迁后的人们将搬到元朗居住,届时,离岛的历史与文化将会被彻底“抹去”。
尽管《杀鱼》的结尾离岛面临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如村子的拆迁取消,阿佑学会了杀鱼,但“决定区域的物质特征是其主题的连续性,它可能包括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比如纹理、空间、形式、细部、标志、建筑、使用、功能、居民等”[20],那些在《杀鱼》中看似被解决的问题到了《街童》中已变成无法挽回的事实,离岛这一区域的功能、居民、建筑等要素都已发生了变化。“这房子政府也要征收,建什么度假村。阿嫲要和他们拼老命”[21],《街童》与《杀鱼》的情节巧合地联系在一起,被征收可以视作香港离岛的村庄面临的共同危机。《街童》中布德离开村子后去香港市区打工,布德的大伯也搬离长洲岛而迁往元朗居住,唯独阿嫲和一些老人留在村里。从区域内部来看,葛亮笔下的离岛逐渐从落魄的渔村变成了秀美的度假区或景点,区域的功能从居住变为旅游观光,一些居民因拆迁获得了一定的收入搬到了交通更发达的地方,构成区域主体的居民也从渔民变为观光客。在离岛这一区域的转变中,原生态的环境被破坏了,构成区域特色的居民和功能不复存在,离岛的文化传统也出现了断裂或消失。在这样的变化产生之后,离岛或许仍可以从“岛”的外部特征进行辨认,但其内在的独特性却消失殆尽,从这个角度来看,葛亮对离岛的书写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
葛亮对北角这一区域也极为关注。北角位于香港岛北岸,北临维多利亚港,随着抗日战争后来自上海的新移民的涌入获得了一个“小上海”的称号。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新移民变成以福建人为主,北角的称号则变成了“小福建”。香港作家也斯曾在《也斯看香港》一书中以散文和图片记录了北角,不仅涉及对这一区域的整体概括,还追忆了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店铺与街道。葛亮的《飞发》与《燕食记》不仅都是发生在北角的故事,而且相同的是《飞发》中的庄锦明与《燕食记》中的戴明义都是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海移民到北角并定居于此的。从小上海到小福建,区域称呼的变化映照着时代的变迁,这两篇小说亦正是在中下层上海移民与福建移民混居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的。
《飞发》中这样描述庄锦明刚来香港时的北角,“那里有许多的上海人,殷实些的迁去了半山继园。到他来港,还有不少散居在民间,在春秧街、明园西街等处和福建人混居在一起。这里便被称为小上海,自然也带来了上海人的品味和生态。”[22]《燕食记》用了几乎相同的描述,“到了戴家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胜景不在,上海籍的有钱人家陆续迁出,搬往地势较高的半山。福建人在这一区多了起来……所以明义家所见的北角,品流已成多元,上海味儿其实凋落了不少,但他们还是感到亲切。”[23]小说中北角这一区域内部显然具备以下特征:建筑多为唐楼;居民多为上海或福建的底层移民,职业较为多样;文化品味上有老上海的气息,但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等等。如果说离岛主要以其外部特征构成了香港特色鲜明的区域,那么,北角这一区域的特色则主要因为其内部独特的历史文化。
葛亮在作品中当然不止描写了离岛与北角这两个区域,但他对这两个区域的书写都别有深意。葛亮对离岛的探寻是试图以对边缘的关注来审视香港的乡土/ 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危机,对北角的关注或许因其本人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对北角的移民文化具有好感,但或许在于北角这一区域实在是香港的“缩小版”,它不仅深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也混杂了上海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东南亚文化等多种地域文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与特色的区域,葛亮对离岛与北角的关注是其探寻香港多元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
(三)香港的节点与标志物
对于葛亮而言,地铁构成了其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还是城市,香港,从我工作的地方到住处,有许多重复的景致。它们往往与都市的脉络——地铁相关。”[24]在散文《气味》中,葛亮以温情的笔触描写了地铁站口的一些人与物:地铁站旁一家婚纱店前黑色的小猫与野猫,站口前常出现的童子军或环保组织,地铁口边昏黄的灯光下卖钵仔糕的年迈老人等等,因此,地铁站实则是葛亮观察和构形香港的重要“节点”。凯文·林奇认为,“节点是人们来往行程的集中焦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与道路与区域具有重要关联,典型的如道路连接点或某些特征的集中点,如街角的集散地或一个围合的广场。”[25]在现代都市中,地铁站往往具备着连接、聚集、转换的特质,无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节点。
散文里葛亮对地铁站的观察充满温情的目光,而在《私人岛屿》《浣熊》《退潮》三篇小说中,葛亮则更直接地强调了地铁站作为城市节点的作用。《私人岛屿》中男女主人公来到香港时乘坐的便是地铁,当女主人公站在地铁东厢的一个角落时窗外的香港是灰色与黄色的,略带荒凉的,地名是乡野与空旷的,而当她在九龙塘站下车出站时,迎面而来的却是通明的灯火与川流不息的人群。“九龙塘站的出口连接着香港最为繁盛与昂贵的商区——又一城”[26],小说中的九龙塘地铁站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节点,它成为了小说女主人公进入与观察香港的重要焦点,转换与表达了人物对香港的感受——从荒凉到繁华。地铁站是城市中人群聚集与行动的重要节点,也自然适宜作为一个让男女主人公邂逅并发生爱情故事的场所。小说《浣熊》中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始于一个地铁站的出口,“她有些头痛,却不能走。地铁站的意义之于她,是工作的阵地。”[27]另外在香港众多的地铁站中,有一个地铁站作为节点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不仅在葛亮在小说《退潮》中写到,在诸多关于香港的小说和电影中也有所提及,那就是地铁罗湖站。该站是香港地铁系统中最北端的车站,连接着深圳市的罗湖口岸,因此该地铁站可以视之为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连接点,电影《过春天》中就有“水客”少女佩佩在走私中经过罗湖站与罗湖大桥的场景。《退潮》的主要情节发生在深圳,但故事却发端在罗湖,在罗湖站挨挨挤挤等待过关的人群中,她看见了正在行窃的他,而他也因此盯上了她。地铁站这一节点所具有的聚集/离散特质使其成为了都市现代性体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葛亮对香港的构形中,地铁站是观察城市人与物的重要视点,是展现城市荒凉或繁华的重要节点,也是一段都市爱恨情仇故事开始或结束的重要地点。
相比于城市中存在的众多节点,或许标志物是构形一座城市时最为重要的城市元素。也斯曾举例,在关于香港的图像中“画面中央老是见到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大厦高耸的建筑物,这些影像好似被公认作为这个城市和它的文化的象征”[28],抑或用帆船来作为代表香港的标志物,因为“过去香港不少旧日的摄影、绘画、明信片,都充斥了帆船的符号。”[29]的确,不论是汇丰银行大厦和中国银行大厦这两个建筑还是帆船这一事物都曾在香港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早已融进了香港的历史文化,因此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香港的标志物。“标志物通常是一个定义简单的有形物体,比如建筑、标志、店铺或山峦,也就是在许多可能元素中挑选出一个突出元素”[30],为辨别与认识一座城市提供了参照,但葛亮笔下香港的标志物却并非是常见的高楼大厦或是帆船这类物事,而是唐楼。
葛亮笔下的香港自然不乏高楼大厦,小说《私人岛屿》就写到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该楼建立之初是香港第一大高楼,位于香港岛中环金融街,是香港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著名地标,也是游客观光的重要景点。然而在小说女主人公的眼中,尽管这栋建筑是巍巍然的,鹤立在众多鳞次栉比的楼宇中,但却是灰色的、造型突兀的。葛亮借男主人公之口说明,“举凡高大的建筑,所谓摩天楼,都有着阳具崇拜的暗示。定海神针似的杵在那里,只因这一个突起,城市的性别就理直气壮起来。”[31]在得知其中具有的性暗示后,女主角再看这座楼时则“蓦然觉得有些仇恨”[32]。可见,尽管葛亮写到了这类高楼大厦,但小说中人物揶揄与暧昧的态度却显示出作者葛亮较为否定的心态。在葛亮的“香港”中,几乎没有人物生活在这样窗明几净、雄伟壮观的高楼之中。
钟华楠在《香港当代建筑》中指出香港战前留下来三类主要建筑物:一是中式的传统建筑物,如围村、祠堂等;二是殖民地式建筑物,如港大的陆佑堂、立法局大楼等;三是唐楼,受战前上海与广州影响,楼下是店铺,楼上是住家的四五层高的楼宇。[33]这三类战前遗留建筑并没有随着香港的发展全部被淘汰或替换,而是同时混杂在香港都市之中。某种程度上,由于独特的名称、风格与历史,这三类具有特色的建筑在作为香港的标志物上或许更具有优势,而唐楼则成为了葛亮笔下的“香港”的标志物之一,在葛亮的诸多作品中均有出现。《阿德与史蒂夫》中曾具体描写了唐楼的环境,小说中“我”是个刚到香港读书的大学生,居住在唐楼的顶楼,这栋唐楼“没有电梯,楼顶有一个潮湿的洗衣房和房东的动植物园,镇守门外的两条恶狗,昼伏夜出的蚊子”[34],房间也被房东隔了又隔。除了《阿德与史蒂夫》,《猴子》中的猿猴饲养员李书朗与父母蜗居在荔枝角的一处唐楼中近二十年,《鹌鹑》中的“万年青旅社”也位于一个破落的唐楼,《燕食记》中作为茶楼总厨的荣师傅虽然有丰厚的积蓄,但依然住在西环一个四十年的老唐楼中,周围“年久失修,空调轰隆作响”[35]。
葛亮小说中的唐楼大多代表着破旧、拥挤、衰老,但同时也意味着烟火气和丰厚的历史感,这就使得小说《飞发》对唐楼的描写显得格外独特。“路两旁的唐楼都带着烟火气,保留了斑驳的外墙,甚而还能看见五十年代鲜红的标语痕迹,墙上装有简洁的工业风外楼梯,虽也是复古的,但因为明亮的红色,却带着劲健的新意。”[36]对这种经过现代化改造又不失其历史感,既保留了烟火气,也能显现新意的唐楼,小说中的“我”显然颇具好感,亦侧面体现了葛亮对唐楼的态度。唐楼代表了我国华南地区、香港及澳门地区19 世纪中后期至1960 年代的某种建筑风格,是一种混合了中式及西式风格的建筑,并且每个地区的唐楼又独具特色,有着不同的名称,如在我国广州地区称广州骑楼,在新加坡则称新加坡店屋。唐楼本身作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体,是香港目前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也代表了香港文化混杂的独特性质。葛亮选择以唐楼作为其笔下“香港”的标志物之一,意在塑造一个不同于游客的想象中充满繁华景象的别样香港。
二、描绘香港的面孔
通过对葛亮“香港”构形中城市形象元素的考察固然能够剖析“葛亮的香港”的内在肌理,然而在此基础之上,“葛亮的香港”仍需要给读者一些更为整体的感觉以显示其“外貌”。王德威曾经认为,“辗转于无常的政经文化因素间,香港能屹立不变,正是因为它的多变。”[37]笔者认为,多变的“香港”有着多样的面孔,“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间,等待你去触摸。”[38]葛亮笔下的香港所展现的恰恰就是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的那些面,那不为人知的神秘,那繁华背后的黑暗以及包裹在黑暗中的温情。
(一)神秘的香港
百年前王韬逃亡香港,在此写文章,办报纸,为香港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张爱玲与香港的相遇则成就了一出“传奇”流传至今。在小说集《浣熊》的自序中,葛亮有意识地梳理了香港史上这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相遇”并把香港与不期而遇这个词联系起来,将其定义为香港的一种特质。“小说香港,为这些年的遇见”[39],小说集《浣熊》更是葛亮与香港“相遇”的结果。
在葛亮的笔下,香港是各种身份的人与各种文化的相遇之处,骗子与卧底警察(《浣熊》)的爱情纠葛、大学生与偷渡者(《阿德与史蒂夫》)的友情,上海文化与广东文化(《飞发》与《燕食记》)的碰撞,黄种人与黑人(《侧拱时期的莲花》)的“交锋”、都市商业文化与香港传统文化(《龙舟》与《街童》)的争斗等等。葛亮的“香港”里,构成相遇的其中一方多是身份不明的人,《浣熊》里的辛赫表面身份是模特但其实是卧底警察,《阿德与史蒂夫》中的阿德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偷渡者,《鹌鹑》中的露姨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燕食记》中的戴明义是孤儿,《侧拱时期的莲花》中的阿咒则是被遗弃的黑人婴儿。不论是人物的身份背景还是情节的安排与人物命运的发展,抑或是小说意象的设置,葛亮似乎始终在书写着香港这座都市中那些颇为奇特的相遇以及这相遇背后所流露出的都市的神秘。
《阿德与史蒂夫》中“我”与阿德的友情逐渐升温,但当我过完一个暑假再回到香港时却再也没有阿德的消息,“很久以后,每每想起阿德,我已不再悲伤。只是感到迷惑,为生活的突兀。一切,戛然而止。”[40]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转折极为突然,人物之间的关系极为不稳定,“我”所感到迷惑的,正是一种现代性的都市体验,一种生活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一种属于香港的神秘性。《浣熊》中不仅男主人公“身份不明”,小说情节也一再发生突转。第一次转折小说揭晓了前文被骗的男主人公辛赫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警察,女主人公陈小姐因此被拘留治罪。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转折,女主人公在辛赫的墓碑前回忆到,“因为那个夏天,他可以与她走过出狱后的三十年。”[41]简单一句,读者才会惊觉,原以为卧底警察不过是逢场作戏,谁知这场骗局最后竟真成全了一段爱情。有评论者认为《浣熊》的大团圆结局纯朴到甚至可能有一些庸俗,[42]但笔者却认为,此一结局颇有效仿乃至汲取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意味。《浣熊》成全于一场忽然来临的热带风暴,《倾城之恋》成全于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都在讲述现代都市未知叵测的境遇中一段弄假成真的爱情邂逅。《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和白流苏曾面对过一堵极高极高的,望不见边的,古怪神秘的墙,而《浣熊》似乎也沾染了那堵墙的神秘色彩。正如浣熊本就是一种多出没于夜间、行踪神秘的动物,葛亮以此意象为小说题目想来并非强调爱情里的忠贞,而是要突出爱情来临时的吊诡与神秘。
同样以动物为题的小说《鹌鹑》更充满了神秘与悬疑的色彩。小说主要讲述了女孩张夏来到香港一家青年旅舍寻找未婚夫的故事,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小说一方面将读者引入有人在用鹌鹑乃至人体做实验的恐怖境地,暗示张夏的未婚夫已遭谋杀,营造了悬疑的气氛,另一方面刻画了行为举止奇怪的旅店老板露姨,暗示着她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极有可能是杀人凶手。但当张夏等人闯入神秘的309 房间时,她们发现露姨竟然是一个男人。这些鹌鹑的确是药物平衡的试验品,但却是露姨用来维持生命的试验品而不是杀人的试验品,而张夏神秘失踪的男友原来不过是去肯尼亚看了一场动物大迁徙。《鹌鹑》中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似乎令前文的悬疑色彩变得有些滑稽,让这场寻人之旅似乎变得有些荒诞,但笔者认为,小说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通过情节的突转和悬疑气氛的营造来讲述这个“死在这里都没人知道”[43]的酒店里一位身份不明的老板露姨的故事,进而展示香港这座都市神秘的一面。当众人撞破了露姨的秘密时小说这样描写到,“房间里挂着层层叠叠的旗袍,忽然幻化出了色彩,像是艳异的丛林”[44],一股幽幽的诡异气息瞬间弥漫起来,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旅馆,这座城市——香港,都被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刘俊教授曾经指出,葛亮有着对“神秘”的追求,其在《问米》中一再书写“神秘”展示了他对人世间种种不可解现象的沉迷和关注,对世界/生命中“谜”的兴趣和探究。[45]葛亮《侧拱时期的莲花》这篇小说则从题目到故事中人物和意象的创造都流露着神秘色彩。从附记来看,小说完成之时葛亮自身仍然不清楚“侧拱”的确切含义,其自身都讶异于梦境中的故事竟与现实中的黑人村落有着“呼应”。葛亮坦言,《侧拱时期的莲花》的题材和内容与其爱用的小说题材其实“大相径庭”,其对香港还有这样的黑人聚居地亦是“一无所知”[46]。葛亮的这篇意外之作和这样一个意外的“香港”愈发显示了葛亮笔下“香港”的神秘。
(二)黑暗的香港
相比于一座都市的神秘,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反复浮现的城市是腐朽与堕落之源,是淫乱、道德沦丧之地。”[47]张英进在讨论20 世纪初期城市的形象时认为,城市的形象大多数时候被看成是负面的,因而才进一步催生出逃离城市这一主题并形成了黑暗的城市形象。在葛亮之前,许多作家在作品中试图塑造的其实是一个功利性极强,竞争残酷的黑暗的“香港”,较为典型的如侣伦的《穷巷》和东瑞的《夜香港》。《穷巷》中的主人公都是从大陆赴港的青壮年男性,然而他们却无法在香港生存下去,小说结局杜全跳楼身亡,其余几个人物也依旧无法负担房租,被房东三姑赶走,踏上回乡的旅程亦或流落街头。侣伦显然试图借小说批判性地反映当时香港残酷黑暗的社会环境。东瑞是70 年代移民香港的作家,《夜香港》从一位刚出社会的大学生的视角出发,通过描写“我”做导游接待日本游客时的复杂心理展现了“我”抑或是东瑞本人对“香港”的认识,一面是对香港这座城市繁华景象的赞叹,一面则是对都市中灰色产业链所暴露的黑暗现实的批判,充满了理想幻灭的失落与生存的焦虑。
葛亮对香港的认识和书写同这些前辈作家既有相似,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心态与视角。葛亮在小说中虽然同样表现了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所具有的功利性特质,描绘出了“香港”黑暗的面孔,但其小说主题却并非以暴露香港社会的黑暗为目的。《浣熊》的女主角陈小姐在大学中掌握了良好的珠宝知识,本想成为一名珠宝鉴定师,却迫于社会环境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找到了一份明面上是当星探实际上是骗子的工作。《猴子》中的饲养员李书朗作为名牌大学的文学系学生,在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情况下最后放弃幻想成为了一名动物饲养员。小说中的报纸记者同样感叹,“在这里,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理想,大概要一天天地磨掉了”[48],表达出理想幻灭的失落和对社会生存环境黑暗的感叹。
葛亮在《浣熊》与《猴子》中描绘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屈从现实的生存困境相比于东瑞在《夜香港》中所描绘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即二者都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黑暗之城的形象。但东瑞主要通过描写大学生理想的幻灭与面对社会黑暗时内心的苦闷来直接批判香港的商业性和功利性,而葛亮的小说中虽有对香港社会现状的反讽,但其批判已不再尖锐,更多是嘲讽与无奈。如《浣熊》中陈小姐即便清楚自己是一个骗子,但对于自己能找到工作的态度仍然是庆幸的,《猴子》中记者即便认为整日追踪的报道没有意义和价值,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他们不似《夜香港》中的男大学生为自己做的事情内心极度挣扎,为理想的失落而过分痛苦,而是能够正视现实、自嘲与自我安慰。葛亮对香港“黑暗”面孔的这种描写并不意味着他对香港“黑暗”的完全认同,反而显示出葛亮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独特认知,即这种生存环境的“黑暗”是城市现代化发展中无可避免的,“香港”繁华背后这“黑暗”的一面是必然存在的。葛亮并非与《穷巷》和《夜香港》的作者一样直接批判和对抗黑暗抑或在黑暗中挣扎,而是以人性的温情来消解“黑暗”,从香港的“黑暗”面孔中发现其“温情”的一面。
(三)黑暗中有温情的香港
葛亮以清醒冷静的姿态审视了“香港”的黑暗一面,却也同时注视着这黑暗之中的人性之善。葛亮在其香港构形中关注的不仅是普通人具体而世俗的理想以及最终仍难逃理想破灭的黑暗生存困境,而且关注着这些普通人在黑暗的生存环境中表现出的人性之温情,即其所言的“许多的和暖。”[49]
《阿德与史蒂夫》中阿德与曲曲都是香港的黑户,没有合法身份,他们的理想就是争取到合法身份,能够光明正大地生活在香港这座城市之中,但最后阿德参与的暴力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被捕入狱,他的母亲伤心自杀,而哑女曲曲其实也身患抑郁症多年,在家中病死。小说结尾曲曲留下的那句遗言不仅是指向她个人的命运,也指向香港社会中许多像她与阿德这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甚至也指向这座都市本身的面孔——“是暗的,不会是明。”[50]然而即便前途黑暗,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极为动人,林医生没有行医执照,收入颇低,但他不仅没有收费,及时地救治了阿德,还在我与阿德离开时递上自己熬的猪肝汤给二人补身体,而老虎叔亦深知林医生的生活窘境和他爱面子的习性,于是趁阿德不在的时候将钱“扔”给林医生。这种温情不仅体现在小说人物的交往之间,亦表现在小说城市形象元素的书写上。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大多居住在环境类似的破败的唐楼或大厦之中,多处于黑暗的空间与社会的边缘,这使得小说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显得更为单纯和真诚。
曾有研究者批评“《街童》的故事甚至很不香港,反倒像是大陆书生穿越到某底层世界去的英雄舍身救美”[51],但笔者认为,《街童》中真正拉近男女主人公距离的,是两个闯入都市/中心但来自岛屿/ 边缘的底层人相似的生存困境,真正要表现的,是香港这座都市中两个孤独者之间倾诉、陪伴、依靠彼此而形成的温情。《杀鱼》中余宛盈之所以与阿佑敞开心扉,原因也或许在于阿佑所提到的展羽凤的角色恰好是她“唯一没靠男人得来的角色”[52]。在二人的这段谈话中,身份地位之间的差距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短暂而真挚的充满温情的心灵交流。这种温情在葛亮近年的《书匠》《飞发》与《燕食记》中同样得到了延续。如《燕食记》中荣师傅在遭遇五举“背叛”后就与其断绝了来往,但戴明义与戴凤行死去后,“明义墓碑前摆着一个食盒,里头整整齐齐地,排了五只莲蓉包。凤行的墓前也有。每个莲蓉包的正中,都点了一个红点。”[53]这些来自同庆楼的糕点显示出荣师傅对五举一家人的暗中关怀,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张爱玲曾用香港这一“她者”来理解自己的“家城”,荒诞、精巧、滑稽,其描绘多少是带着嘲讽的。葛亮也曾将自己成长的南京比作“家城”,把香港称作“我城”,但葛亮却并非以审视香港来理解自己的“家城”。正如葛亮为“香港”所选择的标志物是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唐楼而非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书写的题材并非一直是情爱的“传奇”而是转向那些关乎香港人日常饮食的“一盅两件”,关注的并非始终是香港的黑暗而是转向黑暗中的温情,当葛亮把香港视作“我城”时,尽管他对香港的构形仍多半是外来者的视角,但他对香港这座城市已然多了份贴己的认同。
三、结语
一个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城市形象的五种元素并非完全独立,明确它们,对它们分类,掌握其特征,结合文本进行具体考察,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构形涉及一些认知和感觉行为,以便在一个原本无形式的、不可解读的城市环境中把握空间与时间。”[54]通过目前的考察,葛亮对“香港”的构形显然一方面依赖于书写诸多的城市形象元素——如标志物(如唐楼)、区域(如离岛与北角)、道路(如高街)、边界(如维多利亚港)、节点(如罗湖地铁站),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对香港神秘、黑暗以及黑暗中带有温情等多重面孔的描绘。葛亮对“香港”的构形显示出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从边缘观照中心的企图。葛亮并不着力于对香港现代都市景观的描绘,而常常书写那些不同于一般认知中的香港的城市元素与面孔,最典型的例子如他对维多利亚港和离岛的描写和对比。想到香港,人们似乎无法不联想到维多利亚港的繁华,但葛亮却注重反思填海取地对海岸线的破坏及对香港人历史记忆的损害,相比而言,他更赞叹的是香港的离岛上那未经人破坏的自然海景。显然,葛亮有意识地站在了一个边缘(离岛)的位置去反思了中心(维多利亚港),这成为了葛亮构形“香港”的重要途径。
第二,个人南京经验的对照。葛亮在其香港构形中尤其是在散文中时常将香港与其生长的南京有所关联或比较,从而显示出两座城市的差异或类似。如葛亮提到了电影《重庆森林》中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居住的古董街,他认为这条街风格清幽而又有烟火气,仿佛南京的朝天宫。[55]可见,葛亮对香港的感受并非只是现代的或商业的,香港的一些街道同样充满烟火气。葛亮对香港街道的认知乃至对“香港”的构形正因为有了家乡南京的对照而具有了一定的私人化特质。
第三,多重的角度。葛亮既关注到了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所具有的生存压力和黑暗的生存环境,同时又关注到了黑暗之中的人性温情,从现实和人性的角度对香港进行了构形。葛亮还留意到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想象和书写了香港那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描绘了香港神秘的一面,同时以文化的视阈来构形“香港”,在《燕食记》和《飞发》等作品中描写了上海文化与香港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展现了香港的多元文化传统。
曾有论者指出,“香港是葛亮小说里的梦想之城、现代之城。尽管南京和香港都是葛亮小说的生命之城,但葛亮对南京和香港的把握,确乎是不同的,物事人事自然也就所见所思各异。”[56]通过对葛亮创作中香港城市形象元素的分析和对葛亮笔下香港面孔的描绘,笔者认为,“香港”未必是葛亮小说中的梦想之城与现代之城,葛亮笔下的“香港”是复杂的,是有着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的城市,也是混合着许多老旧特色建筑如唐楼的城市,是充斥着消费符号由填海取地而形成的都市,也是有着传统乡土习俗与自然风情的岛屿,是一座神秘之城与黑暗之城,而又在黑暗中具有温情的一面,亦是中西、沪粤等多种文化的混合体。离岛、北角、唐楼等这些经过葛亮“筛选”后的城市元素与神秘、黑暗、温情这些葛亮描绘到的面孔形成了一个多样的“香港”形象,一个多元交杂的混合体,一个“葛亮的香港”。
①[28][33]也斯:《城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 页,第4 页,第4 页。
②[17][20][25][30][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35 页,第36 页,第51 页,第36 页,第36 页。方益萍的译本中称之为城市意象,但根据具体论述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翻译成形象比意象更为准确,因此虽然引文中为意象,但笔者在论述时主要用形象一词。秦立彦在翻译凯文·林奇的理论时也将其翻译为形象,具体可参见[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③[26][31][32]葛亮:《谜鸦》,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版,第240 页,第240 页,第243 页,第243 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8][24][55]葛亮:《小山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4 页,第4 页,第4 页,第9 页,第16 页,第17 页,第18 页,第16 页,第18 页,第40 页,第41 页,第23 页。
[14]陈浩基:《遗忘,刑警》,新星出版社2019 年版,第31 页。
[15][16][19][21][27][38][39][41][48][49][52]葛亮:《浣熊》,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版,第75 页,第78 页,第80 页,第152 页,第7 页,自序,自序,第36 页,第71 页,自序,第137 页。
[22][36]葛亮:《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7 页,第97 页。
[23][35][53]葛亮:《燕食记》,《收获》2021 年第2 期。
[29]也斯:《香港文化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 页。
[34][40][50]葛亮:《七声》,作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2 页,第210 页,第211 页。
[37]王德威:《如此繁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6 页。
[42]蔡明谚:《论葛亮的〈浣熊〉》,《当代作家评论》2016 年第2 期。
[43][44]葛亮:《问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2 页,第50 页。
[45]刘俊:《“老灵魂”的历史沉迷、神秘追求和物的寄托——论葛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 年第16卷第1 期。
[46]葛亮:《侧拱时期的莲花》,《花城》2021 年第6 期。
[47][54][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 页,第6 页。
[51][56]刘红娟:《葛亮论:城与人,诗与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