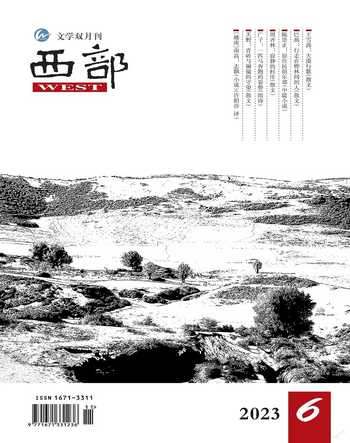潮湿岁月
安宁
一
起床后去鲁院的食堂吃早餐,已经八点半了,估计食堂早已刷了碗盘,进门有些歉疚地问师傅还有饭没,食堂工作人员正一字排开埋头吃饭,见我来,开玩笑道:“还有,你要晚来一会就没了。”不知是内蒙古人饭量大,风卷残云全吃没了,还是我的确去得太晚,每次去食堂,都几乎是最后一个用餐。我坐在因为人少而显得空旷的食堂里,面对着一群穿白色工作服的师傅,享受着这份孤独的美好。我喜欢听他们说笑,操一口北京腔,带着一些小小的得意与骄傲。
饭后去红庙汽车站旁边的一个水果店,取昨晚落在那里的衣服。带着一些可能被人给昧下的怀疑,打车抵达那里,卖苹果给我的小姑娘正忙碌着,我一说来意,她立刻带着歉疚的微笑拿出我的袋子,说:“是这个吧?”失而复得,忍不住欣喜,并对这个明显是外地来的小姑娘心怀感激。
北京的外地人真多。鲁院门口沿护城河的一带,全部都是外地打工者。昨晚打车经过窄窄的巷道,看到他们在下班后真实的生活。房子破旧得像很快就要被拆除的样子,我想象他们的床铺应该是沙发搭建而成,靠门,与收来的破烂堆在一起,需要努力扒开东西,仔细辨认,方能看得清床上的被褥。司机对我讲起这里居住的一户同乡,一家人出售水果,一年竟然可以挣到二三十万。只是,说不上他们是否幸福,男人负责用面包车运输水果,女人负责在集市出售,而他们后半生的指望——独生子,则负责吃喝玩乐,什么也不做。他们的生活,可以一眼看到底——攒了钱,给儿子在老家娶个媳妇,媳妇或者在家生养孙子,或者一两年后,成了旧人,过来挽起袖子,帮婆婆忙,最后,时间长了,也就和丈夫一起,成了自己父辈的模样,做了在京城出售水果的小贩。
护城河右拐,是一溜沿街的杂货铺,卖五金的,修三轮的,做棉被的,售杂货的。见一年轻媳妇,正和她的老公在支起的木板架上,做一床棉被。一个卖水果累了的老太,坐在年轻夫妇店门口的马扎上,跟他们话家常,说起有一个邻居保姆,曾是他们的老乡,有和他们一样的乡音,人很善良淳朴。我喜欢这样素不相识的聊天,没有功利,没有面具,彼此打开,让一个陌生的人,听听陈年的旧事。只有陌生人,才会让你真正袒露内心的种种恐慌、担忧、疑虑、善意和纯真。但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学,却因为彼此曾经有过芥蒂,或因职务级别的高低而生出隔阂,怀着一些无端的刻意的疏离,反而无法交心。
还看到一家店铺门口,有一个卖葱的胖女人,一个本地老太太拼命压价,要少五毛钱购买,胖女人头也不抬,只道:不卖!胖女人的胖儿子长得白净,却喜欢在葱堆上打滚,是个大约四五岁的男孩,一脸幸福模样,他将母亲刚刚摘下来的破败葱叶,全部堆到刚刚整理好的葱上,而后开心地爬上葱堆,等着母亲来训。果然,母亲一回头看见,生了气,边呵斥他,边重新打理大葱。等我转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那里已经围了一群新的顾客。胖女人的小儿子,则拿着一根长相颇似飞鸟的大葱,嘴里咿咿呀呀地喊叫着什么,并做出飞翔的姿态。那根大葱,在他手里俨然成了一件艺术品,有纯白的身体,绿色的翅膀,和一颗飞扬的心。我很想用相机拍下那个瞬间,又怕打扰了他的美梦,只能微笑着看上一眼,而后悄无声息地走开。
与这一溜杂货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刚刚建成的豪华高档小区。2008年我到这里时,这片小区还是和对面一样的杂货铺,而今,只能通过对面的模样,来想象它过去的样子。瞥见一辆豪车里走出四个高挑的外国女孩,从那令人目眩的高跟鞋可以大致推断,她们大概是模特之类的职业。其中一个女孩,吸一根细细的女士香烟,走在不太平坦的水泥路上,依然身姿优雅。只是,她顺手将烟头扔到一摊水洼里的时候,有些电影里女特务的傲气。
阳光有些晒,我跑到鲁院左边的农贸市场里逛了一圈,决定,以后想吃水果,就在这里买。因为,这里新鲜的富士苹果,比昨晚我落下衣服的水果店,整整便宜一塊五。北京真是一个三教九流都能生存的地方。
二
鲁院的小院子,据说只有八亩地,我觉得叫“巴掌地”更合适。它小到只有一个食堂,一个兼做教室、宿舍、报告厅、娱乐室的五层楼房,还有一个门口兼做收发室的保安室。
饭后学员们在小小的院子里四处走。小院虽小,却有许多值得品评之处。食堂师傅们在角落种的一排丝瓜,已经开始爬秧。一根根铁丝早已连到食堂的房顶上,等着丝瓜攀爬。饭后大家闲着无事,会将丝瓜当成小猫小狗一样侍弄一番。
服务生中有一个大约刚刚二十岁的男孩,脸有些瘦长,很像一个日本明星。他估计是新来的,吃饭时总是最后一个,负责给女孩子们拿拿碗筷,给师傅们递递盘子。我喜欢这个沉默内向的男孩,我猜测他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即便如我这样的写作者,也难以窥探到那个世界的全部。女孩子们嘻嘻哈哈,有时还会拿他来开玩笑,他从来都不生气,好脾气地笑笑,而后继续埋头吃饭,就像那饭里有非常神秘的东西,可以持久地吸引着他。
食堂后面的一排红砖平房,是服务生们的宿舍。我常常好奇里面的生活,很想走进去,装作拍一张照片,而后看看里面某个女孩子晾晒的内衣,或者听听她们和老家的某个男孩说着的悄悄话。
更多的时候,我是在生了锈的楼梯旁,看他们来来往往。我总觉得他们是鲁院里最快乐的一群人,彼此没有职务的高低,没有写作水平的较量,不会暗暗地揣摩或者观察,他们的眼睛里,全是世俗的烟火与日常的琐碎。他们更像是这个院子的主人,不管多么有名气的作家,在他们眼里,都只是普通的食客。他们无需奉承,也不必嫉妒。中午有电影放映,年长的杨晓蕾老师问他们是否一起乘车去看,掌勺的师傅用北京腔毫不客气地回绝:我们去看,谁做饭啊?那语气里还有一股子这鲁院缺了他们不行的骄傲。而在我问起鲁院会不会把学生全部搬到新校区,将这里出售时,那师傅立刻朝我一瞪眼道:谁说要卖啊?这院子永远都是我们鲁院的!
以鲁院人自居,大约是他们的优良传统。每届新生开学,物业人员也会派代表出席,和院领导坐在一起,给来自各地的学生讲话。所以他们才会将鲁院当做自己的院子,甚至每天剩下的饭菜,看看还能吃的,也不会像别处师傅,全部倒入垃圾桶里,而是用干净的餐盘装起来。
今天下雨,院子里有些凉意,我在房间里写字,越过低矮的食堂,有两只发情的猫在隔墙遥遥呼唤。对面小区里谁家的孩子在弹琵琶,大约是着急看电视了,便颇急躁,速度像发了怒的河水,快速地冲击着人的耳朵。此外,便是隐约的车声。这小小的院子,到此刻,才能让人体会到它的静寂与美好。对面高楼上的灯,全都熄了。雨滴从院子里细细的草茎上,倏然滑落下去。这难得的一方静谧,浸润着白日浮躁的内心。
三
鲁院真正的好,其实在于,可以让一些有文字理想的人,在这里寻到与自己同质的人。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彼此审视观察以后,大家逐渐熟识,同类的人,会走得更近一些,像两株气息相近的植物,向着蓝天下那共同的阳光,不断地靠近,缠绕,并碰撞出让人欣喜的火花。
我的左邻右舍,一个是市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老贾,一个是在北京做自由编剧的阿雷,皆来自包头,而且,他们还是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的同学。当然,这些都是在前天美好的夜晚,我们彼此打开心灵的大门后,才知晓的。我的左邻,也就是我的同桌老贾,是一个沉稳成熟的文艺男中年,在最初的时候,除了日常的寒暄,我们很少交流。他扛着一个上万元的尼康专业相机,沉默地来去。那相机上不知何时被谁给碰裂了一块,于是便伤病员一样缠了一圈圈的透明胶带。我在第一次上课之前,曾经想要打破尴尬,问了他一些无聊的问题,但得到他一律矜持的简短回答后,便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废话。我们彼此像一只蜗牛,只是碰了一下触角,便立刻缩回安全的壳里。而我的右邻阿雷,其实在来之前,我便从一位与我正在合作的导演口中得知了他的名字,他也刚刚与这个导演合作完一部影片。我猜测他或许也从在读的文研班同学口中听说过我的名字,只是因为彼此的一点骄矜,即使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也选择保持沉默。
我不知道我的左邻右舍是如何商量要请我出去喝咖啡的。同桌老贾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我恰好要准备写作,再加上尽量减少应酬的处事原则,我委婉地拒绝了他。而右邻阿雷在第二天以老贾的名义邀请我的时候,我正在南锣鼓巷的某个咖啡馆里,一个人对窗看夜色中的风景。只是这一次,出于礼貌,我答应第二天请他们一起喝咖啡,并买了两个小巧的笔记本,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三个人沿着鲁院旁边的护城河,在黄昏中走了很久,这中间我很快与阿雷有了更深的交流与创作上的碰撞。而同桌老贾,则依然沉默少语。直到走累了,我们进入一个咖啡馆,喝下一点啤酒的时候,我才终于看到了他掩藏在深处的灵魂。
我们谈了一些什么呢,其实并没有太过深刻的东西。只是彼此交换了喜欢的书籍,看过的电影,走过的城市,做过的事情,有过的困惑,并听了咖啡馆里一个女孩子一首接一首唱着的忧伤的民谣。
但是这些足够让我们坦诚地打开内心的某扇窗户,看到彼此同质的那一部分。并因此在第二天,不再有之前的隔阂。
而今天午后的联欢,大约会让更多的人,寻到彼此的同类。我惊讶于某个坦白自己T恤十九元的女同学,她有惊人的诗歌朗诵天赋。我也诧异那个外号叫“胃出血”的黑脸膛男同学,还有几分的幽默感。而一个自称为农民的总是孤独来去的草根导演,则有出色的自编自导自演的才华。在大热天里,常常穿了蒙古袍和靴子来上课的蒙古族同学,一曲长调,立刻让全场安静下来。
晚饭后,在网上跟同桌聊了他日常所写的文字和拍摄的照片。我让他去掉对我的称呼中带有明显距离感的“老师”二字,而我也开始放开,不再是一副大学老师的严肃模样。其间还收到正在散步的阿雷的短信,提及昨晚他和老贾也去了南锣鼓巷,又说,外面的空气是潮湿的,有些江南的感觉,他喜欢这样湿漉漉的空气。我回复他说,我也喜欢你们,还保有一份理想的文艺男中年。
四
成曾樾副院长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体验、切入和细节”的课。老先生地道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人家王朔一个院子里长大的。自己比他年龄大,却写不出比他大的成绩来,所以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大院里开拍的时候,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啊,想自己白吃这么多年饭了!北京话里的幽默,常常有点石成金的特效,无论怎样平凡的一件事,到了成老先生口中,都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所以尽管他讲得课程不是多么深奥,却是开课以来最活跃的课堂。他几乎将课讲成了单口相声,几分钟就有一个包袱抖出来,而且毫不吝啬对自己没写出传世作品的嘲弄,好像生活在他这里,就是一个玩笑,碌碌无为也好,光芒闪烁也罢,都可以一笑而过。
偶尔也有实在不擅长讲课的老师,空有一肚子学问,却表达不出,让下面听课的我们,恨不能跑上去替他讲完。有实在坐不住的学生,瞅瞅最后一排班主任老师不在,背了书包就大踏步走出了教室,只剩我们这群胆小老实之辈,带着同情之心,陪着讲得头上冒汗的老师,无休无止地枯坐下去。
北京電影学院一老先生性子颇急,恨不能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一生全部心得都倾倒给我们,他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一直讲到十二点半,过了下课时间已经一个小时,而食堂里的师傅们也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到一楼大厅打起了乒乓球。当他试图再给我们“简要”说说某个剧本的问题时,大家都善意地笑起来,并私下里议论:他来之前,肯定是吃了一顿豪华早餐的,否则,怎么会一口气讲三个半小时,还不觉得饿。连做总结的班主任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几次想要站起来,告诉他时间到了,可是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模样,终是不忍心打断,任由他洋洋洒洒地讲下去。后来有人实在饿得头晕眼花,受不住了,起身开门出去,才将他从梦中惊醒,并一再向同学们致歉。
不得不承认,老先生的课内容颇为丰富,影视圈里的名人轶事和幽默笑话,他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讲到葛优,说当年梁天结婚,请了当时任职主任的他前往,葛优到后,主人一一为他介绍,他握完了手,大家都等他说话,结果他半天才憋出一句:这他妈的都是主任啊!老先生想了半天,才明白他这表面是说一群人的职务,实际上是在变相骂人贪恋职务内心虚荣呢!又提及大家对演员潜意识的歧视,说当年他去北京电影学院任教,老母亲耳提面命,让他千万别领个演员回家给她当儿媳妇,老先生幽默,说,就凭您儿子这张丑脸,也没那本事钓美人鱼啊!
也有年龄不大却比老先生还要心高气傲的同学提问,老先生一律以批判的姿态,将人的热情打击回肚子里。其余人看了,立刻乖乖做了看客,随了人群嘲笑一番那个做了出头鸟并被打了一炮的人,然后,任由老师如何启发暗示,都不再提出问题。
我很羡慕那个在教室里每天给老师们倒水的服务生。她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安静听着,并在合适的时候,起身服务。我总是幻想,她听了这么多名人的课,某一天,或许会悄无声息地写出一个名篇来。这个幻想萦绕在我心里,当我回头看她的时候,就感到空气中充满温暖又神秘的气息。
五
夜色笼住鲁院小小的院子的时候,我喜欢穿越走廊,假装去提一壶水,然后用余光观察每一个房间。大多数的房间,都是紧闭着的。写作的人,总是需要一方安静的天地,来思索白日的喧哗。鲁院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有投缘的人,可以关起门来,说一些絮语。有喜欢孤独的人,可以在这方私密的空间里,听着远处的车水马龙声,想一下虚无的心事。而我,则喜欢游走在庭院里,看一眼于夜晚进入鲁院的陌生男人,或者女人。
在来鲁院以前,听说过很多作家们的隐秘八卦。当然,大多数都是关于爱情。那些短暂却足以萦绕一生并滋养了作家文字的爱情,总是比世俗生活更能引起人的好奇。似乎我们可以凭此窥见一个作家文字背后的东西,看到一篇小说的来处、一个角色的所指。
一天夜晚,当我穿过四楼一间间的女生宿舍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与我并肩而行。我忽然间生出好奇,故意放慢脚步,跟在他的身后,看他很熟练地推开一扇虚掩的房门,而后迅速将门关闭,并将门锁连转两圈。门锁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听起来让人浮想联翩。这意味深长的锁的转动声,让我觉得,那个声音能表达门后所有的情欲热望。
鲁院小小的院子里,每日都有只猫,在墙头上发出阵阵哀怨的叫声。我常常希望能有另外的一只猫,来呼应它的喊叫,而不是让它在孤独的夜晚,对月空唤。而在鲁院,精神趋向一致的人群中,很容易寻找到气息相似的同类。这种气息,沉淀在精神层面,与良师的教授,一样重要。
六
闲暇的时候,会和朋友出去游逛,在有女孩子唱歌的咖啡馆,或者前门某个哈根达斯店里有诱人广告的角落,再或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头巷角。我们皆是过客,但却觉得,北京更适宜像我们这样只是路过的人。因为路过,所以可以有闲暇,安静观察它所有的好,而不是像那些在此地每日挤公交地铁上班的白领,被它的高速行驶带领着,疲劳奔走。因为隔门观照,它就在祛除了噪声的咖啡馆的外面,有了让人心动的静寂的姿态。
今天去鲁院附近的八里庄南里小区,在一家几平方米的小店,要了一份毛豆花生、一份过桥米线,而后在室外有风的简易饭桌上,跟一个陌生的小区男人,面对面吃着。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喝一瓶啤酒,吃几瓣大蒜,点一份粉丝,边在风里看着行人,边闲适地自斟自饮。我送他一些毛豆,让他打开了话匣。他提起小区的房价,年幼时租住的陪读的父母,八岁时离开的湖南老家,在我的山东老家度过的六年时光。他讲述这些的时候,脸上有跋涉万水千山后的从容与平静。他和路过的小贩、邻居或者熟人打着招呼、话着家常,他是这个地处繁华北京的小区里,最普通的一个人。尚未退休,也看过了很多的风景,可以不必焦虑地一心行走,而是每日像这样,在某个寻常的角落,坐下来,粗茶淡饭,却内心淡然。
饭后又去了十里堡北里小区散步。看到一家来北京打拼的外乡人,住在一个角落的平房里。桌椅就放在楼房圈起的小天井里,两个小孩子在认真地摆着碗筷,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叽叽喳喳的,唤着爸爸妈妈,丝毫不会关注外人。他们的饭菜,也是简单的,几碗米饭,一大碗青菜。我觉得,他们会吃得很香,在生活简单的时候,人的食欲,反而会无比地饱满,每一种食物都充满了诱惑并结实地抚慰着饥饿的肠胃。这样的一个时刻,像侯孝贤电影里温情的长镜头。我喜欢这个时刻的北京,祛除了繁华与虚荣,水洗一样,回归至日常的琐碎与静寂,它在这样的夜晚,是对所有人敞开着的,包括只是路过的我。
许多年没有看到像今晚这样明亮美好的月亮了。以至于我将睡眠推迟至两点,只是为了抬头看它。它在没有云朵遮掩的夜空里,如一枚饱满的果实,是熟透了的,透着羞涩,等着懂它的人,这样温柔地与它对视。我知道此刻鲁院的宿舍里,一定有同样的一个人,推开窗户,注视着它缓缓地从窗前经过。楼道里悄无声息,许多人已经睡了,那个和我一样失眠看月亮的人,一定与我的灵魂,离得最近。
七
中午下了小雨,空气里有了一些离别的意思。食堂里的师傅们依然在尽职尽责地炒菜做饭,姑娘们也照例嘻嘻哈哈,说说笑笑间就收拾好了东西。晚间去吃饭,见那个在联欢晚会上唱歌的食堂小姑娘,为了给大师傅去宿舍拿一袋吃了一半的豆腐干,从食堂窗户里嗖一下就跳了出去,不过片刻工夫,又猫一样敏捷地跳了进来。食堂后面的那排小平房,尽管很是破旧,但女孩子们依然从低矮的房间里,每日换上漂亮的衣服,嬉笑着走出来,结伴出去散步,或者在小小的院子里,逗引那只总被作家们写来写去的猫。我喜欢這样的时刻,觉得世俗的生活,充满了风情。好像一个女人,站在烟熏火燎的烧烤摊旁,忽然整理了一下头发。
饭后出去散步,想起最初抵达这里的时候,曾经觉得孤独,喜欢离群索居,少与人交流。而现今,在与不同的人产生交集、并碰撞出火花之后,再一个人行走,心里却慢慢浮起雾一样的惆怅。忆起社会实践的时候,去北京郊区一处四面环山的明清古村落,正是雨天,夜晚山间雾气浮动,如在仙境。和朋友坐在山石上,聊起被世俗生活包裹着的微弱的理想,聊起年轻时曾经弹吉他弹到手上起了茧子,而今却已经几年都未曾碰触。理想是什么呢,它像山中的雾霭,明明知道阳光出来,就会全部散去,可是,至少在那一刻,它让人觉得无比美好,且值得追求。我喜欢与有理想的人在一起,不管他是一事无成还是碌碌无为。那一点理想,却让他瞬间有了光,犹如清晨一株草上,一滴露珠的光华。
即将离别,酒成了最好的让人打开自我的钥匙。昔日冷漠的,此时多了一抹温情。一个城市有过隔阂的,也敞开胸襟,让那世俗的疤痕,慢慢消除。两日前李敬泽先生讲过一堂关于人的命运之偶然与必然的课程,忽然想起,我们与每个人,相聚在这个质朴的庭院,接受文学的滋养,吃同一个食堂的饭菜,在同一棵树下散步,喂同一只流浪的小猫,看食堂师傅说说笑笑,透过同一片银杏树叶仰望蓝色的天空,皆是人生的偶然。恰是这样的偶然,汇流成河,丰富了我们个体的生命。
一个有着美好嗓音的女同学,敲开了我的门。她有些微醺地站在我面前,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最终并没有聊得太多。我从别人口中,知道她离婚,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我依然喜欢她身上醉美人的气息,喜欢她唱男声戏曲时的豪迈,和朗诵诗歌时的动人。
夜已经深了,今晚云层很厚,看不到月亮。忽然想起几天前看到那饱满的月亮,它行经我的窗前的时候,我恰好在与朋友聊天。此后再看到圆月,我想月亮一定还会帮我记得,在鲁院与人窗下一起看月的时光。
八
世界上所有的别离,大约都是一样的。离去的人,永远不知道送别的那一个,是怎样难过和孤独。而空了的房间,又常常比空了的心,更让人觉得空旷难挨,让人立即想要落荒而逃。
当我送完朋友,一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校园里,看到已没有人打乒乓球的大厅,凉亭下空了的座椅,被打扫干净的啤酒渍,无人再来唤的黑猫,有些荒凉的走廊……我的心里才发觉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失去,一直到最后,那个地方,忽然完全地空了,无论什么,都无法再将其填满。
我去附近吃了梅州小吃,一個人坐在门口的桌子旁边。昔日与朋友一起坐过的位置,已被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占据。我依然要了一份担担面,吃着,眼前浮现出朋友的影子,还开玩笑告诫我别总是写哼哼唧唧无关痛痒的文字。还有其他同学,路过,打招呼。饭馆里依然是热闹的样子,重庆的女服务生身材小巧却反应灵敏,可以一边给人点菜,一边对离开的顾客点头说,欢迎下次光临。只是,我不忍再看这样的日常,只在吃完后坐着发了一会儿呆,便起身悄无声息地离开。
学院对面的十里堡北里小区的石凳上,还是空无一人。我一个人坐在上面,抬头看树叶间闪烁的一小片让人感伤的蓝,并想象着那一轮始终未曾再出现过的月亮,会隐匿在哪一片云朵后面。我想起与朋友散步至此,讨论过的猫猫狗狗,还有一个老人养的不知名的漂亮小鸟。谁家的孩子在小路上尖叫,风里飘荡着花朵的香气,还有油炸果子的富足味道。这是北京最素常的一个傍晚,老人们摇着蒲扇,说着琐碎的闲话,没有人知道对面的鲁院,正历经着怎样的离别,所有的悲伤,在他们这里,毫无印记。可是我知道,被他们忽略的某些生活的瞬间,早已植入我与朋友共同的记忆之中。
我挥手送朋友走的时候,没有流泪,只抓拍了一张朋友乘车离去的背影。夜晚袭来的时候,我拍下空旷的校园,发给朋友。朋友回复说,感谢那些我们坐在不同的窗前,一起看同一个月亮的夜晚。这一次,我的眼泪,终于从最柔软也最深藏的一个角落,流淌出来。
我知道那一刻,我不只是怀念一个小小的位于八里庄南里27号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