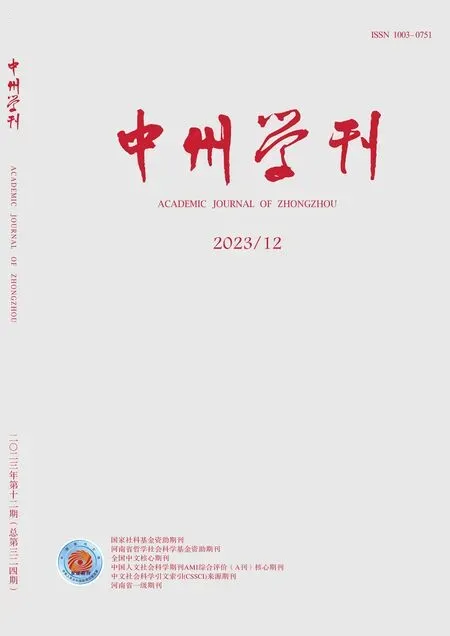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
向柏松
神话仪式叙事的先导是神话仪式理论。神话仪式理论在19世纪末由英国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等创立,后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延绵发展,在神话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话仪式理论已触及神话仪式叙事,但其关注点在神话与仪式关系的阐释,神话仪式叙事并未得到重视。20世纪末广义叙事学理论兴起,神话仪式叙事才真正确立,神话仪式叙事开始与神话语言叙事等并列,成为一种独立的神话叙事方式。借助广义叙事学的理论视野,依据神话学理论,我们可对神话仪式叙事概念作出如下解释:神话仪式叙事是指通过仪式来展演神话情节或神话信仰观念的叙事形式。在神话仪式叙事中,仪式是一种独立的神话系统。神话仪式叙事与神话仪式理论既有渊源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神话仪式理论所涉及举行仪式的人物只是神话中的人物,而神话仪式叙事中的人物可以是神话中的人物,也可以是神话之外的叙事主体,后一种现象更为普遍,这在客观上拓展了神话仪式叙事存在的范围。中国的神话仪式叙事历史悠久,经历了由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到神话祭礼仪式叙事再到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演变历程。本文试图展现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历程,揭示其最终演进到民俗仪式叙事的必然发展逻辑,并揭示其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存在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中国神话巫术仪式叙事
巫术仪式经典理论起源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感应仪式”,此后,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作了系统解释,创立了巫术仪式经典理论。他在《金枝》一书中提出:“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1]根据弗雷泽的理论,巫术仪式可以解释为:巫师或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借助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接触或模拟某种对象而达到求吉或降灾目的的行为。早期产生的神话多与巫术密切相关,或是描写巫师的活动,或是表现、演绎巫术仪式的内容,从而形成神话巫术仪式叙事。
神话巫术仪式叙事的主体是巫师,所以神话中多有关于巫师活动的叙事。《山海经》中有不少关于巫师人物的神话叙事,通过寥寥数语展现出一个个神奇诡异的巫术世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2]320神话叙述10位巫师在灵山不断上升天庭、下降人间,这是他们在实施人神沟通的巫术,10位巫师同时行动,非常壮观。灵山生长各种草药,也暗示巫师有起死回生的法术。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2]188这里叙述群巫在登葆山举行上天下地的巫术仪式。《山海经·海内西经》则记载了群巫救死扶伤的具体巫术活动:“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2]2506位巫师借助不死药举行起死回生的巫术活动,试图救活被杀死的窫窳。在早期农业社会,巫师经常施行祈雨巫术,这也成为神话巫术仪式叙事的内容。《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2]188女丑,袁珂先生认为是女巫,这里反映的是古代天旱暴女巫祈雨巫术。《礼记·檀弓下》:“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3]178郑玄注:“巫主接神,亦觊天哀而雨之。”古时久旱不雨时,就要举行暴女巫巫术,让女巫在太阳下暴晒,以引起神灵同情,降下雨水。神话表现了女巫举行祈雨巫术时被烤死的情景,女巫站在太阳下祈雨,死时用右手遮住脸,状况十分惨烈。神话巫术仪式叙事所述巫师,曾经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但也时常沦为巫术的牺牲品。
神话巫术仪式叙事表现的内容丰富,既涉及部落或国家政治层面,也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主要论述生产、生殖、战争、治水等内容。中国农业生产起源甚早,农业生产十分依赖风调雨顺,人们便创造了司水龙神,并经常对其施行巫术以祈雨,由此形成龙的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其内容是模拟龙的形象或行为,属于模拟巫术。比如造土龙,即是模拟龙形祈雨的巫术仪式叙事。《淮南子》卷四“土龙”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4]241裘锡圭先生认为:“‘作龙’卜辞与焚人求雨卜辞同见于一版,卜辞中并明言作龙的目的在为凡田求雨,可知所谓‘龙’就是求雨的土龙。《佚》二一九:‘十人又五□□龙田□,又(有)雨。’上引第二辞很可能是占卜‘作龙于某田’之辞的残文。”[5]

神话巫术仪式叙事也涉及战争,如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巫术叙事。《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2]347黄帝战蚩尤神话并没有正面叙述战争,而是叙述了战争中的巫术对抗行为。黄帝先是用应龙施行巫术。《大荒东经》载:“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2]292郭璞注:“应龙,龙有翼者也。”应龙是有翅膀的水神,可见黄帝所用之法为水神降雨巫术。蚩尤则针锋相对,利用水神风伯、雨师作法,纵大风雨,以遏制应龙之水,也是运用水神巫术。黄帝又用魃来施行止雨巫术。魃,旱神。郭璞注:“音如旱妭之魃。”郝懿行注:“《玉篇》引《文字指规》曰:‘女妭秃无发,所居之处,天不雨,同魃。’”[2]347旱魃,为旱神,黄帝用她来对付蚩尤的风伯雨师,正是针锋相对。旱魃止住了风雨,黄帝在与蚩尤的斗法中取胜,这从侧面表现了黄帝部落赢得了这场战争。

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周代逐渐式微。但是在漫长的史前时代,神话巫术仪式叙事为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状况的民众增添了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勇气,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对此,马林诺夫斯基有充分的肯定,认为巫术“使人的乐观仪式化,提高希望胜过恐惧的信仰。巫术表现给人的更大价值,是自信力胜过犹豫的价值,有恒胜过动摇的价值,乐观胜过悲观的价值”[10]113。同时,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话巫术仪式叙事所体现的人定胜天的自信精神,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神话巫术仪式的巫舞促进了中国歌乐舞合一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神话巫术仪式直接催生了道教的形成,神话巫术仪式所涉及的巫术方法、技法以及一系列活动,如呼风唤雨、请神送神、招魂续魄、辟邪除恶、驱魔治病等,都对道教仪式和法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神话巫术仪式叙事毕竟是人类蒙昧时代幻想的产物,并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进入文明时代后逐渐为祭礼仪式叙事所替代,但是,神话的巫术仪式叙事作为一种表达人们趋吉避害愿望和心理安慰的方式,仍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长期潜存于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多种民俗仪式的文化之根。
二、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祛除巫魅”与“理性化”两个基本观点,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现象。他认为,一切宗教都可在原始巫术中找到其痕迹,他相信人的思想是渐趋理性的。在中国,由于儒家理性文化逐渐兴起,远古至夏商表现突出的巫觋、卜筮文化进入周代而转化为祭礼文化。巫师渐渐让位于祭司,巫师的巫术活动最终转变为祭司的祈祷献祭职能,由此而形成带有理性化色彩的规范体系——周礼。与此同时,神话的巫术仪式叙事转换为祭礼仪式叙事。重要的祭礼活动都由祭司和天子主持,因此,祭司和天子成了神话仪式叙事的主体。神话的巫术仪式与祭礼仪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试图通过虚幻的法术达到人类的目的,后者则通过对神灵虔诚的祭祀行为来达到目的,两者虽然都表现出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但后者显然减少了虚妄的成分,突出了人自身的作用,如在祭礼中的奉献与虔诚。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自周至近现代,延续时间长,涉及内容广泛,虽然打上了等级制度的烙印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对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涉及对象非常广泛,最初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思想基础,涉及的对象包括天地万物和人类精神所能及的一切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许多自然神淡出了神话祭礼仪式叙事的范畴,只有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神被保留下来。即便如此,神话祭礼仪式叙事对象仍然十分广泛。涉及自然界的有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霞、雾、露、霓、虹、水、火、山、石以及动植物等神灵对象;涉及人类社会的有神话人物神、历史人物神、祖先神、生育神、行业神、世俗生活神、巫觋、魂魄等。如果对神话祭礼仪式叙事对象作概括性划分,则可以分为天神、地神、人神等类别。天神祭礼仪式的主要对象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形成了相关的神话祭礼仪式叙事。
《周礼》是神话巫术仪式叙事转向祭礼仪式叙事的标志性典籍。在《周礼》中,祭日祭月仪式叙事代替了浴日浴月巫术叙事。周代已有帝王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祭礼。《周礼·春官·典瑞》郑玄注:“祭日月,谓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11]所记即为帝王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礼制。《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祭日于东,祭月于西。”[3]76在高台祭日,在坑穴祭月,祭日于东郊或东门之外,祭月于西郊或西门之外,都是根据日月所代表的阴阳属性做出的安排。《史记·孝武本纪》载:“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12]282用牛祭日,用羊猪祭月,也可见古人更重视祭日。
神话祭礼仪式叙事涉及地上的自然神灵主要有山神、河川之神、动植物神等。就动物神而言,有自然与人为制造的区别,这里主要讨论人为制造的动物神——龙神。先秦时代,龙是神话巫术仪式叙事的对象。汉代以来,与龙有关的神话巫术仪式叙事演化为祭祀仪式叙事,龙成为祈雨时的主要祭祀对象,凡有河流、湖泊、井泉之地,莫不建有龙祠、龙坛,供人们祭祀之用。唐代官方祈雨祭祀的对象主要为龙。据《文献通考·郊社考》,唐玄宗在开元二年(714年),降诏祠龙池,又降诏修建祭坛与祠堂,每年仲春都要举行祀龙大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有龙见于兴庆池,因祀而现也”[13]2766。《文献通考·郊社考》载:“京城东旧有五龙,即唐开元中因兴庆宫池设置,常以仲春祭之。”[13]2767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十月诏告天下,为龙封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由于朝廷的提倡,道教、佛教也积极参与祭龙祈雨。祭龙仪式盛行,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龙的祭礼仪式逐渐转化为大众的民俗仪式。
神话祭礼仪式叙事涉及的人神主要有三皇五帝、大禹、西王母以及其他诸神等。三皇之中的女娲,在神话的巫术仪式叙事中,既是补天的治水之神,又是抟黄土造人的创世大神,还是与伏羲配成夫妻的生殖大神。所以,在神话祭礼仪式叙事时代,女娲就成了神话祭礼仪式叙事的重要对象。《论衡·顺鼓》载:“雨不霁,祭女娲。”[14]久旱不雨,就要祭祀女娲,以祈求雨水。《路史·后纪》卷2罗泌注:“《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始此始矣。”[15]143祭祀女娲,又具有祈求婚姻与生殖之意。炎黄是中华人文始祖的代表,关于他们的祭祀活动典籍多有记载。《史记·封禅书》最早记载了炎帝祭礼:秦灵公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16]347。据说炎帝之祀,始于黄帝。《路史·后纪》载,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15]189。《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史记·封禅书》又有祭祀黄帝的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16]347秦国在祭祀炎帝的同时,又祭祀黄帝,可以说是开炎、黄并祀之先河。从《国语》《礼记》《礼祀》等典籍记载可见,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时代均有炎、黄之祀。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祖先神,其祭礼自先秦至今一直延续不断并日趋隆重,炎、黄二帝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炎、黄祭礼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华夏儿女的重要载体。
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的叙事者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即上层与下层的区别、官方与民间的区别。在神话巫术仪式叙事时代的早期,并无等级划分,人人都可以施行巫术与神沟通;到了后期,颛顼施行绝地天通法术与制度,禁绝下层施行与天沟通的法术,与天沟通的巫术成了巫师和部落酋长的特权。从此,神话巫术仪式叙事的叙事者逐渐有了等级区分。进入神话祭礼仪式叙事时代,叙事者的等级划分越来越严格,这种等级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祭祀对象的区别。一部分祭祀对象被赋予了王权或官方色彩,只能为天子或官方所祭祀,百姓不能参与其间。这是宗法礼制的产物,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宗法礼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祭祀对象。《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3]194周代对祭礼对象作了严格的等级划分。二是祭祀目的的区别。官方的祭祀是为了祈求政权的稳固和社稷的兴旺,祭祀本身是一种王权的象征。如秦汉以降天子举行的封禅大典,就是一种宣告获得王位的政治大典。民间的祭祀则只是为了求一己之福祉。三是祭祀仪式的区别。官方的祀典往往规模宏大,参与者众多,并有严格的程序;民间的祭祀则多属个人行为,随意性强。
当然,民间祭祀与古代官方祭祀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也存在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方面。官方阶层的人物,在官方活动中执行的是官方祭祀,在日常生活中则有可能参与民间祭祀。官方的许多礼制也是在民间祭祀基础上形成的,如天子祭祀名山大川,就是在民间祭祀自然神仪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傩本是上古民间驱鬼的仪式,周代以来成为宫廷祭仪。《礼记·月令》记载有周代行傩祭的情况:“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3]233这里的“难”即“傩”,所记为宫廷行傩巫术以驱除春时的疫鬼。傩进入宫廷后,被制度化、程式化,成为一种盛大的祭典;而民间仍有原始、自然状态的傩在流行。官方的祭礼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等级制度,维持其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承礼仪文化的积极作用。
神话祭礼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礼仪之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早在周代就形成了完整的礼仪体系,《周礼》《仪礼》《礼记》所记的周代礼仪,内容囊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等。周代的礼仪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而且波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所以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国礼仪源自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许慎《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7]也就是说,礼仪来自祭祀神灵的活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祭礼活动日益频繁,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日益扩大,逐步形成各个方面的固定祭礼仪式,最终融合成完整的礼仪体系,包括政治与生活两大类别。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直到近现代,随着礼仪的改革,传统礼仪大量缩减和改变,发展成为真正现代意义的礼节和仪式,但其与传统仍然存在根系关系。
神话的巫术仪式叙事转化为祭礼仪式叙事是理性化带来的时代进步的结果。夏商周时代,已进入祭礼的时代,巫觋文化已进化为祭礼文化,祭礼不再依靠神秘的巫术力量,而是通过献祭来达到祈求神灵的目的,神灵神秘的交感力量已经淡化。官方掌控的祭礼逐渐形成礼制,礼制对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过度强调礼制,也制约了个体的创造活力。当然,官方的祭礼一旦融入民间生活,就会获得新的生命,逐渐转化为具有生活性、娱乐性、审美性的民俗事象。神话的仪式叙事再一次实现华丽转身,演变为能够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民俗仪式叙事。
三、中国神话民俗仪式叙事
随着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的日益提升,神话的祭礼仪式叙事逐渐向民俗仪式叙事方向转化,祭礼逐渐演变为生活化、大众化、世俗化的民俗活动。虽然神话民俗仪式叙事在潜在层面还保留着神话原型,但已为一般人所难以察觉。
在神话民俗仪式叙事中,神话的神圣性消弭,神灵不再具有神秘的力量,神灵信仰观念也渐趋淡漠。即使是某些带有祭祀形式的仪式,也不再具有祈求与祷告的性质,以至于人们已很难将神话民俗仪式叙事与神灵联系起来。如伏羲女娲在祭礼仪式时代,是人们祈求生育的配偶神,演化为民俗仪式叙事的对象后,虽然仍保留了生育神的神格,但人们已不对其举行严肃的祭礼,而是对之翩翩起舞,以寄寓生育旺盛的意义。在河南淮阳,每年农历二月二日至三月三日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人们都要在女娲庙举行祭祀女娲的仪式,名为“担花篮”,或“担花挑”。“舞时每班四人,三人担花篮,一人打竹板,以数、唱形式伴舞,三副经担,六种花篮,边舞边唱。舞者皆服黑衣,黑大腰裤,扎裹腿,黑绣花鞋,头上裹长五尺黑纱包头,下有二寸长穗。她们大多是老太婆们……主要是敬老母娘女娲。传女不传男。‘担花篮’舞到高兴处,舞者走到中间背靠背而过,两尾相碰,象征伏羲女娲相交之状。”[18]“担花篮”中的舞蹈虽然仍含有向伏羲女娲祈求生殖之意,但已将祈求寓于娱乐之中;虽然是对着神灵起舞,却已无神圣性可言。无独有偶,湖北地区元宵节时也有挑花担表演,这是中原“担花篮”的流变形式。挑花担由三人表演:妹、哥、嫂。妹肩挑用五彩纸花装饰的花担(即花挑),手持方巾,哥手握竹板,嫂右手持扇、左手持方巾,三人边唱边舞。哥与妹相互倾诉情意,嫂子则穿插其间逗趣,舞蹈活泼而风趣。象征男女交合的舞蹈在此变成男女调情的舞蹈情节,已无丝毫神圣性。
又如灶王爷的民俗仪式叙事也已经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相关仪式也不再具有神圣性。灶王爷出身显赫,有灶神为炎帝、黄帝、祝融三种说法。但在民俗叙事中,灶王爷仅仅是位家宅神。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三为灶王节,俗称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祭灶的仪式非常随意,即揭下灶台上的旧灶王神像焚化,换上新的灶王神像(灶王爷形象只是民间木刻印制得很粗糙的纸马),点燃香烛,摆上麦芽制成的糖果等作为供品。吃麦芽糖是这一天重要的民俗活动。传说在这一天灶神要升天朝见玉皇大帝,禀奏人间善恶之事。人们都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于是在这一天与灶王共食吃又甜又粘口的麦芽糖,是希望灶王爷嘴甜,上天专说好话;或者是希望用麦芽糖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说话,以免他不慎说出对全家不利的话。其实,灶王节处于冬季中最为寒冷的日子,吃麦芽糖也能起到驱寒的作用。灶王节的祭祀仪式十分随意、简单,灶神民俗仪式叙事主要是通过饮食习俗食麦芽糖来表现的。
在神话民俗仪式叙事中,神灵的神格已经消失,代替它们的是人们寄托的某种精神、观念或象征。人们祭祀神灵,或是为了表达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认同与弘扬,如祭祀尧、舜、大禹;或是为了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祭祀炎帝、黄帝、妈祖;或是为了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如对福神、财神、寿神、生育神等的祭祀。在此,人们种种愿望的表达只是成为励志的载体,并不会真正将愿望的实行寄托于神灵身上。
神话民俗仪式叙事对中国节日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节日民俗的核心或者主体。中国传统节日民俗几乎都是神话仪式叙事的对象,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神话节日民俗仪式叙事形态。中国节日民俗之所以与神话民俗仪式叙事有着水乳交融般的关系,是因为几乎所有古老节日都与神话仪式叙事密切相关。其一,中国古老的节日几乎都起源于神话巫术仪式或祭祀仪式,与神话仪式叙事有着天然联系。其二,传统节日民俗多是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由琐碎民俗事象发展成为庞大的节日民俗体系,完全得力于神话的神灵信仰仪式的推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国泰民安,还是天灾人祸,神话信仰仪式总是促进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并度过那些特殊的日子。其三,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但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割断包括天人合一、敬天法地等观念在内的神话仪式的传承,使得与神话一体化的节日民俗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换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是一直保持传承发展的势态。正因为如此,中国节日民俗都可以纳入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范畴,形成了几种主要的叙事类型。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出现在多个节日中,形成多种龙神话节日民俗叙事。正月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晒龙袍等,都属于龙神话民俗仪式叙事。农历二月二龙靠近惊蛰,这也是春回大地、万物生长、春耕开始急需雨水的时节。为了使龙回归,人们就要象征性地举行迎龙回归仪式。龙抬头节最常见的接龙民俗仪式是撒灰,以撒下的灰线引龙回归。《帝京岁时纪胜》载:“二日为龙抬头日。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过。”[19]137龙抬头节引龙回归的仪式还有水引法,即到井、泉、河边挑水回家,注入水缸。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赤城县志》载:“(二月)二日,各家晨起汲水,谓之‘引龙’。”[20]137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龙是水物,生活于水中,而二月二正是龙苏醒之日,此时汲水,水中就有龙的灵魂,挑水回家,就能引龙回归。二月二龙神话仪式叙事还涉及五花八门的饮食民俗,用节令食品来象征龙的身体。如,猪头象征龙头,面条象征龙须,水饺象征龙耳,薄煎饼象征龙皮等。食用这些食品,本身就包含迎接龙的回归,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意义。《燕京岁时记》:“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19]791915年《铁岭县志》载:“二日谓‘中和节’,饮春饼。”[21]1935年《张北县志》载:“二日,俗谓之‘龙抬头’。各家皆焚香供神。有食猪头者,谓之‘食龙头’;有食葱饼者,谓之‘食龙皮’;有食面条者,谓之食‘龙须’。”[20]1561934年《万全县志》载:“二月二日,俗谓之‘龙抬头’,即古俗之所谓中和节。各家皆焚香供神。至本日馔肴,皆以龙字取意,如食水饺者谓之‘食龙耳’;食葱饼者,谓之‘撒龙皮’;食面条者,谓之‘吃龙须’。”[20]207龙神话民俗仪式叙事以饮食习俗为对象,充分体现了神话民俗仪式叙事表现形式生活化的特点。
先秦神话中的官方祭日祭月仪式叙事,至唐代转换为民间拜月拜日民俗仪式叙事,分别形成太阳节与中秋节。唐宋时期,官方祭月活动演变为民间的拜月习俗。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鳌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宵。”[22]明清时期,民间中秋祭月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民俗仪式。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引明代《帝京景物略》描述百姓过中秋节的情形:“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遗相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19]99百姓家中面向月出方向设月光位,即祭台,祭台陈列圆形果饼,瓜必然切成莲花瓣,显然有佛文化因子融入。并在祭台前挂起街市买来的月光纸,即月神神像。上绘有满月像,月中有趺坐莲花上的菩萨,显然是以菩萨来象征月神。与菩萨平起平坐的还有月宫中正在捣不死药的玉兔。人们对着祭台举行祭祀,烧香行跪拜礼,拜完后烧掉月光纸,然后将供品分给家中每一个人。明代民间祭月习俗也有了相应祭祀神像,不像帝王祭祀望月而祀,而是将祭祀神像绘在月光纸上。清代,月光纸又称为“月光马”“月光祃”“兔儿祃”“兔爷祃”,为中秋节祭月所用神像之纸,通常为木刻版水彩印制,上面绘有月神和月宫。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色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19]98月光纸又衍生出儿童玩具“兔儿爷”。中秋节前,街市上就会卖泥巴捏成的兔儿爷玩具,是为民间祭月向娱乐化转变的趋向。
太阳节也形成于唐代。唐贞元五年(789年),德宗采纳大臣李泌的建议,立二月初一为中和节,祭祀太阳神,上行下效,遂成为民众节日。中和节亦称太阳节,俗谓这一天为太阳诞辰,家家户户要在男性家长的带领下向东方太阳神膜拜,并以太阳糕作为祭品。太阳糕一般用糯米加糖制成,上面用红曲水印昂首三足金星君(金鸡)像,或在上面用模具压出“金乌圆光”代表太阳神。太阳糕既是供品,也是应节食品,寓有“太阳高”的意义,深受民众喜爱。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了当时北京过太阳节的情景:“京师于是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门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左安门内有太阳宫,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日。”[19]36《燕京岁时记》也载:“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麦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19]79金鸡是太阳的象征,用作太阳糕图案,说明太阳糕是祭祀太阳神的祭品。山东日照以及云南的彝族、壮族地区都有过太阳节的习俗,虽然节日的日期已向后移动,但仍属同一节日。
古老的神话故事也成为神话节日民俗仪式叙事演绎的对象,如由女娲补天神话衍生出了天穿节,牛郎织女故事衍生出了七夕节。天穿节,时在正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不等,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但多为正月二十日。这一天,家家户户煎面饼为食,并将面饼置于屋顶,谓之补天。此举正是女娲补天神话民俗化的结果。民间用煎饼补天,则是模拟女娲补天的巫术行为,实为祈求风调雨顺。东晋王嘉所撰《拾遗记》中已有天穿节的记载,清《渊鉴类函》卷一三《岁时部》记载:“补天穿。《拾遗记》云:‘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曰补天穿。’相传女娲氏以是日补天故也。”[23]由此可见,至迟在东晋已有补天穿的习俗。晋代以后,天穿节一直延绵不断,至近现代,在有些地方又演化为天仓节等,生活化气息更浓。1944年铅印本《米脂县志》载:“二十日为‘小添仓’,二十五日为‘老添仓’。”[24]天穿节演变为填仓节、添仓节、天仓节,虽然与女娲故事渐行渐远,但其中总是连着一条扯不断的文化之根。
牛郎织女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爱情神话,这一神话与汉代形成的七夕节有着密切的关系。七夕节,又称乞巧节。七夕节的主要民俗是女儿向织女乞巧,似乎与牛郎织女爱情神话故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在节日期间人们总要讲述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故事,所以这一节日又包含了潜在的爱情神话原型。进入当代社会,七夕节在一定的范围内被赋予了情人节仪式的元素,比如相爱的青年男女在这一天相会,潜存的爱情神话原型即上升为显现的爱情神话仪式叙事。
此外,节日民俗仪式叙事涉及的神话还有中秋节的月亮系列神话(包括嫦娥、玉兔、蟾蜍、吴刚、西王母等神话),三月三所涉简狄吞卵生契神话,春节所涉女娲六日造牲畜、一日造人神话,二月二、五月五、六月六、正月十五等有关龙的神话等。这里不再一一分析。众多的神话故事为中国节日民俗仪式叙事增添了浪漫、神秘的色彩。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度,其节日民俗必然打上农业文明的烙印。统摄一年四季农业生产活动的二十四节令,构成中国节日民俗的基本结构。二十四节令是对一年时段的划分,其中包含了春、夏、秋、冬四季神话的原型,属于神话民俗叙事的范畴。农业生产关键性时间节点的仪式是春祈、秋报,祈求和感谢神灵赐给丰收。春祈的祭礼慢慢衍生出了春天的神话节日民俗叙事——春社;秋报的祭礼则衍生出了秋社和春节神话民俗仪式叙事。春社是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时间一般为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分官社和民社。官社庄重肃穆,礼仪繁缛;民社则充满生活气息,乡邻聚集,祭拜土地神,并举行击社鼓、食社饭、饮社酒、观社戏等活动,非常热闹。秋社为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祀土地神以酬报土地神赐给丰收,并欢庆丰收,享受丰收的成果。后来,秋社逐渐式微,其欢庆娱乐的民俗成分逐渐转移至春节。春节一般指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其主题除了除旧迎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主题即欢庆丰收,人们尽情享受一年的劳作成果,而后者正是由秋社移植而来。由上述可见,中国神话仪式叙事成就了中国节日民俗,并建构成为中国节日民俗体系,中国传统节日民俗都可以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并且各种节日因为神话仪式叙事而构成互文性的关系,组成一个难以分割的统一体。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经过巫术仪式叙事到祭礼仪式叙事再到民俗仪式叙事的演变,完成了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社会的进化历程,其间不断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最终以民俗仪式叙事的形态存活于现代社会之中。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人民参与其间,可知可感,喜闻乐见、习惯遵守、自觉传承。神话民俗仪式叙事是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形式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既有深长的文化之根,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而且发挥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深受人们喜爱。